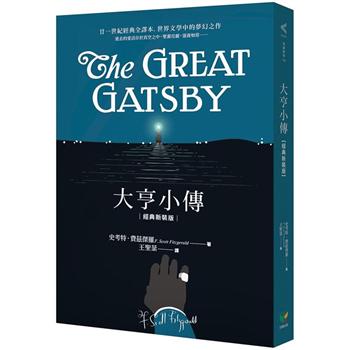第一章(節錄)
在我還少不更事的時候,父親曾送給我一句忠告,直到現在,我仍不斷在心中反覆思索。
「當你想批評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具備你所擁有的條件。」
他沒再多說什麼,不過我們之間的溝通總是默契絕佳,我很清楚他想表達的東西遠超過字面上的意義。因為這句話,使我在判斷所有人事物時都傾向保留,這個習慣讓我認識了許多奇人異士,但也招惹到不少討人厭的傢伙。他們心理雖然不正常,反應卻很敏銳,碰到正常人身上有這種特質立刻就黏上來,這讓我在大學時期被指為政客一名,因為我很清楚那些怪人的祕密傷心事。大多數祕密都沒什麼意思,因為年輕人吐露的私密或者他們用來表達的詞彙都是抄來抄去,而且顯然隱瞞了部分事實,所以只要感覺某人的心事又呼之欲出,我就趕快裝睡,發呆,或是假裝不在乎以惹對方生氣。不妄加評斷他人,是一種無止盡的自我期許。我仍然有點擔心如果忘了那句忠告會錯失些什麼,雖然我父親這麼說顯得有些自以為是,而我也自以為是地重複著他的話,但我們想說的是—基本的道德感是每個人生來就注定了的。
好了,這樣吹噓著自己的寬容大度,我得承認自己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人的外在行為可能建立在堅實的岩石上,也可能建立在濕軟的沼澤裡,一旦包容到某種程度之後,我已經不在乎它們建立在哪了。去年秋天從東岸回來時,我衷心希望這個世界能紀律嚴明,永遠向道德大旗立正致敬。那些自動送上門、混亂又片段的人心之旅我再也不要了。但唯有蓋茲比,也就是本書的主人翁不在此限,儘管他所象徵的一切如此令我由衷輕蔑。如果人的個性是由一連串的成功姿態組成,那麼蓋茲比的確有他神奇之處,他能夠敏銳感應到未來的人生發展,就像一部能記錄萬里之外地震的複雜機器。這種靈敏反應的能力,和那種被所謂「藝術氣息」美化的纖細感受力完全沒關係,而是一種與生俱來、極為少見的樂觀,一種浪漫的積極。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發現過這種特質,看來也不太可能再找到這樣的人。不,蓋茲比臨終時是安詳平和的,令我在意的是困擾著蓋茲比的事,是他幻夢乍醒時飄來的那些個骯髒塵埃,這讓我暫時無暇顧及人世間虛無的憂傷和短暫的歡樂。
我們卡拉威家三代都住在中西部一個城市,生活富裕,聲名卓著,算得上是望族。家族中代代相傳我們是蘇格蘭伯克魯公爵的後裔,但實際上創下這片家業的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來到這裡,弄了個替死鬼去替他打美國內戰,接著開了家五金批發店,並由我父親經營至今。
我從來沒看過這位伯公,但我猜想我們長得很像,尤其是跟懸掛在父親辦公室、一幅表情相當嚴峻的畫像比對之後。一九一五年我從紐哈芬的耶魯大學畢業,距離我父親畢業剛好二十五年。不久之後我參加了那場遲來的日耳曼大遷移,也就是大家通稱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敵人打得落荒而逃還滿有趣的,結果戰爭結束回到家反而平靜不下來。原本,中西部家鄉該是溫暖的世界中心,現在卻像破落的宇宙邊緣。因此我決定前往東岸學學債券業。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走這一行,所以我猜多我這個單身漢應該無妨。所有的叔叔舅舅嬸嬸姑姑為此討論了老半天,好像在幫我選哪一家幼稚園最好,最後終於說「為什麼……好……好吧」,人人臉上的表情既認真又遲疑。父親答應資助我一年的生活費用,後來又有些大小雜事拖延了點時間,最後終於在一九一二年春天來到東岸。不會再回去了吧,我這樣想。
在市區找房子安定下來是很實際的想法,但是那時氣候宜人,而且我才剛離開有著廣大庭院和美麗樹林的故鄉,因此當辦公室裡有個年輕人提議一起在通勤便利的郊區租房子時,這主意聽起來真是太棒了。房子是找到了,一間受盡風吹雨打、紙糊似的平房,一個月只要八十元租金,可是公司又臨時把我同事調到華盛頓,結果我只好自己住到郊區去。我有一隻狗(至少是養了好幾天牠才跑掉)、一部老舊的道奇車,和一個芬蘭籍的女傭人;她會幫我鋪床,煮早餐,還會在電爐前喃喃自語,咕噥著芬蘭的生活智慧。
一剛開始我有點孤單,直到有天早上某個比我晚來這兒幾天的人在路上攔住我。
「西蛋村要怎麼去呢?」他一臉徬徨。
我給他指了路。當我再繼續往前走,孤單的感覺已經離我而去。我儼然成了一個導遊,一個先驅,一個最初的拓荒者。那個問路的人無意間賦予了我在鄰里間通行無阻的自由。
陽光日日潑灑,樹葉從新芽化作一片濃綠,萬物像快轉的電影般迅速生長,我感覺到一股熟悉的信念,我的人生將在這個夏天重新出發。
有很多書要讀是一回事,而且看書還得遠離戶外新鮮空氣,耗費許多寶貴心神。我買了一大堆關於銀行業務、信用貸款和投資理財的書,紅底金字一本本排在書架上閃閃發亮,活像鑄幣廠剛造好的新錢,彷彿從中就能揭露米達斯、摩根和梅賽納斯等人才知道的淘金祕方。此外我還想多看些其他的書。我在大學時代對文學很有興趣,像是有一年我為《耶魯學報》寫了一系列嚴謹而易懂的評論,而現在我要把文學、閱讀等重新帶入生活,再次成為「什麼都懂一點」的專家,那種「萬事通」。但後來我才知道,「心無旁鶩專注於一個領域,人生會更成功」這句話並不只是老生常談。
說起來機緣巧合,我早該在北美洲這個最奇特的地方租房子的。它位於一座細長又喧鬧的島嶼上,這個島朝紐約的正東方延伸出去,島上除了其他天然奇景,還有兩個不尋常的地形—意即,在紐約市二十哩外有兩顆巨大的蛋,形狀一模一樣,有道細長的小海灣將兩者分開。兩顆蛋伸入西半球溫馴平和的大海中,也就是長島海灣附近的海域。它們並非完美的橢圓形,而是像哥倫布的故事裡一端被敲扁地直立著,只不過它們的外形毫無二致肯定會讓飛越其上的海鷗困惑不已。但對於我們這些沒有翅膀的生物來說,除了外型和大小之外,更有趣的一點是,這兩顆蛋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毫無相同之處。
我住在西蛋,就是……呃……比較落後的那顆蛋,用這個說法只能大致形容此地的古怪,以及和東蛋之間的巨大差異。我的房子就在蛋的最頂端,離海灘只有五十碼,左右被兩棟每季租金高達一萬兩千至一萬五千元的大型別墅包夾。在我右手邊這棟不管用什麼標準來看都是氣派豪華的建築,整棟房屋完全依照法國諾曼第某間市政廳風格而興建,側面立著一座塔,嶄新華麗的外觀薄薄披覆了一層常春藤,還有大理石游泳池和占地超過四十畝的庭園。這就是蓋茲比的豪宅。更確切地說,那時我還不認識蓋茲比先生,只知道豪宅在這個人的名下。我的房子則像個刺眼的異物,不過這個異物很小,沒什麼人會注意到,因此從我的房子不但可以看到海,欣賞鄰居家一部份的庭院景色,還能與百萬富翁比鄰而居,真是讓人安慰,而這一切一個月只要八十元。
小灣對岸可以看見,繁榮的東蛋一棟棟純白豪宅沿著海岸線閃閃發亮,而這年夏天的經歷就是從那個傍晚開始—我開車到東蛋和湯姆‧布坎南夫婦吃晚餐。黛西是我的遠房表親,湯姆則是大學時期的朋友。戰後不久,我還到芝加哥叨擾了他們兩天。
黛西的丈夫呢,其他各式各樣的運動成就不說,他是紐哈芬有史以來最厲害的美式足球前鋒,可說是全國皆知的人物,也就是在二十一歲就到達人生巔峰、接下來做每件事只好一直走下坡那種人。他的家族極為富有,即使是大學時期,他手邊能夠花用的錢已經讓人自嘆弗如。現在他離開芝加哥來到東岸,陣仗之大讓人嘖嘖稱奇,比如說,他還從森林湖市帶來一群打馬球專用的馬匹。很難相信,一個和我同輩的人能有錢到這種程度。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來到東岸。他們曾在巴黎待了一年,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接著又蜻蜓點水似地這裡待一陣子,那裡住一會兒,只要哪裡有人打馬球,有錢人聚集在什麼地方,他們就往那裡去。黛西在電話中告訴我,這次是來東岸定居,但是我不相信她的話,因為我看不出她的內心在想什麼。我倒是感覺湯姆會永遠這樣飄蕩下去,尋找他內心的渴望—那些一去不復返的球賽裡激情而喧鬧的歡呼。
所以我就在一個溫暖有風的傍晚,開著車到東蛋去看兩個幾乎認不出來的老朋友。他們的房子是一棟喬治亞殖民時期風格的宅邸,紅磚白櫺的建築俯視著港灣,非常賞心悅目,精心設計的程度超過我的預想。庭院從岸邊開始向屋子大門奔馳,延伸了四分之一哩,躍過日晷、紅磚牆和燦爛盛開的花圃,最後來到屋子前方化為翠綠的藤蔓蜿蜒爬上了側面,彷彿要展現一股奔跑的力量。屋子正前方有一整排落地窗,金色的夕陽映得玻璃閃閃發亮,窗戶大敞迎接這溫暖多風的午後。湯姆‧布坎南一身騎馬裝扮,雙腳大開地站在前廊。
他的模樣已經變了,和以前在紐哈芬時大不相同。現在的他是個體格壯碩、有著稻草色頭髮和一張苛刻嘴巴,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三十來歲男人。一對精光閃閃、不可一世的眼睛在臉上顯得非常醒目,也使他永遠帶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感覺。即使是秀氣亮眼的騎馬套裝也掩蓋不住那副身軀散發出的巨大力量,比如腳上那雙光可鑑人的馬靴,從第一個孔到最後一個孔都繃得實實的;身上那件騎馬專用薄外套底下的肩膀一動,就會有一大塊肌肉跟著牽動。這是一副有著巨大影響力的身軀,一副冷酷無情的身軀。
他說話時聲音高昂中帶著沙啞,更增添他帶給人的易怒印象。他的語氣裡有一種老爸教訓兒子似的輕視,即使是跟他喜歡的人說話也是一樣,在紐哈芬時就有人很痛恨他的蠻橫。
「好了,可別因為我比你壯,比你有男子氣概,就什麼都聽我的。」—這似乎就是他想說的。我們同屬一個高年級社團,雖然並不相熟,但總覺得他很認同我,並且是以一種嚴厲挑釁的態度來表現自己的渴望,想讓我對他有好感。
我們在陽光西曬的長廊上聊了幾分鐘。
「我這個地方真不錯。」他說話的時候眼睛眨個不停。
他扶著我的手臂轉過我的身子,並且伸出一隻寬大的手在我前方的景色指了指,被他手指掃過的包括一個義大利式的低窪花園,一方占了半畝地、芳香濃郁的玫瑰花圃,以及一艘隨著波浪不斷沖撞岸邊的扁鼻汽艇。
「這些原本都是石油大亨迪緬因的。」他又把我轉過來,禮貌中帶著莽撞,「我們進去吧。」
我們走過一道挑高的玄關,來到一個明亮、充滿玫瑰色的地方,兩端以落地窗區隔,精巧地鑲在屋子當中。微微敞開的窗戶閃動著白光,外頭鮮綠的草地像是要漫進屋子裡。一陣微風穿過房間,吹得一頭的窗簾向屋內飄動,另一頭向屋外搖曳,彷彿朝糖霜結婚蛋糕似的天花板飾條扭絞著蒼白的旗幟,又於酒紅色的地毯上留下片片漣漪,像海風在水面上灑下的影子。
房間裡唯一靜止不動的東西是一張巨大沙發,兩個年輕的女人置身其中,就像坐在被拴住的熱氣球裡。她們倆都一身白,衣服被風吹得翩翩擺動,好像才剛在屋子周圍短短繞了一圈又回到這裡。我一定是站了好一會兒,只顧著聽窗簾拍打捲動的聲音和牆上畫像的喟嘆。突然一聲巨響傳來,原來是湯姆‧布坎南關上了後面的落地窗,屋子裡流動的風沉寂下來,讓浮在空中的窗簾和地毯,還有兩位年輕的女士都一起飄然降落。
年紀小一點的那位女士我不認識。她四肢伸得筆直躺在沙發一端,完全靜止不動;下巴微微上揚,像在撐住某個很容易掉下來的東西。我不知道她的眼角餘光有沒有瞄到我,因為從她的眼神完全看不出來;說實話,我差點嚇得想小聲為自己貿然進來打擾到她而道歉。
另外一個就是黛西,她作勢起身,身體微微向前,表情正經八百;接著她笑出聲,一個忍俊不住,風情萬種的輕笑,我也報以微笑走進了房間。
「我開心得整……整個人都軟了。」
她又笑了起來,好像她剛剛說的話很幽默機智;隨即她深深握住我的手,仰起臉龐專注地看著我,表現出這個世界上彷彿她最想見到的人就是我。黛西總是來這招。她輕聲暗示,旁邊那位正在玩平衡遊戲的女孩,姓貝克。(我聽說,黛西之所以輕聲細語只是為了讓人靠近她,但這種無關緊要的批評絲毫無損她的迷人。)
在我還少不更事的時候,父親曾送給我一句忠告,直到現在,我仍不斷在心中反覆思索。
「當你想批評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具備你所擁有的條件。」
他沒再多說什麼,不過我們之間的溝通總是默契絕佳,我很清楚他想表達的東西遠超過字面上的意義。因為這句話,使我在判斷所有人事物時都傾向保留,這個習慣讓我認識了許多奇人異士,但也招惹到不少討人厭的傢伙。他們心理雖然不正常,反應卻很敏銳,碰到正常人身上有這種特質立刻就黏上來,這讓我在大學時期被指為政客一名,因為我很清楚那些怪人的祕密傷心事。大多數祕密都沒什麼意思,因為年輕人吐露的私密或者他們用來表達的詞彙都是抄來抄去,而且顯然隱瞞了部分事實,所以只要感覺某人的心事又呼之欲出,我就趕快裝睡,發呆,或是假裝不在乎以惹對方生氣。不妄加評斷他人,是一種無止盡的自我期許。我仍然有點擔心如果忘了那句忠告會錯失些什麼,雖然我父親這麼說顯得有些自以為是,而我也自以為是地重複著他的話,但我們想說的是—基本的道德感是每個人生來就注定了的。
好了,這樣吹噓著自己的寬容大度,我得承認自己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人的外在行為可能建立在堅實的岩石上,也可能建立在濕軟的沼澤裡,一旦包容到某種程度之後,我已經不在乎它們建立在哪了。去年秋天從東岸回來時,我衷心希望這個世界能紀律嚴明,永遠向道德大旗立正致敬。那些自動送上門、混亂又片段的人心之旅我再也不要了。但唯有蓋茲比,也就是本書的主人翁不在此限,儘管他所象徵的一切如此令我由衷輕蔑。如果人的個性是由一連串的成功姿態組成,那麼蓋茲比的確有他神奇之處,他能夠敏銳感應到未來的人生發展,就像一部能記錄萬里之外地震的複雜機器。這種靈敏反應的能力,和那種被所謂「藝術氣息」美化的纖細感受力完全沒關係,而是一種與生俱來、極為少見的樂觀,一種浪漫的積極。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發現過這種特質,看來也不太可能再找到這樣的人。不,蓋茲比臨終時是安詳平和的,令我在意的是困擾著蓋茲比的事,是他幻夢乍醒時飄來的那些個骯髒塵埃,這讓我暫時無暇顧及人世間虛無的憂傷和短暫的歡樂。
我們卡拉威家三代都住在中西部一個城市,生活富裕,聲名卓著,算得上是望族。家族中代代相傳我們是蘇格蘭伯克魯公爵的後裔,但實際上創下這片家業的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來到這裡,弄了個替死鬼去替他打美國內戰,接著開了家五金批發店,並由我父親經營至今。
我從來沒看過這位伯公,但我猜想我們長得很像,尤其是跟懸掛在父親辦公室、一幅表情相當嚴峻的畫像比對之後。一九一五年我從紐哈芬的耶魯大學畢業,距離我父親畢業剛好二十五年。不久之後我參加了那場遲來的日耳曼大遷移,也就是大家通稱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敵人打得落荒而逃還滿有趣的,結果戰爭結束回到家反而平靜不下來。原本,中西部家鄉該是溫暖的世界中心,現在卻像破落的宇宙邊緣。因此我決定前往東岸學學債券業。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走這一行,所以我猜多我這個單身漢應該無妨。所有的叔叔舅舅嬸嬸姑姑為此討論了老半天,好像在幫我選哪一家幼稚園最好,最後終於說「為什麼……好……好吧」,人人臉上的表情既認真又遲疑。父親答應資助我一年的生活費用,後來又有些大小雜事拖延了點時間,最後終於在一九一二年春天來到東岸。不會再回去了吧,我這樣想。
在市區找房子安定下來是很實際的想法,但是那時氣候宜人,而且我才剛離開有著廣大庭院和美麗樹林的故鄉,因此當辦公室裡有個年輕人提議一起在通勤便利的郊區租房子時,這主意聽起來真是太棒了。房子是找到了,一間受盡風吹雨打、紙糊似的平房,一個月只要八十元租金,可是公司又臨時把我同事調到華盛頓,結果我只好自己住到郊區去。我有一隻狗(至少是養了好幾天牠才跑掉)、一部老舊的道奇車,和一個芬蘭籍的女傭人;她會幫我鋪床,煮早餐,還會在電爐前喃喃自語,咕噥著芬蘭的生活智慧。
一剛開始我有點孤單,直到有天早上某個比我晚來這兒幾天的人在路上攔住我。
「西蛋村要怎麼去呢?」他一臉徬徨。
我給他指了路。當我再繼續往前走,孤單的感覺已經離我而去。我儼然成了一個導遊,一個先驅,一個最初的拓荒者。那個問路的人無意間賦予了我在鄰里間通行無阻的自由。
陽光日日潑灑,樹葉從新芽化作一片濃綠,萬物像快轉的電影般迅速生長,我感覺到一股熟悉的信念,我的人生將在這個夏天重新出發。
有很多書要讀是一回事,而且看書還得遠離戶外新鮮空氣,耗費許多寶貴心神。我買了一大堆關於銀行業務、信用貸款和投資理財的書,紅底金字一本本排在書架上閃閃發亮,活像鑄幣廠剛造好的新錢,彷彿從中就能揭露米達斯、摩根和梅賽納斯等人才知道的淘金祕方。此外我還想多看些其他的書。我在大學時代對文學很有興趣,像是有一年我為《耶魯學報》寫了一系列嚴謹而易懂的評論,而現在我要把文學、閱讀等重新帶入生活,再次成為「什麼都懂一點」的專家,那種「萬事通」。但後來我才知道,「心無旁鶩專注於一個領域,人生會更成功」這句話並不只是老生常談。
說起來機緣巧合,我早該在北美洲這個最奇特的地方租房子的。它位於一座細長又喧鬧的島嶼上,這個島朝紐約的正東方延伸出去,島上除了其他天然奇景,還有兩個不尋常的地形—意即,在紐約市二十哩外有兩顆巨大的蛋,形狀一模一樣,有道細長的小海灣將兩者分開。兩顆蛋伸入西半球溫馴平和的大海中,也就是長島海灣附近的海域。它們並非完美的橢圓形,而是像哥倫布的故事裡一端被敲扁地直立著,只不過它們的外形毫無二致肯定會讓飛越其上的海鷗困惑不已。但對於我們這些沒有翅膀的生物來說,除了外型和大小之外,更有趣的一點是,這兩顆蛋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毫無相同之處。
我住在西蛋,就是……呃……比較落後的那顆蛋,用這個說法只能大致形容此地的古怪,以及和東蛋之間的巨大差異。我的房子就在蛋的最頂端,離海灘只有五十碼,左右被兩棟每季租金高達一萬兩千至一萬五千元的大型別墅包夾。在我右手邊這棟不管用什麼標準來看都是氣派豪華的建築,整棟房屋完全依照法國諾曼第某間市政廳風格而興建,側面立著一座塔,嶄新華麗的外觀薄薄披覆了一層常春藤,還有大理石游泳池和占地超過四十畝的庭園。這就是蓋茲比的豪宅。更確切地說,那時我還不認識蓋茲比先生,只知道豪宅在這個人的名下。我的房子則像個刺眼的異物,不過這個異物很小,沒什麼人會注意到,因此從我的房子不但可以看到海,欣賞鄰居家一部份的庭院景色,還能與百萬富翁比鄰而居,真是讓人安慰,而這一切一個月只要八十元。
小灣對岸可以看見,繁榮的東蛋一棟棟純白豪宅沿著海岸線閃閃發亮,而這年夏天的經歷就是從那個傍晚開始—我開車到東蛋和湯姆‧布坎南夫婦吃晚餐。黛西是我的遠房表親,湯姆則是大學時期的朋友。戰後不久,我還到芝加哥叨擾了他們兩天。
黛西的丈夫呢,其他各式各樣的運動成就不說,他是紐哈芬有史以來最厲害的美式足球前鋒,可說是全國皆知的人物,也就是在二十一歲就到達人生巔峰、接下來做每件事只好一直走下坡那種人。他的家族極為富有,即使是大學時期,他手邊能夠花用的錢已經讓人自嘆弗如。現在他離開芝加哥來到東岸,陣仗之大讓人嘖嘖稱奇,比如說,他還從森林湖市帶來一群打馬球專用的馬匹。很難相信,一個和我同輩的人能有錢到這種程度。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來到東岸。他們曾在巴黎待了一年,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接著又蜻蜓點水似地這裡待一陣子,那裡住一會兒,只要哪裡有人打馬球,有錢人聚集在什麼地方,他們就往那裡去。黛西在電話中告訴我,這次是來東岸定居,但是我不相信她的話,因為我看不出她的內心在想什麼。我倒是感覺湯姆會永遠這樣飄蕩下去,尋找他內心的渴望—那些一去不復返的球賽裡激情而喧鬧的歡呼。
所以我就在一個溫暖有風的傍晚,開著車到東蛋去看兩個幾乎認不出來的老朋友。他們的房子是一棟喬治亞殖民時期風格的宅邸,紅磚白櫺的建築俯視著港灣,非常賞心悅目,精心設計的程度超過我的預想。庭院從岸邊開始向屋子大門奔馳,延伸了四分之一哩,躍過日晷、紅磚牆和燦爛盛開的花圃,最後來到屋子前方化為翠綠的藤蔓蜿蜒爬上了側面,彷彿要展現一股奔跑的力量。屋子正前方有一整排落地窗,金色的夕陽映得玻璃閃閃發亮,窗戶大敞迎接這溫暖多風的午後。湯姆‧布坎南一身騎馬裝扮,雙腳大開地站在前廊。
他的模樣已經變了,和以前在紐哈芬時大不相同。現在的他是個體格壯碩、有著稻草色頭髮和一張苛刻嘴巴,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三十來歲男人。一對精光閃閃、不可一世的眼睛在臉上顯得非常醒目,也使他永遠帶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感覺。即使是秀氣亮眼的騎馬套裝也掩蓋不住那副身軀散發出的巨大力量,比如腳上那雙光可鑑人的馬靴,從第一個孔到最後一個孔都繃得實實的;身上那件騎馬專用薄外套底下的肩膀一動,就會有一大塊肌肉跟著牽動。這是一副有著巨大影響力的身軀,一副冷酷無情的身軀。
他說話時聲音高昂中帶著沙啞,更增添他帶給人的易怒印象。他的語氣裡有一種老爸教訓兒子似的輕視,即使是跟他喜歡的人說話也是一樣,在紐哈芬時就有人很痛恨他的蠻橫。
「好了,可別因為我比你壯,比你有男子氣概,就什麼都聽我的。」—這似乎就是他想說的。我們同屬一個高年級社團,雖然並不相熟,但總覺得他很認同我,並且是以一種嚴厲挑釁的態度來表現自己的渴望,想讓我對他有好感。
我們在陽光西曬的長廊上聊了幾分鐘。
「我這個地方真不錯。」他說話的時候眼睛眨個不停。
他扶著我的手臂轉過我的身子,並且伸出一隻寬大的手在我前方的景色指了指,被他手指掃過的包括一個義大利式的低窪花園,一方占了半畝地、芳香濃郁的玫瑰花圃,以及一艘隨著波浪不斷沖撞岸邊的扁鼻汽艇。
「這些原本都是石油大亨迪緬因的。」他又把我轉過來,禮貌中帶著莽撞,「我們進去吧。」
我們走過一道挑高的玄關,來到一個明亮、充滿玫瑰色的地方,兩端以落地窗區隔,精巧地鑲在屋子當中。微微敞開的窗戶閃動著白光,外頭鮮綠的草地像是要漫進屋子裡。一陣微風穿過房間,吹得一頭的窗簾向屋內飄動,另一頭向屋外搖曳,彷彿朝糖霜結婚蛋糕似的天花板飾條扭絞著蒼白的旗幟,又於酒紅色的地毯上留下片片漣漪,像海風在水面上灑下的影子。
房間裡唯一靜止不動的東西是一張巨大沙發,兩個年輕的女人置身其中,就像坐在被拴住的熱氣球裡。她們倆都一身白,衣服被風吹得翩翩擺動,好像才剛在屋子周圍短短繞了一圈又回到這裡。我一定是站了好一會兒,只顧著聽窗簾拍打捲動的聲音和牆上畫像的喟嘆。突然一聲巨響傳來,原來是湯姆‧布坎南關上了後面的落地窗,屋子裡流動的風沉寂下來,讓浮在空中的窗簾和地毯,還有兩位年輕的女士都一起飄然降落。
年紀小一點的那位女士我不認識。她四肢伸得筆直躺在沙發一端,完全靜止不動;下巴微微上揚,像在撐住某個很容易掉下來的東西。我不知道她的眼角餘光有沒有瞄到我,因為從她的眼神完全看不出來;說實話,我差點嚇得想小聲為自己貿然進來打擾到她而道歉。
另外一個就是黛西,她作勢起身,身體微微向前,表情正經八百;接著她笑出聲,一個忍俊不住,風情萬種的輕笑,我也報以微笑走進了房間。
「我開心得整……整個人都軟了。」
她又笑了起來,好像她剛剛說的話很幽默機智;隨即她深深握住我的手,仰起臉龐專注地看著我,表現出這個世界上彷彿她最想見到的人就是我。黛西總是來這招。她輕聲暗示,旁邊那位正在玩平衡遊戲的女孩,姓貝克。(我聽說,黛西之所以輕聲細語只是為了讓人靠近她,但這種無關緊要的批評絲毫無損她的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