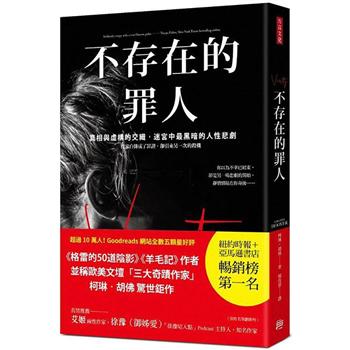C h a p t e r 6 該死的雙胞胎
薇若蒂書房的優點是後院景色透過窗戶一覽無遺,頂天立地的玻璃窗上沒有半點遮擋,全是厚實的玻璃。誰負責打掃?我往玻璃上尋找污垢、髒污什麼都好。
但良好的視野同時也是缺點,看護把薇若蒂的輪椅停在屋後門廊上,正對著書房,她面對西側,側臉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今天天氣適合外出,看護面對薇若蒂唸書給她聽。薇若蒂凝望半空中,她能理解任何事物嗎?能理解到什麼程度?
微風吹起她的金髮,宛如伸手把玩一縷縷髮絲的幽魂。
看著她,我就無法壓抑膨脹的同情心,這是不想看到她的原因,可是這片窗戶粉碎了我的希望。我聽不見看護的聲音,可能這片窗戶跟書房的牆面門板一樣隔音效果極佳吧,但我知道她們就在眼前,實在是難以抵擋每隔幾分鐘就抬頭偷看的衝動。
我實在是找不到跟系列作有關的筆記,不過我才搜了一小塊範圍。我想今天早上還是先把第一集跟第二集迅速翻一遍,針對每一個角色做紀錄。我自己編了一套建檔系統,因為必須跟薇若蒂一樣了解這些角色,我必須知道他們的動機、情緒的臨界點、弱點。
我注意到窗外有動靜,抬起頭發現看護離開薇若蒂,走向後門。我凝視薇若蒂好一會,沒有人替她唸書,不知道她會不會有任何反應。什麼都沒有,她雙手擱在膝上,腦袋歪向一邊,彷彿她的大腦無法傳送信號,讓她知道該挺直身子,不然會害自己脖子痠痛。
天賦異稟的薇若蒂已經不復存在,她的身體是那場車禍中唯一的倖存者嗎?她就像是一顆蛋,被人敲開倒出蛋白蛋黃,只剩硬殼的碎片。
視線移回桌面,努力集中精神,我忍不住納悶傑洛米究竟是如何面對這一切,他這個人外表架起鋼筋水泥,但內在肯定空無一物。知道自己的人生只能這麼過下去,自己只是在照顧一個空蛋殼,實在是太空虛了。
這個想法太過分了。
不是故意要這麼尖酸,只是⋯⋯我也不知道。我覺得要是她在車禍中喪命,大家都會好過許多,下一秒又為這個想法深感愧疚,我想起照顧母親的最後幾個月,知道母親寧可死掉,也不要忍受癌症帶來的重重枷鎖,然而那只是她和我人生的短短幾個月。傑洛米下半輩子全賠在上頭了,照顧空有軀殼的妻子,遭到不再是家的屋子束縛。我無法想像薇若蒂會希望他如此度日,也無法想像薇若蒂會希望自己如此度日,她甚至無法跟自己的孩子玩耍說話。
真希望她已經離去了,這是為了她好,倘若她的意識還在,卻因為腦部損傷太重,使得她無法以肉身傳達內心話。奪走她反應、互動、說出想法的能力,我不敢想像這是多麼痛苦的處境。
我再次抬頭。
她正直直盯著我。
我跳起來,辦公椅往後滑過木頭地板。薇若蒂隔著窗戶直視我,她的腦袋轉向書房,雙眼鎖住我的視線,我掩嘴後退,彷彿受到威脅。
我想離開她的目光,悄悄退向左側的房門。我實在是逃不開,她是蒙娜麗莎,眼神追著我跑,不過等我移到門邊時,我們的視線斷了線。
她的眼睛沒有跟著我移動。
我垂手靠上牆面,看艾普洛拿了條毛巾回到後門門廊,她替薇若蒂擦擦下巴,從她大腿上拿起個小枕頭,扶起她的腦袋,枕頭塞在她的肩膀跟臉頰間。調整過頭部角度後,她不再直視書房。
「媽的。」我低聲咒罵。
我竟然會怕這個幾乎無法動彈、連話都說不出來的女人,這個女人不可能靠著自己的意志轉頭看人,更別說是刻意與我互望了。
我要喝水。
在打開房門的一瞬間,背後書桌上的手機突然響起,我忍不住尖叫。
該死。我恨腎上腺素。脈搏加速,我呼出一大口氣,在接起電話前逼自己冷靜,是陌生的號碼。
「哈囉?」
「艾許雷女士?」
「我是。」
「我是克里伍公寓的多諾文.貝克,妳是否幾天前提出租屋申請?」
太好了,有別的事情分散注意。我回到窗邊,看護移動過薇若蒂的輪椅,我只看得到她的後腦杓。「是的,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今天我們處理到妳的申請書,可惜妳名下最近有一個強制遷離紀錄,因此無法核准妳的申請。」
已經?我兩天前才搬出來。「可是你們不是已經核准我的申請了嗎?我預計下禮拜搬進去耶。」
「事實上,妳的申請只有通過預審,程序到今天才跑完。我們無法核准近期有強制遷離紀錄的申請人,希望妳能理解。」
我捏捏後頸,還要兩個禮拜才拿得到稿費。「拜託,」我試著不讓洩氣的心情反映在語氣上:「我從來沒有拖過房租,這是第一次。我剛找到新工作,如果你們現在讓我搬進去,再兩個禮拜就可以付一整年的房租,我發誓。」
「妳隨時可以提出訴願,可能要多花幾個禮拜,不過某些申請人仔細說明他們的狀況,最後也是通過了。」
「沒辦法再等幾個禮拜,我已經搬出原本的公寓了。」
「我很遺憾,」他說:「我再把審核結果用電子郵件寄給妳,妳可以撥打信件結尾的電話號碼提出訴願。艾許雷女士,祝妳一切順利。」
他掛斷電話,但我繼續把手機按在耳邊,另一手揉捏後頸,真想馬上從這場惡夢中清醒過來。老媽,真是多謝了,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有人輕輕敲響房門,我猛然轉身,又被嚇了一跳,真是夠了。傑洛米站在書房門外,一臉同情地看著我。
手機響起時我沒有關門,他大概聽見整段通話了,我要把「驚慌失措」加進今天適用的形容詞清單。
我把手機放到薇若蒂的書桌上,坐進她的辦公椅:「我的生活其實不是一直這麼慘。」
他輕笑一聲,踏進房裡:「我也是。」
說得好。我低頭盯著手機。「沒事的,」我推著手機在桌上旋轉:「我再想想辦法。」
「在妳從經紀人手上拿到稿費前,我可以借妳錢,從我們的共用基金提領,不過要三天後才可以拿到。」
我這輩子沒有如此窩囊過,相信他全看在眼裡,我往後靠上書桌雙手掩面,整個人縮起來。
「你人真好,可是我不會跟你借錢。」
他沉默半晌,坐上沙發,姿勢隨興,上身前傾雙手在身前交握:「不然就在這裡待到預付款匯入妳的帳戶再說,應該只要一兩個禮拜吧。」他環顧書房,看出我從昨天到現在的進度是多麼的緩慢。「我們一點都不介意,妳完全沒有打擾到我們。」
我搖搖頭,但他硬是接著說下去。
「洛玟,接下的這份工作不簡單,我寧願妳在這裡多花時間準備,而不是明天回到紐約,卻發現少拿了什麼資料。」
我確實需要更多時間,可是在這棟屋子裡待上兩個禮拜?陪著把我嚇得六神無主的女人,陪著我不該看的草稿,陪著我太過了解的男人?
不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對。
我又搖起頭,可是他揚手制止我的拒絕:「別跟我們客氣。也不要這麼難為情。只要一句『好吧』。」
我的視線越過他,飄向他背後牆邊的紙箱那些還沒觸碰到的事物,然後我想:過了兩個禮拜,或許我有辦法看完她的作品,抄好筆記,寫出接下來三本新書的大綱。
我嘆息,不願承認自己感到些許慶幸。「好吧。」他笑了笑,起身,走向門外。
「謝謝。」我說。
傑洛米轉身對著我。真不該引他回頭。我清楚看見他臉上細微的懊悔,他張嘴似乎是打算說「不客氣」或是「小事一樁」,但他只是閉上嘴巴,擠出微笑,關門離開。
下午,傑洛米說我應該在太陽下山前到外頭走走:「妳就能理解薇若蒂要求書房裝上大片玻璃的原因。」
我帶上一本她的作品,準備坐在屋後門廊看,外頭擺了十張椅子,我選了圓桌旁的位置。傑洛米跟克魯在湖邊拆除釣魚平台的老舊木板,克魯從傑洛米手中接過木板的動作可愛極了,他把廢木料堆在一起,再從爸爸手中拿來一片。來回有一段距離,傑洛米從支架拆下木板的速度快得多了,他每次都要等上幾分鐘,這樣的舉動證明他是個充滿耐心的父親。
他讓我想起父親,他在我九歲那年過世,我似乎從沒看過他發怒,即使是面對母親尖銳的批評、不斷沸騰的脾氣,但我後來越來越怨恨他,有時候覺得他在母親面前的耐性跟軟弱沒有兩樣。
我斷斷續續地翻書,又看了那對父子好一會,實在是難以專心,因為傑洛米在幾分鐘前脫下上衣,儘管我看過他脫衣服,但那時他還穿著汗衫。他已經在湖邊勞動了兩個小時了,身上佈滿瑩亮的汗珠,他用鎚子後側撬起木板時,背肌伸展又收縮。我立刻聯想到先前在薇若蒂自傳看過的章節,裡頭滿是他們性生活的火辣細節,根據她的文字這對夫妻發生關係的頻率很高,遠遠超越我歷任男友。
現在看著他,很難不去想到做愛,並不是說我想跟他上床,也不是說我不想,身為作家,我知道他是薇若蒂書中幾個男性角色的靈感來源。因此我在想是否要從他身上獲得接下來三本小說的啟發,被迫站在薇若蒂的角度,在接下來二十四個月的寫作期間,把傑洛米的形象套入小說裡面⋯⋯其實沒有那麼糟。
後門砰地關上,我依依不捨地放下傑洛米,轉頭發現艾普洛站在門外盯著我看,她順著我方才的視線看過去,又回到我身上。她看到了,看到我在偷窺新老闆。可悲的傢伙。
她監視我多久了?真想拿書遮住臉,但我裝作若無其事地勾起嘴角。我又沒有做錯什麼,其實也不用裝。
「我要走了,」艾普洛說:「已經送薇若蒂躺回床上,幫她開電視,如果他問起的話,就說她晚餐跟藥都吃了。」
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我明明就跟這件事無關:「好,晚安。」
她沒有回我晚安,逕自回到屋內,任由後門猛然關起。過了一分鐘,我聽見她車子沿著車道離開的引擎聲消失在樹林間,我回頭望向傑洛米跟克魯,傑洛米又扯下一片木板。
克魯站在廢木料堆旁凝視我,他對我揮手微笑,我揚手打招呼,卻又屈起手指,因為我發現他的善意並不是衝著我來,他看著我的右上方。
他在仰望薇若蒂的臥室窗戶。
我轉過身抬起頭,剛好看到她房間的窗簾掩上。我失手把書摔落到桌上,撞倒水瓶。我起身後退三步,想找個更清楚的角度,可惜窗邊沒有半個人。我瞠目結舌,回頭望向克魯,但他已經轉身走向平台,接下另一片木板。
我看到了。
可是他幹嘛對著她的窗戶揮手?如果說她不在窗邊,他為什麼要揮手?
一點都不合理,她車禍後就無法言語或是行走,假如她從房裡往外看,克魯肯定會有更大的反應。
或是說他不知道除非奇蹟發生,否則他母親絕對無法自己走到窗邊,他才五歲。
我低頭看了看滲到水的小說,拎起來甩水,顫抖著吐氣,這一整天總是膽顫心驚的。稍早誤以為她盯著我看的那時,我一定是受到不小的震撼,所以剛剛才會以為窗簾動了。
我想忘記整件事,關在書房裡徹夜工作,但同時我也知道若是不去看看她,確認自己沒看到那些幻覺,是絕對無法安心的。
我把書本放在圓桌上晾乾,回到屋裡很安靜地走向樓梯,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鬼鬼祟祟的。她對外界的感知應該不太敏銳,就算我吵吵鬧鬧的上樓又有何妨?即便如此,我還是輕輕踏上樓梯,沿著走廊來到她臥室門外。
門板微微開啟,可以看見面對後院的窗戶,我按住房門輕輕一推,咬住下唇把腦袋探進去。
薇若蒂躺在床上,閉著眼睛,雙手擱在兩側壓在毯子上。
我輕輕鬆了口氣,把門推得更開,發現有個電風扇在薇若蒂的病床跟窗戶間轉動,每回轉向窗戶時就會吹動窗簾,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我用力吐氣,不過是個該死的電風扇。洛玟,振作點。
房裡溫度有點低,我關掉風扇,沒想到艾普洛離開前沒有關好,我再次偷瞄薇若蒂,她還是沒醒。回到門邊時,我一愣地望向梳妝台──看著擱在上頭的遙控器,再轉頭看著固定在牆上的電視螢幕。
電源沒開。
艾普洛說她離開前開了電視,可是電視沒開。
我不敢多看薇若蒂一眼,關上房門衝下樓。
我不會再上二樓了,我只是在自己嚇自己,這棟屋子裡最無助的人卻是我最大的恐懼來源,說出來肯定不會有人信。她沒有從屋外看著書房裡的我;她沒有站在窗邊,看著克魯,她沒有關掉房裡的電視,大概是設了定時關機吧,不然就是艾普洛不小心按了兩次電源,以為自己開了電視。
我很清楚都是自己在胡思亂想,但我仍舊回到薇若蒂的書房,關上門,拎起自傳的下一個章節,說不定多看點她的自述,可以讓我相信她毫無害處,而且我得要冷靜下來。
第三章
我知道自己懷孕,是因為自己的胸部從未顯得如此出色。
我十分照顧自己的身體狀況,吃了什麼,怎樣保養,怎樣維持體態。隨著長大,看著我媽的腰線在懶散下日益粗壯,我每天健身,有時一天兩次。
我很早就學到,人不僅僅是單一構造物,人這東西是合二為一的。
我們有意識的構成面,包含神智、心靈和所有無形部分。
我們還有物質的構成面,這是意識賴以為生的「機器」。
要是弄壞機器,你就會死;要是輕忽機器,你就會死;要是以為意識能比機器長命,明白自己錯了之後很快就會死。
這很簡單,真的。照顧好自己的物質層面,攝取物質層面所需,而不是吃意識層面想吃的。任心中渴望予取予求,最終就會傷了身體,像軟弱的父母對自己小孩沒輒:「噢,你今天很不開心?想吃一整盒餅乾?好吧,寶貝。吃吧,順便拿這瓶汽水來配。」
照顧自己身體和照顧小孩沒什麼兩樣,有時很不容易,有時很討人厭,有時讓人只想放棄,但如果真這麼做,接下來的十八年就得後果自負。
這適用在我媽身上,她照料自己身材就跟照料我一樣,少得可憐。有時我猜想她是否依舊那麼胖─要是她仍輕忽自己的機器,我不會知道,我很多年沒跟她講過話了。
但我沒興趣談論一個選擇再也不跟我說話的女人,我要談的是我的寶寶從我這裡最先偷走了什麼。
傑洛米。
一開始我沒察覺遭竊。
起初,在我們發覺訂婚夜成了有喜之夜後,我其實很開心,我開心是因為傑洛米開心,在那時除了胸部看起來更出色,我還不明瞭懷孕會對自己奮力維護的機器造成多大不利。
大概是在第三個月,發現懷孕後過了幾週,我開始留意到變化,那只是一小塊肚子贅肉,但確實存在。我才剛淋浴完,站在鏡子前注視自己的側面,我的手攤在肚子上,我感覺到異物,腹部微微凸起。
我覺得好討厭,發誓要開始一天健身三次。我見過懷孕的女人會變怎樣,並也知道多半都是在第三孕期最受影響,要是我能設法提早生產︙︙也許在三十三週或三十四週,就可以閃避孕期最不利的那段時間。醫療照護已經那麼先進,那週數的早產寶寶幾乎都不會有事。
「哇。」
我放開手望向門口,傑洛米倚著門雙手抱胸,他對我笑:「開始看得出妳懷孕了。」
「才沒有。」我縮了縮小腹。
他笑著拉近我倆的距離,從背後抱住我,把雙手放在我肚子上,望著鏡中的我並吻了吻我肩頭:「妳從沒這麼漂亮過。」
這是讓我心裡好受一點的假話,但我很感激,連他的謊言都有意義。我捏捏他的手,他讓我轉身面對面,接著吻我,帶著我往後退直到抵著洗手檯,讓我坐在檯面上,然後站在我雙腿間。
他衣衫楚楚,才剛下班,我全身赤裸,剛洗完澡,我們之間只隔著他的褲子,和我試著縮回去的贅肉。
他開始在洗手檯跟我做愛,但最後還是回到床上。
他的頭靠在我胸口,在我發出如雷腹鳴的肚皮劃圈圈,我試著咳幾聲來掩蓋,但他大笑:「有人餓了。」
我剛搖頭,他就從我胸口抬起頭看我:「她想要什麼?」
「沒有,我不餓。」
他又笑了。「不是說妳。是她,」他拍拍我的肚子:「女人一懷孕不都會因為寶寶就
突然很餓一直吃嗎?妳沒吃多少,可是妳的肚子在咕咕叫,」他坐起身:「我得餵飽我的女孩們。」
他的女孩們。
「還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
他對我微笑:「是女孩,我有預感。」
我想翻白眼,因為嚴格來講那還啥都不是,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就只是一團肉。我的週數還沒那麼大,肚子裡的東西會餓會想吃特定食物,這種假設實在可笑,但很難跟傑洛米講明這點,因為他那麼欣喜若狂,他的煞有其事我沒放在心上。
有時他的興奮,讓我興奮。
接下來的幾週,他的激動之情幫助我適應,肚子愈大他就愈殷勤,我們晚上躺在床上時,他越來越常親我肚子。
早上孕吐的時候,他會幫我撈住頭髮,他上班時會傳訊息分享寶寶的候選名字,他對我的懷孕著了迷,一如我對他著了迷。去婦產科初診那次,他陪我去。
我很慶幸第二次回診他也陪我去,因為那天起我的世界天翻地覆。
是雙胞胎。
有兩個。
那天我們走出診所時,我很沉默。當一個孩子的媽已經讓我很害怕了,被迫去愛一個傑洛米更愛的東西,而當知道有兩個寶寶,而且是女孩,成為傑洛米人生的第三順位突然讓我接受不了。
他對寶寶們說話的時候,我勉強自己微笑;他摩挲我肚皮時,我會表現得滿心喜悅,但其實厭惡不已,因為他這麼做只為了她們。就算能提早生產也沒用,現在有了兩個寶寶,我的身體會承受更多損害。每天想到她們在我身體裡一起長大,我就發抖,她們撐開我的皮,毀了胸部,毀了腹部,毀了每晚傑洛米都會朝聖的雙腿之際。
在這之後傑洛米怎麼還會想要我?
在懷孕第四個月期間,我開始希望流產,上廁所都祈求能見血,我能想像在失去雙胞胎後,傑洛米會如何重新把我放回第一順位。他會寵溺我、愛慕我、照顧我、擔心我,不再因為長在我肚裡的東西才這麼做。
他沒注意的時候,我吃安眠藥;他不在場的時候,我喝酒,我試遍一切想摧毀令他疏遠我的東西,但絲毫不管用。她們一直長大,我的肚皮持續擴張。
在第五個月,我們兩個都側躺在床上,傑洛米用背後位跟我做愛,他的左手握著我胸乳,右手擱在我肚皮上。我不喜歡他在上床時碰肚子,這會讓我想到寶寶,失了性致。
他停止挺動時,我還以為他射了,但很快察覺他不再動作是因為他感覺到她們動了。他整根拔出來,讓我轉身仰躺,把手心貼在我肚皮上。
「妳有沒有感覺到?」他的眼神狂喜亂舞,他軟了,興奮的原因與我無關。他把耳朵貼到我肚皮上,等待她們哪個再動一動。
「傑洛米?」我悄聲問。
他親吻我肚皮,仰頭看我。
我伸手用手指梳他頭髮:「你愛她們嗎?」
他微笑,因為他以為我要他給出肯定答覆:「我愛她們勝過一切。」
「包括我?」
他不再微笑,手仍放在肚皮上,但整個人往上挪,把手臂枕在我頸下:「是不一樣的
愛。」他親吻我臉頰。
「不一樣,沒錯。可是更愛?你對她們的愛,比對我的愛更熱烈?」
他仔細端詳我,我希望他會笑著說:「當然沒有。」但他沒笑,他看著我,老老實實地說:「沒錯。」
真的嗎?他的回答讓我崩潰,令我窒息,扼殺了我。
「不過這不是理所當然嗎?怎麼了?妳因為自己更愛她們而覺得愧疚?」
我沒回話,他真的認為我愛她們勝過愛他?我甚至還不認識她們。
「別愧疚,」他說:「我要妳愛她們勝過愛我,我們對彼此的愛是有條件的,對她們的愛卻不是。」
「我對你的愛是無條件的。」
他微笑:「不,不是。我會做出妳永遠不能原諒的事,但妳永遠會原諒自己的孩子。」
他錯了,她們光是存在就不能原諒,不能原諒她們逼他把我放在第三順位,不能原諒她們奪走了我們的訂婚夜。
她們還沒出生,卻已奪走曾屬於我的東西。
「薇若蒂,」傑洛米輕喚。他抹掉我眼中落下的一滴淚:「妳沒事吧?」
我搖搖頭:「我只是不敢相信,她們還沒出生你就已經這麼愛她們了。」
薇若蒂書房的優點是後院景色透過窗戶一覽無遺,頂天立地的玻璃窗上沒有半點遮擋,全是厚實的玻璃。誰負責打掃?我往玻璃上尋找污垢、髒污什麼都好。
但良好的視野同時也是缺點,看護把薇若蒂的輪椅停在屋後門廊上,正對著書房,她面對西側,側臉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今天天氣適合外出,看護面對薇若蒂唸書給她聽。薇若蒂凝望半空中,她能理解任何事物嗎?能理解到什麼程度?
微風吹起她的金髮,宛如伸手把玩一縷縷髮絲的幽魂。
看著她,我就無法壓抑膨脹的同情心,這是不想看到她的原因,可是這片窗戶粉碎了我的希望。我聽不見看護的聲音,可能這片窗戶跟書房的牆面門板一樣隔音效果極佳吧,但我知道她們就在眼前,實在是難以抵擋每隔幾分鐘就抬頭偷看的衝動。
我實在是找不到跟系列作有關的筆記,不過我才搜了一小塊範圍。我想今天早上還是先把第一集跟第二集迅速翻一遍,針對每一個角色做紀錄。我自己編了一套建檔系統,因為必須跟薇若蒂一樣了解這些角色,我必須知道他們的動機、情緒的臨界點、弱點。
我注意到窗外有動靜,抬起頭發現看護離開薇若蒂,走向後門。我凝視薇若蒂好一會,沒有人替她唸書,不知道她會不會有任何反應。什麼都沒有,她雙手擱在膝上,腦袋歪向一邊,彷彿她的大腦無法傳送信號,讓她知道該挺直身子,不然會害自己脖子痠痛。
天賦異稟的薇若蒂已經不復存在,她的身體是那場車禍中唯一的倖存者嗎?她就像是一顆蛋,被人敲開倒出蛋白蛋黃,只剩硬殼的碎片。
視線移回桌面,努力集中精神,我忍不住納悶傑洛米究竟是如何面對這一切,他這個人外表架起鋼筋水泥,但內在肯定空無一物。知道自己的人生只能這麼過下去,自己只是在照顧一個空蛋殼,實在是太空虛了。
這個想法太過分了。
不是故意要這麼尖酸,只是⋯⋯我也不知道。我覺得要是她在車禍中喪命,大家都會好過許多,下一秒又為這個想法深感愧疚,我想起照顧母親的最後幾個月,知道母親寧可死掉,也不要忍受癌症帶來的重重枷鎖,然而那只是她和我人生的短短幾個月。傑洛米下半輩子全賠在上頭了,照顧空有軀殼的妻子,遭到不再是家的屋子束縛。我無法想像薇若蒂會希望他如此度日,也無法想像薇若蒂會希望自己如此度日,她甚至無法跟自己的孩子玩耍說話。
真希望她已經離去了,這是為了她好,倘若她的意識還在,卻因為腦部損傷太重,使得她無法以肉身傳達內心話。奪走她反應、互動、說出想法的能力,我不敢想像這是多麼痛苦的處境。
我再次抬頭。
她正直直盯著我。
我跳起來,辦公椅往後滑過木頭地板。薇若蒂隔著窗戶直視我,她的腦袋轉向書房,雙眼鎖住我的視線,我掩嘴後退,彷彿受到威脅。
我想離開她的目光,悄悄退向左側的房門。我實在是逃不開,她是蒙娜麗莎,眼神追著我跑,不過等我移到門邊時,我們的視線斷了線。
她的眼睛沒有跟著我移動。
我垂手靠上牆面,看艾普洛拿了條毛巾回到後門門廊,她替薇若蒂擦擦下巴,從她大腿上拿起個小枕頭,扶起她的腦袋,枕頭塞在她的肩膀跟臉頰間。調整過頭部角度後,她不再直視書房。
「媽的。」我低聲咒罵。
我竟然會怕這個幾乎無法動彈、連話都說不出來的女人,這個女人不可能靠著自己的意志轉頭看人,更別說是刻意與我互望了。
我要喝水。
在打開房門的一瞬間,背後書桌上的手機突然響起,我忍不住尖叫。
該死。我恨腎上腺素。脈搏加速,我呼出一大口氣,在接起電話前逼自己冷靜,是陌生的號碼。
「哈囉?」
「艾許雷女士?」
「我是。」
「我是克里伍公寓的多諾文.貝克,妳是否幾天前提出租屋申請?」
太好了,有別的事情分散注意。我回到窗邊,看護移動過薇若蒂的輪椅,我只看得到她的後腦杓。「是的,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今天我們處理到妳的申請書,可惜妳名下最近有一個強制遷離紀錄,因此無法核准妳的申請。」
已經?我兩天前才搬出來。「可是你們不是已經核准我的申請了嗎?我預計下禮拜搬進去耶。」
「事實上,妳的申請只有通過預審,程序到今天才跑完。我們無法核准近期有強制遷離紀錄的申請人,希望妳能理解。」
我捏捏後頸,還要兩個禮拜才拿得到稿費。「拜託,」我試著不讓洩氣的心情反映在語氣上:「我從來沒有拖過房租,這是第一次。我剛找到新工作,如果你們現在讓我搬進去,再兩個禮拜就可以付一整年的房租,我發誓。」
「妳隨時可以提出訴願,可能要多花幾個禮拜,不過某些申請人仔細說明他們的狀況,最後也是通過了。」
「沒辦法再等幾個禮拜,我已經搬出原本的公寓了。」
「我很遺憾,」他說:「我再把審核結果用電子郵件寄給妳,妳可以撥打信件結尾的電話號碼提出訴願。艾許雷女士,祝妳一切順利。」
他掛斷電話,但我繼續把手機按在耳邊,另一手揉捏後頸,真想馬上從這場惡夢中清醒過來。老媽,真是多謝了,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有人輕輕敲響房門,我猛然轉身,又被嚇了一跳,真是夠了。傑洛米站在書房門外,一臉同情地看著我。
手機響起時我沒有關門,他大概聽見整段通話了,我要把「驚慌失措」加進今天適用的形容詞清單。
我把手機放到薇若蒂的書桌上,坐進她的辦公椅:「我的生活其實不是一直這麼慘。」
他輕笑一聲,踏進房裡:「我也是。」
說得好。我低頭盯著手機。「沒事的,」我推著手機在桌上旋轉:「我再想想辦法。」
「在妳從經紀人手上拿到稿費前,我可以借妳錢,從我們的共用基金提領,不過要三天後才可以拿到。」
我這輩子沒有如此窩囊過,相信他全看在眼裡,我往後靠上書桌雙手掩面,整個人縮起來。
「你人真好,可是我不會跟你借錢。」
他沉默半晌,坐上沙發,姿勢隨興,上身前傾雙手在身前交握:「不然就在這裡待到預付款匯入妳的帳戶再說,應該只要一兩個禮拜吧。」他環顧書房,看出我從昨天到現在的進度是多麼的緩慢。「我們一點都不介意,妳完全沒有打擾到我們。」
我搖搖頭,但他硬是接著說下去。
「洛玟,接下的這份工作不簡單,我寧願妳在這裡多花時間準備,而不是明天回到紐約,卻發現少拿了什麼資料。」
我確實需要更多時間,可是在這棟屋子裡待上兩個禮拜?陪著把我嚇得六神無主的女人,陪著我不該看的草稿,陪著我太過了解的男人?
不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對。
我又搖起頭,可是他揚手制止我的拒絕:「別跟我們客氣。也不要這麼難為情。只要一句『好吧』。」
我的視線越過他,飄向他背後牆邊的紙箱那些還沒觸碰到的事物,然後我想:過了兩個禮拜,或許我有辦法看完她的作品,抄好筆記,寫出接下來三本新書的大綱。
我嘆息,不願承認自己感到些許慶幸。「好吧。」他笑了笑,起身,走向門外。
「謝謝。」我說。
傑洛米轉身對著我。真不該引他回頭。我清楚看見他臉上細微的懊悔,他張嘴似乎是打算說「不客氣」或是「小事一樁」,但他只是閉上嘴巴,擠出微笑,關門離開。
下午,傑洛米說我應該在太陽下山前到外頭走走:「妳就能理解薇若蒂要求書房裝上大片玻璃的原因。」
我帶上一本她的作品,準備坐在屋後門廊看,外頭擺了十張椅子,我選了圓桌旁的位置。傑洛米跟克魯在湖邊拆除釣魚平台的老舊木板,克魯從傑洛米手中接過木板的動作可愛極了,他把廢木料堆在一起,再從爸爸手中拿來一片。來回有一段距離,傑洛米從支架拆下木板的速度快得多了,他每次都要等上幾分鐘,這樣的舉動證明他是個充滿耐心的父親。
他讓我想起父親,他在我九歲那年過世,我似乎從沒看過他發怒,即使是面對母親尖銳的批評、不斷沸騰的脾氣,但我後來越來越怨恨他,有時候覺得他在母親面前的耐性跟軟弱沒有兩樣。
我斷斷續續地翻書,又看了那對父子好一會,實在是難以專心,因為傑洛米在幾分鐘前脫下上衣,儘管我看過他脫衣服,但那時他還穿著汗衫。他已經在湖邊勞動了兩個小時了,身上佈滿瑩亮的汗珠,他用鎚子後側撬起木板時,背肌伸展又收縮。我立刻聯想到先前在薇若蒂自傳看過的章節,裡頭滿是他們性生活的火辣細節,根據她的文字這對夫妻發生關係的頻率很高,遠遠超越我歷任男友。
現在看著他,很難不去想到做愛,並不是說我想跟他上床,也不是說我不想,身為作家,我知道他是薇若蒂書中幾個男性角色的靈感來源。因此我在想是否要從他身上獲得接下來三本小說的啟發,被迫站在薇若蒂的角度,在接下來二十四個月的寫作期間,把傑洛米的形象套入小說裡面⋯⋯其實沒有那麼糟。
後門砰地關上,我依依不捨地放下傑洛米,轉頭發現艾普洛站在門外盯著我看,她順著我方才的視線看過去,又回到我身上。她看到了,看到我在偷窺新老闆。可悲的傢伙。
她監視我多久了?真想拿書遮住臉,但我裝作若無其事地勾起嘴角。我又沒有做錯什麼,其實也不用裝。
「我要走了,」艾普洛說:「已經送薇若蒂躺回床上,幫她開電視,如果他問起的話,就說她晚餐跟藥都吃了。」
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我明明就跟這件事無關:「好,晚安。」
她沒有回我晚安,逕自回到屋內,任由後門猛然關起。過了一分鐘,我聽見她車子沿著車道離開的引擎聲消失在樹林間,我回頭望向傑洛米跟克魯,傑洛米又扯下一片木板。
克魯站在廢木料堆旁凝視我,他對我揮手微笑,我揚手打招呼,卻又屈起手指,因為我發現他的善意並不是衝著我來,他看著我的右上方。
他在仰望薇若蒂的臥室窗戶。
我轉過身抬起頭,剛好看到她房間的窗簾掩上。我失手把書摔落到桌上,撞倒水瓶。我起身後退三步,想找個更清楚的角度,可惜窗邊沒有半個人。我瞠目結舌,回頭望向克魯,但他已經轉身走向平台,接下另一片木板。
我看到了。
可是他幹嘛對著她的窗戶揮手?如果說她不在窗邊,他為什麼要揮手?
一點都不合理,她車禍後就無法言語或是行走,假如她從房裡往外看,克魯肯定會有更大的反應。
或是說他不知道除非奇蹟發生,否則他母親絕對無法自己走到窗邊,他才五歲。
我低頭看了看滲到水的小說,拎起來甩水,顫抖著吐氣,這一整天總是膽顫心驚的。稍早誤以為她盯著我看的那時,我一定是受到不小的震撼,所以剛剛才會以為窗簾動了。
我想忘記整件事,關在書房裡徹夜工作,但同時我也知道若是不去看看她,確認自己沒看到那些幻覺,是絕對無法安心的。
我把書本放在圓桌上晾乾,回到屋裡很安靜地走向樓梯,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鬼鬼祟祟的。她對外界的感知應該不太敏銳,就算我吵吵鬧鬧的上樓又有何妨?即便如此,我還是輕輕踏上樓梯,沿著走廊來到她臥室門外。
門板微微開啟,可以看見面對後院的窗戶,我按住房門輕輕一推,咬住下唇把腦袋探進去。
薇若蒂躺在床上,閉著眼睛,雙手擱在兩側壓在毯子上。
我輕輕鬆了口氣,把門推得更開,發現有個電風扇在薇若蒂的病床跟窗戶間轉動,每回轉向窗戶時就會吹動窗簾,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我用力吐氣,不過是個該死的電風扇。洛玟,振作點。
房裡溫度有點低,我關掉風扇,沒想到艾普洛離開前沒有關好,我再次偷瞄薇若蒂,她還是沒醒。回到門邊時,我一愣地望向梳妝台──看著擱在上頭的遙控器,再轉頭看著固定在牆上的電視螢幕。
電源沒開。
艾普洛說她離開前開了電視,可是電視沒開。
我不敢多看薇若蒂一眼,關上房門衝下樓。
我不會再上二樓了,我只是在自己嚇自己,這棟屋子裡最無助的人卻是我最大的恐懼來源,說出來肯定不會有人信。她沒有從屋外看著書房裡的我;她沒有站在窗邊,看著克魯,她沒有關掉房裡的電視,大概是設了定時關機吧,不然就是艾普洛不小心按了兩次電源,以為自己開了電視。
我很清楚都是自己在胡思亂想,但我仍舊回到薇若蒂的書房,關上門,拎起自傳的下一個章節,說不定多看點她的自述,可以讓我相信她毫無害處,而且我得要冷靜下來。
第三章
我知道自己懷孕,是因為自己的胸部從未顯得如此出色。
我十分照顧自己的身體狀況,吃了什麼,怎樣保養,怎樣維持體態。隨著長大,看著我媽的腰線在懶散下日益粗壯,我每天健身,有時一天兩次。
我很早就學到,人不僅僅是單一構造物,人這東西是合二為一的。
我們有意識的構成面,包含神智、心靈和所有無形部分。
我們還有物質的構成面,這是意識賴以為生的「機器」。
要是弄壞機器,你就會死;要是輕忽機器,你就會死;要是以為意識能比機器長命,明白自己錯了之後很快就會死。
這很簡單,真的。照顧好自己的物質層面,攝取物質層面所需,而不是吃意識層面想吃的。任心中渴望予取予求,最終就會傷了身體,像軟弱的父母對自己小孩沒輒:「噢,你今天很不開心?想吃一整盒餅乾?好吧,寶貝。吃吧,順便拿這瓶汽水來配。」
照顧自己身體和照顧小孩沒什麼兩樣,有時很不容易,有時很討人厭,有時讓人只想放棄,但如果真這麼做,接下來的十八年就得後果自負。
這適用在我媽身上,她照料自己身材就跟照料我一樣,少得可憐。有時我猜想她是否依舊那麼胖─要是她仍輕忽自己的機器,我不會知道,我很多年沒跟她講過話了。
但我沒興趣談論一個選擇再也不跟我說話的女人,我要談的是我的寶寶從我這裡最先偷走了什麼。
傑洛米。
一開始我沒察覺遭竊。
起初,在我們發覺訂婚夜成了有喜之夜後,我其實很開心,我開心是因為傑洛米開心,在那時除了胸部看起來更出色,我還不明瞭懷孕會對自己奮力維護的機器造成多大不利。
大概是在第三個月,發現懷孕後過了幾週,我開始留意到變化,那只是一小塊肚子贅肉,但確實存在。我才剛淋浴完,站在鏡子前注視自己的側面,我的手攤在肚子上,我感覺到異物,腹部微微凸起。
我覺得好討厭,發誓要開始一天健身三次。我見過懷孕的女人會變怎樣,並也知道多半都是在第三孕期最受影響,要是我能設法提早生產︙︙也許在三十三週或三十四週,就可以閃避孕期最不利的那段時間。醫療照護已經那麼先進,那週數的早產寶寶幾乎都不會有事。
「哇。」
我放開手望向門口,傑洛米倚著門雙手抱胸,他對我笑:「開始看得出妳懷孕了。」
「才沒有。」我縮了縮小腹。
他笑著拉近我倆的距離,從背後抱住我,把雙手放在我肚子上,望著鏡中的我並吻了吻我肩頭:「妳從沒這麼漂亮過。」
這是讓我心裡好受一點的假話,但我很感激,連他的謊言都有意義。我捏捏他的手,他讓我轉身面對面,接著吻我,帶著我往後退直到抵著洗手檯,讓我坐在檯面上,然後站在我雙腿間。
他衣衫楚楚,才剛下班,我全身赤裸,剛洗完澡,我們之間只隔著他的褲子,和我試著縮回去的贅肉。
他開始在洗手檯跟我做愛,但最後還是回到床上。
他的頭靠在我胸口,在我發出如雷腹鳴的肚皮劃圈圈,我試著咳幾聲來掩蓋,但他大笑:「有人餓了。」
我剛搖頭,他就從我胸口抬起頭看我:「她想要什麼?」
「沒有,我不餓。」
他又笑了。「不是說妳。是她,」他拍拍我的肚子:「女人一懷孕不都會因為寶寶就
突然很餓一直吃嗎?妳沒吃多少,可是妳的肚子在咕咕叫,」他坐起身:「我得餵飽我的女孩們。」
他的女孩們。
「還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
他對我微笑:「是女孩,我有預感。」
我想翻白眼,因為嚴格來講那還啥都不是,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就只是一團肉。我的週數還沒那麼大,肚子裡的東西會餓會想吃特定食物,這種假設實在可笑,但很難跟傑洛米講明這點,因為他那麼欣喜若狂,他的煞有其事我沒放在心上。
有時他的興奮,讓我興奮。
接下來的幾週,他的激動之情幫助我適應,肚子愈大他就愈殷勤,我們晚上躺在床上時,他越來越常親我肚子。
早上孕吐的時候,他會幫我撈住頭髮,他上班時會傳訊息分享寶寶的候選名字,他對我的懷孕著了迷,一如我對他著了迷。去婦產科初診那次,他陪我去。
我很慶幸第二次回診他也陪我去,因為那天起我的世界天翻地覆。
是雙胞胎。
有兩個。
那天我們走出診所時,我很沉默。當一個孩子的媽已經讓我很害怕了,被迫去愛一個傑洛米更愛的東西,而當知道有兩個寶寶,而且是女孩,成為傑洛米人生的第三順位突然讓我接受不了。
他對寶寶們說話的時候,我勉強自己微笑;他摩挲我肚皮時,我會表現得滿心喜悅,但其實厭惡不已,因為他這麼做只為了她們。就算能提早生產也沒用,現在有了兩個寶寶,我的身體會承受更多損害。每天想到她們在我身體裡一起長大,我就發抖,她們撐開我的皮,毀了胸部,毀了腹部,毀了每晚傑洛米都會朝聖的雙腿之際。
在這之後傑洛米怎麼還會想要我?
在懷孕第四個月期間,我開始希望流產,上廁所都祈求能見血,我能想像在失去雙胞胎後,傑洛米會如何重新把我放回第一順位。他會寵溺我、愛慕我、照顧我、擔心我,不再因為長在我肚裡的東西才這麼做。
他沒注意的時候,我吃安眠藥;他不在場的時候,我喝酒,我試遍一切想摧毀令他疏遠我的東西,但絲毫不管用。她們一直長大,我的肚皮持續擴張。
在第五個月,我們兩個都側躺在床上,傑洛米用背後位跟我做愛,他的左手握著我胸乳,右手擱在我肚皮上。我不喜歡他在上床時碰肚子,這會讓我想到寶寶,失了性致。
他停止挺動時,我還以為他射了,但很快察覺他不再動作是因為他感覺到她們動了。他整根拔出來,讓我轉身仰躺,把手心貼在我肚皮上。
「妳有沒有感覺到?」他的眼神狂喜亂舞,他軟了,興奮的原因與我無關。他把耳朵貼到我肚皮上,等待她們哪個再動一動。
「傑洛米?」我悄聲問。
他親吻我肚皮,仰頭看我。
我伸手用手指梳他頭髮:「你愛她們嗎?」
他微笑,因為他以為我要他給出肯定答覆:「我愛她們勝過一切。」
「包括我?」
他不再微笑,手仍放在肚皮上,但整個人往上挪,把手臂枕在我頸下:「是不一樣的
愛。」他親吻我臉頰。
「不一樣,沒錯。可是更愛?你對她們的愛,比對我的愛更熱烈?」
他仔細端詳我,我希望他會笑著說:「當然沒有。」但他沒笑,他看著我,老老實實地說:「沒錯。」
真的嗎?他的回答讓我崩潰,令我窒息,扼殺了我。
「不過這不是理所當然嗎?怎麼了?妳因為自己更愛她們而覺得愧疚?」
我沒回話,他真的認為我愛她們勝過愛他?我甚至還不認識她們。
「別愧疚,」他說:「我要妳愛她們勝過愛我,我們對彼此的愛是有條件的,對她們的愛卻不是。」
「我對你的愛是無條件的。」
他微笑:「不,不是。我會做出妳永遠不能原諒的事,但妳永遠會原諒自己的孩子。」
他錯了,她們光是存在就不能原諒,不能原諒她們逼他把我放在第三順位,不能原諒她們奪走了我們的訂婚夜。
她們還沒出生,卻已奪走曾屬於我的東西。
「薇若蒂,」傑洛米輕喚。他抹掉我眼中落下的一滴淚:「妳沒事吧?」
我搖搖頭:「我只是不敢相信,她們還沒出生你就已經這麼愛她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