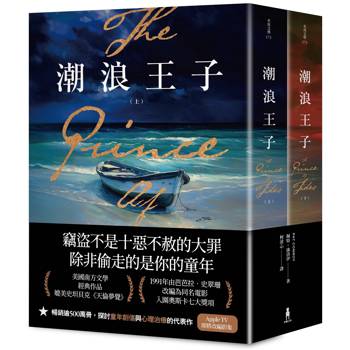我的人生,一直到我鼓足力氣原諒為我漫長童年帶來無盡恐懼的父親之後,才真真正正展開。竊盜不是十惡不赦的大罪,除非偷走的是你的童年。我可以確切地告訴你,他是個可怕又具破壞力的父親,但我絕未料到,自己有一天竟然會對這個男人產生無盡的同情與不知所措的愛,這將是我一生中最難解的謎題。父親的拳頭,就是他統御掌權的船艦,但他的眼睛卻是為人父的眼眸,即使雙手不聽使喚,眼中卻總散放著愛我的慈光。他天生不懂如何適度地關愛家人,沒有一絲人父的慈藹。我們把他的愛之歌誤聽成戰曲,他試圖和解,卻被我們解讀成激烈消耗戰中假意的暫時停火。他缺乏手腕與溫柔,所有通往他心靈的港灣與通路,都被他破壞掉了。只有當他被世界擊倒,我才有辦法抬手撫摸父親的臉,而不會被他揍到滿面是血。我十八歲時,就對警察國家的一切瞭若指掌,一直等我離開父親的家之後,才脫離長久以來的困境。
我的長女珍妮佛出生時,莎瓦娜從紐約飛來照料出院後的莎莉。我們喝白蘭地慶祝孩子平安健康,姊姊用哀傷的口吻問我說:「你愛爸爸嗎?」
我過了好一會兒才有辦法回答:「是的,我愛他,我愛那個混蛋。你愛他嗎?」
她也花了一點時間才答道:「愛。最奇怪的就是這點,我也愛他,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也許是腦子受傷吧。」我打趣。
「也許只是理解他無法違逆自己的本性吧。我們愛他,也是出於本性,一樣是無能為力的事。」
「不,我覺得純粹就是腦子受傷。」我說。
亨利.溫格身材高大,氣色紅潤,走進任何地方,都帶著難以忽略的氣勢。他自認白手起家,是鐵錚錚的南方漢子,缺乏反省力可能賦予的深度與清明。亨利橫衝直撞地來到這個充滿險阻、瘋狂而激烈的世界,在坎坷的人生路上,頂著難以拂逆的強風,逆向而行。他像一股自然的蠻力,不像個父親,每當他進入我童年所住的老家,總像是蒲福氏風級警示上的颶風襲來。
由於欠缺衡量痛恨父親的量表,我學會以沉默和逃避應付他。我從母親的頑抗中記取教訓,用受傷孩子叛逆而記恨的眼光偷偷地檢視他,學習如何發出致命的一擊。我透過望遠鏡的準星研究他,瞄準他的心臟。我對人類的愛的認識,最早得自於父母;對他們而言,愛是剝奪與折磨。我的童年混亂、艱險,布滿各種警訊。
失敗似乎只會令父親愈挫愈勇。姊姊說他有「土手指」——我不記得老姊何時發明這個詞彙,應該是高中時期吧,當時她很愛講髒話,覺得能更清楚明白地表達她的意見與想法。每年秋天捕蝦季結束後,老爸便會把全副心神轉移到其他更具創意的賺錢方法上。他腦子裡裝滿各種一夕致富但難以實踐的妄想。他有源源不絕的計畫、藍圖、方案,他向三個孩子保證,等我們高中畢業,家裡就會成為百萬富翁。他一生深信那些精采創新的點子會讓我們過上無法想像的富貴人生。他具有美國企業界罕見的才華:他從來不曾從自己的錯誤中學到一點長進。每次失敗——而且不下數十次——只會更令他相信,他的時機就快來了,他坎坷的學商歷程就快結束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他缺的只是運氣。
可是當拂曉的柔光遍灑水面,絞盤在沉重的魚網下發出呻吟,站在船舵後方的父親卻能完美無誤地主宰周遭的環境。河上拚搏的歲月在他身上烙下了刻痕,他看起來永遠比實際年齡老十歲。他那張風吹日曬的臉龐每年都會鬆弛一些,卡羅萊納正午的太陽使他的眼袋愈來愈垂腫。他的皮膚粗硬如皮革,下巴上的鬍碴彷彿能拿來畫火柴。他雙手粗糙,手掌長滿一層層牛皮紙色的老繭。他是個勤奮而備受尊敬的捕蝦人,可惜天分並非海陸兩用,一到陸上,便不靈光了。父親從很早以前就念說想離開河域,捕蝦向來是他「短期」的工作。爸媽都不承認捕蝦是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他們跟捕蝦圈保持距離,斷絕同業間會自然形成的團體關係。當然了,捕蝦人和他們的妻子,對於母親悉心培養日益提升的品味來說,實在太過平庸。我父母沒有親密的朋友,兩人一生都在等待幸運翻轉的時機,彷彿運氣是美好的潮流,總有一天會淹漫上來,把我們島上的沼地變成聖土,用彩色油膏般的美好命運為我們施洗。亨利.溫格堅信自己是商業天才,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對自己的認知會嚴重失準到造成自己或家人如此漫長而不必要的痛苦。
父親不在水上的日子,會把絕妙點子打成一手爛牌,而且絲毫不費吹灰之力。幾乎每個人都承認,他有些方案可能成功:他發明了剝蝦頭、清洗螃蟹、除去魚內臟的機器,而且這些機器並非完全無用,但也不具備強大功能,只是一堆奇形怪狀,在屋後打造的小工坊裡哐啷亂響的機器。
父親最棒與最失算的點子,都是他駕著船,在晨光熹微中穿越沼地的河道時,隨意發想出來的。他坐在船舵後,聆聽嗡嗡響的柴油引擎,駛過通往主河道的細小渠流。沼澤雖廣,卻隱不可見,他會在大西洋的朝陽喚醒鳥兒之前,這段美妙的破曉時刻,在幽暗的駕駛艙裡進行大量的獨白。捕蝦人極少帶孩子同行,但父親會盡可能從母親身邊帶走三個孩子,我認為他帶著我們,是為了減輕捕蝦生活的寂苦。
在夏日清晨繁星未退的昏矇中,父親輕輕喚醒我們,大伙悄悄穿衣,輕踏著露水深重的院子離開家門。我們坐在皮卡貨車後方,聽清晨的收音機,父親把車開上通往島嶼彼端木橋的泥土路。大伙吸著沼地的空氣,聽電台主持人播報天氣,以及從哈特拉斯角到聖奧古斯汀的小船警報,聽取風向和風速,以及方圓百里內所有捕蝦人需要知道的精確數字。每天早晨,父親開五英里路抵達捕蝦碼頭時,我都能感受到早起者才有的飽滿活力。父親的貨車出現時,為父親工作十五年的副手里斯特.懷海特正忙著把五百磅的冰塊倒進貨艙裡。魚網如神父的深袍掛在豎起的支架上,從停車場到碼頭,我們一路聞著柴油味、船上的煮咖啡香,和新鮮海產的濃烈氣味。我們經過在廉價燈具下亮著閃閃銀光的巨秤,等我們帶回當日的漁獲,黑人婦女便會等在這裡,用迅捷的速度剝去蝦頭。魚蝦的鮮味總令我覺得登船的這段路就像走在水底下,我用皮膚上的毛細孔呼吸潔淨的鹹水。身為捕蝦人的兒女,我們只是另一種形態的南方海洋生物罷了。
等父親一聲令下,我們便會聽到引擎響動,大伙鬆開繫繩,躍到船上,父親把船駛往群島水域的海聲與渠道中。我們會經過右手邊依然沉睡的科勒頓、沿潮汐街而列的豪宅及商店,接著父親拉響船笛,向大橋管理員示意,請他開橋,讓萊拉小姐號傲然地緩緩航向大海。父親這艘五十八英尺長的漂亮大船,吃水異常地淺。他要三個孩子從小牢記這艘船的重要數據,才讓我們正式成為船上的一員。捕蝦業向來推崇數祕術,捕蝦人討論船的時候,會來來回回說著各種晦澀難懂的數字,以定義他們可貴的技能。父親的主引擎是波士頓埃利思.柴默公司製的6-DAMR-844 Buda。引擎在每分鐘轉速二千一百圈下,能達一百八十八匹馬力。他的減速齒輪是3.88:1 Capitol,黃銅製的船軸轉動四十四乘三十六英寸的聯邦牌四葉螺旋槳。艙底的主排水泵是一又四分之一英寸的賈伯斯柯。甲板室裡有四十二英寸的瑪堤牌船舵、里奇羅盤、馬麥克節流閥和離合器,以及鐵洋牌自動駕駛。有班笛克斯DR16型的測深記錄器、皮爾斯辛普森大西洋七〇型的無線電。萊拉小姐號的甲板上放了一架史特勞斯堡515 1⁄2 T型起重機、威奇威爾電纜、沃爾馬尼拉纜繩。船錨是六十五磅重的丹佛斯,船笛是三十二伏特的史巴頓。在捕蝦人的語言裡,還有其他廠牌名稱表示特定的資訊:油城牌黃銅滑車、蘇雷第海洋電池、道奇軸承台、提肯軸承以及上百種其他名稱。捕蝦如同其他職業,需要用自己的行話精確溝通。對我來說,這套語言如母親的奶水般令人安心,也是我童年在船上的背景音樂。
這一切意謂著,如果穩妥地操作父親的船,便能捕到豐碩的蝦獲。
星光下,我們在無數個明媚的清晨圍聚在父親身邊。小時候,他會讓我們其中一人坐到他的大腿上,讓我們掌舵,然後輕輕壓住舵,矯正我們的失誤。
「我覺得我們應該稍微偏右一點,寶貝。」他輕聲對莎瓦娜說。
「湯姆,你最好牢記,干德角過去會有沙洲。就是這樣,這樣就對了。」
但大多時候,他會自言自語著生意、政治、夢想,以及幻滅。由於我們都是安靜的孩子,加上不信任回到陸地上就變了樣的父親,我們對父親的認識,多半來自聆聽他對黑夜和河流所說的話,得自他對著其他航向蝦群游聚的捕蝦船燈所發的喃喃自語。我們慢慢駛向堰洲島,父親的聲音在清晨顯得活力無限。捕蝦季的每一天,他都重複前一日的樣態;明天總是反映今日的辛勞;昨天向來是上千個未來之日的演練,在演練中展現他捕蝦的絕技。
「好了,孩子聽著。」某個漫長的捕蝦季早晨,父親說。「我是船長,是萊拉小姐號的船長與大副,這艘五十八英尺長的捕蝦船,有南卡羅萊納州核發的證照,可捕撈從大海灘到道夫斯基島之間的蝦子。今天我們要去蓋奇島燈塔東邊的海域,把網設在離溫沃瑪莉號殘船右舷側一英里半、十五英尺深的地方。昨天我們撈到兩百磅三十到五十的白蝦。我說『三十到五十』是指什麼意思,莎瓦娜?」
「意思就是,每一磅有三十到五十隻蝦子,爸爸。」
「好孩子。風會從北風以八十英里時速吹來,小船警報影響範圍南往喬治亞州布倫瑞克,北至德拉瓦州的威明頓。昨天股市跌了五點,交易量正常,因為投資人有些疑慮。昨天里斯.紐布里以每英畝五百元的價格向克羅維斯主教買下兩百英畝的農地,我按現價估算一下,梅洛斯島大約值五十萬元。那個混蛋去年出價兩萬五想買下整座島,我跟他說簡直侮辱人。沒錯,老子就是這麼說的。他以為我亨利.溫格不懂房地產。我有本州最棒的一片地,老子清楚得很,你們母親也是。老子比紐布里和其他混蛋懂得多了,開那種價簡直就是詐欺。我對咱家的地是有規畫的,孩子們,有長遠的大計畫,只要我一搞到動工的錢,就會付諸實行。先別跟你們母親說,但我打算在咱家附近搞個栗鼠養殖場。美國有一堆靠栗鼠發財的笨蛋,這種穩賺不賠的生意,我絕對不能放過。我去紐約跟那些大皮貨商談生意的時候,你們幾個小鬼可以輪流幫忙餵栗鼠,然後我就一路笑到銀行啦。你們覺得如何,很聰明吧?沒錯。我也考慮養貂,可是栗鼠的成本效益更高,我都做過功課了。是的,如果不做功課,就無法跟那些大老闆做生意。你們母親嘲笑我啊,孩子們,我承認,我是犯過一些錯,但那都是因爲時機沒掐準。點子本身絕對是一流的,你們幾個小鬼跟著我就對了,我比一般人有遠見多了,幾乎是罪過。老子腦裡有源源不絕的點子,有熊熊燃燒的各種方案,有時候我會在半夜醒來寫下這些想法。嘿,你們喜歡馬戲團嗎?」
「我們從沒看過馬戲團。」路克說。
「好,咱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馬戲,非去不可。下回有馬戲班到查勒斯登或薩凡納附近,咱們就坐上皮卡,搞個前排的座位。你們只見過小鎮的小型遊樂會,但我們會補看的。我喜歡巴氏馬戲團,貨真價實的馬戲表演。我要開栗鼠場的事別對任何人提,我要是能籌到一點儲備金,一定親手搞定,我受夠了讓別的混蛋拿我的點子去賺大錢了。路克,小心看好,前面有浮標。經過浮標的時候,以四十五度角切過河面,駛向北極星,好孩子。你真是天生好手,兒子。前面有塊岩石,文家老頭的船幾年前就在那兒擱淺。有一次滿潮,我在這條溪裡撈到兩百磅蝦子,不過這條溪通常蝦子不多。我從來搞不懂,為什麼有的溪,每年的蝦產都比別的溪更多,但事情就是這樣。蝦子挺有趣的,跟人一樣,天生有自己的好惡。」
父親又自顧自地長篇大論,他那鬆散、音高八度的獨白,並無特定的發話對象。這些晨間致詞如此流暢而辯才無礙,我能想像,即使三個孩子不在舵手室裡,他也會照講不誤。這是他的私語,對宇宙的沉思,他關心的不是他安靜體貼的孩子,而是獵戶座上的星群。父親在船上說話時,我們大概就跟大地和靜物一樣,是沒有生命的聽眾。船下的廚房飄來早餐的香味,陣陣濃香穿透父親的聲音。里斯特.懷海特做著飯,咖啡、培根、鬆餅的味道如隱形的水袖般,包圍了船身。我們近距離經過主峽灣入口,大伙擺桌準備吃早飯,河岸上的人尚在睡夢中,窗戶敞著。引擎在我們底下喃喃輕語,船身的木架輕輕震唱,破曉前的河面如黑豹般漆黑,潮水對小鎮淺唱頌歌,堂皇地載著我們航向世上最美群島外的碎波。父親在這裡最為自在放鬆,我們只有在河上,才能安全地與他相處。父親在捕蝦船上從不打我們,我們在船上是工人,是漁網的好兄弟,他尊重我們,如同敬重所有以海為生的漁人。
然而父親優異的捕蝦表現,卻沒有一件母親看得上眼。在她眼中,父親脆弱、無助、尖銳。他奮力想成為母親企盼的那種男人,渴求母親的尊重,但他的努力只會弄巧成拙,顯得可悲,無能為力。兩人的婚姻吵吵鬧鬧,波折重重。父親用捕蝦的成就,金援他災難性的生意投資。銀行家在他背後嘲弄他,父親成了郡內的笑柄:他的三個孩子在學校聽到各種訕笑,妻子則是在科勒頓的大街上聽到的。
可是河上的亨利.溫格能與地球和諧共處,蝦群似乎也都開心地游入他的網裡。他每一季都捕獲大量蝦子,謹慎詳細地記錄收穫。他可以看著日誌告訴你,每一磅蝦子是從科勒頓哪一處水域撈上來的、當時的潮汐與天候,就像他說的,「什麼都記下了」。他對河域的狀況倒背如流,引以為樂。當他在河上,漁網裡鼓盈著蝦獲時,我可以信任他。然而他也是在同一片水域裡,籌畫出那些不斷使他擺盪於毀滅或暴富之間的方案。
「我打算明年種西瓜。」有天晚飯時,父親說。
「不要,拜託不要,亨利。」母親說,「如果你跑去種西瓜,科勒頓就會下暴風雪或淹水或鬧蝗災。拜託千萬別種任何東西!想個別的敗光家產的辦法吧。你是我認識的人裡頭,唯一連葛藤都種不起來的人。」
「你說的對,萊拉,你跟以前一樣,說的完全正確。我比較適合當行政官僚,而不是農夫。正正經經做生意或按經濟原理做事更適合我,而不是從事農業。我想我其實一直都知道,可是看到那些種番茄發大財的傢伙,我也想下海撈一把。」
「別再下任何海了,亨利,我們把多的錢拿去投資像南加州電力瓦斯公司這種績優股吧。」
「我今天在查勒斯登買了一架電影攝影機。」
「天哪,為什麼?」
「未來是電影的天下。」父親眼神炯亮地答道。
母親尖叫起來,老爸鎮定地拿出新的手持攝影機,插上插頭,打開聚光燈,完整拍下母親怒斥的過程,供後人餘興。多年來,父親不辭辛勞地拿著攝影機拍攝,攝下婚禮、施洗禮、家庭團聚。他在地方報上登廣告,用了「溫格專業影片」的荒謬標誌。他在電影事業上面賠掉的錢,比任何其他事業都少。從那攝影機光圈看到的父親,是個十足快樂又十足可笑的人。
父親對自己的信念充滿勇氣,莎瓦娜發現,父親這種無法控制的怪癖就是他最大的缺點。
於是父親繼續在河上風風火火地從事不怎麼愛的工作,一邊徒勞地沉迷於不賺錢的事業。我們長大後,才知道他還有其他失敗的計畫。他是邁特海灘迷你高爾夫球場的隱名合夥人,但球場才開一季就關門大吉。他投資過墨西哥餅攤,交給一個滿口破英文、不太會做餅的純正墨西哥人經營。父母親會為了錢和錢的去向大吵特吵。母親笑話他、對他尖吼、罵他、誘導他、哀求他,但全都無效,父親不會輕易受到母親的約束或限制。母親總是先誘以警示,等勸說無效後,便高嚷著說,他若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亂花家裡的錢,一定會完蛋。兩人的爭執與衝突扭曲了家中原有的安詳和樂。由於他倆吵架頻繁,我們並不清楚母親究竟在什麼時間點,把不悅與怨怒化成對父親的恨,但她從很早就有了無能為力的怨氣,經過多年無效的溝通後,她懷著復仇的苦澀心情,伺機而動。亨利.溫格認為,女人根本不該談論生意上的事。南方的男人分兩類:聽老婆話的,跟不聽老婆話的;我父親是對老婆充耳不聞的黑帶高手。
●
如果你生在一個父親既愛你又虐你、且對這樣的矛盾行為毫無自知的家庭,為求自保,你會牢記他的習性,摸熟他的脾氣。我對父親最明顯的缺點做出總結,我很早就知道他既可笑又成不了大器。若非他如此殘酷,我想亨利.溫格的孩子應該會喜歡他,而這份喜愛,足以彌補他所有生意上的失敗。可惜他在我年幼時,把自己拱成家裡的土皇帝,女人和孩子最好都得敬畏他。他的方式一向嚴厲,但又不一致。他用焦土政策管教子女,馴服他意志頑強的妻子。
莎瓦娜在早期的一首詩中,稱他是「暴雨之王,風之至尊」。她到紐約之後,總是笑說,她和兄弟是被閃電戰風格的父親帶大的。他閃避所有可愛的事物,討厭美食,彷彿那是一種會破壞所有重要基本信念的放蕩。
母親含淚說,父親缺的只是腦袋。
某年耶誕節,母親發現父親還剩下三千盒耶誕卡沒有賣掉,這是他跟代銷員買來的。父親僅在查勒斯登挨家挨戶地賣掉七十五盒。莎瓦娜在關上的門後,低聲對我說:「土手指。」
「這跟希臘神話中的金手指麥達司國王恰恰相反。老爸無論碰到什麼,都會變成糞土。」莎瓦娜說。
「他甚至沒告訴媽媽,他還另外買了好幾千盒復活節卡片。我在穀倉裡找到的。」路克表示。
「他老是賠掉一大筆錢。」莎瓦娜說。
「你們看過他賣的那些耶誕卡嗎?」路克在他床上問。
「沒。」
「耶穌、瑪利、約瑟夫、牧羊人、智者、天使,所有人——全部都是黑人。」
「啊?」
「真的。老爸只賣卡片給黑人家庭,他聽說這種卡片在北部賣得很火,所以想跟風在南部賣。」
「可憐的老爸,蠢斃了。」我說。
「知道我們的血管裡流著他的血,真是受不了,超丟臉!」莎瓦娜說。
「他靠任何東西賺過錢嗎?」
「捕蝦,他是世上最厲害的捕蝦人,可惜對他們兩人來說,還不夠滿意。」路克說。
「如果他能滿足,就不會有任何土手指的事了。」莎瓦娜說。
「隨便你怎麼嘲笑他吧,莎瓦娜。可是永遠別忘了,我們父親把魚網丟入水裡,就變成點石成金的麥達司了。」路克說。
我的長女珍妮佛出生時,莎瓦娜從紐約飛來照料出院後的莎莉。我們喝白蘭地慶祝孩子平安健康,姊姊用哀傷的口吻問我說:「你愛爸爸嗎?」
我過了好一會兒才有辦法回答:「是的,我愛他,我愛那個混蛋。你愛他嗎?」
她也花了一點時間才答道:「愛。最奇怪的就是這點,我也愛他,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也許是腦子受傷吧。」我打趣。
「也許只是理解他無法違逆自己的本性吧。我們愛他,也是出於本性,一樣是無能為力的事。」
「不,我覺得純粹就是腦子受傷。」我說。
亨利.溫格身材高大,氣色紅潤,走進任何地方,都帶著難以忽略的氣勢。他自認白手起家,是鐵錚錚的南方漢子,缺乏反省力可能賦予的深度與清明。亨利橫衝直撞地來到這個充滿險阻、瘋狂而激烈的世界,在坎坷的人生路上,頂著難以拂逆的強風,逆向而行。他像一股自然的蠻力,不像個父親,每當他進入我童年所住的老家,總像是蒲福氏風級警示上的颶風襲來。
由於欠缺衡量痛恨父親的量表,我學會以沉默和逃避應付他。我從母親的頑抗中記取教訓,用受傷孩子叛逆而記恨的眼光偷偷地檢視他,學習如何發出致命的一擊。我透過望遠鏡的準星研究他,瞄準他的心臟。我對人類的愛的認識,最早得自於父母;對他們而言,愛是剝奪與折磨。我的童年混亂、艱險,布滿各種警訊。
失敗似乎只會令父親愈挫愈勇。姊姊說他有「土手指」——我不記得老姊何時發明這個詞彙,應該是高中時期吧,當時她很愛講髒話,覺得能更清楚明白地表達她的意見與想法。每年秋天捕蝦季結束後,老爸便會把全副心神轉移到其他更具創意的賺錢方法上。他腦子裡裝滿各種一夕致富但難以實踐的妄想。他有源源不絕的計畫、藍圖、方案,他向三個孩子保證,等我們高中畢業,家裡就會成為百萬富翁。他一生深信那些精采創新的點子會讓我們過上無法想像的富貴人生。他具有美國企業界罕見的才華:他從來不曾從自己的錯誤中學到一點長進。每次失敗——而且不下數十次——只會更令他相信,他的時機就快來了,他坎坷的學商歷程就快結束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他缺的只是運氣。
可是當拂曉的柔光遍灑水面,絞盤在沉重的魚網下發出呻吟,站在船舵後方的父親卻能完美無誤地主宰周遭的環境。河上拚搏的歲月在他身上烙下了刻痕,他看起來永遠比實際年齡老十歲。他那張風吹日曬的臉龐每年都會鬆弛一些,卡羅萊納正午的太陽使他的眼袋愈來愈垂腫。他的皮膚粗硬如皮革,下巴上的鬍碴彷彿能拿來畫火柴。他雙手粗糙,手掌長滿一層層牛皮紙色的老繭。他是個勤奮而備受尊敬的捕蝦人,可惜天分並非海陸兩用,一到陸上,便不靈光了。父親從很早以前就念說想離開河域,捕蝦向來是他「短期」的工作。爸媽都不承認捕蝦是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他們跟捕蝦圈保持距離,斷絕同業間會自然形成的團體關係。當然了,捕蝦人和他們的妻子,對於母親悉心培養日益提升的品味來說,實在太過平庸。我父母沒有親密的朋友,兩人一生都在等待幸運翻轉的時機,彷彿運氣是美好的潮流,總有一天會淹漫上來,把我們島上的沼地變成聖土,用彩色油膏般的美好命運為我們施洗。亨利.溫格堅信自己是商業天才,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對自己的認知會嚴重失準到造成自己或家人如此漫長而不必要的痛苦。
父親不在水上的日子,會把絕妙點子打成一手爛牌,而且絲毫不費吹灰之力。幾乎每個人都承認,他有些方案可能成功:他發明了剝蝦頭、清洗螃蟹、除去魚內臟的機器,而且這些機器並非完全無用,但也不具備強大功能,只是一堆奇形怪狀,在屋後打造的小工坊裡哐啷亂響的機器。
父親最棒與最失算的點子,都是他駕著船,在晨光熹微中穿越沼地的河道時,隨意發想出來的。他坐在船舵後,聆聽嗡嗡響的柴油引擎,駛過通往主河道的細小渠流。沼澤雖廣,卻隱不可見,他會在大西洋的朝陽喚醒鳥兒之前,這段美妙的破曉時刻,在幽暗的駕駛艙裡進行大量的獨白。捕蝦人極少帶孩子同行,但父親會盡可能從母親身邊帶走三個孩子,我認為他帶著我們,是為了減輕捕蝦生活的寂苦。
在夏日清晨繁星未退的昏矇中,父親輕輕喚醒我們,大伙悄悄穿衣,輕踏著露水深重的院子離開家門。我們坐在皮卡貨車後方,聽清晨的收音機,父親把車開上通往島嶼彼端木橋的泥土路。大伙吸著沼地的空氣,聽電台主持人播報天氣,以及從哈特拉斯角到聖奧古斯汀的小船警報,聽取風向和風速,以及方圓百里內所有捕蝦人需要知道的精確數字。每天早晨,父親開五英里路抵達捕蝦碼頭時,我都能感受到早起者才有的飽滿活力。父親的貨車出現時,為父親工作十五年的副手里斯特.懷海特正忙著把五百磅的冰塊倒進貨艙裡。魚網如神父的深袍掛在豎起的支架上,從停車場到碼頭,我們一路聞著柴油味、船上的煮咖啡香,和新鮮海產的濃烈氣味。我們經過在廉價燈具下亮著閃閃銀光的巨秤,等我們帶回當日的漁獲,黑人婦女便會等在這裡,用迅捷的速度剝去蝦頭。魚蝦的鮮味總令我覺得登船的這段路就像走在水底下,我用皮膚上的毛細孔呼吸潔淨的鹹水。身為捕蝦人的兒女,我們只是另一種形態的南方海洋生物罷了。
等父親一聲令下,我們便會聽到引擎響動,大伙鬆開繫繩,躍到船上,父親把船駛往群島水域的海聲與渠道中。我們會經過右手邊依然沉睡的科勒頓、沿潮汐街而列的豪宅及商店,接著父親拉響船笛,向大橋管理員示意,請他開橋,讓萊拉小姐號傲然地緩緩航向大海。父親這艘五十八英尺長的漂亮大船,吃水異常地淺。他要三個孩子從小牢記這艘船的重要數據,才讓我們正式成為船上的一員。捕蝦業向來推崇數祕術,捕蝦人討論船的時候,會來來回回說著各種晦澀難懂的數字,以定義他們可貴的技能。父親的主引擎是波士頓埃利思.柴默公司製的6-DAMR-844 Buda。引擎在每分鐘轉速二千一百圈下,能達一百八十八匹馬力。他的減速齒輪是3.88:1 Capitol,黃銅製的船軸轉動四十四乘三十六英寸的聯邦牌四葉螺旋槳。艙底的主排水泵是一又四分之一英寸的賈伯斯柯。甲板室裡有四十二英寸的瑪堤牌船舵、里奇羅盤、馬麥克節流閥和離合器,以及鐵洋牌自動駕駛。有班笛克斯DR16型的測深記錄器、皮爾斯辛普森大西洋七〇型的無線電。萊拉小姐號的甲板上放了一架史特勞斯堡515 1⁄2 T型起重機、威奇威爾電纜、沃爾馬尼拉纜繩。船錨是六十五磅重的丹佛斯,船笛是三十二伏特的史巴頓。在捕蝦人的語言裡,還有其他廠牌名稱表示特定的資訊:油城牌黃銅滑車、蘇雷第海洋電池、道奇軸承台、提肯軸承以及上百種其他名稱。捕蝦如同其他職業,需要用自己的行話精確溝通。對我來說,這套語言如母親的奶水般令人安心,也是我童年在船上的背景音樂。
這一切意謂著,如果穩妥地操作父親的船,便能捕到豐碩的蝦獲。
星光下,我們在無數個明媚的清晨圍聚在父親身邊。小時候,他會讓我們其中一人坐到他的大腿上,讓我們掌舵,然後輕輕壓住舵,矯正我們的失誤。
「我覺得我們應該稍微偏右一點,寶貝。」他輕聲對莎瓦娜說。
「湯姆,你最好牢記,干德角過去會有沙洲。就是這樣,這樣就對了。」
但大多時候,他會自言自語著生意、政治、夢想,以及幻滅。由於我們都是安靜的孩子,加上不信任回到陸地上就變了樣的父親,我們對父親的認識,多半來自聆聽他對黑夜和河流所說的話,得自他對著其他航向蝦群游聚的捕蝦船燈所發的喃喃自語。我們慢慢駛向堰洲島,父親的聲音在清晨顯得活力無限。捕蝦季的每一天,他都重複前一日的樣態;明天總是反映今日的辛勞;昨天向來是上千個未來之日的演練,在演練中展現他捕蝦的絕技。
「好了,孩子聽著。」某個漫長的捕蝦季早晨,父親說。「我是船長,是萊拉小姐號的船長與大副,這艘五十八英尺長的捕蝦船,有南卡羅萊納州核發的證照,可捕撈從大海灘到道夫斯基島之間的蝦子。今天我們要去蓋奇島燈塔東邊的海域,把網設在離溫沃瑪莉號殘船右舷側一英里半、十五英尺深的地方。昨天我們撈到兩百磅三十到五十的白蝦。我說『三十到五十』是指什麼意思,莎瓦娜?」
「意思就是,每一磅有三十到五十隻蝦子,爸爸。」
「好孩子。風會從北風以八十英里時速吹來,小船警報影響範圍南往喬治亞州布倫瑞克,北至德拉瓦州的威明頓。昨天股市跌了五點,交易量正常,因為投資人有些疑慮。昨天里斯.紐布里以每英畝五百元的價格向克羅維斯主教買下兩百英畝的農地,我按現價估算一下,梅洛斯島大約值五十萬元。那個混蛋去年出價兩萬五想買下整座島,我跟他說簡直侮辱人。沒錯,老子就是這麼說的。他以為我亨利.溫格不懂房地產。我有本州最棒的一片地,老子清楚得很,你們母親也是。老子比紐布里和其他混蛋懂得多了,開那種價簡直就是詐欺。我對咱家的地是有規畫的,孩子們,有長遠的大計畫,只要我一搞到動工的錢,就會付諸實行。先別跟你們母親說,但我打算在咱家附近搞個栗鼠養殖場。美國有一堆靠栗鼠發財的笨蛋,這種穩賺不賠的生意,我絕對不能放過。我去紐約跟那些大皮貨商談生意的時候,你們幾個小鬼可以輪流幫忙餵栗鼠,然後我就一路笑到銀行啦。你們覺得如何,很聰明吧?沒錯。我也考慮養貂,可是栗鼠的成本效益更高,我都做過功課了。是的,如果不做功課,就無法跟那些大老闆做生意。你們母親嘲笑我啊,孩子們,我承認,我是犯過一些錯,但那都是因爲時機沒掐準。點子本身絕對是一流的,你們幾個小鬼跟著我就對了,我比一般人有遠見多了,幾乎是罪過。老子腦裡有源源不絕的點子,有熊熊燃燒的各種方案,有時候我會在半夜醒來寫下這些想法。嘿,你們喜歡馬戲團嗎?」
「我們從沒看過馬戲團。」路克說。
「好,咱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馬戲,非去不可。下回有馬戲班到查勒斯登或薩凡納附近,咱們就坐上皮卡,搞個前排的座位。你們只見過小鎮的小型遊樂會,但我們會補看的。我喜歡巴氏馬戲團,貨真價實的馬戲表演。我要開栗鼠場的事別對任何人提,我要是能籌到一點儲備金,一定親手搞定,我受夠了讓別的混蛋拿我的點子去賺大錢了。路克,小心看好,前面有浮標。經過浮標的時候,以四十五度角切過河面,駛向北極星,好孩子。你真是天生好手,兒子。前面有塊岩石,文家老頭的船幾年前就在那兒擱淺。有一次滿潮,我在這條溪裡撈到兩百磅蝦子,不過這條溪通常蝦子不多。我從來搞不懂,為什麼有的溪,每年的蝦產都比別的溪更多,但事情就是這樣。蝦子挺有趣的,跟人一樣,天生有自己的好惡。」
父親又自顧自地長篇大論,他那鬆散、音高八度的獨白,並無特定的發話對象。這些晨間致詞如此流暢而辯才無礙,我能想像,即使三個孩子不在舵手室裡,他也會照講不誤。這是他的私語,對宇宙的沉思,他關心的不是他安靜體貼的孩子,而是獵戶座上的星群。父親在船上說話時,我們大概就跟大地和靜物一樣,是沒有生命的聽眾。船下的廚房飄來早餐的香味,陣陣濃香穿透父親的聲音。里斯特.懷海特做著飯,咖啡、培根、鬆餅的味道如隱形的水袖般,包圍了船身。我們近距離經過主峽灣入口,大伙擺桌準備吃早飯,河岸上的人尚在睡夢中,窗戶敞著。引擎在我們底下喃喃輕語,船身的木架輕輕震唱,破曉前的河面如黑豹般漆黑,潮水對小鎮淺唱頌歌,堂皇地載著我們航向世上最美群島外的碎波。父親在這裡最為自在放鬆,我們只有在河上,才能安全地與他相處。父親在捕蝦船上從不打我們,我們在船上是工人,是漁網的好兄弟,他尊重我們,如同敬重所有以海為生的漁人。
然而父親優異的捕蝦表現,卻沒有一件母親看得上眼。在她眼中,父親脆弱、無助、尖銳。他奮力想成為母親企盼的那種男人,渴求母親的尊重,但他的努力只會弄巧成拙,顯得可悲,無能為力。兩人的婚姻吵吵鬧鬧,波折重重。父親用捕蝦的成就,金援他災難性的生意投資。銀行家在他背後嘲弄他,父親成了郡內的笑柄:他的三個孩子在學校聽到各種訕笑,妻子則是在科勒頓的大街上聽到的。
可是河上的亨利.溫格能與地球和諧共處,蝦群似乎也都開心地游入他的網裡。他每一季都捕獲大量蝦子,謹慎詳細地記錄收穫。他可以看著日誌告訴你,每一磅蝦子是從科勒頓哪一處水域撈上來的、當時的潮汐與天候,就像他說的,「什麼都記下了」。他對河域的狀況倒背如流,引以為樂。當他在河上,漁網裡鼓盈著蝦獲時,我可以信任他。然而他也是在同一片水域裡,籌畫出那些不斷使他擺盪於毀滅或暴富之間的方案。
「我打算明年種西瓜。」有天晚飯時,父親說。
「不要,拜託不要,亨利。」母親說,「如果你跑去種西瓜,科勒頓就會下暴風雪或淹水或鬧蝗災。拜託千萬別種任何東西!想個別的敗光家產的辦法吧。你是我認識的人裡頭,唯一連葛藤都種不起來的人。」
「你說的對,萊拉,你跟以前一樣,說的完全正確。我比較適合當行政官僚,而不是農夫。正正經經做生意或按經濟原理做事更適合我,而不是從事農業。我想我其實一直都知道,可是看到那些種番茄發大財的傢伙,我也想下海撈一把。」
「別再下任何海了,亨利,我們把多的錢拿去投資像南加州電力瓦斯公司這種績優股吧。」
「我今天在查勒斯登買了一架電影攝影機。」
「天哪,為什麼?」
「未來是電影的天下。」父親眼神炯亮地答道。
母親尖叫起來,老爸鎮定地拿出新的手持攝影機,插上插頭,打開聚光燈,完整拍下母親怒斥的過程,供後人餘興。多年來,父親不辭辛勞地拿著攝影機拍攝,攝下婚禮、施洗禮、家庭團聚。他在地方報上登廣告,用了「溫格專業影片」的荒謬標誌。他在電影事業上面賠掉的錢,比任何其他事業都少。從那攝影機光圈看到的父親,是個十足快樂又十足可笑的人。
父親對自己的信念充滿勇氣,莎瓦娜發現,父親這種無法控制的怪癖就是他最大的缺點。
於是父親繼續在河上風風火火地從事不怎麼愛的工作,一邊徒勞地沉迷於不賺錢的事業。我們長大後,才知道他還有其他失敗的計畫。他是邁特海灘迷你高爾夫球場的隱名合夥人,但球場才開一季就關門大吉。他投資過墨西哥餅攤,交給一個滿口破英文、不太會做餅的純正墨西哥人經營。父母親會為了錢和錢的去向大吵特吵。母親笑話他、對他尖吼、罵他、誘導他、哀求他,但全都無效,父親不會輕易受到母親的約束或限制。母親總是先誘以警示,等勸說無效後,便高嚷著說,他若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亂花家裡的錢,一定會完蛋。兩人的爭執與衝突扭曲了家中原有的安詳和樂。由於他倆吵架頻繁,我們並不清楚母親究竟在什麼時間點,把不悅與怨怒化成對父親的恨,但她從很早就有了無能為力的怨氣,經過多年無效的溝通後,她懷著復仇的苦澀心情,伺機而動。亨利.溫格認為,女人根本不該談論生意上的事。南方的男人分兩類:聽老婆話的,跟不聽老婆話的;我父親是對老婆充耳不聞的黑帶高手。
●
如果你生在一個父親既愛你又虐你、且對這樣的矛盾行為毫無自知的家庭,為求自保,你會牢記他的習性,摸熟他的脾氣。我對父親最明顯的缺點做出總結,我很早就知道他既可笑又成不了大器。若非他如此殘酷,我想亨利.溫格的孩子應該會喜歡他,而這份喜愛,足以彌補他所有生意上的失敗。可惜他在我年幼時,把自己拱成家裡的土皇帝,女人和孩子最好都得敬畏他。他的方式一向嚴厲,但又不一致。他用焦土政策管教子女,馴服他意志頑強的妻子。
莎瓦娜在早期的一首詩中,稱他是「暴雨之王,風之至尊」。她到紐約之後,總是笑說,她和兄弟是被閃電戰風格的父親帶大的。他閃避所有可愛的事物,討厭美食,彷彿那是一種會破壞所有重要基本信念的放蕩。
母親含淚說,父親缺的只是腦袋。
某年耶誕節,母親發現父親還剩下三千盒耶誕卡沒有賣掉,這是他跟代銷員買來的。父親僅在查勒斯登挨家挨戶地賣掉七十五盒。莎瓦娜在關上的門後,低聲對我說:「土手指。」
「這跟希臘神話中的金手指麥達司國王恰恰相反。老爸無論碰到什麼,都會變成糞土。」莎瓦娜說。
「他甚至沒告訴媽媽,他還另外買了好幾千盒復活節卡片。我在穀倉裡找到的。」路克表示。
「他老是賠掉一大筆錢。」莎瓦娜說。
「你們看過他賣的那些耶誕卡嗎?」路克在他床上問。
「沒。」
「耶穌、瑪利、約瑟夫、牧羊人、智者、天使,所有人——全部都是黑人。」
「啊?」
「真的。老爸只賣卡片給黑人家庭,他聽說這種卡片在北部賣得很火,所以想跟風在南部賣。」
「可憐的老爸,蠢斃了。」我說。
「知道我們的血管裡流著他的血,真是受不了,超丟臉!」莎瓦娜說。
「他靠任何東西賺過錢嗎?」
「捕蝦,他是世上最厲害的捕蝦人,可惜對他們兩人來說,還不夠滿意。」路克說。
「如果他能滿足,就不會有任何土手指的事了。」莎瓦娜說。
「隨便你怎麼嘲笑他吧,莎瓦娜。可是永遠別忘了,我們父親把魚網丟入水裡,就變成點石成金的麥達司了。」路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