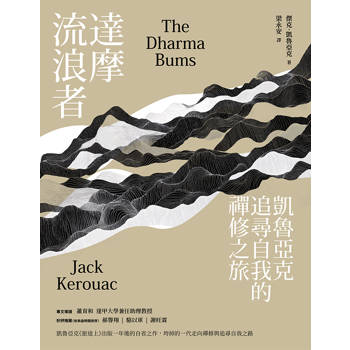二
我生平所遇的第一位達摩流浪者就是上述的小老頭,而第二個則是賈菲‧賴德(Japhy Ryder)──他是「達摩流浪者」的第一名,而且事實上,「達摩流浪者」這個詞,就是他始創的。賈菲來自俄勒岡,自小與父母和姊姊住在俄勒岡東部森林的一間小木屋。他當過伐木工和農夫,熱愛動物和印第安人的傳説,這種興趣,成為他日後在大學裡研究人類學和印第安神話學的雄厚本錢。後來,他又學了中文和日文,成了一名東方學家,並認識了「達摩流浪者」中的佼佼者:中國和日本的禪師。與此同時,身為一個在西北部長大、深具理想主義的青年,他對世界產業工人聯盟那種老式的無政府主義,又有很深的認同。他懂得彈吉他,喜歡唱老工人和印第安人的歌曲。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舊金山的街頭。(我忘了提,離開聖巴巴拉之後,我靠著一趟順風車一路坐到舊金山。説來難以置信的是,載我的人是位年輕的金髮美女,她穿著件無肩帶的泳衣,赤著腳,一隻腳踝上戴著金鐲子,開的是最新款的肉桂色林肯牌「水星」轎車。她告訴我,她很希望有安非他命提神,讓她可以一路開車開到舊金山,而我說剛好我的圓筒包裡就有些安非他命時,她高呼「神奇!」)我碰到賈菲的時候,他正踩著登山者那種奇怪大步在走路,背上揹著個小背包,裡面放著書本、牙刷之類的東西。這是他入城用的背包,有別於他的另一個大背包──裡面裝的是睡袋、尼龍披風、炊具和所有爬山時用得著的東西。他的下巴蓄著一把小山羊鬍,因為有一雙眼角上斜的綠眼睛,讓他很有東方人的味道。但他完全不像波西米亞人,而且生活得一點不像吊兒郎當、繞著藝術團團轉的波西米亞人。他精瘦、皮膚曬得棕黒、活力十足、坦率開放,見到誰都會快活地搭上兩句話,甚至連街頭上碰到的流浪漢,他都會打個招呼。而不管你問他什麼問題,他都會搜索枯腸去思索,而且總是迸出一個精彩絶倫的回答。
當我們走進「好地方」(The Place)酒吧的時候,大夥問他:「咦,你也認識雷‧史密斯?你是在哪認識他的?」「好地方」是北灣區爵士樂迷喜歡聚集的地方。
「我經常都會在街上碰到我的菩薩(Bodhisattvas)!」他喊著回答説,然後點了啤酒。
那是個不同凡響的夜,而且從很多方面來説都是具有歷史性的一夜。當天晚上,賈菲和一些其他的詩人預定要在六號畫廊舉行一場詩歌朗誦會(對,賈菲也是詩人,而且會把中國和日本的詩譯成英文),所以相約在酒吧裡碰面,人人都顯得情緒昂揚。不過在這一票或站或坐的詩人當中,賈菲是唯一不像詩人的一個(雖然他是個如假包換的詩人)。其他的詩人,有像艾瓦‧古德保(Alvah Goldbook)那樣一頭蓬亂黑髮的知識分子型詩人,有像艾克.奧沙伊(Ike O'Shay)那樣纖細、蒼白、英俊的詩人,有像法蘭西斯.達帕維亞(Francis DaPavia)那樣彷彿來自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有像萊茵荷.卡索埃特(Rheinhold Cacoethes)那樣打著蝴蝶領結、一頭亂髮的死硬派無政府主義詩人,也有像沃倫‧庫格林(Warren Coughlin)那樣戴眼鏡、文靜、肥得像大冬瓜的詩人。還有其他有潛力的詩人站在四周,而他們所穿的衣服雖然形形色色,但共同的特徵是袖口已經脫線,鞋頭已經磨損。反觀賈菲,穿的卻是耐穿耐磨的工人服裝,那是他從「善心人」(Goodwill)一類的舊衣商店買來的二手貨。這身服裝,也是他登山或遠足時穿的。事實上,在他的小背包裡,還放著一頂逗趣可愛的綠色登山帽,每當他去到一座幾千英尺高的高山下,就會把這帽子拿出來戴上。他身上的衣服雖然都是便宜貨,但腳上穿的,卻是一雙昂貴的義大利登山靴。那是他的快樂和驕傲,每當他穿著這雙登山靴昂首闊步踩在酒吧的木屑地板上時,都會讓人聯想起舊時代的伐木工。賈菲個子並不高,身高只有大約五尺七吋(約一七○公分),但卻相當強壯、精瘦結實、行動迅速和孔武有力。他雙顴高凸,兩顆眼珠子閃閃發亮,就像一個正在咯咯笑的中國老和尚的眼睛。而他顎下的小山羊鬍,抵消了他英俊臉龐的嚴峻感。他的牙齒有一點泛黃,那是他早期森林歲月不注重口腔衛生的結果,但他並不以為意,回應笑話狂笑的時候仍大大咧開著嘴。有時,他會無緣無故突然安靜下來,憂鬱地看著地板,彷彿心事重重。不過,他還是以快活的時候居多。他結過一次婚。對我表現出極大的投契,對我所談到的事情(像關於小老頭流浪漢的,或關於我坐免費火車或順風車旅行的)都聽得津津有味。他有一次説我是個「菩薩」(Bodhisattva,意思是「大智者」或「有大智慧的天使」),又説我用我的真摯妝點了這個世界。我們心儀的佛教聖者是同一個:觀世音菩薩(Avalokitesvara),或日文稱為十一面觀音(Kwannon the Eleven-Headed)。賈菲對西藏佛教、中國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日本佛教,乃至於緬甸佛教,從裡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我對佛教的神話學、名相以至於不同亞洲國家的佛教之間的差異,都興趣缺缺。我唯一感興趣的只有釋迦牟尼所説的「四聖締」的第一條「所有生命皆苦」,並連帶對它的第三條「苦是可以滅除的」產生多少興趣,只不過,我不太相信苦是可以滅除的(儘管《楞伽經》〔Lankavatara Scripture〕説過世界上除了心以外,別無所有,因此没有事情──包括苦的滅除──是不可能的。但這一點我迄今未能消化)。前面提到的沃倫‧庫格林是賈菲的死黨,是個一百八十磅的好心腸大肉球,不過,賈菲卻私底下告訴我,庫格林可不只我肉眼看到的那麼多。
「他是誰?」
「我的老朋友,打從我在俄勒岡念大學的時代就認識的死黨。乍看之下,你會以為他是個遲鈍笨拙的人,而事實上,他是顆閃閃發亮的鑽石。你以後會明白的。小覷他的話,你準會落得體無完膚。他只要隨便説句話,就可以讓你的腦袋飛出去。」
「為什麼?」
「因為他是個了不起的菩薩,我認為説不定就是大乘學者無著(Asagna)的化身轉世。」
「那我是誰?」
「這個我倒不知道。不過也許你是山羊。」
「山羊?」
「也許你是泥巴臉(Mudface)。」
「誰是泥巴臉?」
「泥巴臉就是你的山羊臉上的泥巴。如果有人問你『狗有佛性嗎?』,那你除了能『汪汪』叫兩聲以外,還能説些什麼呢?」
「我覺得那只是禪宗的猾頭話。」我這話讓賈菲有點側目。「聽著,賈菲,」我説,「我可不是個禪宗佛教徒,而是個嚴肅佛教徒,是個老派、迷迷糊糊的小乘信徒(Hinayānā),對後來的大乘佛教(Mahayanism)感到望而生畏。」我不喜歡禪宗,是因為我認為禪宗並没有強調慈悲的重要性,只懂得搞一些智力的把戲。「那些禪宗大師老是把弟子摔到泥巴裡去,因為他們根本答不出弟子的傻問題,」我説,「我覺得這樣很過分。」
「老兄,你錯了。他們只是想讓弟子明白,泥巴比語言更好罷了。」我無法在這裡一一複述賈菲那些精彩的回答,但他每一個見解,都讓我有被針扎了一下的感覺,到後來,他甚至把一些什麼植入了我的水晶腦袋,讓我的人生計畫為之有了改變。
總之,那晚,我跟著賈菲一票嚎叫詩人前往六號畫廊,參加詩歌朗誦會。這個朗誦會的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帶來了「舊金山詩歌的文藝復興」。每個我們認識的人都在那裡。那是一個瘋到了最高點的晚上。而我則扮演了加温者的角色:我向站在會場四周那些看來相當拘謹的聽眾,每人募來一毛幾角,跑出去買了三瓶大加侖裝的加州勃根地回來,然後對他們頻頻勸酒。因此,到十一點輪到艾瓦‧古德保登場,哀號他的詩歌〈哀號〉時,台下的每個人都像身在爵士樂即興演奏會那樣,不斷大喊「再來!再來!再來!」,而儼如舊金山詩歌之父的卡索埃特(Rheinhold Cacoethes),則高興激動得在一旁拭淚。賈菲朗誦的第一首詩,是以叢林狼為主題(就我的淺薄知識所知,叢林狼是北美高原印第安人的神祇,不然就是西北部印第安人的神祇)。「『操你的!』叢林狼喊道,然後跑走了!」賈菲對著台下一群傑出的聽眾念道,讓他們高興得嚎叫起來。真是神奇,明明是「操」這樣粗俗的一個字,被他放在詩中,竟顯得出奇的純淨。他其他詩歌,有一些是能反映他對動物的愛的抒情詩行(如寫熊吃漿果的一首),有一些是能顯示他淵博的東方知識的神祕詩行(如他寫蒙古的犛牛的一首)。他對東方的歷史文化的了解深入到什麼程度,從他寫玄奘的一首就可見一二(玄奘是個中國的高僧,曾經手持一炷香,從中國出發,途經蘭州、喀什和蒙古,一路徒步走到西藏)。至於賈菲一貫秉持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則表現在一首指陳美國人不懂得怎樣生活的詩歌裡。而在另一首描繪上班族可憐兮兮生活的詩,則流露出他曾在北方當伐木工的背景(他在詩中提到現在的上班族,都被困在由鍊鋸鋸斷的樹木所蓋成的起居室裡)。他的聲音深沉、嘹亮而無畏,就像舊時代的美國英雄和演説家。我喜歡他的詩所流露出的誠摯、剛健和樂觀,至於其他詩人的詩,我覺得不是失之太耽美就是太虛無,要不就是太抽象和太自我,或是太政治,又或是像庫格林的詩那樣,晦澀得難以理解(他詩中提到的「釐不清的過程」這詞兒倒是很適用於形容他的詩。不過,當庫格林的詩説到了「悟」是一種很個人性的體驗時,我注意到其中具有強烈的佛教和理想主義的色彩,跟賈菲很相似,而我猜得到,那是他和賈菲在念大學的死黨時代所共享的。就像我和艾瓦在東部念大學時也共享過相同的思想理念一樣)。
畫廊裡一共有幾十人,三五成群地站在幽暗的台下,全神貫注地聆聽朗誦,唯恐漏掉一個字。我在一群群人之間遊走(面向著他們而背對著舞台),去給每一個人勸酒,有時,我也會坐到舞台的右邊,聆聽朗誦,不時喊一聲「哇噻」或「好」,或説上一句評論的話(雖然没有人請我這樣做,但也没有人提出反對)。那是一個了不起的夜。輪到纖細的達帕維亞上場時,他拿著一疊像洋蔥皮一樣纖細的黃色紙張,用細長白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翻閱,一頁一頁地念。那些詩是他的亡友奧爾特曼(Altman)所寫。奧爾特曼前不久才在墨西哥的齊瓦瓦過世,死因據説是服用了過量的佩奧特鹼(peyote)(一説是死於小兒痲痹症,但這没什麼差)。達帕維亞没有念一首自己的詩──這個做法,本身便夠得上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輓歌,足以在賽凡提斯《唐吉訶德》的第七章裡擠出淚水來。另一方面,他念詩時所使用的纖細英國腔調,卻讓我不由得暗暗在肚裡狂笑。不過,稍後和他熟諳以後,我發現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人。
會場的其中一個聽眾是羅希‧布坎南(Rosie Buchanan)。她是個有著一頭紅短髮、骨感、俊俏的美女,跟沙灘上的誰都能結交或發展出一段羅曼史。她是個畫家模特兒,也寫寫作。當時的她,正跟我的死黨寇迪(Cody Pomeray)打得火熱,所以顯得神釆飛揚。「怎麼樣,羅希,今晚很棒吧?」我喊道,而她則拿起我的酒瓶,仰頭喝了一大口,眼睛閃閃有光地看著我。寇迪就站在她身後,兩手攬住她的腰。今天晚上當主持人的是卡索埃特,他打著個蝴蝶領結,穿著件破舊的西裝。每當一個詩人朗誦過後,他就會走上台,用他一貫的逗趣刻薄語氣,説一小段逗趣的話,介紹下一位朗誦者。所有詩歌在十一點半朗誦完畢,在場的聽眾都議論紛紛,很好奇這個朗誦會將會對美國詩歌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而卡索埃特則如上面提到過的,激動得用手帕拭淚。接下來,一票詩人分乘幾輛汽車,一起到舊金山的唐人街,在其中一家中國餐館裡大肆慶祝叫囂一番。我們去的「南園」餐館,湊巧是賈菲的最愛。他教我該如何點菜和怎樣使用筷子,又説了很多東方禪瘋子的趣聞軼事給我聽。這一切,再加上桌上的一瓶葡萄酒,讓我樂得無以復加,最後甚至跑到廚房的門邊,問裡面的老廚子:「為什麼達摩祖師會想到要向東傳法?」
「不關我的事。」他眨了一眨眼睛回答説。我把這件事告訴賈菲,他説:「好答案,好得無與倫比。現在你應該知道我心目中的禪是怎麼回事了。」
賈菲還有其他好些值得我學習的東西,特別是怎樣泡妞。他那種無與倫比的泡妞禪道,我在接下來那個星期就見識到。
我生平所遇的第一位達摩流浪者就是上述的小老頭,而第二個則是賈菲‧賴德(Japhy Ryder)──他是「達摩流浪者」的第一名,而且事實上,「達摩流浪者」這個詞,就是他始創的。賈菲來自俄勒岡,自小與父母和姊姊住在俄勒岡東部森林的一間小木屋。他當過伐木工和農夫,熱愛動物和印第安人的傳説,這種興趣,成為他日後在大學裡研究人類學和印第安神話學的雄厚本錢。後來,他又學了中文和日文,成了一名東方學家,並認識了「達摩流浪者」中的佼佼者:中國和日本的禪師。與此同時,身為一個在西北部長大、深具理想主義的青年,他對世界產業工人聯盟那種老式的無政府主義,又有很深的認同。他懂得彈吉他,喜歡唱老工人和印第安人的歌曲。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舊金山的街頭。(我忘了提,離開聖巴巴拉之後,我靠著一趟順風車一路坐到舊金山。説來難以置信的是,載我的人是位年輕的金髮美女,她穿著件無肩帶的泳衣,赤著腳,一隻腳踝上戴著金鐲子,開的是最新款的肉桂色林肯牌「水星」轎車。她告訴我,她很希望有安非他命提神,讓她可以一路開車開到舊金山,而我說剛好我的圓筒包裡就有些安非他命時,她高呼「神奇!」)我碰到賈菲的時候,他正踩著登山者那種奇怪大步在走路,背上揹著個小背包,裡面放著書本、牙刷之類的東西。這是他入城用的背包,有別於他的另一個大背包──裡面裝的是睡袋、尼龍披風、炊具和所有爬山時用得著的東西。他的下巴蓄著一把小山羊鬍,因為有一雙眼角上斜的綠眼睛,讓他很有東方人的味道。但他完全不像波西米亞人,而且生活得一點不像吊兒郎當、繞著藝術團團轉的波西米亞人。他精瘦、皮膚曬得棕黒、活力十足、坦率開放,見到誰都會快活地搭上兩句話,甚至連街頭上碰到的流浪漢,他都會打個招呼。而不管你問他什麼問題,他都會搜索枯腸去思索,而且總是迸出一個精彩絶倫的回答。
當我們走進「好地方」(The Place)酒吧的時候,大夥問他:「咦,你也認識雷‧史密斯?你是在哪認識他的?」「好地方」是北灣區爵士樂迷喜歡聚集的地方。
「我經常都會在街上碰到我的菩薩(Bodhisattvas)!」他喊著回答説,然後點了啤酒。
那是個不同凡響的夜,而且從很多方面來説都是具有歷史性的一夜。當天晚上,賈菲和一些其他的詩人預定要在六號畫廊舉行一場詩歌朗誦會(對,賈菲也是詩人,而且會把中國和日本的詩譯成英文),所以相約在酒吧裡碰面,人人都顯得情緒昂揚。不過在這一票或站或坐的詩人當中,賈菲是唯一不像詩人的一個(雖然他是個如假包換的詩人)。其他的詩人,有像艾瓦‧古德保(Alvah Goldbook)那樣一頭蓬亂黑髮的知識分子型詩人,有像艾克.奧沙伊(Ike O'Shay)那樣纖細、蒼白、英俊的詩人,有像法蘭西斯.達帕維亞(Francis DaPavia)那樣彷彿來自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有像萊茵荷.卡索埃特(Rheinhold Cacoethes)那樣打著蝴蝶領結、一頭亂髮的死硬派無政府主義詩人,也有像沃倫‧庫格林(Warren Coughlin)那樣戴眼鏡、文靜、肥得像大冬瓜的詩人。還有其他有潛力的詩人站在四周,而他們所穿的衣服雖然形形色色,但共同的特徵是袖口已經脫線,鞋頭已經磨損。反觀賈菲,穿的卻是耐穿耐磨的工人服裝,那是他從「善心人」(Goodwill)一類的舊衣商店買來的二手貨。這身服裝,也是他登山或遠足時穿的。事實上,在他的小背包裡,還放著一頂逗趣可愛的綠色登山帽,每當他去到一座幾千英尺高的高山下,就會把這帽子拿出來戴上。他身上的衣服雖然都是便宜貨,但腳上穿的,卻是一雙昂貴的義大利登山靴。那是他的快樂和驕傲,每當他穿著這雙登山靴昂首闊步踩在酒吧的木屑地板上時,都會讓人聯想起舊時代的伐木工。賈菲個子並不高,身高只有大約五尺七吋(約一七○公分),但卻相當強壯、精瘦結實、行動迅速和孔武有力。他雙顴高凸,兩顆眼珠子閃閃發亮,就像一個正在咯咯笑的中國老和尚的眼睛。而他顎下的小山羊鬍,抵消了他英俊臉龐的嚴峻感。他的牙齒有一點泛黃,那是他早期森林歲月不注重口腔衛生的結果,但他並不以為意,回應笑話狂笑的時候仍大大咧開著嘴。有時,他會無緣無故突然安靜下來,憂鬱地看著地板,彷彿心事重重。不過,他還是以快活的時候居多。他結過一次婚。對我表現出極大的投契,對我所談到的事情(像關於小老頭流浪漢的,或關於我坐免費火車或順風車旅行的)都聽得津津有味。他有一次説我是個「菩薩」(Bodhisattva,意思是「大智者」或「有大智慧的天使」),又説我用我的真摯妝點了這個世界。我們心儀的佛教聖者是同一個:觀世音菩薩(Avalokitesvara),或日文稱為十一面觀音(Kwannon the Eleven-Headed)。賈菲對西藏佛教、中國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日本佛教,乃至於緬甸佛教,從裡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我對佛教的神話學、名相以至於不同亞洲國家的佛教之間的差異,都興趣缺缺。我唯一感興趣的只有釋迦牟尼所説的「四聖締」的第一條「所有生命皆苦」,並連帶對它的第三條「苦是可以滅除的」產生多少興趣,只不過,我不太相信苦是可以滅除的(儘管《楞伽經》〔Lankavatara Scripture〕説過世界上除了心以外,別無所有,因此没有事情──包括苦的滅除──是不可能的。但這一點我迄今未能消化)。前面提到的沃倫‧庫格林是賈菲的死黨,是個一百八十磅的好心腸大肉球,不過,賈菲卻私底下告訴我,庫格林可不只我肉眼看到的那麼多。
「他是誰?」
「我的老朋友,打從我在俄勒岡念大學的時代就認識的死黨。乍看之下,你會以為他是個遲鈍笨拙的人,而事實上,他是顆閃閃發亮的鑽石。你以後會明白的。小覷他的話,你準會落得體無完膚。他只要隨便説句話,就可以讓你的腦袋飛出去。」
「為什麼?」
「因為他是個了不起的菩薩,我認為説不定就是大乘學者無著(Asagna)的化身轉世。」
「那我是誰?」
「這個我倒不知道。不過也許你是山羊。」
「山羊?」
「也許你是泥巴臉(Mudface)。」
「誰是泥巴臉?」
「泥巴臉就是你的山羊臉上的泥巴。如果有人問你『狗有佛性嗎?』,那你除了能『汪汪』叫兩聲以外,還能説些什麼呢?」
「我覺得那只是禪宗的猾頭話。」我這話讓賈菲有點側目。「聽著,賈菲,」我説,「我可不是個禪宗佛教徒,而是個嚴肅佛教徒,是個老派、迷迷糊糊的小乘信徒(Hinayānā),對後來的大乘佛教(Mahayanism)感到望而生畏。」我不喜歡禪宗,是因為我認為禪宗並没有強調慈悲的重要性,只懂得搞一些智力的把戲。「那些禪宗大師老是把弟子摔到泥巴裡去,因為他們根本答不出弟子的傻問題,」我説,「我覺得這樣很過分。」
「老兄,你錯了。他們只是想讓弟子明白,泥巴比語言更好罷了。」我無法在這裡一一複述賈菲那些精彩的回答,但他每一個見解,都讓我有被針扎了一下的感覺,到後來,他甚至把一些什麼植入了我的水晶腦袋,讓我的人生計畫為之有了改變。
總之,那晚,我跟著賈菲一票嚎叫詩人前往六號畫廊,參加詩歌朗誦會。這個朗誦會的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帶來了「舊金山詩歌的文藝復興」。每個我們認識的人都在那裡。那是一個瘋到了最高點的晚上。而我則扮演了加温者的角色:我向站在會場四周那些看來相當拘謹的聽眾,每人募來一毛幾角,跑出去買了三瓶大加侖裝的加州勃根地回來,然後對他們頻頻勸酒。因此,到十一點輪到艾瓦‧古德保登場,哀號他的詩歌〈哀號〉時,台下的每個人都像身在爵士樂即興演奏會那樣,不斷大喊「再來!再來!再來!」,而儼如舊金山詩歌之父的卡索埃特(Rheinhold Cacoethes),則高興激動得在一旁拭淚。賈菲朗誦的第一首詩,是以叢林狼為主題(就我的淺薄知識所知,叢林狼是北美高原印第安人的神祇,不然就是西北部印第安人的神祇)。「『操你的!』叢林狼喊道,然後跑走了!」賈菲對著台下一群傑出的聽眾念道,讓他們高興得嚎叫起來。真是神奇,明明是「操」這樣粗俗的一個字,被他放在詩中,竟顯得出奇的純淨。他其他詩歌,有一些是能反映他對動物的愛的抒情詩行(如寫熊吃漿果的一首),有一些是能顯示他淵博的東方知識的神祕詩行(如他寫蒙古的犛牛的一首)。他對東方的歷史文化的了解深入到什麼程度,從他寫玄奘的一首就可見一二(玄奘是個中國的高僧,曾經手持一炷香,從中國出發,途經蘭州、喀什和蒙古,一路徒步走到西藏)。至於賈菲一貫秉持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則表現在一首指陳美國人不懂得怎樣生活的詩歌裡。而在另一首描繪上班族可憐兮兮生活的詩,則流露出他曾在北方當伐木工的背景(他在詩中提到現在的上班族,都被困在由鍊鋸鋸斷的樹木所蓋成的起居室裡)。他的聲音深沉、嘹亮而無畏,就像舊時代的美國英雄和演説家。我喜歡他的詩所流露出的誠摯、剛健和樂觀,至於其他詩人的詩,我覺得不是失之太耽美就是太虛無,要不就是太抽象和太自我,或是太政治,又或是像庫格林的詩那樣,晦澀得難以理解(他詩中提到的「釐不清的過程」這詞兒倒是很適用於形容他的詩。不過,當庫格林的詩説到了「悟」是一種很個人性的體驗時,我注意到其中具有強烈的佛教和理想主義的色彩,跟賈菲很相似,而我猜得到,那是他和賈菲在念大學的死黨時代所共享的。就像我和艾瓦在東部念大學時也共享過相同的思想理念一樣)。
畫廊裡一共有幾十人,三五成群地站在幽暗的台下,全神貫注地聆聽朗誦,唯恐漏掉一個字。我在一群群人之間遊走(面向著他們而背對著舞台),去給每一個人勸酒,有時,我也會坐到舞台的右邊,聆聽朗誦,不時喊一聲「哇噻」或「好」,或説上一句評論的話(雖然没有人請我這樣做,但也没有人提出反對)。那是一個了不起的夜。輪到纖細的達帕維亞上場時,他拿著一疊像洋蔥皮一樣纖細的黃色紙張,用細長白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翻閱,一頁一頁地念。那些詩是他的亡友奧爾特曼(Altman)所寫。奧爾特曼前不久才在墨西哥的齊瓦瓦過世,死因據説是服用了過量的佩奧特鹼(peyote)(一説是死於小兒痲痹症,但這没什麼差)。達帕維亞没有念一首自己的詩──這個做法,本身便夠得上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輓歌,足以在賽凡提斯《唐吉訶德》的第七章裡擠出淚水來。另一方面,他念詩時所使用的纖細英國腔調,卻讓我不由得暗暗在肚裡狂笑。不過,稍後和他熟諳以後,我發現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人。
會場的其中一個聽眾是羅希‧布坎南(Rosie Buchanan)。她是個有著一頭紅短髮、骨感、俊俏的美女,跟沙灘上的誰都能結交或發展出一段羅曼史。她是個畫家模特兒,也寫寫作。當時的她,正跟我的死黨寇迪(Cody Pomeray)打得火熱,所以顯得神釆飛揚。「怎麼樣,羅希,今晚很棒吧?」我喊道,而她則拿起我的酒瓶,仰頭喝了一大口,眼睛閃閃有光地看著我。寇迪就站在她身後,兩手攬住她的腰。今天晚上當主持人的是卡索埃特,他打著個蝴蝶領結,穿著件破舊的西裝。每當一個詩人朗誦過後,他就會走上台,用他一貫的逗趣刻薄語氣,説一小段逗趣的話,介紹下一位朗誦者。所有詩歌在十一點半朗誦完畢,在場的聽眾都議論紛紛,很好奇這個朗誦會將會對美國詩歌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而卡索埃特則如上面提到過的,激動得用手帕拭淚。接下來,一票詩人分乘幾輛汽車,一起到舊金山的唐人街,在其中一家中國餐館裡大肆慶祝叫囂一番。我們去的「南園」餐館,湊巧是賈菲的最愛。他教我該如何點菜和怎樣使用筷子,又説了很多東方禪瘋子的趣聞軼事給我聽。這一切,再加上桌上的一瓶葡萄酒,讓我樂得無以復加,最後甚至跑到廚房的門邊,問裡面的老廚子:「為什麼達摩祖師會想到要向東傳法?」
「不關我的事。」他眨了一眨眼睛回答説。我把這件事告訴賈菲,他説:「好答案,好得無與倫比。現在你應該知道我心目中的禪是怎麼回事了。」
賈菲還有其他好些值得我學習的東西,特別是怎樣泡妞。他那種無與倫比的泡妞禪道,我在接下來那個星期就見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