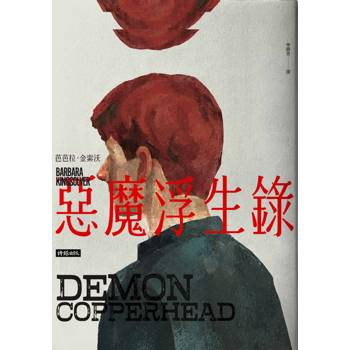感謝我的孤兒獎金,我不必像我大部分的室友那樣全職工作。君兒提議要幫我,如果我需要的話,而且一直盯緊我的情況。但我很習慣自食其力。每月的房租是用我的社會安全帳戶支應,沃爾瑪的兼職工作支付其他開銷。而清醒生活的娛樂是人生最美好的那些事,也就是免費的事。呼吸,睡覺,享受你新近變得規律的腸胃。吃你自己蹩腳廚藝做的菜,討支駱駝牌香菸,玩賭注很小的撲克牌;聽兩個肯塔基男孩講田納西的笑話,而田納西長大的你明明從小就認為那是肯塔基的笑話。聽令人毛骨悚然的街坊故事,但這人講的話讓你很希望配上字幕。我花很多時間在圖書館。
我們這個圖書館的主要館員就是麗拉。不是你老爸的奧斯摩比古董車。她一頭櫻桃紅頭髮,短而直的瀏海,佈滿整條手臂的刺青代表《白鯨記》。下沉的雙桅船,掀捲的波濤,忿怒的鯨魚。她一年四季都穿短褲、蛛網褲襪和機車靴。不動聲色地賣弄風情。從朵麗之後,我就沒和人上床,一次都沒有。這是死亡的一個層面,你對另一個軀體如此熟悉,而那人摸遍你身體的每一部分,再想到如今那軀體已冰冷躺在地下。有些日子,這簡直要了我的命;但其他日子,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性愛就只是狂熱生活模糊麻煩的部分,如今的我早就把那樣的生活隔離在玻璃牆的另一邊了。諮商師警告你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建議你不要涉入感情,先讓你的康復先打下堅實的基礎再說。重要的事要講三遍,如果你是個有多重母子問題的年輕男孩,喜歡上一團糟的救援對象註定會搞死你。麗拉看起來相當牢靠,但我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扯上關係的後果。我要拿棍子逗野獸,肯定會先被野獸給吞掉。除此之外,她呼出的口氣有大麻味,同時從每一方面看來都是愛跑趴的女生。我選擇不去瞭解。
我們找到其他方法分享。她顯然很愛看書,也對我指點很多,有些讓我變得更厲害,有些卻只覺得怪。她幫助我準備高中同等學力考試,結果考試簡單得要命,比多去上兩年課接受羞辱,嗑攙了羊驅蟲藥,索價過高的藥要簡單得太多了。我高中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一個墮落的將軍。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高中最艱難的部分就是人。
麗拉的祕密情人是電腦。她幫我設電子信箱,教我用圖書館的掃描機,把我畫的圖上傳。前面提到,紅脖子不得不停擺六個月,但我的腦袋一開始有辦法運轉,就馬上恢復工作。湯米需要的東西在報社都有,所以我們可以交換草稿。他組織故事概念,我來畫,然後再畫明暗,上色。因為兩個人都清醒運作,所以我們效率一流。萍琪想再和我們續一年約。
有點難過的,我們決定不要。我們兩個都走向新階段了。湯米終於和他的女朋友見面,真的面對面。蘇菲為湯米而瘋狂,她媽媽的親戚也是,因為她辦了一場盛大餐會,請所有的親戚來考核湯米。湯米回家,給萍琪提前兩週的離職通知,和麥克柯伯家的多功能空間切斷關係,搬到賓州的艾倫鎮。他和蘇菲在波蘭美國公民俱樂部結婚,接著是一場波蘭波卡樂團助興的盛大酒會。誰來給我條手帕,我不是開玩笑的。湯米成家了。在我下回見到他之前,他就會成為父親了。
至於我,我已經超過玩超級英雄的年齡了,就算是迫切需要的山巴佬類型也一樣。弗萊舍風格的紅脖子侷限了我,球狀的眼睛,麵條似的四肢,感覺很幼稚。我想嘗試更硬調的東西。麗拉培訓我,但不是我無所事事的腦袋所把玩的那回事。讓我翻完圖書館大人漫畫和圖像小說區的書之後,她帶我透過網路瞭解世界漫畫發展的現況,給我帶來很大的衝擊。她一步步引領我建立自己的網頁。主要也是這樣我就不會吵她,讓她可以飛快敲她的鍵盤,而我則沉浸在她左臂那戲劇性的海洋景觀裡。我可以上傳我的圖畫到網站,就用這種方式展開我的事業。和麥克柯伯先生大部分的事業一樣,第一年什麼錢也沒賺到。和他不同的是,我繼續做。這是我自己的小小宇宙,以我的筆名創造。惡魔‧銅頭蝮。我早已遠離美式足球場和李郡傳說,再次用我媽的姓。大部分人叫我菲爾德斯。但我有這不想失去的另一部分:我爸。
一開始是我很久以前構想的頸骨。徵得湯米同意之後,我透過骸骨之眼述說我們知名的本地歷史。諾克斯礦災,自然隧道火車失事。還有和朵麗在一起的那段最哀傷的日子裡,我構思:無能二人組,講一對毒蟲情侶努力持家的漫畫。那男的叫克拉許,女的叫柏妮,兩個想養活自己的十幾歲青少年。他們開車去找熟人的時候,用汽車引擎烤熱狗,用大麻菸斗和菸夾修理家裡的東西。我竭盡全力畫得既悲傷又真實,刻劃出有毒癮的年輕人搞出的可笑麻煩。同時也有苦澀。我畫的一幅漫畫是:克拉許在非法藥物診所拿了處方箋去領藥,藥局的女士警告他說:「這藥效很強,親愛的,普渡製藥的業務代表要吃這個才睡得著覺。」
我要說的並不是這些東西有市場。但大村落的時代正要開啟。如果這世上每隻腳都有只適合的鞋在等著,那麼我這隻孤單古怪的腳透過網際網路,找到鞋的機會也會大幅提升。我這詭異的漫畫有了逐漸增加的追蹤者,一年之後,我開始收費訂閱。不是很多。幸運的是,我這樣做也不是為了錢。我從阿姆斯壯先生那裡學到一件事,那是他苦口婆心對沒受過教育的人所說的:好的故事不只是複製人生,而且是反抗人生。這是為什麼像察特蘭這樣的人要穿過大的衣服,牙齒鑲金邊;為什麼狄克先生要把字寫在風箏上,讓它們奔向太陽。這是為什麼我要畫我這些畫。
安格斯保持聯繫。她追蹤我的漫畫,很喜歡,從納許維爾前線傳來最新戰況:大學很艱難,唸大學的小孩都是些被寵壞的調皮鬼,每個人,包括教授,都取笑山區口音。她是拿獎學金去上大學的,當時並不知道她會和任性的有錢人、資本主義王子化敵為友,她是這麼形容的。很高興看到安格斯維持她好勝的個性。
我們這個圖書館的主要館員就是麗拉。不是你老爸的奧斯摩比古董車。她一頭櫻桃紅頭髮,短而直的瀏海,佈滿整條手臂的刺青代表《白鯨記》。下沉的雙桅船,掀捲的波濤,忿怒的鯨魚。她一年四季都穿短褲、蛛網褲襪和機車靴。不動聲色地賣弄風情。從朵麗之後,我就沒和人上床,一次都沒有。這是死亡的一個層面,你對另一個軀體如此熟悉,而那人摸遍你身體的每一部分,再想到如今那軀體已冰冷躺在地下。有些日子,這簡直要了我的命;但其他日子,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性愛就只是狂熱生活模糊麻煩的部分,如今的我早就把那樣的生活隔離在玻璃牆的另一邊了。諮商師警告你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建議你不要涉入感情,先讓你的康復先打下堅實的基礎再說。重要的事要講三遍,如果你是個有多重母子問題的年輕男孩,喜歡上一團糟的救援對象註定會搞死你。麗拉看起來相當牢靠,但我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扯上關係的後果。我要拿棍子逗野獸,肯定會先被野獸給吞掉。除此之外,她呼出的口氣有大麻味,同時從每一方面看來都是愛跑趴的女生。我選擇不去瞭解。
我們找到其他方法分享。她顯然很愛看書,也對我指點很多,有些讓我變得更厲害,有些卻只覺得怪。她幫助我準備高中同等學力考試,結果考試簡單得要命,比多去上兩年課接受羞辱,嗑攙了羊驅蟲藥,索價過高的藥要簡單得太多了。我高中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一個墮落的將軍。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高中最艱難的部分就是人。
麗拉的祕密情人是電腦。她幫我設電子信箱,教我用圖書館的掃描機,把我畫的圖上傳。前面提到,紅脖子不得不停擺六個月,但我的腦袋一開始有辦法運轉,就馬上恢復工作。湯米需要的東西在報社都有,所以我們可以交換草稿。他組織故事概念,我來畫,然後再畫明暗,上色。因為兩個人都清醒運作,所以我們效率一流。萍琪想再和我們續一年約。
有點難過的,我們決定不要。我們兩個都走向新階段了。湯米終於和他的女朋友見面,真的面對面。蘇菲為湯米而瘋狂,她媽媽的親戚也是,因為她辦了一場盛大餐會,請所有的親戚來考核湯米。湯米回家,給萍琪提前兩週的離職通知,和麥克柯伯家的多功能空間切斷關係,搬到賓州的艾倫鎮。他和蘇菲在波蘭美國公民俱樂部結婚,接著是一場波蘭波卡樂團助興的盛大酒會。誰來給我條手帕,我不是開玩笑的。湯米成家了。在我下回見到他之前,他就會成為父親了。
至於我,我已經超過玩超級英雄的年齡了,就算是迫切需要的山巴佬類型也一樣。弗萊舍風格的紅脖子侷限了我,球狀的眼睛,麵條似的四肢,感覺很幼稚。我想嘗試更硬調的東西。麗拉培訓我,但不是我無所事事的腦袋所把玩的那回事。讓我翻完圖書館大人漫畫和圖像小說區的書之後,她帶我透過網路瞭解世界漫畫發展的現況,給我帶來很大的衝擊。她一步步引領我建立自己的網頁。主要也是這樣我就不會吵她,讓她可以飛快敲她的鍵盤,而我則沉浸在她左臂那戲劇性的海洋景觀裡。我可以上傳我的圖畫到網站,就用這種方式展開我的事業。和麥克柯伯先生大部分的事業一樣,第一年什麼錢也沒賺到。和他不同的是,我繼續做。這是我自己的小小宇宙,以我的筆名創造。惡魔‧銅頭蝮。我早已遠離美式足球場和李郡傳說,再次用我媽的姓。大部分人叫我菲爾德斯。但我有這不想失去的另一部分:我爸。
一開始是我很久以前構想的頸骨。徵得湯米同意之後,我透過骸骨之眼述說我們知名的本地歷史。諾克斯礦災,自然隧道火車失事。還有和朵麗在一起的那段最哀傷的日子裡,我構思:無能二人組,講一對毒蟲情侶努力持家的漫畫。那男的叫克拉許,女的叫柏妮,兩個想養活自己的十幾歲青少年。他們開車去找熟人的時候,用汽車引擎烤熱狗,用大麻菸斗和菸夾修理家裡的東西。我竭盡全力畫得既悲傷又真實,刻劃出有毒癮的年輕人搞出的可笑麻煩。同時也有苦澀。我畫的一幅漫畫是:克拉許在非法藥物診所拿了處方箋去領藥,藥局的女士警告他說:「這藥效很強,親愛的,普渡製藥的業務代表要吃這個才睡得著覺。」
我要說的並不是這些東西有市場。但大村落的時代正要開啟。如果這世上每隻腳都有只適合的鞋在等著,那麼我這隻孤單古怪的腳透過網際網路,找到鞋的機會也會大幅提升。我這詭異的漫畫有了逐漸增加的追蹤者,一年之後,我開始收費訂閱。不是很多。幸運的是,我這樣做也不是為了錢。我從阿姆斯壯先生那裡學到一件事,那是他苦口婆心對沒受過教育的人所說的:好的故事不只是複製人生,而且是反抗人生。這是為什麼像察特蘭這樣的人要穿過大的衣服,牙齒鑲金邊;為什麼狄克先生要把字寫在風箏上,讓它們奔向太陽。這是為什麼我要畫我這些畫。
安格斯保持聯繫。她追蹤我的漫畫,很喜歡,從納許維爾前線傳來最新戰況:大學很艱難,唸大學的小孩都是些被寵壞的調皮鬼,每個人,包括教授,都取笑山區口音。她是拿獎學金去上大學的,當時並不知道她會和任性的有錢人、資本主義王子化敵為友,她是這麼形容的。很高興看到安格斯維持她好勝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