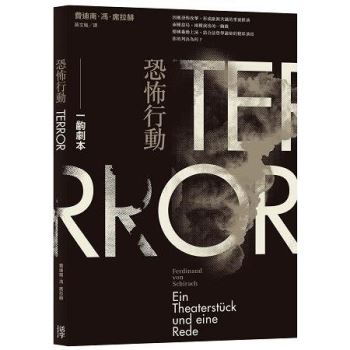第二幕
除了審判長以外的所有訴訟參與人員或坐或站在他們的位置,法警步上舞台邊緣。
法警:
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
審判長進入法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起立。
審判長:
諸位請坐。
所有人都坐了下來。
審判長:
檢察官,勞駕,現在我們可以聆聽檢方的最終陳述。
檢察官:
起立。
庭上、諸位法官女士、先生,我直接講重點:被告不是刑事犯,他的行為和我們平常在法庭上所調查的罪行完全不同。他既不是殺了他的配偶,也不是殺了她的情夫,他沒有搶劫,沒有詐欺,沒有偷竊。相反的,根據一般常民標準,拉爾斯・寇赫截至目前的人生近乎完美,他沒有任何疏失、沒有犯錯、幾乎是無懈可擊。而且我可以說,他的正直和思慮之嚴謹讓我印象深刻。拉爾斯・寇赫不是那種試著把他的犯行歸咎於童年、心理創傷或隨便什麼理由的被告,他是非常聰明的、沉穩的男人,可以明辨是與非,這點他甚至可能好過大多數的人。拉爾斯・寇赫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完全自覺、高度清明的狀態下去做的。他堅信他做的是對的,這點確實沒錯。
敬愛的法官女士、先生,是的,辯護人是對的,在本案中關鍵只在於:我們可以殺害無辜者,只為了拯救其他的無辜者嗎?還是這是人數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死亡,至少可以拯救其他400人,是否就可以拿來相互比較輕重?
我們所有人可能出於本能都會這麼做,在我們看來,這是對的。或許我們不完全確定,內心會有一番掙扎,但若生命中遇到其他狀況時,我們會怎麼衡量。我們捫心自問,然後相信,我們是理性的、公平處事的、坦蕩蕩的,我們支持拉爾斯・寇赫的作法。這樣我們就可以終結審判將他無罪釋放。
但是,諸位已經聽到,憲法對我們的要求有些不同。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訂定的條文是:生命是不容許相互衡估輕重的,就算比例懸殊,也絕不可以。這點讓人感到困惑。而我們也該仔細思考,這是我們欠被告與受難者的。
我們根據哪些標準來決定被告是否可以殺人?事實上,我們是根據良心、根據道德、根據常識,以及另一個概念、也就是前國防部長說這是基於職責所採取的「超越法律的緊急手段」,有些法學家稱此為「自然法」。諸位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個名稱是無關緊要的,它所指的是:我們應該依據我們的觀念來判決,它超越法律、比法律還重要,於是觀念取代了法律。問題在於:這是理性的嗎?我知道,你們每一位都認為,他的道德、他的良知值得信賴,但是,這是錯的。
1951年,德國法哲學家漢斯・韋策爾(Hans Welzel)描述了所謂的「扳道工案例」(Weichenstellerfall):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輛載貨火車失速往山谷下的小火車站衝去,而那裡停著一輛滿載乘客的火車,如果載貨火車持續奔馳,那麼會有數百人死亡。請您設想一下,您是鐵道管理員,您可以扳動轉轍器,把載貨火車引到支線軌道上。問題在於,支線軌道上有五名工人正在修復鐵軌。如果您讓火車改道,那麼就會殺害那五名工人,但卻可以拯救數百名乘客。您會怎麼做?您會選擇犧牲那五條人命嗎?
大多數的人確實選擇讓載貨火車改道,而且稍經思考我們會認為這麼做是對的。
但只要條件稍做改變,立刻會變得讓人難以抉擇。1976年,美國法哲學家茱蒂斯・湯姆森(Judith Thomson)提出另一個擴充討論的版本:載貨火車還是一樣在山路上往下疾馳,但這時沒有轉轍器可以讓您轉換火車軌道。身為旁觀者,這時您站在橋上觀看事件發生,但您身邊有個彪形大漢,如果他從橋上掉下去,剛好會落在鐵軌上,雖然他會被火車輾過,但他龐大的身軀卻可以讓火車停下來。只是男人太高太壯,您無法把他推到橋下,您必須先殺了他,例如找把刀做掉他,然後才能把他丟下去,這樣您才能拯救乘客。敬愛的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時,您又會怎麼做?
除了審判長以外的所有訴訟參與人員或坐或站在他們的位置,法警步上舞台邊緣。
法警:
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
審判長進入法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起立。
審判長:
諸位請坐。
所有人都坐了下來。
審判長:
檢察官,勞駕,現在我們可以聆聽檢方的最終陳述。
檢察官:
起立。
庭上、諸位法官女士、先生,我直接講重點:被告不是刑事犯,他的行為和我們平常在法庭上所調查的罪行完全不同。他既不是殺了他的配偶,也不是殺了她的情夫,他沒有搶劫,沒有詐欺,沒有偷竊。相反的,根據一般常民標準,拉爾斯・寇赫截至目前的人生近乎完美,他沒有任何疏失、沒有犯錯、幾乎是無懈可擊。而且我可以說,他的正直和思慮之嚴謹讓我印象深刻。拉爾斯・寇赫不是那種試著把他的犯行歸咎於童年、心理創傷或隨便什麼理由的被告,他是非常聰明的、沉穩的男人,可以明辨是與非,這點他甚至可能好過大多數的人。拉爾斯・寇赫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完全自覺、高度清明的狀態下去做的。他堅信他做的是對的,這點確實沒錯。
敬愛的法官女士、先生,是的,辯護人是對的,在本案中關鍵只在於:我們可以殺害無辜者,只為了拯救其他的無辜者嗎?還是這是人數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死亡,至少可以拯救其他400人,是否就可以拿來相互比較輕重?
我們所有人可能出於本能都會這麼做,在我們看來,這是對的。或許我們不完全確定,內心會有一番掙扎,但若生命中遇到其他狀況時,我們會怎麼衡量。我們捫心自問,然後相信,我們是理性的、公平處事的、坦蕩蕩的,我們支持拉爾斯・寇赫的作法。這樣我們就可以終結審判將他無罪釋放。
但是,諸位已經聽到,憲法對我們的要求有些不同。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訂定的條文是:生命是不容許相互衡估輕重的,就算比例懸殊,也絕不可以。這點讓人感到困惑。而我們也該仔細思考,這是我們欠被告與受難者的。
我們根據哪些標準來決定被告是否可以殺人?事實上,我們是根據良心、根據道德、根據常識,以及另一個概念、也就是前國防部長說這是基於職責所採取的「超越法律的緊急手段」,有些法學家稱此為「自然法」。諸位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個名稱是無關緊要的,它所指的是:我們應該依據我們的觀念來判決,它超越法律、比法律還重要,於是觀念取代了法律。問題在於:這是理性的嗎?我知道,你們每一位都認為,他的道德、他的良知值得信賴,但是,這是錯的。
1951年,德國法哲學家漢斯・韋策爾(Hans Welzel)描述了所謂的「扳道工案例」(Weichenstellerfall):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輛載貨火車失速往山谷下的小火車站衝去,而那裡停著一輛滿載乘客的火車,如果載貨火車持續奔馳,那麼會有數百人死亡。請您設想一下,您是鐵道管理員,您可以扳動轉轍器,把載貨火車引到支線軌道上。問題在於,支線軌道上有五名工人正在修復鐵軌。如果您讓火車改道,那麼就會殺害那五名工人,但卻可以拯救數百名乘客。您會怎麼做?您會選擇犧牲那五條人命嗎?
大多數的人確實選擇讓載貨火車改道,而且稍經思考我們會認為這麼做是對的。
但只要條件稍做改變,立刻會變得讓人難以抉擇。1976年,美國法哲學家茱蒂斯・湯姆森(Judith Thomson)提出另一個擴充討論的版本:載貨火車還是一樣在山路上往下疾馳,但這時沒有轉轍器可以讓您轉換火車軌道。身為旁觀者,這時您站在橋上觀看事件發生,但您身邊有個彪形大漢,如果他從橋上掉下去,剛好會落在鐵軌上,雖然他會被火車輾過,但他龐大的身軀卻可以讓火車停下來。只是男人太高太壯,您無法把他推到橋下,您必須先殺了他,例如找把刀做掉他,然後才能把他丟下去,這樣您才能拯救乘客。敬愛的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時,您又會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