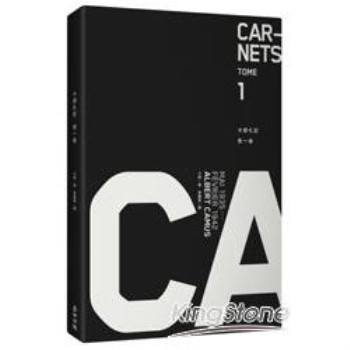第一本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九三七年九月
三五年五月
我要說的是:
人們可能會──非關浪漫地──對過去的苦日子有一種鄉愁。那種一貧如洗的生活過得夠久的話,就會培養出某種敏銳度。在此一特殊情況下,兒子對母親所抱持的那份奇異情感,就成了他整個敏銳度的來源。這種會在各種最不相干的領域裡展現出來的敏銳度,可以透過那些潛伏的記憶,亦即構成他童年的材質(一種緊緊貼在靈魂上的黏膠),而獲得充分的理解。
若果如此,心裡明白的人會心存感激,並感到良心不安。同時,透過比較──如果他的環境已經有所轉換──,會有一種不再富有的感覺。對有錢人來說,天空──而且還是免費的──好像是個理所當然的贈品。窮人才曉得去感激它那種浩瀚無垠的恩慈。
良心不安,就必須告白。作品是一種告白,我需要做出見證。我只想好好地敘述、探討一件事。亦即在那貧困的歲月裡,在那些或卑微或虛榮的人們當中,我曾經真切地觸及了我所認為的生命真諦。這個光靠藝術創作是不夠的。藝術對我而言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個手段。
此外,面對另外那個世界(有錢人的)而感到自慚形穢、軟弱無能和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欽佩景仰,也是重點。我想窮人世界是一種很罕見、甚至是唯一會把自己閉鎖起來的世界,彷彿社會中的一座孤島。在這座島上演魯賓遜,不需要花什麼力氣。非常入戲的人,連提到咫尺外某某醫生的公寓時,都要說那是「那一邊」。
這些全部都要透過母親和兒子兩個角色來表達。
原則上是這樣。
要細論的話,就複雜了:
(一)背景。街區及其居民。
(二)母親及其行事。
(三)母子關係。
如何收尾。母親?末章兒子在鄉愁中體認到了母親的象徵價值???
*
柯尼葉:我們總是瞧不起自己。而貧、病和孤獨:我們意識到了我們的永生。「我們總是必須被到走投無路。」
就是這樣,絲毫不差。
*
「經驗」這個字眼很空乏。經驗不能實驗。經驗不是被激發出來的,我們只能去忍受它。與其說是經驗,還不如稱之為韌性;與其說我們能忍,還不如說我們在受罪。
卻很好用:一旦有了經驗,雖然並非學者,但也算是個專家了。問題是什麼專家?
*
兩個姐妹淘,都病得很厲害。只不過一個是心理上的,還有可能好過來。另一個則是結核末期,只能等死。
一天下午,那個得肺結核的來到女友床前探視,聽見她說:
「妳知道,一直以來,甚至在我病情最告急的時候,我還是覺得自己可以活下去。但如今我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想我已經虛弱到再也起不來了。」
另外一個聽到她這麼說,眼底閃過一抹殘忍的喜色,一面拉起對方的手,「哦!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上路了。」
同樣這兩個女人,一個大限不遠的結核病患,一個就快痊癒了。為此她還前往法國,接受了一種全新的療法。
另一個卻怪起她來。表面上是在怪她棄她遠行,事實上是見不得朋友好起來。之前她一度有種瘋狂的期待,期待不用一個人死,而是拉著最親愛的朋友一起走。她就要孤孤單單地死去了,而這樣的意識在她的友愛中注入了一股可怕的恨意。
*
八月的雷雨天。熱風和烏雲。但東方卻透出一抹晴藍,輕盈而剔透。教人無法直視。這樣的藍,對眼睛和靈魂來說都是一種折磨。 因為美會令人受不了。美讓人萬念俱灰,因為我們是多想要讓這種剎那的永恆一直持續下去。
2
*
他難得一次把心靜下來,感到自在。
*
喜劇的題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種被拋棄、遺世獨立──卻又不至於可憐到備受「他人」的「敬重」──的感覺,可以讓我們從自身最苦的痛楚中解脫出來。這就是為什麼當那種覺得自己實在孤苦伶仃的悲情縈繞不去時,反而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原來幸福往往不過就是一種顧影自憐的感覺罷了。
窮人之不可思議處:上帝讓這群人毫無指望卻又從不反抗,就像祂總是會把解藥放在生病的人旁邊那樣。
*
年輕時,我會向眾生需索他們能力範圍之外的:友誼長存,熱情不滅。
如今,我明白只能要求對方能力範圍之內的:作伴就好,不用說話。而他們的情感、友誼和操守,在我眼中仍然有著奇蹟般的價值:這都是拜寬容之賜。
*
……他們都喝多了,想吃點東西。但那天晚上是除夕,客滿了。人家不接待,他們硬要進去。最後店家只好趕人,身懷六甲的老闆娘還被他們踢了好幾腳。於是老闆──一個瘦弱的金髮青年──便取出他的槍,開了火。子彈射進了那男人右邊的太陽穴。他頭朝著受傷的那邊一歪,倒地不起。一旁的朋友因為酒精作用加上驚嚇過度,竟繞著他的屍體跳起舞來。
整個事件就是這麼簡單,第二天上報後就會結束了。只是,在此當下,在這一區的這個僻靜的角落裡,稀疏的燈光照在雨後泛著油光的路磚上,綿長而潮溼的輪胎痕跡,以及班次不多的電車經過時發出的聲響和光亮,讓整個場景看起來宛如另一個世界般令人不安……當夜色開始在那些巷弄間播上幢幢陰影之際,這一帶便會散發出一股揮之不去的腥甜;偶爾,向晚時分,會有一個沒有名字的黑影,曳著沉悶的腳步和模模糊糊的嘟囔,全身沐浴著血色的榮光,在某個藥局球燈的紅色光芒下冒出來。(待續)三六年一月
窗另一邊的那個院子,我只能看到院牆。還有幾簇上面淌著光的葉片。再上面,還是葉片。更上面,就是太陽了。至於室外空氣中那股可想而知的歡欣鼓舞,那種在這世間到處散播的歡愉,我卻只能從在白窗帘上嬉耍的葉影,以及那五束不厭其煩地為這屋子注入某種乾草的金黃色氣味的日光,領略一二。一陣微風拂過,窗帘上的樹影再度熱絡起來了。一片雲從太陽前面飄過又飄走,於是瓶中的那把金合歡,又從陰影中艷澄澄地躍了出來。這樣就夠了:這道初露的微光,讓我沉浸在一種模模糊糊、令人為之暈眩的喜悅裡。
身為地穴之囚,我在此獨自面對這世界的陰影(地穴之囚出自一則柏拉圖講述的寓言,故事敘述一群被腳鏈銬起來,關在一個巨大的地下洞窟中的囚犯,因為背對著洞口,只能從投映在牆上的影子來認識外界的事物──譯註)。一月的午後。空氣底仍有寒意。到處是薄薄一層、用指甲一掐就會裂開的陽光,但它也讓所有的事物蒙上一朵像是永不凋謝的微笑。我是誰,而我又能幹什麼──除了和那些樹影以及光線一起嬉戲。化身為這道被我的香菸煙霧所繚繞的陽光──這股溫煦和這份在空氣中默默吐納的熱情。如果循著這道光一直過去,我就能找到我自己。如果我試著去理解、去領略這股洩漏了天機的幽香,我就可以在這個宇宙的最深處找到我自己。我自己,亦即此一讓我得以從表象世界解放出來的極度感動。再過一會兒,別的人事物就又要將我擄走了。就讓我在這塊時光布上將這一分鐘剪下來吧!好比有人會把花朵夾在書頁當中一樣。他們想把某次散步時受到愛情眷顧的記憶壓在裡面。我也是,我也在散步,但和我擦肩而過的卻是個神。人生苦短,浪費時間是一種罪。我一整天都在浪費時間,卻被說成很活躍。今天,是該歇一下,我的心就要去找到它自己。
如果我仍然覺得焦慮,那是因為感受到這個難以捉摸的剎那,正如水銀珠般從我的指間滑落。那些要遁世的就讓他們去吧!我既目睹了自己的誕生,便再沒什麼好抱怨的了。能夠活在這個世上,讓我感到很幸福,因為我的王國屬於這個世界。飄過的雲和蒼白的剎那。我自己讓我自己死了。書翻到心愛的那一頁上。這一頁今天在世界這本大書面前,看起來何其索然無味。我若曾經如何地受苦,我今天就如何地離苦。這苦甚至讓我陶醉,因為它就是這光、這影、這熱度,以及這個教人可以遠遠地感覺到、就在空氣深處的陰寒。我還需要去問有沒有什麼東西死了,或有沒有人受苦嗎?既然一切都已經寫在這扇承蒙天地傾其所有的窗戶上了。我可以說,我接下來一定會說,最重要的是保有人性和單純。不,最重要的應該是真,那樣就能涵蓋一切了,包括人性和單純。而還有什麼時候,我會比和世界合而為一之時更真,更剔透呢?
可愛的沉寂時刻。聽不到一點人語響,只有這個世界的天籟在迴盪,而我,被鏈鎖在這個地穴深處,在開始渴望之前,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心滿意足。永恆就在那兒,而我,我期盼著它的到來。現在我可以發言了。我不曉得除了能夠像這樣自我一直面對著自我,我還能希冀什麼更好的。我現在渴望的並非快樂,但求自己不要無知。人們總以為自己和這個世界是隔離的,但只需一株佇立在金色塵埃中的橄欖樹,或晨曦下幾片亮晶晶的沙灘,也許就能讓我們察覺到內心的抗拒正在消解。我於是卸下了自己的心防。我意識到了哪些可能性只能由自己作主。生命中的每一分鐘裡都蘊藏了奇蹟,都有一個永垂不朽的青春臉孔。
*
人習慣用影像思考。如果你想成為哲學家,就去寫小說。(待續) 第二部
(《快樂的死》〔La Mort Heureuse〕的寫作藍圖。《快樂的死》是卡繆的第一部小說,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但直到一九七一年卡繆死後由加利瑪〔Gallimard〕出版社出版,收錄在《卡繆作品集卷一》〔Cahiers Albert Camus, I〕中──原編註)
A:現在
B:過去
第一章之A──臨世之屋。背景描述。
第一章之B──他記得。和露西安的交往。
第二章之A──臨世之屋。他的童年。
第二章之B──露西安承認不忠。
第三章之A──臨世之屋。受邀。
第四章之B──醋勁。薩爾斯堡(Salzbourg)。布拉格。
第四章之A──臨世之屋。太陽。
第五章之B──逃亡(信)。阿爾及爾。著涼,生病,
第五章之A──臨星之夜。凱瑟琳。
*
帕提斯(帕提斯‧梅爾索〔Patrice Mersault〕是「快樂的死」的男主角。這個死刑犯的題材後來出現在《異鄉人》中──原編註)的死刑犯故事:「我看得到他,這個人。他就在我體內。他的每一句話都讓我心痛。他是活生生的,跟著我一起呼吸。跟著我一起恐懼。」
「……還有另外那個想讓他屈服的。我發現他也活著,也住在我的裡面。我每天都會讓傳教士去見他,想讓他軟化下來。」
「我現在知道我會把這些都寫下來。一棵樹,歷經那麼多苦難,最後總要結出果子來。每個冬天的句點都是春暖花開。我需要留下見證。儘管這樣的循環又會週而復始。」
「……我只想表達我對生命的熱愛。但會用自己的方式講出來……」
「別人寫作,是基於遲發性的誘惑。他們人生中的每一個失落,都可以是一部藝術作品,一個用他們生命中的謊言編織起來的謊言。至於我,從我筆下流露出來的將會是我的幸福快樂。即使這其中不乏殘酷的成分。我需要寫作就像我需要游泳,這是一種生理上的需求。」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九三七年九月
三五年五月
我要說的是:
人們可能會──非關浪漫地──對過去的苦日子有一種鄉愁。那種一貧如洗的生活過得夠久的話,就會培養出某種敏銳度。在此一特殊情況下,兒子對母親所抱持的那份奇異情感,就成了他整個敏銳度的來源。這種會在各種最不相干的領域裡展現出來的敏銳度,可以透過那些潛伏的記憶,亦即構成他童年的材質(一種緊緊貼在靈魂上的黏膠),而獲得充分的理解。
若果如此,心裡明白的人會心存感激,並感到良心不安。同時,透過比較──如果他的環境已經有所轉換──,會有一種不再富有的感覺。對有錢人來說,天空──而且還是免費的──好像是個理所當然的贈品。窮人才曉得去感激它那種浩瀚無垠的恩慈。
良心不安,就必須告白。作品是一種告白,我需要做出見證。我只想好好地敘述、探討一件事。亦即在那貧困的歲月裡,在那些或卑微或虛榮的人們當中,我曾經真切地觸及了我所認為的生命真諦。這個光靠藝術創作是不夠的。藝術對我而言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個手段。
此外,面對另外那個世界(有錢人的)而感到自慚形穢、軟弱無能和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欽佩景仰,也是重點。我想窮人世界是一種很罕見、甚至是唯一會把自己閉鎖起來的世界,彷彿社會中的一座孤島。在這座島上演魯賓遜,不需要花什麼力氣。非常入戲的人,連提到咫尺外某某醫生的公寓時,都要說那是「那一邊」。
這些全部都要透過母親和兒子兩個角色來表達。
原則上是這樣。
要細論的話,就複雜了:
(一)背景。街區及其居民。
(二)母親及其行事。
(三)母子關係。
如何收尾。母親?末章兒子在鄉愁中體認到了母親的象徵價值???
*
柯尼葉:我們總是瞧不起自己。而貧、病和孤獨:我們意識到了我們的永生。「我們總是必須被到走投無路。」
就是這樣,絲毫不差。
*
「經驗」這個字眼很空乏。經驗不能實驗。經驗不是被激發出來的,我們只能去忍受它。與其說是經驗,還不如稱之為韌性;與其說我們能忍,還不如說我們在受罪。
卻很好用:一旦有了經驗,雖然並非學者,但也算是個專家了。問題是什麼專家?
*
兩個姐妹淘,都病得很厲害。只不過一個是心理上的,還有可能好過來。另一個則是結核末期,只能等死。
一天下午,那個得肺結核的來到女友床前探視,聽見她說:
「妳知道,一直以來,甚至在我病情最告急的時候,我還是覺得自己可以活下去。但如今我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想我已經虛弱到再也起不來了。」
另外一個聽到她這麼說,眼底閃過一抹殘忍的喜色,一面拉起對方的手,「哦!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上路了。」
同樣這兩個女人,一個大限不遠的結核病患,一個就快痊癒了。為此她還前往法國,接受了一種全新的療法。
另一個卻怪起她來。表面上是在怪她棄她遠行,事實上是見不得朋友好起來。之前她一度有種瘋狂的期待,期待不用一個人死,而是拉著最親愛的朋友一起走。她就要孤孤單單地死去了,而這樣的意識在她的友愛中注入了一股可怕的恨意。
*
八月的雷雨天。熱風和烏雲。但東方卻透出一抹晴藍,輕盈而剔透。教人無法直視。這樣的藍,對眼睛和靈魂來說都是一種折磨。 因為美會令人受不了。美讓人萬念俱灰,因為我們是多想要讓這種剎那的永恆一直持續下去。
2
*
他難得一次把心靜下來,感到自在。
*
喜劇的題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種被拋棄、遺世獨立──卻又不至於可憐到備受「他人」的「敬重」──的感覺,可以讓我們從自身最苦的痛楚中解脫出來。這就是為什麼當那種覺得自己實在孤苦伶仃的悲情縈繞不去時,反而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原來幸福往往不過就是一種顧影自憐的感覺罷了。
窮人之不可思議處:上帝讓這群人毫無指望卻又從不反抗,就像祂總是會把解藥放在生病的人旁邊那樣。
*
年輕時,我會向眾生需索他們能力範圍之外的:友誼長存,熱情不滅。
如今,我明白只能要求對方能力範圍之內的:作伴就好,不用說話。而他們的情感、友誼和操守,在我眼中仍然有著奇蹟般的價值:這都是拜寬容之賜。
*
……他們都喝多了,想吃點東西。但那天晚上是除夕,客滿了。人家不接待,他們硬要進去。最後店家只好趕人,身懷六甲的老闆娘還被他們踢了好幾腳。於是老闆──一個瘦弱的金髮青年──便取出他的槍,開了火。子彈射進了那男人右邊的太陽穴。他頭朝著受傷的那邊一歪,倒地不起。一旁的朋友因為酒精作用加上驚嚇過度,竟繞著他的屍體跳起舞來。
整個事件就是這麼簡單,第二天上報後就會結束了。只是,在此當下,在這一區的這個僻靜的角落裡,稀疏的燈光照在雨後泛著油光的路磚上,綿長而潮溼的輪胎痕跡,以及班次不多的電車經過時發出的聲響和光亮,讓整個場景看起來宛如另一個世界般令人不安……當夜色開始在那些巷弄間播上幢幢陰影之際,這一帶便會散發出一股揮之不去的腥甜;偶爾,向晚時分,會有一個沒有名字的黑影,曳著沉悶的腳步和模模糊糊的嘟囔,全身沐浴著血色的榮光,在某個藥局球燈的紅色光芒下冒出來。(待續)三六年一月
窗另一邊的那個院子,我只能看到院牆。還有幾簇上面淌著光的葉片。再上面,還是葉片。更上面,就是太陽了。至於室外空氣中那股可想而知的歡欣鼓舞,那種在這世間到處散播的歡愉,我卻只能從在白窗帘上嬉耍的葉影,以及那五束不厭其煩地為這屋子注入某種乾草的金黃色氣味的日光,領略一二。一陣微風拂過,窗帘上的樹影再度熱絡起來了。一片雲從太陽前面飄過又飄走,於是瓶中的那把金合歡,又從陰影中艷澄澄地躍了出來。這樣就夠了:這道初露的微光,讓我沉浸在一種模模糊糊、令人為之暈眩的喜悅裡。
身為地穴之囚,我在此獨自面對這世界的陰影(地穴之囚出自一則柏拉圖講述的寓言,故事敘述一群被腳鏈銬起來,關在一個巨大的地下洞窟中的囚犯,因為背對著洞口,只能從投映在牆上的影子來認識外界的事物──譯註)。一月的午後。空氣底仍有寒意。到處是薄薄一層、用指甲一掐就會裂開的陽光,但它也讓所有的事物蒙上一朵像是永不凋謝的微笑。我是誰,而我又能幹什麼──除了和那些樹影以及光線一起嬉戲。化身為這道被我的香菸煙霧所繚繞的陽光──這股溫煦和這份在空氣中默默吐納的熱情。如果循著這道光一直過去,我就能找到我自己。如果我試著去理解、去領略這股洩漏了天機的幽香,我就可以在這個宇宙的最深處找到我自己。我自己,亦即此一讓我得以從表象世界解放出來的極度感動。再過一會兒,別的人事物就又要將我擄走了。就讓我在這塊時光布上將這一分鐘剪下來吧!好比有人會把花朵夾在書頁當中一樣。他們想把某次散步時受到愛情眷顧的記憶壓在裡面。我也是,我也在散步,但和我擦肩而過的卻是個神。人生苦短,浪費時間是一種罪。我一整天都在浪費時間,卻被說成很活躍。今天,是該歇一下,我的心就要去找到它自己。
如果我仍然覺得焦慮,那是因為感受到這個難以捉摸的剎那,正如水銀珠般從我的指間滑落。那些要遁世的就讓他們去吧!我既目睹了自己的誕生,便再沒什麼好抱怨的了。能夠活在這個世上,讓我感到很幸福,因為我的王國屬於這個世界。飄過的雲和蒼白的剎那。我自己讓我自己死了。書翻到心愛的那一頁上。這一頁今天在世界這本大書面前,看起來何其索然無味。我若曾經如何地受苦,我今天就如何地離苦。這苦甚至讓我陶醉,因為它就是這光、這影、這熱度,以及這個教人可以遠遠地感覺到、就在空氣深處的陰寒。我還需要去問有沒有什麼東西死了,或有沒有人受苦嗎?既然一切都已經寫在這扇承蒙天地傾其所有的窗戶上了。我可以說,我接下來一定會說,最重要的是保有人性和單純。不,最重要的應該是真,那樣就能涵蓋一切了,包括人性和單純。而還有什麼時候,我會比和世界合而為一之時更真,更剔透呢?
可愛的沉寂時刻。聽不到一點人語響,只有這個世界的天籟在迴盪,而我,被鏈鎖在這個地穴深處,在開始渴望之前,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心滿意足。永恆就在那兒,而我,我期盼著它的到來。現在我可以發言了。我不曉得除了能夠像這樣自我一直面對著自我,我還能希冀什麼更好的。我現在渴望的並非快樂,但求自己不要無知。人們總以為自己和這個世界是隔離的,但只需一株佇立在金色塵埃中的橄欖樹,或晨曦下幾片亮晶晶的沙灘,也許就能讓我們察覺到內心的抗拒正在消解。我於是卸下了自己的心防。我意識到了哪些可能性只能由自己作主。生命中的每一分鐘裡都蘊藏了奇蹟,都有一個永垂不朽的青春臉孔。
*
人習慣用影像思考。如果你想成為哲學家,就去寫小說。(待續) 第二部
(《快樂的死》〔La Mort Heureuse〕的寫作藍圖。《快樂的死》是卡繆的第一部小說,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但直到一九七一年卡繆死後由加利瑪〔Gallimard〕出版社出版,收錄在《卡繆作品集卷一》〔Cahiers Albert Camus, I〕中──原編註)
A:現在
B:過去
第一章之A──臨世之屋。背景描述。
第一章之B──他記得。和露西安的交往。
第二章之A──臨世之屋。他的童年。
第二章之B──露西安承認不忠。
第三章之A──臨世之屋。受邀。
第四章之B──醋勁。薩爾斯堡(Salzbourg)。布拉格。
第四章之A──臨世之屋。太陽。
第五章之B──逃亡(信)。阿爾及爾。著涼,生病,
第五章之A──臨星之夜。凱瑟琳。
*
帕提斯(帕提斯‧梅爾索〔Patrice Mersault〕是「快樂的死」的男主角。這個死刑犯的題材後來出現在《異鄉人》中──原編註)的死刑犯故事:「我看得到他,這個人。他就在我體內。他的每一句話都讓我心痛。他是活生生的,跟著我一起呼吸。跟著我一起恐懼。」
「……還有另外那個想讓他屈服的。我發現他也活著,也住在我的裡面。我每天都會讓傳教士去見他,想讓他軟化下來。」
「我現在知道我會把這些都寫下來。一棵樹,歷經那麼多苦難,最後總要結出果子來。每個冬天的句點都是春暖花開。我需要留下見證。儘管這樣的循環又會週而復始。」
「……我只想表達我對生命的熱愛。但會用自己的方式講出來……」
「別人寫作,是基於遲發性的誘惑。他們人生中的每一個失落,都可以是一部藝術作品,一個用他們生命中的謊言編織起來的謊言。至於我,從我筆下流露出來的將會是我的幸福快樂。即使這其中不乏殘酷的成分。我需要寫作就像我需要游泳,這是一種生理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