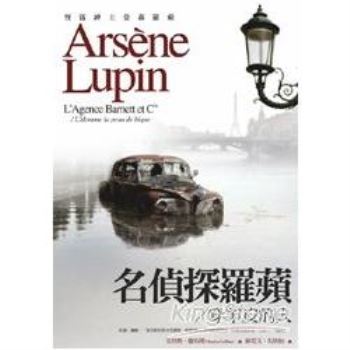聖日爾曼區裡,亞塞曼男爵夫人大宅前院的門鈴響起。幾乎就在鈴響的同時,女僕拿著一只信封走了進來。
「夫人四點鐘約見的先生到了。」
亞塞曼夫人拆開信封,閱讀印在名片上的字樣:「巴內特偵探社,免費諮詢。」
「帶這位先生到我的小客廳裡去。」
薇樂莉啊!三十多年來,人們一直稱她為「美人兒薇樂莉」,她如今雖然身形豐腴,風采大不如前,卻仍衣著華麗而裝扮講究,保持著十足架勢。她的臉龐總是帶著高傲的神情,偶爾略顯嚴肅,但是,在大多數時候依舊會流露出迷人的純真之美。亞塞曼夫人身為銀行家的妻子,自然以丈夫奢華的生活、豐富的人脈、豪宅美邸,以及與自己相關的一切為傲。然而,社交圈曾經針對她的幾樁韻事傳出流言蜚語,甚至言之鑿鑿地指稱男爵一度有意與她離婚。
夫人先來到亞塞曼男爵房裡探視年邁的丈夫,男爵的身體十分虛弱,幾次心臟病發作,讓他臥床休養了好幾個星期。她開口詢問丈夫的狀況,一邊漫不經心地調整他背後的靠枕。
男爵喃喃地問道:「剛剛是不是有人按電鈴?」
「是啊,」她回答:「是朋友推薦的私家偵探,來處理我們的事。據說,他的能力很強。」
「那最好。」這位銀行家說:「這件事讓我放不下心,不管我怎麼想,都還是想不通。」
薇樂莉同樣擔憂,她離開房間來到小客廳。廳裡有個怪異的男人,他的體型魁梧,肩膀壯碩,看來十分結實,但是他身上穿了件正式外套,顏色是偏綠的墨黑,布料卻像雨傘面似地閃著光。他的五官粗獷深邃,充滿了活力,看似年輕,但宛如紅磚般粗糙又泛紅的皮膚卻破壞了整體印象。他的眼神冷漠,目光帶著譏諷,唯一能為這男人增添些許活潑戲謔效果的,是一只可以左右兩側互換配戴的單邊眼鏡。
「您是巴內特先生嗎?」她問道。
他上前一傾身,男爵夫人還不及縮回方才朝男人伸去的手,他便以流暢的動作親吻了夫人的手,接著輕輕一咂舌,幾乎沒發出聲響,彷彿正在回味夫人手腕上的香味。
「在下吉姆‧巴內特,竭誠為您服務,男爵夫人。我收到您的信,只來得及刷刷大衣,就急忙趕了過來。」
夫人愣住了,不知是否該將眼前這名冒犯她的魯莽男子趕出門外。但是他表現出從容不迫的紳士風範,完全符合社交圈的禮節,她只好接著說:「我聽說您經常為人處理棘手事件……」
他露出自負的微笑,說:「這是我的天賦,我就是有洞悉事物的能力。」
他音調溫和,語氣卻不容旁人置疑,說話時還帶著隱約的嘲諷和揶揄。他自信滿滿,對自己的能力有十足把握,似乎任何人都無法左右他。薇樂莉發現,儘管他態度粗魯,自己卻在一瞬間便接受了這名陌生偵探的說法。但她仍然想扳回一些優勢,於是譏諷地說:「也許,我們最好先談好條件。」
「不必多此一舉。」巴內特回答。
「但是,」這會兒輪到她笑著說:「您總不會光求名聲而不計報酬吧?」
「男爵夫人,巴內特偵探社的服務完全免費。」
她明顯開始氣惱起來。
「我寧可讓雙方保持收費計酬的關係。」
「說不定還可以賞點小費?」他冷笑回應。
她仍然堅持地說:「我總不能……」
「欠我人情嗎?任何美麗的女士都不可能虧欠任何人。」
為了緩和這番略嫌放肆的輕佻言語,他隨即補充道:「更何況,您不必擔心的,男爵夫人,無論在下提供哪些服務,都有辦法讓兩造互不相欠。」
這句模稜兩可的話是什麼意思?這名私家偵探難道自有方式索酬?那會是怎樣的性質?
薇樂莉不自在地打起哆嗦,臉色泛紅。這位巴內特先生讓她不安,說真的,這種感覺和面對盜賊沒什麼兩樣。她心想:天哪,說不定他是個仰慕者,選擇用這種與眾不同的方式來接近她。這要怎麼分辨呢?再說,她該如何應對?屈居劣勢的薇樂莉感到慌亂,然而,她同時也信任這個男人,完全願意接受後續的發展。因此,當巴內特開口詢問她需要偵探社協助的理由時,她便遵從他的要求,毫無保留地細說緣由。男爵夫人沒花多少時間解釋,因為巴內特先生似乎是個缺乏耐心的人。
「事情發生在十天前的星期日,」她說:「我約了幾個朋友打橋牌。當晚我早早就寢,而且和往常一樣很快就入睡。凌晨四點左右——正確的時間是四點十分,我聽到聲響醒了過來,隨後我又聽見了像是關門的聲音,聲音是從我的小客廳傳過來的。」
「也就是說,在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巴內特打斷男爵夫人的話。
「是的,這個小客廳一邊和我的寢室相連,」這時巴內特莊重地朝夫人的寢室方向欠身致意,「一邊則通往走廊,再過去便是傭人使用的樓梯。我不是個膽小的人,於是等了一會兒之後,便下床打算查看。」
巴內特聽到這番話,對著想像中男爵夫人跳下床的景象再次致意。
「這麼說,」他說:「您下床去……」
「我先下床,然後進到小客廳開燈。廳裡沒有人,卻見這座小玻璃櫃倒在地上,裡面的擺飾和小雕像四處散落,其中有些物品還摔壞了。接著,我走到我丈夫的臥室,發現他在床上看書,而且表示自己什麼也沒聽到。他急忙按鈴叫來宅邸的總管,總管隨即開始搜查,警方也在隔天早上接手調查。」
「調查結果如何?」巴內特追問。
「是這樣的,我們完全找不出跡象,不知道這個神祕客怎麼進出宅邸,這簡直是個難解之謎。不過,我們在軟墊下某個摔破的擺飾碎片當中找到半截蠟燭和一把骯髒的木把椎鑿。此外,我們也知道在前一天的下午,有個水電工人到家裡來修理我丈夫浴室裡的洗手台水龍頭。所以警方詢問了水電行老闆,他認出工具為他們所有,我們也在水電行裡找出另一截蠟燭。」
「所以說,」吉姆‧巴內特問:「這條線索很明確囉?」
「沒錯,但是這卻和另一件明確的事實有所抵觸,讓人著實摸不著頭腦。根據調查,警方查出這名水電工在當天傍晚六點鐘搭乘快車前往布魯塞爾,大約在午夜時分——也就是說,在事件發生的三個小時之前——早已抵達當地。」
「怎麼會!這名水電工有沒有回到巴黎呀?」
「沒有。他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大肆揮霍之後,便失去了蹤影。」
「就這樣?」
「就只有這樣。」
「負責調查這案子的是哪位警探?」
「貝舒警探。」
巴內特顯得十分高興。
「貝舒嗎?哈!好傢伙貝舒!男爵夫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經常合作。」
「事實上,就是他向我提起巴內特偵探社的。」
「也許是因為他沒有進展,對吧?」
「有可能。」
「這個好貝舒啊!我真的很樂意幫他的忙!對您也一樣,男爵夫人,請相信我,我更樂於為您提供服務!」
巴內特走向窗邊,用手撐著前額,站著思考了好一會兒。他掄起手指輕敲玻璃,吹著口哨,這是首輕快的舞曲。最後,他終於走回亞塞曼夫人身邊,開口說:「依據貝舒的看法—也就是您的想法,夫人,你們都認為有人試圖行竊,對吧?」
「對,試圖行竊未果,因為家中的財物並沒有短少。」
「我們暫且接受這個推斷好了。但無論如何,竊賊總應該有個確切的目標,而且您一定清楚。目標是什麼東西?」
「我不曉得。」薇樂莉回答之前稍有猶豫。
私家偵探巴內特露出微笑。「男爵夫人,請容我聳個肩表示懷疑好嗎?」
小客廳的踢腳板上方是編布壁板牆,巴內特沒等夫人回答,嘲諷地指向其中一片飾板。
「這片飾板後面有什麼東西?」他的口氣,彷彿在質問一個藏起玩具的小孩。
「沒有啊,」她狼狽地說:「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啊,男爵夫人,只有高明的偵探才有能力看出這片長方形飾板的編布顯得較舊,看起來,有些部分已經從木作邊框脫了開來,我理所當然會懷疑這後面是不是藏著個保險箱。」
薇樂莉打了個寒顫,迷惑著巴內特先生怎麼可能光憑如此隱晦的線索看出這件事?她一把推開巴內特所指的壁板,露出後方一小扇鋼門。夫人焦躁地解除門上的三道鎖,心裡也突然湧現一波不安的情緒。她明知不可能,卻仍忍不住猜疑,剛才這名怪異偵探獨自在小客廳裡待了幾分鐘,難不成他已趁機將保險箱洗劫一空?
她掏出口袋裡的鑰匙打開保險箱門,開啟之後,她隨即露出安心的微笑。保險箱裡只有一件物品——一件美麗絕倫的珍珠項鍊,她急匆匆地拿起項鍊,讓三股珠鍊垂落在她的手腕上。
巴內特先生笑了。「您這會兒可放心了,男爵夫人啊!但只要是竊賊,必定手巧又大膽!您要小心哪,男爵夫人,畢竟說真的,這條項鍊實在是極品,我可以瞭解為什麼會有人想把它從您身邊偷走。」
她駁斥這個說法。「但是項鍊沒有遭竊,也許真的有人想偷,但是沒有得逞。」
「您真的這樣想嗎,男爵夫人?」
「正是!因為項鍊不就好端端地放在這裡嗎?我還拿在手上呢!如果真被偷走,怎麼可能還在?」
巴內特語氣和緩地糾正她。「您手上拿著一條項鍊沒錯,但是您能確定這真的是您那條項鍊嗎?您確定這條項鍊真的價值連城嗎?」
「什麼話!」她惱怒地說:「十五天前,我的珠寶商才剛為項鍊鑑定,估計價值至少有五十萬法郎。」
「十五天前——也就是說,在發生事件那個夜晚的五天之前。但現在還是如此嗎?的確,我哪裡會知道哩,我又不是什麼珠寶鑑定專家,純粹猜測罷了。請問夫人,您難道仍是這般確定,一點也沒有懷疑?」
薇樂莉一愣,頓時無法動彈。他所謂的懷疑是指什麼呢?巴內特令人厭惡的堅持讓她既惶恐又焦慮。她掂了掂掌心上沉甸甸的珍珠,突然覺得珍珠似乎越來越輕。她左看右看,仔細審視珍珠項鍊,珠串的顏色彷彿不同了,她認不出折射的光澤,這條項鍊的相似度驚人,和她的幾乎同樣完美,所有的細節也幾可亂真。真相從她心裡最陰暗的角落慢慢浮現,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駭人。
「夫人四點鐘約見的先生到了。」
亞塞曼夫人拆開信封,閱讀印在名片上的字樣:「巴內特偵探社,免費諮詢。」
「帶這位先生到我的小客廳裡去。」
薇樂莉啊!三十多年來,人們一直稱她為「美人兒薇樂莉」,她如今雖然身形豐腴,風采大不如前,卻仍衣著華麗而裝扮講究,保持著十足架勢。她的臉龐總是帶著高傲的神情,偶爾略顯嚴肅,但是,在大多數時候依舊會流露出迷人的純真之美。亞塞曼夫人身為銀行家的妻子,自然以丈夫奢華的生活、豐富的人脈、豪宅美邸,以及與自己相關的一切為傲。然而,社交圈曾經針對她的幾樁韻事傳出流言蜚語,甚至言之鑿鑿地指稱男爵一度有意與她離婚。
夫人先來到亞塞曼男爵房裡探視年邁的丈夫,男爵的身體十分虛弱,幾次心臟病發作,讓他臥床休養了好幾個星期。她開口詢問丈夫的狀況,一邊漫不經心地調整他背後的靠枕。
男爵喃喃地問道:「剛剛是不是有人按電鈴?」
「是啊,」她回答:「是朋友推薦的私家偵探,來處理我們的事。據說,他的能力很強。」
「那最好。」這位銀行家說:「這件事讓我放不下心,不管我怎麼想,都還是想不通。」
薇樂莉同樣擔憂,她離開房間來到小客廳。廳裡有個怪異的男人,他的體型魁梧,肩膀壯碩,看來十分結實,但是他身上穿了件正式外套,顏色是偏綠的墨黑,布料卻像雨傘面似地閃著光。他的五官粗獷深邃,充滿了活力,看似年輕,但宛如紅磚般粗糙又泛紅的皮膚卻破壞了整體印象。他的眼神冷漠,目光帶著譏諷,唯一能為這男人增添些許活潑戲謔效果的,是一只可以左右兩側互換配戴的單邊眼鏡。
「您是巴內特先生嗎?」她問道。
他上前一傾身,男爵夫人還不及縮回方才朝男人伸去的手,他便以流暢的動作親吻了夫人的手,接著輕輕一咂舌,幾乎沒發出聲響,彷彿正在回味夫人手腕上的香味。
「在下吉姆‧巴內特,竭誠為您服務,男爵夫人。我收到您的信,只來得及刷刷大衣,就急忙趕了過來。」
夫人愣住了,不知是否該將眼前這名冒犯她的魯莽男子趕出門外。但是他表現出從容不迫的紳士風範,完全符合社交圈的禮節,她只好接著說:「我聽說您經常為人處理棘手事件……」
他露出自負的微笑,說:「這是我的天賦,我就是有洞悉事物的能力。」
他音調溫和,語氣卻不容旁人置疑,說話時還帶著隱約的嘲諷和揶揄。他自信滿滿,對自己的能力有十足把握,似乎任何人都無法左右他。薇樂莉發現,儘管他態度粗魯,自己卻在一瞬間便接受了這名陌生偵探的說法。但她仍然想扳回一些優勢,於是譏諷地說:「也許,我們最好先談好條件。」
「不必多此一舉。」巴內特回答。
「但是,」這會兒輪到她笑著說:「您總不會光求名聲而不計報酬吧?」
「男爵夫人,巴內特偵探社的服務完全免費。」
她明顯開始氣惱起來。
「我寧可讓雙方保持收費計酬的關係。」
「說不定還可以賞點小費?」他冷笑回應。
她仍然堅持地說:「我總不能……」
「欠我人情嗎?任何美麗的女士都不可能虧欠任何人。」
為了緩和這番略嫌放肆的輕佻言語,他隨即補充道:「更何況,您不必擔心的,男爵夫人,無論在下提供哪些服務,都有辦法讓兩造互不相欠。」
這句模稜兩可的話是什麼意思?這名私家偵探難道自有方式索酬?那會是怎樣的性質?
薇樂莉不自在地打起哆嗦,臉色泛紅。這位巴內特先生讓她不安,說真的,這種感覺和面對盜賊沒什麼兩樣。她心想:天哪,說不定他是個仰慕者,選擇用這種與眾不同的方式來接近她。這要怎麼分辨呢?再說,她該如何應對?屈居劣勢的薇樂莉感到慌亂,然而,她同時也信任這個男人,完全願意接受後續的發展。因此,當巴內特開口詢問她需要偵探社協助的理由時,她便遵從他的要求,毫無保留地細說緣由。男爵夫人沒花多少時間解釋,因為巴內特先生似乎是個缺乏耐心的人。
「事情發生在十天前的星期日,」她說:「我約了幾個朋友打橋牌。當晚我早早就寢,而且和往常一樣很快就入睡。凌晨四點左右——正確的時間是四點十分,我聽到聲響醒了過來,隨後我又聽見了像是關門的聲音,聲音是從我的小客廳傳過來的。」
「也就是說,在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巴內特打斷男爵夫人的話。
「是的,這個小客廳一邊和我的寢室相連,」這時巴內特莊重地朝夫人的寢室方向欠身致意,「一邊則通往走廊,再過去便是傭人使用的樓梯。我不是個膽小的人,於是等了一會兒之後,便下床打算查看。」
巴內特聽到這番話,對著想像中男爵夫人跳下床的景象再次致意。
「這麼說,」他說:「您下床去……」
「我先下床,然後進到小客廳開燈。廳裡沒有人,卻見這座小玻璃櫃倒在地上,裡面的擺飾和小雕像四處散落,其中有些物品還摔壞了。接著,我走到我丈夫的臥室,發現他在床上看書,而且表示自己什麼也沒聽到。他急忙按鈴叫來宅邸的總管,總管隨即開始搜查,警方也在隔天早上接手調查。」
「調查結果如何?」巴內特追問。
「是這樣的,我們完全找不出跡象,不知道這個神祕客怎麼進出宅邸,這簡直是個難解之謎。不過,我們在軟墊下某個摔破的擺飾碎片當中找到半截蠟燭和一把骯髒的木把椎鑿。此外,我們也知道在前一天的下午,有個水電工人到家裡來修理我丈夫浴室裡的洗手台水龍頭。所以警方詢問了水電行老闆,他認出工具為他們所有,我們也在水電行裡找出另一截蠟燭。」
「所以說,」吉姆‧巴內特問:「這條線索很明確囉?」
「沒錯,但是這卻和另一件明確的事實有所抵觸,讓人著實摸不著頭腦。根據調查,警方查出這名水電工在當天傍晚六點鐘搭乘快車前往布魯塞爾,大約在午夜時分——也就是說,在事件發生的三個小時之前——早已抵達當地。」
「怎麼會!這名水電工有沒有回到巴黎呀?」
「沒有。他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大肆揮霍之後,便失去了蹤影。」
「就這樣?」
「就只有這樣。」
「負責調查這案子的是哪位警探?」
「貝舒警探。」
巴內特顯得十分高興。
「貝舒嗎?哈!好傢伙貝舒!男爵夫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經常合作。」
「事實上,就是他向我提起巴內特偵探社的。」
「也許是因為他沒有進展,對吧?」
「有可能。」
「這個好貝舒啊!我真的很樂意幫他的忙!對您也一樣,男爵夫人,請相信我,我更樂於為您提供服務!」
巴內特走向窗邊,用手撐著前額,站著思考了好一會兒。他掄起手指輕敲玻璃,吹著口哨,這是首輕快的舞曲。最後,他終於走回亞塞曼夫人身邊,開口說:「依據貝舒的看法—也就是您的想法,夫人,你們都認為有人試圖行竊,對吧?」
「對,試圖行竊未果,因為家中的財物並沒有短少。」
「我們暫且接受這個推斷好了。但無論如何,竊賊總應該有個確切的目標,而且您一定清楚。目標是什麼東西?」
「我不曉得。」薇樂莉回答之前稍有猶豫。
私家偵探巴內特露出微笑。「男爵夫人,請容我聳個肩表示懷疑好嗎?」
小客廳的踢腳板上方是編布壁板牆,巴內特沒等夫人回答,嘲諷地指向其中一片飾板。
「這片飾板後面有什麼東西?」他的口氣,彷彿在質問一個藏起玩具的小孩。
「沒有啊,」她狼狽地說:「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啊,男爵夫人,只有高明的偵探才有能力看出這片長方形飾板的編布顯得較舊,看起來,有些部分已經從木作邊框脫了開來,我理所當然會懷疑這後面是不是藏著個保險箱。」
薇樂莉打了個寒顫,迷惑著巴內特先生怎麼可能光憑如此隱晦的線索看出這件事?她一把推開巴內特所指的壁板,露出後方一小扇鋼門。夫人焦躁地解除門上的三道鎖,心裡也突然湧現一波不安的情緒。她明知不可能,卻仍忍不住猜疑,剛才這名怪異偵探獨自在小客廳裡待了幾分鐘,難不成他已趁機將保險箱洗劫一空?
她掏出口袋裡的鑰匙打開保險箱門,開啟之後,她隨即露出安心的微笑。保險箱裡只有一件物品——一件美麗絕倫的珍珠項鍊,她急匆匆地拿起項鍊,讓三股珠鍊垂落在她的手腕上。
巴內特先生笑了。「您這會兒可放心了,男爵夫人啊!但只要是竊賊,必定手巧又大膽!您要小心哪,男爵夫人,畢竟說真的,這條項鍊實在是極品,我可以瞭解為什麼會有人想把它從您身邊偷走。」
她駁斥這個說法。「但是項鍊沒有遭竊,也許真的有人想偷,但是沒有得逞。」
「您真的這樣想嗎,男爵夫人?」
「正是!因為項鍊不就好端端地放在這裡嗎?我還拿在手上呢!如果真被偷走,怎麼可能還在?」
巴內特語氣和緩地糾正她。「您手上拿著一條項鍊沒錯,但是您能確定這真的是您那條項鍊嗎?您確定這條項鍊真的價值連城嗎?」
「什麼話!」她惱怒地說:「十五天前,我的珠寶商才剛為項鍊鑑定,估計價值至少有五十萬法郎。」
「十五天前——也就是說,在發生事件那個夜晚的五天之前。但現在還是如此嗎?的確,我哪裡會知道哩,我又不是什麼珠寶鑑定專家,純粹猜測罷了。請問夫人,您難道仍是這般確定,一點也沒有懷疑?」
薇樂莉一愣,頓時無法動彈。他所謂的懷疑是指什麼呢?巴內特令人厭惡的堅持讓她既惶恐又焦慮。她掂了掂掌心上沉甸甸的珍珠,突然覺得珍珠似乎越來越輕。她左看右看,仔細審視珍珠項鍊,珠串的顏色彷彿不同了,她認不出折射的光澤,這條項鍊的相似度驚人,和她的幾乎同樣完美,所有的細節也幾可亂真。真相從她心裡最陰暗的角落慢慢浮現,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