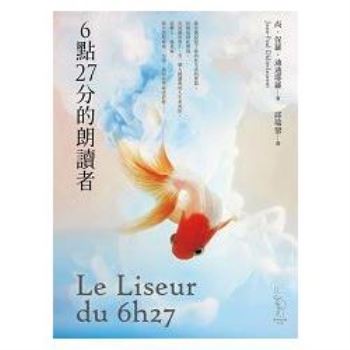1
有人一生下來就是聾子、瞎子或啞巴。有人一生下來就是斜視、兔唇或是在臉面正中央有塊胎記。還有一些人是帶著畸形足來到世間,甚至有一只肢體在還沒生之前就已經死了的。至於季朗.威紐爾(Guylain Vignolles)這個人,他在他出生時必須背負的重擔則是他的姓名,因為他姓和名的前半互調,念來就成了「威朗.季紐爾」(Vilan Guignol),這在法文中的意思就是「醜陋的布偶」。這種討人厭的文字遊戲,從他踏出人生的第一步開始就一直緊緊跟隨著他,永不離開。
他的父母親在一九七六年時,不選日曆上每天都有不同聖人名字來作為兒子的名字,而選了不知從哪兒來的「季朗」這個名字,想都沒想他們這麼一取名,將會為兒子帶來不幸。怪的是,他雖然很好奇父母親為什麼會幫他取這個名字,但他從來不敢問起。也許是擔心會讓自己的父母尷尬。當然也擔心答案其實很普通,解不了他的惑。有時候,他喜歡想像自己如果叫做呂卡、察維耶,或是叫做雨果,人生不知道會不會有不同。甚至如果叫做「季斯朗」都能讓他很開心。季斯朗.威紐爾,一個真正的名字,可以讓他在不傷人的六個音節後面,打造自己的身與心。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他的整個童年時期都是在煩人的姓與名前半互調的文字遊戲中度過,「醜陋的布偶」與他形影不離。直到他三十六歲那年,他終於學會了讓別人忘記自己,讓自己成為一個隱形人,免得一有別人注意到他,他就成為嘲笑、揶揄的對象。他長得既不帥也不醜,不胖也不瘦,只是別人眼角裡不經意撇到的一抹模糊的陰影。他讓自己融入在所處的背景中,甚至直到否認自己,以便自己成為一個從未有人造訪的他方。這麼些年來,季朗.威紐爾就是努力讓自己不存在,只除了這裡,在這個陰暗的車站裡,這個他每天早上必須抵達的車站月台上,他讓自己存在。每一天,在同樣的時間,他等待著他的RER,兩隻腳放在不可跨越的白線上,免得跌入軌道裡。這條畫在水泥地上微不足道的白線擁有某種神秘的力量,能使他平靜下來。一直浮盪在他腦中的堆屍處的味道一來到這裡,就神奇的消失了。在RER到達之前的幾分鐘,他會踩踏著這條白線,就像要讓自己融入它一樣,但是他心裡很清楚這不過是讓自己的錯覺延緩一會兒,唯一能夠逃離在天際另一頭等他的野蠻活動,是離開這條他兩隻腳搖搖擺擺踩踏著的白線,然後回到他自己家裡。沒錯,他其實只要放棄這個動作,只要回到他的床上,把自己包裹在還留著他夜裡餘溫的被子就可以了。以睡覺來逃避。但是,最後,這位年輕男子還是留在白線上,聽著逐漸在他身後聚集起來的人,這些人把眼光都集中在他的頸背上,讓他感受到頸背有一個小小的灼熱之感,使他覺得自己是活著的。幾年下來,其他的乘客都對這個有點瘋瘋的年輕男子寬容起來。季朗像是一股新鮮空氣,在旅程的二十分鐘的時間裡,將乘客從日常的單調中拯救出來。
2
RER響起了煞車聲,停靠在月台邊。季朗跨過了白線,踏進車廂門。他坐在右邊門邊的折疊座椅上。他偏愛硬硬的橘色折疊座椅,而不喜歡比較軟的長座椅。這麼一段時間下來,折疊座椅也成為他儀式的一部分。連壓下折疊座椅來坐,也具有象徵意味,能讓他心中安然。在搖擺的車廂內,他從永不離手的公事包裡拿出了一個卷宗夾。他小心翼翼的打開它,從粉紅糖果色的吸水紙裡拿出一頁紙。他兩手拿著這張左上角略微撕裂、損毀的紙張。這是一本書裡的一頁,13×20開本。這位年輕男子檢查了一下這張紙,然後把紙放在吸水紙上。車廂裡漸漸變無聲。偶爾有人「噓」了一聲,好讓其他還在談話的人也安靜下來。於是每天早上,季朗就在清了一下喉嚨之後,開始高聲的朗讀起來:
「孩子嚇得說不出話來,而且動也不敢動,只看著掛在倉庫門邊氣喘咻咻的兔子。男人探出手來,摸了摸牠還有生命跳動的喉嚨。細長的刀刃無聲的刺入白色的絨毛內,而且從牠的傷口中噴出一股熱熱的血流,使得男人的手腕濺上了幾滴小小的紅點。這個男人是男孩的父親,他把衣袖捲到手肘上,用很準確的動作在兔子身上劃下幾刀。然後,他用有力的雙手像脫襪子一樣的慢慢脫下牠的皮毛。被剝下了皮毛的兔子一下子就露出了光溜溜的身體,身上的肌肉清晰可見,牠雖然死了,整個身子都還散發著生命的熱氣。牠垂著頭,整個看來顯得很醜陋,枯瘦瘦的,兩隻突出來的眼睛,眼神茫然,一點也沒有譴責人的樣子。」
天色漸亮,玻璃窗上的霧氣被日光驅散了,那篇文章化成了他嘴裡吐露的一連串字音,他時而有間歇沈默的時刻,在這時候便可聽見行駛中的火車轟隆隆的聲音。對所有在車廂裡的乘客來說,他是個朗讀者,這個怪人於每週一到週五上班的日子,都會以清朗的聲音高聲朗讀從他公事包裡取出來的幾頁文字。有時讀的是食譜,有時讀的是上一屆龔固爾作品第四十八頁的內容,有時在讀了偵探小說中的一段之後,會接著讀一頁歷史書。對季朗來說,讀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朗讀這個行為。不管讀的是什麼,他都一樣專注用心。而且每一次,都會發生神奇的事。每一次字字句句離開他的唇之後,都會使他在接近工廠時那種噁心的感覺一點一點的散去。
「最後,刀刃打開了神秘之門。男人以長長的一刀劃開了兔子的腹部,裡面還散著熱氣的內臟都傾洩了出來,就好像急著離開禁閉它們的胸腔一樣。兔子這時只剩下淌著血的一個小身軀,裹在一條抹布裡。接下來的幾天,每天都有一隻兔子。在悶熱的兔棚中都有另一隻蹦蹦跳跳的白毛兔,睜著血紅色的眼睛從死亡的國境看著孩子。」
季朗頭連抬也沒抬,小心翼翼的取出第二頁文字:
「這些人憑直覺的把臉埋在地上,帶著強烈的慾望想把自己埋藏起來,把自己埋藏在這片保護他們的土地裡越深越好。有些人則像瘋狗一樣,以兩手挖著土。還有一些人則把自己蜷曲成一團,讓他們脆弱的背脊承受著從四處飛迸而來的炸彈碎片。所有的人都反射性的把自己團縮起來。只有約瑟夫他不這麼做。約瑟夫站在這一堆混亂之中,抱著在他面前的一棵白樺樹。從樹幹一條條的隙縫裡,流出了濃稠的樹脂,這些如淚水一樣的汁液一滴滴從樹幹上滲出來,緩緩的往下流。這株白樺樹流乾了自己,就像約瑟夫暖暖的尿液也沿著他的大腿往下流。每一有新的爆炸,白樺樹就在他臉頰上微微顫動,在他臂彎裡震動起來。」
這位年輕男子用他兩隻眼睛仔細挑選著放在他公事包裡的十來頁文字,直到RER到了站。當他發出的最後字音完全消散得無影無蹤以後,他第一次看了看從他上車以後他都還沒正眼看過的其他乘客。往往,他會從這些乘客面孔裡見到了失望的臉色,甚至是悲傷的臉色。這通常只持續短暫的時間。車廂裡的人很快的下了車。這時也輪到他站起來。自動彈回的折疊座椅,乾乾的發出了「喀」的一聲。結束了。一位中年女士輕輕的對他道了一聲謝。季朗對她微微一笑。他不知道該怎麼對這些乘客解釋,他這麼做並不是為了他們。他乖乖的走出溫暖的車廂,把他今天讀的那幾頁通通留在車廂裡。他喜歡把那幾頁留在車上,自己心裡知道它們就夾在折疊座椅的椅背和椅座之間,遠離摧殘它們的機器。戶外,下起一陣暴雨。每一次走近工廠,居易塞普這位老伯沙啞的聲音就在他腦海裡迴響著:「你不適合這個,小子。你自己還不知道這件事,但是你不適合做這個!」這位老伯知道他自己在說什麼,他自己之所以還有勇氣繼續做下去完全是靠著酒精。季朗沒聽他的話,他天真的以為每天照辦這些例行公事最後就會習慣了。例行公事會像秋天的霧氣一樣充盈他整個存在,麻痺了他的思想。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每當他看見工廠高大、污穢的外牆,他就覺得想嘔吐。在這堵牆後面,有「那東西」躲藏在那裡。「那東西」在那裡等著他。
有人一生下來就是聾子、瞎子或啞巴。有人一生下來就是斜視、兔唇或是在臉面正中央有塊胎記。還有一些人是帶著畸形足來到世間,甚至有一只肢體在還沒生之前就已經死了的。至於季朗.威紐爾(Guylain Vignolles)這個人,他在他出生時必須背負的重擔則是他的姓名,因為他姓和名的前半互調,念來就成了「威朗.季紐爾」(Vilan Guignol),這在法文中的意思就是「醜陋的布偶」。這種討人厭的文字遊戲,從他踏出人生的第一步開始就一直緊緊跟隨著他,永不離開。
他的父母親在一九七六年時,不選日曆上每天都有不同聖人名字來作為兒子的名字,而選了不知從哪兒來的「季朗」這個名字,想都沒想他們這麼一取名,將會為兒子帶來不幸。怪的是,他雖然很好奇父母親為什麼會幫他取這個名字,但他從來不敢問起。也許是擔心會讓自己的父母尷尬。當然也擔心答案其實很普通,解不了他的惑。有時候,他喜歡想像自己如果叫做呂卡、察維耶,或是叫做雨果,人生不知道會不會有不同。甚至如果叫做「季斯朗」都能讓他很開心。季斯朗.威紐爾,一個真正的名字,可以讓他在不傷人的六個音節後面,打造自己的身與心。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他的整個童年時期都是在煩人的姓與名前半互調的文字遊戲中度過,「醜陋的布偶」與他形影不離。直到他三十六歲那年,他終於學會了讓別人忘記自己,讓自己成為一個隱形人,免得一有別人注意到他,他就成為嘲笑、揶揄的對象。他長得既不帥也不醜,不胖也不瘦,只是別人眼角裡不經意撇到的一抹模糊的陰影。他讓自己融入在所處的背景中,甚至直到否認自己,以便自己成為一個從未有人造訪的他方。這麼些年來,季朗.威紐爾就是努力讓自己不存在,只除了這裡,在這個陰暗的車站裡,這個他每天早上必須抵達的車站月台上,他讓自己存在。每一天,在同樣的時間,他等待著他的RER,兩隻腳放在不可跨越的白線上,免得跌入軌道裡。這條畫在水泥地上微不足道的白線擁有某種神秘的力量,能使他平靜下來。一直浮盪在他腦中的堆屍處的味道一來到這裡,就神奇的消失了。在RER到達之前的幾分鐘,他會踩踏著這條白線,就像要讓自己融入它一樣,但是他心裡很清楚這不過是讓自己的錯覺延緩一會兒,唯一能夠逃離在天際另一頭等他的野蠻活動,是離開這條他兩隻腳搖搖擺擺踩踏著的白線,然後回到他自己家裡。沒錯,他其實只要放棄這個動作,只要回到他的床上,把自己包裹在還留著他夜裡餘溫的被子就可以了。以睡覺來逃避。但是,最後,這位年輕男子還是留在白線上,聽著逐漸在他身後聚集起來的人,這些人把眼光都集中在他的頸背上,讓他感受到頸背有一個小小的灼熱之感,使他覺得自己是活著的。幾年下來,其他的乘客都對這個有點瘋瘋的年輕男子寬容起來。季朗像是一股新鮮空氣,在旅程的二十分鐘的時間裡,將乘客從日常的單調中拯救出來。
2
RER響起了煞車聲,停靠在月台邊。季朗跨過了白線,踏進車廂門。他坐在右邊門邊的折疊座椅上。他偏愛硬硬的橘色折疊座椅,而不喜歡比較軟的長座椅。這麼一段時間下來,折疊座椅也成為他儀式的一部分。連壓下折疊座椅來坐,也具有象徵意味,能讓他心中安然。在搖擺的車廂內,他從永不離手的公事包裡拿出了一個卷宗夾。他小心翼翼的打開它,從粉紅糖果色的吸水紙裡拿出一頁紙。他兩手拿著這張左上角略微撕裂、損毀的紙張。這是一本書裡的一頁,13×20開本。這位年輕男子檢查了一下這張紙,然後把紙放在吸水紙上。車廂裡漸漸變無聲。偶爾有人「噓」了一聲,好讓其他還在談話的人也安靜下來。於是每天早上,季朗就在清了一下喉嚨之後,開始高聲的朗讀起來:
「孩子嚇得說不出話來,而且動也不敢動,只看著掛在倉庫門邊氣喘咻咻的兔子。男人探出手來,摸了摸牠還有生命跳動的喉嚨。細長的刀刃無聲的刺入白色的絨毛內,而且從牠的傷口中噴出一股熱熱的血流,使得男人的手腕濺上了幾滴小小的紅點。這個男人是男孩的父親,他把衣袖捲到手肘上,用很準確的動作在兔子身上劃下幾刀。然後,他用有力的雙手像脫襪子一樣的慢慢脫下牠的皮毛。被剝下了皮毛的兔子一下子就露出了光溜溜的身體,身上的肌肉清晰可見,牠雖然死了,整個身子都還散發著生命的熱氣。牠垂著頭,整個看來顯得很醜陋,枯瘦瘦的,兩隻突出來的眼睛,眼神茫然,一點也沒有譴責人的樣子。」
天色漸亮,玻璃窗上的霧氣被日光驅散了,那篇文章化成了他嘴裡吐露的一連串字音,他時而有間歇沈默的時刻,在這時候便可聽見行駛中的火車轟隆隆的聲音。對所有在車廂裡的乘客來說,他是個朗讀者,這個怪人於每週一到週五上班的日子,都會以清朗的聲音高聲朗讀從他公事包裡取出來的幾頁文字。有時讀的是食譜,有時讀的是上一屆龔固爾作品第四十八頁的內容,有時在讀了偵探小說中的一段之後,會接著讀一頁歷史書。對季朗來說,讀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朗讀這個行為。不管讀的是什麼,他都一樣專注用心。而且每一次,都會發生神奇的事。每一次字字句句離開他的唇之後,都會使他在接近工廠時那種噁心的感覺一點一點的散去。
「最後,刀刃打開了神秘之門。男人以長長的一刀劃開了兔子的腹部,裡面還散著熱氣的內臟都傾洩了出來,就好像急著離開禁閉它們的胸腔一樣。兔子這時只剩下淌著血的一個小身軀,裹在一條抹布裡。接下來的幾天,每天都有一隻兔子。在悶熱的兔棚中都有另一隻蹦蹦跳跳的白毛兔,睜著血紅色的眼睛從死亡的國境看著孩子。」
季朗頭連抬也沒抬,小心翼翼的取出第二頁文字:
「這些人憑直覺的把臉埋在地上,帶著強烈的慾望想把自己埋藏起來,把自己埋藏在這片保護他們的土地裡越深越好。有些人則像瘋狗一樣,以兩手挖著土。還有一些人則把自己蜷曲成一團,讓他們脆弱的背脊承受著從四處飛迸而來的炸彈碎片。所有的人都反射性的把自己團縮起來。只有約瑟夫他不這麼做。約瑟夫站在這一堆混亂之中,抱著在他面前的一棵白樺樹。從樹幹一條條的隙縫裡,流出了濃稠的樹脂,這些如淚水一樣的汁液一滴滴從樹幹上滲出來,緩緩的往下流。這株白樺樹流乾了自己,就像約瑟夫暖暖的尿液也沿著他的大腿往下流。每一有新的爆炸,白樺樹就在他臉頰上微微顫動,在他臂彎裡震動起來。」
這位年輕男子用他兩隻眼睛仔細挑選著放在他公事包裡的十來頁文字,直到RER到了站。當他發出的最後字音完全消散得無影無蹤以後,他第一次看了看從他上車以後他都還沒正眼看過的其他乘客。往往,他會從這些乘客面孔裡見到了失望的臉色,甚至是悲傷的臉色。這通常只持續短暫的時間。車廂裡的人很快的下了車。這時也輪到他站起來。自動彈回的折疊座椅,乾乾的發出了「喀」的一聲。結束了。一位中年女士輕輕的對他道了一聲謝。季朗對她微微一笑。他不知道該怎麼對這些乘客解釋,他這麼做並不是為了他們。他乖乖的走出溫暖的車廂,把他今天讀的那幾頁通通留在車廂裡。他喜歡把那幾頁留在車上,自己心裡知道它們就夾在折疊座椅的椅背和椅座之間,遠離摧殘它們的機器。戶外,下起一陣暴雨。每一次走近工廠,居易塞普這位老伯沙啞的聲音就在他腦海裡迴響著:「你不適合這個,小子。你自己還不知道這件事,但是你不適合做這個!」這位老伯知道他自己在說什麼,他自己之所以還有勇氣繼續做下去完全是靠著酒精。季朗沒聽他的話,他天真的以為每天照辦這些例行公事最後就會習慣了。例行公事會像秋天的霧氣一樣充盈他整個存在,麻痺了他的思想。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每當他看見工廠高大、污穢的外牆,他就覺得想嘔吐。在這堵牆後面,有「那東西」躲藏在那裡。「那東西」在那裡等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