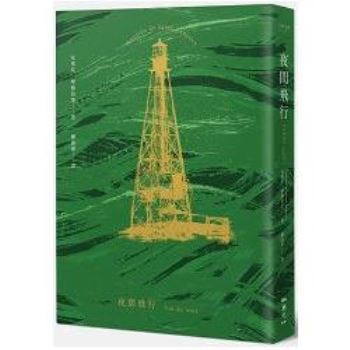XVI.
多虧那幾枚星子指引他方向,他上升了,邊盡量保持平穩。星星蒼白的磁石把他吸了過去。他痛苦掙扎了這麼久,就為了追尋一絲光亮,哪怕再黯淡,他也說什麼都不會放棄。哪怕一盞客棧的小燈,都會讓他感到富有,他都會繞著那讓他如此渴望的光明徵象大兜圈子,至死方休。而此刻的他,正在往光田上升。
他呈螺旋狀逐漸往上爬升,深淵在他下方,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隨著他邊上升,雲層也邊丟失了自己陰沉的雲泥,衝著他迎面飄過,宛如一波波越來越純淨的白浪。費邊破浪而出。
他無比驚喜:明亮到令他眼花撩亂。乃至於有幾秒鐘的時間,他還得閉上雙眼。他永遠都不會相信,雲、夜竟然會如此光彩耀眼。可是那輪滿月和點點繁星正在把那雲、那夜變幻成波波輝光。
飛機突然掙脫了出來,就在它浮出雲層的同一秒鐘,萬物出奇寧靜。毫無任何讓飛機傾斜的波浪。彷彿一葉扁舟通過大壩,駛入安全水域。費邊飛進天際某一個未知又隱蔽的地方,這個地方好似環抱著真福島群的海灣。在他下方,暴風雨形成另一個厚達三千公尺的世界,一個狂風襲擊,水龍捲肆虐,雷電交加的世界,然而暴風雨卻把一張晶瑩、雪白的臉龐轉向星辰。
費邊心想他脫離了怪異的地獄邊緣,因為他的雙手,他的衣服,他的機翼,一切都變得明亮。因為那光不是從星辰灑下來的,而是從他下方、圍繞著他的這些白色儲藏中散發出來的。
在他下方的這些雲彩,把來自月亮、皎潔如白雪的月光全部反射出來。右方和左方,如塔般高聳著的雲彩也一樣。一團乳白光暈在游移,機組人員浸淫於其中。費邊,轉過頭去,看到無線電報務員在微笑。
「好一點了!」 他喊道。
但是聲音淹沒在飛機的噪音中,只能靠微笑溝通。「我簡直瘋了,」費邊笑著想:「我們迷航了。」
然而,萬千黑暗手臂放開他了。解開束縛,好像有人解開囚犯枷鎖,讓他一個人在花間蹓躂一會兒。
「太美了。」費邊想。繁星積累,稠密得有如寶藏,他在星星中徘徊,踟躕於一個沒有任何東西,除了他費邊和他的夥伴之外,絕對沒有任何東西還活著的世界。他們像神話城中的盜賊,受困於寶庫的高牆,再也不知道怎麼出去。他們在這些冰冷的寶石中間徜徉,無比富有,但卻被判了刑。XVII.
巴塔哥尼亞地區的海軍准將城中途站,有個無線電報務員突然打了個手勢,無線電台所有堅守崗位、無能為力的值夜人員全都擠到他身邊,彎下身子。
他們俯在一張被光線照得亮晃晃的白紙上。那位報務員的手還僵在半空中,鉛筆也在搖晃,他的手將字母視為禁臠,還沒放出半個,手指倒先抖了起來。
「暴風雨?」
報務員點了點頭,表示「對」。暴風雨的嘈雜聲,害他聽不懂。
接著,他就記下幾個難以辨認的符號。隨後又寫下幾個字。然後才湊成電文:
「我們被卡在暴風雨上方三千八百公尺處。現在往正西飛向內陸,因為暴風雨害我們偏離航道,被帶到海上。下方整個都被封住,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還飛在海面上。請告訴我們內陸是不是也受到暴風雨影響。」
因為暴風雨的緣故,得經過一站又一站,才能把這封電報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訊息在夜間傳遞,宛如一把輪流點燃的火。
布宜諾斯艾利斯差人幫忙回道:
「暴風雨襲捲內陸各地。你們還有多少燃料?」
「還可以飛半個鐘頭。」
這句話,從值夜班的站點,一站傳一站,才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
三十分鐘內,巴塔哥尼亞號機組人員注定就會被捲進颶風,偏離航道,颳到地面。
XVIII.
此時李維耶則陷入長考。他不再抱希望:這組人會在黑夜某處陷落。
李維耶憶起兒時曾有一幕令他非常震撼:為了找一具屍體,把池塘的水全部抽光。在這一大團黑影從大地消散之前,在這些沙灘、這些平原、這些麥子重見光明之前,費邊他們也什麼都不會找到。或許純樸農民會發現這兩個孩子,手肘彎曲置於臉上,彷彿睡覺了,在一片祥和的金黃背景中,癱躺在草地上。只不過,夜,早已將他倆溺斃。
李維耶想到黑夜深處埋著的寶藏,彷彿深藏在神奇海底……這些夜的蘋果樹,等待著天光才要將花朵綻放,蘋果樹的花朵卻來不及派上用場。夜,何其富有,充滿著芬芳,沉睡中的羔羊,還有尚未著上顏色的花朵。
肥沃的田畦,潤澤的樹林,新鮮的苜蓿,漸漸朝向日光滋長茁壯。但在那些此刻已經無害的山丘之間,在草原之間,在羔羊之間,在世間的智慧中間,有兩個孩子似乎睡著了。屆時就有什麼東西從有形世界流向另一個世界。
李維耶知道費邊的妻子既多愁善感又溫柔多情:她給費邊的這份滿滿的愛,宛如給窮小孩的那個玩具。李維耶想到費邊的手,還能在操縱桿上掌握自己的命運幾分鐘。這隻手曾經愛撫過。這隻手曾經放在女人胸脯上過,還在那兒掀起了一陣心旌神搖,有如神祇的手。這隻手曾經放在一張臉上過,而且改變了那張臉。這隻手曾是如此神奇。
那夜,費邊漫遊於璀璨雲海上,但,在更低處,便是永恆。他獨自一人住在星辰裡,迷失於群星之間。世界依然掌握著在他手中,在他懷中的則是天秤座。他把人類財富的重量緊緊握進他的方向盤裡,絕望地,從一顆星星帶到另一顆,帶著那無用的寶藏,因為是時候該歸還了……
李維耶心想,還有電報站在接聽訊息。費邊跟這個世界的唯一聯繫就是一波音浪,一首變了調的小曲。不是哀鳴,不是吶喊。而是絕望發出來的最最純淨之聲。
多虧那幾枚星子指引他方向,他上升了,邊盡量保持平穩。星星蒼白的磁石把他吸了過去。他痛苦掙扎了這麼久,就為了追尋一絲光亮,哪怕再黯淡,他也說什麼都不會放棄。哪怕一盞客棧的小燈,都會讓他感到富有,他都會繞著那讓他如此渴望的光明徵象大兜圈子,至死方休。而此刻的他,正在往光田上升。
他呈螺旋狀逐漸往上爬升,深淵在他下方,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隨著他邊上升,雲層也邊丟失了自己陰沉的雲泥,衝著他迎面飄過,宛如一波波越來越純淨的白浪。費邊破浪而出。
他無比驚喜:明亮到令他眼花撩亂。乃至於有幾秒鐘的時間,他還得閉上雙眼。他永遠都不會相信,雲、夜竟然會如此光彩耀眼。可是那輪滿月和點點繁星正在把那雲、那夜變幻成波波輝光。
飛機突然掙脫了出來,就在它浮出雲層的同一秒鐘,萬物出奇寧靜。毫無任何讓飛機傾斜的波浪。彷彿一葉扁舟通過大壩,駛入安全水域。費邊飛進天際某一個未知又隱蔽的地方,這個地方好似環抱著真福島群的海灣。在他下方,暴風雨形成另一個厚達三千公尺的世界,一個狂風襲擊,水龍捲肆虐,雷電交加的世界,然而暴風雨卻把一張晶瑩、雪白的臉龐轉向星辰。
費邊心想他脫離了怪異的地獄邊緣,因為他的雙手,他的衣服,他的機翼,一切都變得明亮。因為那光不是從星辰灑下來的,而是從他下方、圍繞著他的這些白色儲藏中散發出來的。
在他下方的這些雲彩,把來自月亮、皎潔如白雪的月光全部反射出來。右方和左方,如塔般高聳著的雲彩也一樣。一團乳白光暈在游移,機組人員浸淫於其中。費邊,轉過頭去,看到無線電報務員在微笑。
「好一點了!」 他喊道。
但是聲音淹沒在飛機的噪音中,只能靠微笑溝通。「我簡直瘋了,」費邊笑著想:「我們迷航了。」
然而,萬千黑暗手臂放開他了。解開束縛,好像有人解開囚犯枷鎖,讓他一個人在花間蹓躂一會兒。
「太美了。」費邊想。繁星積累,稠密得有如寶藏,他在星星中徘徊,踟躕於一個沒有任何東西,除了他費邊和他的夥伴之外,絕對沒有任何東西還活著的世界。他們像神話城中的盜賊,受困於寶庫的高牆,再也不知道怎麼出去。他們在這些冰冷的寶石中間徜徉,無比富有,但卻被判了刑。XVII.
巴塔哥尼亞地區的海軍准將城中途站,有個無線電報務員突然打了個手勢,無線電台所有堅守崗位、無能為力的值夜人員全都擠到他身邊,彎下身子。
他們俯在一張被光線照得亮晃晃的白紙上。那位報務員的手還僵在半空中,鉛筆也在搖晃,他的手將字母視為禁臠,還沒放出半個,手指倒先抖了起來。
「暴風雨?」
報務員點了點頭,表示「對」。暴風雨的嘈雜聲,害他聽不懂。
接著,他就記下幾個難以辨認的符號。隨後又寫下幾個字。然後才湊成電文:
「我們被卡在暴風雨上方三千八百公尺處。現在往正西飛向內陸,因為暴風雨害我們偏離航道,被帶到海上。下方整個都被封住,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還飛在海面上。請告訴我們內陸是不是也受到暴風雨影響。」
因為暴風雨的緣故,得經過一站又一站,才能把這封電報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訊息在夜間傳遞,宛如一把輪流點燃的火。
布宜諾斯艾利斯差人幫忙回道:
「暴風雨襲捲內陸各地。你們還有多少燃料?」
「還可以飛半個鐘頭。」
這句話,從值夜班的站點,一站傳一站,才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
三十分鐘內,巴塔哥尼亞號機組人員注定就會被捲進颶風,偏離航道,颳到地面。
XVIII.
此時李維耶則陷入長考。他不再抱希望:這組人會在黑夜某處陷落。
李維耶憶起兒時曾有一幕令他非常震撼:為了找一具屍體,把池塘的水全部抽光。在這一大團黑影從大地消散之前,在這些沙灘、這些平原、這些麥子重見光明之前,費邊他們也什麼都不會找到。或許純樸農民會發現這兩個孩子,手肘彎曲置於臉上,彷彿睡覺了,在一片祥和的金黃背景中,癱躺在草地上。只不過,夜,早已將他倆溺斃。
李維耶想到黑夜深處埋著的寶藏,彷彿深藏在神奇海底……這些夜的蘋果樹,等待著天光才要將花朵綻放,蘋果樹的花朵卻來不及派上用場。夜,何其富有,充滿著芬芳,沉睡中的羔羊,還有尚未著上顏色的花朵。
肥沃的田畦,潤澤的樹林,新鮮的苜蓿,漸漸朝向日光滋長茁壯。但在那些此刻已經無害的山丘之間,在草原之間,在羔羊之間,在世間的智慧中間,有兩個孩子似乎睡著了。屆時就有什麼東西從有形世界流向另一個世界。
李維耶知道費邊的妻子既多愁善感又溫柔多情:她給費邊的這份滿滿的愛,宛如給窮小孩的那個玩具。李維耶想到費邊的手,還能在操縱桿上掌握自己的命運幾分鐘。這隻手曾經愛撫過。這隻手曾經放在女人胸脯上過,還在那兒掀起了一陣心旌神搖,有如神祇的手。這隻手曾經放在一張臉上過,而且改變了那張臉。這隻手曾是如此神奇。
那夜,費邊漫遊於璀璨雲海上,但,在更低處,便是永恆。他獨自一人住在星辰裡,迷失於群星之間。世界依然掌握著在他手中,在他懷中的則是天秤座。他把人類財富的重量緊緊握進他的方向盤裡,絕望地,從一顆星星帶到另一顆,帶著那無用的寶藏,因為是時候該歸還了……
李維耶心想,還有電報站在接聽訊息。費邊跟這個世界的唯一聯繫就是一波音浪,一首變了調的小曲。不是哀鳴,不是吶喊。而是絕望發出來的最最純淨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