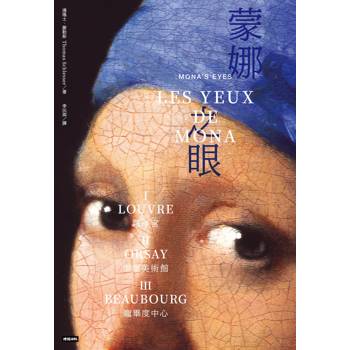序言
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
一切都變暗了。猶如一件喪服。然後,到處都是閃光,如同雙眼在緊閉的眼瞼後方毫無意義地盯住太陽時產生的那些斑點,就像我們緊握拳頭抵抗痛苦或情緒時那樣。
當然,她完全不是這樣描述的。從一個稚嫩且不安的十歲孩子口中表達出來的苦惱,既沒有經過修飾,也不詩情畫意。
「媽媽,全都是黑的!」
蒙娜用哽咽的聲音說出這幾個字。是抱怨嗎?是的,但不僅如此。她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羞愧的聲調,每次她的母親察覺到這一點,態度都會嚴肅起來。因為,如果有什麼是蒙娜從來就不會假裝的,那就是羞愧。一旦羞愧駐足在一個字詞、一種態度、一種語調裡,一切就成定局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已經扎根。
「媽媽,全都是黑的!」
蒙娜瞎了。
似乎事出突然,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她右手握著筆,左手夾著練習簿,乖巧地在桌子的一角做數學題,她的母親正把大蒜塞滿肥滋滋的烤肉。蒙娜小心翼翼地從脖子上取下一個礙事的吊墜,因為這個吊墜在她的習作本上方晃動,而她已經養成駝背寫字的壞習慣。她感覺到自己的雙眼被一層厚重的陰影襲擊,彷彿是因為這雙眼睛如此湛藍、如此圓大、如此純淨,這才受到懲罰。陰影不是來自外面,並非像夜幕降臨或劇院的燈光黯淡下來時所顯現的陰影;陰影是從她自己的身體、從內部攫取了她的視力。一塊不透光的桌布鑽進她的體內,將她與作業簿上的多邊形圖案、棕色的木桌、放在遠處的烤肉、繫著白色圍裙的母親、鋪著磁磚的廚房、坐在隔壁房間的父親、蒙特伊的公寓、籠罩街道的秋日灰色天空以及全世界分開來。這個孩子受到了詛咒,陷入黑暗之中。
蒙娜的母親焦躁不安,她打電話給家庭醫師,困惑地描述了女兒被遮蔽的瞳孔,並在醫師的詢問下,明確指出她似乎沒有出現任何語言障礙或癱瘓。
「這聽起來像是AIT。」他說,但沒有想要更進一步做出判斷。
他要蒙娜立即服用高劑量的阿斯匹靈,但最重要的是緊急將她送到主宮醫院,他會打電話請一位同業立刻進行治療。他不是偶然想到這位同業的:那是一名出色的小兒科醫師,也是一位聲譽卓著的眼科醫師,順帶一提,還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催眠治療師。他推斷在正常情況下,這種失明狀態應該不會超過十分鐘,然後他就掛上電話,然而距離事發當時已經過了整整十五分鐘了。
在車上,小女孩一邊哭泣,一邊拍打太陽穴。她的母親拉住她的手肘,但在她內心深處,她也想要拍打這顆圓圓且脆弱的小腦袋,就像我們會敲打一台壞掉的機器,傻傻地期望它能重新發動一樣。而那位父親則開著他那輛搖晃不已的老舊福斯汽車,希望能揪出讓他小女兒生病的原因。他很生氣,確信廚房裡一定發生過什麼事,而且還瞞著他。他反覆思索所有可能的原因,從一縷蒸氣到重重一跤都有可能。但是,不,蒙娜說了無數次:
「突然就變成這樣子了!」
父親說什麼也不信:
「我們不會就這樣瞎了!」
然而,是的,我們也會「就這樣」變瞎了,證據就在此。而那個我們,如今就是蒙娜、她十年的人生與大量湧現的恐懼淚水──或許她期望這些淚水能洗去在這個十月的週日,當夜幕降臨時沾黏在她瞳孔上的煙灰。才剛抵達西提島上鄰近聖母院的醫院門口,她突然停止哭泣並愣住了:
「媽媽,爸爸,我又看見了!」
她站在冷風颼颼的街上,前後搖晃著脖子,想要重新感受一切。就像被掀開的簾子,擋住她雙眼的遮蔽物也被揭起。線條重新出現在她眼前,接著是臉部的輪廓、近物的立體細節、牆壁的紋理,以及各種顏色從最明亮到最灰暗的所有細微差異。孩子認出她母親纖細的身影、她那如天鵝般細長的脖子與她纖瘦的手臂,還有她父親粗壯的胳膊。最後,她注意到遠處有一隻灰色的鴿子飛了起來,這讓她滿心喜悅。蒙娜一度失明,然後又重見光明。失明貫穿了她,就像一顆子彈穿透皮膚並從身體的另一側飛出去,當然,這會痛,但身體仍可自行癒合。她父親想著「這真是個奇蹟」,他認真地計算這次發作持續的時間:六十三分鐘。
主宮醫院的眼科部門在做完一系列的檢查、提供診斷與處方之前,是絕對不可能讓小女孩離開的。焦慮感確實稍稍壓下了,但並沒有完全消散。一名護士指著醫院二樓的一個診間,接到家庭醫師通知的小兒科醫師就在裡面。馮.奧斯特醫師是一名混血兒,而且年紀輕輕頭就禿了。他那件寬大的白袍閃閃發亮,與牆壁的病態慘綠色形成對比。他燦爛的笑容在臉上刻出許多快活的小皺紋,讓他看起來很和善;但他也承擔了許多悲劇。他邁步向前:
「妳幾歲啊?」他用因抽菸而沙啞的聲音問道。
*
蒙娜十歲了。她是獨生女,父母恩愛。母親卡蜜兒將近四十歲。她不高,留著一頭凌亂的短髮,聲音殘留著些許郊區工人特有的戲謔語調。她的先生曾說她的魅力在於她「略顯散漫」,但是她有著強大的決心,在她身上,無政府狀態與權威不斷交織在一起。她在一間派遣公司工作,是一名好員工,積極、勤勉。至少早上是如此。到了下午,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志工工作讓她精疲力竭,從孤獨老人到受虐動物,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投入的。至於保羅,他已經五十七歲了。卡蜜兒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則跟他的好友跑了。他打著一條領帶來遮掩衣領磨損的襯衫,是個忙碌的小舊貨商,尤其熱衷一九五?年代的美國文化:自動點唱機、彈珠檯、海報……。這一切都源於他青少年時期收藏的心型鑰匙圈,他擁有的數量驚人,但他不想賣掉,反正也沒人對這些東西感興趣。隨著網路的發展,他那隱身在蒙特伊的店鋪差點就要關門了。於是他發揮專業,也開設了一個網站,除了不斷更新,還翻譯成英文。儘管他沒有什麼商業頭腦,但他靠著一群忠實的收藏家,經常能逃過破產的命運。去年夏天,他修復了一台葛特利柏於一九五五年出廠的「許願井」彈珠檯,從中賺進高達一萬歐元。在經過數個月的斷糧之後,這筆交易來得正好……,接著他又再次一無所有。有人告訴他,這就是危機。保羅每天在店裡喝掉一瓶紅酒,然後將瓶子當作戰利品,擺在一個因馬塞爾.杜象而得以流傳後世的刺蝟造型瀝水架上。他獨自舉杯,無法怨恨任何人。他在心中向蒙娜敬酒,願她身體健康。
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
一切都變暗了。猶如一件喪服。然後,到處都是閃光,如同雙眼在緊閉的眼瞼後方毫無意義地盯住太陽時產生的那些斑點,就像我們緊握拳頭抵抗痛苦或情緒時那樣。
當然,她完全不是這樣描述的。從一個稚嫩且不安的十歲孩子口中表達出來的苦惱,既沒有經過修飾,也不詩情畫意。
「媽媽,全都是黑的!」
蒙娜用哽咽的聲音說出這幾個字。是抱怨嗎?是的,但不僅如此。她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羞愧的聲調,每次她的母親察覺到這一點,態度都會嚴肅起來。因為,如果有什麼是蒙娜從來就不會假裝的,那就是羞愧。一旦羞愧駐足在一個字詞、一種態度、一種語調裡,一切就成定局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已經扎根。
「媽媽,全都是黑的!」
蒙娜瞎了。
似乎事出突然,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她右手握著筆,左手夾著練習簿,乖巧地在桌子的一角做數學題,她的母親正把大蒜塞滿肥滋滋的烤肉。蒙娜小心翼翼地從脖子上取下一個礙事的吊墜,因為這個吊墜在她的習作本上方晃動,而她已經養成駝背寫字的壞習慣。她感覺到自己的雙眼被一層厚重的陰影襲擊,彷彿是因為這雙眼睛如此湛藍、如此圓大、如此純淨,這才受到懲罰。陰影不是來自外面,並非像夜幕降臨或劇院的燈光黯淡下來時所顯現的陰影;陰影是從她自己的身體、從內部攫取了她的視力。一塊不透光的桌布鑽進她的體內,將她與作業簿上的多邊形圖案、棕色的木桌、放在遠處的烤肉、繫著白色圍裙的母親、鋪著磁磚的廚房、坐在隔壁房間的父親、蒙特伊的公寓、籠罩街道的秋日灰色天空以及全世界分開來。這個孩子受到了詛咒,陷入黑暗之中。
蒙娜的母親焦躁不安,她打電話給家庭醫師,困惑地描述了女兒被遮蔽的瞳孔,並在醫師的詢問下,明確指出她似乎沒有出現任何語言障礙或癱瘓。
「這聽起來像是AIT。」他說,但沒有想要更進一步做出判斷。
他要蒙娜立即服用高劑量的阿斯匹靈,但最重要的是緊急將她送到主宮醫院,他會打電話請一位同業立刻進行治療。他不是偶然想到這位同業的:那是一名出色的小兒科醫師,也是一位聲譽卓著的眼科醫師,順帶一提,還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催眠治療師。他推斷在正常情況下,這種失明狀態應該不會超過十分鐘,然後他就掛上電話,然而距離事發當時已經過了整整十五分鐘了。
在車上,小女孩一邊哭泣,一邊拍打太陽穴。她的母親拉住她的手肘,但在她內心深處,她也想要拍打這顆圓圓且脆弱的小腦袋,就像我們會敲打一台壞掉的機器,傻傻地期望它能重新發動一樣。而那位父親則開著他那輛搖晃不已的老舊福斯汽車,希望能揪出讓他小女兒生病的原因。他很生氣,確信廚房裡一定發生過什麼事,而且還瞞著他。他反覆思索所有可能的原因,從一縷蒸氣到重重一跤都有可能。但是,不,蒙娜說了無數次:
「突然就變成這樣子了!」
父親說什麼也不信:
「我們不會就這樣瞎了!」
然而,是的,我們也會「就這樣」變瞎了,證據就在此。而那個我們,如今就是蒙娜、她十年的人生與大量湧現的恐懼淚水──或許她期望這些淚水能洗去在這個十月的週日,當夜幕降臨時沾黏在她瞳孔上的煙灰。才剛抵達西提島上鄰近聖母院的醫院門口,她突然停止哭泣並愣住了:
「媽媽,爸爸,我又看見了!」
她站在冷風颼颼的街上,前後搖晃著脖子,想要重新感受一切。就像被掀開的簾子,擋住她雙眼的遮蔽物也被揭起。線條重新出現在她眼前,接著是臉部的輪廓、近物的立體細節、牆壁的紋理,以及各種顏色從最明亮到最灰暗的所有細微差異。孩子認出她母親纖細的身影、她那如天鵝般細長的脖子與她纖瘦的手臂,還有她父親粗壯的胳膊。最後,她注意到遠處有一隻灰色的鴿子飛了起來,這讓她滿心喜悅。蒙娜一度失明,然後又重見光明。失明貫穿了她,就像一顆子彈穿透皮膚並從身體的另一側飛出去,當然,這會痛,但身體仍可自行癒合。她父親想著「這真是個奇蹟」,他認真地計算這次發作持續的時間:六十三分鐘。
主宮醫院的眼科部門在做完一系列的檢查、提供診斷與處方之前,是絕對不可能讓小女孩離開的。焦慮感確實稍稍壓下了,但並沒有完全消散。一名護士指著醫院二樓的一個診間,接到家庭醫師通知的小兒科醫師就在裡面。馮.奧斯特醫師是一名混血兒,而且年紀輕輕頭就禿了。他那件寬大的白袍閃閃發亮,與牆壁的病態慘綠色形成對比。他燦爛的笑容在臉上刻出許多快活的小皺紋,讓他看起來很和善;但他也承擔了許多悲劇。他邁步向前:
「妳幾歲啊?」他用因抽菸而沙啞的聲音問道。
*
蒙娜十歲了。她是獨生女,父母恩愛。母親卡蜜兒將近四十歲。她不高,留著一頭凌亂的短髮,聲音殘留著些許郊區工人特有的戲謔語調。她的先生曾說她的魅力在於她「略顯散漫」,但是她有著強大的決心,在她身上,無政府狀態與權威不斷交織在一起。她在一間派遣公司工作,是一名好員工,積極、勤勉。至少早上是如此。到了下午,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志工工作讓她精疲力竭,從孤獨老人到受虐動物,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投入的。至於保羅,他已經五十七歲了。卡蜜兒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則跟他的好友跑了。他打著一條領帶來遮掩衣領磨損的襯衫,是個忙碌的小舊貨商,尤其熱衷一九五?年代的美國文化:自動點唱機、彈珠檯、海報……。這一切都源於他青少年時期收藏的心型鑰匙圈,他擁有的數量驚人,但他不想賣掉,反正也沒人對這些東西感興趣。隨著網路的發展,他那隱身在蒙特伊的店鋪差點就要關門了。於是他發揮專業,也開設了一個網站,除了不斷更新,還翻譯成英文。儘管他沒有什麼商業頭腦,但他靠著一群忠實的收藏家,經常能逃過破產的命運。去年夏天,他修復了一台葛特利柏於一九五五年出廠的「許願井」彈珠檯,從中賺進高達一萬歐元。在經過數個月的斷糧之後,這筆交易來得正好……,接著他又再次一無所有。有人告訴他,這就是危機。保羅每天在店裡喝掉一瓶紅酒,然後將瓶子當作戰利品,擺在一個因馬塞爾.杜象而得以流傳後世的刺蝟造型瀝水架上。他獨自舉杯,無法怨恨任何人。他在心中向蒙娜敬酒,願她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