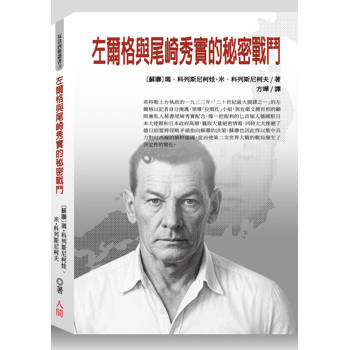前往大和國的危險途程
艙壁均勻地上下起伏。遮在床鋪上的深紅色天鵝絨床罩飄來擺去。悶熱。太陽穴酸痛。衣服蒙上薄薄一層鹽霜。
通過緊閉的舷窗,左爾格看到一片暗得近乎發黑的洋面――像是一片洶湧澎湃、泡沫遍地的沙漠。在水平線的邊緣處升起巨浪:從遠處看來完全是無害的巨浪,它們在眼前變大,化為一排排暗藍色的山脊,湧近舷邊,轟然一聲坍塌在上甲板上。
颱風已經狂吼第三個晝夜了。它在南方很遠的什麼地方,幾乎是在爪哇群島附近出現以後,在太平洋上疾馳,一路上把小船掀翻擊沉,接著向北急轉直下,橫在從溫哥華駛往橫濱的輪船的航線上。旅客不准到上甲板去。
左爾格少年時代寫過詩。對於比喻思維的習慣並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他懷著一種輕鬆的揶揄心情想道,這場被冠以溫柔的女人名字――貝蒂的狂暴颱風,可能是在日本等待他的那件事的獨特序幕。
一望無垠的,被狂飆攪得一片渾濁的水域,漫長的數百海里,雖然把他同整個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絕開來,他彷彿被焊在這小小的鋼鐵船艙裡邊,終歸還是有一種模糊的驚慌不安的感覺縈繞在他心頭。橫濱港上等待他的是什麼呢?是手銬,是監獄?……
……該死的希爾格!在這個顯然是納粹間諜的希爾格出現以前,一切都很順利……他是怎樣仔細打量左爾格面孔的啊!
「我在莫斯科見過您,左爾格博士!就在不太久以前,也就是三四個月以前吧……在大劇院。」
當時只是沉著鎮定才拯救了里哈爾德。
像玻璃一樣透明的藍色巨塊在眼前不斷升起,把龐大的輪船撞擊得左搖右擺,手提箱從船艙的一個角落滾到另一個角落,但左爾格卻一無所見。
他在竭力回憶柏林最後一夜的全部細節。
(未完……)
艙壁均勻地上下起伏。遮在床鋪上的深紅色天鵝絨床罩飄來擺去。悶熱。太陽穴酸痛。衣服蒙上薄薄一層鹽霜。
通過緊閉的舷窗,左爾格看到一片暗得近乎發黑的洋面――像是一片洶湧澎湃、泡沫遍地的沙漠。在水平線的邊緣處升起巨浪:從遠處看來完全是無害的巨浪,它們在眼前變大,化為一排排暗藍色的山脊,湧近舷邊,轟然一聲坍塌在上甲板上。
颱風已經狂吼第三個晝夜了。它在南方很遠的什麼地方,幾乎是在爪哇群島附近出現以後,在太平洋上疾馳,一路上把小船掀翻擊沉,接著向北急轉直下,橫在從溫哥華駛往橫濱的輪船的航線上。旅客不准到上甲板去。
左爾格少年時代寫過詩。對於比喻思維的習慣並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他懷著一種輕鬆的揶揄心情想道,這場被冠以溫柔的女人名字――貝蒂的狂暴颱風,可能是在日本等待他的那件事的獨特序幕。
一望無垠的,被狂飆攪得一片渾濁的水域,漫長的數百海里,雖然把他同整個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絕開來,他彷彿被焊在這小小的鋼鐵船艙裡邊,終歸還是有一種模糊的驚慌不安的感覺縈繞在他心頭。橫濱港上等待他的是什麼呢?是手銬,是監獄?……
……該死的希爾格!在這個顯然是納粹間諜的希爾格出現以前,一切都很順利……他是怎樣仔細打量左爾格面孔的啊!
「我在莫斯科見過您,左爾格博士!就在不太久以前,也就是三四個月以前吧……在大劇院。」
當時只是沉著鎮定才拯救了里哈爾德。
像玻璃一樣透明的藍色巨塊在眼前不斷升起,把龐大的輪船撞擊得左搖右擺,手提箱從船艙的一個角落滾到另一個角落,但左爾格卻一無所見。
他在竭力回憶柏林最後一夜的全部細節。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