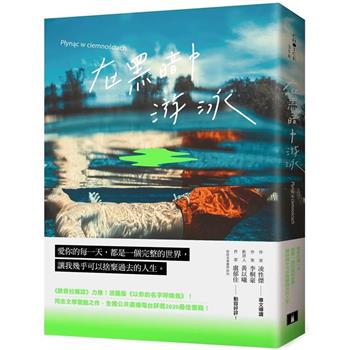雨已經停了,周遭的一切悄然無聲。太陽出來了,只是顯得微弱,而且即將落下地平線。我們往外伸出大拇指沿路行走,但沒有車子停下。我們不斷走著,走到太陽下山,卻還是沒有到達任何地方。雨水讓四周田野潮溼,不適合露營,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我們總算找到一個農場,農場主人同意收留我們一晚,讓我們睡在穀倉。農人女兒帶我們到那裡,還給了麵包和豬油,我們狼吞虎嚥吃得精光,然後在乾草上並排鋪好睡袋。
「晚安。」你關上手電筒後說道。你毫不忸怩地脫掉衣服,只見你黑暗中的剪影爬進了我身邊的睡袋。我聽得到你的呼吸,像是輕柔的浪濤聲。然後,滴滴答答,雨又逐漸下了起來,彷彿練習鋼琴和弦的指尖,敲擊著屋頂。我們仰躺聆聽,靜默不語。我感受到你在附近,你的身子雖然靜止不動,卻不知怎地充滿生氣。我的心跳比雨滴聲更加快速,忽然間,我想要靠近你,迫切想要如此。我可以感覺到你身體的拉力,小小的細繩扯著我靠向你。但我無法移動,心臟直跳,心中度過了數光年的來回,就在我開始認為自己絕不可能有勇氣時,你挪向我,頭枕在我的肩膀上。我的心跳停拍,不敢呼吸。你的頭好沉,像是溫暖的大理石,髮絲拂過我的臉頰。可能性讓我動彈不得,困在滿足的眩暈感以及不確定的深淵之間。我想到多年前的那一晚,在舞會上燈光熄滅時,我對貝尼克的舉動是多麼魯莽,帶來多麼痛苦和無法預料的後果。儘管如此,我才剛鼓起勇氣想著碰觸你的頭髮會怎樣,思索這是唯一可做的正確舉動,而且現在和當時不一樣,就聽到你輕聲說:「晚安,路茲歐。」然後挪離我身邊。這是你第一次這樣呼喚我,深情地變換了我的名字。這讓我肩膀上的空虛感更加難以忍受。
「晚安。」我勉強回答,轉過身子,感覺陣陣懊悔。你的呼吸開始平緩穩定,而我的心思像瘋馬一樣狂奔。雨下了一整晚。
清晨醒來,我見到你的身軀隨著呼吸上下起伏。透過木板縫隙,一道道光束進入穀倉,照亮了你。你的肩膀散落著我從未注意到的小雀斑,如星座一樣隨意而美麗。
我盡可能悄悄爬出睡袋,穿上T恤和短褲,套上涼鞋,走進外頭的晨光。這是個晴朗的日子,太陽已經升起,柔和新鮮,跟剛剝好的雞蛋一樣。空氣聞起來有綠色、黃色和肥沃深棕色的感覺。在白天的光線下,農舍比我記憶中的小,只有一層樓高,深色木材建造,加上老舊棕色瓦片搭成的陡峭屋頂。它看起來既古老又脆弱,彷彿已屹立在這個地方一輩子了,卻可能很容易就被搗毀。在農舍外頭,農人女兒餵著雞,她大約十五歲,戴著頭巾,有著充滿活力的心形臉蛋和孩子氣的羞怯淺笑。她跟我打招呼,並邀請我們去吃早餐。
「我們在廚房。」她說:「帶你的朋友一起來。」
我回到穀倉,發現你已經起身,正往緊身的白色內褲套上長褲。
「嗨。」我說,意識到自己刻意的聲音。
你拉上拉鍊,轉過身來。「嗨。」你看起來幾乎像是害羞,一隻手梳過頭髮。
「餓了嗎?」我問。
「餓死了。」
我們走出穀倉,進入農舍。裡面有一條陰暗的走廊,聞起來有黴味、煤煙和泥土的味道。一切似乎都靜止了。幾道光束揭露了漂浮在空中的塵埃世界,牆壁上,耶穌被釘在十字架,除了纏腰帶外一絲不掛,肌肉和肋骨清晰可見。我們困惑地對視了一眼,忽然在黑暗中又親近起來。沿著吱嘎作響的走道,我們在右邊找到了廚房,屋外的那位年輕女孩現在站在爐子邊看著一鍋熱騰騰的牛奶。她拿下了頭巾,深金色的長髮垂在後背。
「過來坐。」角落餐桌一名老婦人說道:「你們一定餓了吧。」
我們坐在木頭椅子上,椅子吱嘎地承受我們的體重。所有東西像是曾經沾滿了灰塵,因為一代代的使用而磨損,盤子破裂又用黏膠黏回,杯子上的圖案褪去。珍珠似的微弱光線從一扇小窗子透了進來。
老婦人以銳利好奇的眼神打量我們。「我丈夫出去了。」她說:「你們請自便。」我這才明白她其實沒有那麼老,她不是女孩的祖母,而是她的媽媽。
我們開始吃早餐,有黃瓜、蘿蔔、一罐蜂蜜和一大塊麵包。女孩從爐邊走來,把熱牛奶倒進我們的杯子。
「所以你們是學生?」媽媽問道。
「是的,女士。」你嘴巴咬著蘿蔔回答,看起來比我自在。「我們剛畢業。」
她點點頭,彷彿認同了某件不確定的事。「結婚了嗎?」她看著你。
「沒有,女士。」你搖搖頭,對她笑了笑。「還沒有,我還年輕。」
她發出沙啞的笑聲,顯露出她少了兩顆門牙。「你呢?」她轉向我。
我感覺到自己臉紅了。「沒有,女士。」我喝了一口牛奶,隱藏自己的尷尬。我的嘴唇擦過牛奶上方形成的軟膜,使得肚子傳來一陣噁心感,牛奶燙到口腔內部。我努力保持正常神情,伸手去拿麵包。
她明顯滿足地看著我們吃東西。「所以你們是在旅行,知道要去哪嗎?」
「只是要尋找一個安靜的地點。」你說:「女士,可以推薦什麼地方嗎?」
她看著窗外,但這面窗看不太到外面的景象,只有朦朧的樹木綠意和隱約的天空青藍。「離這裡不遠有個地方,我們秋天會過去採蘑菇。一般旅人不知道這地方,那裡很漂亮。」她的眼神閃亮,而剎那間我見到,真的見到她也曾經年輕過。「我會跟你們說怎麼過去。」
早餐過後,我們捲起睡袋,打包行李。
「就一直走,從馬里安基交叉口穿過森林,大約六公里。」婦人站在農舍門口說道:「到了你就知道了。」
「謝謝,你們真是親切。」我說。
她堅實蠟質般的雙手捧住我的臉,往臉頰乾澀一吻。「回來時過來看看我們,旅途愉快。」
在附近的村莊,我們找到一輛要去相同方向的卡車。司機載了櫻桃北上,唯一可以給我們坐的地方是在後方,就在一大堆水果之間。我們一直吃到沒了飢餓感,整個塞滿嘴巴,弄髒雙手,把果核吐向行經的田野。天空明亮,無邊無際;感覺就好像我們飛翔其間。經過的每一個農場屋頂幾乎都有一個鸛巢,這優雅的生物結束從非洲而來的長途飛行後,在上頭休憩,或展翅準備找尋食物。
我們一路不停往前開,經過使用手推車和馬匹在田裡做事的人們,男人、女人和孩子拿著木製鋤頭工作。野花和呈現金黃的高高田野和藍天相連,然後地勢變得平坦,第一座cerkwie映入眼簾,這是最早的東正教教堂,黑色小巧,有著帶有神秘意味的球狀圓頂。這標示出一個不同的國度,是荒涼難解的東方之始,國王曾在這裡狩獵野牛,平原一望無際。司機停在一個幾乎看不出的十字路口,頭探出窗外。「少年們,就是這裡。」我們跳下車,發現自己站在松樹林的入口。
「你確定嗎?」我問。
他點點頭,祝我們好運就揚塵而去。我們對視,猶豫不決。
「我們確定要去嗎?」我問,頓然意識到再度只有我和你,緊張得就跟第一天認識你當時一樣。
「還能怎麼做呢?」你鎮靜地說,面露笑容。「走吧。」你的手放在我的下背部,推著我跟你一起走進森林,一股暖流傳過我全身。
如同那婦人說的,這裡有一條狹窄的小徑。我們走進松木樹海,裡面比陽光底下來得冷暗。我們肩並肩走在滿地肉桂色的乾枯松針上,前一晚的記憶如浮標般漂浮在我腦海:屋頂上的落雨,你的頭靠在我肩膀上的重量。我努力甩開它。你穿著昨天那件亞麻襯衫,隔了一夜已經乾了,現在沾上櫻桃汁,未扣的鈕釦露出鎖骨,可以想見布料底下乳頭的深暈。
森林愈來愈茂密,天空似乎遠離,陽光幾乎照不到我們,但前人走出的小徑始終一直延伸。你敏捷地走在前方,我跟隨在後。我們沒有交談,你也從未轉頭查看我是否落後,彷彿兩人之間有著絲線相連。
「他們人真好,對吧。」我一度開口填補沉默,掩飾自己的思緒。
你點點頭,並未回頭。「對,沒錯。」
你似乎跟我一樣陷入沉思。我們不斷走著,樹木開始變得稀疏;陽光再度透了進來。不久,我們在遠方看到了森林盡頭,還有閃閃發光的東西。我們加快腳步,幾乎跑了起來。來到最後一排樹木時,我們看到了:林間空地中坐落著一汪燦爛的湖泊,高高的草叢圍繞著,像個秘境。我們更加靠近,眼前的發現讓我膝蓋發軟。湖面在午後光線下閃耀著寧靜的深藍。附近毫無人跡,我們走到湖邊,放下背包,望過這片在午後太陽照射下如鏡子般的湖景。森林包圍著我們,我們就在它的正中心,受到這顆晶亮眼睛的保護和撫慰。
「我們到了。」我低語。
你點點頭。
「那老婦人沒有誇大!」你倏地大喊,旋即採取動作。你脫掉衣服,一件接著一件拋開,直到完全自由,白皙的臀部和棕色的背部色形成對比。你發出響徹空地的尖叫聲,跳入湖中,然後帶著得意的笑容重現浮出水面。
「要下來嗎?」
我先脫掉涼鞋,然後是襯衫。我小心翼翼摺好它,放在地面的柔軟處。我脫下短褲,然後略帶遲疑地褪下內褲。你已轉身離開,游得有點遠。我站在這裡感覺微風撫過胸膛,搔弄腿間。我注視著湖水,看不到水底,無法估算它的深度。但我還是踏了進去,湖水柔軟冰涼地擁抱了我。我感覺自己重新出發,彷彿內心有什麼東西經過長久時間後啟動了。這是一種輕盈、有力,完全矛盾的感覺。我開始移動,每一個動作都推動我前進。上方的天空比水面明亮,散落著小小雲朵。我留意著未知的水面下。
「瞧,你辦得到!」你欣喜地從湖的另一頭高喊。
我保持鎮靜。
我的身體游向你的方向,你看著我,突然也平靜下來。你的雙手往兩側伸展,有如舞動空中的芭蕾舞者。在湖面底下,某種溫暖的東西在我的肚子裡騷動。我靠近你,直到可以看見你額頭、鼻尖和嘴角上的水珠。我們默默不語,看著彼此,已經無法言喻。你在,我也在,親近,呼吸著。我游向你的圈圈,一直來到你等待的身軀、開朗沉著的臉龐,以及唇上的水滴。你的雙臂用力緊密地環繞著我,此時,我們成了漂浮在湖中的單一形體,失重,永遠碰不著地面。
那一天晚上,當太陽開始西沉,我們在一棵巨大松樹底下搭起帳篷。氣溫仍舊暖和,湖面變黑,蟬鎮定地鳴叫,除了淡淡的月光外,沒有任何光線。我們躺在睡袋上,風輕輕吹過帳篷,唯一的聲響來自上方松樹的擺動,針葉沙沙作響,對著彼此低喃。我們仰躺,雙手枕著頭,手肘輕觸。透過帳篷頂的掀布,我們見到繁星滿天。星星微小,乍見似乎沒那麼多,但愈是細看,數量就愈多,永遠無法持久看盡全部。看著星星,讓我暖暖地頭暈了起來。
「我很高興這件事發生了。」我說,享受著自己的聲音,以及它在我身體的震動。
「我也是。」你的頭轉向我,眼睛發亮。「我一開始就知道它會發生。」你含笑說道。
「哦,是嗎?」
「對,就在我們抵達的第一天,你看著我的時候,你很容易看透。」
我大笑,推了推你。「哦,是嗎?」
你聞起來是湖水和松樹的味道,有著柔軟,有著堅硬。我可以感覺到你在我指尖下的古銅色,你用強壯堅實的雙手讓我煥然一新,創造我,我的腰際,我的大腿內側……還有你。你的背,你的胸膛,你的腹部,你的大腿,你的昂揚,在柔軟內褲底下堅硬且不可思議地貼近,愛撫我的手掌,明顯的,天崩地裂,索求著。我們熱烈又掙扎地移動,無論我怎麼嘗試,仍有太多我無法饜足,太多我永遠無法掌握和擁有的東西。我嘗試,我們一起嘗試,覆蓋著彼此,融為一體,抽動,跟隨著抽動,讓它的趨向掌控一切。我們的嘆息一致,拒絕釋放我們。那一晚讓我想起小時候在附近公園看到的復活節營火,金字塔狀的木堆從上方燃燒到底下,驅逐冬日的幽魂,帶來融雪,從休眠休憩中釋出溫暖。火焰催眠了我,我和它合而為一,一起舞動、摧毀和承受。我們進行了這場奮力的掙扎,氣喘吁吁,興高采烈,頭暈腦脹,為之目眩,直到筋疲力竭,直到我們對著彼此釋放自己,如水草般交纏著入睡。
我不知道我們在湖邊待了多久,因為每一天都像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每一個時刻都是嶄新和無法重複的。就某方面來說,這彷彿是我生命的最初時日,彷彿我是憑著這座湖、這湖水和你而生。我彷彿蛻了皮,棄置之前的人生。
這座湖和森林成了我們的領土。我們釣魚,利用樹枝製作釣竿,小塊麵包作餌;在火堆上烤著這灰色扁平又美味的魚兒,再直接用手指抓著吃。我們走進湖泊另一頭的森林,發現了漿果灌木,起居室大小的空地,樹枝底下有著一叢叢白色花朵。我們會躺下來做愛,之後入睡。我們會在朦朧的幸福中醒來,發現太陽依舊高掛,走回帳篷時,唯一留下的是,我們在草地上壓出的身形。
湖水每天上午和傍晚洗滌了我們,沖走夏日和做愛的汗水,甚至是我們身體上的指紋。我每次游泳都感受到首次踏入湖水時的相同興奮之情,毫無掙扎,一種我不曾料到自己可以感覺到的失重感。在這些日子裡,我內心的羞恥感像是舌頭上的薄荷融化了,從堅硬釋放出香甜。
我漂浮在水中,而你躺在湖畔讀著《喬凡尼的房間》。溫度跟我們的肌膚相同或略低的空氣,愛撫著我們。之後,我們會並肩躺著,看著雲朵,觀察它們奇妙的形狀變化:從無法辨認到熟悉,熟悉到無法辨認。
在即將結束停留的一天下午,我們走了大約一小時的路程,前往最近的村莊。我們找到一家小店,買了一些麵包、黃瓜、蘋果和啤酒。回程的時候,太陽開始西下,我們還沒走到森林就天黑了,你忘了帶手電筒,小徑只憑藉月光照亮。當我們沿著田野行走,兒時噩夢的景象回到我的腦海,就像來自過去的挑戰──世界空虛寂靜,田野往四面八方延伸,巨石在背後盯著我看。但是,我甚至不用判斷自己是否害怕,我不怕,墓碑──以及羞恥感──只是回憶,像方糖般溶解在夏日雨水中。
我們穿過森林行走,聽著林中鬼祟的聲響,直到抵達我們的空地,見到湖面上月光的倒影。我們駐足凝視,接著默默不語,脫下了衣服,滑入水中。我們游泳,在明亮的黑暗中,感到無所畏懼,自由,而且隱形。
「晚安。」你關上手電筒後說道。你毫不忸怩地脫掉衣服,只見你黑暗中的剪影爬進了我身邊的睡袋。我聽得到你的呼吸,像是輕柔的浪濤聲。然後,滴滴答答,雨又逐漸下了起來,彷彿練習鋼琴和弦的指尖,敲擊著屋頂。我們仰躺聆聽,靜默不語。我感受到你在附近,你的身子雖然靜止不動,卻不知怎地充滿生氣。我的心跳比雨滴聲更加快速,忽然間,我想要靠近你,迫切想要如此。我可以感覺到你身體的拉力,小小的細繩扯著我靠向你。但我無法移動,心臟直跳,心中度過了數光年的來回,就在我開始認為自己絕不可能有勇氣時,你挪向我,頭枕在我的肩膀上。我的心跳停拍,不敢呼吸。你的頭好沉,像是溫暖的大理石,髮絲拂過我的臉頰。可能性讓我動彈不得,困在滿足的眩暈感以及不確定的深淵之間。我想到多年前的那一晚,在舞會上燈光熄滅時,我對貝尼克的舉動是多麼魯莽,帶來多麼痛苦和無法預料的後果。儘管如此,我才剛鼓起勇氣想著碰觸你的頭髮會怎樣,思索這是唯一可做的正確舉動,而且現在和當時不一樣,就聽到你輕聲說:「晚安,路茲歐。」然後挪離我身邊。這是你第一次這樣呼喚我,深情地變換了我的名字。這讓我肩膀上的空虛感更加難以忍受。
「晚安。」我勉強回答,轉過身子,感覺陣陣懊悔。你的呼吸開始平緩穩定,而我的心思像瘋馬一樣狂奔。雨下了一整晚。
清晨醒來,我見到你的身軀隨著呼吸上下起伏。透過木板縫隙,一道道光束進入穀倉,照亮了你。你的肩膀散落著我從未注意到的小雀斑,如星座一樣隨意而美麗。
我盡可能悄悄爬出睡袋,穿上T恤和短褲,套上涼鞋,走進外頭的晨光。這是個晴朗的日子,太陽已經升起,柔和新鮮,跟剛剝好的雞蛋一樣。空氣聞起來有綠色、黃色和肥沃深棕色的感覺。在白天的光線下,農舍比我記憶中的小,只有一層樓高,深色木材建造,加上老舊棕色瓦片搭成的陡峭屋頂。它看起來既古老又脆弱,彷彿已屹立在這個地方一輩子了,卻可能很容易就被搗毀。在農舍外頭,農人女兒餵著雞,她大約十五歲,戴著頭巾,有著充滿活力的心形臉蛋和孩子氣的羞怯淺笑。她跟我打招呼,並邀請我們去吃早餐。
「我們在廚房。」她說:「帶你的朋友一起來。」
我回到穀倉,發現你已經起身,正往緊身的白色內褲套上長褲。
「嗨。」我說,意識到自己刻意的聲音。
你拉上拉鍊,轉過身來。「嗨。」你看起來幾乎像是害羞,一隻手梳過頭髮。
「餓了嗎?」我問。
「餓死了。」
我們走出穀倉,進入農舍。裡面有一條陰暗的走廊,聞起來有黴味、煤煙和泥土的味道。一切似乎都靜止了。幾道光束揭露了漂浮在空中的塵埃世界,牆壁上,耶穌被釘在十字架,除了纏腰帶外一絲不掛,肌肉和肋骨清晰可見。我們困惑地對視了一眼,忽然在黑暗中又親近起來。沿著吱嘎作響的走道,我們在右邊找到了廚房,屋外的那位年輕女孩現在站在爐子邊看著一鍋熱騰騰的牛奶。她拿下了頭巾,深金色的長髮垂在後背。
「過來坐。」角落餐桌一名老婦人說道:「你們一定餓了吧。」
我們坐在木頭椅子上,椅子吱嘎地承受我們的體重。所有東西像是曾經沾滿了灰塵,因為一代代的使用而磨損,盤子破裂又用黏膠黏回,杯子上的圖案褪去。珍珠似的微弱光線從一扇小窗子透了進來。
老婦人以銳利好奇的眼神打量我們。「我丈夫出去了。」她說:「你們請自便。」我這才明白她其實沒有那麼老,她不是女孩的祖母,而是她的媽媽。
我們開始吃早餐,有黃瓜、蘿蔔、一罐蜂蜜和一大塊麵包。女孩從爐邊走來,把熱牛奶倒進我們的杯子。
「所以你們是學生?」媽媽問道。
「是的,女士。」你嘴巴咬著蘿蔔回答,看起來比我自在。「我們剛畢業。」
她點點頭,彷彿認同了某件不確定的事。「結婚了嗎?」她看著你。
「沒有,女士。」你搖搖頭,對她笑了笑。「還沒有,我還年輕。」
她發出沙啞的笑聲,顯露出她少了兩顆門牙。「你呢?」她轉向我。
我感覺到自己臉紅了。「沒有,女士。」我喝了一口牛奶,隱藏自己的尷尬。我的嘴唇擦過牛奶上方形成的軟膜,使得肚子傳來一陣噁心感,牛奶燙到口腔內部。我努力保持正常神情,伸手去拿麵包。
她明顯滿足地看著我們吃東西。「所以你們是在旅行,知道要去哪嗎?」
「只是要尋找一個安靜的地點。」你說:「女士,可以推薦什麼地方嗎?」
她看著窗外,但這面窗看不太到外面的景象,只有朦朧的樹木綠意和隱約的天空青藍。「離這裡不遠有個地方,我們秋天會過去採蘑菇。一般旅人不知道這地方,那裡很漂亮。」她的眼神閃亮,而剎那間我見到,真的見到她也曾經年輕過。「我會跟你們說怎麼過去。」
早餐過後,我們捲起睡袋,打包行李。
「就一直走,從馬里安基交叉口穿過森林,大約六公里。」婦人站在農舍門口說道:「到了你就知道了。」
「謝謝,你們真是親切。」我說。
她堅實蠟質般的雙手捧住我的臉,往臉頰乾澀一吻。「回來時過來看看我們,旅途愉快。」
在附近的村莊,我們找到一輛要去相同方向的卡車。司機載了櫻桃北上,唯一可以給我們坐的地方是在後方,就在一大堆水果之間。我們一直吃到沒了飢餓感,整個塞滿嘴巴,弄髒雙手,把果核吐向行經的田野。天空明亮,無邊無際;感覺就好像我們飛翔其間。經過的每一個農場屋頂幾乎都有一個鸛巢,這優雅的生物結束從非洲而來的長途飛行後,在上頭休憩,或展翅準備找尋食物。
我們一路不停往前開,經過使用手推車和馬匹在田裡做事的人們,男人、女人和孩子拿著木製鋤頭工作。野花和呈現金黃的高高田野和藍天相連,然後地勢變得平坦,第一座cerkwie映入眼簾,這是最早的東正教教堂,黑色小巧,有著帶有神秘意味的球狀圓頂。這標示出一個不同的國度,是荒涼難解的東方之始,國王曾在這裡狩獵野牛,平原一望無際。司機停在一個幾乎看不出的十字路口,頭探出窗外。「少年們,就是這裡。」我們跳下車,發現自己站在松樹林的入口。
「你確定嗎?」我問。
他點點頭,祝我們好運就揚塵而去。我們對視,猶豫不決。
「我們確定要去嗎?」我問,頓然意識到再度只有我和你,緊張得就跟第一天認識你當時一樣。
「還能怎麼做呢?」你鎮靜地說,面露笑容。「走吧。」你的手放在我的下背部,推著我跟你一起走進森林,一股暖流傳過我全身。
如同那婦人說的,這裡有一條狹窄的小徑。我們走進松木樹海,裡面比陽光底下來得冷暗。我們肩並肩走在滿地肉桂色的乾枯松針上,前一晚的記憶如浮標般漂浮在我腦海:屋頂上的落雨,你的頭靠在我肩膀上的重量。我努力甩開它。你穿著昨天那件亞麻襯衫,隔了一夜已經乾了,現在沾上櫻桃汁,未扣的鈕釦露出鎖骨,可以想見布料底下乳頭的深暈。
森林愈來愈茂密,天空似乎遠離,陽光幾乎照不到我們,但前人走出的小徑始終一直延伸。你敏捷地走在前方,我跟隨在後。我們沒有交談,你也從未轉頭查看我是否落後,彷彿兩人之間有著絲線相連。
「他們人真好,對吧。」我一度開口填補沉默,掩飾自己的思緒。
你點點頭,並未回頭。「對,沒錯。」
你似乎跟我一樣陷入沉思。我們不斷走著,樹木開始變得稀疏;陽光再度透了進來。不久,我們在遠方看到了森林盡頭,還有閃閃發光的東西。我們加快腳步,幾乎跑了起來。來到最後一排樹木時,我們看到了:林間空地中坐落著一汪燦爛的湖泊,高高的草叢圍繞著,像個秘境。我們更加靠近,眼前的發現讓我膝蓋發軟。湖面在午後光線下閃耀著寧靜的深藍。附近毫無人跡,我們走到湖邊,放下背包,望過這片在午後太陽照射下如鏡子般的湖景。森林包圍著我們,我們就在它的正中心,受到這顆晶亮眼睛的保護和撫慰。
「我們到了。」我低語。
你點點頭。
「那老婦人沒有誇大!」你倏地大喊,旋即採取動作。你脫掉衣服,一件接著一件拋開,直到完全自由,白皙的臀部和棕色的背部色形成對比。你發出響徹空地的尖叫聲,跳入湖中,然後帶著得意的笑容重現浮出水面。
「要下來嗎?」
我先脫掉涼鞋,然後是襯衫。我小心翼翼摺好它,放在地面的柔軟處。我脫下短褲,然後略帶遲疑地褪下內褲。你已轉身離開,游得有點遠。我站在這裡感覺微風撫過胸膛,搔弄腿間。我注視著湖水,看不到水底,無法估算它的深度。但我還是踏了進去,湖水柔軟冰涼地擁抱了我。我感覺自己重新出發,彷彿內心有什麼東西經過長久時間後啟動了。這是一種輕盈、有力,完全矛盾的感覺。我開始移動,每一個動作都推動我前進。上方的天空比水面明亮,散落著小小雲朵。我留意著未知的水面下。
「瞧,你辦得到!」你欣喜地從湖的另一頭高喊。
我保持鎮靜。
我的身體游向你的方向,你看著我,突然也平靜下來。你的雙手往兩側伸展,有如舞動空中的芭蕾舞者。在湖面底下,某種溫暖的東西在我的肚子裡騷動。我靠近你,直到可以看見你額頭、鼻尖和嘴角上的水珠。我們默默不語,看著彼此,已經無法言喻。你在,我也在,親近,呼吸著。我游向你的圈圈,一直來到你等待的身軀、開朗沉著的臉龐,以及唇上的水滴。你的雙臂用力緊密地環繞著我,此時,我們成了漂浮在湖中的單一形體,失重,永遠碰不著地面。
那一天晚上,當太陽開始西沉,我們在一棵巨大松樹底下搭起帳篷。氣溫仍舊暖和,湖面變黑,蟬鎮定地鳴叫,除了淡淡的月光外,沒有任何光線。我們躺在睡袋上,風輕輕吹過帳篷,唯一的聲響來自上方松樹的擺動,針葉沙沙作響,對著彼此低喃。我們仰躺,雙手枕著頭,手肘輕觸。透過帳篷頂的掀布,我們見到繁星滿天。星星微小,乍見似乎沒那麼多,但愈是細看,數量就愈多,永遠無法持久看盡全部。看著星星,讓我暖暖地頭暈了起來。
「我很高興這件事發生了。」我說,享受著自己的聲音,以及它在我身體的震動。
「我也是。」你的頭轉向我,眼睛發亮。「我一開始就知道它會發生。」你含笑說道。
「哦,是嗎?」
「對,就在我們抵達的第一天,你看著我的時候,你很容易看透。」
我大笑,推了推你。「哦,是嗎?」
你聞起來是湖水和松樹的味道,有著柔軟,有著堅硬。我可以感覺到你在我指尖下的古銅色,你用強壯堅實的雙手讓我煥然一新,創造我,我的腰際,我的大腿內側……還有你。你的背,你的胸膛,你的腹部,你的大腿,你的昂揚,在柔軟內褲底下堅硬且不可思議地貼近,愛撫我的手掌,明顯的,天崩地裂,索求著。我們熱烈又掙扎地移動,無論我怎麼嘗試,仍有太多我無法饜足,太多我永遠無法掌握和擁有的東西。我嘗試,我們一起嘗試,覆蓋著彼此,融為一體,抽動,跟隨著抽動,讓它的趨向掌控一切。我們的嘆息一致,拒絕釋放我們。那一晚讓我想起小時候在附近公園看到的復活節營火,金字塔狀的木堆從上方燃燒到底下,驅逐冬日的幽魂,帶來融雪,從休眠休憩中釋出溫暖。火焰催眠了我,我和它合而為一,一起舞動、摧毀和承受。我們進行了這場奮力的掙扎,氣喘吁吁,興高采烈,頭暈腦脹,為之目眩,直到筋疲力竭,直到我們對著彼此釋放自己,如水草般交纏著入睡。
我不知道我們在湖邊待了多久,因為每一天都像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每一個時刻都是嶄新和無法重複的。就某方面來說,這彷彿是我生命的最初時日,彷彿我是憑著這座湖、這湖水和你而生。我彷彿蛻了皮,棄置之前的人生。
這座湖和森林成了我們的領土。我們釣魚,利用樹枝製作釣竿,小塊麵包作餌;在火堆上烤著這灰色扁平又美味的魚兒,再直接用手指抓著吃。我們走進湖泊另一頭的森林,發現了漿果灌木,起居室大小的空地,樹枝底下有著一叢叢白色花朵。我們會躺下來做愛,之後入睡。我們會在朦朧的幸福中醒來,發現太陽依舊高掛,走回帳篷時,唯一留下的是,我們在草地上壓出的身形。
湖水每天上午和傍晚洗滌了我們,沖走夏日和做愛的汗水,甚至是我們身體上的指紋。我每次游泳都感受到首次踏入湖水時的相同興奮之情,毫無掙扎,一種我不曾料到自己可以感覺到的失重感。在這些日子裡,我內心的羞恥感像是舌頭上的薄荷融化了,從堅硬釋放出香甜。
我漂浮在水中,而你躺在湖畔讀著《喬凡尼的房間》。溫度跟我們的肌膚相同或略低的空氣,愛撫著我們。之後,我們會並肩躺著,看著雲朵,觀察它們奇妙的形狀變化:從無法辨認到熟悉,熟悉到無法辨認。
在即將結束停留的一天下午,我們走了大約一小時的路程,前往最近的村莊。我們找到一家小店,買了一些麵包、黃瓜、蘋果和啤酒。回程的時候,太陽開始西下,我們還沒走到森林就天黑了,你忘了帶手電筒,小徑只憑藉月光照亮。當我們沿著田野行走,兒時噩夢的景象回到我的腦海,就像來自過去的挑戰──世界空虛寂靜,田野往四面八方延伸,巨石在背後盯著我看。但是,我甚至不用判斷自己是否害怕,我不怕,墓碑──以及羞恥感──只是回憶,像方糖般溶解在夏日雨水中。
我們穿過森林行走,聽著林中鬼祟的聲響,直到抵達我們的空地,見到湖面上月光的倒影。我們駐足凝視,接著默默不語,脫下了衣服,滑入水中。我們游泳,在明亮的黑暗中,感到無所畏懼,自由,而且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