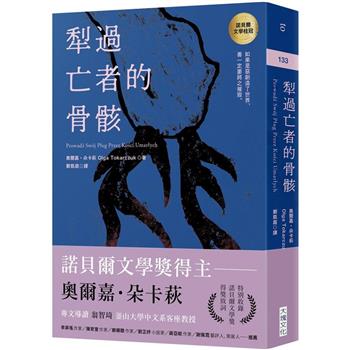1. 現在你們可注意了!
「曾經,正義之人踏上險路,堅定地走過死亡之谷。」
我已經到了這把年紀,處於睡前總得把雙腳好好洗乾淨的狀態,以免救護車得在夜裡把我接走。
要是這天晚上我檢查了星曆表,知道天空中正發生什麼事,我根本就不會去睡覺。那時我睡得可沉了。我以啤酒花茶助眠,還吞了兩粒纈草錠。因此,半夜的敲門聲把我吵醒時──敲得急促、逼人,由此可知是不祥的――我無法清醒過來。我猛然起身站在床邊,因為睡眼迷濛而搖來晃去,鬆軟的身子無法從純真的睡夢切換到現實中。我覺得很虛弱,踉踉蹌蹌,就像快要失去意識。很不幸,最近這才剛發生在我身上,與我的一些疾病有關。我不得不坐下,並重複對自己說好幾次:我在家裡、現在是半夜、有人敲門。這才成功控制住自己的神經。我在黑暗中尋找拖鞋時,聽到那名大力敲門的人正在屋外喃喃自語走來走去,我的防身噴霧在樓下的電錶櫃裡,是迪歐尼西給我防盜獵者用的,而我現在確實認為有盜獵者。我在黑暗中順利找出熟悉且冰涼的噴霧罐,以此武裝自己,並點亮外頭所有的燈,透過側邊窗子盯著門廊。雪地沙沙作響,一位被我稱為「怪人」的鄰居出現在我視線裡。他以雙手將舊羊皮大衣的雙襟按在腰間。他在房子附近做事時我有時會看見這件大衣。兩條穿著條紋睡褲和登山靴的腿從羊皮大衣底下伸出來。
「開門。」他說。
他毫不隱藏訝異,瞥了一眼我的夏季亞麻西裝(我睡覺時都穿著這套西裝,每年夏天教授夫婦都想把它丟掉,它卻能讓我回味舊時潮流和年少時光──我用以連結實用與感性),並毫無歉意地走進屋裡。
「請妳穿好衣服。大腳死了。」
我驚訝得一時說不出話,靜靜穿上高筒雪靴,套上從衣架隨意抓起的羊毛衫。
外頭的雪在門廊射出的光線下成了一場緩慢如夢的落雪。高䠷纖瘦的怪人默默站在我身旁,瘦骨嶙峋,像是以鉛筆撇了幾筆的人形。他每動一下,雪片便會從他身上抖落,像從沾滿糖粉的天使翅膀 1 落下。
「怎麼會死了呢?」開門時,我仍舊用緊縮的喉嚨問了出口,但是怪人沒回答。
他的話原本就很少,水星大概落在沉默的星座上,我認為是摩羯座,要麼是合相、四分相,要麼就是與土星相沖。也可能是水星逆行──那麼特徵便會不那
麼明顯。
1
一種以麵粉製成的脆餅,上面灑滿糖粉,因其扭結形狀得名「天使翅膀」,是波蘭於復活節大齋前的胖胖星期四(Fat Thursday)常吃的食物。
大塊文化我們走出房子,立刻受到熟悉、冷冽的潮溼空氣籠罩。每次冬季都提醒著我們,這世界並不為人類而生,至少有大半年的時間都對我們表現出敵意。冰霜狠狠掃過我們臉頰,白色熱氣從我們嘴裡流出。門廊的燈自動熄滅,我們在一片漆黑中走過沙沙作響的雪地。怪人的頭燈不算在內,它在他前方一個正移動的點上刺穿一片黑暗,我則在黑暗中搖搖晃晃跟在他背後「你沒有手電筒嗎?」他問。
當然了,我有,但是在哪裡?這我得等到早上,藉著白天的光亮才能知道。
手電筒總是這樣的,只有在白天時才看得見。
大腳的家有些偏僻,所在的位置比其他房子都高。那是全年都有人居住的三間房子之一。只有他、怪人和我不畏懼寒冬、住在這裡。其他的住戶早在十月就緊緊鎖上家門,排空水管裡的水,回到城市。
我們現在轉出約略清過積雪的道路。這條路行經我們的聚落,並岔成通往每棟房子的小徑。深厚的積雪被踏出一條通向大腳家的小徑,路窄到得迅速將一腳踩在另一腳前,不斷保持平衡。
「那可不是什麼怡人的畫面,」怪人一邊出言警告,一邊轉朝向我。我一下子頭暈目眩。
我也沒期待會看到別的景象。他沉默了一陣子,似乎想為自己解釋,然後接著說:
「他的廚房燈和那隻母狗的絕望叫聲打擾到我了。妳什麼都沒聽見嗎?」
沒有,我沒聽見。我睡著了,被啤酒花和纈草迷昏了。
「那隻母狗現在在哪裡?」
「我帶回我家了,餵牠吃過東西,現在牠或許已經冷靜下來了。」
又是一陣沉默。
「他通常很早就熄燈睡覺,很省電,這次卻把燈打開、任它亮著。從我的臥室可以看到雪地上有一道亮光,所以我就走過去他家。我想他可能喝多了,或是在對狗做些什麼,牠才會那樣嚎叫。」
我們經過一座廢棄穀倉,過了一會兒,怪人的手電筒引出黑暗中兩雙亮著綠色螢光的眼睛。
「你看,是麃鹿!」我抓住他羊皮大衣的袖子,興奮地低聲說:「牠們走得離房子這麼近,不會害怕嗎?」
麃鹿站在差不多及腰的雪裡,冷靜地盯著我們,彷彿被我們逮到正在進行什麼無法理解意義的儀式。因為太暗,所以我無法判斷牠們是不是秋天時從捷克來到這裡的母麃鹿,又或是新來的?而且為什麼只有兩隻?那群麃鹿至少有四隻。
「你們回家吧!」我揮著手對牠們說,牠們抖了一下,但沒有移動,平靜地目送我們到門口。我的背脊都涼了。
與此同時,怪人正在那間疏於照料的小屋門前跺腳,抖落靴子上的雪。小窗以鋁箔和紙封起,木門被黑色焦油紙蓋住。
大塊文化玄關的牆壁疊滿柴火,全是不均勻的原木。這個空間令人感到不適,沒什麼好說,亂七八糟又骯髒。到處都是潮溼、木頭和土地的氣味──溼濡且貪婪。長年的惡臭煙霧在牆壁上結成一層煙垢。
廚房的門半掩著,我立刻看見攤在地上的大腳屍體,目光一觸碰到他便閃開,花了一段時間才有辦法再次看向那兒。那個畫面很嚇人。
他以詭異的姿勢扭曲地躺著,雙手抱著脖子,似乎想奮力扯下勒在上頭的衣領。我像被催眠般慢慢靠近,看到他睜開的雙眼盯著桌下某處。髒兮兮的 T 恤在靠近喉嚨處被撕破。看上去就像肉體在與自己的搏鬥中遭到打敗、並且陣亡。恐懼令我感到寒冷,凍結了血管中的血液,我感覺血液退入我體內最深處。昨天我看到這副身體時,他還活跳跳的。
「我的天啊!」我喃喃說道。「這是怎麼了?」怪人聳了聳肩。
「我聯繫不了警察,又被捷克的訊號蓋住了。」
我從口袋裡掏出手機,輸入從電視上看到的號碼──997,過了一會兒,捷克的自動語音在我的手機上響起。這裡的情況就是如此,訊號游移不定、無視國界。有時候,電信公司的邊界會在我的廚房裡停留許久,有時又在怪人的房間或陽臺上待個幾天,但它多變的性格令人很難預測。
「得走出去到高一點的地方,去小山上。」我的建議來遲了。
「等不到他們抵達他就會完全僵硬。」怪人說道,用一種我特別不喜歡在他身上聽到的語氣:好像他什麼都懂。他脫下羊皮大衣,掛在椅背上。
「我們不能讓他就這樣躺在這兒,他看起來糟透了,畢竟他也是我們的鄰居。」我看著大腳淒慘捲曲的屍體,難以相信我昨天還對此人感到恐懼。我不喜歡他。說我不喜歡或許還言之過輕。我或許該說他讓我覺得噁心、嫌惡。事實上,我根本不覺得他算人類。現在的他躺在汙跡斑斑的地板上,穿著髒兮兮的內衣,渺小又乾癟,無力且無害。就只是一塊物質,藉著令人摸不著頭緒的轉變,變成與一切分離的脆弱實體。這讓我感到難過驚恐,因為,即使是像他一般令人厭惡的人,也不該死。可是誰又該死呢?同樣的命運正等著我和怪人,以及外面那群麃鹿。我們最終也不過就是一具具的屍體。
我看向怪人,想從他那兒尋求一絲安慰,但他忙著在一團亂的破爛沙發床上鋪髒被單,所以我只好試著在腦中安撫自己。那時,我突然有個想法:大腳的死就某種意義上是件好事。死亡讓他從生命的混亂中解脫,其他生命也從他手中解脫。噢,對,我突然意識到死亡有多美好、多正義,就像消毒劑、吸塵器一般。
我承認我當時就是這麼想。事實上,我到現在仍這麼認為。
他是我的鄰居,我們的房子相距不到半公里,但是我很少和大腳打交道。真是萬幸。我總是遠遠看著他──看他肌肉發達的瘦小身軀,總是搖搖晃晃地在風景中移動。他會一邊走一邊嘟囔,高地上的風響偶爾會把片段獨白遞到我這裡,基本上都是些簡單又沒變化的話語。他的字典主要用咒罵組成,只在其中加入些大塊文化特定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