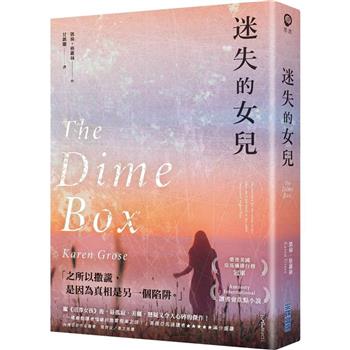第一章
葛芮塔僵硬地坐在硬背椅上。寂靜的氣氛帶來壓迫感。她不想承認的一些想法──那些在她腦海中的角落裡爬行、存在的想法──悄悄進入了光亮處。警方的調查為什麼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她已經給出了說詞,回答了每個問題。只有其中一個問題讓她吃驚。
女兒對父母的義務是什麼?
葛芮塔不確定自己對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有什麼義務。她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答不出來。
但這不是事實……她其實知道為什麼。
如果她老實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刑警們可能會看到她努力馴服的原始、野性的一面,而這麼做的風險太大。她已經埋葬了過去,她想往前走。所以她讓那個特定的疑問懸而未決。
幾分鐘後,門打開了。裴瑞茲警探走進房間,走到她的辦公桌前,在椅子上坐下,查看手裡的文件。她摘下老花眼鏡,放在面前。
葛芮塔胸口緊繃。即使有律師在身邊,她還是覺得呼吸困難。她伸手摸摸牛仔褲的前口袋,發現裡面藏著一枚硬幣。她揉揉它,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用鼻子吸氣,用嘴巴呼氣。緩慢而穩定的呼吸。
裴瑞茲警探盯著她,開口道:「我們走一遍流程。」
葛芮塔嘆氣。走流程?又一次?
「警方負責立案調查。」警探告訴她。
她點頭。她知道。有時候他們會諮詢檢察官。
「我們蒐集證據。」
嗯。她以前都聽過了。
「在妳這樣的案件上,我想說明所有可能性。」警探的語氣像是在進行日常的例行談話。
葛芮塔繃緊身子,咬緊牙關,試著保持鎮定。
裴瑞茲警探舉起一手,把一支鉛筆按在指尖上。「一:一級謀殺;二:二級謀殺;三:誤殺。」
葛芮塔說出第四個可能性。「或是不起訴,我無罪釋放。」
警探沉默幾秒,再次說話時沒看著葛芮塔的律師。「是沒錯,而且──」
手機嗡嗡作響,打斷了她的話語。裴瑞茲警探把手伸過桌面,輕按手機左側的按鈕,將它靜音。她抱歉地笑了笑,瞥一眼自己的筆記。
「之後,透過驗屍官的報告和我們的調查,我會判斷是否有足夠的證據來提出指控。」警探停頓下來,看著她。「而我做了那個決定。」
葛芮塔心跳急促。她口乾舌燥。見真章的時候到了。她盯著警探,好奇對方在想什麼。什麼樣的人下得了手殺害自己的父母?但是警探的眼睛什麼也沒有透露。
手機再次發光。雖然沒發出聲音,但葛芮塔能透過桌面感覺到震動。警探低頭呻吟。這一次她接聽了。「什麼事?」她問,接著聆聽。「真的嗎?」
葛芮塔蜷縮身子。令她驚訝的是,裴瑞茲警探起身,拿起文件,離開了。葛芮塔靠向椅背,手掌在椅子上留下了汗痕。一隻手輕輕捏住她的手。在相鄰的座位上,她的律師聳肩,然後露出微笑,但臉上的表情隨即完全消失。
第二章
四十八小時前
鈴鈴鈴。
葛芮塔將電視靜音,把毯子甩到一邊,從沙發上跌跌撞撞地走到前門。
「我的天啊。」她透過窺視孔查看外面。門外昏暗的走廊裡,兩個穿制服的警察盯著她。她跑回客廳,搖晃菈托亞的肩膀。她的朋友蠕動時,葛芮塔把小酒杯藏到沙發的軟墊後面。無線電的劈啪聲傳來。她循原路回到門前,拔下門鏈,打開門。
「葛芮塔‧吉芬小姐?」
「呃,是的……是我。」
「我是哈登警官。旁邊這位女警是桑切斯警官。」
「你們是怎麼進入這棟大樓的?」
高大粗壯、鬍鬚花白的哈登警官面露微笑。「這份工作的好處之一。」
葛芮塔抓住門的一側,腦袋裡一片混亂。從警官的肩後,她瞥見一名男子從對面的公寓裡向外張望。他嘴裡叼著菸,在口袋裡尋找打火機。她瞇起眼睛。這是怎麼回事?又一個短租客?遊客?應該不是。她不想再搬家,在這個單身公寓已經住了將近一年,她終於有了自己的家。
「出了什麼問題嗎?」男子問道,聲音很細。
警官們沒理他。
「我們可以進來嗎?」桑切斯警官讓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要求而不是疑問。
葛芮塔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選擇。大樓沒有出現火災警報,沒有大樓疏散通知,而如果真的出現什麼緊急情況,全身黑衣的戰術部隊一定會出現。
「你們有什麼事?
兩名嚴肅的警官都沒說話。
菈托亞走到她身後,葛芮塔揮手要她後退,然後打開了門。警官們跟著她們進入公寓。走了兩步,他們就走出了狹小的走廊。
桑切斯警官身形圓潤,一頭紅髮,比搭檔矮一呎,眼睛掃視著公寓。「我們能不能坐下?」
鞋子散落在走廊裡。一件運動衫被扔在沙發的靠背上。茶几上擺滿了披薩盒和一包空的多力多滋。在它旁邊,兩條毯子皺巴巴地躺在地板上。看到伏特加酒瓶,她的胃袋為之收縮,酒瓶裡還有四分之一的酒,高高地聳立在廚房的流理臺上,陪伴著堆在水槽裡的一堆盤子。
她停下來,牢牢站在地板上,轉身面對他們。「到底怎麼回事?」
桑切斯警官清清喉嚨。「是關於令尊。」
「那個王八蛋?」菈托亞咕噥。
「放尊重點。」
葛芮塔聳肩。「就因為他死了?」
桑切斯警官繃緊嘴巴,揉揉脖子根部。「我們想請妳跟我們回局裡,回答幾個問題。」」
她瞥向牆上的時鐘。「在星期天晚上的九點半?」
「不是現在。是明天。」
葛芮塔雙臂抱胸,思索片刻。她可以打掃她的公寓。出去走走。去買菜。上網看《宅男行不行》。還有《使女的故事》,她還沒看第三季。還有《權力遊戲》?
「難道妳不願意去局裡,讓我們聽聽妳的說詞?」
她怒目相視。她受夠了。她聽過這句臺詞,而警察根本不把她的話當一回事。她太熟悉這種制服。深色襯衫。閃閃發亮的黑靴。褲子側面的條紋。胸前徽章上的大寫字母寫著「服務與保護」。他們有做到服務與保護嗎?他們保護了誰?絕對沒有保護她。
「我非去不可嗎?」
哈登警官瞥搭檔一眼。「這是自願性質的,但妳如果願意幫助我們決定如何處理他的死,我們會很感激。」他把手伸進襯衫的口袋裡,指向走廊。「裴瑞茲警探建議妳十一點去。」
「我不是跟你談?」
他搖頭。「她才是老大。」
走這一趟又何妨?她什麼也沒隱藏。「行。」
哈登警官解釋到時候會發生什麼時,她伸手接過名片,聽得心不在焉。
「她會盡可能讓談話迅速又自在。」桑切斯警官補充道。
葛芮塔翻白眼。最好是。她比誰都清楚在警察局回答問題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
「到時候需要我們載妳一程嗎?」哈登警官問。
她嘆氣。
他走回前門時,咧嘴一笑。「我們只是想表達善意。」
桑切斯警官跟著搭檔出去。門關上時,擦過她的背部。
葛芮塔扭開廚房流理臺上的酒瓶蓋子,湊到脣邊,大灌了一口。她來到客廳,倒在沙發上,打開電視,用手撫摸下巴。
「剛剛真的很怪。」菈托亞說道,在她身旁一屁股坐下。
她俯身從地板上撿起一條毯子。
菈托亞啜飲一口酒,黃金耳環在肩上晃來晃去。「他們來這裡幹嘛?」
「我哪知。」
「有什麼想談談的嗎?」
「我知道的都已經跟妳說了。」
「妳在去之前要不要尋求一些建議?」菈托亞指著電視上播放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廣告。「他們怎麼樣?或是打給柯琳?」
葛芮塔渾身發涼,拉緊身上的毯子,瞥向電視螢幕。「現在很晚了。而且這麼做有什麼意義?那傢伙嗝屁了。」
兩人攤在沙發上,腿在沙發中央交錯,彎曲膝蓋,看著剩下的電視節目。節目還沒播放完,菈托亞已經輕輕打著鼾,頭靠在沙發扶手上,毯子蓋到下巴。
雖然躺在摯友旁邊仍然就像躺在全速運轉的暖氣旁邊,但跟她們在小學時第一次睡在一起時相比,太多事情發生了變化。她把酒瓶裡剩下的酒喝乾淨,從沙發上滑下來,來到廚房,打開水槽下面的櫥櫃,盡可能把酒瓶推到最深處,省得以後再拿出來。她來到冰箱前,凝視著裡頭的架子,想找點吃的。她打個寒顫。她在這裡站了多久?
她回到沙發上,把雙腳壓在身下,毯子蓋在身上。柔軟而溫暖,她想起那些炎炎夏夜,在後院的小木屋裡,母親摟著她。布料的邊緣壓在她的鼻子上,她聞不到自己的氣味。她查看手機,然後轉動一旁老舊檯燈上的旋鈕。城市燈火透過客廳窗戶映入,開著的窗戶讓夜晚涼爽的空氣飄進來,她在腦海裡回放著警官的來訪。
她幾乎沒睡。她整晚輾轉反側,不知道明天在警局該說些什麼。
葛芮塔僵硬地坐在硬背椅上。寂靜的氣氛帶來壓迫感。她不想承認的一些想法──那些在她腦海中的角落裡爬行、存在的想法──悄悄進入了光亮處。警方的調查為什麼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她已經給出了說詞,回答了每個問題。只有其中一個問題讓她吃驚。
女兒對父母的義務是什麼?
葛芮塔不確定自己對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有什麼義務。她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答不出來。
但這不是事實……她其實知道為什麼。
如果她老實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刑警們可能會看到她努力馴服的原始、野性的一面,而這麼做的風險太大。她已經埋葬了過去,她想往前走。所以她讓那個特定的疑問懸而未決。
幾分鐘後,門打開了。裴瑞茲警探走進房間,走到她的辦公桌前,在椅子上坐下,查看手裡的文件。她摘下老花眼鏡,放在面前。
葛芮塔胸口緊繃。即使有律師在身邊,她還是覺得呼吸困難。她伸手摸摸牛仔褲的前口袋,發現裡面藏著一枚硬幣。她揉揉它,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用鼻子吸氣,用嘴巴呼氣。緩慢而穩定的呼吸。
裴瑞茲警探盯著她,開口道:「我們走一遍流程。」
葛芮塔嘆氣。走流程?又一次?
「警方負責立案調查。」警探告訴她。
她點頭。她知道。有時候他們會諮詢檢察官。
「我們蒐集證據。」
嗯。她以前都聽過了。
「在妳這樣的案件上,我想說明所有可能性。」警探的語氣像是在進行日常的例行談話。
葛芮塔繃緊身子,咬緊牙關,試著保持鎮定。
裴瑞茲警探舉起一手,把一支鉛筆按在指尖上。「一:一級謀殺;二:二級謀殺;三:誤殺。」
葛芮塔說出第四個可能性。「或是不起訴,我無罪釋放。」
警探沉默幾秒,再次說話時沒看著葛芮塔的律師。「是沒錯,而且──」
手機嗡嗡作響,打斷了她的話語。裴瑞茲警探把手伸過桌面,輕按手機左側的按鈕,將它靜音。她抱歉地笑了笑,瞥一眼自己的筆記。
「之後,透過驗屍官的報告和我們的調查,我會判斷是否有足夠的證據來提出指控。」警探停頓下來,看著她。「而我做了那個決定。」
葛芮塔心跳急促。她口乾舌燥。見真章的時候到了。她盯著警探,好奇對方在想什麼。什麼樣的人下得了手殺害自己的父母?但是警探的眼睛什麼也沒有透露。
手機再次發光。雖然沒發出聲音,但葛芮塔能透過桌面感覺到震動。警探低頭呻吟。這一次她接聽了。「什麼事?」她問,接著聆聽。「真的嗎?」
葛芮塔蜷縮身子。令她驚訝的是,裴瑞茲警探起身,拿起文件,離開了。葛芮塔靠向椅背,手掌在椅子上留下了汗痕。一隻手輕輕捏住她的手。在相鄰的座位上,她的律師聳肩,然後露出微笑,但臉上的表情隨即完全消失。
第二章
四十八小時前
鈴鈴鈴。
葛芮塔將電視靜音,把毯子甩到一邊,從沙發上跌跌撞撞地走到前門。
「我的天啊。」她透過窺視孔查看外面。門外昏暗的走廊裡,兩個穿制服的警察盯著她。她跑回客廳,搖晃菈托亞的肩膀。她的朋友蠕動時,葛芮塔把小酒杯藏到沙發的軟墊後面。無線電的劈啪聲傳來。她循原路回到門前,拔下門鏈,打開門。
「葛芮塔‧吉芬小姐?」
「呃,是的……是我。」
「我是哈登警官。旁邊這位女警是桑切斯警官。」
「你們是怎麼進入這棟大樓的?」
高大粗壯、鬍鬚花白的哈登警官面露微笑。「這份工作的好處之一。」
葛芮塔抓住門的一側,腦袋裡一片混亂。從警官的肩後,她瞥見一名男子從對面的公寓裡向外張望。他嘴裡叼著菸,在口袋裡尋找打火機。她瞇起眼睛。這是怎麼回事?又一個短租客?遊客?應該不是。她不想再搬家,在這個單身公寓已經住了將近一年,她終於有了自己的家。
「出了什麼問題嗎?」男子問道,聲音很細。
警官們沒理他。
「我們可以進來嗎?」桑切斯警官讓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要求而不是疑問。
葛芮塔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選擇。大樓沒有出現火災警報,沒有大樓疏散通知,而如果真的出現什麼緊急情況,全身黑衣的戰術部隊一定會出現。
「你們有什麼事?
兩名嚴肅的警官都沒說話。
菈托亞走到她身後,葛芮塔揮手要她後退,然後打開了門。警官們跟著她們進入公寓。走了兩步,他們就走出了狹小的走廊。
桑切斯警官身形圓潤,一頭紅髮,比搭檔矮一呎,眼睛掃視著公寓。「我們能不能坐下?」
鞋子散落在走廊裡。一件運動衫被扔在沙發的靠背上。茶几上擺滿了披薩盒和一包空的多力多滋。在它旁邊,兩條毯子皺巴巴地躺在地板上。看到伏特加酒瓶,她的胃袋為之收縮,酒瓶裡還有四分之一的酒,高高地聳立在廚房的流理臺上,陪伴著堆在水槽裡的一堆盤子。
她停下來,牢牢站在地板上,轉身面對他們。「到底怎麼回事?」
桑切斯警官清清喉嚨。「是關於令尊。」
「那個王八蛋?」菈托亞咕噥。
「放尊重點。」
葛芮塔聳肩。「就因為他死了?」
桑切斯警官繃緊嘴巴,揉揉脖子根部。「我們想請妳跟我們回局裡,回答幾個問題。」」
她瞥向牆上的時鐘。「在星期天晚上的九點半?」
「不是現在。是明天。」
葛芮塔雙臂抱胸,思索片刻。她可以打掃她的公寓。出去走走。去買菜。上網看《宅男行不行》。還有《使女的故事》,她還沒看第三季。還有《權力遊戲》?
「難道妳不願意去局裡,讓我們聽聽妳的說詞?」
她怒目相視。她受夠了。她聽過這句臺詞,而警察根本不把她的話當一回事。她太熟悉這種制服。深色襯衫。閃閃發亮的黑靴。褲子側面的條紋。胸前徽章上的大寫字母寫著「服務與保護」。他們有做到服務與保護嗎?他們保護了誰?絕對沒有保護她。
「我非去不可嗎?」
哈登警官瞥搭檔一眼。「這是自願性質的,但妳如果願意幫助我們決定如何處理他的死,我們會很感激。」他把手伸進襯衫的口袋裡,指向走廊。「裴瑞茲警探建議妳十一點去。」
「我不是跟你談?」
他搖頭。「她才是老大。」
走這一趟又何妨?她什麼也沒隱藏。「行。」
哈登警官解釋到時候會發生什麼時,她伸手接過名片,聽得心不在焉。
「她會盡可能讓談話迅速又自在。」桑切斯警官補充道。
葛芮塔翻白眼。最好是。她比誰都清楚在警察局回答問題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
「到時候需要我們載妳一程嗎?」哈登警官問。
她嘆氣。
他走回前門時,咧嘴一笑。「我們只是想表達善意。」
桑切斯警官跟著搭檔出去。門關上時,擦過她的背部。
葛芮塔扭開廚房流理臺上的酒瓶蓋子,湊到脣邊,大灌了一口。她來到客廳,倒在沙發上,打開電視,用手撫摸下巴。
「剛剛真的很怪。」菈托亞說道,在她身旁一屁股坐下。
她俯身從地板上撿起一條毯子。
菈托亞啜飲一口酒,黃金耳環在肩上晃來晃去。「他們來這裡幹嘛?」
「我哪知。」
「有什麼想談談的嗎?」
「我知道的都已經跟妳說了。」
「妳在去之前要不要尋求一些建議?」菈托亞指著電視上播放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廣告。「他們怎麼樣?或是打給柯琳?」
葛芮塔渾身發涼,拉緊身上的毯子,瞥向電視螢幕。「現在很晚了。而且這麼做有什麼意義?那傢伙嗝屁了。」
兩人攤在沙發上,腿在沙發中央交錯,彎曲膝蓋,看著剩下的電視節目。節目還沒播放完,菈托亞已經輕輕打著鼾,頭靠在沙發扶手上,毯子蓋到下巴。
雖然躺在摯友旁邊仍然就像躺在全速運轉的暖氣旁邊,但跟她們在小學時第一次睡在一起時相比,太多事情發生了變化。她把酒瓶裡剩下的酒喝乾淨,從沙發上滑下來,來到廚房,打開水槽下面的櫥櫃,盡可能把酒瓶推到最深處,省得以後再拿出來。她來到冰箱前,凝視著裡頭的架子,想找點吃的。她打個寒顫。她在這裡站了多久?
她回到沙發上,把雙腳壓在身下,毯子蓋在身上。柔軟而溫暖,她想起那些炎炎夏夜,在後院的小木屋裡,母親摟著她。布料的邊緣壓在她的鼻子上,她聞不到自己的氣味。她查看手機,然後轉動一旁老舊檯燈上的旋鈕。城市燈火透過客廳窗戶映入,開著的窗戶讓夜晚涼爽的空氣飄進來,她在腦海裡回放著警官的來訪。
她幾乎沒睡。她整晚輾轉反側,不知道明天在警局該說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