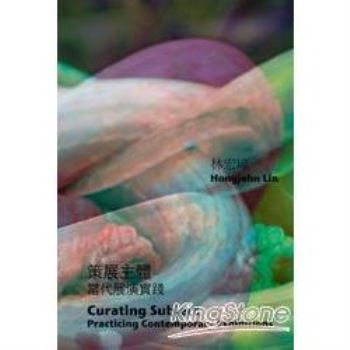第一章 主題與主體
引領我們到一個重大的問題,
但千萬別問,這是甚麼?
就讓我們去拜訪它,
在房間中女人走來走去
談論米蓋朗基羅
-- T.S. Eliot
前言
這段引用自艾略特早期的經典作品的詩句,是整首詩中的高潮點,艾略特在一段描述都會夜遊的場景,突然丟出了一個關鍵字眼「重大(overwhelming)的問題」, 許多不同的詮釋都指向社會及大時代中個人的存在意義,尤其是現代性所產生對於生活的撕裂、拉扯與疏離。但是艾略特的提問,對應著這個類似沙龍的場景描述,它可以是一個相關藝術,尤其是藝術本體的論證,或者說這段詩句是艾略特對於自己以詩的方式呈現自我存在感的反思經驗,這是一個詩學自身本體論的重大問題。在艾略特的自問自答中,問題的答案在語言邏各斯(logos)是個失效的指涉,所以「千萬別問,這是甚麼?」,一個屬於經驗領域的「親歷」身體感知也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解答, 如同這首詩開始時所帶領出的行動感:「讓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待策展在晚近開始發展的專業,關於藝術實踐裡關鍵部分-展演-的思索。換言之,藝術如何呈現?又如何構成這個呈現?與觀眾/讀者的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如何生產?在這個定義下藝術家/展覽的生產者角色為何?在晚近各類雙年展所呈現的展演形式中的意義為何?對應在這些問題所指向的策展專業性,也許回應了所有當代藝術相關策展工作的複雜性,在整個藝術場域的分工中包含的面向最多,也因為晚近的發展而成為最難定義的專業。無論是實質的物理性空間還是藝術語言的語意脈絡,皆包含著展演本身的藝術呈現,策展相較於藝術場域中的其他工作,是另一種重要的察覺與感知對象。
一個重要的面向,不僅僅在於作品是一種「工作」(work), 同時還是一個「作品」(work)。 而策展人與藝術家都稱呼自己的展演為工作與作品,在認定的疊合(一個是作品的「作品」,另外是「展演」的作品),在觀看展演的我們好似面對兩個作品重疊呈現。而且在展演過程中,策展的作用無所不在;也就是說,策展的呈現不但與作品同時出現,並且發展在作品之前,作為一件作品的「前文」(pretext),或者更「回溯性」地定義作品的意義。這個意義不但有著展演藝術作品及意義生產的面向,同時也是一個管理面向上的機制意義。在當代藝術展演中,這種雙重指涉下的展演是個多面向的問題,因為這裡牽涉策展主體/主題(subject)的位置;在這種情境下,展演本身再現的統合性及整體性之關聯,是否攸關藝術意義生產的改變?這些由於策展行為出現而呈現的展演語境,如何從傳統的美術館策展人位置更換為獨立策展人?其發展與演變為何?或者更為重要的,這是一種機制上的盤整?換言之,在整個生產體系中,其最大的意義是影響藝術展演中的製造、消費與流通。而也許,這些問題會引領更為「重大」的問題,藉由對於當代展覽及策展的思考,回應目前盛行的雙年展形式,以及將策展作為一種積極意義創作的可能所在。
?
主題與主體
當代展演中所呈現的「策展主體」(curating subject),回應著從60年代末出現的藝術實踐所開?之藝術文化的對話,包含著對於展演及觀看方式的改變,這裡,聯繫著從「展演主題」(subject)以及策展對於作品主體性的辯證。策展人與藝術家、展出權力、抑或作品與作品之間的策展適當及效果。這些面向更需對應當下因為雙年展的盛行,策展人的角色及其與固定機制的互動和關聯,或者策展人成為藝文場域(抑或機制?)之觸媒的可能,以及現今成為某種專業性與學院訓練的現象。
「策展主體」的開端,必須對應其與「展覽製作人」(exhibition maker)角色的差異,這也是美術館機制中,展覽部門的負責人與管理者脫離「展覽製作」身分的開始。以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s)為例,各個部門如繪畫、雕塑、攝影的主任(director),皆為展覽的製作者,同時也是管理者;而獨立策展做為展覽的製作者,是一個試圖脫離管理者面向的角色。獨立策展人於1960年代末期出現,如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及霍普斯(Walter Hopps)這兩位指標性的人物脫離其所屬的機制,開始區分出與美術館管理者的差別,也形成獨立於機制之外的個體。如史澤曼的重要展覽《當態度成為形式》(Live in Your Head: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因在所屬的柏恩藝術中心(Kunsthalle Bern)展出時得到負面評價,而使他辭去其職位(1970);霍普斯由Pasadena美術館及華盛頓特區的Corcoran畫廊去職後(1970),開始以活動與事件的方式製作展覽。史澤曼於1972年成為「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Kassel)的第一位藝術總監,霍普斯亦在同年於「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中策畫了美國館的阿布(Diane Arbus)展;這種策展人與強調實驗性之國際型藝術展演的連接,開啟了當代策展的原型。由此,獨立策展人拉開與既定機制的距離,並和機制中的管理者有所區分,這種區分與距離即在於獨立策展人的眾多角色—如研究、收藏、呈現、經理、財務等特徵,必然不同於官僚/管理機制中所採取的方式。也就是說,這種執行與策畫展覽的方式改變了美術館既定的獨斷權力安排,也不同於其以系譜學所瞭解的藝術史方式進行對藝術發展的調查,而是更願意在概念、美學、知識生產中冒險;換言之,獨立策展的「開端」是從「離去」開始。這也是由史澤曼及霍普斯所開?的獨立策劃展演特性: 一種策展人做為一位「創作者」(curator as creator)身分的開始;或者,更正確地說,對於作品本身「靈光」(aura)的移置 ,也是一種移動於固定機制之外的「創作」。
引領我們到一個重大的問題,
但千萬別問,這是甚麼?
就讓我們去拜訪它,
在房間中女人走來走去
談論米蓋朗基羅
-- T.S. Eliot
前言
這段引用自艾略特早期的經典作品的詩句,是整首詩中的高潮點,艾略特在一段描述都會夜遊的場景,突然丟出了一個關鍵字眼「重大(overwhelming)的問題」, 許多不同的詮釋都指向社會及大時代中個人的存在意義,尤其是現代性所產生對於生活的撕裂、拉扯與疏離。但是艾略特的提問,對應著這個類似沙龍的場景描述,它可以是一個相關藝術,尤其是藝術本體的論證,或者說這段詩句是艾略特對於自己以詩的方式呈現自我存在感的反思經驗,這是一個詩學自身本體論的重大問題。在艾略特的自問自答中,問題的答案在語言邏各斯(logos)是個失效的指涉,所以「千萬別問,這是甚麼?」,一個屬於經驗領域的「親歷」身體感知也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解答, 如同這首詩開始時所帶領出的行動感:「讓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待策展在晚近開始發展的專業,關於藝術實踐裡關鍵部分-展演-的思索。換言之,藝術如何呈現?又如何構成這個呈現?與觀眾/讀者的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如何生產?在這個定義下藝術家/展覽的生產者角色為何?在晚近各類雙年展所呈現的展演形式中的意義為何?對應在這些問題所指向的策展專業性,也許回應了所有當代藝術相關策展工作的複雜性,在整個藝術場域的分工中包含的面向最多,也因為晚近的發展而成為最難定義的專業。無論是實質的物理性空間還是藝術語言的語意脈絡,皆包含著展演本身的藝術呈現,策展相較於藝術場域中的其他工作,是另一種重要的察覺與感知對象。
一個重要的面向,不僅僅在於作品是一種「工作」(work), 同時還是一個「作品」(work)。 而策展人與藝術家都稱呼自己的展演為工作與作品,在認定的疊合(一個是作品的「作品」,另外是「展演」的作品),在觀看展演的我們好似面對兩個作品重疊呈現。而且在展演過程中,策展的作用無所不在;也就是說,策展的呈現不但與作品同時出現,並且發展在作品之前,作為一件作品的「前文」(pretext),或者更「回溯性」地定義作品的意義。這個意義不但有著展演藝術作品及意義生產的面向,同時也是一個管理面向上的機制意義。在當代藝術展演中,這種雙重指涉下的展演是個多面向的問題,因為這裡牽涉策展主體/主題(subject)的位置;在這種情境下,展演本身再現的統合性及整體性之關聯,是否攸關藝術意義生產的改變?這些由於策展行為出現而呈現的展演語境,如何從傳統的美術館策展人位置更換為獨立策展人?其發展與演變為何?或者更為重要的,這是一種機制上的盤整?換言之,在整個生產體系中,其最大的意義是影響藝術展演中的製造、消費與流通。而也許,這些問題會引領更為「重大」的問題,藉由對於當代展覽及策展的思考,回應目前盛行的雙年展形式,以及將策展作為一種積極意義創作的可能所在。
?
主題與主體
當代展演中所呈現的「策展主體」(curating subject),回應著從60年代末出現的藝術實踐所開?之藝術文化的對話,包含著對於展演及觀看方式的改變,這裡,聯繫著從「展演主題」(subject)以及策展對於作品主體性的辯證。策展人與藝術家、展出權力、抑或作品與作品之間的策展適當及效果。這些面向更需對應當下因為雙年展的盛行,策展人的角色及其與固定機制的互動和關聯,或者策展人成為藝文場域(抑或機制?)之觸媒的可能,以及現今成為某種專業性與學院訓練的現象。
「策展主體」的開端,必須對應其與「展覽製作人」(exhibition maker)角色的差異,這也是美術館機制中,展覽部門的負責人與管理者脫離「展覽製作」身分的開始。以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s)為例,各個部門如繪畫、雕塑、攝影的主任(director),皆為展覽的製作者,同時也是管理者;而獨立策展做為展覽的製作者,是一個試圖脫離管理者面向的角色。獨立策展人於1960年代末期出現,如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及霍普斯(Walter Hopps)這兩位指標性的人物脫離其所屬的機制,開始區分出與美術館管理者的差別,也形成獨立於機制之外的個體。如史澤曼的重要展覽《當態度成為形式》(Live in Your Head: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因在所屬的柏恩藝術中心(Kunsthalle Bern)展出時得到負面評價,而使他辭去其職位(1970);霍普斯由Pasadena美術館及華盛頓特區的Corcoran畫廊去職後(1970),開始以活動與事件的方式製作展覽。史澤曼於1972年成為「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Kassel)的第一位藝術總監,霍普斯亦在同年於「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中策畫了美國館的阿布(Diane Arbus)展;這種策展人與強調實驗性之國際型藝術展演的連接,開啟了當代策展的原型。由此,獨立策展人拉開與既定機制的距離,並和機制中的管理者有所區分,這種區分與距離即在於獨立策展人的眾多角色—如研究、收藏、呈現、經理、財務等特徵,必然不同於官僚/管理機制中所採取的方式。也就是說,這種執行與策畫展覽的方式改變了美術館既定的獨斷權力安排,也不同於其以系譜學所瞭解的藝術史方式進行對藝術發展的調查,而是更願意在概念、美學、知識生產中冒險;換言之,獨立策展的「開端」是從「離去」開始。這也是由史澤曼及霍普斯所開?的獨立策劃展演特性: 一種策展人做為一位「創作者」(curator as creator)身分的開始;或者,更正確地說,對於作品本身「靈光」(aura)的移置 ,也是一種移動於固定機制之外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