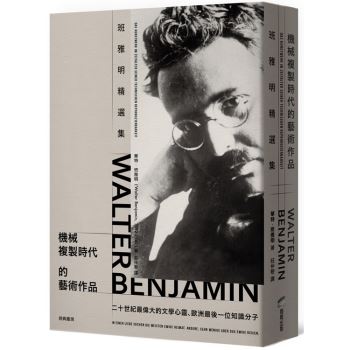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藝術的形成以及各種不同的藝術類型的出現,源起於那個和我們現在大不相同的時代,而那個時代的古人仍未具備我們現代人對事物與環境的支配力。較之往昔,我們所使用的媒介在適應力和精確性方面,已有驚人的進步,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在不久的將來,「美」這個人類古老的產業將出現影響最深遠的變化。所有的藝術都具備有形物質的部分,但由於這部分已無法擺脫現代的知識與實踐的影響,因此,我們已不能再像從前那般地看待它和處理它。這二十年來,不論是時間、空間或物質,都已不同於以往。一切藝術技巧已出現巨大的創新,對此人們必須做好準備,如此一來,才足以影響創新本身,或許最終還能以最巧妙的方式改變藝術概念本身。
──梵樂希(Paul Valéry),〈無所不在的征服〉(La conquête de l’ubiquité),《藝術雜談》(Pièces sur l’art, Paris[o. J.], p. 103f)
前言
當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時,這些生產方式才剛剛出現。馬克思當時非常專注於這方面的分析,因此,這些分析才具有預測未來趨勢的價值。此外,他還探究維繫資本主義生產的人民基本生活條件,並呈現資本主義未來還將如何糟蹋人民的生活。後來的事實發展不僅讓人們相信,資本主義對無產者的剝削已愈來愈嚴重,甚至最後還形成了可能瓦解資本主義的環境條件。相較於經濟層面的下層建築(Unterbau),意識形態層面的上層建築(Überbau)所發生的轉變就緩慢許多。下層建築的改變會逐漸影響上層建築的變革方向,而生產條件的改變其實需要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會在所有的文化領域裡產生效應,所以,遲至今日我們才清楚地看到,這些文化領域如何發生轉變。現在我們應該研究文化領域的轉變所帶有的預測性訊息,不過,一些合乎這類研究的論題(Thesen)往往是針對當前生產條件所形成的藝術發展趨勢,而比較不是針對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所創作的藝術──至於社會在不分階級之後所創作的藝術,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在經濟領域(作為下層建築)裡所發現的生產條件之間的辯證性互動,也同樣可以在上層建築裡看到。因此,我們如果低估無產階級的藝術論題所具有的鬥爭價值,就是一種錯誤!這些藝術論題已經排除從前所流傳下來的一些概念──比如創造、天賦、奧祕和永恆的價值──也就是人們依據法西斯主義觀點,而失控地(如今已難以控制地)運用於事實材料處理的一些概念。以下本文所出現的,就是一些剛被引入藝術理論的新概念。由於它們對法西斯主義毫無用處,因此,通常是人們比較不熟悉的藝術概念,但是,人們卻可以用這些概念來表達本身對藝術政策(Kunstpolitik)的一些革命性要求。Ⅰ
基本上,藝術作品往往是可以複製的。一個人所做出來的東西,總是可以被其他的人仿製出來。不僅進入藝術行業的學徒為了練習技藝而臨摹既有的藝術品,大師為了讓自己的藝術廣為流傳而複製本身所創作的作品,就連貪財的局外人也為了獲取金錢利益,而從事藝術品的仿冒。然而,藉由機械而複製藝術作品卻是晚近才出現的現象。在人類的歷史上,機械的使用所導致的藝術創新是個斷斷續續的發展過程。雖然每次所出現的發展總是間隔長久,但後來卻愈來愈頻繁。古希臘人只知道兩種機械性的複製方法:澆鑄和壓印。因此他們只能使用這兩種複製技術大量生產青銅器、陶製品和錢幣,至於他們其他的藝術品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以機械性操作進行複製。隨著木刻技術的發明,圖繪才成為可以被機械性複製的東西。後來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人類所發明的印刷術才讓文字作品可以藉由機械大量複製生產。我們都知道,印刷術──文字的機械性複製──為書籍文獻帶來了相當驚人的轉變,但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以印刷術大量複製書籍的現象其實不過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特殊情況罷了!在中世紀,除了木刻以外,還出現了銅版雕刻和銅版蝕刻的複製技術。到了十九世紀初期,人們又發明了平版印刷(Lithographie)。複製技術隨著平版印刷的運用而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這種準確度已大幅提高的製版印刷法,是在石版上繪圖,而不是鑿雕木質板材,或蝕刻銅質金屬板。平版印刷不僅使圖繪獲得大量生產(一如從前)的可能性,而且還能每天在市場上推陳出新。平版印刷讓圖繪可以呈現日常生活,而得以和文字印刷並駕齊驅,不過,這項技術在發明數十年後,卻被照相術超越了!在圖像複製的過程裡,人類的雙手因為照相術的發明,而把向來所承擔的最重要的工藝任務,交給了透過鏡頭捕捉影像的眼睛。由於眼睛捕捉影像的速度遠比動手繪圖更為快速,因此,圖像複製的過程便大大加速,而得以跟上人們說話的速度。在攝影棚裡,攝影師便以演員說話的速度攝錄影像。如果說,平版印刷讓報紙可以附上插圖,那麼,照相術便預示著有聲電影的到來──人們在十九世紀末又發明了複製聲音的技術,也就是錄音技術。梵樂希便曾用以下這段話讓我們預見,這些匯集在一起的科學發明即將為人類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轉變:「就像水、電和瓦斯從遠處被引入我們的公寓裡,讓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使用它們一般,我們將來也可以輕鬆地獲得有聲或無聲的影像,只要用手做出一個小動作,它們就會出現或消失。」在一九○○年前後,機械複製的技術已達到某種水準,因此,它不僅能複製所有流傳下來的藝術品,讓它們的效應發揮最深刻的影響,甚至它還在藝術創作的方法裡,為自身爭得了一席之地。如果我們要研究機械複製技術所達到的水準,那麼,再也沒有比研究藝術品的複製和電影藝術這兩個領域,如何反過來影響傳統形態的藝術,更富有啟發性了!Ⅱ
藝術複製品即使已盡善盡美,依然有所欠缺:原作(Original)的此時此地(Hier undJetzt),也就是藝術品在本身所在的空間裡那種獨一無二的存在。藝術品的歷史只發生在它獨一無二的存在裡,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藝術品在存在期間也受制於自身的歷史。藝術品的歷史並不限於,藝術品隨時間的推移而在物質結構方面所出現的改變,它還包括了藝術品歷來的擁有者。物質變化的痕跡只有透過化學或物理的分析,才會顯現出來,但人們卻無法對複製品進行這些科學分析;至於藝術品轉手易主的過程則是藝術界傳統的課題,若要掌握整個過程,就必須從人們創作原作的環境出發。
原作的此時此地構成了它的真實性概念。對一件青銅器的銅綠進行化學分析,可以幫助人們確認該件青銅器是否為真品;同樣地,人們如果能夠證明某一份中世紀手稿是十五世紀的檔案資料,便有助於確認該份手稿是否為真跡。當然,原作的真實性完全和機械性複製無關(當然,還不只和機械性複製無關)。比起通常被視為仿冒的手工複製品,原作仍保有充分的權威性;但如果和機械複製品相比,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其原因有二:其一,機械複製品對原作的依賴少於手工複製品,因此具有更高的獨立性。以攝影為例,機械複製可以突顯攝影對象的某些面向,但這些面向卻是人們的肉眼所無法看到的,只有透過可調節的、可任意選取拍攝角度的鏡頭才能捕捉到。此外,那些透過近距離和快速攝影所獲得的特寫和慢動作的影像,也不是人們憑藉肉眼所能得到的。其二,機械複製品會處於一種連原件或原作本身都無法達到的狀態,而這些複製品──比如照片和唱片──的存在,主要是為了滿足欣賞者的需求。因此,大教堂會離開原本的所在地,而出現在藝術愛好者的攝影工作室裡;還有,人們只要待在房間裡,便可以聆聽那些在音樂廳或露天場地所演出的合唱曲。經由機械複製所生產的藝術複製品,會陷入一種雖不至於侵犯原件或原作的存在、但卻會讓原件或原作的此時此地(獨一無二的存在)失去價值的情況。除了藝術原作以外,那些出現在影片裡的自然風景──舉例來說──也有這種現象。藝術創作的對象會因為機械複製的過程而觸及最敏感的核心,也就是創作對象的真實性。就真實性這一點來說,自然界的一切當然是無懈可擊的。事物的真實性除了包括事物從出現以來可流傳於後世的一切以外,還包括了本身的物質性存續和歷史見證。由於事物的歷史見證建立在它們本身物質性存續的基礎上,因此,人們在複製這些事物時,不僅失去了它們的物質性存續,同時也無法再保有它們的歷史見證。總之,事物的歷史見證會發生動搖,不過,真正讓事物陷入不穩定狀態的,卻是事物的權威性(Autorität)。我們可以用「靈光」(Aura)這個概念總結機械複製過程所失去的東西:藝術作品在機械複製時代所喪失的,正是本身原有的靈光。這個失落的過程曾出現一些徵兆,而它的意義已超越藝術領域。一般來說,複製技術已讓藝術的複製品脫離了傳統的領域:複製技術一方面為原作製造出許多複製品,並以大量的複製取代原作獨一無二的存在;另一方面,複製技術卻也讓藝術複製品滿足了欣賞者在各自不同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需求,而讓這些複製品具有時效性(Aktualität)。這兩個過程大大撼動了從前流傳下來的文物,而對傳統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傳統的反面就是人們當前所面臨的危機以及所進行的改革。這些危機和變革都和當前的群眾運動息息相關,而電影則是這類運動最有力的代言者。電影的社會意義也存在於它本身最具建設性的形態裡,倘若沒有這種形態,電影的顛覆性和淨化性的那一面──也就是對文化遺產的傳統價值的清算──就不可能存在。這種現象在一些歷史長片裡最明顯,而且這些影片總是採用不同於傳統的見解。岡斯(Abel Gance, 1889-1981)便曾在一九二七年狂熱地宣稱:「莎士比亞、林布蘭和貝多芬將被搬上電影……所有的傳說、所有的神話、所有的宗教創始人……莫不等待本身在銀幕上的復活,而英雄則在大門外擠來擠去!」由此看來,岡斯──或許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已邀請我們參與這場文化遺產的全面性整頓。Ⅲ
在漫長的歷史裡,人類的感官知覺(Sinneswahrnehmung)方式也隨著藝術收藏品整體的存在方式(Daseinsweise)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人類的感官知覺運作方式──即感官知覺所依憑的媒介──不僅取決於自然層面,還取決於歷史層面。羅馬帝國晚期的藝術產業以及收藏於維也納的《舊約聖經.創世紀》古抄本(Wiener Genesis)都起源於民族大遷徙時期(Völkerwanderung),當時的藝術不僅不同於古典藝術,而且還代表一種不同的察覺。維也納藝術史學派(Wiener Schule der Kunstgeschichte)的學者禮格爾(Alois Riegl, 1858-1905)和威克霍夫(Franz Wickhoff, 1853-1909)曾大力駁斥古典傳統對羅馬帝國晚期藝術所造成的影響,因為這會讓人們無法真正認識這個時期的藝術。相應於這段歷史時期所特有的藝術創作,他們更率先做出當時的人們具備不同於以往的感官知覺運作方式的結論。雖然他們都是學識淵博的學者,但他們的研究卻仍有其侷限,因為,他們只知道揭示這段歷史時期人們的感官知覺在藝術形式上所出現的特徵,卻未試圖指出──或許也不指望可以指出──這些感官知覺的變化還反映出當時劃時代的社會變革。比起這些學者,我們現在的條件其實更有利於我們洞察這個現象。只要我們把這個時代的感官知覺媒介的改變視為靈光的消褪,就可以進一步揭示其背後相關的社會條件。我們不妨把前面為了分析歷史事物所使用的「靈光」概念,用於說明什麼是自然事物的靈光,並把自然事物的靈光定義為存在於遠處的獨特現象,雖然它可能近在眼前。當我們在某個夏日的午後躺下歇息,看著地平線上的山脈或注視那根投影在我們身上的樹枝時,我們便已浸潤在這片山脈或這根樹枝的靈光裡。透過這段描述,我們能輕易掌握造成如今靈光消散的社會制約性。靈光的褪去起因於兩種情況,它們都和大眾在現代生活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有關。換言之:現在的大眾對於「拉近」自己和藝術品的空間距離和情感距離所投注的關切,就和本身那種以接受複製品來壓制藝術原作的唯一性的傾向,同樣地強烈。人們透過持有周遭事物的影像──尤其是描摹原物的照片和圖片──來掌握這些事物本身,已成為他們每天必須被滿足的需求,而且這些經由機械複製而出現在畫報和新聞短片裡的照片和錄影,顯然不同於繪畫。後者跟唯一性和持久性有緊密的關聯性,而前者則跟短暫性和可重複性密切相關。揭開事物的面紗並破壞它們的靈光,正是現代人感官知覺的特性。這種知覺大大地「感受到世間事物之間的類似性」,所以會使用複製的方法而在事物的唯一性之外,找到了它們之間的類似性。由此可見,凡是在理論領域裡因為本身愈來愈重要的統計學意義,而受到人們關注的東西,就會在具象領域(anschaulicher Bereich)裡顯現出來。對人們的思維和感官知覺來說,外在現實和大眾之間的交互作用,就是一種影響力無遠弗屆的過程。Ⅳ
藝術作品的唯一性跟它們所受到的歷史脈絡的限制息息相關。當然,傳統本身絕對富有生命力,而且很容易發生變化。舉例來說,一尊古希臘的維納斯雕像曾在歷史裡,先後處於不同的傳統脈絡:古希臘人將它視為儀式的崇拜對象,但中世紀的神職人員卻把它當作危害信仰的異教偶像。不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卻仍有相同之處:雕像的唯一性,換句話說,就是雕像的靈光。在儀式裡,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藝術作品起初如何受制於歷史的脈絡。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藝術作品是為了儀式的需要而創作的,起先是巫術儀式,後來則是宗教儀式。藝術作品那種帶有靈光的存在方式,其實從未擺脫本身原有的儀式功能,這一點相當重要。換言之,「真正的」藝術作品的唯一價值是建立在儀式的基礎上,也就是說,藝術作品原本的、最初的使用價值存在於儀式之中。藝術作品的儀式性基礎可能會以本身所期待的方式,而展現在人們眼前。除此之外,人們也在最平凡的、美的崇拜裡發現,它們的儀式性基礎其實是一種世俗化儀式。世俗對美的崇拜在文藝復興時期已逐漸形成,這個趨勢後來還影響歐洲長達三百年之久。即使這種美的崇拜終因十九世紀照相技術的發明,而受到強烈的衝擊,但人們依然可以清楚看到藝術作品的儀式性基礎。在視覺藝術的領域裡,照相術是第一個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複製方法(社會主義亦濫觴於此時)。當時的藝術界人士已發覺,那個他們在往後一百年所必須面對的危機已然來臨,因此便以「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這個信條作為回應,也就是提出所謂的「藝術的神學」(Theologie der Kunst)。這個藝術主張後來還衍生出一種負面的發展:藝術家們紛紛強調「純」藝術的觀念,而他們的「純」藝術既不願擔負任何社會功能,也不願受限於任何創作題材。(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正是以這種「純」藝術立場從事文學創作的第一人)。
藝術的形成以及各種不同的藝術類型的出現,源起於那個和我們現在大不相同的時代,而那個時代的古人仍未具備我們現代人對事物與環境的支配力。較之往昔,我們所使用的媒介在適應力和精確性方面,已有驚人的進步,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在不久的將來,「美」這個人類古老的產業將出現影響最深遠的變化。所有的藝術都具備有形物質的部分,但由於這部分已無法擺脫現代的知識與實踐的影響,因此,我們已不能再像從前那般地看待它和處理它。這二十年來,不論是時間、空間或物質,都已不同於以往。一切藝術技巧已出現巨大的創新,對此人們必須做好準備,如此一來,才足以影響創新本身,或許最終還能以最巧妙的方式改變藝術概念本身。
──梵樂希(Paul Valéry),〈無所不在的征服〉(La conquête de l’ubiquité),《藝術雜談》(Pièces sur l’art, Paris[o. J.], p. 103f)
前言
當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時,這些生產方式才剛剛出現。馬克思當時非常專注於這方面的分析,因此,這些分析才具有預測未來趨勢的價值。此外,他還探究維繫資本主義生產的人民基本生活條件,並呈現資本主義未來還將如何糟蹋人民的生活。後來的事實發展不僅讓人們相信,資本主義對無產者的剝削已愈來愈嚴重,甚至最後還形成了可能瓦解資本主義的環境條件。相較於經濟層面的下層建築(Unterbau),意識形態層面的上層建築(Überbau)所發生的轉變就緩慢許多。下層建築的改變會逐漸影響上層建築的變革方向,而生產條件的改變其實需要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會在所有的文化領域裡產生效應,所以,遲至今日我們才清楚地看到,這些文化領域如何發生轉變。現在我們應該研究文化領域的轉變所帶有的預測性訊息,不過,一些合乎這類研究的論題(Thesen)往往是針對當前生產條件所形成的藝術發展趨勢,而比較不是針對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所創作的藝術──至於社會在不分階級之後所創作的藝術,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在經濟領域(作為下層建築)裡所發現的生產條件之間的辯證性互動,也同樣可以在上層建築裡看到。因此,我們如果低估無產階級的藝術論題所具有的鬥爭價值,就是一種錯誤!這些藝術論題已經排除從前所流傳下來的一些概念──比如創造、天賦、奧祕和永恆的價值──也就是人們依據法西斯主義觀點,而失控地(如今已難以控制地)運用於事實材料處理的一些概念。以下本文所出現的,就是一些剛被引入藝術理論的新概念。由於它們對法西斯主義毫無用處,因此,通常是人們比較不熟悉的藝術概念,但是,人們卻可以用這些概念來表達本身對藝術政策(Kunstpolitik)的一些革命性要求。Ⅰ
基本上,藝術作品往往是可以複製的。一個人所做出來的東西,總是可以被其他的人仿製出來。不僅進入藝術行業的學徒為了練習技藝而臨摹既有的藝術品,大師為了讓自己的藝術廣為流傳而複製本身所創作的作品,就連貪財的局外人也為了獲取金錢利益,而從事藝術品的仿冒。然而,藉由機械而複製藝術作品卻是晚近才出現的現象。在人類的歷史上,機械的使用所導致的藝術創新是個斷斷續續的發展過程。雖然每次所出現的發展總是間隔長久,但後來卻愈來愈頻繁。古希臘人只知道兩種機械性的複製方法:澆鑄和壓印。因此他們只能使用這兩種複製技術大量生產青銅器、陶製品和錢幣,至於他們其他的藝術品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以機械性操作進行複製。隨著木刻技術的發明,圖繪才成為可以被機械性複製的東西。後來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人類所發明的印刷術才讓文字作品可以藉由機械大量複製生產。我們都知道,印刷術──文字的機械性複製──為書籍文獻帶來了相當驚人的轉變,但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以印刷術大量複製書籍的現象其實不過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特殊情況罷了!在中世紀,除了木刻以外,還出現了銅版雕刻和銅版蝕刻的複製技術。到了十九世紀初期,人們又發明了平版印刷(Lithographie)。複製技術隨著平版印刷的運用而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這種準確度已大幅提高的製版印刷法,是在石版上繪圖,而不是鑿雕木質板材,或蝕刻銅質金屬板。平版印刷不僅使圖繪獲得大量生產(一如從前)的可能性,而且還能每天在市場上推陳出新。平版印刷讓圖繪可以呈現日常生活,而得以和文字印刷並駕齊驅,不過,這項技術在發明數十年後,卻被照相術超越了!在圖像複製的過程裡,人類的雙手因為照相術的發明,而把向來所承擔的最重要的工藝任務,交給了透過鏡頭捕捉影像的眼睛。由於眼睛捕捉影像的速度遠比動手繪圖更為快速,因此,圖像複製的過程便大大加速,而得以跟上人們說話的速度。在攝影棚裡,攝影師便以演員說話的速度攝錄影像。如果說,平版印刷讓報紙可以附上插圖,那麼,照相術便預示著有聲電影的到來──人們在十九世紀末又發明了複製聲音的技術,也就是錄音技術。梵樂希便曾用以下這段話讓我們預見,這些匯集在一起的科學發明即將為人類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轉變:「就像水、電和瓦斯從遠處被引入我們的公寓裡,讓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使用它們一般,我們將來也可以輕鬆地獲得有聲或無聲的影像,只要用手做出一個小動作,它們就會出現或消失。」在一九○○年前後,機械複製的技術已達到某種水準,因此,它不僅能複製所有流傳下來的藝術品,讓它們的效應發揮最深刻的影響,甚至它還在藝術創作的方法裡,為自身爭得了一席之地。如果我們要研究機械複製技術所達到的水準,那麼,再也沒有比研究藝術品的複製和電影藝術這兩個領域,如何反過來影響傳統形態的藝術,更富有啟發性了!Ⅱ
藝術複製品即使已盡善盡美,依然有所欠缺:原作(Original)的此時此地(Hier undJetzt),也就是藝術品在本身所在的空間裡那種獨一無二的存在。藝術品的歷史只發生在它獨一無二的存在裡,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藝術品在存在期間也受制於自身的歷史。藝術品的歷史並不限於,藝術品隨時間的推移而在物質結構方面所出現的改變,它還包括了藝術品歷來的擁有者。物質變化的痕跡只有透過化學或物理的分析,才會顯現出來,但人們卻無法對複製品進行這些科學分析;至於藝術品轉手易主的過程則是藝術界傳統的課題,若要掌握整個過程,就必須從人們創作原作的環境出發。
原作的此時此地構成了它的真實性概念。對一件青銅器的銅綠進行化學分析,可以幫助人們確認該件青銅器是否為真品;同樣地,人們如果能夠證明某一份中世紀手稿是十五世紀的檔案資料,便有助於確認該份手稿是否為真跡。當然,原作的真實性完全和機械性複製無關(當然,還不只和機械性複製無關)。比起通常被視為仿冒的手工複製品,原作仍保有充分的權威性;但如果和機械複製品相比,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其原因有二:其一,機械複製品對原作的依賴少於手工複製品,因此具有更高的獨立性。以攝影為例,機械複製可以突顯攝影對象的某些面向,但這些面向卻是人們的肉眼所無法看到的,只有透過可調節的、可任意選取拍攝角度的鏡頭才能捕捉到。此外,那些透過近距離和快速攝影所獲得的特寫和慢動作的影像,也不是人們憑藉肉眼所能得到的。其二,機械複製品會處於一種連原件或原作本身都無法達到的狀態,而這些複製品──比如照片和唱片──的存在,主要是為了滿足欣賞者的需求。因此,大教堂會離開原本的所在地,而出現在藝術愛好者的攝影工作室裡;還有,人們只要待在房間裡,便可以聆聽那些在音樂廳或露天場地所演出的合唱曲。經由機械複製所生產的藝術複製品,會陷入一種雖不至於侵犯原件或原作的存在、但卻會讓原件或原作的此時此地(獨一無二的存在)失去價值的情況。除了藝術原作以外,那些出現在影片裡的自然風景──舉例來說──也有這種現象。藝術創作的對象會因為機械複製的過程而觸及最敏感的核心,也就是創作對象的真實性。就真實性這一點來說,自然界的一切當然是無懈可擊的。事物的真實性除了包括事物從出現以來可流傳於後世的一切以外,還包括了本身的物質性存續和歷史見證。由於事物的歷史見證建立在它們本身物質性存續的基礎上,因此,人們在複製這些事物時,不僅失去了它們的物質性存續,同時也無法再保有它們的歷史見證。總之,事物的歷史見證會發生動搖,不過,真正讓事物陷入不穩定狀態的,卻是事物的權威性(Autorität)。我們可以用「靈光」(Aura)這個概念總結機械複製過程所失去的東西:藝術作品在機械複製時代所喪失的,正是本身原有的靈光。這個失落的過程曾出現一些徵兆,而它的意義已超越藝術領域。一般來說,複製技術已讓藝術的複製品脫離了傳統的領域:複製技術一方面為原作製造出許多複製品,並以大量的複製取代原作獨一無二的存在;另一方面,複製技術卻也讓藝術複製品滿足了欣賞者在各自不同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需求,而讓這些複製品具有時效性(Aktualität)。這兩個過程大大撼動了從前流傳下來的文物,而對傳統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傳統的反面就是人們當前所面臨的危機以及所進行的改革。這些危機和變革都和當前的群眾運動息息相關,而電影則是這類運動最有力的代言者。電影的社會意義也存在於它本身最具建設性的形態裡,倘若沒有這種形態,電影的顛覆性和淨化性的那一面──也就是對文化遺產的傳統價值的清算──就不可能存在。這種現象在一些歷史長片裡最明顯,而且這些影片總是採用不同於傳統的見解。岡斯(Abel Gance, 1889-1981)便曾在一九二七年狂熱地宣稱:「莎士比亞、林布蘭和貝多芬將被搬上電影……所有的傳說、所有的神話、所有的宗教創始人……莫不等待本身在銀幕上的復活,而英雄則在大門外擠來擠去!」由此看來,岡斯──或許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已邀請我們參與這場文化遺產的全面性整頓。Ⅲ
在漫長的歷史裡,人類的感官知覺(Sinneswahrnehmung)方式也隨著藝術收藏品整體的存在方式(Daseinsweise)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人類的感官知覺運作方式──即感官知覺所依憑的媒介──不僅取決於自然層面,還取決於歷史層面。羅馬帝國晚期的藝術產業以及收藏於維也納的《舊約聖經.創世紀》古抄本(Wiener Genesis)都起源於民族大遷徙時期(Völkerwanderung),當時的藝術不僅不同於古典藝術,而且還代表一種不同的察覺。維也納藝術史學派(Wiener Schule der Kunstgeschichte)的學者禮格爾(Alois Riegl, 1858-1905)和威克霍夫(Franz Wickhoff, 1853-1909)曾大力駁斥古典傳統對羅馬帝國晚期藝術所造成的影響,因為這會讓人們無法真正認識這個時期的藝術。相應於這段歷史時期所特有的藝術創作,他們更率先做出當時的人們具備不同於以往的感官知覺運作方式的結論。雖然他們都是學識淵博的學者,但他們的研究卻仍有其侷限,因為,他們只知道揭示這段歷史時期人們的感官知覺在藝術形式上所出現的特徵,卻未試圖指出──或許也不指望可以指出──這些感官知覺的變化還反映出當時劃時代的社會變革。比起這些學者,我們現在的條件其實更有利於我們洞察這個現象。只要我們把這個時代的感官知覺媒介的改變視為靈光的消褪,就可以進一步揭示其背後相關的社會條件。我們不妨把前面為了分析歷史事物所使用的「靈光」概念,用於說明什麼是自然事物的靈光,並把自然事物的靈光定義為存在於遠處的獨特現象,雖然它可能近在眼前。當我們在某個夏日的午後躺下歇息,看著地平線上的山脈或注視那根投影在我們身上的樹枝時,我們便已浸潤在這片山脈或這根樹枝的靈光裡。透過這段描述,我們能輕易掌握造成如今靈光消散的社會制約性。靈光的褪去起因於兩種情況,它們都和大眾在現代生活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有關。換言之:現在的大眾對於「拉近」自己和藝術品的空間距離和情感距離所投注的關切,就和本身那種以接受複製品來壓制藝術原作的唯一性的傾向,同樣地強烈。人們透過持有周遭事物的影像──尤其是描摹原物的照片和圖片──來掌握這些事物本身,已成為他們每天必須被滿足的需求,而且這些經由機械複製而出現在畫報和新聞短片裡的照片和錄影,顯然不同於繪畫。後者跟唯一性和持久性有緊密的關聯性,而前者則跟短暫性和可重複性密切相關。揭開事物的面紗並破壞它們的靈光,正是現代人感官知覺的特性。這種知覺大大地「感受到世間事物之間的類似性」,所以會使用複製的方法而在事物的唯一性之外,找到了它們之間的類似性。由此可見,凡是在理論領域裡因為本身愈來愈重要的統計學意義,而受到人們關注的東西,就會在具象領域(anschaulicher Bereich)裡顯現出來。對人們的思維和感官知覺來說,外在現實和大眾之間的交互作用,就是一種影響力無遠弗屆的過程。Ⅳ
藝術作品的唯一性跟它們所受到的歷史脈絡的限制息息相關。當然,傳統本身絕對富有生命力,而且很容易發生變化。舉例來說,一尊古希臘的維納斯雕像曾在歷史裡,先後處於不同的傳統脈絡:古希臘人將它視為儀式的崇拜對象,但中世紀的神職人員卻把它當作危害信仰的異教偶像。不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卻仍有相同之處:雕像的唯一性,換句話說,就是雕像的靈光。在儀式裡,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藝術作品起初如何受制於歷史的脈絡。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藝術作品是為了儀式的需要而創作的,起先是巫術儀式,後來則是宗教儀式。藝術作品那種帶有靈光的存在方式,其實從未擺脫本身原有的儀式功能,這一點相當重要。換言之,「真正的」藝術作品的唯一價值是建立在儀式的基礎上,也就是說,藝術作品原本的、最初的使用價值存在於儀式之中。藝術作品的儀式性基礎可能會以本身所期待的方式,而展現在人們眼前。除此之外,人們也在最平凡的、美的崇拜裡發現,它們的儀式性基礎其實是一種世俗化儀式。世俗對美的崇拜在文藝復興時期已逐漸形成,這個趨勢後來還影響歐洲長達三百年之久。即使這種美的崇拜終因十九世紀照相技術的發明,而受到強烈的衝擊,但人們依然可以清楚看到藝術作品的儀式性基礎。在視覺藝術的領域裡,照相術是第一個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複製方法(社會主義亦濫觴於此時)。當時的藝術界人士已發覺,那個他們在往後一百年所必須面對的危機已然來臨,因此便以「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這個信條作為回應,也就是提出所謂的「藝術的神學」(Theologie der Kunst)。這個藝術主張後來還衍生出一種負面的發展:藝術家們紛紛強調「純」藝術的觀念,而他們的「純」藝術既不願擔負任何社會功能,也不願受限於任何創作題材。(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正是以這種「純」藝術立場從事文學創作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