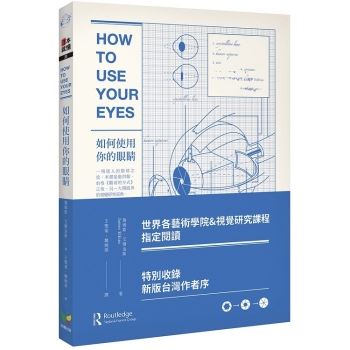第一章 如何看郵票
這張圖是第一枚郵票「黑便士」,郵票上是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上頭的圖解是為了幫助區分這枚郵票幾乎完全相同的兩個版本;指出了雕刻師在哪些地方為原始設計作了潤色、強化,並展現出女王的特徵。經過十五年的使用,這些線條已經磨損了,必須加深。之後幾個版本的黑便士和早期版本相比,只是看起來有點粗糙,但女王總算得到了她在圖1.1中那種專注的目光。在這之後,設計師們改了顏色,女王最終也有了個胖胖的臉頰和略帶傻氣的表情(圖1.2,左上)。
郵票上只印著「郵資」(POSTAGE)和「一便士。」(ONE PENNY.,有句點,好讓它更顯眼。)在一八四○年,英國是唯一印製郵票的國家,所以不需要加上「大不列顛」這個詞。雖然法國曾經一度把國名「法蘭西共和國」(République Française)縮寫成一個小小的「RF」與英國郵票比肩,但即使到了今天,英國郵票也是唯一沒有國名的郵票。設計郵票的時候,空間是很珍貴的。省掉「大不列顛」,就騰出了一平方英寸位置,給了藝術家更多空間展現女王的臉。
郵票是個小宇宙,把廣大的藝術和政治世界壓縮進一個半英寸見方的方塊裡。藝術擠得水洩不通,但也得到了一種令人驚訝的深度,政治則濃縮成了陳腔濫調。郵票以細密的圖樣彌補了它小小的尺寸,有些還是用極精細的雕刻機刻出來的。黑便士兩側立著的輕盈弧狀花格,以及精密車床工藝般的背景,都是使用專門為此設計的機器製作。之後,中心部分被抹除,再由藝術家弗雷德瑞克.希斯雕刻女王的側臉像。許多線條細到難以用肉眼看清楚,但它們是經過設計的,所以我們「幾乎」看得見,這些線條為郵票增添了一種迷人的柔軟感。這張郵票彷彿有自己的氛圍,像個裡面有株植物的小小鐘罩。希斯應該有一個放大裝置,所以這張郵票在他眼裡就像一張大號印刷主版。時至今日,有希斯這種技藝的人幾乎不存在,因為這項工作可以在電腦上完成,製作時可以任意放大。而你看見的黑便士,就是它原本的樣子:一個小小的藝術品,在一個小小的尺寸裡創造出來。今天的郵票都是電子化縮小後的普通圖片。
「郵資」和「一便士。」這兩個詞,和兩道精細的飾邊一起構成了完整的邊框,圍繞著女王的側臉像。邊框上方以兩個馬爾他十字架連接,底部則是兩個空白方塊。在黑便士的實際樣本和之後發行的郵票上,每個框框裡都有一個不同的字母;請注意圖1.2郵票上的「G」和「J」,這是打算用來對付偽造者的「檢查標記」,一整張郵票上的每一枚都有一組不同的字母組合。我可以想像現代偽造者對著這個設計笑出來的樣子──現在的偽造者,連金屬防偽條、防複製圖案和顯微字跡都幾乎擋不住。要偽造這些郵票,他們只需要拿字母表上的字母填到框框裡去就行了。
這一整套設計,最後看起來像一幅鑲了框的畫。對郵票來說,這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典範,但它從未完全達到這個目標。印出來的黑便士(以及圖1.2中的紅色版本)看起來並不真的像一幅畫或一個裱了框的紀念章,即使真的像了,它的大小也會讓它看上去很古怪。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其他設計師也試圖創造出切合郵票本質的設計。在黑便士之後印製的第四張郵票,是由儒貝爾.德.拉.費爾泰(Joubert de la Ferté)設計的「玫瑰紅四便士」;圖1.2右上角那張,是他設計的一個修改版。費爾泰保留了維多利亞的側臉像,但把邊框簡化成一組幾何線條,說不定可以拿去裝飾希臘神廟那種。比起黑便士,它沒那麼濃烈,也就是更不像一幅簡單的鑲框畫了。「檢查標記」對那個框來說變得太大:看起來更像是某一棟新古典主義建築平面圖上的堅固柱子。維多利亞的臉放在一個圓盤裡,圓盤兩側與邊框部分重疊。這個想法是打算讓郵票看起來更像一枚硬幣,但事與願違,它最後看起來像是一個又大又沉重的獎章擺在畫框上。費爾泰的設計也許永遠都不能在三維空間中實際建構出來;這是兩種不同東西的矛盾組合:一個古董紀念章和一幅裱框油畫。
不久之後,出現了一系列郵票,每一種面額都有不同的設計,可以快速分辨。三便士郵票有三道相交的弧線,六便士有六道(如圖1.2正中所示),九便士則是九道。但這種象徵手法很快就成了個問題。一先令郵票是橢圓形的──並不是個一目了然的選擇──而兩先令郵票是個曼陀羅,一種貓眼似的橢圓形。還有其他系列採用了更複雜的形狀象徵,但從來沒有問世過──理由很充分,因為比起有用,它們反而更容易讓人搞混。
接著,設計師們嘗試了別的策略,以建築做為郵票的設計基礎,取代繪畫、錢幣或數字象徵。賽西爾.吉本斯(Cecil Gibbons)是專門研究這個主題的集郵家,他說這種新的建築風郵票「糟透了」。設計圖被切割成許多方塊,好像這張郵票是用劈得很粗的大理石堆出來的。還有些看上去好像建得太趕了點,所以石塊之間沒有完全密合。圖1.2底下有兩枚複製品。左下角的郵票是由小方塊拼出來的,而方塊不怎麼密合(方塊的間隙有一點陰影)。右下角那張則讓人想起某個有大理石裝飾的圓窗。
砌石系列之後,設計師們轉向了紋章和盾徽。他們的郵票使用了小盾徽,還用了一排排的皇室紋樣做分隔,維多利亞的頭像開始像個戴在傳統盾徽上的頭盔,郵票上滿是晦澀難懂的符號。
從這個角度,我們很容易就能弄懂郵票設計的歷史。每種新方案都是一種新的隱喻:首先是油畫,然後是錢幣,然後是數字象徵,然後是砌石,然後是紋章……。喬治五世(一九一○至一九三六年在位)是一位集郵家,他主政時期的郵票引進了橫向的「紀念」版,給了郵票更多空間。一九二九年,英國發行了第一張無邊框郵票,或者應該說,這是第一張以白紙邊緣做為邊框的郵票。身處在現今這個時代,什麼都有可能了,有三角形郵票,浮雕表面郵票,甚至還有3D立體郵票;但這些基本的設計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解決。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依然認為郵票不得不取樣於某些事物(像是繪畫或砌石),而不把它們當成一群自有其主權的小小物體。
之後發行的郵票,幾乎不可能逃過黑便士一開始就觸及的這些問題。十九世紀,一個又一個國家印製了外表和英國一模一樣的郵票,不然就是從英國的創新中借鑑了他們的設計。義大利、德國、法國和美國都是從英國設計師們探索過的主題變體中起步的。即使在今天,郵票設計也非常集中,世界上許多比較小的國家,郵票都由紐約少數幾家公司製作。蒙古早期的郵票是在匈牙利設計的,做為兩國長期協議的一部分,而匈牙利藝術家們又被英國設計影響。十九世紀時印度的一些土邦,如科欽、阿爾瓦爾與奔迪、賈拉瓦爾,以及特拉凡科,這些地方的郵票通常都在英國中部的一個辦公室裡設計,和早期的英國郵票有著相同的古典式邊框(圖1.3)。維多利亞頭像則被各種異國風的東西取代,像這枚科欽郵票就有一只因陀羅的貝殼和一把儀仗傘。尼泊爾的郵票有尼泊爾的象徵──一頂尼泊爾王冠和兩把交叉的廓爾喀彎刀。蒙古郵票有索永布圖案,這是一種盾徽。想找到真正遠離歐洲影響的郵票,必須往一些非常貧窮而與世隔絕的地方找,這些地方因為這兩個原因,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歐洲水準的印刷與設計。例如印度土邦博爾早期發行的部分郵票就只是一些彩色暈染圖,只不過被承認是郵票而已(圖1.4)。
郵票之所以被忽視,是因為裡面的政治元素受到簡化,圖樣也沒有下功夫的價值。它們傾向於簡單,從其他藝術借鑑想法。偶爾郵票也可能會說一些新的東西,或者用一種新的方式說,但大多數時間,郵票一再呈現的,只是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或藝術審美的最低共同點。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世界的普遍趨勢一直是無害或滑稽的主題:花卉、動物、電影明星、陳腔濫調。郵票一年比一年更平凡無奇、更甜美、也更幼稚,像是在為它們問世的第一個世紀時那陣激進濫情的民族主義贖罪。
每隔一陣子,郵票都可能在政治和藝術方面展現新意。新獨立的愛爾蘭自由邦(一九二二~一九四九年)發行的郵票就是一個例子。愛爾蘭剛剛贏得獨立,十分嚴肅認真看待自己。凝重的中世紀風格象徵──三葉草、愛爾蘭豎琴、阿爾斯特紅手──以沉鬱的綠色和棕色印出來。郵票上的文字幾乎不用英語,而使用愛爾蘭語,或是和拉丁語雙語並行。等到愛爾蘭在一九五○年代解除貿易限制,郵票才以現代方式開始輕鬆有趣起來。
在我們急著想變得隨和的時候,我們基本上已經把「郵票可以富含有趣的意義」這個想法丟失了;在我們對現代效率的渴望下,我們忘了郵票可以是一個小小的世界,充滿了幾乎看不見的細節。早期的美國郵票製作精細非凡(圖1.5,最下排),近乎顯微程度的線條產生了一種美妙、閃閃發光的效果;小小的「馬達」狀渦卷裝飾紋樣即使在這張放大圖上也難以看清。右上角那張郵票有些線條實在太細,已經完全看不出是線了。這樣製作,即使是四分之一英寸寬的景色看起來也很廣闊,充滿了光線、距離和空間。把它拿來和中間那些郵票比一下,那是最近為了向老郵票致敬而印製的。新郵票既粗糙、簡陋又無趣。很顯然,這些郵票沒有人會想看。天空布滿了破折號,看起來像一排排遷徙的雁鵝,圖的外圍還繞了一圈假珍珠。
我不會說所有的郵票設計都應該跟這些老郵票一樣精細──但至少,這些老郵票知道不能讓所有東西一望到底。你被一個小小的畫面吸引,越拉越近,驚嘆於它的深度和細節,這是一種美妙的感覺。十九世紀的郵票可以發揮這種魔力,現在我們有的全是些彩色紙片,幾乎沒有能吸引目光的東西。
這張圖是第一枚郵票「黑便士」,郵票上是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上頭的圖解是為了幫助區分這枚郵票幾乎完全相同的兩個版本;指出了雕刻師在哪些地方為原始設計作了潤色、強化,並展現出女王的特徵。經過十五年的使用,這些線條已經磨損了,必須加深。之後幾個版本的黑便士和早期版本相比,只是看起來有點粗糙,但女王總算得到了她在圖1.1中那種專注的目光。在這之後,設計師們改了顏色,女王最終也有了個胖胖的臉頰和略帶傻氣的表情(圖1.2,左上)。
郵票上只印著「郵資」(POSTAGE)和「一便士。」(ONE PENNY.,有句點,好讓它更顯眼。)在一八四○年,英國是唯一印製郵票的國家,所以不需要加上「大不列顛」這個詞。雖然法國曾經一度把國名「法蘭西共和國」(République Française)縮寫成一個小小的「RF」與英國郵票比肩,但即使到了今天,英國郵票也是唯一沒有國名的郵票。設計郵票的時候,空間是很珍貴的。省掉「大不列顛」,就騰出了一平方英寸位置,給了藝術家更多空間展現女王的臉。
郵票是個小宇宙,把廣大的藝術和政治世界壓縮進一個半英寸見方的方塊裡。藝術擠得水洩不通,但也得到了一種令人驚訝的深度,政治則濃縮成了陳腔濫調。郵票以細密的圖樣彌補了它小小的尺寸,有些還是用極精細的雕刻機刻出來的。黑便士兩側立著的輕盈弧狀花格,以及精密車床工藝般的背景,都是使用專門為此設計的機器製作。之後,中心部分被抹除,再由藝術家弗雷德瑞克.希斯雕刻女王的側臉像。許多線條細到難以用肉眼看清楚,但它們是經過設計的,所以我們「幾乎」看得見,這些線條為郵票增添了一種迷人的柔軟感。這張郵票彷彿有自己的氛圍,像個裡面有株植物的小小鐘罩。希斯應該有一個放大裝置,所以這張郵票在他眼裡就像一張大號印刷主版。時至今日,有希斯這種技藝的人幾乎不存在,因為這項工作可以在電腦上完成,製作時可以任意放大。而你看見的黑便士,就是它原本的樣子:一個小小的藝術品,在一個小小的尺寸裡創造出來。今天的郵票都是電子化縮小後的普通圖片。
「郵資」和「一便士。」這兩個詞,和兩道精細的飾邊一起構成了完整的邊框,圍繞著女王的側臉像。邊框上方以兩個馬爾他十字架連接,底部則是兩個空白方塊。在黑便士的實際樣本和之後發行的郵票上,每個框框裡都有一個不同的字母;請注意圖1.2郵票上的「G」和「J」,這是打算用來對付偽造者的「檢查標記」,一整張郵票上的每一枚都有一組不同的字母組合。我可以想像現代偽造者對著這個設計笑出來的樣子──現在的偽造者,連金屬防偽條、防複製圖案和顯微字跡都幾乎擋不住。要偽造這些郵票,他們只需要拿字母表上的字母填到框框裡去就行了。
這一整套設計,最後看起來像一幅鑲了框的畫。對郵票來說,這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典範,但它從未完全達到這個目標。印出來的黑便士(以及圖1.2中的紅色版本)看起來並不真的像一幅畫或一個裱了框的紀念章,即使真的像了,它的大小也會讓它看上去很古怪。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其他設計師也試圖創造出切合郵票本質的設計。在黑便士之後印製的第四張郵票,是由儒貝爾.德.拉.費爾泰(Joubert de la Ferté)設計的「玫瑰紅四便士」;圖1.2右上角那張,是他設計的一個修改版。費爾泰保留了維多利亞的側臉像,但把邊框簡化成一組幾何線條,說不定可以拿去裝飾希臘神廟那種。比起黑便士,它沒那麼濃烈,也就是更不像一幅簡單的鑲框畫了。「檢查標記」對那個框來說變得太大:看起來更像是某一棟新古典主義建築平面圖上的堅固柱子。維多利亞的臉放在一個圓盤裡,圓盤兩側與邊框部分重疊。這個想法是打算讓郵票看起來更像一枚硬幣,但事與願違,它最後看起來像是一個又大又沉重的獎章擺在畫框上。費爾泰的設計也許永遠都不能在三維空間中實際建構出來;這是兩種不同東西的矛盾組合:一個古董紀念章和一幅裱框油畫。
不久之後,出現了一系列郵票,每一種面額都有不同的設計,可以快速分辨。三便士郵票有三道相交的弧線,六便士有六道(如圖1.2正中所示),九便士則是九道。但這種象徵手法很快就成了個問題。一先令郵票是橢圓形的──並不是個一目了然的選擇──而兩先令郵票是個曼陀羅,一種貓眼似的橢圓形。還有其他系列採用了更複雜的形狀象徵,但從來沒有問世過──理由很充分,因為比起有用,它們反而更容易讓人搞混。
接著,設計師們嘗試了別的策略,以建築做為郵票的設計基礎,取代繪畫、錢幣或數字象徵。賽西爾.吉本斯(Cecil Gibbons)是專門研究這個主題的集郵家,他說這種新的建築風郵票「糟透了」。設計圖被切割成許多方塊,好像這張郵票是用劈得很粗的大理石堆出來的。還有些看上去好像建得太趕了點,所以石塊之間沒有完全密合。圖1.2底下有兩枚複製品。左下角的郵票是由小方塊拼出來的,而方塊不怎麼密合(方塊的間隙有一點陰影)。右下角那張則讓人想起某個有大理石裝飾的圓窗。
砌石系列之後,設計師們轉向了紋章和盾徽。他們的郵票使用了小盾徽,還用了一排排的皇室紋樣做分隔,維多利亞的頭像開始像個戴在傳統盾徽上的頭盔,郵票上滿是晦澀難懂的符號。
從這個角度,我們很容易就能弄懂郵票設計的歷史。每種新方案都是一種新的隱喻:首先是油畫,然後是錢幣,然後是數字象徵,然後是砌石,然後是紋章……。喬治五世(一九一○至一九三六年在位)是一位集郵家,他主政時期的郵票引進了橫向的「紀念」版,給了郵票更多空間。一九二九年,英國發行了第一張無邊框郵票,或者應該說,這是第一張以白紙邊緣做為邊框的郵票。身處在現今這個時代,什麼都有可能了,有三角形郵票,浮雕表面郵票,甚至還有3D立體郵票;但這些基本的設計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解決。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依然認為郵票不得不取樣於某些事物(像是繪畫或砌石),而不把它們當成一群自有其主權的小小物體。
之後發行的郵票,幾乎不可能逃過黑便士一開始就觸及的這些問題。十九世紀,一個又一個國家印製了外表和英國一模一樣的郵票,不然就是從英國的創新中借鑑了他們的設計。義大利、德國、法國和美國都是從英國設計師們探索過的主題變體中起步的。即使在今天,郵票設計也非常集中,世界上許多比較小的國家,郵票都由紐約少數幾家公司製作。蒙古早期的郵票是在匈牙利設計的,做為兩國長期協議的一部分,而匈牙利藝術家們又被英國設計影響。十九世紀時印度的一些土邦,如科欽、阿爾瓦爾與奔迪、賈拉瓦爾,以及特拉凡科,這些地方的郵票通常都在英國中部的一個辦公室裡設計,和早期的英國郵票有著相同的古典式邊框(圖1.3)。維多利亞頭像則被各種異國風的東西取代,像這枚科欽郵票就有一只因陀羅的貝殼和一把儀仗傘。尼泊爾的郵票有尼泊爾的象徵──一頂尼泊爾王冠和兩把交叉的廓爾喀彎刀。蒙古郵票有索永布圖案,這是一種盾徽。想找到真正遠離歐洲影響的郵票,必須往一些非常貧窮而與世隔絕的地方找,這些地方因為這兩個原因,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歐洲水準的印刷與設計。例如印度土邦博爾早期發行的部分郵票就只是一些彩色暈染圖,只不過被承認是郵票而已(圖1.4)。
郵票之所以被忽視,是因為裡面的政治元素受到簡化,圖樣也沒有下功夫的價值。它們傾向於簡單,從其他藝術借鑑想法。偶爾郵票也可能會說一些新的東西,或者用一種新的方式說,但大多數時間,郵票一再呈現的,只是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或藝術審美的最低共同點。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世界的普遍趨勢一直是無害或滑稽的主題:花卉、動物、電影明星、陳腔濫調。郵票一年比一年更平凡無奇、更甜美、也更幼稚,像是在為它們問世的第一個世紀時那陣激進濫情的民族主義贖罪。
每隔一陣子,郵票都可能在政治和藝術方面展現新意。新獨立的愛爾蘭自由邦(一九二二~一九四九年)發行的郵票就是一個例子。愛爾蘭剛剛贏得獨立,十分嚴肅認真看待自己。凝重的中世紀風格象徵──三葉草、愛爾蘭豎琴、阿爾斯特紅手──以沉鬱的綠色和棕色印出來。郵票上的文字幾乎不用英語,而使用愛爾蘭語,或是和拉丁語雙語並行。等到愛爾蘭在一九五○年代解除貿易限制,郵票才以現代方式開始輕鬆有趣起來。
在我們急著想變得隨和的時候,我們基本上已經把「郵票可以富含有趣的意義」這個想法丟失了;在我們對現代效率的渴望下,我們忘了郵票可以是一個小小的世界,充滿了幾乎看不見的細節。早期的美國郵票製作精細非凡(圖1.5,最下排),近乎顯微程度的線條產生了一種美妙、閃閃發光的效果;小小的「馬達」狀渦卷裝飾紋樣即使在這張放大圖上也難以看清。右上角那張郵票有些線條實在太細,已經完全看不出是線了。這樣製作,即使是四分之一英寸寬的景色看起來也很廣闊,充滿了光線、距離和空間。把它拿來和中間那些郵票比一下,那是最近為了向老郵票致敬而印製的。新郵票既粗糙、簡陋又無趣。很顯然,這些郵票沒有人會想看。天空布滿了破折號,看起來像一排排遷徙的雁鵝,圖的外圍還繞了一圈假珍珠。
我不會說所有的郵票設計都應該跟這些老郵票一樣精細──但至少,這些老郵票知道不能讓所有東西一望到底。你被一個小小的畫面吸引,越拉越近,驚嘆於它的深度和細節,這是一種美妙的感覺。十九世紀的郵票可以發揮這種魔力,現在我們有的全是些彩色紙片,幾乎沒有能吸引目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