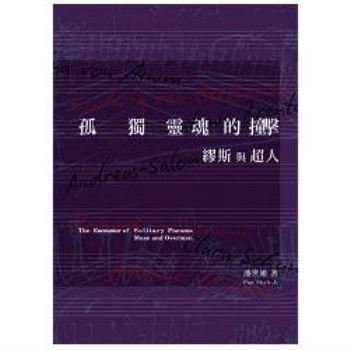情感與想像 vs. 理想與幻想
早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葉,西方的思想圈與文藝圈就為浪漫精神的散播埋下了種子。隨著盧梭「回歸自然」的主張,藝術家的個性與情感開始被解放出來,情感與想像力自由地翱翔,音樂與文學終於有機會可以更進一步擦出燦爛的火花。
音樂與文學的結合,在浪漫主義時代到達發展的高峰。音樂原本就是最能夠直接表達人類情感經驗的藝術媒介之一,在文字的協助妝點下,音樂得以將抽象的內容相對具體化,進而得到更明確的表現力。如同黑格爾所言:「要使音樂充分發揮它的作用,抽象的聲音在時間裡運行是不夠的,還要加上第二個要素,那就是內容,即訴諸心靈的精神洋溢的情感,以及聲音所顯示的這種內容的精華表現」(黑格爾,1979)。這樣的精神表現與古典主義時期的音樂表現是不同的,古典主義時期美學的追求是視音樂作品為自身存在的客體,追求思想邏輯的清晰與形式的完美,而浪漫時期的音樂則是追求更強烈的情感表達。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音樂與文學的結合有了不同的嶄新面貌。
首先,在德國,歌德書寫了大量的抒情詩與著名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1774)。歌德的抒情詩表達了他對生活的熱愛與追求、對愛情的豐富體驗以及對自然無比的崇敬,他是浪漫主義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歌德作為這場新美學運動的實踐家,順勢也帶動了其他文學家的加入,尤以霍夫曼(E.T.A. Hoffmann, 1776-1822)與施萊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為代表,他們二人率先提出浪漫主義藝術運動的思想綱領,他們反對古典主義的理性,強調創作自由、情感與想像的意義,並主張「主體對自己的獨立自由的認識」(朱立元,2000)。這對當時的社會及藝術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自此,作家們紛紛提出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側重表達理想與抒發個人情感,具有強烈的主觀性。透過對理想世界和大自然的描繪,這些作品傳達了對現實世界的不滿與挑戰。
霍夫曼本身也是一位作曲家與音樂評論家,他認為,音樂是一種最浪漫的藝術,這種浪漫是一種世界觀,它代表永恆與和諧,對過去的美好與理想的未來充滿憧憬,然而,卻對現實世界充滿失落感。歌德與霍夫曼可以並列為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與音樂思想的兩大巨匠。霍夫曼的想法深深地影響著十九世紀的音樂與文學創作,他的影響力不只限於當時的德國文學,也擴及歐洲各國的文學,許多作曲家都從他的作品中尋找靈感,例如舒曼的鋼琴作品《克萊斯勒魂》(Kreisleriana, Op.16, 1838)、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的芭蕾舞劇《胡桃鉗》(The Nutcracker, 1892)、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的歌劇《霍夫曼的故事》(Les Contes d’Hoffmann, 1881)中的〈船歌〉(Barcarolle)等。至於歌德的諸多抒情詩,更是許多作曲家取材的對象,譬如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就譜寫了超過兩百首歌德的抒情詩,而貝多芬也採用了許多歌德的抒情詩來譜曲。
音樂與文學的有機結合,將聽覺中的音樂形象轉化為詩所描繪的視覺形象,又將原本詩中靜態的形象和情感轉化為直觀的聽覺體驗。音樂作為特殊的時間與空間藝術,在情感的表達上,不僅可以透過賦比興的手法,細膩且具體地刻劃形象特質,也為詩歌拓展了更豐富的想像空間。這種結合文學與音樂形象的藝術,賦予人們一種直觀與理性的雙重美感。
如果說,歌德的作品側重於詩歌的抒情性,那麼霍夫曼的作品就是想像力實踐的代表,它們富含哲思,同時也充滿著超自然與怪誕事物所構成的驚奇感。這兩條路線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發展的兩大軸線。藝術家們致力於使不可能成為可能,使虛無獲得形象與實體。他們致力於捕捉那稍縱即逝的美,賦予美形式,從而實現創作美的崇高使命。他們以藝術作為中介,大膽地走入生命底層,誘發那混沌世界與靈魂交感。代表第一條路線的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等,他們歌頌生命,寄情自然,既知世界不盡理想,仍然以藝術的獨到眼光,將現實世界的不圓滿寄託於大自然或者烏托邦的理想世界,為他們的時代留下美麗的作品。就此,他們稱得上是理想主義者。代表第二條路線的舒曼、白遼士(Hector Belioz, 1803-1869)、華格納等,則是幻想家,他們以音樂為筆,將世界的不圓滿,化為幻想的神話世界,以個人獨特的手法,將霍夫曼與施萊格爾的美學思想,化為十九世紀最奇幻與驚奇的音樂詩篇。在《權力意志》一書中,尼采說:「藝術比真理更有價值」(尼采,2013)。這句話可以總結十九世紀西歐藝術家的創作思維。於是,超人(?bermensch)大膽地走入創作世界,取得對客體與混沌世界的最高控制權,進而成為自我以及世界的主宰,透過他對生命的謳歌,為歷史留下美麗的見證。
早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葉,西方的思想圈與文藝圈就為浪漫精神的散播埋下了種子。隨著盧梭「回歸自然」的主張,藝術家的個性與情感開始被解放出來,情感與想像力自由地翱翔,音樂與文學終於有機會可以更進一步擦出燦爛的火花。
音樂與文學的結合,在浪漫主義時代到達發展的高峰。音樂原本就是最能夠直接表達人類情感經驗的藝術媒介之一,在文字的協助妝點下,音樂得以將抽象的內容相對具體化,進而得到更明確的表現力。如同黑格爾所言:「要使音樂充分發揮它的作用,抽象的聲音在時間裡運行是不夠的,還要加上第二個要素,那就是內容,即訴諸心靈的精神洋溢的情感,以及聲音所顯示的這種內容的精華表現」(黑格爾,1979)。這樣的精神表現與古典主義時期的音樂表現是不同的,古典主義時期美學的追求是視音樂作品為自身存在的客體,追求思想邏輯的清晰與形式的完美,而浪漫時期的音樂則是追求更強烈的情感表達。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音樂與文學的結合有了不同的嶄新面貌。
首先,在德國,歌德書寫了大量的抒情詩與著名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1774)。歌德的抒情詩表達了他對生活的熱愛與追求、對愛情的豐富體驗以及對自然無比的崇敬,他是浪漫主義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歌德作為這場新美學運動的實踐家,順勢也帶動了其他文學家的加入,尤以霍夫曼(E.T.A. Hoffmann, 1776-1822)與施萊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為代表,他們二人率先提出浪漫主義藝術運動的思想綱領,他們反對古典主義的理性,強調創作自由、情感與想像的意義,並主張「主體對自己的獨立自由的認識」(朱立元,2000)。這對當時的社會及藝術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自此,作家們紛紛提出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側重表達理想與抒發個人情感,具有強烈的主觀性。透過對理想世界和大自然的描繪,這些作品傳達了對現實世界的不滿與挑戰。
霍夫曼本身也是一位作曲家與音樂評論家,他認為,音樂是一種最浪漫的藝術,這種浪漫是一種世界觀,它代表永恆與和諧,對過去的美好與理想的未來充滿憧憬,然而,卻對現實世界充滿失落感。歌德與霍夫曼可以並列為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與音樂思想的兩大巨匠。霍夫曼的想法深深地影響著十九世紀的音樂與文學創作,他的影響力不只限於當時的德國文學,也擴及歐洲各國的文學,許多作曲家都從他的作品中尋找靈感,例如舒曼的鋼琴作品《克萊斯勒魂》(Kreisleriana, Op.16, 1838)、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的芭蕾舞劇《胡桃鉗》(The Nutcracker, 1892)、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的歌劇《霍夫曼的故事》(Les Contes d’Hoffmann, 1881)中的〈船歌〉(Barcarolle)等。至於歌德的諸多抒情詩,更是許多作曲家取材的對象,譬如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就譜寫了超過兩百首歌德的抒情詩,而貝多芬也採用了許多歌德的抒情詩來譜曲。
音樂與文學的有機結合,將聽覺中的音樂形象轉化為詩所描繪的視覺形象,又將原本詩中靜態的形象和情感轉化為直觀的聽覺體驗。音樂作為特殊的時間與空間藝術,在情感的表達上,不僅可以透過賦比興的手法,細膩且具體地刻劃形象特質,也為詩歌拓展了更豐富的想像空間。這種結合文學與音樂形象的藝術,賦予人們一種直觀與理性的雙重美感。
如果說,歌德的作品側重於詩歌的抒情性,那麼霍夫曼的作品就是想像力實踐的代表,它們富含哲思,同時也充滿著超自然與怪誕事物所構成的驚奇感。這兩條路線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發展的兩大軸線。藝術家們致力於使不可能成為可能,使虛無獲得形象與實體。他們致力於捕捉那稍縱即逝的美,賦予美形式,從而實現創作美的崇高使命。他們以藝術作為中介,大膽地走入生命底層,誘發那混沌世界與靈魂交感。代表第一條路線的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等,他們歌頌生命,寄情自然,既知世界不盡理想,仍然以藝術的獨到眼光,將現實世界的不圓滿寄託於大自然或者烏托邦的理想世界,為他們的時代留下美麗的作品。就此,他們稱得上是理想主義者。代表第二條路線的舒曼、白遼士(Hector Belioz, 1803-1869)、華格納等,則是幻想家,他們以音樂為筆,將世界的不圓滿,化為幻想的神話世界,以個人獨特的手法,將霍夫曼與施萊格爾的美學思想,化為十九世紀最奇幻與驚奇的音樂詩篇。在《權力意志》一書中,尼采說:「藝術比真理更有價值」(尼采,2013)。這句話可以總結十九世紀西歐藝術家的創作思維。於是,超人(?bermensch)大膽地走入創作世界,取得對客體與混沌世界的最高控制權,進而成為自我以及世界的主宰,透過他對生命的謳歌,為歷史留下美麗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