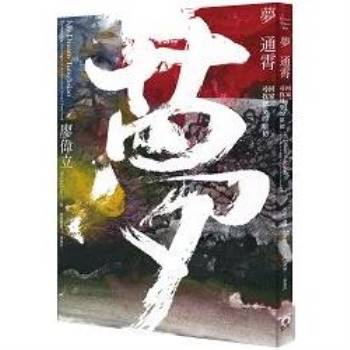「『設計』是一個繭(cocoon)、一個殼,要怎麼將它破解開來?」這是廖偉立在建築創作路上不停自問的問題。
讓他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是已故美國知名建築學者、丹佛大學建築系教授道格拉斯.達爾頓(Douglas Darden)。透過好友建築師徐純一的介紹,廖偉立認識了達爾頓。這位教授在看過廖偉立的手稿後建議他,應該找機會出國再多歷練。
這場景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畫面在他腦海中依舊清晰,教授將他的手擺在紙上畫出手形,並在手形的外圍畫了個圈,看著他說:「Shell yourself.」(「去掉自己的殼」,引申為「自我破解」。)
那一句話,成為廖偉立決定出國再唸書的動力。他時時提醒自己,專業更要避免陷在專業的窠臼裡,不應遠離生活上真正的需求,「不管是學院教育或是專業訓練,都是一種限制、束縛,最後都一定要把它解脫掉,就像脫去一層外衣。」
破繭之後,才能蛻變。
廖偉立的求學之路,就是一段不停蛻變的歷程,每一段路程的衝擊,都是建築設計的養分。十五歲那年,是他人生第一次的蛻變。由於家境的關係,無酒就讀普通高中,於是進入大安高工建築科就讀,於是他從此栽進了建築的世界。
「很好玩!這些訓練讓我對材料力學與結構有更深的認識。」當時高工扎實的技術訓練,讓廖偉立有機會親手碰觸各種建築材料,刨木、砌磚,是每個學生的基本功。他回憶,在他求學的六、七〇年代,職校注重手做、實作的教育方式,恰好呼應了二次大戰時德國包浩斯(Bauhaus)學校「做中學」的理念,當時包浩斯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期望結合建築、藝術與工藝,抹去工匠與藝術家之間的界線,理論與實務並重,進而影響了歐美甚至全球各方面的設計發展。
當時高工的班級學生數不多,在校時間又長,讓師生之間的關係特別親近。「老師把你當自己的小孩!」有件事,讓廖偉立格外感動。二年級時,廖偉立看見對面師大附中的學生樣子格外瀟灑,讓他感覺唸普通高中好像就能夠「走路有風」,他於是決定休學唸書,全力拼高中聯考。但現實與理想間總有距離,高職小孩光靠土法煉鋼,實在愛拼也不會贏,當天才考了一、兩科,廖偉立就走出考場,放棄了考試。沒有金榜題名,他深感臉上無光,就連學校也不敢回,眼看學期都過一、兩個月了,卻只能在家硬撐著。有天,出乎他意料之外,幸運來敲了門,班上老師陳炳嘉親自登門造訪,把他找回了學校,為他開啟了回到建築路上的那扇門。
好玩,讓建築設計自由自在
「好玩」這兩個字,貫穿了廖偉立的求學生涯。他從高工「玩進」台北工專,再插大進入淡江建築系。一個來自工專的大二插班生,一開始的求學生涯很挫折,自覺處處不如人,班上的同學甚至對他「嗆聲」:「你們這些工專轉來的,不要太混!」廖偉立那顆被激起的好勝心,讓他更加認真,即便下課也緊抓著老師不放。大三那年,他的成績越來越好,也遇見開啟他建築視野的恩師王淳隆。
信佛的王淳隆將佛法修行的概念放進建築中,認為「空間」與「人」應是緊密相連,居住者透過建築物而能身心和諧。這也打開了廖偉立對建築更深的思考,「建築就是尋找關係的過程」,他心中一個「好建築師」的樣貌,逐漸出現輪廓。
在淡江那幾年,廖偉立開始拿起畫筆,用雙眼睛去觀察、感受周遭環境,用雙腳上山下海,能走到的地方就去畫,觀音山、渡船頭、學校周遭的稻田,都是他畫筆下的主題,「那時我對地景、村落有種莫名的喜愛,席德進、李雙澤的畫對我都有影響。」
東方的水墨與西方的水彩,在廖偉立的畫作中交融。他從未學畫,但想揮筆作畫的慾望卻強烈得像是攔不住的洪水,在畫紙上恣意揮灑,代替文字訴說他內心更深層的感受,「會想畫畫,是對環境及時間的眷戀,看到美的東西就想畫下來。」
大三時,一堂美學大師蔣勳的「藝術概論」,廖偉立在作業裡畫了插畫,得到了高分,也讓他對自己的畫作更具信心。另一堂課的老師甚至邀請他以漫畫方式詮釋建築人的聖經《模式語彙之再現》(Pattern Language),這一畫,也畫出了興致與名聲。他開始在報紙上畫漫畫,甚至得到了一個日本頒發的獎項。這一切,都出自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念頭:好玩、愛玩。
或許這個「玩」的意念,早從兒時就已經種在他的心中,從來沒有消失過。因為能永遠像孩子那樣盡情的玩,一顆自在無拘束的心,才能讓他的創作力源源不絕。廖偉立曾說:「我希望像西班牙建築師米格爾·費薩克(Miguel Fisac),一生對建築充滿好奇的(curious)、追根究柢的(inquisitive)、頑強的(tenacious)個性。」費薩克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後期西班牙現代建築大師,曾獲西班牙國家建築獎,除了建築創作,他的設計領域更擴及家具、工業、城市設計及繪畫等面相,建築作品從外觀就與眾不同,充滿想像力。像是知名作品「La Pagoda」(寶塔),五個八邊形交叉重疊,外觀超脫一般人對建築筆直方正的刻板印象,彷彿存在童話繪本裡的想像世界。
大三之後,最初被看輕的工專轉學生,開始取代班上原本「永遠第一名」的地位,廖偉立說自己念書其實沒有什麼好方法,除了多看書之外,他總是抓著老師不放,努力填補自己過去的不足。大學五年級,當其他同學為了畢業製作忙得暈頭轉向,廖偉立非但完成了他的「淡水渡船頭」設計案,甚至還在校園舉辦「畢業水彩個展」,登上了《聯合報》版面。
重返校園的蛻變之路
畢業後,廖偉立隨即投入職場,他先是在台灣知名建築師李祖原的事務所工作了九個多月,之後又到潘冀的事務所待了快六年。廖偉立看見李祖原對中國建築所懷抱的使命感,也讓他從歷史人文的角度出發,對於建築格局有更多的思考。相對較為理性的潘冀,則讓廖偉立學習到專業知識技能,蹲馬步、練基本功。
那時,他心裡那個「不足」、「總是想要瞭解更多」的求知慾,又在他身上蠢蠢欲動。一旦決定了,就去做,廖偉立總是如此,他寧可毫不猶豫的啟程,也不願意留在原地躊躇後悔。
工作七年之後,他再度回到校園唸研究所,成為東海大學研究生。當時的東海校園,是由國際知名建築師貝聿銘、陳其寬及張肇康所設計,置身其中,讓廖偉立感受到一個整體的景觀規劃與設計,校園建築受到中國合院的影響,路思義教堂更是信仰建築的新發明,現代主義風格的設計,雙手合十、手掌微開的三角形,成為具有東方意涵的基督教堂。他回憶,「那應該是台灣最好的校園,氛圍和環境對我來說是種洗禮,開闊了我的視野,這些,都比在學校學了些什麼來得重要。」
畢業後,廖偉立成立自己的建築事務所,但心底想要再出國深造的慾望卻一直催促著他,達爾頓教授的那番話,時時在他心裡,成為一股動力,讓他在事務所有穩固的基礎時,仍決定出走,再度破繭。對於年近四十才出國唸書的廖偉立來說,這段一年半的旅程並不容易。抵達洛杉磯頭一天,想家的痛苦幾乎就要將他吞噬。語言的隔閡、人生地不熟的困窘、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在異鄉巨大得讓他難以承受。他一個人開著車,車裡播放著老婆從台灣寄來的台語歌曲,那是他跟家鄉唯一熟悉的連結。廖偉立回憶,「我泡澡的習慣就是那時養成的,水拿掉時,漩渦好像是要把我的靈魂吸走。」
南加州建築學院(Sci-Art,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位於洛杉磯市,在建築界的評價相當高,擁有相當多知名老師與畢業生,讓廖偉立印象格外深刻的是,校園文化崇尚天然手作,呈現出自然的藝術氛圍,也與他的生命觀相容。
當時廖偉立師事Coy Howard及Eric Owen Moss兩位老師。雖置身西方,但Coy Howard卻對東方哲學頗有研究,甚至十分認同老子的道家思想。他告訴廖偉立:「唯有回到母體,才能夠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好建築。」而Eric Owen Moss則經常與他分享:「敞開心靈,挖掘自己最大的潛力與可能性,才有可能做出好作品。」
求學過程中最大的衝擊,是一次對他來說難如登天的作業:設計「以色列博物館」。過去,廖偉立設計建築向來是行雲流水,但面對這個異國課題,他卻完全沒有靈感,「我很勉強的做出來,雖然概念不錯,但做得不好。那是文化的差異,有人做設計不必跟文化對話,但我不行。」
那次震撼教育,讓廖偉立深刻瞭解Coy Howard所說的話,他最終必須回到原鄉,回到屬於母體的文化,「要超越文化,就要跟天地學習,人要跟自然連結在一起,那麼不用充電,每天就會是一個發電機。」
東海與南加州建築學院,這兩次重返校園的學生生活,讓廖偉立接觸到不同的建築教育及文化氛圍,站在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的文化基礎上,以更高的視點重新解讀台灣多元、複雜又混沌的文化場域。
廖偉立曾為文談到,由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複雜,形成一種更多元、衝突、反叛的能量與狀態。因此,台灣的建築師要能打一場又一場「揚長避短」的游擊戰法,才能有所突破。台灣的建築環境,就像在叢林作戰一樣,危險陷阱處處,卻也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要拿出生猛的戰鬥力來應對叢林的瞬息萬變。
廖偉立從來就不是正規軍,打游擊是命定,自由自在的作戰,才能讓他的「建築如水,無處不自在。」
讓他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是已故美國知名建築學者、丹佛大學建築系教授道格拉斯.達爾頓(Douglas Darden)。透過好友建築師徐純一的介紹,廖偉立認識了達爾頓。這位教授在看過廖偉立的手稿後建議他,應該找機會出國再多歷練。
這場景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畫面在他腦海中依舊清晰,教授將他的手擺在紙上畫出手形,並在手形的外圍畫了個圈,看著他說:「Shell yourself.」(「去掉自己的殼」,引申為「自我破解」。)
那一句話,成為廖偉立決定出國再唸書的動力。他時時提醒自己,專業更要避免陷在專業的窠臼裡,不應遠離生活上真正的需求,「不管是學院教育或是專業訓練,都是一種限制、束縛,最後都一定要把它解脫掉,就像脫去一層外衣。」
破繭之後,才能蛻變。
廖偉立的求學之路,就是一段不停蛻變的歷程,每一段路程的衝擊,都是建築設計的養分。十五歲那年,是他人生第一次的蛻變。由於家境的關係,無酒就讀普通高中,於是進入大安高工建築科就讀,於是他從此栽進了建築的世界。
「很好玩!這些訓練讓我對材料力學與結構有更深的認識。」當時高工扎實的技術訓練,讓廖偉立有機會親手碰觸各種建築材料,刨木、砌磚,是每個學生的基本功。他回憶,在他求學的六、七〇年代,職校注重手做、實作的教育方式,恰好呼應了二次大戰時德國包浩斯(Bauhaus)學校「做中學」的理念,當時包浩斯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期望結合建築、藝術與工藝,抹去工匠與藝術家之間的界線,理論與實務並重,進而影響了歐美甚至全球各方面的設計發展。
當時高工的班級學生數不多,在校時間又長,讓師生之間的關係特別親近。「老師把你當自己的小孩!」有件事,讓廖偉立格外感動。二年級時,廖偉立看見對面師大附中的學生樣子格外瀟灑,讓他感覺唸普通高中好像就能夠「走路有風」,他於是決定休學唸書,全力拼高中聯考。但現實與理想間總有距離,高職小孩光靠土法煉鋼,實在愛拼也不會贏,當天才考了一、兩科,廖偉立就走出考場,放棄了考試。沒有金榜題名,他深感臉上無光,就連學校也不敢回,眼看學期都過一、兩個月了,卻只能在家硬撐著。有天,出乎他意料之外,幸運來敲了門,班上老師陳炳嘉親自登門造訪,把他找回了學校,為他開啟了回到建築路上的那扇門。
好玩,讓建築設計自由自在
「好玩」這兩個字,貫穿了廖偉立的求學生涯。他從高工「玩進」台北工專,再插大進入淡江建築系。一個來自工專的大二插班生,一開始的求學生涯很挫折,自覺處處不如人,班上的同學甚至對他「嗆聲」:「你們這些工專轉來的,不要太混!」廖偉立那顆被激起的好勝心,讓他更加認真,即便下課也緊抓著老師不放。大三那年,他的成績越來越好,也遇見開啟他建築視野的恩師王淳隆。
信佛的王淳隆將佛法修行的概念放進建築中,認為「空間」與「人」應是緊密相連,居住者透過建築物而能身心和諧。這也打開了廖偉立對建築更深的思考,「建築就是尋找關係的過程」,他心中一個「好建築師」的樣貌,逐漸出現輪廓。
在淡江那幾年,廖偉立開始拿起畫筆,用雙眼睛去觀察、感受周遭環境,用雙腳上山下海,能走到的地方就去畫,觀音山、渡船頭、學校周遭的稻田,都是他畫筆下的主題,「那時我對地景、村落有種莫名的喜愛,席德進、李雙澤的畫對我都有影響。」
東方的水墨與西方的水彩,在廖偉立的畫作中交融。他從未學畫,但想揮筆作畫的慾望卻強烈得像是攔不住的洪水,在畫紙上恣意揮灑,代替文字訴說他內心更深層的感受,「會想畫畫,是對環境及時間的眷戀,看到美的東西就想畫下來。」
大三時,一堂美學大師蔣勳的「藝術概論」,廖偉立在作業裡畫了插畫,得到了高分,也讓他對自己的畫作更具信心。另一堂課的老師甚至邀請他以漫畫方式詮釋建築人的聖經《模式語彙之再現》(Pattern Language),這一畫,也畫出了興致與名聲。他開始在報紙上畫漫畫,甚至得到了一個日本頒發的獎項。這一切,都出自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念頭:好玩、愛玩。
或許這個「玩」的意念,早從兒時就已經種在他的心中,從來沒有消失過。因為能永遠像孩子那樣盡情的玩,一顆自在無拘束的心,才能讓他的創作力源源不絕。廖偉立曾說:「我希望像西班牙建築師米格爾·費薩克(Miguel Fisac),一生對建築充滿好奇的(curious)、追根究柢的(inquisitive)、頑強的(tenacious)個性。」費薩克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後期西班牙現代建築大師,曾獲西班牙國家建築獎,除了建築創作,他的設計領域更擴及家具、工業、城市設計及繪畫等面相,建築作品從外觀就與眾不同,充滿想像力。像是知名作品「La Pagoda」(寶塔),五個八邊形交叉重疊,外觀超脫一般人對建築筆直方正的刻板印象,彷彿存在童話繪本裡的想像世界。
大三之後,最初被看輕的工專轉學生,開始取代班上原本「永遠第一名」的地位,廖偉立說自己念書其實沒有什麼好方法,除了多看書之外,他總是抓著老師不放,努力填補自己過去的不足。大學五年級,當其他同學為了畢業製作忙得暈頭轉向,廖偉立非但完成了他的「淡水渡船頭」設計案,甚至還在校園舉辦「畢業水彩個展」,登上了《聯合報》版面。
重返校園的蛻變之路
畢業後,廖偉立隨即投入職場,他先是在台灣知名建築師李祖原的事務所工作了九個多月,之後又到潘冀的事務所待了快六年。廖偉立看見李祖原對中國建築所懷抱的使命感,也讓他從歷史人文的角度出發,對於建築格局有更多的思考。相對較為理性的潘冀,則讓廖偉立學習到專業知識技能,蹲馬步、練基本功。
那時,他心裡那個「不足」、「總是想要瞭解更多」的求知慾,又在他身上蠢蠢欲動。一旦決定了,就去做,廖偉立總是如此,他寧可毫不猶豫的啟程,也不願意留在原地躊躇後悔。
工作七年之後,他再度回到校園唸研究所,成為東海大學研究生。當時的東海校園,是由國際知名建築師貝聿銘、陳其寬及張肇康所設計,置身其中,讓廖偉立感受到一個整體的景觀規劃與設計,校園建築受到中國合院的影響,路思義教堂更是信仰建築的新發明,現代主義風格的設計,雙手合十、手掌微開的三角形,成為具有東方意涵的基督教堂。他回憶,「那應該是台灣最好的校園,氛圍和環境對我來說是種洗禮,開闊了我的視野,這些,都比在學校學了些什麼來得重要。」
畢業後,廖偉立成立自己的建築事務所,但心底想要再出國深造的慾望卻一直催促著他,達爾頓教授的那番話,時時在他心裡,成為一股動力,讓他在事務所有穩固的基礎時,仍決定出走,再度破繭。對於年近四十才出國唸書的廖偉立來說,這段一年半的旅程並不容易。抵達洛杉磯頭一天,想家的痛苦幾乎就要將他吞噬。語言的隔閡、人生地不熟的困窘、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在異鄉巨大得讓他難以承受。他一個人開著車,車裡播放著老婆從台灣寄來的台語歌曲,那是他跟家鄉唯一熟悉的連結。廖偉立回憶,「我泡澡的習慣就是那時養成的,水拿掉時,漩渦好像是要把我的靈魂吸走。」
南加州建築學院(Sci-Art,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位於洛杉磯市,在建築界的評價相當高,擁有相當多知名老師與畢業生,讓廖偉立印象格外深刻的是,校園文化崇尚天然手作,呈現出自然的藝術氛圍,也與他的生命觀相容。
當時廖偉立師事Coy Howard及Eric Owen Moss兩位老師。雖置身西方,但Coy Howard卻對東方哲學頗有研究,甚至十分認同老子的道家思想。他告訴廖偉立:「唯有回到母體,才能夠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好建築。」而Eric Owen Moss則經常與他分享:「敞開心靈,挖掘自己最大的潛力與可能性,才有可能做出好作品。」
求學過程中最大的衝擊,是一次對他來說難如登天的作業:設計「以色列博物館」。過去,廖偉立設計建築向來是行雲流水,但面對這個異國課題,他卻完全沒有靈感,「我很勉強的做出來,雖然概念不錯,但做得不好。那是文化的差異,有人做設計不必跟文化對話,但我不行。」
那次震撼教育,讓廖偉立深刻瞭解Coy Howard所說的話,他最終必須回到原鄉,回到屬於母體的文化,「要超越文化,就要跟天地學習,人要跟自然連結在一起,那麼不用充電,每天就會是一個發電機。」
東海與南加州建築學院,這兩次重返校園的學生生活,讓廖偉立接觸到不同的建築教育及文化氛圍,站在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的文化基礎上,以更高的視點重新解讀台灣多元、複雜又混沌的文化場域。
廖偉立曾為文談到,由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複雜,形成一種更多元、衝突、反叛的能量與狀態。因此,台灣的建築師要能打一場又一場「揚長避短」的游擊戰法,才能有所突破。台灣的建築環境,就像在叢林作戰一樣,危險陷阱處處,卻也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要拿出生猛的戰鬥力來應對叢林的瞬息萬變。
廖偉立從來就不是正規軍,打游擊是命定,自由自在的作戰,才能讓他的「建築如水,無處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