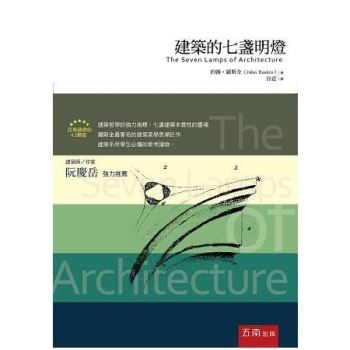第一章
獻祭之燈
Ⅰ
「建築」是這樣一種藝術:它將由人類所築起,不論用途為何的建物,處理、佈置、裝飾,讓它們映入人們眼廉時的象貌,可為心靈帶來愉悅、滿足,和力量,並且促進心靈的圓滿。
任何與此相關的研究,打從最開始,都極有必要謹慎區別「建築」與「建物」。
在英文裡,「建」,字面上的意義,就是加以強化、使之確定;至於我們對它的一般理解,就是對任何具有相當尺寸的建物,或者可供容人納物的空間,就其所擁有的一些組成部分,加以湊合調整、組合連結。於是便有教堂之興建、居家之興建、船艦之興建、車體之興建。它們的建成品有的立於地上,有的浮於水中,有的則是懸吊於鐵製彈簧的避震結構上,表面上儘管有所差異,但是就這門關於建造的,或者說「精化」的技藝──如果可以這樣稱呼它的話──本質上卻沒有不同。精通建造之藝的人,是那些分別隸屬於教會、海軍之下,或者是那些不論名字為何,總之是與他所完成的工作相應的建築(造)工人。不過,建造,不會僅憑它樹立於大地上的成品穩當堅固,就是「建築」;讓一座教堂得以建立,或者讓它有辦法輕鬆容納為了執行某些教會職務所必要的人員,所憑藉的也不是「建築」;讓車箱寬敞舒適、船隻行走迅捷的,也不是。當然,我的意思並非是說,「建築」這個詞不常,或者甚至不可以有上面那種意義,就像英文裡的確很慣用「船的建築 」這種說法。只是,在那樣的用法之下,「建築」就不是一門精妙的藝術了;總之,術語定義若是模糊與不確定,讓屬於建造工程的全部原理原則都可能伸入嚴格意義之建築領域內,從而不時產生,同時也會持續產生種種混淆──這種風險還是別去招攬的好。
職此之故,讓我們馬上給這種藝術下一個確定而不變的定義,它將廣義的建築一詞所必然指涉,並且一般而言皆會指涉的意義吸納進去,當作是運用這個定義的基本條件,在這基礎形式之上,再去強調那些令人肅然起敬,或者是帶來美感,然而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必要性的性質 。據此,容我這樣說:那些定出軍堤應該建至多高,或者稜堡應該座落何處的法則,不會有人稱其為「建築」的法則。但是,如果在那座稜堡的石頭飾面添上某個非必要的外觀特徵,例如立體繩紋裝飾──那,就是「建築」了。若將堞口或槍眼城垛這些東西稱為是「建築上的」特徵,然而一旦它們的構成元件,不過是由居高臨下的主體建物撐起面臨前線的走廊,然後用間隔出現的孔隙向下發動攻擊的話,依據與上述類似的道理,這種稱呼方式就不甚合理。不過,如果在這些高聳的主體建物根處,刻出層層環繞的紋路,而那當然是沒有用處的;或者如果把垛的頂面做成拱形,甚至是三葉形,當然那也是沒有用處的──但那,就是「建築」。這分野或許不總是能夠輕易地清楚得見。因為,很少有建物不擁有些許「建築」的因子,讓它們可以聲稱或者假扮自己就是「建築」;反之,任何「建築」都不免需要以建物為基礎,而所有好「建築」所奠基於上者,也全都是好的建物;不過,即便如此,保持觀念上的清楚區別,並且透澈地理解到:「建築」只關注建物在日常用途之外,更高、更超越的那些特徵──這一點,則是非常必要,也容易至極的事。是的,我是說「日常」用途;因為,若是一棟為了榮耀上帝,或者緬懷偉人而設立的建物,它這用途,無疑可與自身那些具有建築意義的裝飾工程相容;但這用途卻必然不會使它非去滿足某些實際需求不可,以致於限制了它在整體或是細節上的設計。
Ⅱ
承上所述,嚴格意義的建築,依其本然之性質,可以分編到下列五種項目之下:
信仰:包括所有為了服侍、禮拜或榮耀上帝而興建的建物。
記念:無論是墓地、墓碑,或是專門緬懷某人的碑、塔、樓、館等,皆包括在內。
公共:目的在供眾人共同事務之用,或者順應公眾之意願,而由國家、民族、社群、或團體,所興築的任何建物。
軍事:所有私有或公有的防禦建築。
家用:任何階層及任何種類的住所。
此處,我將要努力發展建立的原則,它們雖然如同我曾經提到的,必須全部都能夠適用於任何階段、任何風格的建築上;不過,其中有些,尤其是那些較具有啟發性,而非指導性的原則,它們必然與上述建築中的某一類,有著相對來說更完整的參照價值與關連性;在它們之中,我會將其影響雖然及於所有建築,不過終究與信仰性及記念性建築特別有關的一種精神擺在最先。那是種想替這兩類建築獻出珍貴事物的精神。獻出,單純只是因為那些是珍貴的事物;不是作為那座建物不可或缺之物件,而是身為我們自己渴望與喜愛之物,而被當作一份奉獻、一份呈給、一份祭品。依我看來,時至當下,在那些推動信仰性建物的興建與發展的人們身上,似乎多數都全然欠缺這種精神;非但如此,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甚至把它當作是一項危險的,或者說不定是可恥的原則。有各式各樣的反對意見都可以用來充作大聲疾呼、反對這種精神的論調,礙於篇幅,我不擬對其全部進行辯駁;它們為數太多,而且多半似是而非。不過,或許我可以懇請讀者撥冗一閱,容我書下一些簡單明暸的理由,說明為什麼我會認為自己這樣的看法──若要完成任何一項偉大的建築作品(而這正是我們目前關注的主題),上述精神無庸置疑是不可或缺的──乃是既可令上帝欣然而悅,亦可讓人類深感光榮,從而會是種持平而正確的真知灼見。
Ⅲ
那麼,首先便是界定清楚,這座犧牲獻祭之「燈」(也就是「精神」)所指為何。我曾經提到,我們之所以有股衝動想獻出珍貴的事物,僅僅是因為它們珍貴,而不是因為它們的功用,也不是因為它們對作品來說不可或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呢?舉例來說,當有兩片大理石,同樣漂亮、同樣合用,也同樣經久耐磨,那麼就會想要挑選價格比較高的那片,只是因為它貴;有兩種裝飾作法,效果同樣顯著,會想要挑選比較精緻的那種,只是因為它費心;也就是說,這是追求去在同樣的範疇裡,呈現出一個花費了更高代價,付費了更多心思的成果。它因此是最不符合理性的表現,也因此是最熱情無悔的表現;而或許,要界定這種精神,最清楚的是方式是從反面定義:它,與盛行於現代的觀感──渴望用最少的成本,產出最多的結果──正好相反。
接著,論及奉獻精神時,有兩種壁壘分明的形式:其一是,這種自我否定的行動,單純就是為了達到自律;是為了自律這個願望,而做出放棄自己深愛或者渴望之事物的行為;也就是說,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其他直接的要求或目的,是這種行為要去滿足的。其二則是,渴望用犧牲的代價之重,來榮耀「他者」,或者令其喜悅。現實中,屬於第一種類型者,性質上可能有屬於私人的,也可能有公共的行為;不過,最常見到的是──或許它也最應當是──私人性質的。另一方面,屬於第二種類型者,則通常是公共的,而當它是公共性質時,所帶來的益處也最大。話既如此,若我想做的主張是這樣:不為其他目的,就只為了它本身,而去實行自我否定的行為,自有其合算之處──我不得不說,這樣的主張乍看之下是無法得到認同的;畢竟,對於那許許多多其他種類的目的而言,自我否定的行為也都是如同吃飯喝水般地必要,其必要之程度甚至比親身實行的我們所知道的還深。不過我相信,之所以會如此,只是因為我們並沒有打心底承認這種行為的地位,或者對其思考得並不週全,才會不認為它本身就是件好事──也可以說,當它變成一道非關其他目的的道德誡命時,我們便太容易違背它發出的要求;也太容易去計算(這時立場多少會偏向自己)付予他人的好處,與己身受到的虧損,兩者是否相稱、是否合理;而不會認為這是於個人有益之事,而歡喜地接受這次犧牲奉獻的機會。事情就算如此,此處也沒有必要對其多所強調;畢竟,對那些選擇那麼做的人來說,永遠都有比起藝術更為崇高、也更加有用的途徑,來做到自我犧牲。
至於,說到第二種,也就是與藝術特別相關的形式,犧牲精神的正當性更是備受質疑;關於這一點,則以我們如何回答另一個更為概括的問題為依歸:上帝是否確實會因為任何呈獻給祂的珍貴物品:有形的、物質的事物;又是否真的會因為人類的熱忱與智慧──當它們不論投注於何種領域,總之對人群並沒有直接的助益時──而得到彰顯?
請讀者留心,因為此處問的,並不是建物之美觀與壯麗可不可以滿足於任何倫理目的;此刻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任何一種由勞動穫得的「果實」;而就只是單純在討論材質、勞力,和耗時,這些東西本身所呈現出來的奢華大氣。我們要問:這些東西本身,不看它們所獲致的成果,是不是上帝會接受的獻禮?祂認不認為這是在向祂表示敬意、是在彰顯祂的榮耀?就這個問題,一旦我們所參考者,是單獨源自自我感受、良心,或者源自理性所為的判斷,答案就將會自我矛盾,或者有所遺漏;這個問題,唯有在我們回答完另一個非常迥異的問題之後,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那問題便是:聖經是否可分新約舊約?又或者,舊約裡與新約裡顯示的上帝是否有所不同?Ⅳ
且說,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裡,為了某些具體的目的,人們會依上帝之旨,定下特定的儀禮,而這些儀禮,到了別的時期,可能會被同一個神聖權威所廢除;但是,雖然如此,藉由過去或現在的任何儀禮而得到描述或者示現的神性,卻不可能會有哪一個部分,會因某項儀禮的廢除而受到改變,或者也不可能將其理解成已有所改變──這一點,是最確然無疑的事實。上帝乃唯一與不變,其喜悅與憎厭的永遠都是同樣的事物──就算祂的喜好中有的部分,在某個時代或許會比別的時代表現得更明顯;就算考察祂的喜好的方式,得經祂寬大地依照人類所處之境況而有所調整。從而,以此為例:為了真正理解誰可得救,得救與否,最初必須以血腥獻祭這種模式加以預先顯明。然而,如今,已不似摩西的時代,這種犧牲再也不是上帝的喜好。犧牲,作為贖罪之補償,上帝從來就只接受過一種,而這唯一的一種,就叫做「與時俱進」,這點是我們絲毫都不可加以懷疑的;當祂給出神聖的命令,指定標示著某個時代的典型犧牲時,同時也就表明了所有其他的獻祭皆無價值。上帝是種靈性的存在,只有在心靈與真理的層面上,才有所謂對祂的崇拜可言;在過去的日常慣例裡,除了典型的、有形的、物質上的服侍或獻禮以外別無其他要求,是如此;而現在,祂所要求者唯有心之敬獻,亦是如此。
因此,這會是一個最穩當,也最確實的原則:某個時代的某種儀式,由它的執行方式所追溯、勾勒出的具體作法,若依前人所言,或者依我們自己合理的推斷,認為那是能夠在那個時代取悅上帝的作法,那麼,不論是在哪個時代,同樣的作法,在歸結到類似的執行方式,以完成任何敬神的儀式或服務時,一樣可以取悅上帝;除非,日後我們發現到:為了某些具體的目的,如今上帝有意廢除這些作法。而且,假如有人可以證明,對於儀式之於人類的用途與意義而言,這類作法在促成其完善方面並非必要,它們之所以存在於儀式中,只不過是因為它們本身乃上帝所喜,這麼一來更是大大替上面的說理增添許多說服力。Ⅴ
於是,一個人為了在祭典上以自己之名義獻出某類牲禮:因為那是《利未記》所規定之牲禮類型的一種。但他需要散盡自己所有錢財才辦得到,這對《利未記》那個年代祭典的完善,或者對祭典解釋神之旨意的效果而言是否必要呢?完全不是。牲禮所先行示現的犧牲,在當年也應該是種作為給上帝的免費禮物;取得該類牲禮的難度,或者是它的代價,只會模糊這個牲禮類型的分寸尺度,也使得上帝最終贈予全人類的禮物失去原本深邃的意義。儘管如此,「代價不菲」在當時就已是獻祭之所以能為上帝所接受的要件,沒有例外。「同樣地,若是我不需付出任何代價之物,我也不會獻給吾主,我的上帝。 」也因此,「代價不菲」必然是古往今來,人類獻禮可以為上帝接受的條件;原因是這個性質曾經取悅過上帝,於是它必定一直都能夠取悅上帝,除非在那之後曾經由祂直接禁止,而這是從來不曾發生過的事。
其次,牲禮必須是牲口裡品級最好者,這一點對於利未禮儀本身的完善性而言是必要的嗎?毫無疑問地,就當時而言,獻祭本身越完美無瑕,它在基督徒的心目中越有意義;但是對基督徒越有意義,就會讓這一點成為準確無誤地上帝實際上所要求的嗎?一點也不。上帝在那時候之所以要求最好的,很明顯地,就跟俗世的統治者也會要求最好的,是基於相同的理由:以此作為敬意的證明。「將它獻給你的統治者。 」至於價值較低的獻禮當時之所以為上帝所拒絕,原因並不在於它既無法反應基督的形象,又不能滿足犧牲的目的。而是在於:它傳達了一種情緒或想法:不願意將主賜給我們擁有的東西中,最好的部分獻祭給祂;此外也在於:那會是對人們眼中的上帝施加無禮的侮辱。依據上面所述,可以確定無疑的是:就那些我們現在覺得有理由呈獻給上帝的獻禮而言(此處,我的意思並非指出這些獻禮可以是什麼),它們必須是同類事物中最棒的這一點,在我們這個時代,就跟它在過往一樣,也會是這些獻禮可以為上帝所接受的要件。
獻祭之燈
Ⅰ
「建築」是這樣一種藝術:它將由人類所築起,不論用途為何的建物,處理、佈置、裝飾,讓它們映入人們眼廉時的象貌,可為心靈帶來愉悅、滿足,和力量,並且促進心靈的圓滿。
任何與此相關的研究,打從最開始,都極有必要謹慎區別「建築」與「建物」。
在英文裡,「建」,字面上的意義,就是加以強化、使之確定;至於我們對它的一般理解,就是對任何具有相當尺寸的建物,或者可供容人納物的空間,就其所擁有的一些組成部分,加以湊合調整、組合連結。於是便有教堂之興建、居家之興建、船艦之興建、車體之興建。它們的建成品有的立於地上,有的浮於水中,有的則是懸吊於鐵製彈簧的避震結構上,表面上儘管有所差異,但是就這門關於建造的,或者說「精化」的技藝──如果可以這樣稱呼它的話──本質上卻沒有不同。精通建造之藝的人,是那些分別隸屬於教會、海軍之下,或者是那些不論名字為何,總之是與他所完成的工作相應的建築(造)工人。不過,建造,不會僅憑它樹立於大地上的成品穩當堅固,就是「建築」;讓一座教堂得以建立,或者讓它有辦法輕鬆容納為了執行某些教會職務所必要的人員,所憑藉的也不是「建築」;讓車箱寬敞舒適、船隻行走迅捷的,也不是。當然,我的意思並非是說,「建築」這個詞不常,或者甚至不可以有上面那種意義,就像英文裡的確很慣用「船的建築 」這種說法。只是,在那樣的用法之下,「建築」就不是一門精妙的藝術了;總之,術語定義若是模糊與不確定,讓屬於建造工程的全部原理原則都可能伸入嚴格意義之建築領域內,從而不時產生,同時也會持續產生種種混淆──這種風險還是別去招攬的好。
職此之故,讓我們馬上給這種藝術下一個確定而不變的定義,它將廣義的建築一詞所必然指涉,並且一般而言皆會指涉的意義吸納進去,當作是運用這個定義的基本條件,在這基礎形式之上,再去強調那些令人肅然起敬,或者是帶來美感,然而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必要性的性質 。據此,容我這樣說:那些定出軍堤應該建至多高,或者稜堡應該座落何處的法則,不會有人稱其為「建築」的法則。但是,如果在那座稜堡的石頭飾面添上某個非必要的外觀特徵,例如立體繩紋裝飾──那,就是「建築」了。若將堞口或槍眼城垛這些東西稱為是「建築上的」特徵,然而一旦它們的構成元件,不過是由居高臨下的主體建物撐起面臨前線的走廊,然後用間隔出現的孔隙向下發動攻擊的話,依據與上述類似的道理,這種稱呼方式就不甚合理。不過,如果在這些高聳的主體建物根處,刻出層層環繞的紋路,而那當然是沒有用處的;或者如果把垛的頂面做成拱形,甚至是三葉形,當然那也是沒有用處的──但那,就是「建築」。這分野或許不總是能夠輕易地清楚得見。因為,很少有建物不擁有些許「建築」的因子,讓它們可以聲稱或者假扮自己就是「建築」;反之,任何「建築」都不免需要以建物為基礎,而所有好「建築」所奠基於上者,也全都是好的建物;不過,即便如此,保持觀念上的清楚區別,並且透澈地理解到:「建築」只關注建物在日常用途之外,更高、更超越的那些特徵──這一點,則是非常必要,也容易至極的事。是的,我是說「日常」用途;因為,若是一棟為了榮耀上帝,或者緬懷偉人而設立的建物,它這用途,無疑可與自身那些具有建築意義的裝飾工程相容;但這用途卻必然不會使它非去滿足某些實際需求不可,以致於限制了它在整體或是細節上的設計。
Ⅱ
承上所述,嚴格意義的建築,依其本然之性質,可以分編到下列五種項目之下:
信仰:包括所有為了服侍、禮拜或榮耀上帝而興建的建物。
記念:無論是墓地、墓碑,或是專門緬懷某人的碑、塔、樓、館等,皆包括在內。
公共:目的在供眾人共同事務之用,或者順應公眾之意願,而由國家、民族、社群、或團體,所興築的任何建物。
軍事:所有私有或公有的防禦建築。
家用:任何階層及任何種類的住所。
此處,我將要努力發展建立的原則,它們雖然如同我曾經提到的,必須全部都能夠適用於任何階段、任何風格的建築上;不過,其中有些,尤其是那些較具有啟發性,而非指導性的原則,它們必然與上述建築中的某一類,有著相對來說更完整的參照價值與關連性;在它們之中,我會將其影響雖然及於所有建築,不過終究與信仰性及記念性建築特別有關的一種精神擺在最先。那是種想替這兩類建築獻出珍貴事物的精神。獻出,單純只是因為那些是珍貴的事物;不是作為那座建物不可或缺之物件,而是身為我們自己渴望與喜愛之物,而被當作一份奉獻、一份呈給、一份祭品。依我看來,時至當下,在那些推動信仰性建物的興建與發展的人們身上,似乎多數都全然欠缺這種精神;非但如此,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甚至把它當作是一項危險的,或者說不定是可恥的原則。有各式各樣的反對意見都可以用來充作大聲疾呼、反對這種精神的論調,礙於篇幅,我不擬對其全部進行辯駁;它們為數太多,而且多半似是而非。不過,或許我可以懇請讀者撥冗一閱,容我書下一些簡單明暸的理由,說明為什麼我會認為自己這樣的看法──若要完成任何一項偉大的建築作品(而這正是我們目前關注的主題),上述精神無庸置疑是不可或缺的──乃是既可令上帝欣然而悅,亦可讓人類深感光榮,從而會是種持平而正確的真知灼見。
Ⅲ
那麼,首先便是界定清楚,這座犧牲獻祭之「燈」(也就是「精神」)所指為何。我曾經提到,我們之所以有股衝動想獻出珍貴的事物,僅僅是因為它們珍貴,而不是因為它們的功用,也不是因為它們對作品來說不可或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呢?舉例來說,當有兩片大理石,同樣漂亮、同樣合用,也同樣經久耐磨,那麼就會想要挑選價格比較高的那片,只是因為它貴;有兩種裝飾作法,效果同樣顯著,會想要挑選比較精緻的那種,只是因為它費心;也就是說,這是追求去在同樣的範疇裡,呈現出一個花費了更高代價,付費了更多心思的成果。它因此是最不符合理性的表現,也因此是最熱情無悔的表現;而或許,要界定這種精神,最清楚的是方式是從反面定義:它,與盛行於現代的觀感──渴望用最少的成本,產出最多的結果──正好相反。
接著,論及奉獻精神時,有兩種壁壘分明的形式:其一是,這種自我否定的行動,單純就是為了達到自律;是為了自律這個願望,而做出放棄自己深愛或者渴望之事物的行為;也就是說,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其他直接的要求或目的,是這種行為要去滿足的。其二則是,渴望用犧牲的代價之重,來榮耀「他者」,或者令其喜悅。現實中,屬於第一種類型者,性質上可能有屬於私人的,也可能有公共的行為;不過,最常見到的是──或許它也最應當是──私人性質的。另一方面,屬於第二種類型者,則通常是公共的,而當它是公共性質時,所帶來的益處也最大。話既如此,若我想做的主張是這樣:不為其他目的,就只為了它本身,而去實行自我否定的行為,自有其合算之處──我不得不說,這樣的主張乍看之下是無法得到認同的;畢竟,對於那許許多多其他種類的目的而言,自我否定的行為也都是如同吃飯喝水般地必要,其必要之程度甚至比親身實行的我們所知道的還深。不過我相信,之所以會如此,只是因為我們並沒有打心底承認這種行為的地位,或者對其思考得並不週全,才會不認為它本身就是件好事──也可以說,當它變成一道非關其他目的的道德誡命時,我們便太容易違背它發出的要求;也太容易去計算(這時立場多少會偏向自己)付予他人的好處,與己身受到的虧損,兩者是否相稱、是否合理;而不會認為這是於個人有益之事,而歡喜地接受這次犧牲奉獻的機會。事情就算如此,此處也沒有必要對其多所強調;畢竟,對那些選擇那麼做的人來說,永遠都有比起藝術更為崇高、也更加有用的途徑,來做到自我犧牲。
至於,說到第二種,也就是與藝術特別相關的形式,犧牲精神的正當性更是備受質疑;關於這一點,則以我們如何回答另一個更為概括的問題為依歸:上帝是否確實會因為任何呈獻給祂的珍貴物品:有形的、物質的事物;又是否真的會因為人類的熱忱與智慧──當它們不論投注於何種領域,總之對人群並沒有直接的助益時──而得到彰顯?
請讀者留心,因為此處問的,並不是建物之美觀與壯麗可不可以滿足於任何倫理目的;此刻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任何一種由勞動穫得的「果實」;而就只是單純在討論材質、勞力,和耗時,這些東西本身所呈現出來的奢華大氣。我們要問:這些東西本身,不看它們所獲致的成果,是不是上帝會接受的獻禮?祂認不認為這是在向祂表示敬意、是在彰顯祂的榮耀?就這個問題,一旦我們所參考者,是單獨源自自我感受、良心,或者源自理性所為的判斷,答案就將會自我矛盾,或者有所遺漏;這個問題,唯有在我們回答完另一個非常迥異的問題之後,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那問題便是:聖經是否可分新約舊約?又或者,舊約裡與新約裡顯示的上帝是否有所不同?Ⅳ
且說,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裡,為了某些具體的目的,人們會依上帝之旨,定下特定的儀禮,而這些儀禮,到了別的時期,可能會被同一個神聖權威所廢除;但是,雖然如此,藉由過去或現在的任何儀禮而得到描述或者示現的神性,卻不可能會有哪一個部分,會因某項儀禮的廢除而受到改變,或者也不可能將其理解成已有所改變──這一點,是最確然無疑的事實。上帝乃唯一與不變,其喜悅與憎厭的永遠都是同樣的事物──就算祂的喜好中有的部分,在某個時代或許會比別的時代表現得更明顯;就算考察祂的喜好的方式,得經祂寬大地依照人類所處之境況而有所調整。從而,以此為例:為了真正理解誰可得救,得救與否,最初必須以血腥獻祭這種模式加以預先顯明。然而,如今,已不似摩西的時代,這種犧牲再也不是上帝的喜好。犧牲,作為贖罪之補償,上帝從來就只接受過一種,而這唯一的一種,就叫做「與時俱進」,這點是我們絲毫都不可加以懷疑的;當祂給出神聖的命令,指定標示著某個時代的典型犧牲時,同時也就表明了所有其他的獻祭皆無價值。上帝是種靈性的存在,只有在心靈與真理的層面上,才有所謂對祂的崇拜可言;在過去的日常慣例裡,除了典型的、有形的、物質上的服侍或獻禮以外別無其他要求,是如此;而現在,祂所要求者唯有心之敬獻,亦是如此。
因此,這會是一個最穩當,也最確實的原則:某個時代的某種儀式,由它的執行方式所追溯、勾勒出的具體作法,若依前人所言,或者依我們自己合理的推斷,認為那是能夠在那個時代取悅上帝的作法,那麼,不論是在哪個時代,同樣的作法,在歸結到類似的執行方式,以完成任何敬神的儀式或服務時,一樣可以取悅上帝;除非,日後我們發現到:為了某些具體的目的,如今上帝有意廢除這些作法。而且,假如有人可以證明,對於儀式之於人類的用途與意義而言,這類作法在促成其完善方面並非必要,它們之所以存在於儀式中,只不過是因為它們本身乃上帝所喜,這麼一來更是大大替上面的說理增添許多說服力。Ⅴ
於是,一個人為了在祭典上以自己之名義獻出某類牲禮:因為那是《利未記》所規定之牲禮類型的一種。但他需要散盡自己所有錢財才辦得到,這對《利未記》那個年代祭典的完善,或者對祭典解釋神之旨意的效果而言是否必要呢?完全不是。牲禮所先行示現的犧牲,在當年也應該是種作為給上帝的免費禮物;取得該類牲禮的難度,或者是它的代價,只會模糊這個牲禮類型的分寸尺度,也使得上帝最終贈予全人類的禮物失去原本深邃的意義。儘管如此,「代價不菲」在當時就已是獻祭之所以能為上帝所接受的要件,沒有例外。「同樣地,若是我不需付出任何代價之物,我也不會獻給吾主,我的上帝。 」也因此,「代價不菲」必然是古往今來,人類獻禮可以為上帝接受的條件;原因是這個性質曾經取悅過上帝,於是它必定一直都能夠取悅上帝,除非在那之後曾經由祂直接禁止,而這是從來不曾發生過的事。
其次,牲禮必須是牲口裡品級最好者,這一點對於利未禮儀本身的完善性而言是必要的嗎?毫無疑問地,就當時而言,獻祭本身越完美無瑕,它在基督徒的心目中越有意義;但是對基督徒越有意義,就會讓這一點成為準確無誤地上帝實際上所要求的嗎?一點也不。上帝在那時候之所以要求最好的,很明顯地,就跟俗世的統治者也會要求最好的,是基於相同的理由:以此作為敬意的證明。「將它獻給你的統治者。 」至於價值較低的獻禮當時之所以為上帝所拒絕,原因並不在於它既無法反應基督的形象,又不能滿足犧牲的目的。而是在於:它傳達了一種情緒或想法:不願意將主賜給我們擁有的東西中,最好的部分獻祭給祂;此外也在於:那會是對人們眼中的上帝施加無禮的侮辱。依據上面所述,可以確定無疑的是:就那些我們現在覺得有理由呈獻給上帝的獻禮而言(此處,我的意思並非指出這些獻禮可以是什麼),它們必須是同類事物中最棒的這一點,在我們這個時代,就跟它在過往一樣,也會是這些獻禮可以為上帝所接受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