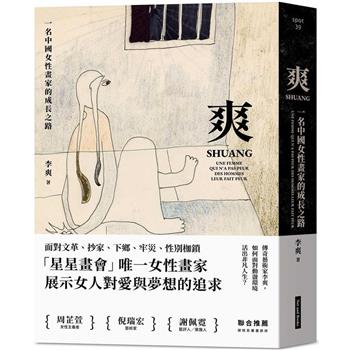刑事犯
坐在一輛上海牌汽車上,車開出了炮局的高牆、電網和崗樓,在這兒我整整住了三個月。在這兒我品嘗到了痛苦盡頭的──蟬蛻超脫。我依然無法明白為什麼闖過痛苦,後面會有快樂?但炮局是我要紀念開悟的地方。
小辮子女員警坐我右邊,長方臉左邊,白眼鏡在司機旁邊。
我深深呼吸著。
你哪個季節被關起來,哪個季節就被鎖在記憶中,空氣特冷,已不習慣。即便才三個月,已如隔世。北京熟悉的街道從車窗外緩緩移動,商店、飯鋪、自行車、居民樓窗戶上晾著的衣服、紅的藍的公共汽車、小孩、老頭、老太太、紅燈停綠燈走,我的北京,今天看得見摸不著了。
夕陽西下,地平線越來越暗,一些沒砍掉的玉米稈兒豎在田裡。我迷戀美麗的黃昏,插隊時常常在此刻追畫夕陽。前面又出現了高牆,電網,崗樓,我再也忍不住了,不能回去⋯⋯長方臉兒用胳膊頂了我一下,歪過頭兒來說:「李爽,哭什麼呀!到教養所表現好還能提早出來嘛,就看你的了。」
生活中有些地方真像陷阱,明明知道,還是會跳下去。當你感到受害而自憐的時候,你發現原來又在陷阱裡了。有的人乾脆萎謝在裡面,他們對自己說:「人太壞,認輸吧。」於是他們放棄挑起尊重生命的擔子,卸下一切責任,去做怨天尤人的人,還告訴別人:「認命吧,省得爬上來還會被推下去。」有的人繼續攀登──人所有的努力都是面對自己內心的一次又一次挑戰。
良鄉勞改營俗稱「二六八」。
二層樓的長條形房子,每間號兒裡是大通鋪,少說十五個人一間,中間有一米寬窄的過道,每個人鋪底下有小板凳,一隻臉盆,一個行李袋。
進炮局的時候我的頭髮就不短了,三個月已是大辮子。我一進去,姑娘們就圍著我,問我叫什麼?判了幾年?唧唧喳喳。
女隊長姓呂,她一進來,鴉雀無聲。她問:「有剪子嗎?」
「有,隊長!」值班的犯人看守立刻應聲。
「拿來。」
「隊長,我們的剪子都是做針線活兒用的,太小。」
「那也拿來!」
「是!」
隊長吃力地試著用小剪子剪我粗黑的頭髮,沒剪幾根兒就累了,吩咐一個叫翔子的犯人看守:「去隊部要把大剪刀。」
這裡是犯人管犯人,翔子把我的辮子給剪了。我要求:「辮子請還給我吧。」
呂隊長問:「幹嘛?」
「留個紀念。」
「好好想想接受改造思想的事,比留戀辮子重要。」
我從辮子上剪下一小綢兒頭髮。
我依然沒有任何外面的消息,老白怎麼樣了?「星星」的朋友是否有被抓的?我們家人承受得了嗎?
良鄉勞教所的勞改工廠專門生產軍用大炮和坦克上的防雨罩。禁止我外出去工廠幹活,取消了我的「探親日」。
每月一次,家屬坐專車來良鄉勞教所給犯人送東西和食品。探親日我聽到鈴鐺響,女犯們興高彩烈拿著小板凳跑到通道門口等著叫她們。
我一個人坐在十幾張空蕩蕩的鋪間,號脈,聽自己的心跳聲⋯⋯
沒有人明白為什麼我不能接受「探親」,而我的解釋大概是封鎖消息,但如果需要「封鎖」就說明有「進攻」。
同屋有幾個闖過江湖,性格兇猛的姑娘,第一個是小胖子,年紀大概只有二十的樣子,第二個瘦高條兒,臉孔秀氣,第三個是頭兒,叫榮榮,三個人在廁所把新來的我逮住。
榮榮問:「哎,新來的!我猜你丫是個政治犯?」我不理會她。秀氣的瘦高條兒仿佛喜歡和酷主兒打交道地說:「你殺過人嗎?」我還不吭聲兒,榮榮覺得她們的榮譽受到了威脅,道:「你丫是啞巴?騷屄還他媽挺清高!」
「你嘴乾淨點兒行不行!」我忍不住了。
秀氣的瘦高條說:「嘴乾淨管屁事兒,屄不乾淨怎麼辦,我看她準是洋妓!」我有些擔心了,這種流氓叉架絕不是我的強項,看氣勢她們不準備輕易放過我這個新來的。廁所有五個茅坑兒,茅坑之間沒有隔段,對面一槽長長的水池子有五個龍頭,這兒是大家祕密約會的地方,筒道「大號」裡是沒有任何隱私的,睡覺都開著燈,門上有大玻璃。
我在小便,旁邊有個女孩也在撒尿,她膽小地看了我一眼。江湖姑娘威脅這個女孩:「哎!你丫別『扎針兒』!這邊兒治不了你,外邊兒花了你!」女孩趕緊逃跑了。我的確慌張,隨後提起褲子要下臺階。高個姑娘拱了我一下,小胖子飛速下了一個絆兒。她們動作麻利,我摔在骯髒的茅坑邊,不得不用手扶著沾滿屎尿的茅坑沿爬起來。「這回誰比誰髒?你還嘴硬嗎?把你的皮帶給我!」她倆按住我,姑娘榮榮抽出我的皮帶。那是一條法國的真羊皮細皮帶,皮帶頭上有精緻的花紋。「哇!還是金色的呢!」小胖子感歎。
「又是你們幾個,幹什麼呢!」看守隊長突然站門口,盯著我那副骯髒的狼狽樣兒,問我:「誰把你推茅坑裡的,你指給我。」我是懂得玩鬧規矩的人,看著員警撒謊道:「我自己不小心摔的。」隊長揮手讓幾個姑娘走。接著,我堅持道:「我自己摔的!」
「李爽隨你的便,願意扛你就扛,倒楣的是你!」
第二天,我在洗碗,又在廁所見到了她們,榮榮湊過來,又拱了我一下,我挪個地方,她掀起襯衣露出繫在自己腰上的法國皮帶,示意胖姑娘去望風兒,說:「唉,謝謝啦!你原來是哪兒的?還挺仗義。現在,在『二六八』別管有什麼事儘管哼一聲,你的事我包了!」
「我的事兒我自己包。」
「我早看出你有來頭兒,別瞧你『蔫不出溜』的!」
另一個秀氣的女孩說:「你有什麼事兒需要幫忙?」
「暫時沒有。」
「不讓你探親?你肯定需要捎信。」
這話使我靈機一動,說:「有!」
「啊!這還像個朋友的樣兒,說吧!」
我把那绺兒頭髮和信縫在手套裡,榮榮帶給了她哥哥。過了一段時間,在廁所裡,榮榮有消息給我:「你姊到我家把手套取走啦,還送了好多禮呢!」幾經周折,幾個月後,我那绺兒頭髮到了法國,出現在老白的書桌前的一個小鏡框兒裡。榮榮用欽佩的樣子看著我,貼在我耳朵上神祕地說:「我哥說你不是一般的人兒,電視上都批判你了。」
「啊!不可能。」我狐疑地說。
「我肏你大爺,我告訴你的事兒能是假的嗎?」榮榮顯出很重視自己名譽的樣子。
我反擊:「嘿,我沒有大爺給你肏!」
「呵呵,別生我粗人的氣。」坦誠從她心中流露,這是我第一次得到外面的消息!
每天早上洗漱完畢,整理一下內務,如果工廠沒活兒,大家要整齊地坐在鋪腳前,學習政治材料,反省錯誤。天熱可以有一個小時的午休。
有一天午休,犯人看守大翔子值班,在走廊上看報紙,看完之後,她悄悄進屋把報紙遞過來,小聲兒問我:「嘿,你不是也叫李爽嗎?看看這報上說的是不是你啊?」接過《北京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登著一篇新華社記者述評,文章題為是〈小題大做——評白天祥等人在所謂「李爽事件」上的喧嚷〉。
「是你不是?說呀!」
「是又怎麼著?」我白了她一眼。
「真的啊!」她上下打量我,又側過身兒從窗玻璃的影子裡打量自己。
「哎,你啥本事啊,連大使都為你『小題大做』。」
「不是大使,一個普通外交官。」
「嘿!你還得了便宜賣上乖了,人家可是法國的外交官,你看看那邊的電視、電臺、報紙都為你大作文章!人家還要和你結婚⋯⋯」
「你是值班呢?還是演講呢!」員警聽見大翔子的大嗓門。
「隊長,我正值班呐,是她來跟我要報紙。」我對滿嘴說慌的人,一點輒沒有。隊長吩咐:「大翔子,你趕緊趁午休,幫李爽把行李搬到小號去。」
「是!隊長。」
從《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以及電視臺點名批判我這天起,我一直被關在小號裡,雖然比別人多出一張桌子,但失去的卻是全部自由。
我給隊長寫信,要求像其他人一樣有工作的機會,我需要走路,呼吸空氣,與人交流。
強烈的好奇心,使女人們冒著罰站的危險,溜出來往我住的小窗探頭,品頭論足,我完全像一隻猴,卻不如猴兒,猴兒好歹不明白人話。
「我肏!不就一個洋妓嗎,國家幹嘛動那麼大干戈?」
有的說:「她要只是賣屄的,老外不會死乞百賴非要惱火不可。」
「准跟政治有關係唄。」
「李爽長得也不怎麼好看呀?」
「還行,一般般。」
「五官端正吧。」
「哎唷!還不如我呢!」
「是,也不如我。」
「不難看也不好看,不明白老外看上她哪兒了。」
「老外傻屄!」
「誰傻?有本事你給我弄一個外交官來看看!」
「騷屄你丫吃醋啦?」瘦高條兒秀氣的臉孔出現在我的視窗,衝我一笑,道:「我們給你解圍來了。」她站我門口,直到上班鈴響。
可苦了隊長們的嗓子:「看什麼!有什麼好看的!再看我罰你站!」
通過《北京日報》帶來的資訊,證明榮榮她哥的話是真實的!我暗自高興──老白沒有拋棄我,「星星」、「民刊」的哥們一定為了營救我而盡了不少力,不像提審說的「沒戲」、「白坐」、「往外擇」。於是夜裡我把能想起來的哥們、朋友的名字念叨了一大通兒,叨叨:「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老天爺!」
我一去上廁所,烏泱就被跟上,榮榮她們幾個姑娘馬上當起我的保鏢來。小胖子背靠門上,一隻腳蹬門框上,凡是來看李爽的都不讓進,真有屎有尿,蹲那兒裝假拉撒不出來,可就走不了嘍,非放下幾毛錢不行。一個女孩發誓憋不住尿了,一進來,她看著我說:「你還認識我嗎?」
我看著她乾淨漂亮的臉兒,的確似曾相識:「見過,在哪兒想不起來了。」
秀氣瘦高條兒說:「你丫套什麼雞巴近乎。」
榮榮想在我面前整頓一下她手下的形像,說:「就你丫嘴不乾淨,你丫有真雞巴就先掏亮出來看看,再罵別人,在『國際案件』面前你得刷刷牙再說話。」
女孩在榮榮教訓秀氣瘦高條兒時趁機對我說:「在圓明園詩歌朗誦會上我們見過。」
「是嗎?很可能!」
「我叫小紅,是軍事博物館的。」
我問:「判了幾年?」
「四年。」
「因為什麼?」
小紅猶豫了一下:「和你不一樣⋯⋯」她顯然不想多談,一定有未癒傷疤。而我又多了一個認識人,很欣慰。小紅體魄健壯,婉轉流盼的眼神,高雅的鼻子,唇櫻齒白,寬厚的背影有點小夥子的勁頭兒。
後來榮榮、小胖子、秀氣瘦高條兒,因為我在外邊認識小紅,大大方方地向她問好,他們像男人結拜兄弟般拍著肩豪放大笑。
晚上,犯人看守來敲我的小窗戶:「李爽,隊長叫。」我去了,隊長的臉很嚴肅:「報紙看了嗎?」
「看了。」
「瞧你幹的喪失國格兒和人格兒的事兒!」
我壓低聲音道:「我代表不了國家,有什麼國格兒可言?」
「你給我閉嘴!明天所長找你談話!」
「呂隊長我不想住小號,能不能讓我回大號,並且下工廠勞動?」
「你的事鬧到國際上去了,這是所裡開會討論的結果,對你也是個保護。」
「我為什麼沒有探親日?」
「有你問的分嗎!我不是你的老師,是你的『管教』,你是一個犯人,來這兒受懲罰和改造思想!」
「報上說我的事不是判刑,所以我不是犯人是失足青年,連判大刑的都可以接見親人。」
「你可以給公安二處你的提審寫信,是他們決定你是否可以探親。」
我寫了一封又一封要求享有接見權的信,所長終於傳我談話。我拿著小板凳,穿過中庭,一進隊長辦公室一眼認出提審長方臉和小辮子,他們站了起來,很快又坐回去說:「李爽,我們聽說你表現不錯。」
我學著榮榮的調子懶洋洋地:「是嗎,怎麼不錯法兒啊?」。
「你寫的信,我們看了。」
「我為什麼不可以接見!」
「我們來就是要和你討論這事兒。」
「接見需要討論嗎?」
「李爽,你是不是聽說過表現好的犯人,可以提前釋放的?」
「嗯。」
「現在你已經學習了好幾個月黨的從寬政策,坦白屬於是犯罪後對自己罪行認識過程的關鍵,如果你準備好了,寫一封與那個法國人的斷交信,別說探親日,提前釋放都有可能。還是那句話,你不是喜歡繪畫嗎,我們可以説明你聯繫美院⋯⋯」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美院等「好處」。我帶著偏見去聽這些,想起姥姥講的故事:驢看見人拿著胡蘿蔔在眼前晃,大叫:「恩啊,恩啊!」之後人把胡蘿蔔吃了。
「我沒準備寫這封信。」我用一種識破了詭計口氣說完,並且等著他們爆發。
「好吧,現在,你可以接見了。」
我完全不相信我的耳朵!
「什麼?」
「寫封讓你家人帶著東西來看你的信。」
「真的啊?」
「真的!」
「我能畫畫嗎?特小油畫棒的?」
「特小?」長方臉提審看看所長,點點頭兒,大家通過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們也報以回笑。
「二處的人和所長來傳迅李爽啦!李爽可以接見了!」消息傳開。
人是多麼頑強的物種,憑著一股精神,憑著一個期望,憑著一個信念。人是多麼有彈性,為了活下去、活得好一些,像彈簧一樣適應著環境。每個人都是一本了不起的小說,他們講完自己的故事常常說同一句話:「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是怎麼過來的。」
與小紅談話的機會只限於早晚洗漱,午飯,晚飯,星期日大家坐在中廳看電視的時候。我進來時小紅已經待了六個月,我眼看著她的天真與淑雅一點點被蠶食,走路的架勢都流裡流氣的,滿口髒話。
一天她道來一個故事:「我有一個姊們兒叫齊京晶,是我們家樓下的鄰居,她爸下放『五七幹校』以後,她媽老跑外邊跟人搞去,齊京晶沒人照管,有時沒飯吃就來我家吃一兩頓。後來她認識了幾個外國人,我那天⋯⋯真他媽傻屄!」小紅好像顯然需要新鮮空氣,大口呼吸,她並不是為了講得更加繪聲繪色,是冤屈恥辱不堪回首。
「你別講了。」我要求。
好一會兒,她繼續:「我有一個男朋友瑞金,寫詩的,我特喜歡他。我想買高跟鞋臭美。一天京晶說帶我去老外家玩兒,還說你不是想要一雙高跟鞋嗎,我托老外給你帶了,你去試試。晚上我們在軍博附近的黑地裡,來了一輛日本吉普,我們鑽進後備箱,是什麼使館我也不清楚。進屋兒一看仨老黑,上來就把我往另一間屋裡推。」
「發現上當了我求京晶:『我還是處女呢,我要留給瑞金。』京晶說:『裝什麼嫩呀,給誰不是給。』我急了:『給誰也不給老黑!』其中一個會說中文的老黑也急了說:『我們都付過好多錢了!』愣把我拖了進去⋯⋯」
小紅把頭扭開,我也挪開視線,不忍看那張淒美的臉。
我的耳朵已經難以承受,小紅又是如何承受這個夢魘的,她以自己的美麗和單純擁抱生活,生活把她打蒙了,也毀掉了這個女孩對所有的信任。
小紅看著不潔淨的天花板道:「半夜三更老黑把我們送出來,他們的車剛走,我們就被等在路邊兒的警車抓走了。提審了一個月,京晶被放了,判我四年,當時我喊,『判我死刑啊,死了到輕省了!』」小紅幾個月前還是盈盈秋水的美目,如今閃著對人性不共戴天之仇。
小紅準備把自己處女之身獻給瑞金──她的最愛,為了取悅最愛想要一雙高跟鞋,被最親信的女朋友欺騙,天真和自尊受到了最殘酷的戲弄。
坐在一輛上海牌汽車上,車開出了炮局的高牆、電網和崗樓,在這兒我整整住了三個月。在這兒我品嘗到了痛苦盡頭的──蟬蛻超脫。我依然無法明白為什麼闖過痛苦,後面會有快樂?但炮局是我要紀念開悟的地方。
小辮子女員警坐我右邊,長方臉左邊,白眼鏡在司機旁邊。
我深深呼吸著。
你哪個季節被關起來,哪個季節就被鎖在記憶中,空氣特冷,已不習慣。即便才三個月,已如隔世。北京熟悉的街道從車窗外緩緩移動,商店、飯鋪、自行車、居民樓窗戶上晾著的衣服、紅的藍的公共汽車、小孩、老頭、老太太、紅燈停綠燈走,我的北京,今天看得見摸不著了。
夕陽西下,地平線越來越暗,一些沒砍掉的玉米稈兒豎在田裡。我迷戀美麗的黃昏,插隊時常常在此刻追畫夕陽。前面又出現了高牆,電網,崗樓,我再也忍不住了,不能回去⋯⋯長方臉兒用胳膊頂了我一下,歪過頭兒來說:「李爽,哭什麼呀!到教養所表現好還能提早出來嘛,就看你的了。」
生活中有些地方真像陷阱,明明知道,還是會跳下去。當你感到受害而自憐的時候,你發現原來又在陷阱裡了。有的人乾脆萎謝在裡面,他們對自己說:「人太壞,認輸吧。」於是他們放棄挑起尊重生命的擔子,卸下一切責任,去做怨天尤人的人,還告訴別人:「認命吧,省得爬上來還會被推下去。」有的人繼續攀登──人所有的努力都是面對自己內心的一次又一次挑戰。
良鄉勞改營俗稱「二六八」。
二層樓的長條形房子,每間號兒裡是大通鋪,少說十五個人一間,中間有一米寬窄的過道,每個人鋪底下有小板凳,一隻臉盆,一個行李袋。
進炮局的時候我的頭髮就不短了,三個月已是大辮子。我一進去,姑娘們就圍著我,問我叫什麼?判了幾年?唧唧喳喳。
女隊長姓呂,她一進來,鴉雀無聲。她問:「有剪子嗎?」
「有,隊長!」值班的犯人看守立刻應聲。
「拿來。」
「隊長,我們的剪子都是做針線活兒用的,太小。」
「那也拿來!」
「是!」
隊長吃力地試著用小剪子剪我粗黑的頭髮,沒剪幾根兒就累了,吩咐一個叫翔子的犯人看守:「去隊部要把大剪刀。」
這裡是犯人管犯人,翔子把我的辮子給剪了。我要求:「辮子請還給我吧。」
呂隊長問:「幹嘛?」
「留個紀念。」
「好好想想接受改造思想的事,比留戀辮子重要。」
我從辮子上剪下一小綢兒頭髮。
我依然沒有任何外面的消息,老白怎麼樣了?「星星」的朋友是否有被抓的?我們家人承受得了嗎?
良鄉勞教所的勞改工廠專門生產軍用大炮和坦克上的防雨罩。禁止我外出去工廠幹活,取消了我的「探親日」。
每月一次,家屬坐專車來良鄉勞教所給犯人送東西和食品。探親日我聽到鈴鐺響,女犯們興高彩烈拿著小板凳跑到通道門口等著叫她們。
我一個人坐在十幾張空蕩蕩的鋪間,號脈,聽自己的心跳聲⋯⋯
沒有人明白為什麼我不能接受「探親」,而我的解釋大概是封鎖消息,但如果需要「封鎖」就說明有「進攻」。
同屋有幾個闖過江湖,性格兇猛的姑娘,第一個是小胖子,年紀大概只有二十的樣子,第二個瘦高條兒,臉孔秀氣,第三個是頭兒,叫榮榮,三個人在廁所把新來的我逮住。
榮榮問:「哎,新來的!我猜你丫是個政治犯?」我不理會她。秀氣的瘦高條兒仿佛喜歡和酷主兒打交道地說:「你殺過人嗎?」我還不吭聲兒,榮榮覺得她們的榮譽受到了威脅,道:「你丫是啞巴?騷屄還他媽挺清高!」
「你嘴乾淨點兒行不行!」我忍不住了。
秀氣的瘦高條說:「嘴乾淨管屁事兒,屄不乾淨怎麼辦,我看她準是洋妓!」我有些擔心了,這種流氓叉架絕不是我的強項,看氣勢她們不準備輕易放過我這個新來的。廁所有五個茅坑兒,茅坑之間沒有隔段,對面一槽長長的水池子有五個龍頭,這兒是大家祕密約會的地方,筒道「大號」裡是沒有任何隱私的,睡覺都開著燈,門上有大玻璃。
我在小便,旁邊有個女孩也在撒尿,她膽小地看了我一眼。江湖姑娘威脅這個女孩:「哎!你丫別『扎針兒』!這邊兒治不了你,外邊兒花了你!」女孩趕緊逃跑了。我的確慌張,隨後提起褲子要下臺階。高個姑娘拱了我一下,小胖子飛速下了一個絆兒。她們動作麻利,我摔在骯髒的茅坑邊,不得不用手扶著沾滿屎尿的茅坑沿爬起來。「這回誰比誰髒?你還嘴硬嗎?把你的皮帶給我!」她倆按住我,姑娘榮榮抽出我的皮帶。那是一條法國的真羊皮細皮帶,皮帶頭上有精緻的花紋。「哇!還是金色的呢!」小胖子感歎。
「又是你們幾個,幹什麼呢!」看守隊長突然站門口,盯著我那副骯髒的狼狽樣兒,問我:「誰把你推茅坑裡的,你指給我。」我是懂得玩鬧規矩的人,看著員警撒謊道:「我自己不小心摔的。」隊長揮手讓幾個姑娘走。接著,我堅持道:「我自己摔的!」
「李爽隨你的便,願意扛你就扛,倒楣的是你!」
第二天,我在洗碗,又在廁所見到了她們,榮榮湊過來,又拱了我一下,我挪個地方,她掀起襯衣露出繫在自己腰上的法國皮帶,示意胖姑娘去望風兒,說:「唉,謝謝啦!你原來是哪兒的?還挺仗義。現在,在『二六八』別管有什麼事儘管哼一聲,你的事我包了!」
「我的事兒我自己包。」
「我早看出你有來頭兒,別瞧你『蔫不出溜』的!」
另一個秀氣的女孩說:「你有什麼事兒需要幫忙?」
「暫時沒有。」
「不讓你探親?你肯定需要捎信。」
這話使我靈機一動,說:「有!」
「啊!這還像個朋友的樣兒,說吧!」
我把那绺兒頭髮和信縫在手套裡,榮榮帶給了她哥哥。過了一段時間,在廁所裡,榮榮有消息給我:「你姊到我家把手套取走啦,還送了好多禮呢!」幾經周折,幾個月後,我那绺兒頭髮到了法國,出現在老白的書桌前的一個小鏡框兒裡。榮榮用欽佩的樣子看著我,貼在我耳朵上神祕地說:「我哥說你不是一般的人兒,電視上都批判你了。」
「啊!不可能。」我狐疑地說。
「我肏你大爺,我告訴你的事兒能是假的嗎?」榮榮顯出很重視自己名譽的樣子。
我反擊:「嘿,我沒有大爺給你肏!」
「呵呵,別生我粗人的氣。」坦誠從她心中流露,這是我第一次得到外面的消息!
每天早上洗漱完畢,整理一下內務,如果工廠沒活兒,大家要整齊地坐在鋪腳前,學習政治材料,反省錯誤。天熱可以有一個小時的午休。
有一天午休,犯人看守大翔子值班,在走廊上看報紙,看完之後,她悄悄進屋把報紙遞過來,小聲兒問我:「嘿,你不是也叫李爽嗎?看看這報上說的是不是你啊?」接過《北京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登著一篇新華社記者述評,文章題為是〈小題大做——評白天祥等人在所謂「李爽事件」上的喧嚷〉。
「是你不是?說呀!」
「是又怎麼著?」我白了她一眼。
「真的啊!」她上下打量我,又側過身兒從窗玻璃的影子裡打量自己。
「哎,你啥本事啊,連大使都為你『小題大做』。」
「不是大使,一個普通外交官。」
「嘿!你還得了便宜賣上乖了,人家可是法國的外交官,你看看那邊的電視、電臺、報紙都為你大作文章!人家還要和你結婚⋯⋯」
「你是值班呢?還是演講呢!」員警聽見大翔子的大嗓門。
「隊長,我正值班呐,是她來跟我要報紙。」我對滿嘴說慌的人,一點輒沒有。隊長吩咐:「大翔子,你趕緊趁午休,幫李爽把行李搬到小號去。」
「是!隊長。」
從《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以及電視臺點名批判我這天起,我一直被關在小號裡,雖然比別人多出一張桌子,但失去的卻是全部自由。
我給隊長寫信,要求像其他人一樣有工作的機會,我需要走路,呼吸空氣,與人交流。
強烈的好奇心,使女人們冒著罰站的危險,溜出來往我住的小窗探頭,品頭論足,我完全像一隻猴,卻不如猴兒,猴兒好歹不明白人話。
「我肏!不就一個洋妓嗎,國家幹嘛動那麼大干戈?」
有的說:「她要只是賣屄的,老外不會死乞百賴非要惱火不可。」
「准跟政治有關係唄。」
「李爽長得也不怎麼好看呀?」
「還行,一般般。」
「五官端正吧。」
「哎唷!還不如我呢!」
「是,也不如我。」
「不難看也不好看,不明白老外看上她哪兒了。」
「老外傻屄!」
「誰傻?有本事你給我弄一個外交官來看看!」
「騷屄你丫吃醋啦?」瘦高條兒秀氣的臉孔出現在我的視窗,衝我一笑,道:「我們給你解圍來了。」她站我門口,直到上班鈴響。
可苦了隊長們的嗓子:「看什麼!有什麼好看的!再看我罰你站!」
通過《北京日報》帶來的資訊,證明榮榮她哥的話是真實的!我暗自高興──老白沒有拋棄我,「星星」、「民刊」的哥們一定為了營救我而盡了不少力,不像提審說的「沒戲」、「白坐」、「往外擇」。於是夜裡我把能想起來的哥們、朋友的名字念叨了一大通兒,叨叨:「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老天爺!」
我一去上廁所,烏泱就被跟上,榮榮她們幾個姑娘馬上當起我的保鏢來。小胖子背靠門上,一隻腳蹬門框上,凡是來看李爽的都不讓進,真有屎有尿,蹲那兒裝假拉撒不出來,可就走不了嘍,非放下幾毛錢不行。一個女孩發誓憋不住尿了,一進來,她看著我說:「你還認識我嗎?」
我看著她乾淨漂亮的臉兒,的確似曾相識:「見過,在哪兒想不起來了。」
秀氣瘦高條兒說:「你丫套什麼雞巴近乎。」
榮榮想在我面前整頓一下她手下的形像,說:「就你丫嘴不乾淨,你丫有真雞巴就先掏亮出來看看,再罵別人,在『國際案件』面前你得刷刷牙再說話。」
女孩在榮榮教訓秀氣瘦高條兒時趁機對我說:「在圓明園詩歌朗誦會上我們見過。」
「是嗎?很可能!」
「我叫小紅,是軍事博物館的。」
我問:「判了幾年?」
「四年。」
「因為什麼?」
小紅猶豫了一下:「和你不一樣⋯⋯」她顯然不想多談,一定有未癒傷疤。而我又多了一個認識人,很欣慰。小紅體魄健壯,婉轉流盼的眼神,高雅的鼻子,唇櫻齒白,寬厚的背影有點小夥子的勁頭兒。
後來榮榮、小胖子、秀氣瘦高條兒,因為我在外邊認識小紅,大大方方地向她問好,他們像男人結拜兄弟般拍著肩豪放大笑。
晚上,犯人看守來敲我的小窗戶:「李爽,隊長叫。」我去了,隊長的臉很嚴肅:「報紙看了嗎?」
「看了。」
「瞧你幹的喪失國格兒和人格兒的事兒!」
我壓低聲音道:「我代表不了國家,有什麼國格兒可言?」
「你給我閉嘴!明天所長找你談話!」
「呂隊長我不想住小號,能不能讓我回大號,並且下工廠勞動?」
「你的事鬧到國際上去了,這是所裡開會討論的結果,對你也是個保護。」
「我為什麼沒有探親日?」
「有你問的分嗎!我不是你的老師,是你的『管教』,你是一個犯人,來這兒受懲罰和改造思想!」
「報上說我的事不是判刑,所以我不是犯人是失足青年,連判大刑的都可以接見親人。」
「你可以給公安二處你的提審寫信,是他們決定你是否可以探親。」
我寫了一封又一封要求享有接見權的信,所長終於傳我談話。我拿著小板凳,穿過中庭,一進隊長辦公室一眼認出提審長方臉和小辮子,他們站了起來,很快又坐回去說:「李爽,我們聽說你表現不錯。」
我學著榮榮的調子懶洋洋地:「是嗎,怎麼不錯法兒啊?」。
「你寫的信,我們看了。」
「我為什麼不可以接見!」
「我們來就是要和你討論這事兒。」
「接見需要討論嗎?」
「李爽,你是不是聽說過表現好的犯人,可以提前釋放的?」
「嗯。」
「現在你已經學習了好幾個月黨的從寬政策,坦白屬於是犯罪後對自己罪行認識過程的關鍵,如果你準備好了,寫一封與那個法國人的斷交信,別說探親日,提前釋放都有可能。還是那句話,你不是喜歡繪畫嗎,我們可以説明你聯繫美院⋯⋯」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美院等「好處」。我帶著偏見去聽這些,想起姥姥講的故事:驢看見人拿著胡蘿蔔在眼前晃,大叫:「恩啊,恩啊!」之後人把胡蘿蔔吃了。
「我沒準備寫這封信。」我用一種識破了詭計口氣說完,並且等著他們爆發。
「好吧,現在,你可以接見了。」
我完全不相信我的耳朵!
「什麼?」
「寫封讓你家人帶著東西來看你的信。」
「真的啊?」
「真的!」
「我能畫畫嗎?特小油畫棒的?」
「特小?」長方臉提審看看所長,點點頭兒,大家通過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們也報以回笑。
「二處的人和所長來傳迅李爽啦!李爽可以接見了!」消息傳開。
人是多麼頑強的物種,憑著一股精神,憑著一個期望,憑著一個信念。人是多麼有彈性,為了活下去、活得好一些,像彈簧一樣適應著環境。每個人都是一本了不起的小說,他們講完自己的故事常常說同一句話:「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是怎麼過來的。」
與小紅談話的機會只限於早晚洗漱,午飯,晚飯,星期日大家坐在中廳看電視的時候。我進來時小紅已經待了六個月,我眼看著她的天真與淑雅一點點被蠶食,走路的架勢都流裡流氣的,滿口髒話。
一天她道來一個故事:「我有一個姊們兒叫齊京晶,是我們家樓下的鄰居,她爸下放『五七幹校』以後,她媽老跑外邊跟人搞去,齊京晶沒人照管,有時沒飯吃就來我家吃一兩頓。後來她認識了幾個外國人,我那天⋯⋯真他媽傻屄!」小紅好像顯然需要新鮮空氣,大口呼吸,她並不是為了講得更加繪聲繪色,是冤屈恥辱不堪回首。
「你別講了。」我要求。
好一會兒,她繼續:「我有一個男朋友瑞金,寫詩的,我特喜歡他。我想買高跟鞋臭美。一天京晶說帶我去老外家玩兒,還說你不是想要一雙高跟鞋嗎,我托老外給你帶了,你去試試。晚上我們在軍博附近的黑地裡,來了一輛日本吉普,我們鑽進後備箱,是什麼使館我也不清楚。進屋兒一看仨老黑,上來就把我往另一間屋裡推。」
「發現上當了我求京晶:『我還是處女呢,我要留給瑞金。』京晶說:『裝什麼嫩呀,給誰不是給。』我急了:『給誰也不給老黑!』其中一個會說中文的老黑也急了說:『我們都付過好多錢了!』愣把我拖了進去⋯⋯」
小紅把頭扭開,我也挪開視線,不忍看那張淒美的臉。
我的耳朵已經難以承受,小紅又是如何承受這個夢魘的,她以自己的美麗和單純擁抱生活,生活把她打蒙了,也毀掉了這個女孩對所有的信任。
小紅看著不潔淨的天花板道:「半夜三更老黑把我們送出來,他們的車剛走,我們就被等在路邊兒的警車抓走了。提審了一個月,京晶被放了,判我四年,當時我喊,『判我死刑啊,死了到輕省了!』」小紅幾個月前還是盈盈秋水的美目,如今閃著對人性不共戴天之仇。
小紅準備把自己處女之身獻給瑞金──她的最愛,為了取悅最愛想要一雙高跟鞋,被最親信的女朋友欺騙,天真和自尊受到了最殘酷的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