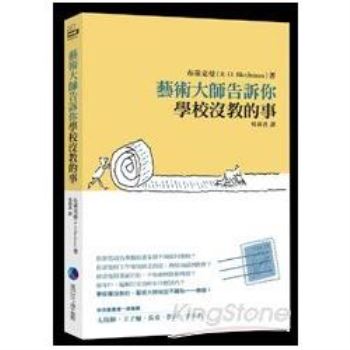得知你打算離職,我很遺憾。如果我是你,我不會這麼做,至少不會急在一時。我知道這工作很無聊,很愚蠢,有時很踐踏人格,挫敗感更是有如家常便飯(你得打通層層關卡才能得到同意!)。而且弄到最後,是誰去向客戶簡報你的作品?是客戶經理。他的重責大任是讓客戶開心——不是你,不是廣告文案,也不是你的創意雙胞胎:美術指導,而是客戶,這些人絕不會冒險下海,除非找不到其他人先去探底。
我會知道這些是因為我親身經驗。你知道嗎?我當過美術指導,那真是我人生中最愚蠢糊塗的一年啊!我的老闆是個不斷哀求我:「鮑伯,讓它粗俗一點!拜託!粗俗一點!」的傢伙(我發誓這是真的)。
不過,請想想你得到的好處,不要只看缺點。每隔一兩個星期,你就能拿到一筆薪水,讓你付房租、吃飯、看電影、聽音樂會,還有最重要的,買筆、買繪圖紙、買顏料,你需要這些東西來做你的正事。
你可以免除那磨人的焦慮,不必擔心什麼時候才能看到你的下一張支票。但是還有一個更好的理由,讓你應該繼續上班(附帶一提,當我想到這裡,我想說的是,你碰到的工作越蠢,你就會越自由,而你越自由,你的原創性就越大;這不是件壞事)。言歸正傳,你該繼續上班的更好理由是,當你沒埋頭在藝術裡,沒去思考它的時候,你的潛意識就會接下這工作。豪斯曼(A. E. Hauseman)有好多首詩就是在他離開書桌時寫出來的。他習慣每天散步兩三個小時,他察覺就是在這時候,「間或有一兩行詩句,間或有一整節詩文同時」冒上心頭。
蒙田(Montaigne)也注意到,他有很多想法是在他離開工作桌的時候浮現的。然而,他也抱怨他最好的想法竟然是在騎馬時出現,害他根本找不到羽毛筆和羊皮紙。詹姆斯,你會發現當你徹底放鬆,也就是自我意識最少的時候,你的創意將達到顛峰。
想想跳舞,如果你太過擔心腳步該怎麼踩,你就會變成那隻可憐的蜈蚣。有人問牠:「這麼多隻腳你到底是怎麼走路的啊?」蜈蚣先生被這問題難倒,反而不知該怎麼走了。唯有在他忘記這個問題時,他才能夠邁開腳步。
我會說一點法文。當我忘記我是在說法文這種語言,而是碰巧地跟某個法國人說話時,我說得最流利。不然我也很可能會變成那隻蜈蚣,一整個打結。
想想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他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多產的作家,他一共寫了八十四本偵探小書,一百三十本其他書籍,用過的筆名差不多有二十四個。如果你認為他創下的紀錄只有這些,不妨想想這點:據他所稱,至少他在回憶錄《當我老的時候》(Quand J’etais vieux)裡是這樣寫的,他跟兩萬個女人上過床(後來他修正為一萬個)。他這樣還有時間寫書?不過他的前妻卻表示,一千兩百個才是比較可靠的數字。
「我們想盡辦法達成,」她說,「我想,如果你像兔子一樣追在目標後面跑,那麼任何目標都有可能達到⋯⋯!」
別以為西默農會遵照嚴格的日常作息表工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一整年花在寫作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但他的潛意識倒是一直在工作。遠離書桌幾個月後,他會找到構想開始研究,鎖上房門拿出打字機,兩三個禮拜後,他將再次出現——帶著一聲響亮的喔—呼,以及一本厚厚的手稿。
罪惡感也對他的驚人產量有所貢獻,這麼久沒做他死也想做的那件事的罪惡感。不過為了公平起見,關於西默農這種異乎常人的產量,還有一點非提不可,那就是他的超高生產力還有其他刺激因素。因為結過三次婚,所以他得支付沉重的贍養費。還有他自己的開銷也很龐大。他在日內瓦湖畔蓋了一座有二十六個房間的古堡,擁有五輛車,而且收藏了大量的名畫,包括畢卡索、雷捷(Léger)和烏拉曼克(Vlaminck)的好幾件作品。而這些似乎還不夠激勵他寫作似的,他還簽下一年寫作好幾本書的合約來逼迫自己。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不但寫得很多,也寫得很棒,因為他是間歇性發作似地寫。
最後——因為紙快沒了,我不得不停筆——讓我引用海明威年輕時在巴黎寫的一段話:「我知道⋯⋯我一定要寫小說。但我會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我不得不寫為止。倘若我把寫小說當成我該做的事,像我們每天都要照三餐吃飯那樣,那我就死定了。當我不得不寫的時候,它就會變成我唯一要做的事,而且別無選擇。所以,讓壓力累積吧。」
讓壓力累積吧。等你二十八⋯⋯三十八⋯⋯或管他多少八的時候——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鐘,而有些時鐘的時辰一直都很瘋狂——小說、詩歌、繪畫、插畫的靈感會突然泉湧爆發。
所以,別把工作辭掉,還不急。幫廣告公司寫文案,把它寫好。然後回家給自己倒杯酒,脫掉鞋子,如果你願意的話(只有你願意的時候)就畫圖。讓你的潛意識,讓你那更自由、更美好的心靈發揮功效,你的素描會因此變得更豐富。
期待你的下一封信——我希望它是寫在揚雅廣告公司(Young& Rubicam)的信紙上。
一切順心
R.O.布萊克曼
附記:我剛好無意中發現了一封絕妙好信,是英國詩人拉金(Philip Larkin)寫的,內容是關於他身為全職圖書館員和兼職詩人(而且是非常棒的詩人!)的雙重生涯。我忍不住想引述一下。
「⋯⋯凡是擁有一份專職工作的『藝術家』,一定會對這種情況感到又愛又恨:而有時又基於同樣的理由而愛它。我不認為,在需要賺錢之時還可以用當藝術家作藉口,逃避賺錢工作、養活自己的義務,以及我之所以認真把工作做好,只是基於這個理由。⋯⋯最好試著全然精神分裂地應對之——讓分裂的人格彼此從對方那裡得到庇護。」
我很喜歡讓彼此「從對方那裡得到庇護」那句。這真是個不要當全職藝術家的超棒理由。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親愛的詹姆斯
我想要打你手心――但不是畫圖那隻――因為你拒絕那件工作。沒錯,那工作很蠢。素肉丸廣告??饒了我吧!但你還是應該接下來的。我幫最差勁的客戶做案子時,往往能做出最棒的作品。因為在那種時候,我可以自由畫我想畫的,就這樣。而且,就算他或她或他們不喜歡,至少我做了我想做的東西,而且可以養活自己(還可以散步到銀行去領我的取消委託費)。
班‧夏恩是這樣說的:「……不管哪種藝術,哪怕再高貴,或再普通,都要接,絕對不能害怕,而且要做出特色。」
「做出特色。」這適用於畫壁畫,拖地板,或捏肉丸。
如果你接下工作,接下這個肉丸廣告或諸如此類的案子,你就可以免除那些只會被人視為腦筋有問題的閒言閒語。西摩‧史瓦斯特(Seymour Chwast)幫《富比士》雜誌工作,也替天知道多少進步團體和理想事業工作,但沒人指責他輕浮善變,筆風不專。
畢竟他也得糊口謀生。民眾理解這點。當然啦,如果他為美國肺臟協會(American Lung Society)工作,接著又跑去接赫伯特塔頓香菸(Herbert Tareyton Cigarettes)的案子,那就另當別論。大眾的容忍有其界限,而一個人需要多少錢才能謀生,也有其限度。(說得好像工作都是為了「謀生」。其實我們工作都是為了賺錢――而且多多益善,不是嗎?)
讓自己開心的結果,往往也能讓別人開心。我們和大眾之間的差異並不比相似多。「我包含眾生,」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如是說。正因如此,每一位稱職的藝術家,都是為唯一一名觀眾工作,也就是他自己,他真正了解的那名觀眾。也唯有如此,他才能打動「眾生」。
我想起最近我去看了馬內(Edouard Manet)的靜物展。起先我不太想去。誰想去看馬內畫蘋果和橘子啊?我知道的馬內是畫《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馬克西米利安的處決》(The Execution of Emperor Maximilian)和裸體《奧林匹亞》(Olympia)的那位畫家,那才是我喜歡的馬內,也才是我想看的馬內,至於他的靜物畫嘛,不,謝謝。但因為無法拒絕朋友的好意,所以我還是去了。讓我喜出望外,且著實嚇了一跳的是,我沒看到蘋果和橘子,我看到偉大的畫作,純粹而簡單。馬內可以描畫的主題多如繁星,但他卻選擇把自己局限在靜物的小小世界裡,這反而讓他得以自由探索油畫這項媒材的各種可能性。他盡情在畫布上揮灑顏料,展現它們豐潤多汁的一面。馬內和他的前輩導師委拉斯蓋茲(Verlazquez)、晚期的哈爾斯(Frans Hals),或畫出剝皮牛的林布蘭一樣,將油彩的獨特質地和筆觸發揮到極致,並陶醉在這樣的狂喜之中。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是的!――肉丸。找出最大的可能性,來展現你的幽默、技巧和概念。所以,打電話給肉丸先生,說你改變心意,或說你現在有空檔,可以接這個案子,然後……開心大玩一場吧!你開心,別人也會開心。包括肉丸先生
一切順心
鮑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