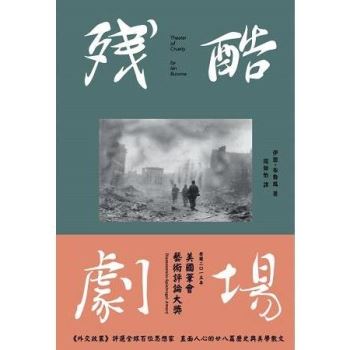第一章 受害者情結的歡愉與險境
……猶太大屠殺也出乎意料地啟發了許多人。幾乎每一個社群,無論國家民族、宗教、種族或少數性別團體,或多或少都有段沒有被公平對待的歷史。所有的人都蒙受過不公不義,而有愈來愈多人,有時甚至是太多人,要求要讓大眾知道真相,並用各種儀式,甚至是金錢來彌補。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關心過去發生的事。若沒有這些歷史事件,包括最讓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我們沒辦法了解自己,了解別人。缺乏對歷史的了解,我們就無法有深刻的觀點。沒有深刻的觀點,我們彷彿在黑暗中摸索,就算是小人之言也輕易相信。所以了解歷史是好事,我們不該遺忘死於孤寂和苦難的受害者。然而,今日各少數族群仍然容易受到各種迫害:穆斯林迫害基督徒;什葉派迫害遜尼派;遜尼派迫害什葉派;中國漢人迫害維吾爾回教徒;塞爾維亞人迫害波士尼亞人等等。但令人不安的是,愈來愈多的少數族群認為自己是歷史洪流中最大的受害者。這種看法正是缺乏歷史觀點的結果。
有時好像每個人都在和猶太人的悲劇較勁,我的一個猶太朋友稱這現象為「受難奧運」。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因描寫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一書而成為暢銷作家。當我讀到她說,希望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能拍一部電影還原歷史真相時,我似乎嗅到了嫉妒的味道。(無獨有偶,她的書名的副標題正是「被遺忘的二次大戰大屠殺」。)華裔美國人似乎不只希望被視為是一個偉大文明的後裔,也希望被視為一場大屠殺的倖存者。在一次專訪中,張純如談到一位女士在一場公開朗讀會後,熱淚盈眶地上前告訴她,她的書讓她感到「身為華裔美國人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一場大屠殺似乎會讓人感到莫名的驕傲。
近年來,電影成了再次體驗歷史悲劇的主要方式,因此導演史匹柏的名字會出現在這番討論中也是意料中事。好萊塢電影讓這些歷史事件活了起來。美國脫口秀名主持人歐普拉(Oprah Winfrey)在電影《魅影情真》(Beloved)中飾演一名奴隸。她告訴媒體記者,自己在一場演出中情緒崩潰,不停地哭泣、發抖。「我完完全全投入演出場景,整個人變得歇斯底里。」她說:「那次經驗讓我脫胎換骨。肉體上的折磨、鞭打、到田裡工作、每天被凌虐,這些和無法掌握自己人生的痛苦比起來,都不算什麼。」請記住,這還只是參與電影演出而已。我並不是要說受害者的苦難都不算什麼。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殘殺幾十萬中國人,這的確是場歷史悲劇。我們絕不能忘記,當年數不清的非洲男女被販賣為奴,過著淒苦的日子,不得善終。我們無法否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當年迫害了成千上萬的亞美尼亞人。回教侵略者殘殺了許多印度教徒,破壞了許多印度神廟。女性和同性戀者仍然受到歧視。一九九八年,美國懷俄明州拉勒米(Laramie)一位同性戀大學生慘遭殺害,這件事告訴我們人類距離公義的社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儘管每逢哥倫布紀念日,大家還在爭辯他是不是屠殺者,當年許多美洲原住民被殺卻是不爭的事實。以上皆是確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然而要是一個文化、種族、宗教、民族國家,將鞏固社群的認同感完全植基於受害者情結上,問題就來了。這種短視觀點無視於史實脈絡,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更被拿來當作仇殺的藉口。……
事情究竟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地步的?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想要對號入座,成為受難者?這些問題並沒有統一的答案。歷史論述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的目的。遭受迫害的集體記憶,無論是真是假,是十九世紀大多數國家民族主義的基礎。我們在今日集體受害情結的論述中,仍可以發現民族主義的思維,但是民族主義似乎不是發展這些論述的主要動機。別的因素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首先,真正的受害者,包括死去的人和倖存者,往往對這些事件保持緘默。當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乘著破舊、擁擠的船到達以色列時,羞恥感和心理創傷,讓之中大部分人無法談論當年所受的折磨。在這個由猶太英雄所建立的新國度中,倖存者的地位可說是模稜兩可。他們似乎急欲卸下當年集中營所留下的包袱,對那段歷史裝作視而不見,因此大部分的受害者寧願保持緘默。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情況也類似。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特地為所有在戰時反抗德軍者建了一座屋子,紀念包括前反抗軍成員、反維奇政府分子、地下與法國政府合作者、自由法國陣線、猶太倖存者。但法裔猶太人卻對這份盛情敬謝不敏。他們最不想要的,就是再一次被單獨從群眾中挑出來。這些倖存者選擇保持緘默。日裔美國人在戰時被美國政府視為內奸,其所受的苦難或許無法和和歐洲猶太人相提並論,但他們在戰後的態度卻十分類似。他們和法裔猶太人一樣,寧願當個平凡老百姓,用沉默塵封當年所受的屈辱。中國受難者則因政治變遷而有不同的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京大屠殺著墨不多,因為沒有任何共產黨英雄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殉國。其實南京當時沒有半個共產黨成員。死於南京、上海以及中國南方的士兵,多隸屬於蔣介石麾下。這些入錯黨的生還者,光是在毛澤東統治下保全性命就有極大的困難,哪來的功夫談論日本軍隊對他們的待遇?
緬懷父母,心生敬意,普世皆然,這是一種追思的方式。特別是在追憶我們父母經歷那段避而不談、沒有被公開承認的苦難時,我們像是在告訴世人我們是誰。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法裔猶太人或日裔美國人選擇隱藏自己的傷疤,悄悄融入主流社會中,假裝自己和別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對他們的兒孫輩來說,這並不夠,彷彿他們自我的一部分被父母的沉默消滅了。打破沉默,公開談論先人的集體苦難,無論是猶太人、日裔美國人、中國人或印度教徒,彷彿是在全世界面前確立自己的定位。年輕的一代若想要和上一代所受的苦難產生淵源,就必須要大眾一而再、再而三地確認這些歷史悲劇。正因為這些倖存者刻意抹去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因此他們的子女除了祖先受難的史實之外,別無區分自己和他人不同的要素。當猶太傳統只剩下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和貝果,中國傳統只剩下譚恩美(《喜福會》的作者)和星期天吃飲茶,共同的受難記憶似乎更能確實地凝聚整個社群。
學者安東尼・阿皮亞(K. Anthony Appiah)在分析現代美國的政治認同時,也提到了這點。當新移民的子女變成了美國人時,也淡忘了祖先母國的語言、宗教信仰、神話和歷史。這往往讓他們開始強調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之處,雖然他們大部分和一般美國人已經沒有什麼不同了。阿皮亞談到各族裔美國人,包括非洲裔美國人時說:
他們的中產階級後裔平常說英語,日常生活充斥著電視影集《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吃外賣中國菜等各種異文化。但想到祖父母時,他們便為了自己膚淺的文化認同而自慚形穢。有些人開始害怕,一旦周遭的人無法注意到他們的不同,他們就什麼都不是了。阿皮亞繼續說:「當過去溫暖人心的種族認同不再,這類新的自我認同論述似乎讓人重新找到自我價值和鞏固社群的依歸。」只不過,這些新論述往往和費迪蘭德所言,將死亡和譁眾取寵結合的行為相去不遠。愈來愈多的自我認同,立基於如同偽宗教一般的受害者情結之上。阿皮亞對少數族裔的觀察,也可套用在女性身上:女性愈得到解放,就有愈多的極端女性主義者出現,將自己定位為受男性迫害者。
……我們在這個意識型態、宗教、國界、文化分際皆瓦解的世界,又該何去何從呢?從世俗、國際主義、世界一家的角度而言,這個世界似乎還不錯,不過前提是你要住在富裕的西方世界。我們捨棄了民族主義的歷史論述,同性戀者可以放心地出櫃加入主流社會,女性可以從事從前只有男性可擔任的工作,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讓我們的文化更為豐富,我們也不再受到宗教或政治教條的迫害。這些當然都是好事。半個世紀以來,世俗、民主、進步等改變值得額手稱慶,我們終於能夠從非理性的民族情結中解脫。但就在我們達到這些成就之後,卻有愈來愈多人想要回頭到民族主義的舒適圈中。而這一回,他們常用的手段是死亡和譁眾取寵的偽宗教。瑟吉夫認為當前以色列之所以將納粹大屠殺變成一種公民宗教,是對世俗化的猶太建國運動——錫安主義——的一種反對運動。原本被視為英雄的社會主義建國先驅,到頭來卻讓人失望,愈來愈多人因此想要探詢自己的歷史根源。然而認真遵循宗教信仰卻非易事。正如同瑟吉夫所言:「對大屠殺的情感和歷史覺知,是猶太人讓自己重回猶太歷史正統的方便捷徑,這條路不需要任何個人實際的道德承諾。憑弔大屠殺,很大一部分已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表現自己和猶太傳統之間連結的方法。」
猶太人、華裔美國人或其他族群,在這點上並無二致。舉例來說,印度近年來,特別是在中產階級印度教徒之間重新燃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即是在反抗尼赫魯(Nehru)所發想的,一個社會主義、世俗化印度的願景。由於多數都市化、中產階級的印度教徒對印度教只有粗淺的認識,於是,仇視回教徒就成了傳達宗教認同的方法。因此在印度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占人口多數的族群,利用歧視較為貧窮、勢力薄弱的少數族群,來鞏固自己的自我認同。但事情必須從更大的脈絡觀察,西方世界尤其如此。正如同浪漫理想主義對赫德(Herder)和費希特(Fichte)的文化崇拜,其後緊接著發生法國啟蒙智士的世俗理性主義;我們對大眾文化和死亡的欣賞,也預告了一個新浪漫時代的來臨,它會以反理性、感性、社群主義的方式出現。我們在柯林頓和布萊爾的政治操作上都可以看到這個傾向,他們用社群情感取代社會主義,強調大家一起分擔每個人的痛苦。我們也在英國戴安娜王妃過世時看到這個傾向,新聞記者傳達這個噩耗,於是所有的人一起哀悼。其實,戴安娜王妃正是我們執迷於受害者情結的最佳證明。她經常以讓人稱道的方式,和受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擁抱愛滋病患和無家可歸的人。她自己也被視為受害者,遭到男性沙文主義、皇家勢利之徒、媒體、英國媒體等等的欺侮。所有覺得自己在某方面是受難者的人,特別是女性和少數族裔,都能在戴妃身上找到認同。這也讓我們看到各國移民、美國和歐洲體制為英國社會所帶來的變遷。英國在歐洲內部的地位妾身未明,而許多人只有在哀悼王妃的逝世時,才感覺到國家是團結一致的。
共同承擔痛苦,也改變了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歷史學不再是發現過去確實發生了什麼事,或是試圖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大家不僅僅認為歷史真相不再重要,還假設這個真相根本不可得。所有的事都是主觀的,都是一種社會政治因素下的人為建構。假如要說我們在學校公民課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要尊重別人所建構的真相。更明確的說,是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所建構的真相。於是乎,我們學習人類對歷史的感受,特別是受害者的感受。透過分擔別人的痛苦,我們學著了解他們的感受,也進一步探索自己的內在。……
但是,這裡的重點應該不是啟蒙大眾的理性,真實性才是關鍵。當所有的真相都是由主觀認定時,只有感受才是真實的,只有主角本身才能知道自身感受的真偽。小說家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對此有精闢的見解。在一篇關於愛滋病文學的文章中,他主張我們不應批判愛滋病的文學表現。他略帶矯情地說:「這實在不足以說明我的感受,但為即將踏進墳墓的男女打分數,不是高尚的行為。」但事情必須從更大的脈絡觀察,西方世界尤其如此。正如同浪漫理想主義對赫德(Herder)和費希特(Fichte)的文化崇拜,其後緊接著發生法國啟蒙智士的世俗理性主義;我們對大眾文化和死亡的欣賞,也預告了一個新浪漫時代的來臨,它會以反理性、感性、社群主義的方式出現。我們在柯林頓和布萊爾的政治操作上都可以看到這個傾向,他們用社群情感取代社會主義,強調大家一起分擔每個人的痛苦。我們也在英國戴安娜王妃過世時看到這個傾向,新聞記者傳達這個噩耗,於是所有的人一起哀悼。其實,戴安娜王妃正是我們執迷於受害者情結的最佳證明。她經常以讓人稱道的方式,和受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擁抱愛滋病患和無家可歸的人。她自己也被視為受害者,遭到男性沙文主義、皇家勢利之徒、媒體、英國媒體等等的欺侮。所有覺得自己在某方面是受難者的人,特別是女性和少數族裔,都能在戴妃身上找到認同。這也讓我們看到各國移民、美國和歐洲體制為英國社會所帶來的變遷。英國在歐洲內部的地位妾身未明,而許多人只有在哀悼王妃的逝世時,才感覺到國家是團結一致的。
共同承擔痛苦,也改變了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歷史學不再是發現過去確實發生了什麼事,或是試圖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大家不僅僅認為歷史真相不再重要,還假設這個真相根本不可得。所有的事都是主觀的,都是一種社會政治因素下的人為建構。假如要說我們在學校公民課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要尊重別人所建構的真相。更明確的說,是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所建構的真相。於是乎,我們學習人類對歷史的感受,特別是受害者的感受。透過分擔別人的痛苦,我們學著了解他們的感受,也進一步探索自己的內在。……
但是,這裡的重點應該不是啟蒙大眾的理性,真實性才是關鍵。當所有的真相都是由主觀認定時,只有感受才是真實的,只有主角本身才能知道自身感受的真偽。小說家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對此有精闢的見解。在一篇關於愛滋病文學的文章中,他主張我們不應批判愛滋病的文學表現。他略帶矯情地說:「這實在不足以說明我的感受,但為即將踏進墳墓的男女打分數,不是高尚的行為。」接著,他將愛滋病文學擴大至一般多元文化主義,聲明一般文學的準則,不適用於多元文化,他甚至認為「確切來說,多元文化和評價作品好壞的這個行業,互不相容」;換言之,我們的批判能力不適用於任何表達他人痛苦的小說、詩詞、短文、戲劇。正如同懷特談到愛滋病文學時說:「我們不允許讓讀者評論我們。我們要他們和我們一起翻來覆去,在我們夜晚的汗水中溼透。」
不可否認的,無論是身為猶太人、同性戀、印度教徒或中國人,我們受過的創傷以及受害者的身分,讓我們真實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如此粗淺的佛洛伊德式觀點,會出現在這個駁斥佛洛伊德的時代,實在讓人驚訝。其實,佛洛伊德的學說,正是典型十九世紀末政治認同下的產物。對世俗化、中產階級、德國或奧匈化的猶太人來說,心理分析是發現自我的理性方法。佛洛伊德為他在維也納的病患所做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懷特和其他玩弄自我認同政治學的人為各種「族群」所做的事,而這些論述則被真正的政客拿去使用。
這種以死亡為題材,譁眾取寵的新宗教,撇開對大眾心理的影響不談,還有其他因素讓人擔憂。在舒教授大談各個傷痛的族群之間建立起共同橋梁的同時,我卻以為,這種將真實性建立在集體苦難的傾向,反而有礙人類對彼此的了解。因為,我們只能表達感受,而無法討論感受,或辯論感受是否為真。這種做法不能促進相互的理解,無論別人說什麼,我們只能默默接受,就算是發生暴力衝突,也不容置喙。政治論述也適用這個情況。意識型態確實帶來了許多苦難,尤其是在那些將意識型態強行加諸人民身上的政體;但沒有了政治型態,任何的政治辯論就沒有了貫穿的邏輯,政客只能用情感,而不是理念來遊說大眾。這十分容易落入極權主義,因為你沒有辦法和情感辯論;任何試著講道理的人,都會被指為沒心沒肝的冷血動物,其意見不值一聽。接著,他將愛滋病文學擴大至一般多元文化主義,聲明一般文學的準則,不適用於多元文化,他甚至認為「確切來說,多元文化和評價作品好壞的這個行業,互不相容」;換言之,我們的批判能力不適用於任何表達他人痛苦的小說、詩詞、短文、戲劇。正如同懷特談到愛滋病文學時說:「我們不允許讓讀者評論我們。我們要他們和我們一起翻來覆去,在我們夜晚的汗水中溼透。」
不可否認的,無論是身為猶太人、同性戀、印度教徒或中國人,我們受過的創傷以及受害者的身分,讓我們真實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如此粗淺的佛洛伊德式觀點,會出現在這個駁斥佛洛伊德的時代,實在讓人驚訝。其實,佛洛伊德的學說,正是典型十九世紀末政治認同下的產物。對世俗化、中產階級、德國或奧匈化的猶太人來說,心理分析是發現自我的理性方法。佛洛伊德為他在維也納的病患所做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懷特和其他玩弄自我認同政治學的人為各種「族群」所做的事,而這些論述則被真正的政客拿去使用。
這種以死亡為題材,譁眾取寵的新宗教,撇開對大眾心理的影響不談,還有其他因素讓人擔憂。在舒教授大談各個傷痛的族群之間建立起共同橋梁的同時,我卻以為,這種將真實性建立在集體苦難的傾向,反而有礙人類對彼此的了解。因為,我們只能表達感受,而無法討論感受,或辯論感受是否為真。這種做法不能促進相互的理解,無論別人說什麼,我們只能默默接受,就算是發生暴力衝突,也不容置喙。政治論述也適用這個情況。意識型態確實帶來了許多苦難,尤其是在那些將意識型態強行加諸人民身上的政體;但沒有了政治型態,任何的政治辯論就沒有了貫穿的邏輯,政客只能用情感,而不是理念來遊說大眾。這十分容易落入極權主義,因為你沒有辦法和情感辯論;任何試著講道理的人,都會被指為沒心沒肝的冷血動物,其意見不值一聽。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要人回到傳統宗教,用既有宗教傳統取代偽宗教。我原則上並不反對宗教組織,但我本身並沒有信仰,也沒有立場提倡這個解決方案。我也不反對為戰爭受難者或遭到迫害者豎立紀念碑。德國政府決定在柏林蓋一座大屠殺博物館,這決定可喜可賀,因為博物館內設有圖書館和檔案中心,若沒有這些中心,博物館就只會是一塊巨石紀念碑。在這個新計畫中,回憶和教育會同時進行。無論是事實或杜撰,和個人及社群苦難相關的文獻必須有一席之地。歷史非常重要,我們應儘量保存更多歷史;且若有人認為歷史可以促進不同的文化和社群彼此寬容了解,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但是,近年來在公眾領域中,許多人試圖用和緩的療癒論述取代原本的政治討論,我認為十分不妥。
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可以是更進一步區辨不同事物。政治雖然深受宗教與精神科學的影響,但畢竟不能與這兩者劃上等號。回憶不等同於歷史,追悼不等同於書寫歷史。要確立一個文化傳承,並不光只是和其他人「協商自我認同的界線」。或許對我們這些已失去和先人在宗教、語言、文化連結的新生代,現在正是放下過去的時機。最後,我認為問題的核心關鍵,是我們要認清真相並不只是一種觀點。事實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存在的。若欺騙自己事實和虛構小說並無不同,或是任何寫作均與小說創作無異,這簡直是在摧毀我們分辨真偽的能力。從大屠殺倖存下來的列維並非憂心未來的人無法理解他的苦痛,而是人無法認清真相。當真相和虛構失去了分別,這就是我們對列維和過去所有受難者最嚴重的背叛。
……猶太大屠殺也出乎意料地啟發了許多人。幾乎每一個社群,無論國家民族、宗教、種族或少數性別團體,或多或少都有段沒有被公平對待的歷史。所有的人都蒙受過不公不義,而有愈來愈多人,有時甚至是太多人,要求要讓大眾知道真相,並用各種儀式,甚至是金錢來彌補。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關心過去發生的事。若沒有這些歷史事件,包括最讓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我們沒辦法了解自己,了解別人。缺乏對歷史的了解,我們就無法有深刻的觀點。沒有深刻的觀點,我們彷彿在黑暗中摸索,就算是小人之言也輕易相信。所以了解歷史是好事,我們不該遺忘死於孤寂和苦難的受害者。然而,今日各少數族群仍然容易受到各種迫害:穆斯林迫害基督徒;什葉派迫害遜尼派;遜尼派迫害什葉派;中國漢人迫害維吾爾回教徒;塞爾維亞人迫害波士尼亞人等等。但令人不安的是,愈來愈多的少數族群認為自己是歷史洪流中最大的受害者。這種看法正是缺乏歷史觀點的結果。
有時好像每個人都在和猶太人的悲劇較勁,我的一個猶太朋友稱這現象為「受難奧運」。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因描寫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一書而成為暢銷作家。當我讀到她說,希望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能拍一部電影還原歷史真相時,我似乎嗅到了嫉妒的味道。(無獨有偶,她的書名的副標題正是「被遺忘的二次大戰大屠殺」。)華裔美國人似乎不只希望被視為是一個偉大文明的後裔,也希望被視為一場大屠殺的倖存者。在一次專訪中,張純如談到一位女士在一場公開朗讀會後,熱淚盈眶地上前告訴她,她的書讓她感到「身為華裔美國人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一場大屠殺似乎會讓人感到莫名的驕傲。
近年來,電影成了再次體驗歷史悲劇的主要方式,因此導演史匹柏的名字會出現在這番討論中也是意料中事。好萊塢電影讓這些歷史事件活了起來。美國脫口秀名主持人歐普拉(Oprah Winfrey)在電影《魅影情真》(Beloved)中飾演一名奴隸。她告訴媒體記者,自己在一場演出中情緒崩潰,不停地哭泣、發抖。「我完完全全投入演出場景,整個人變得歇斯底里。」她說:「那次經驗讓我脫胎換骨。肉體上的折磨、鞭打、到田裡工作、每天被凌虐,這些和無法掌握自己人生的痛苦比起來,都不算什麼。」請記住,這還只是參與電影演出而已。我並不是要說受害者的苦難都不算什麼。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殘殺幾十萬中國人,這的確是場歷史悲劇。我們絕不能忘記,當年數不清的非洲男女被販賣為奴,過著淒苦的日子,不得善終。我們無法否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當年迫害了成千上萬的亞美尼亞人。回教侵略者殘殺了許多印度教徒,破壞了許多印度神廟。女性和同性戀者仍然受到歧視。一九九八年,美國懷俄明州拉勒米(Laramie)一位同性戀大學生慘遭殺害,這件事告訴我們人類距離公義的社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儘管每逢哥倫布紀念日,大家還在爭辯他是不是屠殺者,當年許多美洲原住民被殺卻是不爭的事實。以上皆是確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然而要是一個文化、種族、宗教、民族國家,將鞏固社群的認同感完全植基於受害者情結上,問題就來了。這種短視觀點無視於史實脈絡,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更被拿來當作仇殺的藉口。……
事情究竟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地步的?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想要對號入座,成為受難者?這些問題並沒有統一的答案。歷史論述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的目的。遭受迫害的集體記憶,無論是真是假,是十九世紀大多數國家民族主義的基礎。我們在今日集體受害情結的論述中,仍可以發現民族主義的思維,但是民族主義似乎不是發展這些論述的主要動機。別的因素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首先,真正的受害者,包括死去的人和倖存者,往往對這些事件保持緘默。當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乘著破舊、擁擠的船到達以色列時,羞恥感和心理創傷,讓之中大部分人無法談論當年所受的折磨。在這個由猶太英雄所建立的新國度中,倖存者的地位可說是模稜兩可。他們似乎急欲卸下當年集中營所留下的包袱,對那段歷史裝作視而不見,因此大部分的受害者寧願保持緘默。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情況也類似。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特地為所有在戰時反抗德軍者建了一座屋子,紀念包括前反抗軍成員、反維奇政府分子、地下與法國政府合作者、自由法國陣線、猶太倖存者。但法裔猶太人卻對這份盛情敬謝不敏。他們最不想要的,就是再一次被單獨從群眾中挑出來。這些倖存者選擇保持緘默。日裔美國人在戰時被美國政府視為內奸,其所受的苦難或許無法和和歐洲猶太人相提並論,但他們在戰後的態度卻十分類似。他們和法裔猶太人一樣,寧願當個平凡老百姓,用沉默塵封當年所受的屈辱。中國受難者則因政治變遷而有不同的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京大屠殺著墨不多,因為沒有任何共產黨英雄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殉國。其實南京當時沒有半個共產黨成員。死於南京、上海以及中國南方的士兵,多隸屬於蔣介石麾下。這些入錯黨的生還者,光是在毛澤東統治下保全性命就有極大的困難,哪來的功夫談論日本軍隊對他們的待遇?
緬懷父母,心生敬意,普世皆然,這是一種追思的方式。特別是在追憶我們父母經歷那段避而不談、沒有被公開承認的苦難時,我們像是在告訴世人我們是誰。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法裔猶太人或日裔美國人選擇隱藏自己的傷疤,悄悄融入主流社會中,假裝自己和別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對他們的兒孫輩來說,這並不夠,彷彿他們自我的一部分被父母的沉默消滅了。打破沉默,公開談論先人的集體苦難,無論是猶太人、日裔美國人、中國人或印度教徒,彷彿是在全世界面前確立自己的定位。年輕的一代若想要和上一代所受的苦難產生淵源,就必須要大眾一而再、再而三地確認這些歷史悲劇。正因為這些倖存者刻意抹去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因此他們的子女除了祖先受難的史實之外,別無區分自己和他人不同的要素。當猶太傳統只剩下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和貝果,中國傳統只剩下譚恩美(《喜福會》的作者)和星期天吃飲茶,共同的受難記憶似乎更能確實地凝聚整個社群。
學者安東尼・阿皮亞(K. Anthony Appiah)在分析現代美國的政治認同時,也提到了這點。當新移民的子女變成了美國人時,也淡忘了祖先母國的語言、宗教信仰、神話和歷史。這往往讓他們開始強調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之處,雖然他們大部分和一般美國人已經沒有什麼不同了。阿皮亞談到各族裔美國人,包括非洲裔美國人時說:
他們的中產階級後裔平常說英語,日常生活充斥著電視影集《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吃外賣中國菜等各種異文化。但想到祖父母時,他們便為了自己膚淺的文化認同而自慚形穢。有些人開始害怕,一旦周遭的人無法注意到他們的不同,他們就什麼都不是了。阿皮亞繼續說:「當過去溫暖人心的種族認同不再,這類新的自我認同論述似乎讓人重新找到自我價值和鞏固社群的依歸。」只不過,這些新論述往往和費迪蘭德所言,將死亡和譁眾取寵結合的行為相去不遠。愈來愈多的自我認同,立基於如同偽宗教一般的受害者情結之上。阿皮亞對少數族裔的觀察,也可套用在女性身上:女性愈得到解放,就有愈多的極端女性主義者出現,將自己定位為受男性迫害者。
……我們在這個意識型態、宗教、國界、文化分際皆瓦解的世界,又該何去何從呢?從世俗、國際主義、世界一家的角度而言,這個世界似乎還不錯,不過前提是你要住在富裕的西方世界。我們捨棄了民族主義的歷史論述,同性戀者可以放心地出櫃加入主流社會,女性可以從事從前只有男性可擔任的工作,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讓我們的文化更為豐富,我們也不再受到宗教或政治教條的迫害。這些當然都是好事。半個世紀以來,世俗、民主、進步等改變值得額手稱慶,我們終於能夠從非理性的民族情結中解脫。但就在我們達到這些成就之後,卻有愈來愈多人想要回頭到民族主義的舒適圈中。而這一回,他們常用的手段是死亡和譁眾取寵的偽宗教。瑟吉夫認為當前以色列之所以將納粹大屠殺變成一種公民宗教,是對世俗化的猶太建國運動——錫安主義——的一種反對運動。原本被視為英雄的社會主義建國先驅,到頭來卻讓人失望,愈來愈多人因此想要探詢自己的歷史根源。然而認真遵循宗教信仰卻非易事。正如同瑟吉夫所言:「對大屠殺的情感和歷史覺知,是猶太人讓自己重回猶太歷史正統的方便捷徑,這條路不需要任何個人實際的道德承諾。憑弔大屠殺,很大一部分已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表現自己和猶太傳統之間連結的方法。」
猶太人、華裔美國人或其他族群,在這點上並無二致。舉例來說,印度近年來,特別是在中產階級印度教徒之間重新燃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即是在反抗尼赫魯(Nehru)所發想的,一個社會主義、世俗化印度的願景。由於多數都市化、中產階級的印度教徒對印度教只有粗淺的認識,於是,仇視回教徒就成了傳達宗教認同的方法。因此在印度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占人口多數的族群,利用歧視較為貧窮、勢力薄弱的少數族群,來鞏固自己的自我認同。但事情必須從更大的脈絡觀察,西方世界尤其如此。正如同浪漫理想主義對赫德(Herder)和費希特(Fichte)的文化崇拜,其後緊接著發生法國啟蒙智士的世俗理性主義;我們對大眾文化和死亡的欣賞,也預告了一個新浪漫時代的來臨,它會以反理性、感性、社群主義的方式出現。我們在柯林頓和布萊爾的政治操作上都可以看到這個傾向,他們用社群情感取代社會主義,強調大家一起分擔每個人的痛苦。我們也在英國戴安娜王妃過世時看到這個傾向,新聞記者傳達這個噩耗,於是所有的人一起哀悼。其實,戴安娜王妃正是我們執迷於受害者情結的最佳證明。她經常以讓人稱道的方式,和受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擁抱愛滋病患和無家可歸的人。她自己也被視為受害者,遭到男性沙文主義、皇家勢利之徒、媒體、英國媒體等等的欺侮。所有覺得自己在某方面是受難者的人,特別是女性和少數族裔,都能在戴妃身上找到認同。這也讓我們看到各國移民、美國和歐洲體制為英國社會所帶來的變遷。英國在歐洲內部的地位妾身未明,而許多人只有在哀悼王妃的逝世時,才感覺到國家是團結一致的。
共同承擔痛苦,也改變了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歷史學不再是發現過去確實發生了什麼事,或是試圖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大家不僅僅認為歷史真相不再重要,還假設這個真相根本不可得。所有的事都是主觀的,都是一種社會政治因素下的人為建構。假如要說我們在學校公民課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要尊重別人所建構的真相。更明確的說,是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所建構的真相。於是乎,我們學習人類對歷史的感受,特別是受害者的感受。透過分擔別人的痛苦,我們學著了解他們的感受,也進一步探索自己的內在。……
但是,這裡的重點應該不是啟蒙大眾的理性,真實性才是關鍵。當所有的真相都是由主觀認定時,只有感受才是真實的,只有主角本身才能知道自身感受的真偽。小說家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對此有精闢的見解。在一篇關於愛滋病文學的文章中,他主張我們不應批判愛滋病的文學表現。他略帶矯情地說:「這實在不足以說明我的感受,但為即將踏進墳墓的男女打分數,不是高尚的行為。」但事情必須從更大的脈絡觀察,西方世界尤其如此。正如同浪漫理想主義對赫德(Herder)和費希特(Fichte)的文化崇拜,其後緊接著發生法國啟蒙智士的世俗理性主義;我們對大眾文化和死亡的欣賞,也預告了一個新浪漫時代的來臨,它會以反理性、感性、社群主義的方式出現。我們在柯林頓和布萊爾的政治操作上都可以看到這個傾向,他們用社群情感取代社會主義,強調大家一起分擔每個人的痛苦。我們也在英國戴安娜王妃過世時看到這個傾向,新聞記者傳達這個噩耗,於是所有的人一起哀悼。其實,戴安娜王妃正是我們執迷於受害者情結的最佳證明。她經常以讓人稱道的方式,和受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擁抱愛滋病患和無家可歸的人。她自己也被視為受害者,遭到男性沙文主義、皇家勢利之徒、媒體、英國媒體等等的欺侮。所有覺得自己在某方面是受難者的人,特別是女性和少數族裔,都能在戴妃身上找到認同。這也讓我們看到各國移民、美國和歐洲體制為英國社會所帶來的變遷。英國在歐洲內部的地位妾身未明,而許多人只有在哀悼王妃的逝世時,才感覺到國家是團結一致的。
共同承擔痛苦,也改變了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歷史學不再是發現過去確實發生了什麼事,或是試圖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大家不僅僅認為歷史真相不再重要,還假設這個真相根本不可得。所有的事都是主觀的,都是一種社會政治因素下的人為建構。假如要說我們在學校公民課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要尊重別人所建構的真相。更明確的說,是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所建構的真相。於是乎,我們學習人類對歷史的感受,特別是受害者的感受。透過分擔別人的痛苦,我們學著了解他們的感受,也進一步探索自己的內在。……
但是,這裡的重點應該不是啟蒙大眾的理性,真實性才是關鍵。當所有的真相都是由主觀認定時,只有感受才是真實的,只有主角本身才能知道自身感受的真偽。小說家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對此有精闢的見解。在一篇關於愛滋病文學的文章中,他主張我們不應批判愛滋病的文學表現。他略帶矯情地說:「這實在不足以說明我的感受,但為即將踏進墳墓的男女打分數,不是高尚的行為。」接著,他將愛滋病文學擴大至一般多元文化主義,聲明一般文學的準則,不適用於多元文化,他甚至認為「確切來說,多元文化和評價作品好壞的這個行業,互不相容」;換言之,我們的批判能力不適用於任何表達他人痛苦的小說、詩詞、短文、戲劇。正如同懷特談到愛滋病文學時說:「我們不允許讓讀者評論我們。我們要他們和我們一起翻來覆去,在我們夜晚的汗水中溼透。」
不可否認的,無論是身為猶太人、同性戀、印度教徒或中國人,我們受過的創傷以及受害者的身分,讓我們真實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如此粗淺的佛洛伊德式觀點,會出現在這個駁斥佛洛伊德的時代,實在讓人驚訝。其實,佛洛伊德的學說,正是典型十九世紀末政治認同下的產物。對世俗化、中產階級、德國或奧匈化的猶太人來說,心理分析是發現自我的理性方法。佛洛伊德為他在維也納的病患所做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懷特和其他玩弄自我認同政治學的人為各種「族群」所做的事,而這些論述則被真正的政客拿去使用。
這種以死亡為題材,譁眾取寵的新宗教,撇開對大眾心理的影響不談,還有其他因素讓人擔憂。在舒教授大談各個傷痛的族群之間建立起共同橋梁的同時,我卻以為,這種將真實性建立在集體苦難的傾向,反而有礙人類對彼此的了解。因為,我們只能表達感受,而無法討論感受,或辯論感受是否為真。這種做法不能促進相互的理解,無論別人說什麼,我們只能默默接受,就算是發生暴力衝突,也不容置喙。政治論述也適用這個情況。意識型態確實帶來了許多苦難,尤其是在那些將意識型態強行加諸人民身上的政體;但沒有了政治型態,任何的政治辯論就沒有了貫穿的邏輯,政客只能用情感,而不是理念來遊說大眾。這十分容易落入極權主義,因為你沒有辦法和情感辯論;任何試著講道理的人,都會被指為沒心沒肝的冷血動物,其意見不值一聽。接著,他將愛滋病文學擴大至一般多元文化主義,聲明一般文學的準則,不適用於多元文化,他甚至認為「確切來說,多元文化和評價作品好壞的這個行業,互不相容」;換言之,我們的批判能力不適用於任何表達他人痛苦的小說、詩詞、短文、戲劇。正如同懷特談到愛滋病文學時說:「我們不允許讓讀者評論我們。我們要他們和我們一起翻來覆去,在我們夜晚的汗水中溼透。」
不可否認的,無論是身為猶太人、同性戀、印度教徒或中國人,我們受過的創傷以及受害者的身分,讓我們真實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如此粗淺的佛洛伊德式觀點,會出現在這個駁斥佛洛伊德的時代,實在讓人驚訝。其實,佛洛伊德的學說,正是典型十九世紀末政治認同下的產物。對世俗化、中產階級、德國或奧匈化的猶太人來說,心理分析是發現自我的理性方法。佛洛伊德為他在維也納的病患所做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懷特和其他玩弄自我認同政治學的人為各種「族群」所做的事,而這些論述則被真正的政客拿去使用。
這種以死亡為題材,譁眾取寵的新宗教,撇開對大眾心理的影響不談,還有其他因素讓人擔憂。在舒教授大談各個傷痛的族群之間建立起共同橋梁的同時,我卻以為,這種將真實性建立在集體苦難的傾向,反而有礙人類對彼此的了解。因為,我們只能表達感受,而無法討論感受,或辯論感受是否為真。這種做法不能促進相互的理解,無論別人說什麼,我們只能默默接受,就算是發生暴力衝突,也不容置喙。政治論述也適用這個情況。意識型態確實帶來了許多苦難,尤其是在那些將意識型態強行加諸人民身上的政體;但沒有了政治型態,任何的政治辯論就沒有了貫穿的邏輯,政客只能用情感,而不是理念來遊說大眾。這十分容易落入極權主義,因為你沒有辦法和情感辯論;任何試著講道理的人,都會被指為沒心沒肝的冷血動物,其意見不值一聽。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要人回到傳統宗教,用既有宗教傳統取代偽宗教。我原則上並不反對宗教組織,但我本身並沒有信仰,也沒有立場提倡這個解決方案。我也不反對為戰爭受難者或遭到迫害者豎立紀念碑。德國政府決定在柏林蓋一座大屠殺博物館,這決定可喜可賀,因為博物館內設有圖書館和檔案中心,若沒有這些中心,博物館就只會是一塊巨石紀念碑。在這個新計畫中,回憶和教育會同時進行。無論是事實或杜撰,和個人及社群苦難相關的文獻必須有一席之地。歷史非常重要,我們應儘量保存更多歷史;且若有人認為歷史可以促進不同的文化和社群彼此寬容了解,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但是,近年來在公眾領域中,許多人試圖用和緩的療癒論述取代原本的政治討論,我認為十分不妥。
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可以是更進一步區辨不同事物。政治雖然深受宗教與精神科學的影響,但畢竟不能與這兩者劃上等號。回憶不等同於歷史,追悼不等同於書寫歷史。要確立一個文化傳承,並不光只是和其他人「協商自我認同的界線」。或許對我們這些已失去和先人在宗教、語言、文化連結的新生代,現在正是放下過去的時機。最後,我認為問題的核心關鍵,是我們要認清真相並不只是一種觀點。事實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存在的。若欺騙自己事實和虛構小說並無不同,或是任何寫作均與小說創作無異,這簡直是在摧毀我們分辨真偽的能力。從大屠殺倖存下來的列維並非憂心未來的人無法理解他的苦痛,而是人無法認清真相。當真相和虛構失去了分別,這就是我們對列維和過去所有受難者最嚴重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