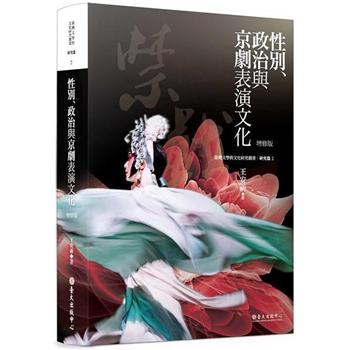第一章 乾旦梅蘭芳──完美女性 雅正典型(摘錄)
一、前言
本書論京劇的性別與政治,第一章先從乾旦開始,梅蘭芳自是代表。梅蘭芳男扮女妝應無性別認同的尷尬,因為乾旦在戲曲史上早有傳統。
關於乾旦的歷史淵源,曾永義老師早在〈男扮女妝與女扮男妝〉一文中即有考證,張發穎《中國戲班史》、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以及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等都有詳盡討論,近年么書儀有〈明清演劇史上乾旦的興衰〉專文考察。學位論文也有香港陳家威之《清代京劇中之乾旦研究》等。
二、乾旦傳統:男身塑女形
演劇史上男優女優起源都很早,孰先孰後很難考察。《魏書.齊王芳紀》裴注引司馬師廢帝奏中,郭懷、袁信扮「遼東妖婦」,應是男扮女妝最早資料。崔令欽《教坊記.踏搖娘》因有「丈夫著婦人衣」,更可明確視作乾旦。元代家庭戲班居多,男女演員並存,但並無男扮女妝記載,反而多見女扮男妝。也有妓女演劇,往往「旦末雙全」兼扮男女。明代妓女演劇更盛,擅長各行腳色。宣德三年左都御史顧佐奏禁歌妓,席間用孌童小唱及演劇,「孌童妝旦」乃應運而生。不過,女性演劇仍難全面禁止,陸萼庭具體考察出「娼兼優」、「專業女伶」和「私家歌姬」三類崑劇女子演劇。
明代崑劇職業戲班幾乎都是男班組成,私人家班也有全男班,包括童伶小廝和成人優伶兩類,各種行當都由男性扮飾,男演員妝旦已是常態,「豔婉」的姿態和演技已成為崑劇表演史上的亮點。例如申時行家班名張三者,工小旦,嗜酒,「醉時上場,其豔入神,非醉中不能盡其技」,因而贏得「醉張三」美名。飾演《西廂記》的紅娘,「一音一步,居然婉弱女子,魂為之銷。」又如業餘客串男旦的趙必達演杜麗娘,有「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的效果。擅長演《躍鯉記》的男旦柳生,也能「供頓清饒,折旋婉便,稱一時之冠」。
男旦的表演藝術,到了清代一直都是劇場的重要風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可以集秀班旦色金德輝為例,他演《牡丹亭.尋夢》、《療妒羹.題曲》,被讚為「春蠶欲死」,「彷彿江采蘋樓東獨步,冷淡處別饒一種哀絕」。這些伶人精湛技藝影響所及,是劇場文化重藝不重色。金德輝老年登臺仍被稱讚「南部絕調」,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見者都忘其醜」,馬繼美則是「年九十,為小旦,如十五六處子」。
清代滿族入關後整頓女樂,女戲子一再為政府所禁。順治八年清世祖下旨命教坊司停止女樂,改用太監替代。雖然不久後順治十二年宮中又一度使用女樂,但到順治十六年裁革教坊司,不用女樂遂成定制。這項整頓自然波及了戲班,康熙十年禁唱秧歌婦女,康熙四十五年同樣內容的禁令又一次公布,而且更為嚴峻。康熙五十八年,「雖禁止女戲,今戲女有坐車進城遊唱者,名雖戲女,乃於妓女相同,不肖官員人等迷戀,以致罄其產業,亦未可定,應禁止進城。」矛頭對準「名雖戲女」實則與妓女相同的藝妓。直到乾隆朝,仍有「嚴禁秧歌婦女及女戲遊唱」禁令。
在連續性的政令禁止下,私人家樂雖仍有女班,宮廷卻嚴格革除官妓、民間禁止買良為娼,城裡禁止女戲,城外女藝人也一律不准進京。整頓的結果是:京城中少了公開的妓院,戲班子一律成為男班,戲園的觀眾也一律為男性。因此清中葉成形的京劇劇種,在形成初期根本不存在女演員,各腳色行當全部由男演員扮演,劇中女子也由男性扮演,稱為「乾旦」,也叫「男旦」。直到同治末、光緒初,才有女演員「坤伶」登場。起初是「全女班」,民國後還明令禁止男女合演,以免「有傷風化」。一九一七年上海「大世界」遊樂場落成開張,座落在法租界,內有「乾坤大京班」,首先實行男女合演,法租界「共舞臺」廣告,也以男女合演為號召。京劇乾旦代表梅蘭芳,對於在舞臺上以男扮女,應該沒有尷尬不安的心理問題需要調適。如前所述,男扮女並不始於京劇,「乾旦傳統」在戲曲表演史上早已形成,而此傳統更有另一傳統為其奠基,即是戲曲表演程式中的核心關鍵:腳色。傳統戲曲在「演員」和「劇中人」之間,多了「腳色」這一道關卡,演員必須通過「腳色」的扮飾才能轉換成劇中人,人物塑造的流程不是直接由「演員」體驗「劇中人」,而是「演員→腳色→劇中人」。就腳色與演員之間的關係而論,腳色代表演員對於「表演藝術」的專精,必須熟練本行腳色程式化的唱念做打才能進入人物扮演;就腳色和劇中人的關係而言,不同的腳色象徵著不同的「人物類型」,包括性別、身分、性格。
「反串」與演員的性別無關,當以本工的腳色行當為基準,凡是演出不屬於本行腳色應工的戲,即稱之為「反串」,正如方問溪在《梨園話》裡所說:「反其常態,謂之反串」,「如令生飾旦、令旦飾生、淨飾丑而丑飾淨」之類即是。反串是「演員」與「腳色行當」之間的關係,非關「演員」與「劇中人」之性別。本為男性的梅蘭芳演《轅門射戟》的呂布是反串,演楊貴妃反倒是正常的。戲曲表演因妝扮甚濃且唱念做表程式化,所以師父只根據嗓音寬窄、個頭身段等資質條件,分派學生的腳色行當,性別不是分行的重點。因此男扮女並不需要特別的心理調適。在清政府禁女演員的前提下,劇中女子當然只得由男性扮演,這是不得不遵守的社會法規,在此現實條件下,乾旦並不特別。
既然「乾旦」在戲曲界已經成為一項表演以及文化傳統,表演本身自有一套規範程式,因此男性演員在京劇行業裡學習旦角、飾演女性時,並沒有任何性別認同的問題,這些唱旦的男孩子,努力學習旦角身段唱念,使得自己在形體聲音等各方面,都要比女人還女人,於是「貼片子」、「綁蹺」、「線尾子」等等化妝穿戴,都是以修飾男性面容身材為前提,而「小嗓」(假音)的使用,當然更是為了趨近於女子音聲。一心想的,只是如何精準扎實地學習旦角程式化的功夫,如何「男身塑女形」。
但是,觀眾對待乾旦的眼光心態,以及乾旦養成的教育和環境,卻可能在梅蘭芳心理蒙上一層陰影,進而影響他的京劇旦行性格塑造。關於觀眾對待乾旦的態度,「梨園花譜」的研究在學界已然展開,本文集中於乾旦梅蘭芳本人對於自身性別轉換的心理探析。這項研究,先從京崑不同的旦行表演美學說起。
三、她╱他的雅正:梅蘭芳的性別陰影
(一)從風情旖旎到端莊雅正
梅蘭芳首創京劇以旦行掛頭牌之風氣後,京劇女性的形象塑造至今仍以梅派為最高美學標準。而梅蘭芳的女性塑造卻不同於之前的崑劇,崑旦的表演以「風情旖旎、纏綿婉轉」為主要表徵,梅蘭芳卻刻意削弱淡化綽態柔情,轉而以「大方沉著、端莊雅正」為京劇女性形象塑造的美學高標。講究身體的「重度」,強調「剛柔相濟」、「外圓內方」、「藏在內裡的勁兒」,表演追求「大氣」。
崑劇的「正旦」也要求沉著穩重,衣著多為素色褶子,以唱工為重,多扮演受苦而貞烈的中年或青年已婚婦女,與「閨門旦」的「幽約怨悱、纏綿多情」氣質不同。但崑劇最受歡迎的才子佳人戲,女主角以窈窕淑女、大家閨秀或娼門名妓為多,杜麗娘、陳妙常、李亞仙、霍小玉、崔鶯鶯、謝素秋、花魁女等,幾乎成了崑旦代表人物,她們都由閨門旦應工,深掘幽微的曲文,配上悠緩細微的身形挪移、旖旎嫵媚的神色姿態,整體表演「春蠶欲死」。
京崑的「身體」在似與不似間,同為戲曲代表,同具戲曲特質,但二者又有極精微的差異。上海崑劇院名旦張靜嫻曾在演講中提到,她曾向陳正薇老師學過京劇,陳老師在她表演時一路提醒糾正:「穩著點,穩著點,這是京劇!」張靜嫻原擅崑劇正旦兼演閨門旦,纏綿婉媚、顧盼含情,整個「身體」和京劇的大方沉穩不同。雖然張的時代較晚,但陳正薇的提醒,精微地點出了京崑身體表現的不同,可為輔證之例。而二者的不同,並不是行當劃分的不對應。
京劇在「青衣」和「花旦」之間也有另一個介乎其間的行當「花衫」。所謂介於二者之間,是指「兼備青衣表演之擅長(唱工),以及花旦表演之特質(身段靈巧、念白爽利)」,追求的是唱念做表舞蹈身段俱佳,而非整體氣質介於端莊和俏皮之間。「派頭大方」始終是梅派公認的先決條件,而梅派正是京劇旦行代表,「雅正」是梅蘭芳所確立的京劇旦行表演典範。由風情旖旎到端莊雅正,戲曲表演史上女性丰姿的轉變,是梅蘭芳刻意的追求。和「身體」的改變相呼應的,是他對於所飾人物的性格,也精心挑選、嚴加把關,「他」所演的「她們」,絕對不涉情慾。例如他堅持不演性格不貞的東方氏(《虹霓關》),刻意修改腿部身段、沖淡《牡丹亭.驚夢》中杜麗娘的思春情態,更花了一生心思漸次修改《貴妃醉酒》,使其由風情放恣轉化為雍容華貴的代表(詳下文)。對於人物塑造與表演風格,梅蘭芳是自覺自主的整體思考。
筆者認為,梅蘭芳刻意追求女性端莊形象,意在擺脫個人出身於「相公堂子」(稚齡乾旦侑酒陪宴)的陰影。此點筆者在〈梅蘭芳以雅正為女性塑造的內在隱衷〉一文中,曾試圖探析,提出梅蘭芳力求雅正的內在隱衷分為兩點:從大處說,可視為梅蘭芳對外在大環境文化思潮的回應;從個人因素分析,則或與梅蘭芳試圖擺脫相公堂子的出身陰影有關。
(二)以雅正擺脫相公堂子出身陰影
四大徽班進京之後,除了給京師舞臺帶來新劇目、新唱腔、新演員,從而引起了戲曲變革之外,新的娛樂業「打茶圍」(又稱「逛堂子」)也在京城開始盛行,一直流行到清末。關於「打茶圍」(逛堂子),么書儀在《晚清戲曲的變革》一書中有詳細考察:「打茶圍」主要內容是以歌侑酒,是由戲班中年輕的男演員(特別是乾旦)在演出的餘暇從事侍宴、陪酒、唱曲、閒談等應酬的收費行業。營業地點,可以應召前往顧客指定的酒樓飯莊,而大多數是在營業者的「下處」。下處即住處,一般的伶人大夥兒住在一起稱「大下處」,自稱「公中人」;成名的伶人別立下處,稱作「私寓」或「私坊」。伶人各立「堂名」為住處的標誌,自稱「堂名中人」,伶界自己的習慣叫「堂號」。歌郎臺上演戲畢,臺下侑酒作陪,堂子的興盛,事關戲班興盛與伶人走紅。嘉慶以後直到光緒間,堂子與「科班」共存,共同擔當培養藝人的職責。據么書儀統計,晚清戲曲演員,從堂子培養出來的所占比例最大,曲界的名伶,也大多是堂子的主人。「同光十三絕」中,梅巧玲稱景和堂主人,劉趕三為保身堂主人,余紫雲為勝春堂主人,徐小香為岫雲堂主人,時小福為綺春堂主人⋯⋯今人敘其事跡,大多朦朧其事,彷彿如文人之堂號,其實他們實實在在地開著堂子,養著許多立過賣身契的歌郎,這是主人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歌郎被捧紅後,有客人「老斗」為之贖身,則可另立門戶,開設自己的堂子。
梅蘭芳出身於堂子。這段歷史,在戲曲論著中詳略不一,大都已被隱去或「淨化」。么書儀在〈一幀照片的五種說明〉一文中,根據同一張照片不同時期的文字解說(圖說),做出了明確考察:梅蘭芳幼年在「雲和堂」裡學藝,人稱梅郎,為雲和堂「十二金釵」中之人物。堂子在民國以後被禁止,田際雲於民國元年四月十五日遞呈子給北京外城總廳,要求「查禁韓家潭像姑堂子,以重人道」,十二月,外城巡警總廳刊出告示,批准了田際雲的申請。告示中對堂子的定位是「實乖人道」的「藏汙納垢之場」,「玷汙全國,貽笑外邦」;對於堂子裡的歌郎,作了這樣的貶抑譴責:「以媚人為生活,效私娼之行為」、「人格之卑,乃達極點」。從此堂子歌郎成為被歧視和忌諱的字眼。相公堂子出身的藝人,當然不願舊事重提。
「堂子出身」是在梅蘭芳舞臺生涯回顧、傳記、文集以及相關論著中幾乎被抹去的一段歷史,不僅為梅蘭芳著書立傳的作者有意為賢者諱,梅蘭芳本人一定更不願意重提童年往事。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穆辰公所著小說《梅蘭芳》由奉天時報社出版,該書以小說體從梅之出身敘起,幼年為歌郎的生活也化為書中情節。書一出版,愛護梅的馮耿光,立即將書全數收購焚燒銷毀。這段過程被記錄在鄭逸梅的《藝林散葉續編》第一五三條,梅蘭芳及其友人對於自己名譽的維護是這麼刻意謹慎,這麼小心翼翼。
筆者以為,梅蘭芳在所飾女性的性格塑造上有意識地力求端莊雅正,很有可能和這段歷史有關。
梅蘭芳對於所飾角色的性格以及整體戲的風格,都有意識地力求典雅端正,這樣清晰的自覺自主,表現在他邀請文人為自己量身打造新編戲時,也表現在他對傳統老戲的改編、詮釋與定調,最明顯的例子是《貴妃醉酒》。
《貴妃醉酒》原來傳統的演法大致都遵循筱翠花,做表十分細膩,充分發揮腰腿、水袖和蹺工。但梅蘭芳覺得有些地方未免「做過了頭」,甚至人物性格都因此而扭曲了,因此做了明顯的改造。在回憶錄《舞台生活四十年》裡,梅蘭芳特別詳細說明了這段過程。梅氏的這齣戲學自路三寶,也是筱翠花的路數,學全了之後經常演出,但每次演的時候都自我反省,對於做過了頭的部分「陸續加以沖淡」,但仍覺得不夠理想,因而動了「徹底改念白唱詞」的念頭。最後的定本,不僅把原來「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的詞,改為「酒入愁腸人易醉、平白誆駕為何情」;也將酒醉後和高裴二太監輕狂調笑的做表徹底改掉;更將「臥魚」身段深化為「嗅花聞香、醉倒花叢」。一再精修之後,這齣戲成為梅派代表作,取代了原來筱翠花的路數。後來演這戲的後學者,幾乎一面倒地以梅派為依歸。筱派的演法,流傳至今,只能在二○○六年過世的乾旦藝術家陳永玲的演出中窺見端倪。
梅蘭芳對這齣戲的修改歷程很長,根據梅派愛好者齊崧《談梅蘭芳》一書所記,他不僅看過早年梅蘭芳根據筱翠花版本所演的放浪形骸的貴妃,抗戰勝利後,看到的演出都還和最後的定本有一些不同。齊崧曾根據現場觀看的印象和後期的錄音相比,提出「且自由他」的「他」字念法,即有三個階段的不同:最初為大聲念出,在眾宮女面前宣洩自我的不滿;之後採小聲輕念,唯恐眾人窺出她的失意;最後則只化為一聲自憐自傷的喟嘆。齊崧認為一個「他」字的念法,就能夠體現出梅氏藝術的幾個演進階段。這齣戲的修改歷程,幾乎貫穿梅氏一生的演出歷程,早期的修改多半從深刻體會劇中人心情出發,愈到後期,梅派戲中梅氏自我的形象已經愈來愈明晰,劇中貴妃的氣度與梅蘭芳個人的特質已經完全貼合為一了,最後定型的《貴妃醉酒》,堪稱華麗與孤寂的交織。觀眾幾乎很難具體分辨,這樣迥異於最初筱翠花形象的貴妃,到底是梅蘭芳對劇中人的詮釋形塑,還是他想在觀眾面前所呈現的「純淨自我」。
一、前言
本書論京劇的性別與政治,第一章先從乾旦開始,梅蘭芳自是代表。梅蘭芳男扮女妝應無性別認同的尷尬,因為乾旦在戲曲史上早有傳統。
關於乾旦的歷史淵源,曾永義老師早在〈男扮女妝與女扮男妝〉一文中即有考證,張發穎《中國戲班史》、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以及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等都有詳盡討論,近年么書儀有〈明清演劇史上乾旦的興衰〉專文考察。學位論文也有香港陳家威之《清代京劇中之乾旦研究》等。
二、乾旦傳統:男身塑女形
演劇史上男優女優起源都很早,孰先孰後很難考察。《魏書.齊王芳紀》裴注引司馬師廢帝奏中,郭懷、袁信扮「遼東妖婦」,應是男扮女妝最早資料。崔令欽《教坊記.踏搖娘》因有「丈夫著婦人衣」,更可明確視作乾旦。元代家庭戲班居多,男女演員並存,但並無男扮女妝記載,反而多見女扮男妝。也有妓女演劇,往往「旦末雙全」兼扮男女。明代妓女演劇更盛,擅長各行腳色。宣德三年左都御史顧佐奏禁歌妓,席間用孌童小唱及演劇,「孌童妝旦」乃應運而生。不過,女性演劇仍難全面禁止,陸萼庭具體考察出「娼兼優」、「專業女伶」和「私家歌姬」三類崑劇女子演劇。
明代崑劇職業戲班幾乎都是男班組成,私人家班也有全男班,包括童伶小廝和成人優伶兩類,各種行當都由男性扮飾,男演員妝旦已是常態,「豔婉」的姿態和演技已成為崑劇表演史上的亮點。例如申時行家班名張三者,工小旦,嗜酒,「醉時上場,其豔入神,非醉中不能盡其技」,因而贏得「醉張三」美名。飾演《西廂記》的紅娘,「一音一步,居然婉弱女子,魂為之銷。」又如業餘客串男旦的趙必達演杜麗娘,有「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的效果。擅長演《躍鯉記》的男旦柳生,也能「供頓清饒,折旋婉便,稱一時之冠」。
男旦的表演藝術,到了清代一直都是劇場的重要風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可以集秀班旦色金德輝為例,他演《牡丹亭.尋夢》、《療妒羹.題曲》,被讚為「春蠶欲死」,「彷彿江采蘋樓東獨步,冷淡處別饒一種哀絕」。這些伶人精湛技藝影響所及,是劇場文化重藝不重色。金德輝老年登臺仍被稱讚「南部絕調」,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見者都忘其醜」,馬繼美則是「年九十,為小旦,如十五六處子」。
清代滿族入關後整頓女樂,女戲子一再為政府所禁。順治八年清世祖下旨命教坊司停止女樂,改用太監替代。雖然不久後順治十二年宮中又一度使用女樂,但到順治十六年裁革教坊司,不用女樂遂成定制。這項整頓自然波及了戲班,康熙十年禁唱秧歌婦女,康熙四十五年同樣內容的禁令又一次公布,而且更為嚴峻。康熙五十八年,「雖禁止女戲,今戲女有坐車進城遊唱者,名雖戲女,乃於妓女相同,不肖官員人等迷戀,以致罄其產業,亦未可定,應禁止進城。」矛頭對準「名雖戲女」實則與妓女相同的藝妓。直到乾隆朝,仍有「嚴禁秧歌婦女及女戲遊唱」禁令。
在連續性的政令禁止下,私人家樂雖仍有女班,宮廷卻嚴格革除官妓、民間禁止買良為娼,城裡禁止女戲,城外女藝人也一律不准進京。整頓的結果是:京城中少了公開的妓院,戲班子一律成為男班,戲園的觀眾也一律為男性。因此清中葉成形的京劇劇種,在形成初期根本不存在女演員,各腳色行當全部由男演員扮演,劇中女子也由男性扮演,稱為「乾旦」,也叫「男旦」。直到同治末、光緒初,才有女演員「坤伶」登場。起初是「全女班」,民國後還明令禁止男女合演,以免「有傷風化」。一九一七年上海「大世界」遊樂場落成開張,座落在法租界,內有「乾坤大京班」,首先實行男女合演,法租界「共舞臺」廣告,也以男女合演為號召。京劇乾旦代表梅蘭芳,對於在舞臺上以男扮女,應該沒有尷尬不安的心理問題需要調適。如前所述,男扮女並不始於京劇,「乾旦傳統」在戲曲表演史上早已形成,而此傳統更有另一傳統為其奠基,即是戲曲表演程式中的核心關鍵:腳色。傳統戲曲在「演員」和「劇中人」之間,多了「腳色」這一道關卡,演員必須通過「腳色」的扮飾才能轉換成劇中人,人物塑造的流程不是直接由「演員」體驗「劇中人」,而是「演員→腳色→劇中人」。就腳色與演員之間的關係而論,腳色代表演員對於「表演藝術」的專精,必須熟練本行腳色程式化的唱念做打才能進入人物扮演;就腳色和劇中人的關係而言,不同的腳色象徵著不同的「人物類型」,包括性別、身分、性格。
「反串」與演員的性別無關,當以本工的腳色行當為基準,凡是演出不屬於本行腳色應工的戲,即稱之為「反串」,正如方問溪在《梨園話》裡所說:「反其常態,謂之反串」,「如令生飾旦、令旦飾生、淨飾丑而丑飾淨」之類即是。反串是「演員」與「腳色行當」之間的關係,非關「演員」與「劇中人」之性別。本為男性的梅蘭芳演《轅門射戟》的呂布是反串,演楊貴妃反倒是正常的。戲曲表演因妝扮甚濃且唱念做表程式化,所以師父只根據嗓音寬窄、個頭身段等資質條件,分派學生的腳色行當,性別不是分行的重點。因此男扮女並不需要特別的心理調適。在清政府禁女演員的前提下,劇中女子當然只得由男性扮演,這是不得不遵守的社會法規,在此現實條件下,乾旦並不特別。
既然「乾旦」在戲曲界已經成為一項表演以及文化傳統,表演本身自有一套規範程式,因此男性演員在京劇行業裡學習旦角、飾演女性時,並沒有任何性別認同的問題,這些唱旦的男孩子,努力學習旦角身段唱念,使得自己在形體聲音等各方面,都要比女人還女人,於是「貼片子」、「綁蹺」、「線尾子」等等化妝穿戴,都是以修飾男性面容身材為前提,而「小嗓」(假音)的使用,當然更是為了趨近於女子音聲。一心想的,只是如何精準扎實地學習旦角程式化的功夫,如何「男身塑女形」。
但是,觀眾對待乾旦的眼光心態,以及乾旦養成的教育和環境,卻可能在梅蘭芳心理蒙上一層陰影,進而影響他的京劇旦行性格塑造。關於觀眾對待乾旦的態度,「梨園花譜」的研究在學界已然展開,本文集中於乾旦梅蘭芳本人對於自身性別轉換的心理探析。這項研究,先從京崑不同的旦行表演美學說起。
三、她╱他的雅正:梅蘭芳的性別陰影
(一)從風情旖旎到端莊雅正
梅蘭芳首創京劇以旦行掛頭牌之風氣後,京劇女性的形象塑造至今仍以梅派為最高美學標準。而梅蘭芳的女性塑造卻不同於之前的崑劇,崑旦的表演以「風情旖旎、纏綿婉轉」為主要表徵,梅蘭芳卻刻意削弱淡化綽態柔情,轉而以「大方沉著、端莊雅正」為京劇女性形象塑造的美學高標。講究身體的「重度」,強調「剛柔相濟」、「外圓內方」、「藏在內裡的勁兒」,表演追求「大氣」。
崑劇的「正旦」也要求沉著穩重,衣著多為素色褶子,以唱工為重,多扮演受苦而貞烈的中年或青年已婚婦女,與「閨門旦」的「幽約怨悱、纏綿多情」氣質不同。但崑劇最受歡迎的才子佳人戲,女主角以窈窕淑女、大家閨秀或娼門名妓為多,杜麗娘、陳妙常、李亞仙、霍小玉、崔鶯鶯、謝素秋、花魁女等,幾乎成了崑旦代表人物,她們都由閨門旦應工,深掘幽微的曲文,配上悠緩細微的身形挪移、旖旎嫵媚的神色姿態,整體表演「春蠶欲死」。
京崑的「身體」在似與不似間,同為戲曲代表,同具戲曲特質,但二者又有極精微的差異。上海崑劇院名旦張靜嫻曾在演講中提到,她曾向陳正薇老師學過京劇,陳老師在她表演時一路提醒糾正:「穩著點,穩著點,這是京劇!」張靜嫻原擅崑劇正旦兼演閨門旦,纏綿婉媚、顧盼含情,整個「身體」和京劇的大方沉穩不同。雖然張的時代較晚,但陳正薇的提醒,精微地點出了京崑身體表現的不同,可為輔證之例。而二者的不同,並不是行當劃分的不對應。
京劇在「青衣」和「花旦」之間也有另一個介乎其間的行當「花衫」。所謂介於二者之間,是指「兼備青衣表演之擅長(唱工),以及花旦表演之特質(身段靈巧、念白爽利)」,追求的是唱念做表舞蹈身段俱佳,而非整體氣質介於端莊和俏皮之間。「派頭大方」始終是梅派公認的先決條件,而梅派正是京劇旦行代表,「雅正」是梅蘭芳所確立的京劇旦行表演典範。由風情旖旎到端莊雅正,戲曲表演史上女性丰姿的轉變,是梅蘭芳刻意的追求。和「身體」的改變相呼應的,是他對於所飾人物的性格,也精心挑選、嚴加把關,「他」所演的「她們」,絕對不涉情慾。例如他堅持不演性格不貞的東方氏(《虹霓關》),刻意修改腿部身段、沖淡《牡丹亭.驚夢》中杜麗娘的思春情態,更花了一生心思漸次修改《貴妃醉酒》,使其由風情放恣轉化為雍容華貴的代表(詳下文)。對於人物塑造與表演風格,梅蘭芳是自覺自主的整體思考。
筆者認為,梅蘭芳刻意追求女性端莊形象,意在擺脫個人出身於「相公堂子」(稚齡乾旦侑酒陪宴)的陰影。此點筆者在〈梅蘭芳以雅正為女性塑造的內在隱衷〉一文中,曾試圖探析,提出梅蘭芳力求雅正的內在隱衷分為兩點:從大處說,可視為梅蘭芳對外在大環境文化思潮的回應;從個人因素分析,則或與梅蘭芳試圖擺脫相公堂子的出身陰影有關。
(二)以雅正擺脫相公堂子出身陰影
四大徽班進京之後,除了給京師舞臺帶來新劇目、新唱腔、新演員,從而引起了戲曲變革之外,新的娛樂業「打茶圍」(又稱「逛堂子」)也在京城開始盛行,一直流行到清末。關於「打茶圍」(逛堂子),么書儀在《晚清戲曲的變革》一書中有詳細考察:「打茶圍」主要內容是以歌侑酒,是由戲班中年輕的男演員(特別是乾旦)在演出的餘暇從事侍宴、陪酒、唱曲、閒談等應酬的收費行業。營業地點,可以應召前往顧客指定的酒樓飯莊,而大多數是在營業者的「下處」。下處即住處,一般的伶人大夥兒住在一起稱「大下處」,自稱「公中人」;成名的伶人別立下處,稱作「私寓」或「私坊」。伶人各立「堂名」為住處的標誌,自稱「堂名中人」,伶界自己的習慣叫「堂號」。歌郎臺上演戲畢,臺下侑酒作陪,堂子的興盛,事關戲班興盛與伶人走紅。嘉慶以後直到光緒間,堂子與「科班」共存,共同擔當培養藝人的職責。據么書儀統計,晚清戲曲演員,從堂子培養出來的所占比例最大,曲界的名伶,也大多是堂子的主人。「同光十三絕」中,梅巧玲稱景和堂主人,劉趕三為保身堂主人,余紫雲為勝春堂主人,徐小香為岫雲堂主人,時小福為綺春堂主人⋯⋯今人敘其事跡,大多朦朧其事,彷彿如文人之堂號,其實他們實實在在地開著堂子,養著許多立過賣身契的歌郎,這是主人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歌郎被捧紅後,有客人「老斗」為之贖身,則可另立門戶,開設自己的堂子。
梅蘭芳出身於堂子。這段歷史,在戲曲論著中詳略不一,大都已被隱去或「淨化」。么書儀在〈一幀照片的五種說明〉一文中,根據同一張照片不同時期的文字解說(圖說),做出了明確考察:梅蘭芳幼年在「雲和堂」裡學藝,人稱梅郎,為雲和堂「十二金釵」中之人物。堂子在民國以後被禁止,田際雲於民國元年四月十五日遞呈子給北京外城總廳,要求「查禁韓家潭像姑堂子,以重人道」,十二月,外城巡警總廳刊出告示,批准了田際雲的申請。告示中對堂子的定位是「實乖人道」的「藏汙納垢之場」,「玷汙全國,貽笑外邦」;對於堂子裡的歌郎,作了這樣的貶抑譴責:「以媚人為生活,效私娼之行為」、「人格之卑,乃達極點」。從此堂子歌郎成為被歧視和忌諱的字眼。相公堂子出身的藝人,當然不願舊事重提。
「堂子出身」是在梅蘭芳舞臺生涯回顧、傳記、文集以及相關論著中幾乎被抹去的一段歷史,不僅為梅蘭芳著書立傳的作者有意為賢者諱,梅蘭芳本人一定更不願意重提童年往事。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穆辰公所著小說《梅蘭芳》由奉天時報社出版,該書以小說體從梅之出身敘起,幼年為歌郎的生活也化為書中情節。書一出版,愛護梅的馮耿光,立即將書全數收購焚燒銷毀。這段過程被記錄在鄭逸梅的《藝林散葉續編》第一五三條,梅蘭芳及其友人對於自己名譽的維護是這麼刻意謹慎,這麼小心翼翼。
筆者以為,梅蘭芳在所飾女性的性格塑造上有意識地力求端莊雅正,很有可能和這段歷史有關。
梅蘭芳對於所飾角色的性格以及整體戲的風格,都有意識地力求典雅端正,這樣清晰的自覺自主,表現在他邀請文人為自己量身打造新編戲時,也表現在他對傳統老戲的改編、詮釋與定調,最明顯的例子是《貴妃醉酒》。
《貴妃醉酒》原來傳統的演法大致都遵循筱翠花,做表十分細膩,充分發揮腰腿、水袖和蹺工。但梅蘭芳覺得有些地方未免「做過了頭」,甚至人物性格都因此而扭曲了,因此做了明顯的改造。在回憶錄《舞台生活四十年》裡,梅蘭芳特別詳細說明了這段過程。梅氏的這齣戲學自路三寶,也是筱翠花的路數,學全了之後經常演出,但每次演的時候都自我反省,對於做過了頭的部分「陸續加以沖淡」,但仍覺得不夠理想,因而動了「徹底改念白唱詞」的念頭。最後的定本,不僅把原來「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的詞,改為「酒入愁腸人易醉、平白誆駕為何情」;也將酒醉後和高裴二太監輕狂調笑的做表徹底改掉;更將「臥魚」身段深化為「嗅花聞香、醉倒花叢」。一再精修之後,這齣戲成為梅派代表作,取代了原來筱翠花的路數。後來演這戲的後學者,幾乎一面倒地以梅派為依歸。筱派的演法,流傳至今,只能在二○○六年過世的乾旦藝術家陳永玲的演出中窺見端倪。
梅蘭芳對這齣戲的修改歷程很長,根據梅派愛好者齊崧《談梅蘭芳》一書所記,他不僅看過早年梅蘭芳根據筱翠花版本所演的放浪形骸的貴妃,抗戰勝利後,看到的演出都還和最後的定本有一些不同。齊崧曾根據現場觀看的印象和後期的錄音相比,提出「且自由他」的「他」字念法,即有三個階段的不同:最初為大聲念出,在眾宮女面前宣洩自我的不滿;之後採小聲輕念,唯恐眾人窺出她的失意;最後則只化為一聲自憐自傷的喟嘆。齊崧認為一個「他」字的念法,就能夠體現出梅氏藝術的幾個演進階段。這齣戲的修改歷程,幾乎貫穿梅氏一生的演出歷程,早期的修改多半從深刻體會劇中人心情出發,愈到後期,梅派戲中梅氏自我的形象已經愈來愈明晰,劇中貴妃的氣度與梅蘭芳個人的特質已經完全貼合為一了,最後定型的《貴妃醉酒》,堪稱華麗與孤寂的交織。觀眾幾乎很難具體分辨,這樣迥異於最初筱翠花形象的貴妃,到底是梅蘭芳對劇中人的詮釋形塑,還是他想在觀眾面前所呈現的「純淨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