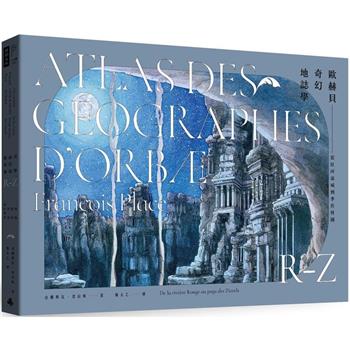塞爾瓦叢林島
——塞爾瓦島僅由一棵樹所形成,這棵樹占地之遼闊,枝葉之繁茂,竟致一木成林。居住於鄰近群島村落裡的年輕人們來到這棵樹上,在一次驚險的狩獵行動中,得到成年考驗之洗禮。
黎明前不久,兩艘獨木舟划向島嶼。它們沿著海岸靜靜滑行,任退潮之海水載到一片紅樹林蔓延的小灣。短槳前方,小小魚兒紛紛彈躍。一隻鱷魚宛如枯木潛伏,身軀扭擺兩三下,倏地游遠。獨木舟在一片沙濱擱淺停下。十二名少年從船上躍下。每個人都帶了一口網袋,套在額前以布條繫攏,裡面裝有幾根香蕉,裹在新鮮蕉葉裡,另外還有芋泥糊和椰果肉。身上唯一的兵刃是一把薄竹刀,插在樹纖編織的腰帶上。
歐皮尤克最年長,由他來開路──縱使他也尚未滿十六歲。他走在前頭,有時捆綁一束樹葉,或折斷一截棕櫚樹枝,這麼做只為一個目的:方便稍後回程時找到原路。整支隊伍,沒有人開口。紅樹林將他們四面八方圍繞,鬚根深搗泥床淤沙,支撐樹幹露出水面。
歐皮尤克試圖找出一條樹徑。他知道,這裡有上百萬條樹根衍生盤結,糾纏不清,他必須找出哪些屬於大樹。因為,這整座島就只是一棵樹,而此樹本身又被千百株其他樹種占據,無數植物在此寄生,往四面八方生長,成為一座空中林園,供數不盡的生物棲息生養。蕨類與棕櫚成叢,苔絲成瀑,藤蔓處處延伸,遍島花團錦簇;觸碰撫摸之間暗藏陷阱:劇毒、勾爪、尖刺,攀爬而上,此起彼落,搖搖欲墜,紛紛滾落,無窮無盡之程度令人難以想像。這棵樹,樹首浮游九霄雲端,底部潛入陰曹地府。這一切,歐皮尤克都知道,一如他的父親與祖先知道得那般清楚。他緩緩前進,半個身子陷在泥濘之中,雙腳在詭譎多變的泥床中尋覓支撐點,雙手被所有能抓的東西刮傷。
一隻手在歐皮尤克肩膀上碰了一下。是波依,與他同一個奶媽哺大的乳弟。波依使了個眼神,望向一截扭曲的樹根,只略比人的手臂粗一些,無數新枝深植鹹海之中,彷彿一隻蜈蚣。少年們半爬半游,朝它前去,抵達之後,一個接著一個,踏上樹徑。那是條不折不扣的險惡艱途,既濕滑又蜿蜒,而且竟然逐漸上升,托拱得愈來愈高,弧度愈來愈大,鑽入岩石之間,撫探鐵樹的掌葉。路徑從樹根變成樹枝。事實上,這棵大樹並沒有主幹,只是朝所有方向無限蔓長,像一條蛇,不斷盤纏扭轉。
歐皮尤克決定停下小歇。於是,在天與水之間某個位置,三條粗枝會合之處,少年們在此聚集。太陽漸高,天氣愈來愈熱。他們的胸口悶塞著一層濕熱的薄霧,汗流浹背,喘不過氣。他們以手勢交談;在這兒,文字不可運用,所有話語都是禁忌。
在他們腳下,霧氣積成厚重的雲,凡膨脹、萌發、滾過之處,一切淹沒;而後拉成一股股濃密的長巾,不由自主地,被樹頂葉叢吸引過去。幾縷雲朵碎片脫落,方短暫洞開,景物只從其中隱約可見。這整股雲霧升騰得好快,少年們動也不敢動,感覺似乎墜入一座逐漸昏暗漆黑的深谷。大滴雨點開始打落在他們身上,雨點由下往上打,愈來愈多,不一會兒功夫就成一片水濛,而他們所在的枝幹剛好用來遮蔽。一道道閃電在他們下方劈開。大樹邊緣被雷擊中,枝葉紛落,發出一股強烈的臭氧味。這陣急驟而至的「逆雨」風暴持續了如此之久,久到樹頂上烈日的熱度已升至當日之巔,但藏身於樹蔭中的他們絲毫未覺。
少年隊繼續樹徑上危機重重的路程。大樹扭曲的枝臂將他們全方位圍繞,漸漸沒入遠方一片淋漓綠意之中,無形無狀,模糊消失。
黃昏竟已驀然降臨,少年們吃了一驚。他們蜷成一團,縮在矛鐵狀的大片樹葉下。到處滴水──隨著黑夜到來,大樹在流淚,滴下白天最炎熱時它噴濺至天空的那淚水。少年互相分享糧食。當暗影擴大,醜惡愈發深沉,會有哪些鬼魅在這裡出沒晃盪呢?一想至此,他們的心都凍涼了。最教他們懼怕的是灌木人。那是一種介於動物與植物之間的生物,全身布滿苔絲粗纖,平時懸掛在樹枝上生活,一聞到人的氣味,就一聲不響,慢慢接近獵物,令人絲毫無法察覺;到了深夜,趁著睡夢,將人悶死。接著,以唾涎包成人繭,等屍肉腐化爛透之後吸食。
沒有人敢真的睡著。蝙蝠在他們營地周圍嘎吱飛繞。黑暗之中,光芒一點一點亮起,彷彿星星排列星座,卻是一道道銳利的目光閃爍。大樹中迴盪起各種嚎叫,或神祕如謎,或悲傷悽涼,鴉鳴聒聒、窸窸窣窣、歇斯底里的狂笑、粗魯野蠻的嗝聲,構成一片刺耳難聽的合唱。還有,來自幽暗最深處,宛如遠方雷鳴隱隱轟隆,不時傳來的塞爾瓦飛虎的低聲咆叫,驚嚇所致的寧靜猛然湧現,劃破混合於黑夜中一團千百雜響。
一隻蜂鳥帶來吉兆,宣告太陽升起,讓少年們從黑夜之恐怖解脫。他們伸展四肢,活動慵懶的筋骨;忍住不打呵欠,以免四處晃盪的鬼魅趁機闖入。不過,納烏埃突然緊張起來,急忙用手捂住張開的大嘴。他剛才瞥見,就在那兒,一個灌木人走遠,像隻蒼老又疲憊的猿猴,緩緩消失在薄霧之中。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只要那傢伙看他一眼,他的靈魂就將失去:魂魄將永遠被囚禁在這座島上。
他們共享早餐,存糧又減少了些。周遭並不缺乏食物──各式各樣的水果、可食性植物,以及一點也不可怕的獵物可充當野味,但他們卻都被禁止取用。歐皮尤克和波依之間起了一番短暫的爭論,兩人比劃著手勢,想判定昨晚聽到的飛虎吼聲從哪裡發出。最後總算協議出要走的方向。他們朝樹頂走了一整天,在和前日同樣的時刻,再次讓暴雨淋個濕透。雨停後不久,他們終於發現了登島以來初見的響藤群,於是每個人都拿出小刀,找一條最適合自己的,一刀砍下,然後纏在肩膀上。在他們周圍的藤條拚命鞭抽、鳴響、蛇狀扭轉。現在,飛虎已經知道他們來了。他們艱辛地繼續向上爬升之考驗,幾乎能夠感受到飛虎的魂魄緊盯著他們,無法預測、殺氣騰騰、無所不在。
歐皮尤克停下了腳步。他仔細觀察他們剛才經過的地方良久。光線從葉縫中穿透進來,無論哪一個方向,視線都很明朗,不至於受突來事物驚嚇。許多枝幹騰空竄伸,各枝之間還算靠近,或許能從這枝跳到那枝;不過,洞隙仍嫌大了些,要在空中飛躍而過並不容易。這裡正是他們等待飛虎的最佳所在。男孩們分頭散開,各據一方,彼此之間調整到大約相等的距離。每個少年的雙臂、雙腿及上半身都纏上樹纖織布,然後將響藤的一端繫在腳踝上,另一端綁在自己足下的粗幹上。歐皮尤克和波依,最年長的兩名,面對面站著,聽得見彼此的聲音,中間卻隔有萬丈之深。
於是,他們呼叫飛虎。
他們開始對牠說話,先用非常小的聲音,諷刺嘲笑:「沒牙沒爪的老公公,氣喘吁吁的老頭。」接著稍微提高音量:「臭老頭,全身斑點小心眼,老鳥一隻掉出窩,又老又硬咬不動。」不過並未引起任何反應;於是他們使出全力叫嚷,扯開嗓子大吼:「沼澤裡的臭老貓,箭頭磨鈍失靈光,閒來無用守跳蚤,蛤蟆群中稱大王,無所事事愛扒糞……」
好大一陣咆哮應聲響起,而幾乎就在同一瞬間,一個形影從葉叢中躍出,直接撲向年紀最小的獵者歐伊普。眼看就要被抓,他只來得及往下跳,這才躲開猛獸攻擊;即使如此,從肩膀到腰間仍被撩出一道長痕。腳上的藤條拉住了他,在他墜地之前猛力晃動縮扯,發出響聲,朝上捲起。同一時間,阿多阿迪和塔爾朝飛虎彈跳追去,那猛獸則張開寬膜雙翼,繼續滑翔飛行,藉此轉移其他少年同伴的注意,同時少年們正懸空攀爬,就距飛虎躍出之處不遠。阿多阿迪發出勝利喊聲,他的雙手碰到了猛獸的毛皮。飛虎一百八十度大迴轉,發出怒吼。杜爾、波勒和尼力亞也身手不凡,展現空躍本領,盡量靠近那頭飛獸,波勒甚至非常幸運地被銳利的尖爪刺中。另外兩名少年足纏藤纜,單腳旋轉,從空中快速趕來。飛虎變換滑翔方向,對付這些新目標,他們竟敢對牠又喊又叫,不把牠當一回事。牠跳上一枝樹幹,再跳上另一枝,接著奮力一躍,又高又遠,然而,背部卻被一個人撞上,令牠不得不再度改變飛行路線。牠迴轉身軀,出其不意地猛烈一抓,撕傷羅埃克的大腿。而尼歐瑪則已做好準備,隨時就要跳下。
飛虎似乎已經明白遊戲規則。現在,少年們必須提升技巧,加倍靈活,才能拂掠到牠的皮毛,並且不致受太嚴重的抓傷。圍繞猛獸的圈子愈舞愈小。他們驍勇過人,在空中縱身飛躍,一次又一次驚險萬分地從高處躍下,凌空交會,就在距離野獸獠牙利爪兩指之處,展現各式招數與翻滾流線,相互較勁。同時,隨著少年們的律動,繫在他們身上的響藤也時而縮彈,時而滾捲,時而拉長。至於飛虎,牠已初步平息怒氣,不輕舉妄動,故意避開他們,並等候出手時機;減少跳躍,抑制猛衝,偶爾在最後一刻揮劃一爪,在離牠最近的耍猴戲跳躍者身上留下印記。牠決定不發動致命攻擊,或許好奇地想看看,這些氣味淡乏的鳥人究竟能瘋狂到什麼地步。不過,他們的氣息與牠的混合在一起,而且他們皮肉光滑,傷口淌著鮮血,這一切又勾撓著牠的食欲。牠有些衝動,思緒翻攪、嘈雜、混亂,卻依舊能平穩操控,長距離滑翔,並隨時隨處跳躍。要在起飛之前擒住一、兩個小人,對牠來說,其實易如反掌,但若要大開殺戒,牠想在空中進行。
受害者就是納烏埃。由於清晨所見之景象,小少年一直有種預感,覺得自己末日將至。在薄霧中瞥見的那個灌木人,趁他受到驚嚇時,就已從他張大的嘴巴深處偷走了他的靈魂。因為這個緣故,現在的他恍恍惚惚,人在心不在。猛虎在飛行中擄獲納烏埃,尖爪插入少年的後頸。這一擊力道猛烈,牽繫納烏埃的藤條啪啦扯斷。歐皮尤克和波依立即跳到猛獸背上,但即使小刀深刺兩肋,牠仍不肯鬆手放開。響藤繃得太緊,一陣激烈晃盪,將兩名小獵人突然往後拉扯,飛虎於是趁機擺脫這些煩人的傢伙。
在較低的地方停下,飛虎逐漸調節平復,同時確保獵物到手。接著,牠再度起飛騰躍,帶著戰利品,準備回洞穴飽餐一頓。
歐皮尤克割下納烏埃剩下的藤條,捲收妥當,放進自己的網袋。少年們將傷口繃纏起來。他們為陣亡的伙伴納烏埃歌唱了一整晚。不過,隔日一大清早,回程的路上,失去伙伴一事幾乎不再讓他們沉痛哀傷。他們輕快迅速地爬下樹,對傷口感到驕傲,賣弄靈活的身手,克服樹徑上各種障礙:彈躍、滑溜、跳高,一點也不怕可能隨時墜落,從此揮別人世。他們歡笑著度過半日暴風雨,在天黑之前回到獨木舟上。(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