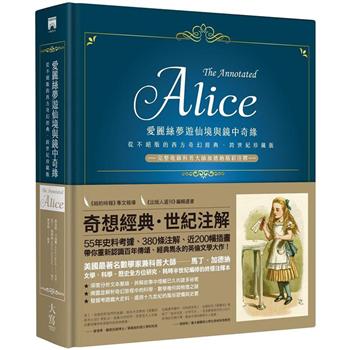本書導讀
/馬克.伯斯坦(北美路易斯.卡洛爾學會前任會長)
根據美學判斷的傳統,當我們在提出任何主張時,總是會加上「可以說是」或者類似的保守措詞。但是,我很懷疑有人會不同意以下我直接斷言的一句話:「自從卡洛爾的兩本經典小說分別於1865年(到66年)與1872年問世以來,最重要的版本莫過於馬丁.加德納於1960年推出的《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
儘管加德納並非第一個在書裡面使用注腳、尾注與頁邊附注等文本批判工具的人,但是在他規劃出來的小說文本格式、進行的廣泛研究、敏銳判斷與寬厚評論,多少年來為許許多多讀者提供了小說的脈絡、參照比較、替代選擇、文本解釋,為此獲得樂趣的與洞見的讀者群真是前所未有的廣泛。極其偶然的,許多人有樣學樣,也開始為其他經典文學作品進行類似的注釋工作。
現在的學生很難,甚或不可能想像得到五十年前的人是怎樣做研究的。那是一個還沒有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年代,也沒有網際網路、維基百科,沒有谷歌搜尋引擎與圖書服務,更沒有電子郵件與社群網站。當時只有圖書館、大學與紙本信件。就連研究卡洛爾的人,也是要等到莫頓.柯亨與羅傑.葛林編的信件集於1978年問世,才接觸得到他的信件;至於在日記方面,更是要等到愛德華.威克林(Edward Wakeling)編的十冊卡洛爾日記全集於2007年問世,才得以窺見他日記之全貌。在那個時候沒有雅俗共賞的卡洛爾研究雜誌,《卡洛爾學刊》與《騎士信件》的創刊都是後來的事(分別於1969與1974年創刊,到目前仍在出刊),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路易斯.卡洛爾學會的存在。加德納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是以紙本郵件的方式進行,偶爾直接打電話。儘管當時還沒有「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一詞,但那已經是他一貫的作業模式,而且每當與他通信的人提供觀點、資訊或有趣的理論,得以讓他深入研究時,他也都不吝於公開表彰他們的功勞。
接任北美路易斯.卡洛爾學會會刊《騎士信件》編輯一職的幾年後,我在1997年秋天接獲馬丁的來信,當時我實在很興奮。他的信件措詞總是如此溫和有禮,習慣以打字機寫信,在需要畫底線的地方親筆畫上,必須修改之處也用鋼筆改寫。我們的雜誌曾經刊出他的幾封信件,多年來我們倆始終斷斷續續地通信,後來到了2005年5月我收到一封裝在牛皮紙信封裡的信件。裡面的信是這樣開頭的:「親愛的馬克,信封裡的文件適合由《騎士信件》刊登嗎?」那一份文件的標題是「《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補遺」(A Supplement to Annotated Alice),是十四頁包含全新與修正注釋的打字稿,再度證明卡洛爾始終縈繞於他的心頭。「適合嗎?」當然,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把那一批稿件刊登在第七十五期《騎士信件》(2005年夏季號)上面,隨後他很快地又寄了另一批稿件給我,後來也刊登在下一期會刊中(2006年春季號)。儘管這兩批稿件是加德納生前最後一次讓自己的注釋被刊登出來,不過他未曾停止研究工作。馬丁.加德納於2010年去世後,他的兒子吉姆又給了我一些影印稿,其中有些注釋是他用潦草筆跡寫下的,也有用打字的。加德納在二十一世紀撰寫了許多注釋,有些曾被刊登過,有些沒有,但全都被收錄在這本書裡,構成它與先前版本的不同之處。
本會認為,最能紀念他的方式,莫過於把一本有料的書獻給他,於是我促成了《獻花給園丁:馬丁.加德納紀念文集》在2011年問世,書中除了有許多追憶專文、一篇小傳、一個參考書目,還有由道格拉斯.霍夫史塔特(Douglas Hofstadter)、莫頓.柯亨、大衛.辛麥斯特(David Singmaster)與麥可.赫恩等才智之士寫的紀念專文。
加德納與學術界
愛德華.顧里亞諾博士是本會創會會員之一兼前任會長,目前擔任美國紐約理工學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院長一職,他也幫上述紀念文集寫了一篇文章。文中他提及加德納對於大學學界造成的影響時,是這麼說的:因果關係是很難捉摸的,但如今路易斯.卡洛爾與他的(這兩本)「愛麗絲」系列小說之所以在學界與全球文化圈那麼受到歡迎與普遍被人接受,馬丁.加德納可說居功厥偉。……在加德納出現之前,卡洛爾並非受到大學認可的作家與研究主題。他並不會出現在書單上。沒有人會在正式的研討會上發表有關於他的論文。……卡洛爾死後,依循著其他知名的慣例,許多關於他的傳記、信件、參考書目等東西開始如同雨後春筍般問世。
但一直要等到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於1935年把〈愛麗絲夢遊仙境:愛麗絲即作者〉(The Child as Swain)一文放進他的論文集《田園詩的幾種版本》(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裡面,卡洛爾才算是初次出現在重要學術著作裡。接下來則是1952年,伊麗莎白.塞維爾(Elizabeth Sewell)那一本迄今仍然令人費解的《荒謬的原野》(The Field of Nonsense)。菲麗絲.葛林艾克則是在1955年推出了一本關於史威夫特(Swift)與卡洛爾的半傳記式心理分析研究。但是,在卡洛爾受到忽略的普遍現象中,上述作品只是稍具能見度的例外而已。
在卡洛爾逝世後的六十年之間,的確有其他出色論文問世,但是學界或文學批評界對他的興趣與評論並未持續出現,這一點是如今我們很難想像的。無論是1964年的初版,或1978年的第二版《維多利亞小說研究指南》(Victorian Fiction: A Guide to Research)裡面,都沒有把卡洛爾放進去。然而,到了1980年,學界對於卡洛爾的興趣已經輕易地超過某些最令人尊敬的維多利亞時代作家。
馬丁.加德納對我們的貢獻,是為卡洛爾的愛麗絲系列小說開拓出一個廣大的世界,而且就某方面而言向我們說明了「兒童文學」這個分類的不可行,因為「童書」是一種過於簡化的稱呼。事實上,即便是大人也能從書裡獲得有意義的洞見與樂趣。他帶我們認識一部小說藝術之作,讓我們有更多體悟、收穫與樂趣,能夠好好欣賞其中許多與遊戲、邏輯、語言有關的故事元素,還有喜劇風格。
他揭露了書中許多大人也關切的主題,還有與世人普遍相關的東西。
就這樣,卡洛爾才會在當今學界佔有穩固的一席之地。……對我而言,卡洛爾的研究之所以會崛起,並且獲得接受,全都是因為馬丁充滿好奇心,品味與興趣極其折衷而廣博,才有《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的問世。
關於《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緣:從不絕版的西方奇幻經典.跨世紀珍藏版》
《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就像總是可以刮去重寫的羊皮紙。只要有機會推出新的版本,加德納就會增加新注釋或更新舊注釋。自從《最終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於1999年問世後,加德納又新增或更新了一百多個囊括了新研究結果與觀念的注釋,全都放進了你手上拿的這本書裡面。書中還有一百張新的插畫(所謂新插畫,並非未曾問世,而是從沒出現在先前加德納編的那幾本書裡)或圖畫,有些能讓我們更瞭解這兩本「愛麗絲」系列小說,有些則是深具代表性,其問世時間從1887年,也就是從初次有田尼爾以外的畫家幫這系列小說畫插畫開始,直到現在。除了將「主要參考書目」、「各國路易斯.卡洛爾學會簡介」與「『愛麗絲』系列小說改編之影視作品清單」等三大附錄予以更新之外,本書也新增了一篇「插畫家簡介」。
《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裡的文字取材於卡洛爾生前問世的最後一個版本(也就是麥克米倫出版社於1897年推出的版本,通稱「八萬六千版」),無論卡洛爾本人或者他的研究者,都普遍認為那是最可靠與正確的版本,而且裡面也保留了卡洛爾本來就使用的「ca’n’t」與「sha’n’t」等等拼字方式,還有特別的標點符號與連字號用法。
1985年,達爾吉爾兄弟(Brothers Dalziel)為田尼爾的插畫製作的原版版畫,在某個銀行的地窖裡被人發現,這本書裡收錄的田尼爾插畫就是使用那一批原版版畫重製的。在把其他插畫作品予以數位化的時候,只要可能的話,我們都會採用原畫,否則就會從收錄那些插畫的書裡面取材。因為曾以愛麗絲為題材創作的畫家成千上萬(其中有些曾刊登在書裡面,有些未曾),任誰都能想像那種篩選工作的難度有多驚人。我希望各位能認同我們的篩選結果,而我們在篩選時所根據的,是以多樣性的原則還有是否能忠於原文,最重要的仍是原創性。
這本書也收錄了加德納為前面三個版本寫的導讀,另一個導讀則是他為了自己刊登在《騎士信件》上面的注釋寫的。此外,我們也把卡洛爾在世時為了這兩本「愛麗絲」系列小說寫的各種傳單、廣告的文字,還有小說前面或後面的介紹文都收錄了進來。
2013年冬天,馬丁的兒子吉姆要我承擔起這一本書的文編與美編工作,最後我要用短短的一句話來表達當時我五味雜陳的心情。除了深感榮耀之外,同時我也深怕自己不能勝任之餘,卻也感到興奮無比,因為自己有機會參與編務而激動不已。
/馬克.伯斯坦(北美路易斯.卡洛爾學會前任會長)
根據美學判斷的傳統,當我們在提出任何主張時,總是會加上「可以說是」或者類似的保守措詞。但是,我很懷疑有人會不同意以下我直接斷言的一句話:「自從卡洛爾的兩本經典小說分別於1865年(到66年)與1872年問世以來,最重要的版本莫過於馬丁.加德納於1960年推出的《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
儘管加德納並非第一個在書裡面使用注腳、尾注與頁邊附注等文本批判工具的人,但是在他規劃出來的小說文本格式、進行的廣泛研究、敏銳判斷與寬厚評論,多少年來為許許多多讀者提供了小說的脈絡、參照比較、替代選擇、文本解釋,為此獲得樂趣的與洞見的讀者群真是前所未有的廣泛。極其偶然的,許多人有樣學樣,也開始為其他經典文學作品進行類似的注釋工作。
現在的學生很難,甚或不可能想像得到五十年前的人是怎樣做研究的。那是一個還沒有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年代,也沒有網際網路、維基百科,沒有谷歌搜尋引擎與圖書服務,更沒有電子郵件與社群網站。當時只有圖書館、大學與紙本信件。就連研究卡洛爾的人,也是要等到莫頓.柯亨與羅傑.葛林編的信件集於1978年問世,才接觸得到他的信件;至於在日記方面,更是要等到愛德華.威克林(Edward Wakeling)編的十冊卡洛爾日記全集於2007年問世,才得以窺見他日記之全貌。在那個時候沒有雅俗共賞的卡洛爾研究雜誌,《卡洛爾學刊》與《騎士信件》的創刊都是後來的事(分別於1969與1974年創刊,到目前仍在出刊),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路易斯.卡洛爾學會的存在。加德納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是以紙本郵件的方式進行,偶爾直接打電話。儘管當時還沒有「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一詞,但那已經是他一貫的作業模式,而且每當與他通信的人提供觀點、資訊或有趣的理論,得以讓他深入研究時,他也都不吝於公開表彰他們的功勞。
接任北美路易斯.卡洛爾學會會刊《騎士信件》編輯一職的幾年後,我在1997年秋天接獲馬丁的來信,當時我實在很興奮。他的信件措詞總是如此溫和有禮,習慣以打字機寫信,在需要畫底線的地方親筆畫上,必須修改之處也用鋼筆改寫。我們的雜誌曾經刊出他的幾封信件,多年來我們倆始終斷斷續續地通信,後來到了2005年5月我收到一封裝在牛皮紙信封裡的信件。裡面的信是這樣開頭的:「親愛的馬克,信封裡的文件適合由《騎士信件》刊登嗎?」那一份文件的標題是「《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補遺」(A Supplement to Annotated Alice),是十四頁包含全新與修正注釋的打字稿,再度證明卡洛爾始終縈繞於他的心頭。「適合嗎?」當然,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把那一批稿件刊登在第七十五期《騎士信件》(2005年夏季號)上面,隨後他很快地又寄了另一批稿件給我,後來也刊登在下一期會刊中(2006年春季號)。儘管這兩批稿件是加德納生前最後一次讓自己的注釋被刊登出來,不過他未曾停止研究工作。馬丁.加德納於2010年去世後,他的兒子吉姆又給了我一些影印稿,其中有些注釋是他用潦草筆跡寫下的,也有用打字的。加德納在二十一世紀撰寫了許多注釋,有些曾被刊登過,有些沒有,但全都被收錄在這本書裡,構成它與先前版本的不同之處。
本會認為,最能紀念他的方式,莫過於把一本有料的書獻給他,於是我促成了《獻花給園丁:馬丁.加德納紀念文集》在2011年問世,書中除了有許多追憶專文、一篇小傳、一個參考書目,還有由道格拉斯.霍夫史塔特(Douglas Hofstadter)、莫頓.柯亨、大衛.辛麥斯特(David Singmaster)與麥可.赫恩等才智之士寫的紀念專文。
加德納與學術界
愛德華.顧里亞諾博士是本會創會會員之一兼前任會長,目前擔任美國紐約理工學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院長一職,他也幫上述紀念文集寫了一篇文章。文中他提及加德納對於大學學界造成的影響時,是這麼說的:因果關係是很難捉摸的,但如今路易斯.卡洛爾與他的(這兩本)「愛麗絲」系列小說之所以在學界與全球文化圈那麼受到歡迎與普遍被人接受,馬丁.加德納可說居功厥偉。……在加德納出現之前,卡洛爾並非受到大學認可的作家與研究主題。他並不會出現在書單上。沒有人會在正式的研討會上發表有關於他的論文。……卡洛爾死後,依循著其他知名的慣例,許多關於他的傳記、信件、參考書目等東西開始如同雨後春筍般問世。
但一直要等到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於1935年把〈愛麗絲夢遊仙境:愛麗絲即作者〉(The Child as Swain)一文放進他的論文集《田園詩的幾種版本》(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裡面,卡洛爾才算是初次出現在重要學術著作裡。接下來則是1952年,伊麗莎白.塞維爾(Elizabeth Sewell)那一本迄今仍然令人費解的《荒謬的原野》(The Field of Nonsense)。菲麗絲.葛林艾克則是在1955年推出了一本關於史威夫特(Swift)與卡洛爾的半傳記式心理分析研究。但是,在卡洛爾受到忽略的普遍現象中,上述作品只是稍具能見度的例外而已。
在卡洛爾逝世後的六十年之間,的確有其他出色論文問世,但是學界或文學批評界對他的興趣與評論並未持續出現,這一點是如今我們很難想像的。無論是1964年的初版,或1978年的第二版《維多利亞小說研究指南》(Victorian Fiction: A Guide to Research)裡面,都沒有把卡洛爾放進去。然而,到了1980年,學界對於卡洛爾的興趣已經輕易地超過某些最令人尊敬的維多利亞時代作家。
馬丁.加德納對我們的貢獻,是為卡洛爾的愛麗絲系列小說開拓出一個廣大的世界,而且就某方面而言向我們說明了「兒童文學」這個分類的不可行,因為「童書」是一種過於簡化的稱呼。事實上,即便是大人也能從書裡獲得有意義的洞見與樂趣。他帶我們認識一部小說藝術之作,讓我們有更多體悟、收穫與樂趣,能夠好好欣賞其中許多與遊戲、邏輯、語言有關的故事元素,還有喜劇風格。
他揭露了書中許多大人也關切的主題,還有與世人普遍相關的東西。
就這樣,卡洛爾才會在當今學界佔有穩固的一席之地。……對我而言,卡洛爾的研究之所以會崛起,並且獲得接受,全都是因為馬丁充滿好奇心,品味與興趣極其折衷而廣博,才有《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的問世。
關於《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緣:從不絕版的西方奇幻經典.跨世紀珍藏版》
《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就像總是可以刮去重寫的羊皮紙。只要有機會推出新的版本,加德納就會增加新注釋或更新舊注釋。自從《最終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於1999年問世後,加德納又新增或更新了一百多個囊括了新研究結果與觀念的注釋,全都放進了你手上拿的這本書裡面。書中還有一百張新的插畫(所謂新插畫,並非未曾問世,而是從沒出現在先前加德納編的那幾本書裡)或圖畫,有些能讓我們更瞭解這兩本「愛麗絲」系列小說,有些則是深具代表性,其問世時間從1887年,也就是從初次有田尼爾以外的畫家幫這系列小說畫插畫開始,直到現在。除了將「主要參考書目」、「各國路易斯.卡洛爾學會簡介」與「『愛麗絲』系列小說改編之影視作品清單」等三大附錄予以更新之外,本書也新增了一篇「插畫家簡介」。
《注釋版:愛麗絲系列小說》裡的文字取材於卡洛爾生前問世的最後一個版本(也就是麥克米倫出版社於1897年推出的版本,通稱「八萬六千版」),無論卡洛爾本人或者他的研究者,都普遍認為那是最可靠與正確的版本,而且裡面也保留了卡洛爾本來就使用的「ca’n’t」與「sha’n’t」等等拼字方式,還有特別的標點符號與連字號用法。
1985年,達爾吉爾兄弟(Brothers Dalziel)為田尼爾的插畫製作的原版版畫,在某個銀行的地窖裡被人發現,這本書裡收錄的田尼爾插畫就是使用那一批原版版畫重製的。在把其他插畫作品予以數位化的時候,只要可能的話,我們都會採用原畫,否則就會從收錄那些插畫的書裡面取材。因為曾以愛麗絲為題材創作的畫家成千上萬(其中有些曾刊登在書裡面,有些未曾),任誰都能想像那種篩選工作的難度有多驚人。我希望各位能認同我們的篩選結果,而我們在篩選時所根據的,是以多樣性的原則還有是否能忠於原文,最重要的仍是原創性。
這本書也收錄了加德納為前面三個版本寫的導讀,另一個導讀則是他為了自己刊登在《騎士信件》上面的注釋寫的。此外,我們也把卡洛爾在世時為了這兩本「愛麗絲」系列小說寫的各種傳單、廣告的文字,還有小說前面或後面的介紹文都收錄了進來。
2013年冬天,馬丁的兒子吉姆要我承擔起這一本書的文編與美編工作,最後我要用短短的一句話來表達當時我五味雜陳的心情。除了深感榮耀之外,同時我也深怕自己不能勝任之餘,卻也感到興奮無比,因為自己有機會參與編務而激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