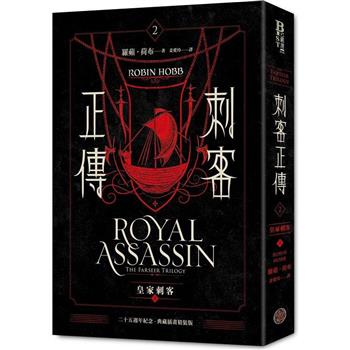我停頓片刻清洗我的筆。我的字跡在粗糙的紙上,從蜘蛛網般的綿密,變成混亂的一片迷濛。我不會將這些字句寫在上好的羊皮紙上,只因時機未到,而且我並不確定是否應該寫下這些。我自問:為什麼要寫下這些?如果把這知識用口耳相傳的方式傳給有資格傳承的人豈不更好?也許是,也許不是。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這些知識,對我們的後代來說可能是個謎。
有關魔法的文獻少之又少。我費盡心力從拼湊的資訊中尋找知識的蛛絲馬跡,找到了散亂的參考文獻和不經意的暗示,但僅止於此。我總想將過去幾年收集而來、並儲存在腦海中的相關訊息寫在紙上;我將寫下自身體驗和查明真相後所獲得的知識。或許,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為其他像我一樣深受內心魔法交戰所害的傻子提供解答。
但是,當我坐下來準備動筆時,卻遲疑了。我有什麼資格執意違抗先人的智慧?我應該平鋪直敘擁有原智的人是如何拓展能力,或讓自己和動物有所牽繫?還是應該詳述成為精技使用者應必備的種種訓練?我從未擁有鄉野術法和傳說中的魔法,所以我有什麼權利把挖掘出來的祕密,像眾多供研究的蝴蝶和樹葉標本般固定在紙上?
我試著思索該如何處理這類取之無道的知識,也納悶自己從這知識中得到了什麼。權勢、財富,還是女性的愛情?我不禁嘲笑自己,因為精技和原智都沒讓我得到這些。就算有,我無意、也無野心將之據為己有。
權勢。我從來不因為喜歡權勢而想要得到它。有時當我遭禁錮,或當親近我的人被利慾薰心的權勢濫用者迫害時,我會渴望權勢。財富。我從未認真思考過。自從我這個私生孫子對黠謀國王立誓之後,他總會確保滿足我所有的需求。我吃得飽,也受了不少教育,擁有簡便和時髦到惱人的服飾,還有足夠的零用錢可花,而在公鹿堡長大也讓我擁有比大多數男孩更充裕的財富。愛?我的馬兒煤灰用牠自己溫柔的方式喜歡我,獵犬大鼻子對我的忠心也至死不渝,而一隻小狗對我狂熱的愛,或許就讓牠賠上性命。因此,我不敢去想為了愛我所要付出的代價。
我在陰謀和成串的祕密中成長,總帶著特有的寂寞和孤立,以至於無法全然相信別人。我不能追隨宮廷文書費德倫,雖然他不斷稱讚我俐落的字跡和著墨完美的插畫,我卻無法透露自己皇家刺客的學徒身分。我也不能對我的外交策略兼刺客師傅切德洩露我是如何熬過精技師傅蓋倫的種種殘酷暴行,更不敢公開談論我對古老的野獸魔法原智油然而生的興致,只因使用它的人將招致墮落和腐敗。
甚至不能告訴莫莉。
莫莉是個珍寶,也是個真正的避難所。她和我的日常生活完全無關;不單因為她是女性,雖然性別差異對我來說仍是個謎。我幾乎在男人堆裡成長,不但失去雙親,也沒有任何一位血親公開與我相認。粗魯的馬廄總管博瑞屈曾是我父親的得力助手,並在我的童年時期照顧我,而馬夫和侍衛也天天陪著我。當時就有女性侍衛,雖然人數沒有現在多,但如同她們的男性同袍一般,女性侍衛也必須執行勤務,也得在不執行看守勤務時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和家庭,因此我不能占據她們的時間。我沒有親生的母親、姊妹或姑姨,也從來沒有任何女性用她們特有的溫柔對待我。
只有莫莉例外。
她比我年長一歲或兩歲,如同小小的樹枝衝破鵝卵石缺口般成長。不論是她父親慣常的酩酊大醉和凶暴殘酷,或是一個孩子為了粉飾太平所需做的表面工夫,都無法擊垮她。當我初次遇到她的時候,她就像初生狐狸般充滿野性和機警,而街頭的孩子們都叫她莫莉.小花臉。她身上常帶著被父親鞭打的傷痕,但不論父親多麼凶暴,她依然照顧他,我卻從來無法理解。甚至當她步履蹣跚地扶著酒醉的父親回家就寢時,都能承受他的牢騷和嚴厲指責。當他醒來之後,對前一晚的酩酊大醉和嚴酷指責可從不後悔,卻只會變本加厲地咒罵,例如為什麼蠟燭店沒人打掃,也沒人把新鮮的藥草鋪灑在地板上?為什麼她不去照顧幾乎快沒蜂蜜可賣的蜂窩?為什麼她讓燒牛油鍋的爐火燃燒殆盡?我沉默地目睹這一幕幕情景已太多次了。
但是,莫莉還是在艱困中成長。她像花一般地綻放,忽然就在某年夏季成為一個小女人,而她的精明幹練和女性魅力也使我敬畏。當我們四目相對的時候,我的舌頭猶如皮革般僵在嘴裡動彈不得,根本說不出話來,但我想她完全不知道這檔事。就算我擁有魔法、精技或原智,但當我們的手不經意碰觸時,我的內心依然產生悸動,而當她微笑的時候,我也仍感受一股難言的尷尬。
我應該將她髮絲隨風飄揚的丰采記錄下來,或詳述她的雙眼如何因心情由深琥珀色變成濃棕色,還有長外衣的顏色?當我在市場的人群中瞥見她那緋紅裙子和紅披肩時,就突然忘了其他人的存在。這是我親眼目睹的魔法,儘管我可能會寫下來,但不會有人能夠像她這樣自如的運用這種魔法。
我該如何追求她?帶著男孩笨拙的殷勤,像呆子盯著戲班的旋轉盤子般追求她?她比我早知道我愛著她,雖然我比她年幼幾歲,她依然讓我而非鎮上其他較稱頭的男孩追求她。她認為我是文書的雜工和馬廄的兼差助手,以及公鹿堡裡的跑腿。她從未懷疑我是讓駿騎王子無法繼承王位的私生子,光那檔事就是個天大的祕密了。對於我的魔法和其他專業,她也一無所知。
或許這正是我能愛她的原因。
這也正是我失去她的原因。
有關魔法的文獻少之又少。我費盡心力從拼湊的資訊中尋找知識的蛛絲馬跡,找到了散亂的參考文獻和不經意的暗示,但僅止於此。我總想將過去幾年收集而來、並儲存在腦海中的相關訊息寫在紙上;我將寫下自身體驗和查明真相後所獲得的知識。或許,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為其他像我一樣深受內心魔法交戰所害的傻子提供解答。
但是,當我坐下來準備動筆時,卻遲疑了。我有什麼資格執意違抗先人的智慧?我應該平鋪直敘擁有原智的人是如何拓展能力,或讓自己和動物有所牽繫?還是應該詳述成為精技使用者應必備的種種訓練?我從未擁有鄉野術法和傳說中的魔法,所以我有什麼權利把挖掘出來的祕密,像眾多供研究的蝴蝶和樹葉標本般固定在紙上?
我試著思索該如何處理這類取之無道的知識,也納悶自己從這知識中得到了什麼。權勢、財富,還是女性的愛情?我不禁嘲笑自己,因為精技和原智都沒讓我得到這些。就算有,我無意、也無野心將之據為己有。
權勢。我從來不因為喜歡權勢而想要得到它。有時當我遭禁錮,或當親近我的人被利慾薰心的權勢濫用者迫害時,我會渴望權勢。財富。我從未認真思考過。自從我這個私生孫子對黠謀國王立誓之後,他總會確保滿足我所有的需求。我吃得飽,也受了不少教育,擁有簡便和時髦到惱人的服飾,還有足夠的零用錢可花,而在公鹿堡長大也讓我擁有比大多數男孩更充裕的財富。愛?我的馬兒煤灰用牠自己溫柔的方式喜歡我,獵犬大鼻子對我的忠心也至死不渝,而一隻小狗對我狂熱的愛,或許就讓牠賠上性命。因此,我不敢去想為了愛我所要付出的代價。
我在陰謀和成串的祕密中成長,總帶著特有的寂寞和孤立,以至於無法全然相信別人。我不能追隨宮廷文書費德倫,雖然他不斷稱讚我俐落的字跡和著墨完美的插畫,我卻無法透露自己皇家刺客的學徒身分。我也不能對我的外交策略兼刺客師傅切德洩露我是如何熬過精技師傅蓋倫的種種殘酷暴行,更不敢公開談論我對古老的野獸魔法原智油然而生的興致,只因使用它的人將招致墮落和腐敗。
甚至不能告訴莫莉。
莫莉是個珍寶,也是個真正的避難所。她和我的日常生活完全無關;不單因為她是女性,雖然性別差異對我來說仍是個謎。我幾乎在男人堆裡成長,不但失去雙親,也沒有任何一位血親公開與我相認。粗魯的馬廄總管博瑞屈曾是我父親的得力助手,並在我的童年時期照顧我,而馬夫和侍衛也天天陪著我。當時就有女性侍衛,雖然人數沒有現在多,但如同她們的男性同袍一般,女性侍衛也必須執行勤務,也得在不執行看守勤務時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和家庭,因此我不能占據她們的時間。我沒有親生的母親、姊妹或姑姨,也從來沒有任何女性用她們特有的溫柔對待我。
只有莫莉例外。
她比我年長一歲或兩歲,如同小小的樹枝衝破鵝卵石缺口般成長。不論是她父親慣常的酩酊大醉和凶暴殘酷,或是一個孩子為了粉飾太平所需做的表面工夫,都無法擊垮她。當我初次遇到她的時候,她就像初生狐狸般充滿野性和機警,而街頭的孩子們都叫她莫莉.小花臉。她身上常帶著被父親鞭打的傷痕,但不論父親多麼凶暴,她依然照顧他,我卻從來無法理解。甚至當她步履蹣跚地扶著酒醉的父親回家就寢時,都能承受他的牢騷和嚴厲指責。當他醒來之後,對前一晚的酩酊大醉和嚴酷指責可從不後悔,卻只會變本加厲地咒罵,例如為什麼蠟燭店沒人打掃,也沒人把新鮮的藥草鋪灑在地板上?為什麼她不去照顧幾乎快沒蜂蜜可賣的蜂窩?為什麼她讓燒牛油鍋的爐火燃燒殆盡?我沉默地目睹這一幕幕情景已太多次了。
但是,莫莉還是在艱困中成長。她像花一般地綻放,忽然就在某年夏季成為一個小女人,而她的精明幹練和女性魅力也使我敬畏。當我們四目相對的時候,我的舌頭猶如皮革般僵在嘴裡動彈不得,根本說不出話來,但我想她完全不知道這檔事。就算我擁有魔法、精技或原智,但當我們的手不經意碰觸時,我的內心依然產生悸動,而當她微笑的時候,我也仍感受一股難言的尷尬。
我應該將她髮絲隨風飄揚的丰采記錄下來,或詳述她的雙眼如何因心情由深琥珀色變成濃棕色,還有長外衣的顏色?當我在市場的人群中瞥見她那緋紅裙子和紅披肩時,就突然忘了其他人的存在。這是我親眼目睹的魔法,儘管我可能會寫下來,但不會有人能夠像她這樣自如的運用這種魔法。
我該如何追求她?帶著男孩笨拙的殷勤,像呆子盯著戲班的旋轉盤子般追求她?她比我早知道我愛著她,雖然我比她年幼幾歲,她依然讓我而非鎮上其他較稱頭的男孩追求她。她認為我是文書的雜工和馬廄的兼差助手,以及公鹿堡裡的跑腿。她從未懷疑我是讓駿騎王子無法繼承王位的私生子,光那檔事就是個天大的祕密了。對於我的魔法和其他專業,她也一無所知。
或許這正是我能愛她的原因。
這也正是我失去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