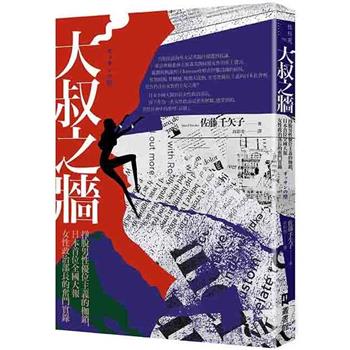意料之外的淚水
另一個是已經過世的大議員和我之間的事,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年前。深夜跑新聞的記者們,幾乎每晚都擠在那位議員宿舍的房間,議員則是會和記者們談一個小時左右。某個晚上,湊巧其他記者都沒來跑新聞,議員只好和我進行一對一的訪談。一開始是老樣子,我坐在沙發上稀鬆平常地和議員聊天,突然間,他靠了過來,並用手腕環繞著我的肩膀把我抱住。當時我說了好幾次「請住手」,但他還是不肯停下,最後我只好揮掉他的手逃了出去。那時我看見了在別的房間等待的秘書,秘書一點也不驚慌,就只是很平常地待在那裡。
議員的行動嚇到了我,秘書的表現也是。很明顯的,秘書對議員性騷擾他人的狀況早已習以為常,我無法停止想像「到底有多少女性遭遇了跟我一樣的事」。
那一晚我向兩位男性前輩記者報告這件事,也討論了後續的處理方式。前輩們聽完後馬上表示:「不要再去他那裡跑新聞了!就算拿不到情報也沒關係。」當時,這位議員並不是可以被放著不管的小人物,從報社的角度,一定會想要他提供的情報,對於他們的反應,我感到很欣慰。如果他們告訴我「挑男記者在的時候去就好了吧!你採訪時自己要小心點。」或是叫我乾脆不要負責這位議員了,我一定會感到沮喪。
「不要再去他那裡跑新聞了!」,公司即使付出失去情報的代價,也要守護記者的態度非常堅定。如果是「採訪時小心點吧」或「你就別負責了」的態度,乍看之下好像是體貼記者,但依舊把能不能拿到情報當作最優先,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我對前輩說:「不,明天開始,我一樣會在晚上去議員宿舍跑新聞。但我會小心不要和議員單獨相處。」在那之後,我很平常地在晚上去跑新聞,平安無事的把工作做好了。再次見面時,議員和秘書都像是完全沒事般,不,比起沒事,可以說是完全不在意,他們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罪惡感。
在座談會分享這件事時,席間有位男性工作人員表示:「性騷擾這種事沒辦法預防。重要的是,性騷擾發生後周圍的反應。」聽到這句話的瞬間,我的眼淚無預警的噴了出來,心想「明明應該已經忘記了才對,這件事居然成為了我的創傷」除了向前輩報告之外,是我第一次談論這個性騷擾的經驗。
應該有很多女性跟我一樣,把自己的感受封印起來,儘量不去回想,只是跟平常一樣過生活。在寫性騷擾這個主題時,我訪問了好幾位女性,很多次都能感覺到「她也跟我一樣,用封印情緒的方式,才能讓日子繼續過下去吧」。
那算是性騷擾嗎?
身為政治記者,在自己遇到性騷擾的經驗中,還有一件事讓我始終難以忘懷。那是我當上政治部記者的第二年,宮澤喜一、渡邊美智雄和三塚博三人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互相競爭。當時為了要獲得總裁選舉的情報,每天早上,記者們都會聚集在某位中堅議員宿舍的房間。這位議員非常體貼,為了照顧記者們的健康,準備了大量的沖泡式味噌湯,說「早上一定要喝味噌湯吧」,也會體貼地幫每個人倒熱水,是個溫柔的人。
某天早上,很偶然地,其他記者沒出現,變成我和議員一對一採訪。我們兩個像平常一樣,在廚房一邊喝味噌湯一邊聊天時,他突然說:「妳應該常常睡眠不足吧?要不要稍微睡一下?」,接著他就去隔壁房間把棉被拿過來,開始把棉被鋪在榻榻米上。我婉拒之後,很快地離開現場。議員年事已高,又是一個體貼的人,而且還是早上,那樣算是性騷擾嗎?我陷入了混亂,馬上跟前輩討論。
前輩記者表示:「太誇張了吧!就算累了,怎麼可能在那種地方睡覺啊!那個大叔真是的!還好妳拒絕了。」後來想想,那是很明顯的性騷擾,但我當時還年輕,作為記者的資歷也淺,又因為完全沒把年老又體貼的議員和性騷擾連結在一起,差點就陷入「這樣的話,我就恭敬不如從命,稍微補個眠好了」的危險狀況。
除了上述的經驗之外,在一九九零年代,也發生過另一件事。當時一位大老議員答應接受我的採訪,卻因為是複雜的案件,希望可以面對面採訪。在和他約見面時,他卻說:「我想拿資料給妳,再好好談談,妳能不能到我旅館的房間慢慢聊呢?」。因為是熟識的議員,我不知道該不該答應。和前輩聊過後他卻說:「絕對不能去」。那位前輩連理由都很仔細地講給我聽,「即使什麼都沒發生,如果被別人看到妳進了議員的房間,那就是百口莫辯。」聽完他的分析後,我覺得確實不妥,我便拒絕了對方,「我不能去您的房間」,議員還糾纏著「這樣的話,能不能到房間那層樓的走廊來呢?」我也拒絕了這個提案。結果,對方很不情願地到旅館底下的餐廳接受採訪。
身為記者,我後來並沒有和這位議員撕破臉,但假設那時被對方強迫進去房間,或前輩給我的建議有所不同的話,會怎麼樣呢?我直到現在也時常在思考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