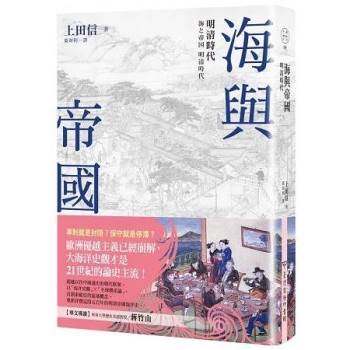【第七章 王朝更迭──十七世紀】
海上世界的終焉
◎海上的變化
自古以來的港口都市泉州,在附近的安南縣,有個叫石井的小漁村。登上後方的小山丘,可以眺望村落的全貌。幾乎沒有農地,村子的南方是一片連接到臺灣的海洋,東側則是白沙灘,凝視著大海;沙灘北側停了幾艘遠洋船,像是守護著這個港口不被南側的強風吹襲。走下山丘,道路兩旁有許多鄭姓墓碑,這幅光景跟四百年前沒什麼兩樣。
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一名叫鄭芝龍,後日又名鄭一官的男孩,誕生在這個村子。他在十八歲時搭乘遠洋船出海,在耕地稀少的泉州一帶,這是非常自然的選擇。
鄭芝龍面對的東歐亞海域,已非王直活躍時的十六世紀海上世界,海洋一直在變。首先,提供倭寇活動據點的日本,在豐臣秀吉時統一後,十七世紀由德川家康繼承。以日本為主的海上世界,接受豐臣、德川之後的統一政權統治。
過去由九州領主負責的海洋交易,到了十六世紀末,豐臣政權企圖插手掌控。豐臣政權直接控制日本國內的銀礦,掌握了從日本出口到中國的最大宗商品—白銀。將這些白銀投資海外貿易,成為經由東南亞與中國交易的最大贊助者;此外,豐臣政權還掌握了全國的領海權,從如何因應漂流到海岸的遇難船,可看出這些變化的端倪。
日本在中世紀時對於漂流物的所屬權認定,原則上歸給在漂流處發現的沿岸居民。十六世紀,這塊土地的領主為了占據漂流物,遇難船隻上的船員經常被視為奴隸。然而在一五九六年,一艘西班牙的船隻漂流到高知,豐臣秀吉派了奉行去沒收船上的貨物,並分給船員糧食,幫他們修好船隻後讓他們回國。
這也顯示了中世紀的慣例到此結束,海洋轉變為由統一政權管理的公共空間。豐臣政權封鎖了原先在日本沿海到中國、朝鮮半島這片廣大海域上活動的海盜,同時在一五九二年,對於日本赴海外的船隻發放相當於許可證的朱印狀,提出了允許特定商人對海外進行交易的方針。後來德川政權也延續這項政策,估計從一六○四年到一六三五年之間,光是能確認發放的朱印狀,就有三百五十六份。由於明朝不認可日本船隻進港,朱印狀上的前往地點多為馬尼拉、臺灣,以及印尼半島的港口城市。
帶著朱印狀的船隻,也就是朱印船,不止前往目的地的港口購買沉香等熱帶亞洲的物產,也跟中國商人交易,採購生絲等中國物產。雖然日本船隻無法直航中國,卻能在東南亞各個港口進行接頭貿易。可說德川政權將朱印狀當作一種手段,用來管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間接交易。
不僅日本,在海上世界活躍的歐洲人也從過去只在乎交易獲利的體質逐漸蛻變,將海洋納入殖民地經營所依據的體系中。一六○三年十月,西班牙統治的馬尼拉發生了據說多達兩萬名中國人慘遭殺害的案件。起因是中國宦官以增加宮廷資產為名目,進行開礦所致。因為一封謊稱在馬尼拉海岸能挖到金銀的奏文,明朝便派遣使節來辨明真偽。西班牙人卻認為使節來訪的目的是為了攻打馬尼拉而收集情資,特別加強對中國人的取締。此舉招來中國人的暴動,更演變成大規模的殘殺事件。從這起事件的背景,可隱約了解西班牙政府企圖管理不斷從海上湧進的中國海商。
另一方面,曾以冒險商人在海上大展身手的葡萄牙人,進入十七世紀後逐漸消聲匿跡,取而代之在東歐亞海域出現的勢力,是以「東印度公司」這間國家特許公司的名義推動各項活動的荷蘭人。相對於葡萄牙人以個人海商的才華來進行商業活動,新興的荷蘭人則是有組織地推動交易。荷蘭人無法在中國本土建立交易據點,於是在一六二三年於臺灣南部安平設置商館,著手開發島嶼。
◎倭寇的接棒人
前面提過,十六世紀的倭寇領袖王直出身徽州,他的商業活動就靠新安商人間的交流來支持。然而,面對十七世紀變化的海上世界,能最迅速因應的卻不是新安商人,而是出身泉州一帶的安平商人。離開故鄉的鄭芝龍,在這群商人之中嶄露頭角。
泉州一帶依山傍海,耕地不多,據說十戶人家裡就有七戶得到外地經商。安平商人的商業圈遍及大運河要塞的臨清,以及江南大都市蘇州、杭州等地。此外,也有不少人定居日本長崎及平戶,頻繁往來日本與中國從事交易。
鄭芝龍起先投靠經常往來於廣東與日本的舅舅。有一次,舅舅趁著有其他船隻赴日時,順便運送自己的貨物,就讓鄭芝龍搭船負責管理貨物,這艘船的船主是在日本平戶設有據點的李旦。一六二一年抵達日本的鄭芝龍,受到中國商人領袖李旦的信任,收他為義子。
李旦也出身泉州,在鄭芝龍投入海上世界時,李旦已擁有強大勢力。他取得朱印狀,派遣船隻到越南北圻、呂宋等地展開交易。同時也派遣朱印船到臺灣,計畫運用臺灣來當作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中繼點。更進一步攻擊航行於中國本土與臺灣之間的船隻,企圖獨占經過臺灣的交易路線。另一方面,荷蘭人在進到臺灣安平港時,也遇上了李旦的船。李旦曾收下荷蘭人的一筆錢,答應幫對方採購中國物產,後來卻幾乎沒實踐承諾。
鄭芝龍的野心和才智,隱藏在他一表人才的外貌之下。一六二四年,平戶的日本人田川七左衛門的女兒阿松為他產下一子,取名為福松,中文名是鄭森,也就是後來的鄭成功。之後鄭芝龍很可能是受了李旦之命,前往臺灣在荷蘭商館擔任口譯。
李旦在一六二五年於平戶過世,他的資產幾乎都進到鄭芝龍手裡。此外,相傳同一時期,有位名叫顏思齊的海商在臺灣過世時,他的船隊也由鄭芝龍繼承。鄭芝龍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海上世界的龐大勢力,有許多不解之謎。也有人認為,顏思齊是李旦的化名,其實根本是同一個人。總之,鄭芝龍發跡的過程為歷史小說提供了絕佳的題材。
繼承了李旦與顏思齊海上勢力的鄭芝龍,一六二六年在中國福建沿海地區展開武裝行動,陸續吸收他的競爭對手。起初在他手下的一百數十艘船也增加了數量。隔年,也就是一六二七年,明朝都督為了取締海上勢力,要求臺灣的荷蘭官員派兵支援,沒想到鄭芝龍以數百艘船隊包圍荷蘭船,一舉擊敗對方。據說此時鄭芝龍手中已握有七百艘船隻。一六二八年,鄭芝龍占領廈門後,明朝即任命他為「海防遊擊」,負責守衛沿岸地區,之後他不斷立下驅逐海盜的功績,連連升官。這是他與明朝合作,驅逐其他海上勢力,完全掌控東海制海權的一步。
航行在東海上的船隻,要是沒掛上鄭芝龍的旗幟就無法安全航行。為了掛上這面旗幟,海商的每艘船必須繳納白銀兩千兩。這項制度後來也由鄭成功繼承。鄭成功寫給在日本的同母胞弟的信中,具體說明了這項稱為「牌餉」的海上通行稅。根據書信中的說明,大型船隻繳納兩千一百兩,小型船隻繳納五百兩,則可獲得照牌,照牌的有效期間為一年。掛上照牌的船隻可以安全航行,但若沒有照牌,或是有效期限已過,會遭到緝拿且沒收貨物及船隻,船主及船員也會被逮捕。
運用這套制度,鄭芝龍的海上勢力不但能在財政上獲益,也可強化守衛海上安全的船隊。以武力背景保障往來船隻的安全,代價就是向商人收取通行稅。由鄭芝龍建立、再經由鄭成功發展的這套制度,已經超越私人海商的領域,具備公權力的功能。這股異於倭寇的政治勢力,與中國、日本、荷蘭等國的權力並駕齊驅。鄭芝龍在一六三一年,聯絡荷蘭在臺灣的官員,表示自己已取得由清朝發出、航行臺灣的正式許可,這也等於宣布,未來由中國到臺灣的物資,將全數由鄭芝龍手下的船隻壟斷運輸。荷蘭船不容易進入中國的港口,而荷蘭人要來臺灣也得仰賴中國的船隻。
◎交易基調的變化
十六世紀在東海上開啟的海上交易,大致的基調就是日本出口白銀到中國,再從中國進口生絲。由於明朝嚴禁與日本直接交易,就讓倭寇有發揮的空間,或是出現了經由東南亞其他港灣城市來做接頭貿易的迂迴方式。葡萄牙人就是加入這類交易。因為日本大量進口了中國產的優質生絲,讓日本國內的養蠶業者大受打擊,出現衰退。京都西陣織等高級絲綢織品的原料,幾乎已經完全仰賴進口的生絲。然而,從十七世紀中葉後,這樣的交易基調出現變化。起因是受到技術上的限制,日本的白銀產量逐漸下滑,實際上已經無法像十六世紀時讓大量白銀流出海外。
因應江戶幕府這個統一政權整頓貨幣制度,在日本國內經濟的運作上,也開始需要保有一定程度數量的白銀。幕府為了確保鑄造國內銀幣的原料,在一六○九年下令,禁止出口精鍊到一定高純度的銀錠,但依然有人以走私的方式出口。這樣的狀況從德川家康時期就懸而未解,直到德川家光統治的一六三○年代,才具備了能管理正式交易的條件。而實際上採取的政策,是配合幕府為建立日本統一的理念打壓基督教徒的步調。
對幕府而言,要面對的課題是如何處理與基督教傳教士無法完全切割的葡萄牙商船。自十六世紀後期,耶穌會為了取得在中國與日本傳教時不可或缺的經費,投資了在中國採購生絲後從澳門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隻。利瑪竇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一六○三年時,一艘在澳門港內準備往日本出發的葡萄牙船隻,遭到三艘荷蘭船隻搶劫,使得耶穌會蒙受高額損失。
而站在葡萄牙商人的角度,耶穌會是個少不了的投資者,就算會妨礙他們在日本的生意,也不可能清楚切斷雙方的關係。因此,該如何從交易中排除與基督教傳教士聯手的葡萄牙商人,就成為幕府的一大課題。然而,一旦趕走了葡萄牙人,日本之後該如何取得需要的生絲呢?這一點讓幕府傷透腦筋。
取代葡萄牙人的選項,就是荷蘭人。一六三二年,日本重啟與荷蘭人曾中斷一時的交流,但荷蘭人失去與幕府談判的權力,是將軍特別通融才得以進行交易。荷蘭商館館長為了表達感謝,從隔年一六三三年起,每年都會前往江戶。對幕府來說,荷蘭人很好應付。
過去來到平戶、坊津、博多等港口的中國商船,在一六三五年全部集中到幕府直轄地長崎管理,互市地點也只限於長崎。此外,這一年幕府還禁止日本人出國,也禁止居住在外國的日本人回國。
中國產的生絲、絲綢織品等貨物,主要也由中國商人取代了被迫退出與海外交易的日本商人。多數中國船隻不直航日本,而是繞到臺灣,把貨物賣給荷蘭商館。於是,荷蘭人向日本商人支付利息、借貸白銀,購買中國產品後再整批運到日本。這項成果讓幕府認為,不需要倚賴葡萄牙商船也能進口需要的生絲,便在一六三九年決定將葡萄牙人逐出日本。到了一六四一年,更將荷蘭人從平戶遷往長崎,限定他們在出島一地接受管理。
由幕府控制的交易路線成形後,鄭芝龍開始將中國生絲直接運到長崎。由於已經沒有任何能與他抗衡的勢力,鄭芝龍幾乎壟斷了生絲與白銀的交易。看得更透徹一點,也可說鄭芝龍利用了臺灣荷蘭商館,讓能與自己競爭的葡萄牙人被趕出日本。鄭芝龍收取做為生絲代償的白銀,其中也包含幕府發行、純度百分之八十的慶長銀,等級由幕府控制,並有鑄造所(銀座)的刻印保證。
以臺灣為據點的荷蘭勢力,如果不依附掛著鄭芝龍旗幟的中國商船,根本無法取得生絲、絲綢織品。要是鄭芝龍下令旗下的商船不要繞道臺灣,直接前往日本的話,荷蘭人的交易量就會銳減。果不其然,一六四一年之後,鄭芝龍讓旗下的船隻直航長崎,以獲得龐大利潤,無法在臺灣取得中國生絲的荷蘭人,只得到越南尋求新的供應來源。
◎從遷界令到展界令
明朝的滅亡與清軍入關,對鄭芝龍而言是個很大的分歧點。南京福王政權被清朝滅了之後,鄭芝龍擁立在福州的皇族朱聿鍵為唐王,卻在一六四六年福州被攻陷時投降清朝。鄭芝龍發展的限制,在於他擅長操縱既有的政治權來拓展自己的勢力,但他本身並無建立政權的意願。相對來說,他的兒子鄭成功多年來鑽研該如何為官,不僅如此,在他揮鄭成功畫像別父親走上抗清這條路之後,就展開行動,朝建立政權邁進。
鄭成功獲得唐王賜予明朝皇族的姓氏「朱」,以廈門、金門島為據點,將勢力拓展到從福建到廣東一帶的沿海地區。他自稱國姓爺,獲得政治上的向心力。此外,日本江戶時代前期的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以鄭成功為藍本撰寫的人形淨瑠璃劇,為了表示劇情是虛構,將劇名寫成「國性爺合戰」。
鄭成功在全盛時期,於廈門有仁、義、禮、智、信,五間批發商店,杭州則有金、木、水、火、土等五間。此外,他向勢力範圍區域內的居民徵稅,對航行海上的船舶徵收通行稅,還會出借資金收取利息。另一方面,他在長崎也握有生絲貿易的主導權。鄭成功的旗幟顯得鮮明之後,對於先前想藉由他的父親來籠絡鄭成功的清朝而言,鄭芝龍已經毫無價值。於是,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就以鄭芝龍疑似與鄭成功聯絡的罪名將他處刑。
清朝為了消減鄭成功的勢力,在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頒發海禁令,禁止沿海地區的商船出港銷售糧食跟貨物給鄭成功。玄燁(康熙帝)即位後,
更於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將以福建為中心,從廣東到山東、距離海岸線三十里(約十五公里)以內的居民全部強行遷居到內陸。
這道讓沿海地區無人化的遷界令,以現代人來看會覺得莫名其妙,但實際上在福建沿海地區的村落調查,發現當時的確實施過。鄭成功的勢力從中國本土被切割,孤立於海上;他從廈門撤退,將據點移到臺灣。率領兩萬五千名兵將來到臺灣的鄭成功,在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攻破荷蘭人打造的普羅民遮城(赤崁樓),包圍熱遮蘭城(安平古堡,又稱臺灣城),迫使荷蘭人勢力撤出臺灣。將臺灣納入勢力範圍後,鄭成功整頓官僚體系,從福建與廣東招募移民,進行開發。許多因為遷界令而流離失所的人,都因應招募渡海來臺灣。
鄭成功因為遷界令,無法直接從中國調度生絲,試圖改由經馬尼拉取得。持續迫害中國人的西班牙,成了這項策略的阻礙。於是在一六六二年,鄭成功以義大利傳教士為特使,對西班牙在呂宋的提督遞交國書。其中陳述因為荷蘭人虐待中國人並搶奪商船,所以將其驅逐,希望之後能順利進行交易,最後並恐嚇,若不照辦將會面臨與荷蘭人相同的命運。西班牙人收到這份國書,解讀為這是鄭成功下的最後通牒,決定驅逐所有中國商人。鄭成功接獲消息,得知在菲律賓的中國人遭到虐殺,立刻準備派兵前往菲律賓。沒想到,卻在這關鍵時刻病倒過世。
鄭成功的兒子鄭經也始終採取抗清的態度,呼應三藩之亂在沿岸各地展開攻擊。他修復了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派遣船隻到馬尼拉跟當地的中國商人採購生絲,然後到長崎轉賣,保持財政上的收入,然而,在遷界令導致海域封鎖之下,他也無力挽回劣勢。一六八一年鄭經過世,由誰接班卻引起內訌,水師提督施琅見縫插針,展開攻擊,一六八三年,臺灣的鄭氏政權就此瓦解。
在攻打鄭氏政權站在第一線的施琅,也是泉州出身,屬於安平商人圈裡的人物。平定臺灣之後,施氏一族在臺灣中部鹿港設置據點,積極開發臺灣。此外,施琅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派遣自己的商船到長崎,要求進行交易。
清朝在對平定臺灣勝券在握後,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解除遷界令,但仍持續禁止商船出海。直到鄭氏政權垮台後的隔年,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才頒發展界令,開放民間的海外貿易。以海上世界為基礎的海洋勢力就此消失,東歐亞的海域轉變為與陸上政權共同管理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