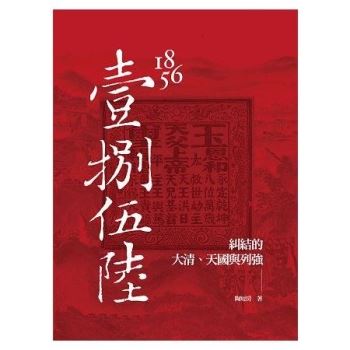第一回 長江,長江
黃金水道
清朝時,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尚不十分豐富,他們甚至還不知道長江的源頭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與長江間有什麼淵源。事實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多數人還錯誤地以為,長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內的那曲,而在一八五六年的時候,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大清朝」人或「天國」人,都普遍把岷江當作長江的正源,所謂「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在那個年代,是默認為一位四川人對一位江蘇人的遙遙思念的。
儘管如此,任何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不可能將這條中國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對於遠在北京的清廷和咸豐皇帝而言,長江流域關乎國家財政的穩定,甚至國家的運數。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關中、河南,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政和糧食來源,曾擔任要職的著名文學家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百分之九十)」,語雖誇張,卻凸顯了江南對全國經濟的重要意義。唐德宗李適貞元年間,由於藩鎮割據,坐困關中的唐朝君臣無時無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餉缺糧的禁軍再度嘩變,當大批江南漕米沿著運河–黃河水道運抵陝州的消息傳出,一向沉穩的李適竟狂喜失態,抱住太子的頭高呼「吾父子得生」。當時因為江南的米糧、財賦無法運進長安,皇宮裡居然連酒都找不到(釀酒需用的米也來自江南)。有記載稱,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間,全國每年租賦收入約為一千二百萬緡,其中來自江南的竟占逾百分之五十。
宋室南渡和北方連年戰亂,令長江流域在全國財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給,仰賴東南半壁」的格局。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武狀元、江蘇吳縣人于國柱在康熙廿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為《江南通志》作序,稱「國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為重地……國之大計,以財用為根本,而江南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鹽莢,關河之征榷,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於清朝以少數民族而入主中原,為恐漢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師屯駐大軍,僅八旗京營總兵力就達十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八人(魏源,《聖武記》),加上綠營巡捕五營一萬人,京城常備兵總數近十五萬,連同官員、差役、商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
不僅如此,除東三省外,清朝駐防全國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制都算「出差」性質,其家屬則領取圈占的「旗地」,加上駐京八旗官兵、官員家屬,人數已逾數百萬口,這些人同樣是清朝的「國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費錢糧豢養。
上述龐大開支,絕大多數仰賴長江沿線的供應,因此清朝對長江一直投入極大關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採用集中駐防、居中馭外的布防形式,京師以外,僅扼守最重要的據點,而這些據點又以長江或連接長江與京師的運河沿線最為密集。據道光十二年(西元一八三二年)《欽定中樞政考》記載,當年除京畿、東北以外,全國駐防八旗總兵力為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三人,其中沿江布防的有成都(設將軍,二千三百七十六人)、荊州(設將軍,六千四百六十人)、江寧(即南京,設將軍,四千五百四十六人)、京口(即鎮江,設副都統一千六百四十四人),沿運河布防的有乍浦(設副都統一千六百五十人)、青州(設副都統一千八百八十人)、德州(設城守尉,五百五十人),總數達一萬九千一百零六人,占了近百分之十。考慮到長江、運河沿線幾乎都是治安良好、社會穩定的內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見清廷對長江財賦的重視。
八旗以外的行政體系,對長江的重視程度更異乎尋常。沿江自西向東,有三總督(四川總督駐成都、湖廣總督駐武昌、兩江總督駐江寧。當時清朝統轄地方行政的總督總共只有八位)、三巡撫(湖北巡撫駐武昌、安徽巡撫駐安慶、江蘇巡撫駐蘇州。其中江蘇巡撫還特轄江寧、蘇州兩位布政使,其餘各省都只有一位);而全部三位元河道總督(南河總督駐江蘇淮安清江浦、東河總督駐山東濟寧、北河總督由直隸總督兼)和一位漕運總督(駐江蘇淮安),也全部分布在運河一線,其主要職責,實際上就是維繫長江–京師生命線的穩定與暢通。
割據長江
不過一八五六年年初,這條長江生命線連同運河這條臍帶,對清廷而言卻顯得不那麼通暢。
曾經被小刀會占據十八個月的上海縣城,此時已被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所收復,「長江尾」算是勉強被打通,但在上海縣城之外,英法兩國卻趁火打劫,建立了兩塊租界地的雛形,在未來幾十年裡,這些原本的城外「爛泥濱」,將發展成整個遠東最繁華的城市,而上海縣城卻會凋敝落魄,甚至縣城的「上級單位」松江府以及當時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商業都市蘇州府,也都會因之衰落下去。
沿江口上溯,很快就會進入太平軍大炮的射程範圍。一八五六年年初,太平天國在長江沿線所控制的要點並不多,由上游而下,主要為瓜洲–鎮江、南京、東西梁山、安慶、九江–湖口和武昌,而這些要點間的大多數江段,則被清朝水師所控制,如武昌和九江之間的金口,有湖北巡撫胡林翼所率領的湘軍水師主力,附近的新堤更設有水師船廠;安慶和南京間的蕪湖和三山磯,有綠營水師吳全美部「紅單船」二十五艘駐泊;鎮江和瓜洲之間的焦山島附近,則巡弋著吳全美部另二十五艘紅單船,他們還能得到更下游上海吳淞口蘇松太道組建船隊支援。但太平軍所控制的,恰是江淮漕運要衝,尤其鎮江–瓜洲據點不偏不倚,直接卡住了長江、運河兩條航道的交叉點,這不啻捏住了清廷的喉管。
好在一八五六年已不是一八五三年,當年太平軍上萬艘船隻「行若浮雲,止若疊雪」,自宜昌至鎮江,「制江權」完全掌握在「天朝水營」手裡。而此時,大清才是大部分江面的主人。
一八五三年年底,在籍侍郎、奉旨幫辦湖南團練事務的曾國藩設廠於衡陽,仿造廣西、廣東內河水師船型,並自廣州購買西洋熟鐵前膛炮(俗稱「洋莊」),建立了湘軍水師。一八五四年春,湘軍水師(十營、五千人,戰船二百四十艘)出湘江,經湘潭、嶽州、武漢、田家鎮諸戰,焚毀太平軍大小船隻數千艘,一度肅清了上游江面。一八五五年年初,湘軍水師乘勝進逼九江、湖口,試圖將太平軍水師一舉全殲於鄱陽湖內,太平軍名將翼王石達開、冬官正丞相羅大綱等利用曾國藩急於求成的心理,以及湘軍水師每營由大小船隻組成、一旦分拆則戰鬥力大減的破綻,在湖口會戰中引誘湘軍水師三板小船衝入鄱陽湖口,然後將湖口封鎖,致使湖中小船失去大船依託,無法休息、補給,官兵疲憊不堪;而外江大船失去小船,幾乎完全喪失自衛能力,結果被太平軍各個擊破,武漢三鎮重新落入太平軍手中。此刻的曾國藩正坐鎮南昌,緊張應付著從湖北轉戰而來的太平軍石達開部與從廣東、湖南源源湧入的數萬天地會「紅軍」,湘軍內河水師遭到重創後,剩下的三板駐泊在南昌、樟樹鎮等地的內河,而只剩大船的湘軍外江水師,則在胡林翼的統帶下駐紮金口。新堤船廠裡正熱火朝天地製造嶄新的三板小船,在這些得力內河戰船造成前,湘軍水師只能偃旗息鼓。
下游的情形則有很大差異。
一八五四年七月,五十艘紅單船在吳全美的率領下抵達鎮江焦山江面,接受江南大營主帥向榮調度。向榮分其中一半,在當年和次年兩次溯江而上,一直攻到三山磯、蕪湖一帶。太平軍當時的戰船多為民船改造,大小不一,水軍又缺乏水戰經驗,故連戰連敗,就連「水賊」出身的頭號水師名將羅大綱,也在一八五五年年底反攻蕪湖時身負重傷,因無法忍受劇痛而「吞金自斃」。不過紅單船水師屬於綠營體系,沾染了綠營所特有的習氣,且其官兵多數為廣東人,在外征戰既久,人心浮動,戰意漸懈,對天京、鎮江、瓜洲等堅城構不成重大威脅;不過,紅單船掌握下游「制江權」,便截斷了天京、鎮江、瓜洲三座要塞間的聯繫。
清廷也知道,僅憑水師是無法肅清長江的,因此一方面催促上游湘軍儘快沿江東下,另一方面不斷強化江南、江北兩大營的實力,力圖水陸配合,「犁庭掃穴」,奪取天京,消滅太平天國。然而上游湘軍欲速則不達,九江、湖口一敗之後,便被分割在湖北、江西兩地,對天京暫時鞭長莫及,因此,下游的江南、江北大營,成了一八五六年年初清廷的希望所系。
江南大營是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清咸豐三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正月廿日)由從廣西一路追擊太平軍至天京城下的欽差大臣向榮所建。一八五六年大本營設在天京城東孝陵衛,並控制了秣陵關、七橋甕等城外要塞,對天京城構成直接威脅。江南大營可調動的八旗、綠營總兵力共為三萬二千六百一十五人,其中天京附近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五人,直接部署在一線的為一萬七千八百人。江北大營於一八五三年四月在揚州城北組建,當時的主帥為欽差大臣琦善。此時琦善已死,由江寧將軍托明阿接任。這支負責浦口以下北岸江防的清軍,可調動兵力二萬四千人,直接部署在一線的兵力也是一萬七千八百人,此時兵分兩路,駐紮運河兩岸的秦家橋、桂家莊。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太平軍已放棄了揚州,此刻江北大營的主要使命,一是守住運河口,防範太平軍渡江北上,威脅中原和京畿;二是圍攻奪取太平軍在江北的最後一個據點—瓜洲,並配合江南大營進逼天京、鎮江。
這時的鎮江、瓜洲是清軍圍攻的重點。一八五五年二月,小刀會在上海失敗,原本圍攻上海縣城的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部近四千人得以抽調回顧上游。此刻的吉爾杭阿已掛上了幫辦江南大營軍務頭銜,率領本部、圍困鎮江的原有清軍(四千餘人),以及從江南大營抽調的清軍共約萬餘人圍攻鎮江。這些清軍主力分別部署在鎮江城西的九華山和鎮江城東的京峴山。此外,湖南提督余萬清、宜昌鎮總兵虎嵩林分別屯兵鎮江以西的下蜀、高資,兵力分別為二千三百人和一千六百人,這兩路人馬部署在天京、鎮江之間,目的是阻擊從天京經陸路來援的太平軍。
此時的太平軍則沿著長江,擺出了「一字長蛇陣」。
上游的武漢,由北王韋昌輝的親弟弟、國宗提督軍務韋俊任主帥,因為遭到上游荊州和下游金口方向清軍的進逼,目前稍顯不利;由金口而下,九江、湖口牢牢掌握在太平軍守將林啟榮、黃文金手裡,而上游太平軍最高軍政負責人—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則正在江西腹地對曾國藩的湘軍展開咄咄逼人的攻勢;再往下游,皖南、皖北都是拉鋸態勢,皖南太平軍喪失了沿江最大城市蕪湖,卻仍堅守著東西梁山的要塞,皖北重鎮廬州得而復失,不過安徽省城安慶和眾多郡縣,卻是太平軍此際最鞏固的根據地和最可靠的糧源。
天京附近,太平軍占據江中八卦洲、九洑洲、七里洲等據點,控扼江南京郊眾多要塞,令江南大營始終難以真正合圍,但江北浦口為清軍占據,江面上往來巡弋的紅單船,也令太平軍船隊無力駛出夾江正面決戰,更難突破水路封鎖,增援、補給下游的鎮江、瓜洲。
鎮江、瓜洲此時已被圍困了三年之久,自揚州、焦山失守後,這兩座城鎮的補給,主要靠天京從水路運來,但紅單船抵達後,這種補給變得越來越困難,至一八五六年年初已近乎斷絕。鎮江守將原本是羅大綱,但此時已去世,此刻的主將是殿左五檢點吳如孝,此人在太平軍中資格很老,曾參加過天地會,還是受過洗禮的基督教徒,他不僅以欽差大臣頭銜負責鎮江軍政、民政,而且還要兼轄江北瓜洲防務。作為下遊江北太平軍唯一據點,瓜洲孤懸敵後,駐軍很少但防禦嚴密,此刻守將為指揮謝錦章,他的要塞周圍,是西起儀征土橋江邊,東至揚州新橋江邊,綿亙四十餘里的土牆,以及沿牆密布的四十多座江北大營營盤、炮臺。
一八五六年年初,清廷已經發現,撬開天京堅城縫隙、打通長江這條命脈的關鍵點,是與天京成掎角之勢的鎮江、瓜洲,並正逐步將兵力、裝備移向這裡,緩慢、但有效地取得進展;而此時實際主持太平天國軍政事務的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清也同樣意識到了這點,並正試圖組建一支足以在鎮江戰場打開局面,甚至能發揮更大作用的機動部隊。
靜觀時變
至於外國人方面,自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七日,英國公使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之子小包令(Lewin Bowring)和翻譯麥華陀爵士所率使團訪問天京。在與太平天國官方進行了很不愉快的正式交涉後,英、法、美似乎達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儘管長江「黃金水道」的開埠、通商、通航,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但在目前中國內戰雙方戰局膠著、未來贏家尚不明朗之際,長江對外國人及其商務而言,仍是「高危地域」。因此,暫且順水推舟地回到華南珠江流域,跟清廷所指派、與洋人辦交涉的唯一合法官方代表—兩廣總督葉名琛交涉,似乎更有利些。至於長江,也只能先滿足於占據江尾一隅的上海租界和「五口通商」中的上海開港,這點已不再是「紙面上的開放」,而是千真萬確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