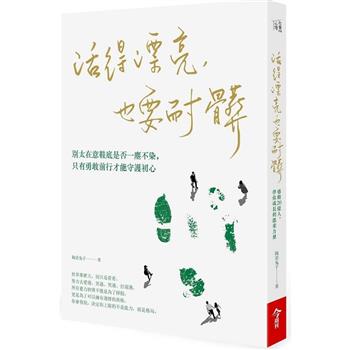活得漂亮,也要耐髒
我妹妹上大四那年,以一個實習生的身分參加人生中第一次公司酒會。她老早就為自己挑選好一件漂亮的小晚禮服,配上一雙白色細帶的高跟鞋,連丸子頭的髮型和甜美的夏日風妝容都演練了許多回。
興高采烈地出了門,回來的時候卻有些不開心的樣子。她語調怏怏地跟爸媽彙報完酒會的情況,便一頭走進我的書房:「為什麼酒會是這樣的?跟我同期的那些實習生都拚了命地往老闆身邊湊,討好完老闆,討好部門主管和副主管,她們還叫我一起……」
「那說明她們對你還不錯啊,居然還叫你一起。」我說。
可她卻長長地嘆了口氣,用那種看老年人的眼神看著我:「酒會不該是這樣的啊,難道不應該像電視劇上那樣,俊男美女觥籌交錯,穿著華麗的公主遇到白馬王子,一見鍾情然後牽手離場嗎?」
「那不是酒會,那是相親節目……」我一臉黑線。
她不理我,繼續喪氣地嘆著氣:「我真想去讀研究所了,社會好黑暗,連個酒會都不能好好玩,搞得那麼複雜,真沒意思。」
我認識一個小女生,畢業之後在當地的一家報社當記者。她屢次跟主編發生衝突,原因幾乎如出一轍:那些出自她筆下鋒利的指責和揭露,都被主編用更圓滑,當然,看上去也更像是官腔的語言替換了下來。試用期還沒結束她就辭了職,只留下一句話:「我就要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人,要到一個乾淨的地方去。」
她的主編與我也是舊識,一次吃飯的時候提起她,有點惋惜地說:「我只是幫她改得委婉一點,她要是到其他地方去,可能都見不了報。這世界上哪有真正乾淨的地方,她那個非黑即白的價值觀,恐怕今後會吃虧啊。」
小女生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企業裡做秘書,除了公務之外,有時也需要幫老闆打理一些私事,她離職的時候沮喪地約我吃飯:「我以為我的老闆是個好人,可是他……他居然養小三。」
我失笑:「他一沒對公司裡的人出手,二沒影響工作效率,人家的感情生活又關你什麼事?」
她紅著眼睛吐出一句話:「可是我嫌他髒,整個公司都是髒的,我一分鐘也待不下去了。」
***回想起我剛畢業的時候,好像也是這副模樣,眼裡容不得沙子,對一切不按光明規則行事的人深惡痛絕。可是人行走在這世間,即便是不經意也會帶上許多塵土,哪裡有一塵不染的人呢?對「人際潔癖」的過分渴求,會將一個人困在最小的生活半徑之內,跟最少的人打交道,做最少的事,用隔絕的方式來保持自我。但你無法一輩子都躲在孤島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小的時候看歷史,總會對那些動輒以死證清白,口口聲聲喊著「文死諫、武死戰」的人心生敬佩,覺得人生就是這般的非黑即白、對錯分明,要麼得到所有,要麼毀滅一切。可是愈長大,便愈會欣賞那些可以忍得一時髒,以圖今後的人。
完全不懂世故的人,與太懂世故的人一樣不可愛,強極則辱,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而你對這個世界骯髒之處的容忍程度,就是你的行走範圍。
所謂潔淨,所謂自我,從來都不是將自己關在一個閉塞的角落,小心翼翼地守衛著易碎的價值觀。而是走出去,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將價值觀反覆打碎錘煉,知道自己能改變的是什麼,可以放棄的是什麼,想要堅守的又是什麼。
十八歲的時候,眼裡容不得一點沙子,希望全世界都一絲不苟地按照烏托邦一般運行,然後逐漸明白,生活中從來沒有絕對的黑白對錯,更多人,更多事,是停留在灰色地帶的無可奈何。十八歲的時候,痛恨一切骯髒,然後逐漸明白,任何一塊硬幣,都有正反兩面。十八歲的時候,滿腔熱血一心屠龍,然後逐漸明白,所謂改變,只有做好自己。
很喜歡網路上有人評價郭襄的那一句話:「知世故而不弄世故,懂人情而不靠人情。」沒有人可以永不摔跤,但你選擇站起身拍拍塵土繼續前行,還是索性一屁股坐在泥潭裡同流合污,這才是本質的區別。
別太在意鞋底是不是一塵不染,只要守好自己的心就好。
願你活得漂亮,也成為一個耐點髒的人。
你發合照的時候能不能也幫我美顏?
有個女孩找我聊天,說起最近跟閨蜜鬧彆扭的事。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兩個人結伴出去旅行,一路拍了很多照片,每晚入睡前都要精心挑選幾張,美美地妝點好然後發動態。她修圖的時候都會順手把同伴的照片也進行同樣的處理,可是她的朋友每每發出去的合照卻只有自己光鮮亮麗,身邊的她頭髮凌亂滿面油光,正好襯得朋友花容月貌、天生麗質。她看到之後有點不爽,又不好意思為這點小事開口質問對方,可偏巧她暗戀的男生只給她的朋友按讚,之後又在那個女孩的動態下回覆了一句留言:同一張照片,她在自己的IG清新可人,在人家的IG卻是無比真實的灰頭土臉。
這下她抓狂了,可閨蜜的回答更讓她惱火:「你也太小題大作了吧,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不就是一張照片,你有必要這樣?」
好像也是啊,有什麼大不了的?她說不上來,心裡卻總存著一個疙瘩。女生的友誼最是微妙,雖然這件事兩人都再沒提起,可她們終究再也不像從前那樣形影不離了。
她問我:「是不是我太小心眼了?可是我只是要求她幫我做這一點小事,好像也沒錯。」
我念大學的時候,也曾經因為類似的一件小事而跟朋友分道揚鑣。
那時實名制火車票剛剛普及,我們一起出去玩,回來出站時路過一個垃圾桶,她順手就把我的火車票拿過去,毫無停頓地扔了進去,卻把自己的那張細細地撕碎再扔。我全程目睹她的差別對待,她扔完車票又回過頭來接著聊天,我心裡卻覺得十分不是滋味。你的個人資訊需要保護,我的就不需要嗎?你口口聲聲說著我們是能穿一條褲子的最好朋友,可細枝末節處還是會將「你」與「我」分得那麼清楚。原來對你而言,我也沒那麼重要。
現實生活中的友誼真的很脆弱,用不著電視劇裡你搶我男友、我奪你家產的狗血糾葛,裂痕往往起於小事,可它一旦開始蔓延,就沒了轉寰的可能。我們漸行漸遠,到了畢業那年,也淪落成了在宿舍樓下相遇會寒暄「吃了嗎」的點頭之交。
***
在《社會性動物》一書中,將人的社交關係分為兩種:共情社交和功利社交。
所謂共情,便是喜對方所喜、憂對方所憂,有共同的話題,有相似的興趣和弱點,能夠與對方產生情感連結。而功利社交則更好理解,為了逃離孤單,為了獲得陪伴,為了遲到時有人可以幫自己簽到,為了吃飯時不要顯得那麼形隻影單,兩個人的友誼與其說是出於感情,不如說是出於彼此的需要。
大一剛開學的時候,我在餐廳見過不少這樣的女生們,明明話不投機,卻依然要圍在一個桌子上吃飯,貌合神離各自玩著手機,幾乎沒有人說話。她們算不上是什麼朋友,各懷各的心思和志向,湊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只是不想讓自己顯得那麼孤僻和怪異而已。
而這樣氣氛詭異的小團體,往往在大二的時候開始瓦解,交往的圈子從宿舍、班級開始擴展為社團和年級,開始擁有選擇的權利,開始主動尋求能跟自己共情的人展開新的友誼。功利社交依舊存在,面對學生會的前輩,社團裡的競爭對手,不大喜歡但是又繞不開關係的同學,也能立刻擺出熱情寒暄的笑容。
共情和功利並不是誰取代誰的關係,它們並存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唯一的區別是對象不同。我想通這個道理之前,也曾經反思過無數次:自己是不是太小心眼?對方到底有沒有錯?如果今後再遇到這樣的人,我該怎麼辦?後來我明白了,我跟那位朋友的漸行漸遠,其實無關於誰錯誰對,無關於寬容與原諒,不過是她與我的交往基於功利,而我卻在要求共情,因此才會顯得格格不入,都覺得對方莫名其妙。
這世間不存在明確的槓桿來衡量朋友之間為彼此付出了多少,可終究還是有一種不平等如鯁在喉。那種不平等並不在於我為你買了飯你卻忘了幫我倒水,我幫你美了顏你卻沒幫我修圖,或是一些讓人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雞毛蒜皮。而是我對你付出了真感情,你卻只當我無關緊要。
佛洛姆在《愛的藝術》裡這樣寫:
不成熟的愛是——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愛你;
成熟的愛是——因為我愛你,所以我需要你。
這句話不僅僅適用於愛情,友誼也如是。
我想跟你做朋友,不是要靠你擺脫孤單,不是要靠你幫我代購,不是要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找你借錢;而是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卻依然很喜歡跟你相處。
而真正能夠跟你共情的人,是不需要你開口,也會幫你修圖的,這並不是因為她們會比其他人更體貼入微,只是因為在意,所以才會留心。因為己若不欲,所以也不會施加於你。
我後來甚至有些慶幸自己是這樣一個有點小心眼的人,在一些小事上發現端倪後,往往會很自覺地退回到功利社交的範圍,不再強求共情,也不會再在對方身上付出心力和時間。做不成朋友也沒關係,至少能保持點頭之交的體面。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得以走向擁有更多選擇的地方,去找到那些志趣相投又情意相通的朋友,那些不用你開口,就會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你的人。獲得共情朋友的前提,不是一味地討好迎合,以互相遷就為名彼此捆綁;而是我們各自出發,然後在途中相遇,驚喜地發現原來你也在這裡。真正無效的社交,並不是功利與功利的結合,而是明明出於功利,卻還要努力扮演一副親密無間的假象。
你到底要我怎樣才肯喜歡我?
小優在晚上十一點打電話給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就在一個小時前,她剛剛被男神禮貌地提出分手,連Line也封鎖,斷得一乾二淨。
她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跟我哭訴:「你說他到底嫌我什麼啊?我買了一書櫃的書,我推掉了多少個聚會活動,為了他我連歐洲史都惡補完了,他為什麼就不能喜歡我一點點?」
愛情這個東西是很奇怪的,戀愛的雙方都是因為先有了自己,愛情才能存在,一旦一個人開始費盡心思地去迎合討好另一個人,反而會打翻它的天平。
小優和她的男神結識於一次公益活動。那天是兒童節,他們一行人到附近的兒童公益機構為孩子們送禮物。小優正好跟男神分到一組,她常去那裡參加這種活動,人又開朗活潑,孩子們很快就跟她打成一片,歡聲笑語地玩起了遊戲。沉默寡言的男神搬完禮物就站在一旁看著,被小優一把拖過來:「正好,我當母雞,你來當老鷹,來抓我們吧。」
活動結束後,她主動要了他的Line,晚上偷偷把他的照片發給我看:「我要找的人終於出現啦。」
「他真的很好,腿長、臉帥、有風度,溫柔、細緻、書卷氣,正好也是單身!!!」她用了三個驚嘆號,「真的,超好。」
不久之後就聽說兩人開始戀愛的消息,我們打趣小優,誇她效率又高目標又準。她在群裡跟大家插科打諢的同時私訊我問:「你家裡有沒有講哲學或者歐洲史之類的書?」
我跌破眼鏡,這可是除了課本之外,看不進任何東西的小優啊,連言情小說看到一半都會打瞌睡,更別說這種枯燥無味的大部頭。
她說:「因為男神喜歡啊,他爸媽都是老師,平時也特別喜歡看書,我總得多讀點,才能跟他有共同語言。跟他一起出去見朋友,也要出口成章,才能不給他丟臉。」
「他敢嫌棄你?」我反問。
「才不是呢,」她用那種少女的嬌羞口吻回答我,「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為了男神我要變成更好的人。」
即便是每看十分鐘就需要去用冷水洗把臉,即便是推掉她曾經最喜歡的聚會和登山,即便是把自己折騰得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即便是做著自己完全看不懂的筆記,她手中那本厚厚的歐洲史終於還是讀完了,可依然沒能扭轉這結局。她在電話那頭帶著哭腔說:「他為什麼要封鎖我呀?我好想問問他,我到底哪點不好,他到底要我怎麼樣才會喜歡我。」
你到底要我怎樣才肯喜歡我?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到這樣的問題。
是嫌我不夠好看嗎?是嫌我身材不夠好?是嫌我太過內向或是太過張揚?那我瘦下來,化了妝,強顏歡笑地陪你參加聚會,強忍無聊地陪你去圖書館看書,你會不會喜歡我呢?為了愛情削足適履,美其名曰為愛奉獻,可是又有哪個身穿白色婚紗的新娘,能拖著流血不止的腳走完那樣長的一程?
***
我認識一對情侶,女孩心疼男朋友工作辛苦,每天通勤一兩個小時回家連口熱飯都吃不上,索性辭了工作,在家當起了全職女友,專心研究各種菜式,中餐西餐主食甜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花式不重複。
男生工作不錯,收入支撐兩個人的開支綽綽有餘,可兩個人的摩擦卻愈來愈多。女孩做好了飯他卻忽然有應酬,他週末想隨便吃點外賣她堅持讓他吃健康午餐。慢慢地,他開始藉口工作太忙,加班加得愈來愈頻繁;她在家等著,將一盤盤菜熱了又熱,他都沒有回來。
女孩跟我們訴苦:「我還不是為了他,認識他之前,我也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小姐,他以為我真的是閒得發慌,才往那油煙裡鑽當黃臉婆嗎?我為愛情犧牲了這麼多,他怎麼就一點都不在乎。」
是啊,你犧牲了那麼多。可是他樂見這樣的犧牲嗎?他又能享受這犧牲背後的幸福嗎?
當年你們兩人一起啃便當,一邊吃一邊談著工作上的事,你的臉上有愛、眼中有光。而現在,你像飼養一隻寵物般,用慈愛的眼神打斷他講述職場上的種種煩心:「噓,吃飯的時候幹嘛講這些煩心事。來,多吃點,這條魚我可是為你燉了一早上呢。」
身邊伶俐可愛的解語花變成了絮絮叨叨的黃臉婆,你覺得自己虧了,可是不好意思,他也這麼覺得。他若能將你一鍵還原,恐怕早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你還想讓他對你感恩戴德?
戀愛的過程並不僅僅是在向對方靠近,而是在靠近的同時也確認自我。確認你的喜惡,你的性格與愛好,你的亮點與那些差強人意略顯黯淡的缺點,你的底線與意願。愛情從來都不僅僅是它本身,更是關於身在其中的兩個人。在漫長的舞會中,姿勢難看地踩過腳,失魂落魄地流過淚,你慢慢學會了配合,而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節奏。
我們女孩子從小被灌輸了太多次的「要順從,要溫柔,要犧牲,要妥協,自我沒那麼重要」,我們總是太過在意別人的眼光和看法,但愛情偏偏任性,你若找不到自己,便找不到它。一段關係或許可以始於偽裝或矯飾,可是任何感情到了最後,卻只關乎於你是誰。
你不是AI,不是SIRI,你帶著你過去那麼多年的經歷,成為一顆獨一無二的小星球。而你是誰,便是他愛你的原因。與其將自己弄得面目全非卻也了無生氣,每天苦兮兮地散發著慘綠的幽光,動輒抱怨、動輒委屈,不時地搬出「我還不是為了你」將對方壓得喘不過氣,還不如好好地做自己。
因為人只有在做自己真心喜歡的東西時,眼裡才會有光,只有在感到舒適自然時,才能像貓一般慵懶地收起利爪,變成柔軟而又自在的一團。
很喜歡陳文茜的那句話:
愛情本來就只是在捕捉自我,可是我們大多數的人不肯承認這一點。
願你終得所愛,也願你不忘初心。
我妹妹上大四那年,以一個實習生的身分參加人生中第一次公司酒會。她老早就為自己挑選好一件漂亮的小晚禮服,配上一雙白色細帶的高跟鞋,連丸子頭的髮型和甜美的夏日風妝容都演練了許多回。
興高采烈地出了門,回來的時候卻有些不開心的樣子。她語調怏怏地跟爸媽彙報完酒會的情況,便一頭走進我的書房:「為什麼酒會是這樣的?跟我同期的那些實習生都拚了命地往老闆身邊湊,討好完老闆,討好部門主管和副主管,她們還叫我一起……」
「那說明她們對你還不錯啊,居然還叫你一起。」我說。
可她卻長長地嘆了口氣,用那種看老年人的眼神看著我:「酒會不該是這樣的啊,難道不應該像電視劇上那樣,俊男美女觥籌交錯,穿著華麗的公主遇到白馬王子,一見鍾情然後牽手離場嗎?」
「那不是酒會,那是相親節目……」我一臉黑線。
她不理我,繼續喪氣地嘆著氣:「我真想去讀研究所了,社會好黑暗,連個酒會都不能好好玩,搞得那麼複雜,真沒意思。」
我認識一個小女生,畢業之後在當地的一家報社當記者。她屢次跟主編發生衝突,原因幾乎如出一轍:那些出自她筆下鋒利的指責和揭露,都被主編用更圓滑,當然,看上去也更像是官腔的語言替換了下來。試用期還沒結束她就辭了職,只留下一句話:「我就要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人,要到一個乾淨的地方去。」
她的主編與我也是舊識,一次吃飯的時候提起她,有點惋惜地說:「我只是幫她改得委婉一點,她要是到其他地方去,可能都見不了報。這世界上哪有真正乾淨的地方,她那個非黑即白的價值觀,恐怕今後會吃虧啊。」
小女生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企業裡做秘書,除了公務之外,有時也需要幫老闆打理一些私事,她離職的時候沮喪地約我吃飯:「我以為我的老闆是個好人,可是他……他居然養小三。」
我失笑:「他一沒對公司裡的人出手,二沒影響工作效率,人家的感情生活又關你什麼事?」
她紅著眼睛吐出一句話:「可是我嫌他髒,整個公司都是髒的,我一分鐘也待不下去了。」
***回想起我剛畢業的時候,好像也是這副模樣,眼裡容不得沙子,對一切不按光明規則行事的人深惡痛絕。可是人行走在這世間,即便是不經意也會帶上許多塵土,哪裡有一塵不染的人呢?對「人際潔癖」的過分渴求,會將一個人困在最小的生活半徑之內,跟最少的人打交道,做最少的事,用隔絕的方式來保持自我。但你無法一輩子都躲在孤島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小的時候看歷史,總會對那些動輒以死證清白,口口聲聲喊著「文死諫、武死戰」的人心生敬佩,覺得人生就是這般的非黑即白、對錯分明,要麼得到所有,要麼毀滅一切。可是愈長大,便愈會欣賞那些可以忍得一時髒,以圖今後的人。
完全不懂世故的人,與太懂世故的人一樣不可愛,強極則辱,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而你對這個世界骯髒之處的容忍程度,就是你的行走範圍。
所謂潔淨,所謂自我,從來都不是將自己關在一個閉塞的角落,小心翼翼地守衛著易碎的價值觀。而是走出去,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將價值觀反覆打碎錘煉,知道自己能改變的是什麼,可以放棄的是什麼,想要堅守的又是什麼。
十八歲的時候,眼裡容不得一點沙子,希望全世界都一絲不苟地按照烏托邦一般運行,然後逐漸明白,生活中從來沒有絕對的黑白對錯,更多人,更多事,是停留在灰色地帶的無可奈何。十八歲的時候,痛恨一切骯髒,然後逐漸明白,任何一塊硬幣,都有正反兩面。十八歲的時候,滿腔熱血一心屠龍,然後逐漸明白,所謂改變,只有做好自己。
很喜歡網路上有人評價郭襄的那一句話:「知世故而不弄世故,懂人情而不靠人情。」沒有人可以永不摔跤,但你選擇站起身拍拍塵土繼續前行,還是索性一屁股坐在泥潭裡同流合污,這才是本質的區別。
別太在意鞋底是不是一塵不染,只要守好自己的心就好。
願你活得漂亮,也成為一個耐點髒的人。
你發合照的時候能不能也幫我美顏?
有個女孩找我聊天,說起最近跟閨蜜鬧彆扭的事。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兩個人結伴出去旅行,一路拍了很多照片,每晚入睡前都要精心挑選幾張,美美地妝點好然後發動態。她修圖的時候都會順手把同伴的照片也進行同樣的處理,可是她的朋友每每發出去的合照卻只有自己光鮮亮麗,身邊的她頭髮凌亂滿面油光,正好襯得朋友花容月貌、天生麗質。她看到之後有點不爽,又不好意思為這點小事開口質問對方,可偏巧她暗戀的男生只給她的朋友按讚,之後又在那個女孩的動態下回覆了一句留言:同一張照片,她在自己的IG清新可人,在人家的IG卻是無比真實的灰頭土臉。
這下她抓狂了,可閨蜜的回答更讓她惱火:「你也太小題大作了吧,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不就是一張照片,你有必要這樣?」
好像也是啊,有什麼大不了的?她說不上來,心裡卻總存著一個疙瘩。女生的友誼最是微妙,雖然這件事兩人都再沒提起,可她們終究再也不像從前那樣形影不離了。
她問我:「是不是我太小心眼了?可是我只是要求她幫我做這一點小事,好像也沒錯。」
我念大學的時候,也曾經因為類似的一件小事而跟朋友分道揚鑣。
那時實名制火車票剛剛普及,我們一起出去玩,回來出站時路過一個垃圾桶,她順手就把我的火車票拿過去,毫無停頓地扔了進去,卻把自己的那張細細地撕碎再扔。我全程目睹她的差別對待,她扔完車票又回過頭來接著聊天,我心裡卻覺得十分不是滋味。你的個人資訊需要保護,我的就不需要嗎?你口口聲聲說著我們是能穿一條褲子的最好朋友,可細枝末節處還是會將「你」與「我」分得那麼清楚。原來對你而言,我也沒那麼重要。
現實生活中的友誼真的很脆弱,用不著電視劇裡你搶我男友、我奪你家產的狗血糾葛,裂痕往往起於小事,可它一旦開始蔓延,就沒了轉寰的可能。我們漸行漸遠,到了畢業那年,也淪落成了在宿舍樓下相遇會寒暄「吃了嗎」的點頭之交。
***
在《社會性動物》一書中,將人的社交關係分為兩種:共情社交和功利社交。
所謂共情,便是喜對方所喜、憂對方所憂,有共同的話題,有相似的興趣和弱點,能夠與對方產生情感連結。而功利社交則更好理解,為了逃離孤單,為了獲得陪伴,為了遲到時有人可以幫自己簽到,為了吃飯時不要顯得那麼形隻影單,兩個人的友誼與其說是出於感情,不如說是出於彼此的需要。
大一剛開學的時候,我在餐廳見過不少這樣的女生們,明明話不投機,卻依然要圍在一個桌子上吃飯,貌合神離各自玩著手機,幾乎沒有人說話。她們算不上是什麼朋友,各懷各的心思和志向,湊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只是不想讓自己顯得那麼孤僻和怪異而已。
而這樣氣氛詭異的小團體,往往在大二的時候開始瓦解,交往的圈子從宿舍、班級開始擴展為社團和年級,開始擁有選擇的權利,開始主動尋求能跟自己共情的人展開新的友誼。功利社交依舊存在,面對學生會的前輩,社團裡的競爭對手,不大喜歡但是又繞不開關係的同學,也能立刻擺出熱情寒暄的笑容。
共情和功利並不是誰取代誰的關係,它們並存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唯一的區別是對象不同。我想通這個道理之前,也曾經反思過無數次:自己是不是太小心眼?對方到底有沒有錯?如果今後再遇到這樣的人,我該怎麼辦?後來我明白了,我跟那位朋友的漸行漸遠,其實無關於誰錯誰對,無關於寬容與原諒,不過是她與我的交往基於功利,而我卻在要求共情,因此才會顯得格格不入,都覺得對方莫名其妙。
這世間不存在明確的槓桿來衡量朋友之間為彼此付出了多少,可終究還是有一種不平等如鯁在喉。那種不平等並不在於我為你買了飯你卻忘了幫我倒水,我幫你美了顏你卻沒幫我修圖,或是一些讓人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雞毛蒜皮。而是我對你付出了真感情,你卻只當我無關緊要。
佛洛姆在《愛的藝術》裡這樣寫:
不成熟的愛是——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愛你;
成熟的愛是——因為我愛你,所以我需要你。
這句話不僅僅適用於愛情,友誼也如是。
我想跟你做朋友,不是要靠你擺脫孤單,不是要靠你幫我代購,不是要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找你借錢;而是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卻依然很喜歡跟你相處。
而真正能夠跟你共情的人,是不需要你開口,也會幫你修圖的,這並不是因為她們會比其他人更體貼入微,只是因為在意,所以才會留心。因為己若不欲,所以也不會施加於你。
我後來甚至有些慶幸自己是這樣一個有點小心眼的人,在一些小事上發現端倪後,往往會很自覺地退回到功利社交的範圍,不再強求共情,也不會再在對方身上付出心力和時間。做不成朋友也沒關係,至少能保持點頭之交的體面。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得以走向擁有更多選擇的地方,去找到那些志趣相投又情意相通的朋友,那些不用你開口,就會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你的人。獲得共情朋友的前提,不是一味地討好迎合,以互相遷就為名彼此捆綁;而是我們各自出發,然後在途中相遇,驚喜地發現原來你也在這裡。真正無效的社交,並不是功利與功利的結合,而是明明出於功利,卻還要努力扮演一副親密無間的假象。
你到底要我怎樣才肯喜歡我?
小優在晚上十一點打電話給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就在一個小時前,她剛剛被男神禮貌地提出分手,連Line也封鎖,斷得一乾二淨。
她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跟我哭訴:「你說他到底嫌我什麼啊?我買了一書櫃的書,我推掉了多少個聚會活動,為了他我連歐洲史都惡補完了,他為什麼就不能喜歡我一點點?」
愛情這個東西是很奇怪的,戀愛的雙方都是因為先有了自己,愛情才能存在,一旦一個人開始費盡心思地去迎合討好另一個人,反而會打翻它的天平。
小優和她的男神結識於一次公益活動。那天是兒童節,他們一行人到附近的兒童公益機構為孩子們送禮物。小優正好跟男神分到一組,她常去那裡參加這種活動,人又開朗活潑,孩子們很快就跟她打成一片,歡聲笑語地玩起了遊戲。沉默寡言的男神搬完禮物就站在一旁看著,被小優一把拖過來:「正好,我當母雞,你來當老鷹,來抓我們吧。」
活動結束後,她主動要了他的Line,晚上偷偷把他的照片發給我看:「我要找的人終於出現啦。」
「他真的很好,腿長、臉帥、有風度,溫柔、細緻、書卷氣,正好也是單身!!!」她用了三個驚嘆號,「真的,超好。」
不久之後就聽說兩人開始戀愛的消息,我們打趣小優,誇她效率又高目標又準。她在群裡跟大家插科打諢的同時私訊我問:「你家裡有沒有講哲學或者歐洲史之類的書?」
我跌破眼鏡,這可是除了課本之外,看不進任何東西的小優啊,連言情小說看到一半都會打瞌睡,更別說這種枯燥無味的大部頭。
她說:「因為男神喜歡啊,他爸媽都是老師,平時也特別喜歡看書,我總得多讀點,才能跟他有共同語言。跟他一起出去見朋友,也要出口成章,才能不給他丟臉。」
「他敢嫌棄你?」我反問。
「才不是呢,」她用那種少女的嬌羞口吻回答我,「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為了男神我要變成更好的人。」
即便是每看十分鐘就需要去用冷水洗把臉,即便是推掉她曾經最喜歡的聚會和登山,即便是把自己折騰得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即便是做著自己完全看不懂的筆記,她手中那本厚厚的歐洲史終於還是讀完了,可依然沒能扭轉這結局。她在電話那頭帶著哭腔說:「他為什麼要封鎖我呀?我好想問問他,我到底哪點不好,他到底要我怎麼樣才會喜歡我。」
你到底要我怎樣才肯喜歡我?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到這樣的問題。
是嫌我不夠好看嗎?是嫌我身材不夠好?是嫌我太過內向或是太過張揚?那我瘦下來,化了妝,強顏歡笑地陪你參加聚會,強忍無聊地陪你去圖書館看書,你會不會喜歡我呢?為了愛情削足適履,美其名曰為愛奉獻,可是又有哪個身穿白色婚紗的新娘,能拖著流血不止的腳走完那樣長的一程?
***
我認識一對情侶,女孩心疼男朋友工作辛苦,每天通勤一兩個小時回家連口熱飯都吃不上,索性辭了工作,在家當起了全職女友,專心研究各種菜式,中餐西餐主食甜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花式不重複。
男生工作不錯,收入支撐兩個人的開支綽綽有餘,可兩個人的摩擦卻愈來愈多。女孩做好了飯他卻忽然有應酬,他週末想隨便吃點外賣她堅持讓他吃健康午餐。慢慢地,他開始藉口工作太忙,加班加得愈來愈頻繁;她在家等著,將一盤盤菜熱了又熱,他都沒有回來。
女孩跟我們訴苦:「我還不是為了他,認識他之前,我也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小姐,他以為我真的是閒得發慌,才往那油煙裡鑽當黃臉婆嗎?我為愛情犧牲了這麼多,他怎麼就一點都不在乎。」
是啊,你犧牲了那麼多。可是他樂見這樣的犧牲嗎?他又能享受這犧牲背後的幸福嗎?
當年你們兩人一起啃便當,一邊吃一邊談著工作上的事,你的臉上有愛、眼中有光。而現在,你像飼養一隻寵物般,用慈愛的眼神打斷他講述職場上的種種煩心:「噓,吃飯的時候幹嘛講這些煩心事。來,多吃點,這條魚我可是為你燉了一早上呢。」
身邊伶俐可愛的解語花變成了絮絮叨叨的黃臉婆,你覺得自己虧了,可是不好意思,他也這麼覺得。他若能將你一鍵還原,恐怕早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你還想讓他對你感恩戴德?
戀愛的過程並不僅僅是在向對方靠近,而是在靠近的同時也確認自我。確認你的喜惡,你的性格與愛好,你的亮點與那些差強人意略顯黯淡的缺點,你的底線與意願。愛情從來都不僅僅是它本身,更是關於身在其中的兩個人。在漫長的舞會中,姿勢難看地踩過腳,失魂落魄地流過淚,你慢慢學會了配合,而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節奏。
我們女孩子從小被灌輸了太多次的「要順從,要溫柔,要犧牲,要妥協,自我沒那麼重要」,我們總是太過在意別人的眼光和看法,但愛情偏偏任性,你若找不到自己,便找不到它。一段關係或許可以始於偽裝或矯飾,可是任何感情到了最後,卻只關乎於你是誰。
你不是AI,不是SIRI,你帶著你過去那麼多年的經歷,成為一顆獨一無二的小星球。而你是誰,便是他愛你的原因。與其將自己弄得面目全非卻也了無生氣,每天苦兮兮地散發著慘綠的幽光,動輒抱怨、動輒委屈,不時地搬出「我還不是為了你」將對方壓得喘不過氣,還不如好好地做自己。
因為人只有在做自己真心喜歡的東西時,眼裡才會有光,只有在感到舒適自然時,才能像貓一般慵懶地收起利爪,變成柔軟而又自在的一團。
很喜歡陳文茜的那句話:
愛情本來就只是在捕捉自我,可是我們大多數的人不肯承認這一點。
願你終得所愛,也願你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