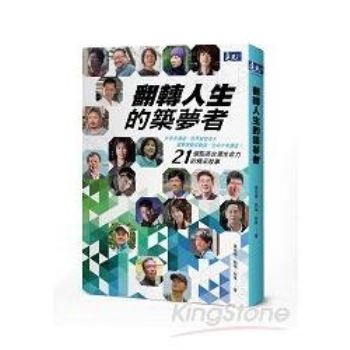齊柏林
他的心、他的眼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空拍好像是一條不歸路,因為空拍,我把視線伸展到了城市之外,看見了大自然,看見了土地,也看見了破壞。其中充滿無力感,想為這塊土地做點什麼,也許就是這個念頭一直驅使我往前進。」
在台灣,「齊柏林」這三個字幾乎等同於「空拍」的代號了。每次提到自己的名字,齊柏林就帶著笑意,在二十世紀初期,「齊柏林飛船」是現今民航機前身飛行器的總稱,齊柏林本人說,「我父親來自河南,不知道有這樣的飛船存在,對飛行也沒有任何夢想,卻幫我取了這個名字。」
冥冥之中,父親就為齊柏林安排了一個奇妙的人生:從小就迷戀各種會飛的事物,童年最喜歡的卡通是《科學小飛俠》,少年時最大嗜好是養鳥,最高紀錄曾經在家中頂樓養了一百多隻各種品種的鳥類,今年半百的他,至今大半輩子都在「飛」。
更有趣的是,一九六〇年代的搖滾大團《齊柏林飛船》最負盛名的搖滾聖歌就叫做《通往天堂的階梯》(Stairway to Heaven),「齊柏林」彷彿是一組代碼,引領著與此相關的人們,追尋並始終嚮往世界的高空。
空中攝影,喚醒熱情
服完兵役之後,因為對攝影的興趣,齊柏林首先到婚紗公司應徵,接著進入一家室內設計雜誌當攝影,拍一些燈光美、陳設美、家具美,但看起來假假的室內設計案件。一開始還覺得很有成就感,但是拍久了,都有固定模式,有好一陣子,他竟然下班之後就不想再碰相機,少年時對生態攝影的熱忱,一點一滴的消失。
剛好這個時期,房地產狂飆,打開報紙,裡面眾多的建案廣告經常有實地空拍的照片。好奇的他到處打聽這些照片是怎麼拍的,這才知道有「空中攝影」這個領域,他甚至主動認識空拍攝影師,要求一起上飛機當助理。齊柏林說,「我不記得那時看到什麼景物,但在空中熱血翻騰的感覺至今難忘。」這是無償的工作,但沖上雲霄飛行的震撼,讓他願意用一輩子的力氣不斷重溫。
之後為了有穩定工作收入,齊柏林考上公職,進入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任職,負責空拍各項重大工程的興建過程,例如北二高工程施工的紀錄。為了拍攝,國工局每年會租用直升機,這是齊柏林最期待的時刻,也讓他跟直升機航空公司有了交情,「他們知道我沒錢,空有熱情,常會接案子委由我拍攝,甚至只要有飛行任務,他們也會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拍。」齊柏林笑說,「不管天涯海角,只要有機會,我就一定跟到底。」
這些飛行任務五花八門,有的是為高山上難以到達的氣象站補給物資、有林務局巡山監視濫墾開發、或吊橋興建工程,「有時直升機載離島的臨終病人回家,會空機返回,這時他們也會通知我。」齊柏林說,「不管他們在何地出任務,我都會想辦法請假,坐客機過去等直升機。」上直升機的時間彌足珍貴,「只要在飛機上,不管環境如何惡劣、身體多麼疲累,我一定睜著眼睛四處看,因為飛機一飛就過去了,必須在幾秒鐘之內選擇要取什麼景、如何構圖,一心得多用。」
有時齊柏林還是得自己出錢、出機拍攝,「真的很貴,十幾年前,直升機一小時的飛行費用就要五萬元,現在更是漲到十五萬元。」空中攝影需要很龐大的費用,齊柏林笑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存摺裡的錢都不到十萬元,房貸也總是還不完。」一直以來,齊柏林在正職工作之外,都得兼職打工,才能兼顧生活與夢想。
發現台灣正面臨生態浩劫
其實齊柏林在攝影圈成名很早,但為了空拍的夢,他當了十幾年的「攝影工人」。齊柏林說,「以前下班後,身上就會揹著大包小包的攝影器材,騎著機車去拍食譜、拍新裝潢好的賓館房間,各式各樣的攝影工作我都接,甚至還經常替大師捉刀。接案的收入很好,但從來都存不起來,因為,都用到租飛機上了。」為了多攢錢,他很早就在eBay拍賣網站上買國外二手相機,在台灣出售,有時還會買到美國軍用偵察相機的空拍鏡頭或經典相機,他就留著收藏,提升自己空拍影像的品質,算是在著迷空拍之外的嗜好。
三十多歲時,齊柏林接觸空中攝影已經有五、六年,主要是記錄公共工程的過程,他說,「我經常在台灣高空飛來飛去,拍攝我以為是重要建設紀錄的照片,包括高速公路的興建,當時的確有看到一些不美麗的照片,但我不以為意,認為這是國家發展的必然過程,那時從沒想過,這些工程一旦開始動工,生態環境就無法再逆轉。」
齊柏林的心裡,偶爾會冒出些許狐疑,但也是一閃即逝,因為當時的他還不了解環境問題、還相信人定勝天的理念,「看到高山上大面積的菜園、茶園及果園,都覺得是很正面的事情,從高空看就那麼一大片,這樣要花多少力氣去種植。」
直到一九九八年,《大地地理雜誌》開始跟他調照片,這對齊柏林來說猶如暮鼓晨鐘,「我一開始並不知道他們要如何使用這些照片,只是把他們要的題材提供出去,例如梨山上的果園、沿海的魚塭等等。」等到報導出來後,「原來他們把照片交給關心生態的專家學者重新解讀,我才發現,我真的紀錄了台灣這塊土地許多的變化。看著這些報導,也跟著重新學習用新的角度,觀看自己拍的照片、觀看台灣這塊土地。一段時間下來,我深深地理解,這些景象,真的是生態浩劫。」
從小受制式教育長大的齊柏林陷入省思,「過去我只著迷拍攝美麗的照片,一點也不關心被拍攝的對象發生什麼事,鏡頭會自動避開醜陋的事實,以為沒人看到,就能躲過心中的疑慮。」
想盡辦法,拍紀錄片
尤其令他震撼的是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這是齊柏林第一次拍攝巨大天災,「從空中看到九份二山大面積的崩落、房子橫躺在大地上,視覺經驗非常巨大,我開始感受到,原來我做的事很獨特。從此之後,我知道不用再把照片鎖在櫃子裡孤芳自賞,它們是極有意義的歷史影像。」這樣的經驗讓齊柏林人生出現轉折,「我愈來愈有方向、使命感,了解很多事情不能再等。」這時再飛行於台灣上空,齊柏林的心情完全不一樣,他恨不得自己長出一雙翅膀,能夠鎮日看護這塊他熱愛的土地。
二○○三年,齊柏林成為「第一屆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得主,當時的計畫內容,是空拍台灣高山雪景(河川源頭)及高屏溪流域(台灣流域面積最廣之河流),為台灣水資源留下完整記錄。二○○六年七月,齊柏林正式出版《從空中看台灣》攝影集,讓更多人一起關心台灣的土地樣貌。但空拍了十幾年,光是按相機的快門,已經無法再滿足他,他看到BBC(注:英國廣播公司主要的電視頻道)的空拍影片十分心動,開始動念做更具挑戰性的高空動態拍攝,然而光是器材,就要價兩千多萬台幣,令他很是掙扎。
二〇〇九年的八八風災,滿目瘡痍的災區景象,成了推他一把的關鍵。「我嚇壞了,」齊柏林曾經多次拍過山區的土石流,「但跟八八風災比起來,真的小巫見大巫。」為了發展經濟,台灣在環保和環境開發上始終難兩全,他認真開始思考辭去公職,全心投入拍攝紀錄片的可能,「那一年,我四十七歲,再過三年就可以退休了,我不斷問自己:『再等三年不行嗎?』」但是,另外一種聲音也一直出現:「我已經四十七歲了,再等三年,真的還有體力嗎?」
「再不做些什麼,以後就沒機會了。」最後,這個信念獲勝,他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空拍攝影師,為了籌措紀錄片資金,他抵押房子、還向友人借錢購買器材。這是一個金錢、人員都缺乏的計畫,除了對夢想的堅持,還要有破釜沈舟的勇氣,所幸他都一一堅持地走過來,即使最初為了八千萬的製作預算,他到處尋求支持,不少人問他:「投資報酬率是多少?如何回收?觀眾在哪裡?」有時,他快要招架不住,只能苦笑說:「我的觀眾還在家裡!」那時,許多人對於他的夢想,都還抱持觀望態度。
三年後,台灣首部空拍電影紀錄片《看見台灣》真的出現在大家面前,不僅讓台灣人自己重新看見台灣,也讓許許多多的國家、城市看見了台灣,甚至看見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願意低頭反省自己的契機。
勇敢追夢,生命將帶給你驚喜
自從《看見台灣》上映後,「電影包場超過一千場,還跑了全台三百多場映後座談會,」齊柏林說,「這是我原本根本想像不到的。但對我而言,我多了一個媒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所關心的台灣,她的美與她的苦。」幾乎,電影下片之後,他每一週都要出國,到日本、美國、新加坡……,四處參加影展,電影也應觀眾的要求不斷加映,「不只是華僑來看,更多當地的人,擠滿了各處的電影院。」齊柏林跑行程跑得很累,曾因舟車勞頓生病,好幾天都發不出聲音,但所有的努力,都只為了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二十多年來,齊柏林在天空飛行了超過兩千小時,無數的日子都得看老天爺臉色,「即使到現在,每天飛機要不要升空,都得當天才能決定。」為了夢想,他必須放棄陪伴孩子們成長的過程,「別的孩子不喜歡下雨天,但我的孩子卻最愛下雨天,因為只有這時爸爸才有空陪他們。」齊柏林與家人都很無奈,但為了他的夢想,只能默默接受。
溫暖、熱情且執著的齊柏林,願意犧牲所有個人的生活成就追求的夢想,成為老天最佳的代言人,在在地提醒著人類,善待自己的家園、自己的土地。他示範了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勇於追求夢想,不管身處人生那個階段,齊柏林都鼓勵每個人:「請立即擁抱內心所渴望的夢想,不要猶豫,生命自然會給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
我是齊柏林
第一屆(2003~2004)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得主,台灣首席空中攝影家,從事空拍二十多年,以飛行高空的角度,呈現另一種觀看及記錄台灣的方式。一九九八年起,齊柏林於《大地地理雜誌》發表攝影作品,至今累積近四十萬張台灣地理空拍影像,出版攝影著作二十餘冊。然而多次飛覽台灣、空照大地,深感平面影像已不足讓民眾感受台灣面臨的濫墾、污染、災害等危機,決心藉由動態紀錄,讓大家感受台灣的美麗與苦難,進而能多加關注這塊土地。二○○九年八八風災後,斥資拍攝台灣首部空拍電影紀錄片《看見台灣》,引起台灣各界乃至世界各地的熱烈迴響,更於二○一三年獲第五十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
他的心、他的眼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空拍好像是一條不歸路,因為空拍,我把視線伸展到了城市之外,看見了大自然,看見了土地,也看見了破壞。其中充滿無力感,想為這塊土地做點什麼,也許就是這個念頭一直驅使我往前進。」
在台灣,「齊柏林」這三個字幾乎等同於「空拍」的代號了。每次提到自己的名字,齊柏林就帶著笑意,在二十世紀初期,「齊柏林飛船」是現今民航機前身飛行器的總稱,齊柏林本人說,「我父親來自河南,不知道有這樣的飛船存在,對飛行也沒有任何夢想,卻幫我取了這個名字。」
冥冥之中,父親就為齊柏林安排了一個奇妙的人生:從小就迷戀各種會飛的事物,童年最喜歡的卡通是《科學小飛俠》,少年時最大嗜好是養鳥,最高紀錄曾經在家中頂樓養了一百多隻各種品種的鳥類,今年半百的他,至今大半輩子都在「飛」。
更有趣的是,一九六〇年代的搖滾大團《齊柏林飛船》最負盛名的搖滾聖歌就叫做《通往天堂的階梯》(Stairway to Heaven),「齊柏林」彷彿是一組代碼,引領著與此相關的人們,追尋並始終嚮往世界的高空。
空中攝影,喚醒熱情
服完兵役之後,因為對攝影的興趣,齊柏林首先到婚紗公司應徵,接著進入一家室內設計雜誌當攝影,拍一些燈光美、陳設美、家具美,但看起來假假的室內設計案件。一開始還覺得很有成就感,但是拍久了,都有固定模式,有好一陣子,他竟然下班之後就不想再碰相機,少年時對生態攝影的熱忱,一點一滴的消失。
剛好這個時期,房地產狂飆,打開報紙,裡面眾多的建案廣告經常有實地空拍的照片。好奇的他到處打聽這些照片是怎麼拍的,這才知道有「空中攝影」這個領域,他甚至主動認識空拍攝影師,要求一起上飛機當助理。齊柏林說,「我不記得那時看到什麼景物,但在空中熱血翻騰的感覺至今難忘。」這是無償的工作,但沖上雲霄飛行的震撼,讓他願意用一輩子的力氣不斷重溫。
之後為了有穩定工作收入,齊柏林考上公職,進入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任職,負責空拍各項重大工程的興建過程,例如北二高工程施工的紀錄。為了拍攝,國工局每年會租用直升機,這是齊柏林最期待的時刻,也讓他跟直升機航空公司有了交情,「他們知道我沒錢,空有熱情,常會接案子委由我拍攝,甚至只要有飛行任務,他們也會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拍。」齊柏林笑說,「不管天涯海角,只要有機會,我就一定跟到底。」
這些飛行任務五花八門,有的是為高山上難以到達的氣象站補給物資、有林務局巡山監視濫墾開發、或吊橋興建工程,「有時直升機載離島的臨終病人回家,會空機返回,這時他們也會通知我。」齊柏林說,「不管他們在何地出任務,我都會想辦法請假,坐客機過去等直升機。」上直升機的時間彌足珍貴,「只要在飛機上,不管環境如何惡劣、身體多麼疲累,我一定睜著眼睛四處看,因為飛機一飛就過去了,必須在幾秒鐘之內選擇要取什麼景、如何構圖,一心得多用。」
有時齊柏林還是得自己出錢、出機拍攝,「真的很貴,十幾年前,直升機一小時的飛行費用就要五萬元,現在更是漲到十五萬元。」空中攝影需要很龐大的費用,齊柏林笑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存摺裡的錢都不到十萬元,房貸也總是還不完。」一直以來,齊柏林在正職工作之外,都得兼職打工,才能兼顧生活與夢想。
發現台灣正面臨生態浩劫
其實齊柏林在攝影圈成名很早,但為了空拍的夢,他當了十幾年的「攝影工人」。齊柏林說,「以前下班後,身上就會揹著大包小包的攝影器材,騎著機車去拍食譜、拍新裝潢好的賓館房間,各式各樣的攝影工作我都接,甚至還經常替大師捉刀。接案的收入很好,但從來都存不起來,因為,都用到租飛機上了。」為了多攢錢,他很早就在eBay拍賣網站上買國外二手相機,在台灣出售,有時還會買到美國軍用偵察相機的空拍鏡頭或經典相機,他就留著收藏,提升自己空拍影像的品質,算是在著迷空拍之外的嗜好。
三十多歲時,齊柏林接觸空中攝影已經有五、六年,主要是記錄公共工程的過程,他說,「我經常在台灣高空飛來飛去,拍攝我以為是重要建設紀錄的照片,包括高速公路的興建,當時的確有看到一些不美麗的照片,但我不以為意,認為這是國家發展的必然過程,那時從沒想過,這些工程一旦開始動工,生態環境就無法再逆轉。」
齊柏林的心裡,偶爾會冒出些許狐疑,但也是一閃即逝,因為當時的他還不了解環境問題、還相信人定勝天的理念,「看到高山上大面積的菜園、茶園及果園,都覺得是很正面的事情,從高空看就那麼一大片,這樣要花多少力氣去種植。」
直到一九九八年,《大地地理雜誌》開始跟他調照片,這對齊柏林來說猶如暮鼓晨鐘,「我一開始並不知道他們要如何使用這些照片,只是把他們要的題材提供出去,例如梨山上的果園、沿海的魚塭等等。」等到報導出來後,「原來他們把照片交給關心生態的專家學者重新解讀,我才發現,我真的紀錄了台灣這塊土地許多的變化。看著這些報導,也跟著重新學習用新的角度,觀看自己拍的照片、觀看台灣這塊土地。一段時間下來,我深深地理解,這些景象,真的是生態浩劫。」
從小受制式教育長大的齊柏林陷入省思,「過去我只著迷拍攝美麗的照片,一點也不關心被拍攝的對象發生什麼事,鏡頭會自動避開醜陋的事實,以為沒人看到,就能躲過心中的疑慮。」
想盡辦法,拍紀錄片
尤其令他震撼的是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這是齊柏林第一次拍攝巨大天災,「從空中看到九份二山大面積的崩落、房子橫躺在大地上,視覺經驗非常巨大,我開始感受到,原來我做的事很獨特。從此之後,我知道不用再把照片鎖在櫃子裡孤芳自賞,它們是極有意義的歷史影像。」這樣的經驗讓齊柏林人生出現轉折,「我愈來愈有方向、使命感,了解很多事情不能再等。」這時再飛行於台灣上空,齊柏林的心情完全不一樣,他恨不得自己長出一雙翅膀,能夠鎮日看護這塊他熱愛的土地。
二○○三年,齊柏林成為「第一屆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得主,當時的計畫內容,是空拍台灣高山雪景(河川源頭)及高屏溪流域(台灣流域面積最廣之河流),為台灣水資源留下完整記錄。二○○六年七月,齊柏林正式出版《從空中看台灣》攝影集,讓更多人一起關心台灣的土地樣貌。但空拍了十幾年,光是按相機的快門,已經無法再滿足他,他看到BBC(注:英國廣播公司主要的電視頻道)的空拍影片十分心動,開始動念做更具挑戰性的高空動態拍攝,然而光是器材,就要價兩千多萬台幣,令他很是掙扎。
二〇〇九年的八八風災,滿目瘡痍的災區景象,成了推他一把的關鍵。「我嚇壞了,」齊柏林曾經多次拍過山區的土石流,「但跟八八風災比起來,真的小巫見大巫。」為了發展經濟,台灣在環保和環境開發上始終難兩全,他認真開始思考辭去公職,全心投入拍攝紀錄片的可能,「那一年,我四十七歲,再過三年就可以退休了,我不斷問自己:『再等三年不行嗎?』」但是,另外一種聲音也一直出現:「我已經四十七歲了,再等三年,真的還有體力嗎?」
「再不做些什麼,以後就沒機會了。」最後,這個信念獲勝,他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空拍攝影師,為了籌措紀錄片資金,他抵押房子、還向友人借錢購買器材。這是一個金錢、人員都缺乏的計畫,除了對夢想的堅持,還要有破釜沈舟的勇氣,所幸他都一一堅持地走過來,即使最初為了八千萬的製作預算,他到處尋求支持,不少人問他:「投資報酬率是多少?如何回收?觀眾在哪裡?」有時,他快要招架不住,只能苦笑說:「我的觀眾還在家裡!」那時,許多人對於他的夢想,都還抱持觀望態度。
三年後,台灣首部空拍電影紀錄片《看見台灣》真的出現在大家面前,不僅讓台灣人自己重新看見台灣,也讓許許多多的國家、城市看見了台灣,甚至看見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願意低頭反省自己的契機。
勇敢追夢,生命將帶給你驚喜
自從《看見台灣》上映後,「電影包場超過一千場,還跑了全台三百多場映後座談會,」齊柏林說,「這是我原本根本想像不到的。但對我而言,我多了一個媒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所關心的台灣,她的美與她的苦。」幾乎,電影下片之後,他每一週都要出國,到日本、美國、新加坡……,四處參加影展,電影也應觀眾的要求不斷加映,「不只是華僑來看,更多當地的人,擠滿了各處的電影院。」齊柏林跑行程跑得很累,曾因舟車勞頓生病,好幾天都發不出聲音,但所有的努力,都只為了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二十多年來,齊柏林在天空飛行了超過兩千小時,無數的日子都得看老天爺臉色,「即使到現在,每天飛機要不要升空,都得當天才能決定。」為了夢想,他必須放棄陪伴孩子們成長的過程,「別的孩子不喜歡下雨天,但我的孩子卻最愛下雨天,因為只有這時爸爸才有空陪他們。」齊柏林與家人都很無奈,但為了他的夢想,只能默默接受。
溫暖、熱情且執著的齊柏林,願意犧牲所有個人的生活成就追求的夢想,成為老天最佳的代言人,在在地提醒著人類,善待自己的家園、自己的土地。他示範了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勇於追求夢想,不管身處人生那個階段,齊柏林都鼓勵每個人:「請立即擁抱內心所渴望的夢想,不要猶豫,生命自然會給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
我是齊柏林
第一屆(2003~2004)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得主,台灣首席空中攝影家,從事空拍二十多年,以飛行高空的角度,呈現另一種觀看及記錄台灣的方式。一九九八年起,齊柏林於《大地地理雜誌》發表攝影作品,至今累積近四十萬張台灣地理空拍影像,出版攝影著作二十餘冊。然而多次飛覽台灣、空照大地,深感平面影像已不足讓民眾感受台灣面臨的濫墾、污染、災害等危機,決心藉由動態紀錄,讓大家感受台灣的美麗與苦難,進而能多加關注這塊土地。二○○九年八八風災後,斥資拍攝台灣首部空拍電影紀錄片《看見台灣》,引起台灣各界乃至世界各地的熱烈迴響,更於二○一三年獲第五十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