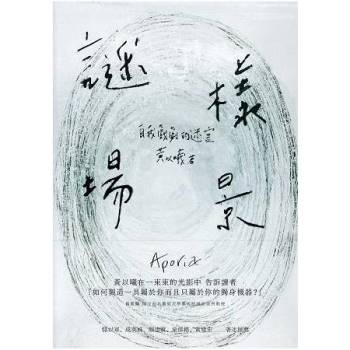空間
理論狂熱者
「你是個理論狂熱者。」她滿臉淚水。這遣詞讓我分心,遺忘了面前的爭執。
她說得對,我想我是個理論狂熱者。畢竟,對情感暴漲的人而言,沒有理論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不親手研發更繁複理論套式,亦是不可想像的。
情感沒有輪廓,不需要支撐軸架,不在乎核心與邊陲。情感輕視設定與假說,不在乎效率,不要求結果。情感不知道人會死,誰都無法飛升地離開地面。情感是青春之泉,滿載譫妄。
我不介意那樣活,可我不能。我得用感受到的去催生詞彙,鍛造原則,然後是體系與系統。我用理論的抽象,製作傳說中的永動機(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第一套感觸,催生第一部永動機。永動機將平凡的經驗框架為新鮮的感觸。新的感觸抵住上限、催生再一部永動機,然後是新一套感觸……。唯有理論,讓我對抗黏熱的生存亢進。
唯有理論,我才能質疑現實。像在白色的密閉房間,用力將整個身體往牆撞去,竟也就穿牆而過了。密閉不過是前提約制的幻覺。
我沈醉地思考著,不再介意她的離開。
比哀傷更多的是
好久沒能想念妳。單純、單向的思念,而非無盡的意義淘洗。
最艱難的時刻,我仍無法停止創造意義。再深的入戲,我仍無法擺脫清明。人竟擁有如此的結構性,永無法委身給情緒,為喜悲所撼動。
痛的時候,我仍釀造意義。潛入我屬於或不屬於的現場,染上傷懷。但我總又越過情感稜線,一行一行演算著。
妳離開了。我想為妳寫下什麼,可那些終究不關於哀傷,而是關於失語。消失的人無所謂語言,被留下的人,卻被語言的還一本正經、被意義的活躍,給徹底地傷了心。……關於哀傷,我為何與如何,可以說得更多?
城市作為加總的結果
我的城市並非一直是現在的模樣,它曾隨時日有變化:流入、流出、有所逝去、亦有累積與新誕生。可某一天起,它成為現在的樣子。我的城市是凝止的,像關於長生不老的古老妄想。
城裡的人會變老,我們遷往不同職位、進了別的公司,有家庭的人隨成員連動往階段進展,媒體出現有新面孔,城市頒佈新的法令並攪生新的抗爭,全新定位與功能的產品持續迸現,及其全套的推廣企劃。
然而,儘管一切細項都在動,可城市不老,而是一日日更清爽。沒有剩餘、沒有積累,像是旺盛的活動,只是不同部位互換著,加總的結果始終一樣。當人將衰亡,他所隸屬的城市卻可永保青春,則此間所上演的運作,會否是憑空填入了新一批年輕、可勝任的項目呢?仍慢慢變老的我,會否在某一天,發現自己的身份已被另外填入,而「我」則被拋棄往虛空。
……我與我的人們,共享的掛念,我們的記憶,為空無所吞噬。城市的總和是相同的,新的非誕生由舊的,舊的不被賦予醞釀的任務。當消耗完畢,等著的是徹底的消失。
任何規格的迷路
時間晚了,總想拖延得更晚,我喜愛在黯淡的街巷漫步。白天的城市,物事被一項一項指出;入了夜,原串連的勢力將被截斷,物事成為某種殘剩,它們承載著時間的洶湧而上、又不負責任地離開,在夜晚,世界被孤立為一座廢墟,一個被進進出出的人生,有蹂躪的氣味。
總只有在這時刻,才能逃脫生活的勢利。任何規模的遭遇,都在我心上寫下刻痕。我以為時間要停住了,水流將大幅改變;可無論是否有任何事情發生,我總之如幻覺般遺忘一切。
然後天光亮起,我把昨夜浮動的念頭捧在手心。
我需要任何規格的迷路。闖進一個小鎮,在那裡,夜已籠罩,燈微微亮著,空氣盪著無數起了一半的話語。我的活著,在無垠宇宙之正中,自成一格。
不再於夜晚睡去,不再於白日醒來。去到一個烏有之所,被囑咐私密的任務。我的城市為我備好訂製的夢。
所有豪華的浪費
日子離去,我將物件收藏起來。不再合身的襯衫、缺角的杯盤、場次和片名的墨色已淡得無法辨識的電影票根,它們佔用太多空間。我非為了念舊,畢竟生命的消逝無法被遏止、亦無法被反轉,我只是想從它們的邊緣,記得其他可能發生的世界。
那些物件來自迥異的脈絡,可當俱被拋入我的生活,它們處在的就是就共享同一套秩序。日子離去,物件如沙灘上的貝殼,撤除時序的框架,來不及訴說的心事,不合時宜的意味。……它們獨立於我面前持續展開的生活,藉著它們,我可以建構一個不在過去、亦不在未來的我的生活。
浸淫於其共通氣蘊,物件投射出一幅完成的景象,像一座主理一切惦記與痛楚的圖書館。如同每本書非自第一頁開始,亦不在最後一頁結束,終極的認見、固執與愛,被精確編碼。我不需要檢索,循氣味的漸層,路徑會自動打開。抽屜深處的密門,層架間的通道,所通往的故事互相矛盾,卻全是真的。我感覺憑空出現了一個我,他成為我的代理人,逡行於記憶暗角。很大的動作,最細的調節,在超越的瞬間回頭。物不再有任何一件顯得莫名與多餘,它們被組裝,流動不止。被正名的迷亂,所有豪華的浪費。
劇場
話語的觸鬚
每當見面,我們從上次談話中斷的地方接續。其間隔了兩天、三個禮拜或幾個月。當時為什麼中斷?或許被誰打岔、或時間到了、或未明的軋然停住。我們其中一人,斷然離開。
然後我們又見面了。總有一人起頭,妳,或我,從上回中斷的地方開始說。妳記得我說過的話,我耙梳著未盡的妳的思緒。
上回的談話慢慢被收束,浮冰般,震盪地,擦上新的論題。它們仍生澀,未有形體,它們被撥觸開,將被記得、被珍惜。下一回合面對面、坐著、看著對方,變得可能。我們這樣對抗時間,超越時間。
許久沒見到妳了。我感覺著那些即將落定的話語的觸鬚,熱切地探出,愈來愈確鑿地將鉤上什麼。
然後,妳推門進來。
也許終極的愛情,只好是……
一段感情可以有微微起落,有類近情趣的張力,但怎樣不俗的愛情也不願背叛、失卻特權。我得留住妳。
可如何留住一個完整的個體?怎樣是封閉卻舒服的安全感?怎樣是自由的的藝術?
應允她一完整自我,則我還能給出可被珍惜的什麼?我在那裡的哪裡?她有了什麼都有的世界,我怎麼讓她心動?
終極的愛情,只好是兩個人都懷抱著一點點的、可忍耐的不幸與遺憾。湊合著,我有妳為伴,我不交出自我,不允許妳實現自我。微妙的拉扯,在時光中稠化爲絕對性背景。我們將爲對方包裹,卻自以為仍有某個遠方。
我看到一個個「我」誕生、長大,而我原來這麼害怕這東西。每個我,都是一處失控的宇宙,我永遠追不上它。
作為一個難以嵌進現實的人,我錯在哪?能怎麼修正?這樣的我有資格擁有愛情嗎?我能讓他人幸福嗎?
我該找另個非現實的人嗎?還是我需要的是為我調和現實的人?又或者,我可以建構現實的定義,可以整頓邊界,成全我非要不可與絕對不要的東西,依由我的真實,創造出最適現實?
愛情不過是個關於放棄完美的誘惑,但我甘心被蒙蔽。
「生活」的質地
週五下午,辦公室照例是心不在焉,我對週末漠無感覺,一週復一週在特定午後處於這種默契的全體騷動,令我煩躁。突然,有人拍了拍我,是隔了幾條走道的同事。「嗨,今天是我上班最後一天,我下週就不進公司了。」他親切說。我抬頭看了他一眼,聳聳肩,「嗯。」我說。
我不討厭客套,但我無法做缺乏絕對性必要的事。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知道他要離職,但無論任何情況,我看不出真有哪些話是我必要說的。「在同一個辦公室這麼幾年,好像還沒跟你好好聊過。」他鄭重、有點緊張地說。
回想,當時或該浮現有千種想法,但並沒有。像是件不自然的事,我卻從迷霧中抓取到其中亦有的當然的成分。「是啊。」我說。他似乎已備有進一步的說明,當過程被簡陋關閉,他停在話語之間,顯出一種,預備地拉了很高、其中的路途卻逕被取消,的茫然。
噢。他頓了一下,「對了。」還沒能配合上進度地,他乾乾地說,但隨即又輕鬆起來,「明晚大家幫我辦了歡送會。我想你也一起來吧。」他是個乾脆的人。
他走回座位、還一路停下與其他同事笑談,他們之間,除去應該有的一點點的離情,就是尋常的週五光景。
我往那裡看去,偌大的辦公室,充滿活力的騷動,因為這同事的造訪,景色從一貫的灰淡,一點一點顯得立體。反而讓方才的交談變得不真實。
我怔想著更多。他回到座位,望了過來,半玩笑卻仍誠懇地對我做了個致意的手勢。我心裡像是被轉開了的水龍頭,源源湧著某種「生活」的質地,即是我眼中他人那種自然而然生活就轉動起來、兜進一干人、隨後自己才發現自己早已在其中,的溫潤或說無害感。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天。
戲劇性畫面
我總是把生活的段落看為一張張戲劇性畫面(tableau),我只能這樣記得事情。這些畫面獨立於它來自的脈絡。當場每個元素,從零開始,新的逢遇,互相辨識,探入彼此靈魂。
戲劇性畫面像憑空發生、隨即消失的情節斷片,不必延伸的線索,遽然的電光石火,自動連上自身存在。
我感覺在一個與下一個畫面間移動,以自己的邏輯,宣稱記憶,新寫一個合理故事。又或者反過來,紛飛的什麼,一個瞥見、一次心動、一回領會,被還原成一張張畫面。永恆的獨立劇場。
一切景觀有概念的打磨,由此模擬一部辭典、一部求生指南,像是真帶著這麼多、著魔這麼多、人生有這麼多。藉由戲劇性畫面的幻術,在原地,可以飛得最遠、潛得最深,所有最危險的旅程本來就該最安全。向光驅力
每天上班,把事做好,爬得更高,為何這麼理所當然?朝向光亮的驅力,是否來自對體系的過份信賴?
我情願地養肥這宇宙,可隨著愈奮力,我反而被排出,因為當超過了臨界點,我就無法繼續那樣相信。
某天醒來,我感覺錯過什麼,不再能聽與看得真切。接著,我無法泰然地收下面前的東西,找不著任何切入點去引用它。是這樣的脫落。
當我只能以日夜的流動幻夢去描摹視界,我的相信,就只能走那麼遠。可我在這體系所貢獻的不斷前行的凝視,匯成更高階的系統,那個系統沒有這種反思,沒有這個憂鬱。
時間
永恆的氾濫與匱乏
我總是掛念著想發展一套技術,通過它,生存可以獲得更為清晰的圖景。那該是個秩序嚴謹的過程。首先雕塑結實的自我狀態,接著將這樣的自己投入混沌,破解虛無。
離開制高點,潛入現實,讓設定的自我融入新脈絡,在裡頭發展直覺,隸屬進全新的動態平衡。在這階段,世界是無聲的。人與世界連動,意念勻稱。一個和諧的所在。
被收編的流動,仍是更大混沌的一部分,外頭的漶動仍牽曳它,差別在於,此刻我們已擁有一處邊界,不再輕易被現實撼動。接著,當有新的遭逢,我們走上前,試著理解湧上的直覺,是屬於舊的自我嗎,或已是新的呢?
我們來到相對安靜的生存狀態,不再有原先的靈活,必須更小心。這階段若作了錯誤判斷,會造成更大的傷害。這樣的過程,需反覆歷經,直到原本的自我蛻去。
當淘洗到更為純粹的自我,人各自的「非如此不可」慢慢確立。從這時起,我們能更澄澈地看。微細的成分,事物的邊界,終極的線條,都那麼清晰。
我感覺自己在等著某個答案,它或曾抽象而遙遠,可通過一次次的框取,我往那裡逼近。我讓空氣更流通一點,緩和因專注所帶來的緊張感。如果這是收成的一刻,我得做好在這之前所有該做好的事。
從空無之中造出一件存在……。生命中,我持續演練整套流程。許多時候我甚至感覺到這無止的操演,讓我成為一齣有限的劇場,某個擁有更多可能性的我的人生,被我親手抑制。
秩序的透明的美,一切流動被落定了某種看待。非如此不可的斷然,我願為此付出代價,開啟能相容於這個世界的我的創造。每日,我面對這樣的問題,一是永恆,一是永恆的匱乏。永恆,也許是擁有後設天賦的人類之某種幻覺,但延續一輩子的幻覺,只能是我的生命的一部份。而永恆的匱乏,每一天、每一人、另一天與另一人,徒勞與荒謬,正是現實。
錘鍊一個對的形式,以非如此不可的模樣,在永恆的氾濫與匱乏間存活下去。
迷宮中央的獸
倘若一本書裡有一落階梯,旋律裡有錨定之繩,電影是一扇門,那麼,一本書讀過一本書、旋律流向旋律、電影中的電影……,階梯連上階梯、繩結住繩、一扇門推出接著又一扇門……。一直下去,會怎樣呢?
我不會因此攀上任一處制高點,擁有更清明的視野,那些長長的路,構連著、繞出迷宮,我成為最中央的獸……。
有時,時間似是線性的,另些時候,它是環形、螺旋或無數瞬間的散置,再另些時候,它是條不回返的線,穿入一個與再一個不同介面,兜起的樣子,從最外頭看,顯出無限回歸的意味。
年輕時,不知道時間的結構可被改變,不知道永恆、不死、青春永駐,無論可不可能,那總之是很容易可以感受到的東西──你只要放開自己,不懷疑、不分心,隨一落階梯連通下一個、一條繩勾纏下一條、堅定地推開門……,只要這樣就夠了。
一個點上,我發現自己遺失了現實的肉體感。對生沒有好奇,對死沒有恐懼,痛只是另類的恍惚。
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是現實的部件,我可能隸屬給一個漂浮的幻覺整體。如同那些被寫出的書、被譜出的曲、被連綴著一格接一格的畫面,它們不支援所在的時代,僅僅為了未來的夢遊者,鋪設金色大道……。
理論狂熱者
「你是個理論狂熱者。」她滿臉淚水。這遣詞讓我分心,遺忘了面前的爭執。
她說得對,我想我是個理論狂熱者。畢竟,對情感暴漲的人而言,沒有理論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不親手研發更繁複理論套式,亦是不可想像的。
情感沒有輪廓,不需要支撐軸架,不在乎核心與邊陲。情感輕視設定與假說,不在乎效率,不要求結果。情感不知道人會死,誰都無法飛升地離開地面。情感是青春之泉,滿載譫妄。
我不介意那樣活,可我不能。我得用感受到的去催生詞彙,鍛造原則,然後是體系與系統。我用理論的抽象,製作傳說中的永動機(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第一套感觸,催生第一部永動機。永動機將平凡的經驗框架為新鮮的感觸。新的感觸抵住上限、催生再一部永動機,然後是新一套感觸……。唯有理論,讓我對抗黏熱的生存亢進。
唯有理論,我才能質疑現實。像在白色的密閉房間,用力將整個身體往牆撞去,竟也就穿牆而過了。密閉不過是前提約制的幻覺。
我沈醉地思考著,不再介意她的離開。
比哀傷更多的是
好久沒能想念妳。單純、單向的思念,而非無盡的意義淘洗。
最艱難的時刻,我仍無法停止創造意義。再深的入戲,我仍無法擺脫清明。人竟擁有如此的結構性,永無法委身給情緒,為喜悲所撼動。
痛的時候,我仍釀造意義。潛入我屬於或不屬於的現場,染上傷懷。但我總又越過情感稜線,一行一行演算著。
妳離開了。我想為妳寫下什麼,可那些終究不關於哀傷,而是關於失語。消失的人無所謂語言,被留下的人,卻被語言的還一本正經、被意義的活躍,給徹底地傷了心。……關於哀傷,我為何與如何,可以說得更多?
城市作為加總的結果
我的城市並非一直是現在的模樣,它曾隨時日有變化:流入、流出、有所逝去、亦有累積與新誕生。可某一天起,它成為現在的樣子。我的城市是凝止的,像關於長生不老的古老妄想。
城裡的人會變老,我們遷往不同職位、進了別的公司,有家庭的人隨成員連動往階段進展,媒體出現有新面孔,城市頒佈新的法令並攪生新的抗爭,全新定位與功能的產品持續迸現,及其全套的推廣企劃。
然而,儘管一切細項都在動,可城市不老,而是一日日更清爽。沒有剩餘、沒有積累,像是旺盛的活動,只是不同部位互換著,加總的結果始終一樣。當人將衰亡,他所隸屬的城市卻可永保青春,則此間所上演的運作,會否是憑空填入了新一批年輕、可勝任的項目呢?仍慢慢變老的我,會否在某一天,發現自己的身份已被另外填入,而「我」則被拋棄往虛空。
……我與我的人們,共享的掛念,我們的記憶,為空無所吞噬。城市的總和是相同的,新的非誕生由舊的,舊的不被賦予醞釀的任務。當消耗完畢,等著的是徹底的消失。
任何規格的迷路
時間晚了,總想拖延得更晚,我喜愛在黯淡的街巷漫步。白天的城市,物事被一項一項指出;入了夜,原串連的勢力將被截斷,物事成為某種殘剩,它們承載著時間的洶湧而上、又不負責任地離開,在夜晚,世界被孤立為一座廢墟,一個被進進出出的人生,有蹂躪的氣味。
總只有在這時刻,才能逃脫生活的勢利。任何規模的遭遇,都在我心上寫下刻痕。我以為時間要停住了,水流將大幅改變;可無論是否有任何事情發生,我總之如幻覺般遺忘一切。
然後天光亮起,我把昨夜浮動的念頭捧在手心。
我需要任何規格的迷路。闖進一個小鎮,在那裡,夜已籠罩,燈微微亮著,空氣盪著無數起了一半的話語。我的活著,在無垠宇宙之正中,自成一格。
不再於夜晚睡去,不再於白日醒來。去到一個烏有之所,被囑咐私密的任務。我的城市為我備好訂製的夢。
所有豪華的浪費
日子離去,我將物件收藏起來。不再合身的襯衫、缺角的杯盤、場次和片名的墨色已淡得無法辨識的電影票根,它們佔用太多空間。我非為了念舊,畢竟生命的消逝無法被遏止、亦無法被反轉,我只是想從它們的邊緣,記得其他可能發生的世界。
那些物件來自迥異的脈絡,可當俱被拋入我的生活,它們處在的就是就共享同一套秩序。日子離去,物件如沙灘上的貝殼,撤除時序的框架,來不及訴說的心事,不合時宜的意味。……它們獨立於我面前持續展開的生活,藉著它們,我可以建構一個不在過去、亦不在未來的我的生活。
浸淫於其共通氣蘊,物件投射出一幅完成的景象,像一座主理一切惦記與痛楚的圖書館。如同每本書非自第一頁開始,亦不在最後一頁結束,終極的認見、固執與愛,被精確編碼。我不需要檢索,循氣味的漸層,路徑會自動打開。抽屜深處的密門,層架間的通道,所通往的故事互相矛盾,卻全是真的。我感覺憑空出現了一個我,他成為我的代理人,逡行於記憶暗角。很大的動作,最細的調節,在超越的瞬間回頭。物不再有任何一件顯得莫名與多餘,它們被組裝,流動不止。被正名的迷亂,所有豪華的浪費。
劇場
話語的觸鬚
每當見面,我們從上次談話中斷的地方接續。其間隔了兩天、三個禮拜或幾個月。當時為什麼中斷?或許被誰打岔、或時間到了、或未明的軋然停住。我們其中一人,斷然離開。
然後我們又見面了。總有一人起頭,妳,或我,從上回中斷的地方開始說。妳記得我說過的話,我耙梳著未盡的妳的思緒。
上回的談話慢慢被收束,浮冰般,震盪地,擦上新的論題。它們仍生澀,未有形體,它們被撥觸開,將被記得、被珍惜。下一回合面對面、坐著、看著對方,變得可能。我們這樣對抗時間,超越時間。
許久沒見到妳了。我感覺著那些即將落定的話語的觸鬚,熱切地探出,愈來愈確鑿地將鉤上什麼。
然後,妳推門進來。
也許終極的愛情,只好是……
一段感情可以有微微起落,有類近情趣的張力,但怎樣不俗的愛情也不願背叛、失卻特權。我得留住妳。
可如何留住一個完整的個體?怎樣是封閉卻舒服的安全感?怎樣是自由的的藝術?
應允她一完整自我,則我還能給出可被珍惜的什麼?我在那裡的哪裡?她有了什麼都有的世界,我怎麼讓她心動?
終極的愛情,只好是兩個人都懷抱著一點點的、可忍耐的不幸與遺憾。湊合著,我有妳為伴,我不交出自我,不允許妳實現自我。微妙的拉扯,在時光中稠化爲絕對性背景。我們將爲對方包裹,卻自以為仍有某個遠方。
我看到一個個「我」誕生、長大,而我原來這麼害怕這東西。每個我,都是一處失控的宇宙,我永遠追不上它。
作為一個難以嵌進現實的人,我錯在哪?能怎麼修正?這樣的我有資格擁有愛情嗎?我能讓他人幸福嗎?
我該找另個非現實的人嗎?還是我需要的是為我調和現實的人?又或者,我可以建構現實的定義,可以整頓邊界,成全我非要不可與絕對不要的東西,依由我的真實,創造出最適現實?
愛情不過是個關於放棄完美的誘惑,但我甘心被蒙蔽。
「生活」的質地
週五下午,辦公室照例是心不在焉,我對週末漠無感覺,一週復一週在特定午後處於這種默契的全體騷動,令我煩躁。突然,有人拍了拍我,是隔了幾條走道的同事。「嗨,今天是我上班最後一天,我下週就不進公司了。」他親切說。我抬頭看了他一眼,聳聳肩,「嗯。」我說。
我不討厭客套,但我無法做缺乏絕對性必要的事。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知道他要離職,但無論任何情況,我看不出真有哪些話是我必要說的。「在同一個辦公室這麼幾年,好像還沒跟你好好聊過。」他鄭重、有點緊張地說。
回想,當時或該浮現有千種想法,但並沒有。像是件不自然的事,我卻從迷霧中抓取到其中亦有的當然的成分。「是啊。」我說。他似乎已備有進一步的說明,當過程被簡陋關閉,他停在話語之間,顯出一種,預備地拉了很高、其中的路途卻逕被取消,的茫然。
噢。他頓了一下,「對了。」還沒能配合上進度地,他乾乾地說,但隨即又輕鬆起來,「明晚大家幫我辦了歡送會。我想你也一起來吧。」他是個乾脆的人。
他走回座位、還一路停下與其他同事笑談,他們之間,除去應該有的一點點的離情,就是尋常的週五光景。
我往那裡看去,偌大的辦公室,充滿活力的騷動,因為這同事的造訪,景色從一貫的灰淡,一點一點顯得立體。反而讓方才的交談變得不真實。
我怔想著更多。他回到座位,望了過來,半玩笑卻仍誠懇地對我做了個致意的手勢。我心裡像是被轉開了的水龍頭,源源湧著某種「生活」的質地,即是我眼中他人那種自然而然生活就轉動起來、兜進一干人、隨後自己才發現自己早已在其中,的溫潤或說無害感。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天。
戲劇性畫面
我總是把生活的段落看為一張張戲劇性畫面(tableau),我只能這樣記得事情。這些畫面獨立於它來自的脈絡。當場每個元素,從零開始,新的逢遇,互相辨識,探入彼此靈魂。
戲劇性畫面像憑空發生、隨即消失的情節斷片,不必延伸的線索,遽然的電光石火,自動連上自身存在。
我感覺在一個與下一個畫面間移動,以自己的邏輯,宣稱記憶,新寫一個合理故事。又或者反過來,紛飛的什麼,一個瞥見、一次心動、一回領會,被還原成一張張畫面。永恆的獨立劇場。
一切景觀有概念的打磨,由此模擬一部辭典、一部求生指南,像是真帶著這麼多、著魔這麼多、人生有這麼多。藉由戲劇性畫面的幻術,在原地,可以飛得最遠、潛得最深,所有最危險的旅程本來就該最安全。向光驅力
每天上班,把事做好,爬得更高,為何這麼理所當然?朝向光亮的驅力,是否來自對體系的過份信賴?
我情願地養肥這宇宙,可隨著愈奮力,我反而被排出,因為當超過了臨界點,我就無法繼續那樣相信。
某天醒來,我感覺錯過什麼,不再能聽與看得真切。接著,我無法泰然地收下面前的東西,找不著任何切入點去引用它。是這樣的脫落。
當我只能以日夜的流動幻夢去描摹視界,我的相信,就只能走那麼遠。可我在這體系所貢獻的不斷前行的凝視,匯成更高階的系統,那個系統沒有這種反思,沒有這個憂鬱。
時間
永恆的氾濫與匱乏
我總是掛念著想發展一套技術,通過它,生存可以獲得更為清晰的圖景。那該是個秩序嚴謹的過程。首先雕塑結實的自我狀態,接著將這樣的自己投入混沌,破解虛無。
離開制高點,潛入現實,讓設定的自我融入新脈絡,在裡頭發展直覺,隸屬進全新的動態平衡。在這階段,世界是無聲的。人與世界連動,意念勻稱。一個和諧的所在。
被收編的流動,仍是更大混沌的一部分,外頭的漶動仍牽曳它,差別在於,此刻我們已擁有一處邊界,不再輕易被現實撼動。接著,當有新的遭逢,我們走上前,試著理解湧上的直覺,是屬於舊的自我嗎,或已是新的呢?
我們來到相對安靜的生存狀態,不再有原先的靈活,必須更小心。這階段若作了錯誤判斷,會造成更大的傷害。這樣的過程,需反覆歷經,直到原本的自我蛻去。
當淘洗到更為純粹的自我,人各自的「非如此不可」慢慢確立。從這時起,我們能更澄澈地看。微細的成分,事物的邊界,終極的線條,都那麼清晰。
我感覺自己在等著某個答案,它或曾抽象而遙遠,可通過一次次的框取,我往那裡逼近。我讓空氣更流通一點,緩和因專注所帶來的緊張感。如果這是收成的一刻,我得做好在這之前所有該做好的事。
從空無之中造出一件存在……。生命中,我持續演練整套流程。許多時候我甚至感覺到這無止的操演,讓我成為一齣有限的劇場,某個擁有更多可能性的我的人生,被我親手抑制。
秩序的透明的美,一切流動被落定了某種看待。非如此不可的斷然,我願為此付出代價,開啟能相容於這個世界的我的創造。每日,我面對這樣的問題,一是永恆,一是永恆的匱乏。永恆,也許是擁有後設天賦的人類之某種幻覺,但延續一輩子的幻覺,只能是我的生命的一部份。而永恆的匱乏,每一天、每一人、另一天與另一人,徒勞與荒謬,正是現實。
錘鍊一個對的形式,以非如此不可的模樣,在永恆的氾濫與匱乏間存活下去。
迷宮中央的獸
倘若一本書裡有一落階梯,旋律裡有錨定之繩,電影是一扇門,那麼,一本書讀過一本書、旋律流向旋律、電影中的電影……,階梯連上階梯、繩結住繩、一扇門推出接著又一扇門……。一直下去,會怎樣呢?
我不會因此攀上任一處制高點,擁有更清明的視野,那些長長的路,構連著、繞出迷宮,我成為最中央的獸……。
有時,時間似是線性的,另些時候,它是環形、螺旋或無數瞬間的散置,再另些時候,它是條不回返的線,穿入一個與再一個不同介面,兜起的樣子,從最外頭看,顯出無限回歸的意味。
年輕時,不知道時間的結構可被改變,不知道永恆、不死、青春永駐,無論可不可能,那總之是很容易可以感受到的東西──你只要放開自己,不懷疑、不分心,隨一落階梯連通下一個、一條繩勾纏下一條、堅定地推開門……,只要這樣就夠了。
一個點上,我發現自己遺失了現實的肉體感。對生沒有好奇,對死沒有恐懼,痛只是另類的恍惚。
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是現實的部件,我可能隸屬給一個漂浮的幻覺整體。如同那些被寫出的書、被譜出的曲、被連綴著一格接一格的畫面,它們不支援所在的時代,僅僅為了未來的夢遊者,鋪設金色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