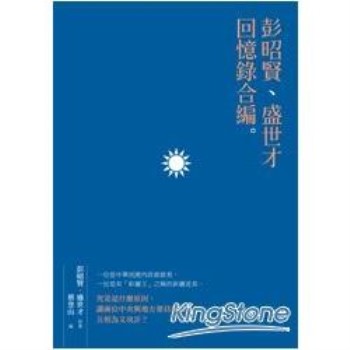一、從流落哈爾濱賣文為活說起
筆者按:彭昭賢先生早歲留學蘇俄,當年在莫斯科即為中國留學生中之突出人物。返國後,服官從政,歷居要津,為國府行憲後之首任內政部長。李宗仁代總統時期,與中共進行和談,曾遴選彭氏為北上和談代表之一,但為中共所拒絕接受。自大陸變色,彭氏南來香港,旋即東渡扶桑,隱居彼邦,不再與聞政事。
刻下彭氏應筆者之請,承允於旅居之暇,講述當年親身目擊之種種近代事蹟,由筆者記錄成帙,交由《春秋》發表,其中頗多從未為外間所知之秘辛軼聞,彌足珍貴,當為關心中國近代史實者所歡迎。爰於本文代付刊之始,謹綴數語,敬告讀者。
日作家談莫斯科大學
我月前旅居日本東京時,遇見一位到過蘇俄的日本作家,彼此在閒談中,不覺談到了蘇俄的「巨大主義」。據這位作家說:
「我參觀過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和莫斯科大學。地下鐵道的四通八達的路線佈滿於莫斯科各個角落。每一車站的建築材料都是用大理石和花岡石,既高貴而又大方。除了蘇俄以外,恐怕任何國家都不會對公共建築下這麼大的成本!」
這位作家提到莫斯科大學龐大規模的時候,他又說:
「莫斯科大學之大,已經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有一次我問該校負責招待的人員道:『貴究竟有多大的範圍?』那位招待員朝我笑了笑,用手一指我們正在參觀的那間教室說:『像這樣大的房子(意思是包括另外部份的宿舍房間在內),你如果每一間都走進去看一遍,又如果你在每一間房裡只停留五分鐘的話,全部需要的時間大概是三十年吧。』」
這位作家於說罷了蘇俄的「巨大主義」之後,接著又很幽默的提到了蘇俄之「小」。
他說他曾經去參觀過一家平民小學,發現過一件很有趣的事。他到那家小學參觀之時,正好碰上教師們在把彩色的列寧照片分發給每名小學生各人一張,並且吩咐學生們回家以後要懸掛在牆壁上。
這時他看見一名身體不甚健康的小孩子站起來說:
「報告老師,我們家裡沒有牆。」
「為什麼?」教師非常詫異的問。
小學生回答說:
「我們住的那間房子,一共有五戶人家,因為沒有間隔,每家只是堆些雜物箱籠作為分界,甲住在東邊一角,乙住在西邊一角,丙住在南邊一角,丁住在北部一角。我們這一家卻住在中間,所以沒有牆。」
小學生這樣一說,立即引起全課室裡面的人哄堂大笑。
疑團莫釋請教彭昭賢
這種情形,和前面他所介紹蘇俄的「巨大主義」,恰恰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我知道我國行憲後的首任內政部部長彭昭賢先生,過去曾在莫斯科大學就讀,是中國有名的「蘇俄通」,剛巧彭先生旅居東瀛,和我又時常見面,所以我就拿這個問題,向彭氏去請教,據彭告訴我:
「我在莫斯科大學就讀時是一九二一年,那時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己經有四五萬人,裡面包括有政治系、經濟系、法律系、外國語文系、教育系、文學系、工科、醫科等等。談到它的規模,的確非常的大,至於後來又擴充到什麼程度,我雖不十分清楚,但像那位日本作家所說的未免太駭人了,如果不是他把三十天或三個月,誤聽為三十年,那就是向他作說明的那位招待員,有意的誇張。你要知道,在蘇俄的誇大主義之下,對外宣傳,多數是要予以擴大和渲染的。」
話匣子打開以後,我的靈機一動,便立即向彭氏提出一項要求說:
「香港出版一本《春秋》雜誌,是專門刊載近代珍史的,你也看過不少了,你老兄服官從政數十年,在宦海裡耳濡目染,親身經歷的事,必多富有歷史價值的珍貴史料,如今大家既都作客東京,旅窗無俚,何不就記憶所及,作一個閒話開元天寶的白頭宮女?只要你老兄不嫌我的文筆粗陋,儘可你講我記,寫些出來,寄交《春秋》發表,讓海外讀者,多知道些近代的故實,亦旅中一樂也。」
彭氏笑了笑說:「事情隔了很久,你叫我從何說起?」
我說:「我們不妨就從你老兄當年赴莫斯科大學讀書說起。我知道你府上是山東牟平縣,但在數十年前風氣那樣不開通的時代,你是怎會跑到莫斯科大學去讀書的呢?」
彭微笑著說:「那還不是因為年青人好奇心理,想多了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所以才千辛萬苦跑到蘇聯去探險。」
「後來呢?」我又追問了一句。
彭氏非常感慨的說:「結果還不是使我非常的失望!否則,我今天就不會住在東京了。」
早年投考醫校的經過
原來,彭先生的老家牟平縣屬於山東登州府所管,為蓬萊的鄰縣。那裡,在膠州半島算是一個很富饒的縣份,但由於交通不便,貨物不能暢流,風氣仍甚閉塞。彭的家中擁有二十畝地的一處果園。另外在青島和煙台兩地還開著兩間規模不算太小的絲房。
當彭氏十幾歲的時候,因為家中接二連三發生了幾件不如意的事情,屢遭損折,家道中落。彭的年紀雖輕,卻是一個知道求上進的青年,眼看家中的經濟情況,一天不如一天,若要繼續求學,已經沒有可能,於是,便打算用自力更生的辦法到外埠去讀書。
他既有了這個念頭,便每天留心閱讀報紙,以便找尋機會。某日,他終於看到青島報紙上登載著一條「長春南滿醫學校」招生的廣告。經他進一步的設法打聽,知道這家醫學校是「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所主辦。倘若能夠考取,不但學、膳、宿、服裝等項,都是官費,而且在醫藥、儀器和教師方面,該校也都夠上世界水準。
彭為了要減輕家庭負擔,遂決心去投考這間學校。找了一個機會先和他的老太爺作了一次說明式的談判,並請老人家替他籌措旅費。
彭老先生聽到自己的兒子如此上進求學,自然非常高興,立即答應了彭的要求。彭計算了一下日子,由青島坐船去長春,在投考時間上還有餘裕,所以心裡並不怎樣著急。
但為了要籌措那一筆為數不多的旅費,竟使彭老先生傷透腦筋,最後只差了大洋四元怎樣也湊不上,結果還是用五分利錢借了一筆高利貸,才算勉強湊足。
彭氏由青島搭船到了大連,正遇上那幾天豪雨不止,把南滿鐵路鐵嶺段的路基沖毀了,迫使彭在大連困住了幾日,不能前進,這時他心中盤算著:如果在兩三天時間內鐵路修不好,不但學校的考期趕不上,而且所攜帶的旅費也成了問題,焦灼之情,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幸而到了翌日的下午,有了通車的訊息,他馬上收拾行李,趕著購買車票去了長春。
事情也真不巧,就在他抵達長春的那天,正是南滿醫學校舉行入學考試的日子。他絲毫不敢耽擱,立即僱了一輛人力車,飛奔往南滿醫學校而去。
走投無路闖到哈爾濱
我們現在回想,這大概就是所謂命運的安排吧!彭氏如果那次考入了醫學校,又怎會有他後來的那段輝煌事業呢?彭當日趕到學校一問,始知考試恰告終了。他曾設法面見教務長苦苦請求准予補考。可是那個日本人說什麼也不肯答應。
這時的彭氏好似在萬丈高樓上失足一樣,立即陷於進退兩難的窘境,他離開學校,垂頭喪氣的走回了旅舍,一路走,一路想:怎麼辦呢?回去吧,無顏見江東父老;留在這裡吧?又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留在長春又能幹什麼呢?
正在胡思亂想、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猛然抬頭,看見高?在旅舍對面的「哈爾濱煙草公司」的一塊廣告招牌。他靈機一動,心裡默想著:哈爾濱是一個新開闢的碼頭,我何不到那裡去碰碰運氣,無論是半工半讀,或是找點事做都可以。
彭自己計算了一下,口袋裡還剩有十幾元的旅費,到哈爾濱去若坐四等火車(彼時的中東鐵路有四等火車),由長春到哈爾濱的車票只需一元四五角錢,到了哈爾濱以後住小旅館大約只需兩角錢一天,再加上吃飯,一天四五角錢也就夠應付了,在哈爾濱住上十天半月,慢慢打主意還不成問題。他想到這裡,把心一橫說:好!就這麼辦。
彭上了火車,找一個臨窗的位子坐好,由於滿懷心事,也懶得向外面瀏覽沿途的風景,只呆呆的靠在那裡想心事。這時坐在彭對面的有一位穿著非常樸素的山東老鄉,他注視了彭很久,忽然開口問彭道:「小兄弟貴姓?」
「姓彭。」
「到什麼地方去?」
「哈爾濱。」
「到那裡做什麼哪?」
「哦!哦!哦!」
彭哦了半天都答不出來,那個人知道彭是一個未曾出過遠門的小伙子,也不再使他為難,即自我介紹的道:「我姓韓,名字叫復興。小兄弟你是新出門吧!有什麼話儘管說,一個人出門在外,誰還不是靠著朋友照應呢。」
旅途有巧遇酒舖容身
彭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忽然遇見了一位老鄉,心中別提有多麼高興了!除了尊稱他一聲:「韓大哥」之外,馬上便把他由家中出來到長春投考「南滿醫學院」過了考期這段經過對韓說了一遍。韓楞了一下問道:
「小兄弟你到哈爾濱去準備找什麼人哪?」
彭答:「哈爾濱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韓聽罷之後,毫不遲疑地向彭道:「小兄弟!你在哈爾濱既然沒有熟人,如果你不嫌棄的話,請住到我那裡去好不好?」
彭答:「我同韓大哥萍水相逢,怎好去打擾呢?」
韓道:「既然老鄉,就毋須客套,你孤零零的住在小旅館裡決不是辦法。」
兩個人經過這番談話,彭的心情為之一振,一路上和韓有說有笑的頗不寂寞!
韓那時還未結婚,光桿一人在哈爾濱「道裡」(按:以中東鐵路為界,在鐵路以東的地方稱為「道外」,鐵路以西的地方便叫「道裡」)大石頭道開了一家賣酒的小舖子。這條路完全是用麻石鋪成的,哈爾濱的人在習慣上都把它叫做大石頭道。那間酒舖的招牌就用韓自己的名字叫:「復興號」。
酒舖只有一間小小的門面。在一進門的地方放了一個櫃台,前面做生意,後面放了兩張小床,由韓和他僱用的一名伙計分住。
彭住到韓那裡之後,韓特別把自己睡的那小床讓了出來給彭睡,他自己到了晚間就睡在櫃台上面。彭雖暫時有了住處,但未來的日子怎樣打發呢?找事做或者讀書,他心中不能不有一個打算。
天無絕人路報館投稿
那時哈爾濱一共有兩家中文報館,一家是《東陲日報》,另一家是《東昇報》。彭在家鄉的時候,便曾經向青島的報館投過稿,對於報館的工作,他自信還勉強可以幹得來,於是,他便打算向報館去謀一個訪員的職位。
主意拿定之後,到了第二天他就跑到《東陲日報》去求見該報的編輯王目空先生,先對王簡單的說明來意,請予安插。王告訴彭,他們的報館不用訪員,但如果彭能寫稿則非常歡迎。
王目空對彭的印象似乎不錯,他還向彭道:「本報的消息稿費是兩毛錢一條,字數不超過二百字,稿費每半個月結算一次。」
彭得到了這麼一個結果,總算是不虛此行。他千謝萬謝的由《東陲日報》走出來之後,又跑到《東昇報》去見到了一位姓周的編輯。經接談後,所得的答覆,和王目空告訴他的完全一樣。
彭回到酒舖,想了一想,在暫時沒有辦法的時候,能先投投稿也好。遂在附近紙筆店買了一些紙張應用文具,開始在街頭東遊西逛,獵取社會新聞,經過一整天的努力,居然寫了四五條小稿,每稿都謄寫了兩份,分別的送給《東陲日報》和《東昇報》兩家報館。如果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這就叫做「一稿兩投」了。
第二天早晨,彭很早就起床,來不及漱洗,趕忙跑到大街轉角的貼報處一看,兩家報館把他的稿子都登出來了。他在精神苦悶之中,忽然找到這麼一個出路,眼睛一亮,心境也寬了許多。他約略計算了一下,每天如果能夠寫四五條新聞,分投於兩家報館,起碼可以拿到一元幾角一天的稿費,眼前的生活是不會發生問題了。
從此以後,他每天一早起來就跑到外面去做採訪新聞的工作,有時候找不到消息就自己編上一兩條,總以每天能寫四五條為度。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凡是經他投送進去稿子,報館是一律照登,從未打過退堂鼓,因此,格外使他充滿了信心。過了一些日子,他從兩家報館中領到稿費,還特別請韓大哥和他的伙計到「道外」去吃一頓小館子,飯罷又去看京戲。
筆者按:彭昭賢先生早歲留學蘇俄,當年在莫斯科即為中國留學生中之突出人物。返國後,服官從政,歷居要津,為國府行憲後之首任內政部長。李宗仁代總統時期,與中共進行和談,曾遴選彭氏為北上和談代表之一,但為中共所拒絕接受。自大陸變色,彭氏南來香港,旋即東渡扶桑,隱居彼邦,不再與聞政事。
刻下彭氏應筆者之請,承允於旅居之暇,講述當年親身目擊之種種近代事蹟,由筆者記錄成帙,交由《春秋》發表,其中頗多從未為外間所知之秘辛軼聞,彌足珍貴,當為關心中國近代史實者所歡迎。爰於本文代付刊之始,謹綴數語,敬告讀者。
日作家談莫斯科大學
我月前旅居日本東京時,遇見一位到過蘇俄的日本作家,彼此在閒談中,不覺談到了蘇俄的「巨大主義」。據這位作家說:
「我參觀過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和莫斯科大學。地下鐵道的四通八達的路線佈滿於莫斯科各個角落。每一車站的建築材料都是用大理石和花岡石,既高貴而又大方。除了蘇俄以外,恐怕任何國家都不會對公共建築下這麼大的成本!」
這位作家提到莫斯科大學龐大規模的時候,他又說:
「莫斯科大學之大,已經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有一次我問該校負責招待的人員道:『貴究竟有多大的範圍?』那位招待員朝我笑了笑,用手一指我們正在參觀的那間教室說:『像這樣大的房子(意思是包括另外部份的宿舍房間在內),你如果每一間都走進去看一遍,又如果你在每一間房裡只停留五分鐘的話,全部需要的時間大概是三十年吧。』」
這位作家於說罷了蘇俄的「巨大主義」之後,接著又很幽默的提到了蘇俄之「小」。
他說他曾經去參觀過一家平民小學,發現過一件很有趣的事。他到那家小學參觀之時,正好碰上教師們在把彩色的列寧照片分發給每名小學生各人一張,並且吩咐學生們回家以後要懸掛在牆壁上。
這時他看見一名身體不甚健康的小孩子站起來說:
「報告老師,我們家裡沒有牆。」
「為什麼?」教師非常詫異的問。
小學生回答說:
「我們住的那間房子,一共有五戶人家,因為沒有間隔,每家只是堆些雜物箱籠作為分界,甲住在東邊一角,乙住在西邊一角,丙住在南邊一角,丁住在北部一角。我們這一家卻住在中間,所以沒有牆。」
小學生這樣一說,立即引起全課室裡面的人哄堂大笑。
疑團莫釋請教彭昭賢
這種情形,和前面他所介紹蘇俄的「巨大主義」,恰恰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我知道我國行憲後的首任內政部部長彭昭賢先生,過去曾在莫斯科大學就讀,是中國有名的「蘇俄通」,剛巧彭先生旅居東瀛,和我又時常見面,所以我就拿這個問題,向彭氏去請教,據彭告訴我:
「我在莫斯科大學就讀時是一九二一年,那時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己經有四五萬人,裡面包括有政治系、經濟系、法律系、外國語文系、教育系、文學系、工科、醫科等等。談到它的規模,的確非常的大,至於後來又擴充到什麼程度,我雖不十分清楚,但像那位日本作家所說的未免太駭人了,如果不是他把三十天或三個月,誤聽為三十年,那就是向他作說明的那位招待員,有意的誇張。你要知道,在蘇俄的誇大主義之下,對外宣傳,多數是要予以擴大和渲染的。」
話匣子打開以後,我的靈機一動,便立即向彭氏提出一項要求說:
「香港出版一本《春秋》雜誌,是專門刊載近代珍史的,你也看過不少了,你老兄服官從政數十年,在宦海裡耳濡目染,親身經歷的事,必多富有歷史價值的珍貴史料,如今大家既都作客東京,旅窗無俚,何不就記憶所及,作一個閒話開元天寶的白頭宮女?只要你老兄不嫌我的文筆粗陋,儘可你講我記,寫些出來,寄交《春秋》發表,讓海外讀者,多知道些近代的故實,亦旅中一樂也。」
彭氏笑了笑說:「事情隔了很久,你叫我從何說起?」
我說:「我們不妨就從你老兄當年赴莫斯科大學讀書說起。我知道你府上是山東牟平縣,但在數十年前風氣那樣不開通的時代,你是怎會跑到莫斯科大學去讀書的呢?」
彭微笑著說:「那還不是因為年青人好奇心理,想多了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所以才千辛萬苦跑到蘇聯去探險。」
「後來呢?」我又追問了一句。
彭氏非常感慨的說:「結果還不是使我非常的失望!否則,我今天就不會住在東京了。」
早年投考醫校的經過
原來,彭先生的老家牟平縣屬於山東登州府所管,為蓬萊的鄰縣。那裡,在膠州半島算是一個很富饒的縣份,但由於交通不便,貨物不能暢流,風氣仍甚閉塞。彭的家中擁有二十畝地的一處果園。另外在青島和煙台兩地還開著兩間規模不算太小的絲房。
當彭氏十幾歲的時候,因為家中接二連三發生了幾件不如意的事情,屢遭損折,家道中落。彭的年紀雖輕,卻是一個知道求上進的青年,眼看家中的經濟情況,一天不如一天,若要繼續求學,已經沒有可能,於是,便打算用自力更生的辦法到外埠去讀書。
他既有了這個念頭,便每天留心閱讀報紙,以便找尋機會。某日,他終於看到青島報紙上登載著一條「長春南滿醫學校」招生的廣告。經他進一步的設法打聽,知道這家醫學校是「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所主辦。倘若能夠考取,不但學、膳、宿、服裝等項,都是官費,而且在醫藥、儀器和教師方面,該校也都夠上世界水準。
彭為了要減輕家庭負擔,遂決心去投考這間學校。找了一個機會先和他的老太爺作了一次說明式的談判,並請老人家替他籌措旅費。
彭老先生聽到自己的兒子如此上進求學,自然非常高興,立即答應了彭的要求。彭計算了一下日子,由青島坐船去長春,在投考時間上還有餘裕,所以心裡並不怎樣著急。
但為了要籌措那一筆為數不多的旅費,竟使彭老先生傷透腦筋,最後只差了大洋四元怎樣也湊不上,結果還是用五分利錢借了一筆高利貸,才算勉強湊足。
彭氏由青島搭船到了大連,正遇上那幾天豪雨不止,把南滿鐵路鐵嶺段的路基沖毀了,迫使彭在大連困住了幾日,不能前進,這時他心中盤算著:如果在兩三天時間內鐵路修不好,不但學校的考期趕不上,而且所攜帶的旅費也成了問題,焦灼之情,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幸而到了翌日的下午,有了通車的訊息,他馬上收拾行李,趕著購買車票去了長春。
事情也真不巧,就在他抵達長春的那天,正是南滿醫學校舉行入學考試的日子。他絲毫不敢耽擱,立即僱了一輛人力車,飛奔往南滿醫學校而去。
走投無路闖到哈爾濱
我們現在回想,這大概就是所謂命運的安排吧!彭氏如果那次考入了醫學校,又怎會有他後來的那段輝煌事業呢?彭當日趕到學校一問,始知考試恰告終了。他曾設法面見教務長苦苦請求准予補考。可是那個日本人說什麼也不肯答應。
這時的彭氏好似在萬丈高樓上失足一樣,立即陷於進退兩難的窘境,他離開學校,垂頭喪氣的走回了旅舍,一路走,一路想:怎麼辦呢?回去吧,無顏見江東父老;留在這裡吧?又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留在長春又能幹什麼呢?
正在胡思亂想、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猛然抬頭,看見高?在旅舍對面的「哈爾濱煙草公司」的一塊廣告招牌。他靈機一動,心裡默想著:哈爾濱是一個新開闢的碼頭,我何不到那裡去碰碰運氣,無論是半工半讀,或是找點事做都可以。
彭自己計算了一下,口袋裡還剩有十幾元的旅費,到哈爾濱去若坐四等火車(彼時的中東鐵路有四等火車),由長春到哈爾濱的車票只需一元四五角錢,到了哈爾濱以後住小旅館大約只需兩角錢一天,再加上吃飯,一天四五角錢也就夠應付了,在哈爾濱住上十天半月,慢慢打主意還不成問題。他想到這裡,把心一橫說:好!就這麼辦。
彭上了火車,找一個臨窗的位子坐好,由於滿懷心事,也懶得向外面瀏覽沿途的風景,只呆呆的靠在那裡想心事。這時坐在彭對面的有一位穿著非常樸素的山東老鄉,他注視了彭很久,忽然開口問彭道:「小兄弟貴姓?」
「姓彭。」
「到什麼地方去?」
「哈爾濱。」
「到那裡做什麼哪?」
「哦!哦!哦!」
彭哦了半天都答不出來,那個人知道彭是一個未曾出過遠門的小伙子,也不再使他為難,即自我介紹的道:「我姓韓,名字叫復興。小兄弟你是新出門吧!有什麼話儘管說,一個人出門在外,誰還不是靠著朋友照應呢。」
旅途有巧遇酒舖容身
彭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忽然遇見了一位老鄉,心中別提有多麼高興了!除了尊稱他一聲:「韓大哥」之外,馬上便把他由家中出來到長春投考「南滿醫學院」過了考期這段經過對韓說了一遍。韓楞了一下問道:
「小兄弟你到哈爾濱去準備找什麼人哪?」
彭答:「哈爾濱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韓聽罷之後,毫不遲疑地向彭道:「小兄弟!你在哈爾濱既然沒有熟人,如果你不嫌棄的話,請住到我那裡去好不好?」
彭答:「我同韓大哥萍水相逢,怎好去打擾呢?」
韓道:「既然老鄉,就毋須客套,你孤零零的住在小旅館裡決不是辦法。」
兩個人經過這番談話,彭的心情為之一振,一路上和韓有說有笑的頗不寂寞!
韓那時還未結婚,光桿一人在哈爾濱「道裡」(按:以中東鐵路為界,在鐵路以東的地方稱為「道外」,鐵路以西的地方便叫「道裡」)大石頭道開了一家賣酒的小舖子。這條路完全是用麻石鋪成的,哈爾濱的人在習慣上都把它叫做大石頭道。那間酒舖的招牌就用韓自己的名字叫:「復興號」。
酒舖只有一間小小的門面。在一進門的地方放了一個櫃台,前面做生意,後面放了兩張小床,由韓和他僱用的一名伙計分住。
彭住到韓那裡之後,韓特別把自己睡的那小床讓了出來給彭睡,他自己到了晚間就睡在櫃台上面。彭雖暫時有了住處,但未來的日子怎樣打發呢?找事做或者讀書,他心中不能不有一個打算。
天無絕人路報館投稿
那時哈爾濱一共有兩家中文報館,一家是《東陲日報》,另一家是《東昇報》。彭在家鄉的時候,便曾經向青島的報館投過稿,對於報館的工作,他自信還勉強可以幹得來,於是,他便打算向報館去謀一個訪員的職位。
主意拿定之後,到了第二天他就跑到《東陲日報》去求見該報的編輯王目空先生,先對王簡單的說明來意,請予安插。王告訴彭,他們的報館不用訪員,但如果彭能寫稿則非常歡迎。
王目空對彭的印象似乎不錯,他還向彭道:「本報的消息稿費是兩毛錢一條,字數不超過二百字,稿費每半個月結算一次。」
彭得到了這麼一個結果,總算是不虛此行。他千謝萬謝的由《東陲日報》走出來之後,又跑到《東昇報》去見到了一位姓周的編輯。經接談後,所得的答覆,和王目空告訴他的完全一樣。
彭回到酒舖,想了一想,在暫時沒有辦法的時候,能先投投稿也好。遂在附近紙筆店買了一些紙張應用文具,開始在街頭東遊西逛,獵取社會新聞,經過一整天的努力,居然寫了四五條小稿,每稿都謄寫了兩份,分別的送給《東陲日報》和《東昇報》兩家報館。如果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這就叫做「一稿兩投」了。
第二天早晨,彭很早就起床,來不及漱洗,趕忙跑到大街轉角的貼報處一看,兩家報館把他的稿子都登出來了。他在精神苦悶之中,忽然找到這麼一個出路,眼睛一亮,心境也寬了許多。他約略計算了一下,每天如果能夠寫四五條新聞,分投於兩家報館,起碼可以拿到一元幾角一天的稿費,眼前的生活是不會發生問題了。
從此以後,他每天一早起來就跑到外面去做採訪新聞的工作,有時候找不到消息就自己編上一兩條,總以每天能寫四五條為度。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凡是經他投送進去稿子,報館是一律照登,從未打過退堂鼓,因此,格外使他充滿了信心。過了一些日子,他從兩家報館中領到稿費,還特別請韓大哥和他的伙計到「道外」去吃一頓小館子,飯罷又去看京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