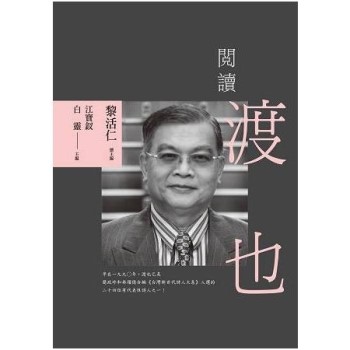■渡也詩與迷宮/黎活仁
◆論文提要
阿達利(Jacques Attali 1943- )《智慧之路──論迷宮》(Labyrinth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athways to Wisdom)一書,對迷宮的類型作了概括,並加以說明。本文據這本書的論述,研究渡也詩中的女性、遊戲、八陣圖和微型空間。渡也愛情詩的數量比較多,故女性與迷宮的素材,也較為豐富。
◆關鍵詞:渡也、女性、迷宮、八陣圖、微型空間
◆一、引言
本稿準備以阿達利(Jacques Attali 1943- )《智慧之路─論迷宮》(Labyrinth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athways to Wisdom)有關迷宮的理論,對渡也詩作一研究。
◆二、女人
女性與迷宮的關係,見於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 1905-60)《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的論述。弗洛依德弟子蘭克(Otto Rank 1884-1939)的「出生受傷」(the birth trauma)說嬰兒從母體脫離誕生的過程,其中的劇烈震動,留下在嬰兒的記憶之中,人類常常想著回到子宮這個樂園(reunion with mother)。
(一)女性與容器
弗洛依德以後,影響最大的精神分析家是容格(Carl G. Yung 1875 -1961),而諾伊曼又是容格的首徒,《大母神:原型分析》論證了集體無意識之中,如果擬人化的話,是一位女性,一位母親,換言之,人類思維的主宰,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容格心理學在中國,仍算流行,但不是普及到啷啷上口的常識。迷宮與女性的生殖功能有關,子宮是生與死的空間,無意識回歸子宮,回歸未誕生的狀況,即沒有生命的時空,就相當於死。諾伊曼特別引茱亞德(John W. Layard)的歸納以為談助:迷宮的主要原型特徵是:1).總是與死亡和再生;2).總是與洞穴(極或是建造的居所有關);3).迷宮的主持人是一位女人;4).想進入迷宮取勝的,都是男人。也就是說女陰是迷宮的入口:渡也詩比較重要的,是寫他與幾位女性的戀情。前述茱亞德之論,迷宮有可能以建築物的形式出現,在渡也則是把女友比喻為一座城,所謂情場如戰場,比作攻城也是合理的:
我想妳就是三國蜀人諸葛亮/鎮守在高高的西城上/悠閒地彈琴/自在的琴聲中並沒有/暗藏兵器/這樣,我想妳就是企圖讓我猜測/妳城裏囤積了用不完的/情/取不盡的/愛//
這樣,我豈可效法魏人司馬懿/不戰而退/我一定要帶領三十萬大軍/闖進城裏/勇敢地/把妳以及妳綿綿的情愛/擄走//
率軍入城/我才發現城中竟然/一無所有/甚至妳/也不在城內/我才發現,原來 妳是最難攻打/最難抵抗的一座/空城//
茫然的我已不再猜測/棄劍立在風中並且開始幻想/幻想妳早已派遣大兵/在空城四周團團包圍我的一生/哎,既然中計,既然失策/即使能成為妳的俘虜 也是好的(渡也,〈臺灣榕樹〉,《空城計》)
另外有一首〈棄城〉,城自動失守之後,卻不知何故放棄了,重返之時,但見已變為蕪城:
十五年前,嚴冬/我決心攻城/雖然護城河很廣,很深/牆高三千丈//
我下令攻城/並未攜帶一兵一卒/以及任何武器/我只率領幾十封情書/和一大群愛/妳的城便被我俘虜了//
今年春天我返回城裏/回想十一年前/我離城的情景,並且感到/抱歉/護城河乾了/城牆病倒了/妳在那裏?/妳在那裏?/我大聲喊/荒烟蔓草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渡也,〈棄城〉,《空城計》)
〈暴君焚城錄〉是對橫刀奪愛者表示要用攻城的玉石俱焚手段,收復失地,失地即心愛的佳人:
接到密告後/我立刻領十萬大軍/埋伏在妳城外/並且高聲喊/「趕快投降吧/妳巳經被包圍了」/早巳嫁人的妳/只從城內拋出一段往事還我/我一聲號令/千萬支擁抱著火的箭/便向妳燒過去了//
熊熊的火/憤怒的愛的暴君/就要去索取妳的宮殿/妳的倩影/我就要教世上最痛的一場大火/到城裡去/迎娶妳的一生(渡也,〈暴君焚城錄〉,《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
(二)航海
「迷宮之路永遠是夜海遠航的開端」,「男性追隨著太陽,沉落到吞噬的冥界,沉落到恐怖母神的死亡子宮。導向危險的旋渦的迷宮之路」(《大母神》)應該說明的是,古代人看到夕陽西沉,以為太陽是去了地獄,去了黑暗的國度,死者的冥界,到早上又再誕生。太陽在茫茫大海西沉,如同大航海,進入大地的子宮。年輕人談情說愛,到沙灘漫步,看著晚霞,然後海誓山盟,也是常有的事,〈妹妹〉一詩寫兩人在海邊談分手,心情像太陽沈下去:最苦楚最無奈時/我一定要帶妳去海邊/看潔白的浪花結合又揮手分離/看潮汐滾滾湧向我們的一,生/又頭也不回地奔到遠方去//……
最痛心最難忍時/也只有這樣坐在一起/在遼闊的淡水海灘上/看蒼老的夕陽在海平線/看我們依偎坐在即將沈下去的/夕陽心中(渡也,〈妹妹〉,《空城計》)
於集體無意識中就回憶起迷宮,如下的〈魚〉,就寫這種相擁作慾海夜航的的情色詩:
也只有在夜晚/燈冷卻以後/我們才能開始發熱/開始泅泳/在沒有水的河床/我奮力游入妳生命深處/為了讓妳也能游入我的一生/讓我們這無鱗無鰭的/兩尾魚/邂逅彼此的春天/〈有斑鳩在草叢中不斷地啼叫〉/並且在黑暗而又滚蜜的草叢中/互贈因感激而流下來的/水/然後斑鳩停止歡唱/我們分離/為了下次的泅游//
也只有在夜晚/燈冷卻以後/所謂生命的意義/在乾涸的河床/才能獲得圓滿的闡釋/因為我們都從河床來/子子孫孫也從河床來/因為世界/也是(渡也,〈魚〉,《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
《大母神》說,迷宮出現於埃及的死者審判和古代原始祕儀,在現代人的心理發展進程也會出現。「在午夜時分,在死者的國度,在夜海航行的中途」,會出現「裁決降臨的時候」,故「迷宮具有危險性」。渡也〈兼愛非攻〉是寫幾個女人爭風呷醋,對他進行責難。春秋時代的墨家主家「兼愛非攻」,因為提倡非攻,故對守城的戰略甚有研究:
我在研究兼愛的思想/並且實踐這套理論/阿桃卻站在我心的邊緣地帶/哭得墨子束手無策/阿桃指責王蘭花搶走她的地盤/搶走了我的心/那株蘭花動手抓破阿桃的果皮/後來李小梅也加入/兵荒馬亂之中/在我小小的心裏/製造一個愛的/春秋戰國//
她們一起打破了墨子的哲學體系/我彷彿聽到/墨子揮汗高聲急呼/非攻非攻(渡也,〈兼愛非攻〉,《空城計》)
(三)打電話
德里達說電影、電視、電話之類的聲音再生產,大大增加了幽靈的因素。利蘭‧萊肯(Leland Ryken)《聖經文學導論》(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說:呼語(Apostrophe)是「用以稱呼實際上不在場的人或擬似的物」,以下是該書舉的例:「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你說的」(〈詩篇〉87:3);「我的心哪,……你要稱頌他的聖名」(〈詩篇〉 103:1)。保羅・德曼(Paul de Man, 1919-83)〈失去原貌的自傳〉(“Autobiography as Defacement”),以擬人法虛擬死者的聲音,虛擬的聲音以「呼語」呈現,「從呼語到一個缺席的、死亡的,或者不具聲音的實體的虛構」,並「假定了後者進行回答的可能性」。把佳麗當作女神來供奉,是熱戀的癥候,語音即邏各斯,邏各斯最早的定義是神的聲音,把佳人的邏各斯奉若神明,在兩情相悅,失去理智之時,未必是壞事,應視為人生的一個階段;因愛情的神聖,以至佳人的「呼語」就有著宗教感情那麼的崇敬。相好不在場,即各在天一方,於是有感於「芙蓉如臉,柳如眉」,像幽靈無處理在,還有在耳邊迴響著的呼喚:
早晨我喝豆漿/妳浮在碗裡/午覺醒來/我對鏡梳髮/妳坐在鏡裡/晚上我在燈下讀書/妳躺在書裡/我把燈熄去/妳亮在黑暗裡/我急急閤上眼/妳站在我眼裡/我睡著時/妳醒在我夢裡//
這樣/日夜不停/跟隨我到北部/七年來/被我遣棄在南方的妳/從沒閤過眼/不曾微笑過/總是帶著淚痕/躲在每個深夜的電話裡/低聲對我說/「回來好嗎」(渡也〈回來好嗎〉,《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
電話是渡也讀大學時最時麾的溝通工具,當然現在有了互聯網,方法多樣化了,阿利達說因為有可以拒絕不接電話的可能,而讓電話變得像迷宮,〈喂〉是寫女性在睡夢中,還來不及醒過來長談,或故意不講話:
深夜突然/投入一枚等待十多年的/銅板/電話響了,好久/她才接/似乎剛自一個夢裏/剛從某一男人的體溫中/突然醒來//
「還記得我吧」/我拿出十幾年前的聲音/再度使用/她淡淡地回答/「喂」/我問她/「好嗎」/
又是一聲/「喂」//
深夜突然/放回極度疲倦/極度失望的聽筒/讓她的聲音/讓她的世界/消失(渡也,〈喂〉,《空城計》)
◆三、遊戲、八陣圖
伊利亞德是容格派的宗教學家,他的神話學是以月、女姓、農耕連成一個體系,並採類似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學方法。又認為月相的變幻,起支配的作用。《神聖的存在》(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說月的周期循環不息,這種生死的節奏,在還沒進入文明時代的人看來,像控制著一些周期性的自然現象,如水的潮汐和下雨)、植物的周期(種子、生長、豐收),女性的月事。月神於是主宰著宇宙,編織著周期以及人類的命運,因此月神擬人之時常坐在紡綞車旁邊。(一)編織
戀愛時會編織綺夢,編毛衣送給男友,男友送對方以絲綢,紗巾,以為信物,並作人生規劃,人生規劃,就是編織人生的美夢。〈詩經衛風:氓〉是重寫《詩經‧氓》的內容,本來原詩是諷諭女性不要與男的太隨便,因為容易始亂終棄,吃了大虧。據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 )的誤讀論,是後世作家於前輩經典,心理上會有著類似「弒父娶母」情結的弒父傾向,一定會加以扭曲、改寫,以謀求創新,渡也詩中的男士,變成了對婚姻有所期待,沒有把女的遺棄:
除了布與絲的交談是/最溫微的陰謀/夜晚的星星是我們祕密放上去的/但是……你說,鳩在復關/豈僅是一種等待哪/桑還未墜落//
桑還未墜落/我已急欲將自己織成一方/繫在你車上/飄在你襟上/的一方帷巾/繽紛了三年//
然後便是無岸的淇水了//
除了/緩緩飄落之中,湯湯淇水之外/漸漸轉暗的,一片/桑葉(渡也,〈詩經衛風:氓〉,《空城計》)
在〈一段錦〉,女方為一家人編織著美夢:
她把我們的/害羞,對視/細語和心跳/再加上一些糖/織成一段/錦//
她把年華縫了又縫/笑聲一律錠放在外/模仿錦花/有皺紋的憂愁只許/藏在內面當裏子/鮮明的顏彩/照亮我/暗的/她自己留著//
她把我和她/和即將來的孩子/密密縫起來/用她手中看不見的/針/再加上永遠拉不斷的/線(渡也,〈一段錦〉,《空城計》)
〈秋娘〉的女主人公能「日夜紡織」黑紗,無疑是月神,長廊像款款衣帶,是因為如印度人所認為時間在冥冥中是一條條黑色的線,故時間空間,都不過是編織命運黑紗的結果:
回憶年少時也曾暗藏一把溫柔的劍蓄意化装跟蹤一株身披古典/衣裳的秋菊於潔白如伊款款衣帶的長廊終因伊手上孱潺的琴音/一如輕飛的花香逼我現身復因深處的一番回眸猝不及防的美麗/將我擊倒還要我仰望伊成一面黑亮的星空緩緩下降並用微微負/氣的髮絲一如伊日夜紡織的黑紗輕輕將我和劍一起覆蓋(渡也,〈秋娘〉,《空城計‧秋娘》)(二)陸地如棋局
「蒼天如圓蓋,陸地為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三國演義》第37回)。西方古典主義時期,把宇宙想像為一部靜態機器,現在大概以「熱學第二定律」來理解,認為宇宙不斷對外擴散,擴散之後不能收回來。古代中國流行蓋天和渾天說,說宇宙好像一個蓋,或一團氣:〈起手無回〉就是據古代的迷宮論,來刻劃下棋的心境:
我低著頭下棋/派兩匹儂出征/牠們併肩作戰/麈土飛揚/子彈尖叫,砲彈大吼//
楚河對岸有卒受傷/漢界那邊/士、象皆為國陣亡了/似乎歷代將士都在都在這小小戰場/衝鋒、仆倒/為了什麼?//
一個年輕人在旁觀看/默默不語/似乎隔了許久/他的鬚髮漸漸霜白//
對方想改變攻勢……我說,人生/起手無回/血/在棋盤蜿蜒流竄/為了什麼?//
我殺了黑將/
黑將臨終前/慘叫一聲/來不及留下遺言/我並沒有救他/只有微笑/那年輕人仍然不語,仍然/注視著我//
其實,黑方不是輸家/我也沒有打勝仗/那年輕人仍然不語,仍然/注視著鬚髮霜白的我//
我一面推進部隊,竟然/想起古代文人/首先想赶坎坷的蘇東坡/後來,陶淵明竟然/在棋盤走動//
我擦乾汗/擦乾血/把受驚的兵吁回/把俥偽收回/把主炮收回/讓它們安安靜靜 回到原來的位置,回到/沒有戰火的家鄉(渡也,〈起手無回〉,《不准破裂》)
〈俥〉也是以下棋比喻人生:
一個俥/在棋盤橫衝直撞,殺賊/擒王的俥/迷失在街頭/他並未在戰場遺失心/遺失了頭顱/他只是躺在二十世紀/燈紅酒綠的鬧區//
離開棋盤/等於離開戰場,離開了/家鄉,他神色倉皇/弟兄們一定在尋找他/馬炮兵一定/有的被困,有的/受傷,有的含笑/陣亡//
這俥也許在尋找/敵人,將士象車馬包卒/如今安在?/此番是為尋仇而來?/或者敗陣而逃?/是厭倦殺伐、血、炮聲而逃離戰場?//
這孤立無援的/俥來到市中心,來到/人的世界,來到/更大的棋盤/面對人生,抬望眼/前程全是悔恨/下錯一著/只好流浪街頭,任人/踩踏//
何時重披戰袍/再出征啊上楚河漢界/何時與帥會合,救亡/圖存(渡也,〈俥〉,《我是一件行李》)
◆論文提要
阿達利(Jacques Attali 1943- )《智慧之路──論迷宮》(Labyrinth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athways to Wisdom)一書,對迷宮的類型作了概括,並加以說明。本文據這本書的論述,研究渡也詩中的女性、遊戲、八陣圖和微型空間。渡也愛情詩的數量比較多,故女性與迷宮的素材,也較為豐富。
◆關鍵詞:渡也、女性、迷宮、八陣圖、微型空間
◆一、引言
本稿準備以阿達利(Jacques Attali 1943- )《智慧之路─論迷宮》(Labyrinth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athways to Wisdom)有關迷宮的理論,對渡也詩作一研究。
◆二、女人
女性與迷宮的關係,見於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 1905-60)《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的論述。弗洛依德弟子蘭克(Otto Rank 1884-1939)的「出生受傷」(the birth trauma)說嬰兒從母體脫離誕生的過程,其中的劇烈震動,留下在嬰兒的記憶之中,人類常常想著回到子宮這個樂園(reunion with mother)。
(一)女性與容器
弗洛依德以後,影響最大的精神分析家是容格(Carl G. Yung 1875 -1961),而諾伊曼又是容格的首徒,《大母神:原型分析》論證了集體無意識之中,如果擬人化的話,是一位女性,一位母親,換言之,人類思維的主宰,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容格心理學在中國,仍算流行,但不是普及到啷啷上口的常識。迷宮與女性的生殖功能有關,子宮是生與死的空間,無意識回歸子宮,回歸未誕生的狀況,即沒有生命的時空,就相當於死。諾伊曼特別引茱亞德(John W. Layard)的歸納以為談助:迷宮的主要原型特徵是:1).總是與死亡和再生;2).總是與洞穴(極或是建造的居所有關);3).迷宮的主持人是一位女人;4).想進入迷宮取勝的,都是男人。也就是說女陰是迷宮的入口:渡也詩比較重要的,是寫他與幾位女性的戀情。前述茱亞德之論,迷宮有可能以建築物的形式出現,在渡也則是把女友比喻為一座城,所謂情場如戰場,比作攻城也是合理的:
我想妳就是三國蜀人諸葛亮/鎮守在高高的西城上/悠閒地彈琴/自在的琴聲中並沒有/暗藏兵器/這樣,我想妳就是企圖讓我猜測/妳城裏囤積了用不完的/情/取不盡的/愛//
這樣,我豈可效法魏人司馬懿/不戰而退/我一定要帶領三十萬大軍/闖進城裏/勇敢地/把妳以及妳綿綿的情愛/擄走//
率軍入城/我才發現城中竟然/一無所有/甚至妳/也不在城內/我才發現,原來 妳是最難攻打/最難抵抗的一座/空城//
茫然的我已不再猜測/棄劍立在風中並且開始幻想/幻想妳早已派遣大兵/在空城四周團團包圍我的一生/哎,既然中計,既然失策/即使能成為妳的俘虜 也是好的(渡也,〈臺灣榕樹〉,《空城計》)
另外有一首〈棄城〉,城自動失守之後,卻不知何故放棄了,重返之時,但見已變為蕪城:
十五年前,嚴冬/我決心攻城/雖然護城河很廣,很深/牆高三千丈//
我下令攻城/並未攜帶一兵一卒/以及任何武器/我只率領幾十封情書/和一大群愛/妳的城便被我俘虜了//
今年春天我返回城裏/回想十一年前/我離城的情景,並且感到/抱歉/護城河乾了/城牆病倒了/妳在那裏?/妳在那裏?/我大聲喊/荒烟蔓草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渡也,〈棄城〉,《空城計》)
〈暴君焚城錄〉是對橫刀奪愛者表示要用攻城的玉石俱焚手段,收復失地,失地即心愛的佳人:
接到密告後/我立刻領十萬大軍/埋伏在妳城外/並且高聲喊/「趕快投降吧/妳巳經被包圍了」/早巳嫁人的妳/只從城內拋出一段往事還我/我一聲號令/千萬支擁抱著火的箭/便向妳燒過去了//
熊熊的火/憤怒的愛的暴君/就要去索取妳的宮殿/妳的倩影/我就要教世上最痛的一場大火/到城裡去/迎娶妳的一生(渡也,〈暴君焚城錄〉,《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
(二)航海
「迷宮之路永遠是夜海遠航的開端」,「男性追隨著太陽,沉落到吞噬的冥界,沉落到恐怖母神的死亡子宮。導向危險的旋渦的迷宮之路」(《大母神》)應該說明的是,古代人看到夕陽西沉,以為太陽是去了地獄,去了黑暗的國度,死者的冥界,到早上又再誕生。太陽在茫茫大海西沉,如同大航海,進入大地的子宮。年輕人談情說愛,到沙灘漫步,看著晚霞,然後海誓山盟,也是常有的事,〈妹妹〉一詩寫兩人在海邊談分手,心情像太陽沈下去:最苦楚最無奈時/我一定要帶妳去海邊/看潔白的浪花結合又揮手分離/看潮汐滾滾湧向我們的一,生/又頭也不回地奔到遠方去//……
最痛心最難忍時/也只有這樣坐在一起/在遼闊的淡水海灘上/看蒼老的夕陽在海平線/看我們依偎坐在即將沈下去的/夕陽心中(渡也,〈妹妹〉,《空城計》)
於集體無意識中就回憶起迷宮,如下的〈魚〉,就寫這種相擁作慾海夜航的的情色詩:
也只有在夜晚/燈冷卻以後/我們才能開始發熱/開始泅泳/在沒有水的河床/我奮力游入妳生命深處/為了讓妳也能游入我的一生/讓我們這無鱗無鰭的/兩尾魚/邂逅彼此的春天/〈有斑鳩在草叢中不斷地啼叫〉/並且在黑暗而又滚蜜的草叢中/互贈因感激而流下來的/水/然後斑鳩停止歡唱/我們分離/為了下次的泅游//
也只有在夜晚/燈冷卻以後/所謂生命的意義/在乾涸的河床/才能獲得圓滿的闡釋/因為我們都從河床來/子子孫孫也從河床來/因為世界/也是(渡也,〈魚〉,《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
《大母神》說,迷宮出現於埃及的死者審判和古代原始祕儀,在現代人的心理發展進程也會出現。「在午夜時分,在死者的國度,在夜海航行的中途」,會出現「裁決降臨的時候」,故「迷宮具有危險性」。渡也〈兼愛非攻〉是寫幾個女人爭風呷醋,對他進行責難。春秋時代的墨家主家「兼愛非攻」,因為提倡非攻,故對守城的戰略甚有研究:
我在研究兼愛的思想/並且實踐這套理論/阿桃卻站在我心的邊緣地帶/哭得墨子束手無策/阿桃指責王蘭花搶走她的地盤/搶走了我的心/那株蘭花動手抓破阿桃的果皮/後來李小梅也加入/兵荒馬亂之中/在我小小的心裏/製造一個愛的/春秋戰國//
她們一起打破了墨子的哲學體系/我彷彿聽到/墨子揮汗高聲急呼/非攻非攻(渡也,〈兼愛非攻〉,《空城計》)
(三)打電話
德里達說電影、電視、電話之類的聲音再生產,大大增加了幽靈的因素。利蘭‧萊肯(Leland Ryken)《聖經文學導論》(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說:呼語(Apostrophe)是「用以稱呼實際上不在場的人或擬似的物」,以下是該書舉的例:「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你說的」(〈詩篇〉87:3);「我的心哪,……你要稱頌他的聖名」(〈詩篇〉 103:1)。保羅・德曼(Paul de Man, 1919-83)〈失去原貌的自傳〉(“Autobiography as Defacement”),以擬人法虛擬死者的聲音,虛擬的聲音以「呼語」呈現,「從呼語到一個缺席的、死亡的,或者不具聲音的實體的虛構」,並「假定了後者進行回答的可能性」。把佳麗當作女神來供奉,是熱戀的癥候,語音即邏各斯,邏各斯最早的定義是神的聲音,把佳人的邏各斯奉若神明,在兩情相悅,失去理智之時,未必是壞事,應視為人生的一個階段;因愛情的神聖,以至佳人的「呼語」就有著宗教感情那麼的崇敬。相好不在場,即各在天一方,於是有感於「芙蓉如臉,柳如眉」,像幽靈無處理在,還有在耳邊迴響著的呼喚:
早晨我喝豆漿/妳浮在碗裡/午覺醒來/我對鏡梳髮/妳坐在鏡裡/晚上我在燈下讀書/妳躺在書裡/我把燈熄去/妳亮在黑暗裡/我急急閤上眼/妳站在我眼裡/我睡著時/妳醒在我夢裡//
這樣/日夜不停/跟隨我到北部/七年來/被我遣棄在南方的妳/從沒閤過眼/不曾微笑過/總是帶著淚痕/躲在每個深夜的電話裡/低聲對我說/「回來好嗎」(渡也〈回來好嗎〉,《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
電話是渡也讀大學時最時麾的溝通工具,當然現在有了互聯網,方法多樣化了,阿利達說因為有可以拒絕不接電話的可能,而讓電話變得像迷宮,〈喂〉是寫女性在睡夢中,還來不及醒過來長談,或故意不講話:
深夜突然/投入一枚等待十多年的/銅板/電話響了,好久/她才接/似乎剛自一個夢裏/剛從某一男人的體溫中/突然醒來//
「還記得我吧」/我拿出十幾年前的聲音/再度使用/她淡淡地回答/「喂」/我問她/「好嗎」/
又是一聲/「喂」//
深夜突然/放回極度疲倦/極度失望的聽筒/讓她的聲音/讓她的世界/消失(渡也,〈喂〉,《空城計》)
◆三、遊戲、八陣圖
伊利亞德是容格派的宗教學家,他的神話學是以月、女姓、農耕連成一個體系,並採類似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學方法。又認為月相的變幻,起支配的作用。《神聖的存在》(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說月的周期循環不息,這種生死的節奏,在還沒進入文明時代的人看來,像控制著一些周期性的自然現象,如水的潮汐和下雨)、植物的周期(種子、生長、豐收),女性的月事。月神於是主宰著宇宙,編織著周期以及人類的命運,因此月神擬人之時常坐在紡綞車旁邊。(一)編織
戀愛時會編織綺夢,編毛衣送給男友,男友送對方以絲綢,紗巾,以為信物,並作人生規劃,人生規劃,就是編織人生的美夢。〈詩經衛風:氓〉是重寫《詩經‧氓》的內容,本來原詩是諷諭女性不要與男的太隨便,因為容易始亂終棄,吃了大虧。據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 )的誤讀論,是後世作家於前輩經典,心理上會有著類似「弒父娶母」情結的弒父傾向,一定會加以扭曲、改寫,以謀求創新,渡也詩中的男士,變成了對婚姻有所期待,沒有把女的遺棄:
除了布與絲的交談是/最溫微的陰謀/夜晚的星星是我們祕密放上去的/但是……你說,鳩在復關/豈僅是一種等待哪/桑還未墜落//
桑還未墜落/我已急欲將自己織成一方/繫在你車上/飄在你襟上/的一方帷巾/繽紛了三年//
然後便是無岸的淇水了//
除了/緩緩飄落之中,湯湯淇水之外/漸漸轉暗的,一片/桑葉(渡也,〈詩經衛風:氓〉,《空城計》)
在〈一段錦〉,女方為一家人編織著美夢:
她把我們的/害羞,對視/細語和心跳/再加上一些糖/織成一段/錦//
她把年華縫了又縫/笑聲一律錠放在外/模仿錦花/有皺紋的憂愁只許/藏在內面當裏子/鮮明的顏彩/照亮我/暗的/她自己留著//
她把我和她/和即將來的孩子/密密縫起來/用她手中看不見的/針/再加上永遠拉不斷的/線(渡也,〈一段錦〉,《空城計》)
〈秋娘〉的女主人公能「日夜紡織」黑紗,無疑是月神,長廊像款款衣帶,是因為如印度人所認為時間在冥冥中是一條條黑色的線,故時間空間,都不過是編織命運黑紗的結果:
回憶年少時也曾暗藏一把溫柔的劍蓄意化装跟蹤一株身披古典/衣裳的秋菊於潔白如伊款款衣帶的長廊終因伊手上孱潺的琴音/一如輕飛的花香逼我現身復因深處的一番回眸猝不及防的美麗/將我擊倒還要我仰望伊成一面黑亮的星空緩緩下降並用微微負/氣的髮絲一如伊日夜紡織的黑紗輕輕將我和劍一起覆蓋(渡也,〈秋娘〉,《空城計‧秋娘》)(二)陸地如棋局
「蒼天如圓蓋,陸地為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三國演義》第37回)。西方古典主義時期,把宇宙想像為一部靜態機器,現在大概以「熱學第二定律」來理解,認為宇宙不斷對外擴散,擴散之後不能收回來。古代中國流行蓋天和渾天說,說宇宙好像一個蓋,或一團氣:〈起手無回〉就是據古代的迷宮論,來刻劃下棋的心境:
我低著頭下棋/派兩匹儂出征/牠們併肩作戰/麈土飛揚/子彈尖叫,砲彈大吼//
楚河對岸有卒受傷/漢界那邊/士、象皆為國陣亡了/似乎歷代將士都在都在這小小戰場/衝鋒、仆倒/為了什麼?//
一個年輕人在旁觀看/默默不語/似乎隔了許久/他的鬚髮漸漸霜白//
對方想改變攻勢……我說,人生/起手無回/血/在棋盤蜿蜒流竄/為了什麼?//
我殺了黑將/
黑將臨終前/慘叫一聲/來不及留下遺言/我並沒有救他/只有微笑/那年輕人仍然不語,仍然/注視著我//
其實,黑方不是輸家/我也沒有打勝仗/那年輕人仍然不語,仍然/注視著鬚髮霜白的我//
我一面推進部隊,竟然/想起古代文人/首先想赶坎坷的蘇東坡/後來,陶淵明竟然/在棋盤走動//
我擦乾汗/擦乾血/把受驚的兵吁回/把俥偽收回/把主炮收回/讓它們安安靜靜 回到原來的位置,回到/沒有戰火的家鄉(渡也,〈起手無回〉,《不准破裂》)
〈俥〉也是以下棋比喻人生:
一個俥/在棋盤橫衝直撞,殺賊/擒王的俥/迷失在街頭/他並未在戰場遺失心/遺失了頭顱/他只是躺在二十世紀/燈紅酒綠的鬧區//
離開棋盤/等於離開戰場,離開了/家鄉,他神色倉皇/弟兄們一定在尋找他/馬炮兵一定/有的被困,有的/受傷,有的含笑/陣亡//
這俥也許在尋找/敵人,將士象車馬包卒/如今安在?/此番是為尋仇而來?/或者敗陣而逃?/是厭倦殺伐、血、炮聲而逃離戰場?//
這孤立無援的/俥來到市中心,來到/人的世界,來到/更大的棋盤/面對人生,抬望眼/前程全是悔恨/下錯一著/只好流浪街頭,任人/踩踏//
何時重披戰袍/再出征啊上楚河漢界/何時與帥會合,救亡/圖存(渡也,〈俥〉,《我是一件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