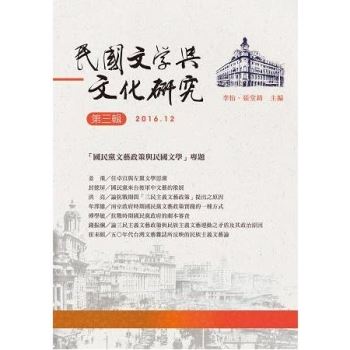[我看「民國文學」]
■李瑞騰
一
傳統中國史學以「朝代」為歷史分期,這有其方便性,也符合民間傳統改朝換代的認知。準此,在「清」之後,理當就是「民國」了;在大陸,「民國」之後,即「共和國」;但是1949 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後,中華民國沒有消失,而是遷移來台,即是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說,「民國文學」在大陸是指中共建政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接續晚清;在台灣是指國府遷台以後的文學,在時間上,亦可上推到1945年,接續日本時代。
這是兩個不同空間的「民國文學」,在大陸,過去跳過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把五四當作現代的起點,「民國文學」比較接近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但有幾年的時間差,而既稱「現代」,則舊體文學就似乎有不加理會的正當性了,不過,在「民國文學」的架構下,舊體沒理由排除。
在台灣,在「台灣文學」未獲得正名以前,比較能代表官方主流論述的是尹雪曼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1975),柏楊在1960 年代編過兩年文學年鑑,稱「中國文藝年鑑」,在1980 年代之初再編文學年鑑時,則稱「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余光中擔任總編輯的三套大系,在1970年代稱「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80 年代以後稱「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另標明時間及地點「台灣」。一般是不大用「民國」這個概念,但史學界是有「民國史」的。
二
要深入探討民國文學,首先要了解晚清,包括維新和革命等政治運動、新興都會(通商口岸)與文藝傳媒的發達、由東西洋引入的文學觀念、白話與淺語等書寫媒介的普及等,對文學的變化產生極大的影響,它們如洪流湧入民國,終與五四狂潮匯流,成為民國文學的主潮。
這本來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如何面對傳統?在新與舊當中如何調節?在文言和白話之間如何融裁?在向內探索和往外奔馳之間如何掌握?都值得放進時局中去看去想。進一步說,留學生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學之於文學提供了什麼樣的助力?政治的糾葛、軍閥的混戰、外來勢力的蠶食掠奪、文學社群的駁辯激盪、文化產業如摸石過河,諸多因素對文學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大陸學界過去把歷史割裂成近、現、當代,是有問題的,近代當然不只反帝反封建,現代當然不只魯郭茅巴,當代也不只十七年文學、十年浩劫過後就撥亂反正了,於是而有1980 年代中期的重寫文學史運動。但不管怎樣,相關的既有研究成果其實很多,包括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現在叫「世界華文文學」,最近幾年出現把中國「包括在外」的「華語語系文學」),許許多多的研究成果,民國文學的研究者都可以消化吸收。
這不應只是一場「熱」─民國熱,而是回到常軌,民國從建立到它在中國大陸本土消失,這是一個客觀的史實,當我們在談文學的時候,它曾有過什麼?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都應該全面清理,還原其本來面貌,給予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與評價,和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必須疏濬,使之脈流清晰;而且不只要往上溯源,也要往下追蹤。
三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真正完全擺脫國共糾葛,時間的距離可能還要更長;而在台灣,本土浪潮席捲下,兩黨鬥爭30 年所積壓的怨和恨,要去除談何容易,「民國」和國民黨被等同起來,因之現階段要談民國是需要勇氣的。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有人不想談「民國」,當然不能勉強;如果要談,要怎麼談,這見仁見智,以最寬廣的說法,除大陸時期(1912-1949),還得包括1945 年(或1949)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甚至1949 前後從大陸去歐美及從台灣去歐美的留學生或移民。
但真正的難題是,怎麼看大陸時期的民國文學?民初的遺老遺少文學、新文學之產生、反新文學的陣營在反什麼?各門各派的文學,乃至於30 年代文學、抗戰文學、左翼文學等等,特別是為數龐大的反國民政府作家群,如何定性定位等,都必須處理;而國共合而又分,大撤退時期文人如何抉擇去留的問題,都該有所處理。我們應該有綜攝上述議題的一部大陸時期民國文學史。
四
把焦點移到台灣,既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它的文學,也就是台灣文學的一個時期,也許可以稱為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之前是戰後初期,更上則是日本時代、清領時期、明鄭時期。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從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到現代文學的這個傳統,一個是日本時代漢語詩文和新文學傳統,大概就是「中國」加「東、西洋」。不過,場域是台灣,「台灣」島嶼時空因素的加入,以及兩岸長期的互動、國際潮流的沖激,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
這樣看來,要有一部統合兩岸文學史實而且體大慮周的民國文學史,實非易事了;不過,我想這是可以期待的,首要之務可能是呼喚同道,營造研究的環境和氣氛,然後在文獻上儘可能拾遺補缺,把許許多多被遺忘或遺棄者找出來,放進歷史的脈絡,而這特別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歷史的詮釋本來就是艱難的事,特別是現當代,但只要我們心胸開闊,也有耐心,應該可以有一些成績出來的。
[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周質平
《漢字簡化方案》是1956 年1 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60 年。生活在中國大陸60 歲以下的人,絕大部分視簡化漢字為當今中國人書寫的通用字體,基本上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台灣、香港和海外的華人社會中,簡化漢字遠沒有達到「一統」的地位。因此,這個在國內已經不再熱烈議論的話題,在海外、台、港還不時有人提出討論。這最足以說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60 年來億萬人的使用依舊改變不了兩三千萬人對當年舊物的依戀。
這種對簡化字抗拒的情緒,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敵對情緒,有的來自文化上對傳統的捍衛,也有的只是舊習慣的延續,當然也有不少是三種情緒的混合。且不論這種抗拒情緒究竟源自何處,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從早年的「勢不兩立」漸漸發展到了「和平共存」。
因此,近年來有所謂「識繁寫簡」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識楷書行」。也就是「認讀楷書,而書寫行書」的建議。這一提法,在我看來,與所謂「識繁寫簡」或「識正書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而這些提法最大的「盲點」,是無視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已經使「以手握筆」這一行之數千年的「書寫」技能,隨著筆記型電腦和手機的快速普及,瀕臨幾乎「滅絕」的困境。「寫字」,(不只是寫漢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內),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已經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寫漢字」只是少數書法家的藝術活動,而不是人與人之間賴以溝通的日常技能了。換句話說,「識字」和「寫字」的距離,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任何一個能用電腦輸入漢字的人,只要能「識」漢字─從同音字中,選出對的漢字來─,也就能「打」出這個字來,於是便完成了所謂「書寫」的任務。在這個情況下,「行書」也就不「行」了。更何來「行、楷」之分呢?
正因為工具的改變,使原本握筆書寫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鍵盤的配合。
在地鐵裡,看到小學生、初中生埋頭運指如飛,我們必須瞭解,他們正在「寫」信。雖然此「寫」已非「筆寫」,但其為「寫」則一。對他們來說,那裡還有什麼楷書、行書、草書之別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誤,「提筆忘字」的人勢必與日俱增,但只要一打開手機、電腦,所忘的字,卻都一時湧入眼簾。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期盼的「書同文」,與其從字形入手,不如從語音入手。換言之,以現在漢字輸入法來說,「語同音」其實是「書同文」的先決條件。除了台、港兩地,十三四億中國人最常用的漢字輸入法是拼音輸入法。「老師吃飯」是「laoshichifan」,而不是台灣國語的「laosicifan」。南方人的普通話,在發音時,或許分不清zhi/chi/shi 和zi/ci/si,但在他的腦海中卻不能沒有翹舌和平舌的分別。否則在打漢字的時候,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所以,在提倡「書同文」的同時也不能忽略「語同音」的重要。
台、港兩地有不少捍衛方言的仁人義士,視台語、粵語為兩地文化認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漢字台語化或粵語化。寫出來的漢字,在字形上容或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字義上卻全然不能與普通話互通。這一現象所造成的隔閡,遠比繁簡體的不同嚴重得多。用漢字寫方言,與其說是「母語化」,不如說是「孤島化」。
海峽兩岸關心漢字發展的人士在論漢字的演變時,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字形的繁簡而言,而沒有意識到,繁簡的不同,就時間的先後來看,也就是古今的差異。台、港地區至今使用的繁體字,對廣大的大陸人民而言,與其說是「繁體」,不如說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所使用的「古體」。
這一「古體」只有在書法作品或刻印古書時使用,在平日報刊雜誌或電郵往返中是不常見到的。這樣的敘述是符合當前中國大陸十三四億人書寫漢字的實際情況的。
台灣、香港的語文現象,和大陸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不僅字體為然,台灣的拼音方式依舊是民國初年制定的「注音符號」,而從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許多書籍報刊的排印格式。甚至於標點符號也一仍舊貫。「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給人一種「有文化」的錯覺,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島現象」一定的體現。在不知不覺之中,正應了「禮失求諸野」的古訓,這句話的精義是:就文化和制度發展而言,邊緣往往較中心更保守。許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經失傳的禮儀,在邊陲海隅還保存得相當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儀式,在紐約唐人街,偶爾還能看到。這時,我們大概不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中國」的;我們只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古老的。
因此,「禮失求諸野」的另一個意義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灣人喜歡把「繁體字」叫做「正體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最好寫照。如果「越古越正」,那麼,「正體字」應該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說文》中的小篆,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隸定」之後的「楷書」。《說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卻從無「正文作某」的例子。就漢字的發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體」,而小篆取得了「正體」的地位;同樣的,當「隸書」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體」,而「隸書」成了「正體」;「楷書」取代「隸書」之後,「楷書」成了「正體」,「隸書」又不得不退居而為「古體」。而今「簡體」取代了「繁體」,「繁體」當然也就成了「古體」,而「簡體」反而成了「正體」。
反對現行簡化字的人總喜歡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約定俗成」,並視之為文字發展的自然規律。「約定俗成」固然有它緩和漸進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將錯就錯,積非成是,多數壟斷的一面。因此,「約定俗成」的精義是語文的議題只論「已然」,而不論「應然」。當多數人把「滑稽」說成「華稽」,你卻堅持說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當十三四億人都把「愛」寫成「無心」的「愛」,而二三千萬人卻堅持寫「有心」的「愛」,結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愛」了。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宜」與「不宜」,端看多數人怎麼說,怎麼寫,而不論其字源本義。「眾口鑠金」,「隨波逐流」是語文發展「約定俗成」最後的判斷。任何頑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絕於多數的反動!
套句黑格爾的話來瞭解荀子的「約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語文發展,有些反對簡化字的人所擔心的「政治力不當的介入」,其實,是無的放矢,不足為慮的。
1951 年,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後的改革卻只能是「簡化」,而不能是「拼音化」。這並不是因為毛的權力不夠大,更不是因為提倡不力。而是漢語漢字經千萬年的發展,億萬人的使用,漢字和漢語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這一點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的)。這個合理性並不因毛的個人意願而有所轉移。
莫說一個毛澤東做不到用拼音來取代漢字,即使有千百個毛澤東也不可能廢滅漢字而以拼音代之。政治力的介入使繁體字在短時間之內成了簡體,並為億萬中國人所接受使用。這恰好說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對簡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認:「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數服從多數。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無視於「多數」的存在。對十三、四億人已經使用了60 年的簡化漢字,始終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舉世滔滔」的真實存在,而認為是「徒勞無功」,「治絲益棼」,對當年舊物表現出無限追懷。
必須指出:不喜歡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大陸目前通用的簡化漢字,是十幾億人每天寢饋期間,賴以溝通的書面文字。60 年的實踐證明,簡化漢字並沒有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幾個常被台、港人士拿來取笑的同音字的合併,也並沒有混淆視聽,譬如:「他靠理发发了財。」「在單位裡干了30 年的干部,退休下來賣餅干。」文義是很清楚的。如果「頭髮」的「髮」和「發財」的「發」,合併為「发」之後,真的引起混淆,這個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
■李瑞騰
一
傳統中國史學以「朝代」為歷史分期,這有其方便性,也符合民間傳統改朝換代的認知。準此,在「清」之後,理當就是「民國」了;在大陸,「民國」之後,即「共和國」;但是1949 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後,中華民國沒有消失,而是遷移來台,即是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說,「民國文學」在大陸是指中共建政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接續晚清;在台灣是指國府遷台以後的文學,在時間上,亦可上推到1945年,接續日本時代。
這是兩個不同空間的「民國文學」,在大陸,過去跳過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把五四當作現代的起點,「民國文學」比較接近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但有幾年的時間差,而既稱「現代」,則舊體文學就似乎有不加理會的正當性了,不過,在「民國文學」的架構下,舊體沒理由排除。
在台灣,在「台灣文學」未獲得正名以前,比較能代表官方主流論述的是尹雪曼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1975),柏楊在1960 年代編過兩年文學年鑑,稱「中國文藝年鑑」,在1980 年代之初再編文學年鑑時,則稱「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余光中擔任總編輯的三套大系,在1970年代稱「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80 年代以後稱「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另標明時間及地點「台灣」。一般是不大用「民國」這個概念,但史學界是有「民國史」的。
二
要深入探討民國文學,首先要了解晚清,包括維新和革命等政治運動、新興都會(通商口岸)與文藝傳媒的發達、由東西洋引入的文學觀念、白話與淺語等書寫媒介的普及等,對文學的變化產生極大的影響,它們如洪流湧入民國,終與五四狂潮匯流,成為民國文學的主潮。
這本來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如何面對傳統?在新與舊當中如何調節?在文言和白話之間如何融裁?在向內探索和往外奔馳之間如何掌握?都值得放進時局中去看去想。進一步說,留學生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學之於文學提供了什麼樣的助力?政治的糾葛、軍閥的混戰、外來勢力的蠶食掠奪、文學社群的駁辯激盪、文化產業如摸石過河,諸多因素對文學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大陸學界過去把歷史割裂成近、現、當代,是有問題的,近代當然不只反帝反封建,現代當然不只魯郭茅巴,當代也不只十七年文學、十年浩劫過後就撥亂反正了,於是而有1980 年代中期的重寫文學史運動。但不管怎樣,相關的既有研究成果其實很多,包括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現在叫「世界華文文學」,最近幾年出現把中國「包括在外」的「華語語系文學」),許許多多的研究成果,民國文學的研究者都可以消化吸收。
這不應只是一場「熱」─民國熱,而是回到常軌,民國從建立到它在中國大陸本土消失,這是一個客觀的史實,當我們在談文學的時候,它曾有過什麼?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都應該全面清理,還原其本來面貌,給予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與評價,和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必須疏濬,使之脈流清晰;而且不只要往上溯源,也要往下追蹤。
三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真正完全擺脫國共糾葛,時間的距離可能還要更長;而在台灣,本土浪潮席捲下,兩黨鬥爭30 年所積壓的怨和恨,要去除談何容易,「民國」和國民黨被等同起來,因之現階段要談民國是需要勇氣的。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有人不想談「民國」,當然不能勉強;如果要談,要怎麼談,這見仁見智,以最寬廣的說法,除大陸時期(1912-1949),還得包括1945 年(或1949)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甚至1949 前後從大陸去歐美及從台灣去歐美的留學生或移民。
但真正的難題是,怎麼看大陸時期的民國文學?民初的遺老遺少文學、新文學之產生、反新文學的陣營在反什麼?各門各派的文學,乃至於30 年代文學、抗戰文學、左翼文學等等,特別是為數龐大的反國民政府作家群,如何定性定位等,都必須處理;而國共合而又分,大撤退時期文人如何抉擇去留的問題,都該有所處理。我們應該有綜攝上述議題的一部大陸時期民國文學史。
四
把焦點移到台灣,既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它的文學,也就是台灣文學的一個時期,也許可以稱為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之前是戰後初期,更上則是日本時代、清領時期、明鄭時期。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從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到現代文學的這個傳統,一個是日本時代漢語詩文和新文學傳統,大概就是「中國」加「東、西洋」。不過,場域是台灣,「台灣」島嶼時空因素的加入,以及兩岸長期的互動、國際潮流的沖激,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
這樣看來,要有一部統合兩岸文學史實而且體大慮周的民國文學史,實非易事了;不過,我想這是可以期待的,首要之務可能是呼喚同道,營造研究的環境和氣氛,然後在文獻上儘可能拾遺補缺,把許許多多被遺忘或遺棄者找出來,放進歷史的脈絡,而這特別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歷史的詮釋本來就是艱難的事,特別是現當代,但只要我們心胸開闊,也有耐心,應該可以有一些成績出來的。
[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周質平
《漢字簡化方案》是1956 年1 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60 年。生活在中國大陸60 歲以下的人,絕大部分視簡化漢字為當今中國人書寫的通用字體,基本上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台灣、香港和海外的華人社會中,簡化漢字遠沒有達到「一統」的地位。因此,這個在國內已經不再熱烈議論的話題,在海外、台、港還不時有人提出討論。這最足以說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60 年來億萬人的使用依舊改變不了兩三千萬人對當年舊物的依戀。
這種對簡化字抗拒的情緒,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敵對情緒,有的來自文化上對傳統的捍衛,也有的只是舊習慣的延續,當然也有不少是三種情緒的混合。且不論這種抗拒情緒究竟源自何處,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從早年的「勢不兩立」漸漸發展到了「和平共存」。
因此,近年來有所謂「識繁寫簡」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識楷書行」。也就是「認讀楷書,而書寫行書」的建議。這一提法,在我看來,與所謂「識繁寫簡」或「識正書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而這些提法最大的「盲點」,是無視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已經使「以手握筆」這一行之數千年的「書寫」技能,隨著筆記型電腦和手機的快速普及,瀕臨幾乎「滅絕」的困境。「寫字」,(不只是寫漢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內),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已經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寫漢字」只是少數書法家的藝術活動,而不是人與人之間賴以溝通的日常技能了。換句話說,「識字」和「寫字」的距離,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任何一個能用電腦輸入漢字的人,只要能「識」漢字─從同音字中,選出對的漢字來─,也就能「打」出這個字來,於是便完成了所謂「書寫」的任務。在這個情況下,「行書」也就不「行」了。更何來「行、楷」之分呢?
正因為工具的改變,使原本握筆書寫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鍵盤的配合。
在地鐵裡,看到小學生、初中生埋頭運指如飛,我們必須瞭解,他們正在「寫」信。雖然此「寫」已非「筆寫」,但其為「寫」則一。對他們來說,那裡還有什麼楷書、行書、草書之別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誤,「提筆忘字」的人勢必與日俱增,但只要一打開手機、電腦,所忘的字,卻都一時湧入眼簾。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期盼的「書同文」,與其從字形入手,不如從語音入手。換言之,以現在漢字輸入法來說,「語同音」其實是「書同文」的先決條件。除了台、港兩地,十三四億中國人最常用的漢字輸入法是拼音輸入法。「老師吃飯」是「laoshichifan」,而不是台灣國語的「laosicifan」。南方人的普通話,在發音時,或許分不清zhi/chi/shi 和zi/ci/si,但在他的腦海中卻不能沒有翹舌和平舌的分別。否則在打漢字的時候,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所以,在提倡「書同文」的同時也不能忽略「語同音」的重要。
台、港兩地有不少捍衛方言的仁人義士,視台語、粵語為兩地文化認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漢字台語化或粵語化。寫出來的漢字,在字形上容或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字義上卻全然不能與普通話互通。這一現象所造成的隔閡,遠比繁簡體的不同嚴重得多。用漢字寫方言,與其說是「母語化」,不如說是「孤島化」。
海峽兩岸關心漢字發展的人士在論漢字的演變時,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字形的繁簡而言,而沒有意識到,繁簡的不同,就時間的先後來看,也就是古今的差異。台、港地區至今使用的繁體字,對廣大的大陸人民而言,與其說是「繁體」,不如說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所使用的「古體」。
這一「古體」只有在書法作品或刻印古書時使用,在平日報刊雜誌或電郵往返中是不常見到的。這樣的敘述是符合當前中國大陸十三四億人書寫漢字的實際情況的。
台灣、香港的語文現象,和大陸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不僅字體為然,台灣的拼音方式依舊是民國初年制定的「注音符號」,而從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許多書籍報刊的排印格式。甚至於標點符號也一仍舊貫。「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給人一種「有文化」的錯覺,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島現象」一定的體現。在不知不覺之中,正應了「禮失求諸野」的古訓,這句話的精義是:就文化和制度發展而言,邊緣往往較中心更保守。許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經失傳的禮儀,在邊陲海隅還保存得相當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儀式,在紐約唐人街,偶爾還能看到。這時,我們大概不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中國」的;我們只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古老的。
因此,「禮失求諸野」的另一個意義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灣人喜歡把「繁體字」叫做「正體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最好寫照。如果「越古越正」,那麼,「正體字」應該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說文》中的小篆,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隸定」之後的「楷書」。《說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卻從無「正文作某」的例子。就漢字的發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體」,而小篆取得了「正體」的地位;同樣的,當「隸書」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體」,而「隸書」成了「正體」;「楷書」取代「隸書」之後,「楷書」成了「正體」,「隸書」又不得不退居而為「古體」。而今「簡體」取代了「繁體」,「繁體」當然也就成了「古體」,而「簡體」反而成了「正體」。
反對現行簡化字的人總喜歡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約定俗成」,並視之為文字發展的自然規律。「約定俗成」固然有它緩和漸進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將錯就錯,積非成是,多數壟斷的一面。因此,「約定俗成」的精義是語文的議題只論「已然」,而不論「應然」。當多數人把「滑稽」說成「華稽」,你卻堅持說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當十三四億人都把「愛」寫成「無心」的「愛」,而二三千萬人卻堅持寫「有心」的「愛」,結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愛」了。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宜」與「不宜」,端看多數人怎麼說,怎麼寫,而不論其字源本義。「眾口鑠金」,「隨波逐流」是語文發展「約定俗成」最後的判斷。任何頑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絕於多數的反動!
套句黑格爾的話來瞭解荀子的「約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語文發展,有些反對簡化字的人所擔心的「政治力不當的介入」,其實,是無的放矢,不足為慮的。
1951 年,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後的改革卻只能是「簡化」,而不能是「拼音化」。這並不是因為毛的權力不夠大,更不是因為提倡不力。而是漢語漢字經千萬年的發展,億萬人的使用,漢字和漢語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這一點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的)。這個合理性並不因毛的個人意願而有所轉移。
莫說一個毛澤東做不到用拼音來取代漢字,即使有千百個毛澤東也不可能廢滅漢字而以拼音代之。政治力的介入使繁體字在短時間之內成了簡體,並為億萬中國人所接受使用。這恰好說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對簡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認:「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數服從多數。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無視於「多數」的存在。對十三、四億人已經使用了60 年的簡化漢字,始終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舉世滔滔」的真實存在,而認為是「徒勞無功」,「治絲益棼」,對當年舊物表現出無限追懷。
必須指出:不喜歡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大陸目前通用的簡化漢字,是十幾億人每天寢饋期間,賴以溝通的書面文字。60 年的實踐證明,簡化漢字並沒有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幾個常被台、港人士拿來取笑的同音字的合併,也並沒有混淆視聽,譬如:「他靠理发发了財。」「在單位裡干了30 年的干部,退休下來賣餅干。」文義是很清楚的。如果「頭髮」的「髮」和「發財」的「發」,合併為「发」之後,真的引起混淆,這個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