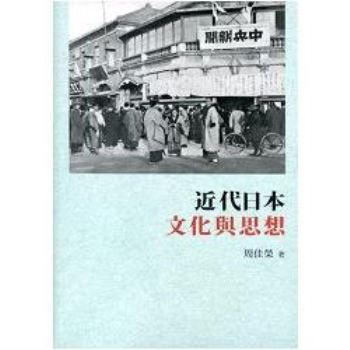第一章近代日本的文化轉承
日本是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邊緣的一個島國,與中國和朝鮮為鄰。古代日本在大陸文明的薰陶下,形成一種頗具獨特性格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明顯可見。到了近代,日本改以西歐文明為模仿和學習的對象,開展了耳目一新的文化面貌。總之,外來文化的攝取,實為日本自古至今的一貫特色,文化的內涵則隨着時代而有所轉換。因此,探討日本的文化問題,便要特別考慮到一些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政治局勢的演變、對外關係的進展以及不同時代的社會實況等等。
第一節開國前後的文化狀況
近代日本始於「明治維新」。在政治上,這是打破長達二百多年「幕藩體制」的一大變革,使日本成為「近代天皇制國家」;在社會經濟上,則是擺脫封建制度的種種羈絆,從而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
所謂幕藩體制,是指德川幕府(又稱江戶幕府;1603-1867)通過地方諸藩(即「大名」所支配的領國及其機構)以維持封建關係及推行封建統治的一種國家組織,可以說是日本最成熟的封建制度。
這個體制有兩大支柱:
其一、是世襲的身份制度。這時代的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等,還有特別身份的公卿、神官、僧侶和學者。以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士是統治階級,享有種種特權,且以庶民的模範自勉,要注重修養、鍛煉武藝與鑽研學問。被統治階級當中,農民的地位最高,這是農本思想的表現,也反映了封建制度是怎樣依存於土地經濟;職工與商人合稱「町人」,其地位雖低,但消費生活不若農民之受限制,又由於近世商業的發展,導致一批新興商人抬頭,有些甚至富甲一方。
其二、是嚴密的鎖國政策。幕府禁止日本船與日人出國,而且只容許中國人及荷蘭人到九州的長崎通商。此舉是要徹底消弭基督教在日本傳播,因為幕府對這既具規模、又有強大背景的外來宗教,從警戒心一變而為猜疑,再變而為恐懼。還有,鎖國在維持封建制度方面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為地方上的大名領國若能自由與海外貿易,勢必累積大量財富,對幕府構成威脅;相反的,由幕府獨佔外交權和貿易權,既鞏固了本身的權力基礎,又能與中央集權政策互為呼應,長期保障了政權的安定。
日本在國際間人為地保持封閉的狀態,文化方面自然選擇了自給自足的途徑。十七世紀的日本人,依然沒有改變舊有的世界觀,他們心目中的「實體」世界,仍只及於中國而已。自從中國經歷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以後,日本也極少與中國接觸,實際上近於一國獨處的局面。要到1853年(嘉永六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MatthewC.Perry,1794-1858)叩關,日本被迫於翌年「開國」,才結束了200年的「鎖國時代」。這時期的封建文化,可從下列幾點反映出來:
首先,在政治思想方面,幕府以儒家學說作為文教政策的基礎,奉朱子學為正宗,藉此維護封建統治下的社會秩序。此外,陽明學派亦很盛行,又有主張直接從孔孟之書探求真義的「古學派」的出現。
其次,在技術發展方面,由於封建社會僅限於本身循環性的再生產,加上鎖國狀態的特殊環境,使日本沒有自覺到與他國競爭求進,同時也缺乏了開發新技術的刺激。當然,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藝、灌溉、土木工事等,是有若干改進的,至於需要應用自然科學原理的領域如造船、醫學、兵術等,便顯得無甚進展了。所以江戶時代的職人,仍只局限於傳統技能的磨煉,並不能有所創革。
再次,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最大的特色是產生了一種在商人之間發展起來、而又肯定商人生活的「町人文學」,及以庶民的感覺去描繪庶民生活的「浮世繪」。大體上說,這時期的作品多集中於描寫享樂的生活,能對封建制度作出正面批判的極少,充其量只是在封建社會的桎梏下刻畫人間的苦痛而已。
不過,隨着封建社會的動搖,學問領域中顯露了一些新的趨勢。除了儒學方面形成折衷各派學說和尊重清代考據學的風氣外,在尊王思想的影響下,具有保守、復古傾向及排外性格的日本「國學」,以一門新興學問的姿態出現;通過荷蘭吸收西洋文物的「蘭學」,也有相當的發展,而且為醫學、天文學、曆學及一些自然科學奠定了基礎。
1774年(安永三年)前野良澤(1723-1803)、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翻譯出版《解體新書》,是日本翻譯「蘭書」的開始,日本出版有關人體解剖的西洋醫學書籍,也以此為最早。其後有兩部主要的蘭學工具書面世,一是大槻玄澤(1757-1827)的入門指南《蘭學階梯》(1783),一是稻村三伯(1758-1811)的蘭日辭典《波留麻和解》(1796)。幕府也鑒於外交事務日增,開始設局翻譯有關文獻,1855年(安政二年)獨立為「洋學所」(後來改稱「蕃書調所」、「洋書調所」、「開成所」等,最後併入東京大學)。至此,蘭學業已擴展成為範圍更廣的「洋學」了。洋學所既是外交文書的翻譯局,又同時從事洋學教育和研究,在幕末時期至明治初年,一直是洋學的中心,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1867年(慶應三年),明治天皇(1852-1912)即位,朝廷計劃以薩摩、長州三藩的武力討伐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省察時勢,奏請「大政奉還」。朝廷於是宣佈「王政復古」,一方面着意於革新國內的體制,一方面開始積極參加國際性的活動。這一連串的歷史過程,包括政治、經濟以至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變革,統稱為「明治維新」。但明治維新究竟始於何時,學界有兩種意見,即「天保」(1830-1840)說和「開國」(1853-1858)說;至於它的下限,更是眾說紛紜,主要有1873年(明治六年)、1877年(明治十年)、1884年(明治十七年)及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等主張,甚至有定在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以1868年改元「明治」作為明治維新的「象徵性」年份,只是一種權宜方式而已。
無論如何,幕末日本與近代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開國前後的文化情況,可以說是近代日本文化的序幕。第二節近代出版活動的發端
出版報刊是近代文化活動的一環,又是文化發展的工具之一。日本近代報業的產生和形成,是明治政府成立以後的事,比歐洲近代報業的興起遲了200年左右。不過,日本報業從最初時起,就與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密切的聯繫,並沿着日本社會變革的特殊軌跡發展下去,在文化、思想、經濟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
近代報刊能夠在日本出現,首先是由於封建制度的崩潰,因為只有這樣,民眾始能置身於全國性的關係之中,才會要求知道廣泛的社會消息;而且,廢止了對報導活動的嚴厲束縛,報刊然後可以充分地回應民眾的要求。此外,印刷術的改善也是一個必需的因近素,否則便沒法迅速地產生向大眾報導各種消息的媒介物。幕末時代雖還沒有具備上述的條件,但近代式的出版活動,已經踏入醞釀的階段了。
日本早在十七世紀,便有《大阪夏之陣圖》、《心中繪草紙》之類單面新聞印刷品的出現,內容都是有關火災、地震、水災、復仇、殉情等,通常附有粗糙的插畫。因為是用黏土雕刻並燒成瓦片印刷出來的,又於街上叫賣,所以稱為「讀賣」或「瓦版」。在德川時代,各種出版物均在禁止之列,但印刷品本身如無傷風敗俗的文字,官府是不嚴加追究的。
在日本的鎖國政策下,荷蘭是中國以外僅有的一個通商國家。幕府允許荷蘭人在長崎海面的出島設立商館,統籌外國商人和幕府間的官方貿易。荷蘭商館的長官把各商船所帶來的外國消息加以整理,然後呈送幕府作為參考,通稱《阿蘭陀風說書》(荷蘭傳聞書)。
1854年(安政元年)日本被迫開國後,荷蘭商館改以荷蘭東印度羣島荷蘭總督府的機關誌「JavascheCourant」(週刊)獻上。幕府認為這是了解海外情況的好材料,於是進行翻譯,由1862年(文久二年)起發行一種十數頁的新聞書,名為《官版巴達維亞新聞》,用木版印刷,是日本最早的新聞印刷品。
譯報之外,又從事翻刻寧波、上海、香港各地英美人士所出版的中文報刊,並加上日本式閱讀法的符號,例如《官版中外新聞》、《官版六合叢談》、《官版香港新聞》等都是。其後由於主張「尊王攘夷」的浪人時常狙擊專與外人接觸的官僚,這類新聞書便停止發行了。
幕末時代的報紙,大約分為兩個系統:一類是外國人經營的英文報,最早的一種,是1861年(文久元年)英人漢沙德(A.W.Hansard)所創的「NagasakiShippingListandAdvertising」(《長崎航訊》),但不久停刊,轉至橫濱另辦「TheJapanHerald」(《日本先鋒報》);此外還有「TheJapanExpress」(《日本快訊》;1862)及「TheJapanCommercialNews」(《日本商業新聞》;1863)等。另一類是洋書調所、開成所系統的報紙,以柳河春三(1830-1870)為中心的一班洋學專家,為了翻譯橫濱等地的外文報刊,結成「會譯社」,出版《日本貿易新聞》、《日本新聞》等,可以稱得上是日本報業的先驅。1865年(慶應元年)間,曾任美國駐日領事館譯官的美籍日本人約瑟‧海科(JosephHeco;後改名濱田彥藏,1837-1897),在橫濱創辦日文的《海外新聞》,轉載英美政經新聞,每月出版一次。近代日本報業,至此才正式宣告開始,會譯社在1868年所辦的《中外新聞》,則是明治時代最早的報紙。
在維新戰亂期中發行的近20種報刊,率先報導了一些有關國內的事情,並且表達了對政治的見解。當時京都、大阪一帶的報紙,都持「勤王」觀點;江戶、橫濱一帶的報紙,則多「佐幕」主張。這些報刊都是十數頁的小冊子,每週出版一次或兩次,其中以佐幕派的《中外新聞》銷數最多,每期約1,500份至數千份。1868年明治新政府的軍隊進駐江戶後,立即取締所有佐幕派報紙,並逮捕了《江湖新聞》的主辦人福地源一郎(櫻痴:1841-1906)。隨後江戶易名東京,定為國都,並逐漸發展成新的文化中心。但這時的日本,對報刊仍未有普遍的需求,即使是沒有遭受禁止的報紙,其壽命也不長。1869-1870年(明治二、三年)間,僅有少數為時短促的報紙出現而已。加上印刷術落後,是一個很大的限制,上述報刊都用木版或木刻活字印刷,就算很受歡迎的書籍,例如銷數達到十萬冊的福澤諭吉(1834-1901)的《西洋事情》初編(1866),也是這樣印成的。
雖然如此,幕末日本在出版事業方面已奠下基礎。舉例來說,幕末最負盛名的出版商,如江戶「老皂館」的萬屋兵四郎,「須原屋」的茂兵衛,「山城屋」的佐吉、政吉,還有京都的村上勘兵衛、井上治兵衛等,他們在進入明治以後,仍然相當活躍。還有,長崎的本木昌造(1824-1875)於1852年(嘉永五年)試製日本鉛字成功,1870年(明治三年)他的弟子陽其二開始用鉛字來印刷《橫濱每日新聞》,1872年(明治五年)他的另一個徒弟平野富在東京神田設立活字販賣店,日本的新式印刷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當然,要到日本大舉學習西方新思想、新事物,教育文化事業日趨普及之後,具備了近代的條件,日本報業才有飛躍的進展。第三節明治文化的特質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致力汲取西洋文化。從當時的情勢來看,日本既已捲入世界潮流,為了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是必須首先從鞏固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入手的,而學習西洋文明正是增強國家實力的一條便捷途徑。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和鼓吹,目的既在於打破封建社會的種種束縛,以建立近代的社會;同時也在於提高國民的程度,使與政府配合,達到富國強兵的地步。至於西方立憲制度的移植,與其說是為了國內的民主化,則毋寧說是為了國家權力的集中和加強,要來得更為恰當。
換言之,近代日本文化是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最大特徵,是以政治力量為主導,實行從上而下的改革。通觀明治時期(1868-1912),文化問題與國家權力的關連是十分密切的,明治政府積極推行的「文明開化」政策,雖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同為指導一切改革的總方針,實際上是從屬於後兩者的,因為文化政策的着眼點是國家,而不是國民個性的成長。而在西洋文化之中,最受到注意的,當然是能夠使國家走向富強的產業技術和軍事科學。這與幕末時代佐久間象山(1811-1864)所說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意即東方以道德、精神為優,西方則擅長科學、技術),本質上並無二致。
1873年(明治六年)創立「明六社」的一班洋學人士,是當時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他們根據「天賦人權論」,把西洋文化作「百科全書式」的介紹,希望藉以養成自發的、奮鬥的國民。照他們所說,眾人都由上天平等地賦予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主張人類平近等,同時也肯定人的慾望是自然之物;不過,天賦人權的保護,則是國家存在的理由。加藤弘之(1836-1916)的《真政大意》(1870)更認為,個人的「不羈自立之情」是秩序形成的根據,但不成為秩序形成的能力主體,國家才是依從「自然之道理」從天降立的。明顯可見,所謂天賦人權,實際上介入了「天賦國權」,成為「國賦人權」。
總之,明六社的思想家雖然站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立場,對封建思想大加撻伐,但由於他們在當時幾乎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大體上是配合着政府的文化政策,為確立強有力的集權政治而努力的。他們置國權於人權之上,在原理上並不認為人民是政治的主體,只承認政府在現階段中對人民「勸導」的重要性;至於強調國民的自主奮鬥,最終亦僅視之為國家發展的動力資源而已。
此外,還需一提,天賦人權論固然是從西方而來,但在日本的傳統思想中是有其淵源的,例如幕末時代對人欲的肯定,重商主義思潮的萌芽,以至富國強兵論等等都是,加藤弘之實際上也具有濃厚的儒家的安民思想。啟蒙思想家並非批判地把傳統思想的一些因素繼承下來,但把這些因素與西洋思想接枝則是事實。明治初年政壇上的領導者,雖有改革的意願,卻不希望進行徹底的變革,對於超越改良程度的變革思想是加以排拒的。這說明了自由主義思想和民權運動,後來何以一轉而為針對統治機構的力量,並且受到彈壓而沉寂下去。一度被人捨棄的儒家思想,竟再次成為御用的學問,也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
至於近代日本所輸入的西洋文化,其實在不同的時期,隨着國內情勢與國際關係的變遷,是有所選擇的。從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接觸最多的是英、美兩國,因此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與美國的新興資本主義文化率先輸入,進化思想與自由思想一同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根基。法國系統的理論也傳到日本,人權思想和社會契約思想對民權運動有莫大的影響。德國系統的思想學問,則是明治政府的保守主義和國權主義的根據,並藉以彈壓民權思想的發展。在明治後半期,更成為支配性的力量。
作為「近代文化」來說,明治文化是有不透徹之處的。它既與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本身自發形成的形態不同,帶有濃厚的外來色彩;也由於從上而下進行的結果,出現了中央與地方、都市與農村、上層社會與下層民眾等等的差距,沒有全面性的均衡發展;還有,不少前近代的因素,如極端的家父長制家族構造、派閥意識、權威主權等,依然盤踞於日本近代社會,有時甚至成為近代化的阻力。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著名的文學家夏目漱石(1867-1976)在一次題為「現代日本之開化」的演講中,指出明治日本的文化是外發的,並沒有像西洋文化一樣,自然地從內部孕育出來。他更認為,不斷接受先進文化的結果,使日本文化的發展呈現了不自然之感,日本人大抵也不能適應,而有神經衰弱的現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夏目漱石是深切體會到明治文化的不協調,從而流露出一種不安感的。
還可留意的是,西洋文化的攝取,目的是為了建設近代國家;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意識自然高漲,而與西洋文化相拮抗的民族主義,也必然隨着出現。明治二十(1877)年代抬頭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的「國粹主義」,以及明治三十(1897)年代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雖各有不同的性格,而都代表這樣的思想。況且明治的民族主義,由於沿着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路線,結果並沒有走向形成國民文化的方面去,而是朝着國家主義發展,甚至後來出現了極端的國家至上主義。
總的來說,近代日本的文化更新是很特異的,若純粹視為一個西化的過程,則所見未免太淺。混雜性、多元性的文化構造,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使日本在處理繁複的近代社會的事務上更見靈巧,但也增添了不少內在的矛盾和混亂。最為明顯的,莫如國家規模有德國之風,社會風氣及經濟結構則富英美色彩;皇室典範模仿英國,「大日本帝國憲法」(或稱明治憲法)則以德國式的君主憲法為藍本;還有德國化的陸軍,英國式的海軍等等,而表現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便是自由民權與國家主義兩種思潮的對峙。明治文化的種種破綻,在踏入大正時期(1912-1926)以後,便漸次顯露出來了。
日本是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邊緣的一個島國,與中國和朝鮮為鄰。古代日本在大陸文明的薰陶下,形成一種頗具獨特性格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明顯可見。到了近代,日本改以西歐文明為模仿和學習的對象,開展了耳目一新的文化面貌。總之,外來文化的攝取,實為日本自古至今的一貫特色,文化的內涵則隨着時代而有所轉換。因此,探討日本的文化問題,便要特別考慮到一些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政治局勢的演變、對外關係的進展以及不同時代的社會實況等等。
第一節開國前後的文化狀況
近代日本始於「明治維新」。在政治上,這是打破長達二百多年「幕藩體制」的一大變革,使日本成為「近代天皇制國家」;在社會經濟上,則是擺脫封建制度的種種羈絆,從而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
所謂幕藩體制,是指德川幕府(又稱江戶幕府;1603-1867)通過地方諸藩(即「大名」所支配的領國及其機構)以維持封建關係及推行封建統治的一種國家組織,可以說是日本最成熟的封建制度。
這個體制有兩大支柱:
其一、是世襲的身份制度。這時代的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等,還有特別身份的公卿、神官、僧侶和學者。以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士是統治階級,享有種種特權,且以庶民的模範自勉,要注重修養、鍛煉武藝與鑽研學問。被統治階級當中,農民的地位最高,這是農本思想的表現,也反映了封建制度是怎樣依存於土地經濟;職工與商人合稱「町人」,其地位雖低,但消費生活不若農民之受限制,又由於近世商業的發展,導致一批新興商人抬頭,有些甚至富甲一方。
其二、是嚴密的鎖國政策。幕府禁止日本船與日人出國,而且只容許中國人及荷蘭人到九州的長崎通商。此舉是要徹底消弭基督教在日本傳播,因為幕府對這既具規模、又有強大背景的外來宗教,從警戒心一變而為猜疑,再變而為恐懼。還有,鎖國在維持封建制度方面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為地方上的大名領國若能自由與海外貿易,勢必累積大量財富,對幕府構成威脅;相反的,由幕府獨佔外交權和貿易權,既鞏固了本身的權力基礎,又能與中央集權政策互為呼應,長期保障了政權的安定。
日本在國際間人為地保持封閉的狀態,文化方面自然選擇了自給自足的途徑。十七世紀的日本人,依然沒有改變舊有的世界觀,他們心目中的「實體」世界,仍只及於中國而已。自從中國經歷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以後,日本也極少與中國接觸,實際上近於一國獨處的局面。要到1853年(嘉永六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MatthewC.Perry,1794-1858)叩關,日本被迫於翌年「開國」,才結束了200年的「鎖國時代」。這時期的封建文化,可從下列幾點反映出來:
首先,在政治思想方面,幕府以儒家學說作為文教政策的基礎,奉朱子學為正宗,藉此維護封建統治下的社會秩序。此外,陽明學派亦很盛行,又有主張直接從孔孟之書探求真義的「古學派」的出現。
其次,在技術發展方面,由於封建社會僅限於本身循環性的再生產,加上鎖國狀態的特殊環境,使日本沒有自覺到與他國競爭求進,同時也缺乏了開發新技術的刺激。當然,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藝、灌溉、土木工事等,是有若干改進的,至於需要應用自然科學原理的領域如造船、醫學、兵術等,便顯得無甚進展了。所以江戶時代的職人,仍只局限於傳統技能的磨煉,並不能有所創革。
再次,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最大的特色是產生了一種在商人之間發展起來、而又肯定商人生活的「町人文學」,及以庶民的感覺去描繪庶民生活的「浮世繪」。大體上說,這時期的作品多集中於描寫享樂的生活,能對封建制度作出正面批判的極少,充其量只是在封建社會的桎梏下刻畫人間的苦痛而已。
不過,隨着封建社會的動搖,學問領域中顯露了一些新的趨勢。除了儒學方面形成折衷各派學說和尊重清代考據學的風氣外,在尊王思想的影響下,具有保守、復古傾向及排外性格的日本「國學」,以一門新興學問的姿態出現;通過荷蘭吸收西洋文物的「蘭學」,也有相當的發展,而且為醫學、天文學、曆學及一些自然科學奠定了基礎。
1774年(安永三年)前野良澤(1723-1803)、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翻譯出版《解體新書》,是日本翻譯「蘭書」的開始,日本出版有關人體解剖的西洋醫學書籍,也以此為最早。其後有兩部主要的蘭學工具書面世,一是大槻玄澤(1757-1827)的入門指南《蘭學階梯》(1783),一是稻村三伯(1758-1811)的蘭日辭典《波留麻和解》(1796)。幕府也鑒於外交事務日增,開始設局翻譯有關文獻,1855年(安政二年)獨立為「洋學所」(後來改稱「蕃書調所」、「洋書調所」、「開成所」等,最後併入東京大學)。至此,蘭學業已擴展成為範圍更廣的「洋學」了。洋學所既是外交文書的翻譯局,又同時從事洋學教育和研究,在幕末時期至明治初年,一直是洋學的中心,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1867年(慶應三年),明治天皇(1852-1912)即位,朝廷計劃以薩摩、長州三藩的武力討伐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省察時勢,奏請「大政奉還」。朝廷於是宣佈「王政復古」,一方面着意於革新國內的體制,一方面開始積極參加國際性的活動。這一連串的歷史過程,包括政治、經濟以至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變革,統稱為「明治維新」。但明治維新究竟始於何時,學界有兩種意見,即「天保」(1830-1840)說和「開國」(1853-1858)說;至於它的下限,更是眾說紛紜,主要有1873年(明治六年)、1877年(明治十年)、1884年(明治十七年)及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等主張,甚至有定在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以1868年改元「明治」作為明治維新的「象徵性」年份,只是一種權宜方式而已。
無論如何,幕末日本與近代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開國前後的文化情況,可以說是近代日本文化的序幕。第二節近代出版活動的發端
出版報刊是近代文化活動的一環,又是文化發展的工具之一。日本近代報業的產生和形成,是明治政府成立以後的事,比歐洲近代報業的興起遲了200年左右。不過,日本報業從最初時起,就與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密切的聯繫,並沿着日本社會變革的特殊軌跡發展下去,在文化、思想、經濟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
近代報刊能夠在日本出現,首先是由於封建制度的崩潰,因為只有這樣,民眾始能置身於全國性的關係之中,才會要求知道廣泛的社會消息;而且,廢止了對報導活動的嚴厲束縛,報刊然後可以充分地回應民眾的要求。此外,印刷術的改善也是一個必需的因近素,否則便沒法迅速地產生向大眾報導各種消息的媒介物。幕末時代雖還沒有具備上述的條件,但近代式的出版活動,已經踏入醞釀的階段了。
日本早在十七世紀,便有《大阪夏之陣圖》、《心中繪草紙》之類單面新聞印刷品的出現,內容都是有關火災、地震、水災、復仇、殉情等,通常附有粗糙的插畫。因為是用黏土雕刻並燒成瓦片印刷出來的,又於街上叫賣,所以稱為「讀賣」或「瓦版」。在德川時代,各種出版物均在禁止之列,但印刷品本身如無傷風敗俗的文字,官府是不嚴加追究的。
在日本的鎖國政策下,荷蘭是中國以外僅有的一個通商國家。幕府允許荷蘭人在長崎海面的出島設立商館,統籌外國商人和幕府間的官方貿易。荷蘭商館的長官把各商船所帶來的外國消息加以整理,然後呈送幕府作為參考,通稱《阿蘭陀風說書》(荷蘭傳聞書)。
1854年(安政元年)日本被迫開國後,荷蘭商館改以荷蘭東印度羣島荷蘭總督府的機關誌「JavascheCourant」(週刊)獻上。幕府認為這是了解海外情況的好材料,於是進行翻譯,由1862年(文久二年)起發行一種十數頁的新聞書,名為《官版巴達維亞新聞》,用木版印刷,是日本最早的新聞印刷品。
譯報之外,又從事翻刻寧波、上海、香港各地英美人士所出版的中文報刊,並加上日本式閱讀法的符號,例如《官版中外新聞》、《官版六合叢談》、《官版香港新聞》等都是。其後由於主張「尊王攘夷」的浪人時常狙擊專與外人接觸的官僚,這類新聞書便停止發行了。
幕末時代的報紙,大約分為兩個系統:一類是外國人經營的英文報,最早的一種,是1861年(文久元年)英人漢沙德(A.W.Hansard)所創的「NagasakiShippingListandAdvertising」(《長崎航訊》),但不久停刊,轉至橫濱另辦「TheJapanHerald」(《日本先鋒報》);此外還有「TheJapanExpress」(《日本快訊》;1862)及「TheJapanCommercialNews」(《日本商業新聞》;1863)等。另一類是洋書調所、開成所系統的報紙,以柳河春三(1830-1870)為中心的一班洋學專家,為了翻譯橫濱等地的外文報刊,結成「會譯社」,出版《日本貿易新聞》、《日本新聞》等,可以稱得上是日本報業的先驅。1865年(慶應元年)間,曾任美國駐日領事館譯官的美籍日本人約瑟‧海科(JosephHeco;後改名濱田彥藏,1837-1897),在橫濱創辦日文的《海外新聞》,轉載英美政經新聞,每月出版一次。近代日本報業,至此才正式宣告開始,會譯社在1868年所辦的《中外新聞》,則是明治時代最早的報紙。
在維新戰亂期中發行的近20種報刊,率先報導了一些有關國內的事情,並且表達了對政治的見解。當時京都、大阪一帶的報紙,都持「勤王」觀點;江戶、橫濱一帶的報紙,則多「佐幕」主張。這些報刊都是十數頁的小冊子,每週出版一次或兩次,其中以佐幕派的《中外新聞》銷數最多,每期約1,500份至數千份。1868年明治新政府的軍隊進駐江戶後,立即取締所有佐幕派報紙,並逮捕了《江湖新聞》的主辦人福地源一郎(櫻痴:1841-1906)。隨後江戶易名東京,定為國都,並逐漸發展成新的文化中心。但這時的日本,對報刊仍未有普遍的需求,即使是沒有遭受禁止的報紙,其壽命也不長。1869-1870年(明治二、三年)間,僅有少數為時短促的報紙出現而已。加上印刷術落後,是一個很大的限制,上述報刊都用木版或木刻活字印刷,就算很受歡迎的書籍,例如銷數達到十萬冊的福澤諭吉(1834-1901)的《西洋事情》初編(1866),也是這樣印成的。
雖然如此,幕末日本在出版事業方面已奠下基礎。舉例來說,幕末最負盛名的出版商,如江戶「老皂館」的萬屋兵四郎,「須原屋」的茂兵衛,「山城屋」的佐吉、政吉,還有京都的村上勘兵衛、井上治兵衛等,他們在進入明治以後,仍然相當活躍。還有,長崎的本木昌造(1824-1875)於1852年(嘉永五年)試製日本鉛字成功,1870年(明治三年)他的弟子陽其二開始用鉛字來印刷《橫濱每日新聞》,1872年(明治五年)他的另一個徒弟平野富在東京神田設立活字販賣店,日本的新式印刷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當然,要到日本大舉學習西方新思想、新事物,教育文化事業日趨普及之後,具備了近代的條件,日本報業才有飛躍的進展。第三節明治文化的特質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致力汲取西洋文化。從當時的情勢來看,日本既已捲入世界潮流,為了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是必須首先從鞏固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入手的,而學習西洋文明正是增強國家實力的一條便捷途徑。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和鼓吹,目的既在於打破封建社會的種種束縛,以建立近代的社會;同時也在於提高國民的程度,使與政府配合,達到富國強兵的地步。至於西方立憲制度的移植,與其說是為了國內的民主化,則毋寧說是為了國家權力的集中和加強,要來得更為恰當。
換言之,近代日本文化是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最大特徵,是以政治力量為主導,實行從上而下的改革。通觀明治時期(1868-1912),文化問題與國家權力的關連是十分密切的,明治政府積極推行的「文明開化」政策,雖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同為指導一切改革的總方針,實際上是從屬於後兩者的,因為文化政策的着眼點是國家,而不是國民個性的成長。而在西洋文化之中,最受到注意的,當然是能夠使國家走向富強的產業技術和軍事科學。這與幕末時代佐久間象山(1811-1864)所說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意即東方以道德、精神為優,西方則擅長科學、技術),本質上並無二致。
1873年(明治六年)創立「明六社」的一班洋學人士,是當時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他們根據「天賦人權論」,把西洋文化作「百科全書式」的介紹,希望藉以養成自發的、奮鬥的國民。照他們所說,眾人都由上天平等地賦予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主張人類平近等,同時也肯定人的慾望是自然之物;不過,天賦人權的保護,則是國家存在的理由。加藤弘之(1836-1916)的《真政大意》(1870)更認為,個人的「不羈自立之情」是秩序形成的根據,但不成為秩序形成的能力主體,國家才是依從「自然之道理」從天降立的。明顯可見,所謂天賦人權,實際上介入了「天賦國權」,成為「國賦人權」。
總之,明六社的思想家雖然站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立場,對封建思想大加撻伐,但由於他們在當時幾乎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大體上是配合着政府的文化政策,為確立強有力的集權政治而努力的。他們置國權於人權之上,在原理上並不認為人民是政治的主體,只承認政府在現階段中對人民「勸導」的重要性;至於強調國民的自主奮鬥,最終亦僅視之為國家發展的動力資源而已。
此外,還需一提,天賦人權論固然是從西方而來,但在日本的傳統思想中是有其淵源的,例如幕末時代對人欲的肯定,重商主義思潮的萌芽,以至富國強兵論等等都是,加藤弘之實際上也具有濃厚的儒家的安民思想。啟蒙思想家並非批判地把傳統思想的一些因素繼承下來,但把這些因素與西洋思想接枝則是事實。明治初年政壇上的領導者,雖有改革的意願,卻不希望進行徹底的變革,對於超越改良程度的變革思想是加以排拒的。這說明了自由主義思想和民權運動,後來何以一轉而為針對統治機構的力量,並且受到彈壓而沉寂下去。一度被人捨棄的儒家思想,竟再次成為御用的學問,也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
至於近代日本所輸入的西洋文化,其實在不同的時期,隨着國內情勢與國際關係的變遷,是有所選擇的。從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接觸最多的是英、美兩國,因此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與美國的新興資本主義文化率先輸入,進化思想與自由思想一同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根基。法國系統的理論也傳到日本,人權思想和社會契約思想對民權運動有莫大的影響。德國系統的思想學問,則是明治政府的保守主義和國權主義的根據,並藉以彈壓民權思想的發展。在明治後半期,更成為支配性的力量。
作為「近代文化」來說,明治文化是有不透徹之處的。它既與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本身自發形成的形態不同,帶有濃厚的外來色彩;也由於從上而下進行的結果,出現了中央與地方、都市與農村、上層社會與下層民眾等等的差距,沒有全面性的均衡發展;還有,不少前近代的因素,如極端的家父長制家族構造、派閥意識、權威主權等,依然盤踞於日本近代社會,有時甚至成為近代化的阻力。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著名的文學家夏目漱石(1867-1976)在一次題為「現代日本之開化」的演講中,指出明治日本的文化是外發的,並沒有像西洋文化一樣,自然地從內部孕育出來。他更認為,不斷接受先進文化的結果,使日本文化的發展呈現了不自然之感,日本人大抵也不能適應,而有神經衰弱的現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夏目漱石是深切體會到明治文化的不協調,從而流露出一種不安感的。
還可留意的是,西洋文化的攝取,目的是為了建設近代國家;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意識自然高漲,而與西洋文化相拮抗的民族主義,也必然隨着出現。明治二十(1877)年代抬頭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的「國粹主義」,以及明治三十(1897)年代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雖各有不同的性格,而都代表這樣的思想。況且明治的民族主義,由於沿着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路線,結果並沒有走向形成國民文化的方面去,而是朝着國家主義發展,甚至後來出現了極端的國家至上主義。
總的來說,近代日本的文化更新是很特異的,若純粹視為一個西化的過程,則所見未免太淺。混雜性、多元性的文化構造,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使日本在處理繁複的近代社會的事務上更見靈巧,但也增添了不少內在的矛盾和混亂。最為明顯的,莫如國家規模有德國之風,社會風氣及經濟結構則富英美色彩;皇室典範模仿英國,「大日本帝國憲法」(或稱明治憲法)則以德國式的君主憲法為藍本;還有德國化的陸軍,英國式的海軍等等,而表現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便是自由民權與國家主義兩種思潮的對峙。明治文化的種種破綻,在踏入大正時期(1912-1926)以後,便漸次顯露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