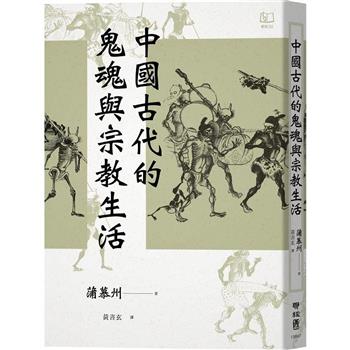早期中國鬼的初跡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西元前四世紀的一位畫家曾被要求替齊國國王作畫。齊王問:「畫孰最難者?」畫家回答:「犬馬最難。」國王又問:「孰最易者?」他回答:「鬼魅最易。」故事的作者解釋說,這是因為狗和馬為人們所熟知,每天都可以看到,因此人們很容易發現畫家畫中的任何缺陷。另一方面,由於從來沒有人真的看過鬼,任何最古怪的畫法都不令人奇怪;因此,要畫它們很容易。這段文獻的作者是韓非(?—西元前二三三年),他是中國歷史上對法律和治國之道發展影響最為深遠的法家思想的創始人。這個故事的初衷,考慮到韓非的動機和敘述的背景,是為了闡述一個概念,即人在有一定規矩系統的限制下做事,要比在沒有任何規矩系統的限制下更難。由此可見法律的重要性。然而作者以鬼畫的例子來說明他的觀點,卻無意中告訴我們,鬼或許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無形的東西,靠人類的想像難以捕捉。的確,曾經有人聽到孔子自己說: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這段話出自《禮記》,這是一部儒家教義和軼事的文集,可能是在西元前三世紀收錄和編輯的。我們很難知道儒學的追隨者在多大程度上會認同這種觀點,但由於它被記錄在盛譽卓越的經典中,並被視為孔子的說法,這句話往往給人的印象是孔子(或他的弟子)視鬼神為無形之物。孔子在《論語》中曾說「敬鬼神而遠之」。這種說法的道理似乎是,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孔子鼓勵他的學生應該根據世俗精神,更多關注在生人的事務上面,而不是聽從薩滿之類從事宗教傳播的人所說的神諭鬼示。然而這句話以及上面引用的《禮記》中的段落,都清楚地表明孔子並沒有否認鬼神的力量和能耐。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孔子及其追隨者在當時社會上只是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在前帝國時期的中國,從西元前十到三世紀,大多數人對鬼是什麼模樣應該都有一些想法,儘管他們可能彼此不同意。然而,如果要追溯鬼的概念的起源和發展,我們有必要回顧最早的文獻。
一、「鬼」的含義與起源
正如前一章所討論的,在漢語語境中鬼的概念通常以「鬼」一字來表示。然而,鬼這個字,就像英文的「ghost」一樣,有不止一層含義。因此,嚴格來說,鬼=ghost這樣的對等式並非沒有問題,我們將在往後繼續討論。
現代漢字的鬼是商代(約西元前一六○○—一一○○年)的甲骨文鬼的直系後裔。對這個字的原始意義的解釋眾說紛紜,有的將其視為死亡面具,有的將其視為薩滿面具,有的認為源自意味恐懼的畏字,或是認為與歸字有關,因為人死歸於地下,《禮記》也說:「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但這種說法是不確定的。東漢學者許慎(約西元三○—一二四年)在其巨著《說文解字》中解釋了鬼字的由來:「鬼者歸也」。這個相當簡短的解釋基本上與《禮記》一致,並假設鬼字的含義與人死後回歸地下的想法有關。然而,這種聯繫僅只是基於鬼和歸兩個字的語音相似,而沒有對鬼這個字本身進行解釋。可以確定的是,在古代使用甲骨文占卜的時候,人們就已經有了某種可以對人類造成傷害的神靈的概念,並用甲骨文表達出來,後來被證明就是鬼這個字。例如,商王夢中出現鬼:「貞,亞(人名)多鬼夢」;「卜,常夢見鬼」;雖然不清楚這些夢是否是惡夢,但其他鬼的出現表明了它的惡意:「卜,鬼為害。」或者鬼可能與疾病有關。因此,這些例子出現的上下文似乎都表明鬼被理解為一種能造成傷害或疾病的惡靈。
此外,鬼也是一支外族部落「鬼方」(字面意思是「鬼域」)名字的一部分,這個名字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現,是商王所進攻的地方。可以合理地推測,這個詞用在異族身上帶有一定的貶義,類似於後來的詞彙蠻、夷、戎、狄(即位居四方的野蠻人)。
至於隨後的周朝(約西元前一一○○—二五六年),當時的文獻呈現出的情況有些複雜。在這個時期的青銅銘文中,鬼這個字的出現似乎沒有「鬼」(死者的精神)的意思,而大多都被用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的複合詞「鬼方」的裡面。然而,鬼作為一個字符,常被結合到其他字中,表明它已經獲得了獨特的含義,可以作為形成某個字或概念的一個「表意符號」或「部首」。這些以鬼為「部首」的文字表明,鬼的符號形象代表一個種類的惡靈,這與商代早期的用法並無區別。
在現存最早的周代典籍之一《詩經》中,鬼這個詞只出現過兩次;其中一個詞又是作為「鬼方」一詞的一部分,另一個則有邪靈或鬼的意味:
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
則不可得。
這裡的鬼與蜮被一起提到,蜮是一種水中的邪靈,被認為能夠給人們帶來傷害。這也與甲骨文和青銅銘文中鬼的意義相吻合。在《詩經》的其他段落中,神一詞經常被用於表示祖先或神靈的精神,是一種榮譽且崇敬的用法。因此,中文中的同一個詞「神」在英文中可以理解為「神」或「精神/靈魂」。
由於神和鬼都表示靈性的存在,因此兩者似乎很自然地會有一些重疊的地方。事實上,在許多先秦文獻中,鬼的概念可以應用於多種的靈性存在。例如,在大約西元前四世紀編纂的第一部大型的編年史《左傳》中,鬼一詞有兩種含義。第一,當與神組成複合詞時,如鬼神,它可以與神同義,指神靈。在《易經》、《尚書》或道家哲學著作《莊子》等早期文獻中也發現鬼同樣的用法。此外,一些例子表明神、鬼神和鬼這三個詞是可以互換的,這表明鬼的概念經常被用來指代神靈。
其次,《左傳》中也有許多鬼的例子,但明確是指死者的靈魂,沒有神性。《論語》中也有類似的情況。《論語》中少數提及鬼和神靈的例子說明鬼可以指某人祖先,而鬼神作為一個複合詞既可以指一般的神靈(包括祖靈和神),也可以與鬼同義。這種含義的轉變表明,鬼的本義是一個通用詞語,泛指人類、神祇甚至動物的精神或靈魂。在甲骨文和青銅銘文以及《詩經》中,鬼一詞似乎僅指具有惡意的人之鬼,這一事實可以理解為是廣義的鬼的概念中的狹隘解釋。
這種鬼與神的混用顯示,後來作為死者精神的鬼和作為神祇精神的神二者之間的區別還沒有明確。這就是為什麼鬼的概念不能被視為現代英語中「ghost」的絕對對等詞的另一個原因。在這裡,現代中國西南地區民族學材料中的鬼魂概念可以提供一個有意義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少數民族中鬼的概念—無論好壞—都很普遍,但神的概念則相對模糊。在某些情況看來,良善的鬼似乎後來可以成為神,而不友善的鬼就成為傷害人的「鬼」。早期中國也有類似的案例。
《禮記》中有一個關於鬼起源的明確陳述,似乎將鬼的概念限制在人類死者身上:「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在《周禮》中,鬼概念也明確與「天神」的神概念區分開來,稱之為「人鬼」——人所變成的鬼。然而,這並不排除其他種類的靈性存在仍然可以被稱為鬼的可能性。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西元前四世紀的一位畫家曾被要求替齊國國王作畫。齊王問:「畫孰最難者?」畫家回答:「犬馬最難。」國王又問:「孰最易者?」他回答:「鬼魅最易。」故事的作者解釋說,這是因為狗和馬為人們所熟知,每天都可以看到,因此人們很容易發現畫家畫中的任何缺陷。另一方面,由於從來沒有人真的看過鬼,任何最古怪的畫法都不令人奇怪;因此,要畫它們很容易。這段文獻的作者是韓非(?—西元前二三三年),他是中國歷史上對法律和治國之道發展影響最為深遠的法家思想的創始人。這個故事的初衷,考慮到韓非的動機和敘述的背景,是為了闡述一個概念,即人在有一定規矩系統的限制下做事,要比在沒有任何規矩系統的限制下更難。由此可見法律的重要性。然而作者以鬼畫的例子來說明他的觀點,卻無意中告訴我們,鬼或許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無形的東西,靠人類的想像難以捕捉。的確,曾經有人聽到孔子自己說: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這段話出自《禮記》,這是一部儒家教義和軼事的文集,可能是在西元前三世紀收錄和編輯的。我們很難知道儒學的追隨者在多大程度上會認同這種觀點,但由於它被記錄在盛譽卓越的經典中,並被視為孔子的說法,這句話往往給人的印象是孔子(或他的弟子)視鬼神為無形之物。孔子在《論語》中曾說「敬鬼神而遠之」。這種說法的道理似乎是,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孔子鼓勵他的學生應該根據世俗精神,更多關注在生人的事務上面,而不是聽從薩滿之類從事宗教傳播的人所說的神諭鬼示。然而這句話以及上面引用的《禮記》中的段落,都清楚地表明孔子並沒有否認鬼神的力量和能耐。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孔子及其追隨者在當時社會上只是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在前帝國時期的中國,從西元前十到三世紀,大多數人對鬼是什麼模樣應該都有一些想法,儘管他們可能彼此不同意。然而,如果要追溯鬼的概念的起源和發展,我們有必要回顧最早的文獻。
一、「鬼」的含義與起源
正如前一章所討論的,在漢語語境中鬼的概念通常以「鬼」一字來表示。然而,鬼這個字,就像英文的「ghost」一樣,有不止一層含義。因此,嚴格來說,鬼=ghost這樣的對等式並非沒有問題,我們將在往後繼續討論。
現代漢字的鬼是商代(約西元前一六○○—一一○○年)的甲骨文鬼的直系後裔。對這個字的原始意義的解釋眾說紛紜,有的將其視為死亡面具,有的將其視為薩滿面具,有的認為源自意味恐懼的畏字,或是認為與歸字有關,因為人死歸於地下,《禮記》也說:「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但這種說法是不確定的。東漢學者許慎(約西元三○—一二四年)在其巨著《說文解字》中解釋了鬼字的由來:「鬼者歸也」。這個相當簡短的解釋基本上與《禮記》一致,並假設鬼字的含義與人死後回歸地下的想法有關。然而,這種聯繫僅只是基於鬼和歸兩個字的語音相似,而沒有對鬼這個字本身進行解釋。可以確定的是,在古代使用甲骨文占卜的時候,人們就已經有了某種可以對人類造成傷害的神靈的概念,並用甲骨文表達出來,後來被證明就是鬼這個字。例如,商王夢中出現鬼:「貞,亞(人名)多鬼夢」;「卜,常夢見鬼」;雖然不清楚這些夢是否是惡夢,但其他鬼的出現表明了它的惡意:「卜,鬼為害。」或者鬼可能與疾病有關。因此,這些例子出現的上下文似乎都表明鬼被理解為一種能造成傷害或疾病的惡靈。
此外,鬼也是一支外族部落「鬼方」(字面意思是「鬼域」)名字的一部分,這個名字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現,是商王所進攻的地方。可以合理地推測,這個詞用在異族身上帶有一定的貶義,類似於後來的詞彙蠻、夷、戎、狄(即位居四方的野蠻人)。
至於隨後的周朝(約西元前一一○○—二五六年),當時的文獻呈現出的情況有些複雜。在這個時期的青銅銘文中,鬼這個字的出現似乎沒有「鬼」(死者的精神)的意思,而大多都被用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的複合詞「鬼方」的裡面。然而,鬼作為一個字符,常被結合到其他字中,表明它已經獲得了獨特的含義,可以作為形成某個字或概念的一個「表意符號」或「部首」。這些以鬼為「部首」的文字表明,鬼的符號形象代表一個種類的惡靈,這與商代早期的用法並無區別。
在現存最早的周代典籍之一《詩經》中,鬼這個詞只出現過兩次;其中一個詞又是作為「鬼方」一詞的一部分,另一個則有邪靈或鬼的意味:
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
則不可得。
這裡的鬼與蜮被一起提到,蜮是一種水中的邪靈,被認為能夠給人們帶來傷害。這也與甲骨文和青銅銘文中鬼的意義相吻合。在《詩經》的其他段落中,神一詞經常被用於表示祖先或神靈的精神,是一種榮譽且崇敬的用法。因此,中文中的同一個詞「神」在英文中可以理解為「神」或「精神/靈魂」。
由於神和鬼都表示靈性的存在,因此兩者似乎很自然地會有一些重疊的地方。事實上,在許多先秦文獻中,鬼的概念可以應用於多種的靈性存在。例如,在大約西元前四世紀編纂的第一部大型的編年史《左傳》中,鬼一詞有兩種含義。第一,當與神組成複合詞時,如鬼神,它可以與神同義,指神靈。在《易經》、《尚書》或道家哲學著作《莊子》等早期文獻中也發現鬼同樣的用法。此外,一些例子表明神、鬼神和鬼這三個詞是可以互換的,這表明鬼的概念經常被用來指代神靈。
其次,《左傳》中也有許多鬼的例子,但明確是指死者的靈魂,沒有神性。《論語》中也有類似的情況。《論語》中少數提及鬼和神靈的例子說明鬼可以指某人祖先,而鬼神作為一個複合詞既可以指一般的神靈(包括祖靈和神),也可以與鬼同義。這種含義的轉變表明,鬼的本義是一個通用詞語,泛指人類、神祇甚至動物的精神或靈魂。在甲骨文和青銅銘文以及《詩經》中,鬼一詞似乎僅指具有惡意的人之鬼,這一事實可以理解為是廣義的鬼的概念中的狹隘解釋。
這種鬼與神的混用顯示,後來作為死者精神的鬼和作為神祇精神的神二者之間的區別還沒有明確。這就是為什麼鬼的概念不能被視為現代英語中「ghost」的絕對對等詞的另一個原因。在這裡,現代中國西南地區民族學材料中的鬼魂概念可以提供一個有意義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少數民族中鬼的概念—無論好壞—都很普遍,但神的概念則相對模糊。在某些情況看來,良善的鬼似乎後來可以成為神,而不友善的鬼就成為傷害人的「鬼」。早期中國也有類似的案例。
《禮記》中有一個關於鬼起源的明確陳述,似乎將鬼的概念限制在人類死者身上:「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在《周禮》中,鬼概念也明確與「天神」的神概念區分開來,稱之為「人鬼」——人所變成的鬼。然而,這並不排除其他種類的靈性存在仍然可以被稱為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