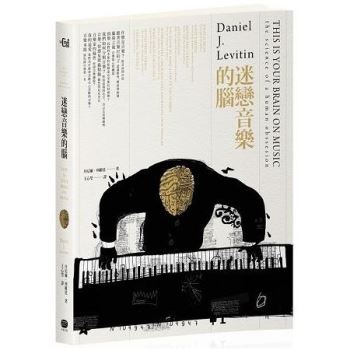第三章 簾幕之後 音樂與心智機器
人類的大腦分為四葉,分別是額葉、顳葉、頂葉和枕葉,外加小腦。我們可對這些部位的功能做粗略的歸納,但事實上,人的行為是很複雜的,無法輕易化約成簡單的分布圖。額葉與規畫能力及自制有關,也具有從感覺系統接收的龐雜訊號中抽繹意義的能力,這正是完形心理學家所說的知覺組織(perceptual organization)。顳葉與聽覺和記憶有關,額葉後區與運動能力有關,枕葉則與視覺有關。小腦與情緒和整體動作協調有關,許多動物(例如爬行類)缺少功能較高級的大腦皮質,但都有小腦。切下額葉內的前額葉皮質,使之與視丘分離的手術稱作前額葉切割術。雷蒙斯樂團(Ramones)有首歌叫〈青少年前額葉切割術〉(Teenage Lobotomy),歌詞內容如下「如今我得告訴他們/我沒有小腦」由解剖學看來並不正確,但考慮到藝術表現的自由,以及他們創作出了搖滾樂史上偉大的歌詞韻腳份上,讓人很難不給他們掌聲。
音樂活動牽涉目前已知的近乎全部腦區,也涵蓋將近所有周圍神經系統。音樂的各種要素分別由不同神經處理,亦即大腦會以各個不同功能的分區來處理音樂,並運用偵測系統分析音樂訊號的音高、速度、音色等各種要素。處理音樂訊息的部分過程與分析其他聲音的方式具有共通性,例如接收他人的話語時,需把聲音切分成字詞、句子和片語,我們才能理解話語的言外之意,如諷刺意味(這點就不那麼有趣了)等,而樂音也可分作數個層面來分析,通常牽涉數種「類獨立神經過程」(quasi-independent neural processes),分析結果也需要經過整合,才能使樂音形成完整的心智表徵。腦部對音樂的反應由皮質下結構(包括耳蝸神經核、腦幹和小腦)開始,然後移至大腦兩側的聽覺皮質。聆聽熟知的樂曲或音樂類型,例如巴洛克音樂或藍調音樂,則會動用大腦中更多區域,包括記憶中樞的海馬迴及部分額葉(特別是下額葉皮質,這個部位在額葉的最下方)。隨著音樂打拍子時,無論是否結合肢體動作,都會牽涉小腦的計時迴路。演奏音樂(無論演奏何種樂器,或是哼唱、指揮音樂)則會再度動用額葉,以規畫肢體行為,同時結合位於額葉後方、靠近頭頂的運動皮質,當你按下琴鍵,或依心中所想地揮動指揮棒時,感覺皮質便會提供觸覺回饋。閱讀樂譜則會使用頭部後方、位於枕葉的視覺皮質。聆聽或回想歌詞則需運用語言中樞,包括布羅卡區(額下迴)和維尼克區,以及位於顳葉和額葉的其他語言中樞。
接著我們來看大腦更深層的運作,音樂所引發的情緒來自杏仁核,以及深藏在原始爬蟲類腦內的小腦蚓部(verebellar vermis)。前者是大腦皮質的情緒中樞。整體來看,大腦各區域的功能專一性十分明顯,但各功能分區間的互補原則也能發揮效用。大腦是高度平行運作的裝置,各種運作過程牽涉腦中諸多區域。大腦沒有單一的語言中樞,也沒有單一的音樂中樞,而是由許多區域分別處理,另有一些區域負責協調訊息的統整程序。直到最近,我們終於發現大腦具有遠超乎想像的重組能力,稱為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這項能力意味著大腦中部分區域的功能專一性是暫時的,當個體遭受創傷或腦部受創,處理重要心智功能的中樞便會轉移至大腦其他區域。
由於描述腦部運作所需的數字實在太過龐大,完全超出日常經驗(除非你是宇宙學家)的水準,因此一般人難以體會大腦的複雜程度。大腦平均由一千億個神經元組成,若將神經元比作一元硬幣,而你站在街角,要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硬幣遞給路過的人。假設你每秒遞出一元,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地遞出硬幣,那麼從耶穌出生起算至今,你也才遞出全部的三分之二。就算一秒可以遞出一百個硬幣,也要花費三十二年才能全部送出。神經元的數目確實十分龐大,不過大腦與思想真正的能力與複雜度,乃是來自神經元之間的連結。神經元之間會互相連結,一個神經元所能連結的數量從一千個到一萬個不等。區區四個神經元就有六十三種連結方式,總共產生六十四種連結。一旦神經元數目增加,連結數更會呈指數成長:
n 個神經元會產生2(n*(n-1)/2) 種連結
兩個神經元會產生兩種連結
三個神經元會產生八種連結
四個神經元會產生六十四種連結
五個神經元會產生一、○二四種連結
六個神經元會產生三二、七六八種連結
由於數字實在太龐大,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大腦內所有神經元共有多少種連結方式,也無從得知這些連結所代表的意義。連結的數量代表可能產生的思想數量,或者大腦狀態,而這數目遠遠超過宇宙中的已知粒子數。
第四章 預期 我們對李斯特和路達克里斯有何預期?
參加婚禮時,最能使我熱淚盈眶的,並非新人站在親朋好友面前,懷抱著滿滿的希望與愛迎向未來人生的情景。我往往在婚禮音樂響起的那一刻就落下淚來。觀賞電影時,當劇中佳偶歷經重重考驗後終於再度團圓,這時的背景音樂也會觸動我,將我的情緒推至感性的臨界點。
如先前所述,音樂是有組織的聲音,但這組織應包含某些令人無法預期的元素,在情感上才不會顯得平淡而呆板。對音樂的鑑賞能力,取決於理解音樂結構(如同語言或手語的語法)的能力,能否對樂曲的發展做出預期也同等重要。作曲家要為音樂注入情感,須能了解聽者對音樂的預期,然後巧妙地操作樂曲走向,決定何時滿足這份預期,何時則否。我們之所以為音樂而興奮、顫慄甚至感動落淚,往往是因為熟練的作曲家以及負責詮釋的音樂家,能夠高明地操控我們的預期之故。
西方古典音樂中,紀錄最豐富的錯覺(或說應酬伎倆),稱為「假終止式」。終止式是一段和弦序列,令聽者對樂曲走向產生清楚的預期後走向結束,通常會以能夠滿足聽者預期的「解決」(resolution)作結。在假終止式中,作曲家則會再三重複同一段和弦序列,令聽者確信自己預期的結果即將來臨,然而就在最後一刻,作曲家會丟出一個意想不到的和弦,不是走調,而是一個未完全解決,告知樂曲尚未結束的和弦。海頓經常運用這種假終止式,簡直有點像是著了魔。庫克比之為魔術戲法:魔術師先製造一些預期,再加以推翻,而你完全無法得知他們將如何、何時推翻你的預期。作曲家也會玩同樣的把戲,如披頭四的歌曲〈不為誰〉結束於五級和弦(音階的第五音級),聽者所期待的解決並未出現(至少不在這首),而同張專輯的下一首曲目,竟是從聽者所期待的解決降下一個全音級(降七級音)開始奏起,形成半終止式,令人又是驚訝,又覺鬆了口氣。建立預期然後操控,這正是音樂的核心,而且有無數種方式可達到目的。史提利丹樂團(Steely Dan)的做法是以藍調形式演奏歌曲(運用藍調的結構與和弦進行),並為和弦加上一些特殊的和聲,使之聽來非常不像藍調音樂,如〈廉價威士忌〉(Chain Lightning)便是採用這樣的作法。邁爾斯.戴維斯和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之所以能在爵士樂壇享有崇高地位,正是因為他們為藍調音樂重配和聲,創造出揉合舊曲新聲的全新樂曲。史提利丹樂團的唐諾.費根(Donald Fagen)曾單飛出輯《螳螂》(Kamakiriad),其中一首歌開頭帶有藍調和放克的節奏,使我們預期該曲將有標準的藍調和弦進行,然而這首歌開頭的一分半之內只用了一個和弦,而且不曾離開同一個的把位。艾瑞莎.弗蘭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歌曲〈一群傻子〉(Chain of Fools)則更徹底,整首歌只用了一個和弦。披頭四的〈昨日〉(Yesterday)主旋律樂句長達七個小節,顛覆了流行音樂的基本假設,即樂句應以四小節或八小節為一單位(幾乎所有流行與搖滾歌曲都是以這樣長度的樂句組成)。另一首歌〈我要你(她是如此重要)〉(I Want You 〔Shes So Heavy〕)則顛覆了另一項預期,開頭是如催眠般不斷重複,彷彿永遠不會結束的終止曲式,而根據以往聆聽搖滾樂的經驗,我們以為這首歌會以逐漸降低音量,即典型的淡出結尾,相反地,這首歌卻?然而止,甚至不是停在樂句的結束,而是中間的某個音!
木匠兄妹合唱團(Carpenters)則以音色顛覆我們的預期。他們應該是樂迷心目中最不可能運用電吉他破音音效的合唱團體,然而在〈請等一下,郵差先生〉(Please Mr Postman)等歌曲中,這樣的假設遭到了推翻。滾石樂團堪稱世上最激烈的硬式搖滾樂團,前幾年卻反其道而行,甚至在〈淚水流逝〉(As Tears Go By)等曲目中使用了小提琴。范海倫樂團還是新起之秀時,便做了一件讓樂迷驚訝不已的事:他們把奇想樂團(The Kinks)一首不那麼時髦的老歌〈迷上了妳〉改編成重金屬搖滾版本。對節奏的預期更是經常遭到顛覆。電子藍調中的標準手法是讓樂團先醞釀情緒後中止演奏,留下歌手或主奏吉他手繼續唱奏,這種手法可見於史提夫.雷.范(Stevie Ray Vaughan)的歌曲〈驕傲與快樂〉(Pride and Joy)、貓王的〈獵犬〉(Hound Dog),或者歐曼兄弟樂團(Allman Brothers)的〈別無他路〉(One Way Out)。電子藍調歌曲典型的結尾也是一例,曲子以穩定的拍子進行二至三分鐘,然後??重重一擊!當和弦暗示著樂曲即將結束,樂團卻開始用原先的一半速度演奏。還有雙重打擊。清水樂團在〈看好我的後門〉(Lookin Out My Back Door)的結尾逐漸放慢速度(這在當時已是常見手法),然後顛覆我們的預期,拉回原本的速度演奏真正的結尾。
警察合唱團也以顛覆節奏預期而聞名。搖滾樂標準的節奏模式是強拍落在第一和第三拍(即低音鼓的落點),小鼓則敲在第二和第四拍(反拍)。雷鬼音樂聽來速度彷彿只有搖滾樂的一半(巴布.馬利的音樂是最明顯的例子),因為低音鼓和小鼓在樂句中的敲擊次數只有搖滾樂的一半。雷鬼音樂的基本拍子是吉他彈在「上拍」(或稱弱拍),也就是說,吉他彈在主要拍子之間的空檔,例如:1 AND-A 2 AND 3 AND-A 4 AND 。這種「只有一半速度」的感覺,使得雷鬼音樂表現出慵懶的特質,然而弱拍則傳遞一種動感,將音樂往前推進。警察樂團結合雷鬼音樂與搖滾樂,創造出一種新曲風,既顛覆也滿足我們對節奏的某些預期。主唱史汀經常以嶄新的方式彈奏貝斯,避開搖滾樂總是彈在強拍或與低音鼓同拍的慣用手法。正如頂尖錄音室貝斯手蘭迪.傑克森(Randy Jackson)所告訴我的(我們曾於一九八○年代共用錄音室的辦公室),史汀的貝斯聲線與眾不同,甚至無法用於任何其他人的歌曲中。警察樂團的專輯《機器裡的幽靈》(Ghost in the Machine)中一首〈物質世界裡的幽魂〉(Spirits in the Material World),便將其獨特的節奏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聽者幾乎無法分辨曲中的強拍落在何處。
荀白克等現代音樂作曲家同樣將預期拋諸腦後。他們所用的音階完全剝除我們對和弦中的解決與根音以及音樂的「家」(home)的概念,製造出沒有家的錯覺,產生一種漂流無依的音樂,也許這正是二十世紀存在主義式的隱喻(又或許只是想標新立異)。如今我們仍可在電影配樂聽到這類音階,用來搭配夢境一般的場景,襯托劇中人漂浮無依、潛入水中或身處太空失重狀態的情境。
第五章 我們如何分類音樂? 你知道我的名字, 自己去查號碼吧
我對音樂最早的記憶來自三歲時,我的母親彈著家中的平台式鋼琴,我則躺在鋼琴下一塊毛茸茸的綠色羊毛地毯上。平台式鋼琴就在我頭上,只見母親的腿不斷上下踩著踏板,我彷彿被鋼琴的聲音淹沒。琴音充塞四面八方,那振動穿透地板和我的身體,我感覺低音就在身體右方,高音則在左方。貝多芬的和弦響亮而緊密;蕭邦的音符如雜耍般舞動,如風雪吹拂;舒曼的節奏嚴整如行軍,他和母親同樣是德國人──這一切構成我對音樂最早的記憶,那聲音令我完全入迷,將我帶往未曾體驗的感官世界。當音樂持續演奏,時間彷彿靜止。
音樂的記憶與其他記憶有何不同?為何音樂似乎能觸動深藏心底或已然流逝的回憶?音樂的預期如何使我們體驗音樂中的情感?我們又是如何認出以往聽過的歌曲?辨認曲調牽涉不少複雜的神經運算,並且與記憶息息相關。當我們專注於樂曲中多次演奏都未曾改變的特徵時,大腦則須忽略其他某些特徵,如此才能擷取出歌曲中不變的特質。也就是說,大腦的運算系統必須將歌曲的各個部分獨立開來,留下每次聆聽經驗中相同的部分,剔除每次都有所變化的部分,或某次的獨特詮釋。如果大腦不這麼做,只要一首歌以不同音量播放,你就會以為自己聽到的是一首全新的歌!而音量並非唯一即使大幅度改變也不影響我們辨識歌曲的參數。演奏用的樂器、速度和音高也都不影響歌曲的辨識基準。也就是說,在擷取能夠辨識歌曲的特徵時,這類特徵即使有任何變化,我們也都不予理會。
辨識歌曲大幅增加了神經系統處理音樂的複雜性。從各種變化中擷取歌曲不變的特徵,可說是件浩大的運算工程。一九九○年代末期,我曾在一家網路公司工作,該公司正在發展辨識MP3 檔案的軟體。很多人的電腦都存有聲音檔,但那些檔案往往不是檔名錯誤,就是根本沒有檔名。沒有人願意逐一檢查所有檔案、修正像「Etlon John」這樣的拼字錯誤,或者把艾維斯.卡斯提洛(Elvis Costello)的〈我是認真的〉(My Aim Is True)更名為〈艾莉森〉(Alison,「我是認真的」是副歌中一句歌詞,而非歌名)。
自動命名的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因為每首歌都有數位指紋,我們只須學會如何在包含五十萬首歌曲的資料庫中有效率地搜尋,以正確地指認歌曲。電腦科學家稱之為「查找表」(lookup table)。當你查詢社會安全號碼資料庫時,輸入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資料庫應該只會顯示一組社會安全號碼。同樣地,查詢歌曲資料庫時,輸入某首歌的某個特定版本之數位值,應該只會得到一
首相應的歌曲。查找程式看似運作得完美無瑕,但還是有其限制,它無法找出資料庫中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假設我的硬碟內存有八種版本的〈沙人〉(Mr. Sandman),當我輸入吉他大師查特.亞金斯(Chet Atkins)的演奏,並要求程式依此找出電吉他手吉姆.坎皮隆戈(Jim Campilongo),或和聲女音四重唱(The Chordettes)演唱的版本時,電腦就無法做到了。這是因為MP3 檔案開頭的數值串需經過轉譯才會成為旋律、節奏或響度等要素,而我們還不知道如何進行轉譯。查找程式必須能夠辨識相對不變的旋律與節奏,並忽略因不同表演而生的差異,才可能建立版本的連結。以目前的電腦設備,連起步都有困難,而人腦卻能輕鬆地做到這點。
電腦和人腦在這方面有不同的能力,正與我們對人類記憶的本質與功能所進行的討論有關。近來針對音樂記憶所做的實驗,恰好為釐清真相提供了確切的線索。過去一百多年來,記憶理論學者激烈地爭辯著:人與動物的記憶是相對的,抑或絕對的?主張相對的學派認為,我們的記憶系統儲存的是事物與想法之間的關係,無需記住事物本身的細節。這派論點也稱為構成主義觀點,意指即使缺乏感知細節,我們依然能根據感知之間的關係,立即自行填補或重建細節,建構對現實的記憶表徵。構成主義者認為記憶的功能是忽略不相關的細節,只保留「要點」。與之相對的是「紀錄保存理論」(record-keeping theory),其擁護者認為記憶就像錄音機或數位錄影機,精確記錄我們的全數或多數體驗,並以近乎完美的水準忠實再現。音樂也是論辯主題之一,因為如同一百多年前的完形心理學家所言,旋律是由音高之間的關係所決定(這是構成主義觀點),卻也由確切的音高所組成(這是紀錄保存觀點,但前提是音高會儲存在記憶裡)。兩派論點都累積了大量的證據。持構成主義觀點的實驗研究者請受試者聆聽講詞(聽覺記憶)或閱讀文章(視覺記憶),然後說出他們聽到或讀到些什麼。一般來說,人們不太能逐字重述內容,他們能記住大意,但記不住特定的用詞。
許多研究也指出記憶具有可塑性。小小的干擾也可能會對記憶提取造成重大影響。華盛頓大學的伊莉莎白.羅夫塔斯(Elizabeth F. Loftus)做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她對法庭上證人講述證詞的精確度非常感興趣。羅夫塔斯讓受試者觀看錄影帶,然後針對影片內容提出誘導式的提問。當錄影帶中兩輛汽車幾乎發生擦撞時,她會問一組受試者:「兩車發生擦撞時,雙方車速多少?」
然後問另一組受試者:「兩車猛烈撞擊時,雙方車速多少?」結果光是用詞上的差異,就讓兩組受試者估計的車速相差十萬八千里。接著,羅夫塔斯會在一段時間之後(有時長達一星期之久),再次邀請受試者來到實驗室,然後問他們:「你看見幾片玻璃破裂?」(事實上沒有任何玻璃破裂。)當時接收到「猛烈撞擊」字眼的受試者,有較高比例的人「記得」影片中有玻璃破裂。這群受試者其實是根據一週前的提問,重新建構了自己的記憶。
人類的大腦分為四葉,分別是額葉、顳葉、頂葉和枕葉,外加小腦。我們可對這些部位的功能做粗略的歸納,但事實上,人的行為是很複雜的,無法輕易化約成簡單的分布圖。額葉與規畫能力及自制有關,也具有從感覺系統接收的龐雜訊號中抽繹意義的能力,這正是完形心理學家所說的知覺組織(perceptual organization)。顳葉與聽覺和記憶有關,額葉後區與運動能力有關,枕葉則與視覺有關。小腦與情緒和整體動作協調有關,許多動物(例如爬行類)缺少功能較高級的大腦皮質,但都有小腦。切下額葉內的前額葉皮質,使之與視丘分離的手術稱作前額葉切割術。雷蒙斯樂團(Ramones)有首歌叫〈青少年前額葉切割術〉(Teenage Lobotomy),歌詞內容如下「如今我得告訴他們/我沒有小腦」由解剖學看來並不正確,但考慮到藝術表現的自由,以及他們創作出了搖滾樂史上偉大的歌詞韻腳份上,讓人很難不給他們掌聲。
音樂活動牽涉目前已知的近乎全部腦區,也涵蓋將近所有周圍神經系統。音樂的各種要素分別由不同神經處理,亦即大腦會以各個不同功能的分區來處理音樂,並運用偵測系統分析音樂訊號的音高、速度、音色等各種要素。處理音樂訊息的部分過程與分析其他聲音的方式具有共通性,例如接收他人的話語時,需把聲音切分成字詞、句子和片語,我們才能理解話語的言外之意,如諷刺意味(這點就不那麼有趣了)等,而樂音也可分作數個層面來分析,通常牽涉數種「類獨立神經過程」(quasi-independent neural processes),分析結果也需要經過整合,才能使樂音形成完整的心智表徵。腦部對音樂的反應由皮質下結構(包括耳蝸神經核、腦幹和小腦)開始,然後移至大腦兩側的聽覺皮質。聆聽熟知的樂曲或音樂類型,例如巴洛克音樂或藍調音樂,則會動用大腦中更多區域,包括記憶中樞的海馬迴及部分額葉(特別是下額葉皮質,這個部位在額葉的最下方)。隨著音樂打拍子時,無論是否結合肢體動作,都會牽涉小腦的計時迴路。演奏音樂(無論演奏何種樂器,或是哼唱、指揮音樂)則會再度動用額葉,以規畫肢體行為,同時結合位於額葉後方、靠近頭頂的運動皮質,當你按下琴鍵,或依心中所想地揮動指揮棒時,感覺皮質便會提供觸覺回饋。閱讀樂譜則會使用頭部後方、位於枕葉的視覺皮質。聆聽或回想歌詞則需運用語言中樞,包括布羅卡區(額下迴)和維尼克區,以及位於顳葉和額葉的其他語言中樞。
接著我們來看大腦更深層的運作,音樂所引發的情緒來自杏仁核,以及深藏在原始爬蟲類腦內的小腦蚓部(verebellar vermis)。前者是大腦皮質的情緒中樞。整體來看,大腦各區域的功能專一性十分明顯,但各功能分區間的互補原則也能發揮效用。大腦是高度平行運作的裝置,各種運作過程牽涉腦中諸多區域。大腦沒有單一的語言中樞,也沒有單一的音樂中樞,而是由許多區域分別處理,另有一些區域負責協調訊息的統整程序。直到最近,我們終於發現大腦具有遠超乎想像的重組能力,稱為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這項能力意味著大腦中部分區域的功能專一性是暫時的,當個體遭受創傷或腦部受創,處理重要心智功能的中樞便會轉移至大腦其他區域。
由於描述腦部運作所需的數字實在太過龐大,完全超出日常經驗(除非你是宇宙學家)的水準,因此一般人難以體會大腦的複雜程度。大腦平均由一千億個神經元組成,若將神經元比作一元硬幣,而你站在街角,要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硬幣遞給路過的人。假設你每秒遞出一元,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地遞出硬幣,那麼從耶穌出生起算至今,你也才遞出全部的三分之二。就算一秒可以遞出一百個硬幣,也要花費三十二年才能全部送出。神經元的數目確實十分龐大,不過大腦與思想真正的能力與複雜度,乃是來自神經元之間的連結。神經元之間會互相連結,一個神經元所能連結的數量從一千個到一萬個不等。區區四個神經元就有六十三種連結方式,總共產生六十四種連結。一旦神經元數目增加,連結數更會呈指數成長:
n 個神經元會產生2(n*(n-1)/2) 種連結
兩個神經元會產生兩種連結
三個神經元會產生八種連結
四個神經元會產生六十四種連結
五個神經元會產生一、○二四種連結
六個神經元會產生三二、七六八種連結
由於數字實在太龐大,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大腦內所有神經元共有多少種連結方式,也無從得知這些連結所代表的意義。連結的數量代表可能產生的思想數量,或者大腦狀態,而這數目遠遠超過宇宙中的已知粒子數。
第四章 預期 我們對李斯特和路達克里斯有何預期?
參加婚禮時,最能使我熱淚盈眶的,並非新人站在親朋好友面前,懷抱著滿滿的希望與愛迎向未來人生的情景。我往往在婚禮音樂響起的那一刻就落下淚來。觀賞電影時,當劇中佳偶歷經重重考驗後終於再度團圓,這時的背景音樂也會觸動我,將我的情緒推至感性的臨界點。
如先前所述,音樂是有組織的聲音,但這組織應包含某些令人無法預期的元素,在情感上才不會顯得平淡而呆板。對音樂的鑑賞能力,取決於理解音樂結構(如同語言或手語的語法)的能力,能否對樂曲的發展做出預期也同等重要。作曲家要為音樂注入情感,須能了解聽者對音樂的預期,然後巧妙地操作樂曲走向,決定何時滿足這份預期,何時則否。我們之所以為音樂而興奮、顫慄甚至感動落淚,往往是因為熟練的作曲家以及負責詮釋的音樂家,能夠高明地操控我們的預期之故。
西方古典音樂中,紀錄最豐富的錯覺(或說應酬伎倆),稱為「假終止式」。終止式是一段和弦序列,令聽者對樂曲走向產生清楚的預期後走向結束,通常會以能夠滿足聽者預期的「解決」(resolution)作結。在假終止式中,作曲家則會再三重複同一段和弦序列,令聽者確信自己預期的結果即將來臨,然而就在最後一刻,作曲家會丟出一個意想不到的和弦,不是走調,而是一個未完全解決,告知樂曲尚未結束的和弦。海頓經常運用這種假終止式,簡直有點像是著了魔。庫克比之為魔術戲法:魔術師先製造一些預期,再加以推翻,而你完全無法得知他們將如何、何時推翻你的預期。作曲家也會玩同樣的把戲,如披頭四的歌曲〈不為誰〉結束於五級和弦(音階的第五音級),聽者所期待的解決並未出現(至少不在這首),而同張專輯的下一首曲目,竟是從聽者所期待的解決降下一個全音級(降七級音)開始奏起,形成半終止式,令人又是驚訝,又覺鬆了口氣。建立預期然後操控,這正是音樂的核心,而且有無數種方式可達到目的。史提利丹樂團(Steely Dan)的做法是以藍調形式演奏歌曲(運用藍調的結構與和弦進行),並為和弦加上一些特殊的和聲,使之聽來非常不像藍調音樂,如〈廉價威士忌〉(Chain Lightning)便是採用這樣的作法。邁爾斯.戴維斯和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之所以能在爵士樂壇享有崇高地位,正是因為他們為藍調音樂重配和聲,創造出揉合舊曲新聲的全新樂曲。史提利丹樂團的唐諾.費根(Donald Fagen)曾單飛出輯《螳螂》(Kamakiriad),其中一首歌開頭帶有藍調和放克的節奏,使我們預期該曲將有標準的藍調和弦進行,然而這首歌開頭的一分半之內只用了一個和弦,而且不曾離開同一個的把位。艾瑞莎.弗蘭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歌曲〈一群傻子〉(Chain of Fools)則更徹底,整首歌只用了一個和弦。披頭四的〈昨日〉(Yesterday)主旋律樂句長達七個小節,顛覆了流行音樂的基本假設,即樂句應以四小節或八小節為一單位(幾乎所有流行與搖滾歌曲都是以這樣長度的樂句組成)。另一首歌〈我要你(她是如此重要)〉(I Want You 〔Shes So Heavy〕)則顛覆了另一項預期,開頭是如催眠般不斷重複,彷彿永遠不會結束的終止曲式,而根據以往聆聽搖滾樂的經驗,我們以為這首歌會以逐漸降低音量,即典型的淡出結尾,相反地,這首歌卻?然而止,甚至不是停在樂句的結束,而是中間的某個音!
木匠兄妹合唱團(Carpenters)則以音色顛覆我們的預期。他們應該是樂迷心目中最不可能運用電吉他破音音效的合唱團體,然而在〈請等一下,郵差先生〉(Please Mr Postman)等歌曲中,這樣的假設遭到了推翻。滾石樂團堪稱世上最激烈的硬式搖滾樂團,前幾年卻反其道而行,甚至在〈淚水流逝〉(As Tears Go By)等曲目中使用了小提琴。范海倫樂團還是新起之秀時,便做了一件讓樂迷驚訝不已的事:他們把奇想樂團(The Kinks)一首不那麼時髦的老歌〈迷上了妳〉改編成重金屬搖滾版本。對節奏的預期更是經常遭到顛覆。電子藍調中的標準手法是讓樂團先醞釀情緒後中止演奏,留下歌手或主奏吉他手繼續唱奏,這種手法可見於史提夫.雷.范(Stevie Ray Vaughan)的歌曲〈驕傲與快樂〉(Pride and Joy)、貓王的〈獵犬〉(Hound Dog),或者歐曼兄弟樂團(Allman Brothers)的〈別無他路〉(One Way Out)。電子藍調歌曲典型的結尾也是一例,曲子以穩定的拍子進行二至三分鐘,然後??重重一擊!當和弦暗示著樂曲即將結束,樂團卻開始用原先的一半速度演奏。還有雙重打擊。清水樂團在〈看好我的後門〉(Lookin Out My Back Door)的結尾逐漸放慢速度(這在當時已是常見手法),然後顛覆我們的預期,拉回原本的速度演奏真正的結尾。
警察合唱團也以顛覆節奏預期而聞名。搖滾樂標準的節奏模式是強拍落在第一和第三拍(即低音鼓的落點),小鼓則敲在第二和第四拍(反拍)。雷鬼音樂聽來速度彷彿只有搖滾樂的一半(巴布.馬利的音樂是最明顯的例子),因為低音鼓和小鼓在樂句中的敲擊次數只有搖滾樂的一半。雷鬼音樂的基本拍子是吉他彈在「上拍」(或稱弱拍),也就是說,吉他彈在主要拍子之間的空檔,例如:1 AND-A 2 AND 3 AND-A 4 AND 。這種「只有一半速度」的感覺,使得雷鬼音樂表現出慵懶的特質,然而弱拍則傳遞一種動感,將音樂往前推進。警察樂團結合雷鬼音樂與搖滾樂,創造出一種新曲風,既顛覆也滿足我們對節奏的某些預期。主唱史汀經常以嶄新的方式彈奏貝斯,避開搖滾樂總是彈在強拍或與低音鼓同拍的慣用手法。正如頂尖錄音室貝斯手蘭迪.傑克森(Randy Jackson)所告訴我的(我們曾於一九八○年代共用錄音室的辦公室),史汀的貝斯聲線與眾不同,甚至無法用於任何其他人的歌曲中。警察樂團的專輯《機器裡的幽靈》(Ghost in the Machine)中一首〈物質世界裡的幽魂〉(Spirits in the Material World),便將其獨特的節奏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聽者幾乎無法分辨曲中的強拍落在何處。
荀白克等現代音樂作曲家同樣將預期拋諸腦後。他們所用的音階完全剝除我們對和弦中的解決與根音以及音樂的「家」(home)的概念,製造出沒有家的錯覺,產生一種漂流無依的音樂,也許這正是二十世紀存在主義式的隱喻(又或許只是想標新立異)。如今我們仍可在電影配樂聽到這類音階,用來搭配夢境一般的場景,襯托劇中人漂浮無依、潛入水中或身處太空失重狀態的情境。
第五章 我們如何分類音樂? 你知道我的名字, 自己去查號碼吧
我對音樂最早的記憶來自三歲時,我的母親彈著家中的平台式鋼琴,我則躺在鋼琴下一塊毛茸茸的綠色羊毛地毯上。平台式鋼琴就在我頭上,只見母親的腿不斷上下踩著踏板,我彷彿被鋼琴的聲音淹沒。琴音充塞四面八方,那振動穿透地板和我的身體,我感覺低音就在身體右方,高音則在左方。貝多芬的和弦響亮而緊密;蕭邦的音符如雜耍般舞動,如風雪吹拂;舒曼的節奏嚴整如行軍,他和母親同樣是德國人──這一切構成我對音樂最早的記憶,那聲音令我完全入迷,將我帶往未曾體驗的感官世界。當音樂持續演奏,時間彷彿靜止。
音樂的記憶與其他記憶有何不同?為何音樂似乎能觸動深藏心底或已然流逝的回憶?音樂的預期如何使我們體驗音樂中的情感?我們又是如何認出以往聽過的歌曲?辨認曲調牽涉不少複雜的神經運算,並且與記憶息息相關。當我們專注於樂曲中多次演奏都未曾改變的特徵時,大腦則須忽略其他某些特徵,如此才能擷取出歌曲中不變的特質。也就是說,大腦的運算系統必須將歌曲的各個部分獨立開來,留下每次聆聽經驗中相同的部分,剔除每次都有所變化的部分,或某次的獨特詮釋。如果大腦不這麼做,只要一首歌以不同音量播放,你就會以為自己聽到的是一首全新的歌!而音量並非唯一即使大幅度改變也不影響我們辨識歌曲的參數。演奏用的樂器、速度和音高也都不影響歌曲的辨識基準。也就是說,在擷取能夠辨識歌曲的特徵時,這類特徵即使有任何變化,我們也都不予理會。
辨識歌曲大幅增加了神經系統處理音樂的複雜性。從各種變化中擷取歌曲不變的特徵,可說是件浩大的運算工程。一九九○年代末期,我曾在一家網路公司工作,該公司正在發展辨識MP3 檔案的軟體。很多人的電腦都存有聲音檔,但那些檔案往往不是檔名錯誤,就是根本沒有檔名。沒有人願意逐一檢查所有檔案、修正像「Etlon John」這樣的拼字錯誤,或者把艾維斯.卡斯提洛(Elvis Costello)的〈我是認真的〉(My Aim Is True)更名為〈艾莉森〉(Alison,「我是認真的」是副歌中一句歌詞,而非歌名)。
自動命名的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因為每首歌都有數位指紋,我們只須學會如何在包含五十萬首歌曲的資料庫中有效率地搜尋,以正確地指認歌曲。電腦科學家稱之為「查找表」(lookup table)。當你查詢社會安全號碼資料庫時,輸入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資料庫應該只會顯示一組社會安全號碼。同樣地,查詢歌曲資料庫時,輸入某首歌的某個特定版本之數位值,應該只會得到一
首相應的歌曲。查找程式看似運作得完美無瑕,但還是有其限制,它無法找出資料庫中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假設我的硬碟內存有八種版本的〈沙人〉(Mr. Sandman),當我輸入吉他大師查特.亞金斯(Chet Atkins)的演奏,並要求程式依此找出電吉他手吉姆.坎皮隆戈(Jim Campilongo),或和聲女音四重唱(The Chordettes)演唱的版本時,電腦就無法做到了。這是因為MP3 檔案開頭的數值串需經過轉譯才會成為旋律、節奏或響度等要素,而我們還不知道如何進行轉譯。查找程式必須能夠辨識相對不變的旋律與節奏,並忽略因不同表演而生的差異,才可能建立版本的連結。以目前的電腦設備,連起步都有困難,而人腦卻能輕鬆地做到這點。
電腦和人腦在這方面有不同的能力,正與我們對人類記憶的本質與功能所進行的討論有關。近來針對音樂記憶所做的實驗,恰好為釐清真相提供了確切的線索。過去一百多年來,記憶理論學者激烈地爭辯著:人與動物的記憶是相對的,抑或絕對的?主張相對的學派認為,我們的記憶系統儲存的是事物與想法之間的關係,無需記住事物本身的細節。這派論點也稱為構成主義觀點,意指即使缺乏感知細節,我們依然能根據感知之間的關係,立即自行填補或重建細節,建構對現實的記憶表徵。構成主義者認為記憶的功能是忽略不相關的細節,只保留「要點」。與之相對的是「紀錄保存理論」(record-keeping theory),其擁護者認為記憶就像錄音機或數位錄影機,精確記錄我們的全數或多數體驗,並以近乎完美的水準忠實再現。音樂也是論辯主題之一,因為如同一百多年前的完形心理學家所言,旋律是由音高之間的關係所決定(這是構成主義觀點),卻也由確切的音高所組成(這是紀錄保存觀點,但前提是音高會儲存在記憶裡)。兩派論點都累積了大量的證據。持構成主義觀點的實驗研究者請受試者聆聽講詞(聽覺記憶)或閱讀文章(視覺記憶),然後說出他們聽到或讀到些什麼。一般來說,人們不太能逐字重述內容,他們能記住大意,但記不住特定的用詞。
許多研究也指出記憶具有可塑性。小小的干擾也可能會對記憶提取造成重大影響。華盛頓大學的伊莉莎白.羅夫塔斯(Elizabeth F. Loftus)做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她對法庭上證人講述證詞的精確度非常感興趣。羅夫塔斯讓受試者觀看錄影帶,然後針對影片內容提出誘導式的提問。當錄影帶中兩輛汽車幾乎發生擦撞時,她會問一組受試者:「兩車發生擦撞時,雙方車速多少?」
然後問另一組受試者:「兩車猛烈撞擊時,雙方車速多少?」結果光是用詞上的差異,就讓兩組受試者估計的車速相差十萬八千里。接著,羅夫塔斯會在一段時間之後(有時長達一星期之久),再次邀請受試者來到實驗室,然後問他們:「你看見幾片玻璃破裂?」(事實上沒有任何玻璃破裂。)當時接收到「猛烈撞擊」字眼的受試者,有較高比例的人「記得」影片中有玻璃破裂。這群受試者其實是根據一週前的提問,重新建構了自己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