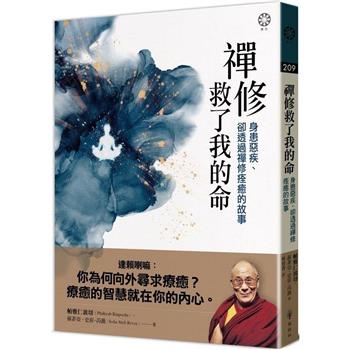7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我寫信給達賴喇嘛
二○○三年十一月,醫生給我的最後通牒已然迫在眉睫。時序已進入秋天,在紐約市的貝爾維尤醫院接受了六個月的治療之後,我的病況愈來愈糟。壞疽仍繼續化膿,不斷粉碎我的右腳踝骨。最新的X光報告顯示,踝骨已完全被摧毀,病症更開始侵蝕脛骨底部。抗生素治療無法限制其進程:既無法阻止胸膜炎、也無法抑制骨結核病。在這種情況下,遵循醫生的建議並接受截肢,是更合情合理的做法;然而,我內心的聲音仍繼續警告我,我必須拒絕截肢手術。
肢體的傷殘當然會使人失能,但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問題。切掉我部分的腿,也意味著摧毀了精微神經系統對應的肉體支撐部位,其後,這將會是我練習內在能量瑜伽時的障礙;因為在進階階段時,這項練習要求生命力得以在完整的身體中循環。即便是在死亡的過程中,盡可能保持經絡與脈輪的完整性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心識會經由九大脈輪門戶其中一門――包括位於囟門上通往梵天之門,以及上方與下方的孔竅,離開我們的肉體。但是,唯有位於頭頂的頂輪是一道「白」門,其餘的門都是「黑」門;因為,後者是通往低等生存境界的重生之門。為了成功地將人的心識從頭頂射出,命氣的能量必須保持在正確軌道上並且不能被堵塞住。由此可見,保持完整的能量精微體及與其相互關聯的身體,是多麼地重要。
由於我心中充滿了類似的問題,瑪麗娜出於好意地提供了我一個建議:她告訴我,羅伯特.瑟曼兩天後要前往達蘭薩拉;瑪麗娜告訴過他關於我的事,如果我有意願的話,他同意幫我傳達訊息給達賴喇嘛,我可以向他說明我的情況,並懇求他建議我該做什麼樣的決定。
達賴喇嘛是我今生與生生世世的庇護源頭。每天早晨當我醒來時,我會觀想他就在我的頭頂上方,散發出慈愛的光環照亮我的一天;到了傍晚,我會祈請他降臨到我心輪之中的蓮花杯上,然後我會闔上圍繞這道神聖之光的蓮花花瓣,讓它從我的內心照亮我。我日夜都為世間慈悲之佛的化身達賴喇嘛誦念祈願文,他在我內心的存在,已經幫助我度過在監獄中最痛苦的時刻,並支持如今在貝爾維尤醫院承受磨難的我。想到能夠把這個決定留給他,我感到平靜而寬慰。
儘管我急切地想寫信給昆敦,但這封信必須符合嚴格的禮節。為了這封非常特別的信,我求助於佩瑪多傑。透過廷禮的傳達,這名僧人已經在紐約市的藏族社區中聽說過我,而當他來看我時,我總是很高興;他會幫我做美味的素食饃饃,一種西藏的蒸餃,並帶給我糌粑跟犛牛奶酪。我不僅感謝他帶給我這些菜餚,它們為醫院尋常而平淡的伙食添加了變化,而且他令人快活又溫暖熱情的陪伴,對我來說更是一大安慰。此時此刻,他是我在紐約市遇到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僧人,他的故事彷彿是所有流亡海外藏人的故事縮影:經由各種慘痛事件的失落、分離、對摯愛之人的哀悼,標記了兩個世代的西藏人。
佩瑪多傑比我年長十歲左右,出生在世界屋脊阿里地區的高草原上,西藏西部沿著拉達克邊界的一個遊牧家庭,他的父母擁有大群的犛牛、馬、羊;每年,他的父親納剛格都會帶一小隊有篷卡車前往尼泊爾,以產於鹹水湖岸的鹽、黃油、緊密編織的犛牛毛等物資來交換米、玉米、小米、辣椒以及紙張。佩瑪對他的出生地有著美好的回憶,那是一個岩石會祈禱的壯麗所在,由「冰雪的珍寶」康仁波切(Khang Rinpoche)――西藏對吉羅娑山的暱稱――守護著。他回想起瑪那薩羅瓦湖(Lake Manasarovar),宛如迷人的鏡子,映照著轉瞬即逝的雲彩行經鈷藍色的天空;這座湖被暱稱為瑪旁雍錯(Mapham Tso),意思是「無敵者」,據說它在這片神聖水域中蒐集了全知心智的無限力量,並以其戰勝了幻相。
佩瑪一家人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威脅,不得不在一九六○年離開這處廣袤無垠的仙境,並將他們的牲畜託付給一位年長的阿姨跟她的兒子來照顧;然而在逃亡途中,他們還是遭到中國巡邏兵的攔截。佩瑪的父親與兩個叔叔都被送進監牢,而只有他的父親從這場慘絕人寰的牢獄之災中倖存下來。被釋放出來一年之後,他與家人團聚,但他的家人們則跟其他的游牧民族一起被集中在可憎的監獄中,生活條件極糟,食物與衛生狀況也慘不忍睹,他的父母在一週內相繼死亡;佩瑪的母親臨終時,要他答應將以平等的善意與慈悲來對待眾生。她臨終的願望就是希望佩瑪可以不惜任何代價地去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在達賴喇嘛的教導下接受佛法教育並成為一名僧人。一九七五年,佩瑪二十二歲,他申請進入乃瓊寺,也就是西藏流亡於達蘭薩拉的國家神諭處總部;之後,一九九四年,他來到紐約市尋求庇護。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乃瓊基金會的祕書以及專為紐約與紐澤西藏族社區設立的週日學校校長。
佩瑪多傑跟我一見如故,不僅因為我們都是僧侶,更是因為我們藉由艱困經歷淬鍊出來的韌性而深有共鳴;不像其他糾結於仇恨與憤怒情感的西藏人,我們對中國的兄弟姐妹們深感同情。但我們之間的情誼尚不止於此,因為我們的關係還可以回溯至我們的前世。
在我所有轉世化身的經歷中,帕雅仁波切與乃瓊護法(Nechung Oracle)的命運曾經在不尋常的情況下交會。乃瓊住持也是達賴喇嘛的私人護法,亦擔任著西藏流亡政府的副部長職務;身為密宗法教傳播的護法,他被視為一名吹忠(ku-ten),也就是神靈的人形化身,在出神狀態下可以接收訊息與預言。「就像我會徵詢幕僚的建議或是捫心自問我的良心,我也會尋求神諭的忠告。」達賴喇嘛曾經如此承認。
我的前世,也就是第七世的帕雅仁波切,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剛好來到拉薩;當時三十三歲的他,正好前來這座神聖的城市朝聖,遇上第十三世的達賴喇嘛在哲蚌寺傳授灌頂。於是,他也在七千多名僧侶中毫不張揚地默然坐下,身著雲遊四海的瑜伽士法衣,看起來跟其他僧侶沒有兩樣,但乃瓊護法一眼就認出了他,來到他面前向他禮敬並獻供,稱呼他為日巴帕津巴(Rigpa Zinpa),亦即「心的明光持有者」。乃瓊護法邀請仁波切跟隨他,並陪同仁波切來到台前,請他坐在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腳下。
八○年之後,二○○三年的初冬,遠離西藏的我在紐約市的醫院裡,而一位來自乃瓊寺的僧人來到了我的病床邊。只是這一次,是為了撰寫要傳達給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訊息;業力巧妙安排著時空,用看不見的絲線織成了我們所謂的命運。
我很高興看到佩瑪多傑出現在我的病房門口。他不高但肩膀寬闊,有著高聳顴骨的三角形臉龐總是因他對眾生的慈愛而顯得容光煥發、平靜沉著。他在美國還是維持著僧人的身分,但只有在宗教法會與社區慶典時會穿上他的袈裟;白天,他在建築工地辛勤地工作,所以他寧可穿著平民的便服。而我的選擇則跟他不同,我仍然穿著我的袈裟,儘管廷禮從我抵達之後便一直要求我將袈裟留在櫥櫃裡;拄著枴杖走路的確不容易,我的袈裟只會更礙事,我得非常小心才不會絆倒。同時,穿著這樣的衣服會讓人們更注意我;而當我們經過人群,人們全都轉頭看我時,廷禮感到極為尷尬。
但是,袈裟對我的意義遠非平常的簡單服飾;我在剃度受戒時接受了我的袈裟,它象徵了為眾生奉獻我的生命。穿上這套服裝,我宛如披上了佛陀的祝福,讓佛陀的愛散發、照耀在他人身上。在醫院,儘管護士大力讚揚醫院的病服穿起來舒適多了,我每天早上還是把我的深紅色袈裟穿在藏紅色襯衫外頭。
但就算佩瑪多傑看起來不像僧人,他也體現了僧人平靜、十足謙卑、喜悅的特質。我昨晚打電話給他,他今天下午就來看我,因為今天星期一是他的休假日。我們一起準備我寫信給達賴喇嘛的措辭用語,並用足以表達虔敬之情的既定公式寫給他:「慈悲聖尊」(Holy Compassionate Lord)、「妙樂」(Gentle Glory)、「如意寶珠」(Wish-Fulfilling Jewel)以及「寶勝者」(Precious Conqueror)。首先,佩瑪多傑抄下一份虔誠的祈禱文,以佛經華麗的詞藻風格來致敬並讚揚昆敦的不凡了悟:
嗡梭地!諸佛菩薩之化現,一切智愛功德力,具足圓滿相顯現。
慈悲化身蓮華手,手持白蓮觀自在,幻化藏紅袈裟相。人間之至尊導師,世間之和平使者,雪域眾生救護主,大能之最勝尊者。丹增嘉措,吾等謹以滿懷虔敬之情獻供予您的身語意!
正等覺佛淨土現,苦難世間自示現,施出離與了悟智,學究能者如浩海,傳承佛經與密續,頂禮供養白蓮尊。
三界眾生齊熱望,祈願親炙尊者容,祈願聆聽尊者言,光照大地遍四方,世間最勝無倫比。
接著,我們簡單而直接地敘述了我的問題。首先,我們回溯了一九九四年時,昆敦正式認證我為第八世的帕雅仁波切,阿什寺的法座持有者。去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帶著他的祝福啟程前往美國;抵達之後,我的右腳就被診斷出罹患了無法治癒的壞疽;我該接受右腿膝蓋以下的截肢,還是我該尋求其他的治療方法?
待我們打好草稿又反覆閱讀了好幾次,寫得一手好書法的佩瑪多傑便將信件內容以金色墨水寫在淺綠色的美麗有機紙上,那是他為了這類場合而特別購買的紙張,最後我再附上我的簽名。當瑪麗娜下午來取信時,信封也已經準備好了。瑪麗娜會親自拿給羅伯特.瑟曼,而他第二天早上即將啟程飛往達蘭薩拉。
達賴喇嘛很迅速地回覆了。五天之後,十一月十六日,瑪麗娜接到羅伯特.瑟曼打來的電話,然後她打給我;當她傳達給我達賴喇嘛回覆的訊息時,我的心怦怦地跳,因為剛好這時,曼哈頓正下著一場雷聲轟隆的大雷雨,我得請她重覆說好幾次才聽得清楚,每個字都宛如銘刻在我的記憶中,令我永誌不忘。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昆敦問我,「療癒的智慧就在你的內心,一旦痊癒了,你會教導這個世界如何療癒。」
這項訊息以二十五個藏文寫成,這二十五個字決定了我的命運。
訊息還有些其他的指示,包括了有幫助的練習建議、適當的觀想以及誦念的咒語。
病由心生
昆敦並未叫我拒絕截肢,他只是試煉我、質疑我。事實上這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反覆思考這個問題。我來到美國,深信美國先進的醫療體系必能輕易地治好像我這樣的人――正當壯年、被高原簡樸而健康的生活方式鍛鍊得身強力壯的人。掌握了這麼多驚人技術的西方文化,怎麼可能不知道如何治療我腳踝的病症?我花了好幾個月才了解,事實並非如此。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當我內心的聲音第一次告訴我別接受截肢,我的確聽從了它的話,因為我拒絕了醫生們不斷催促我接受的手術療程;但是,我並未深入思考這件事的原因;我並未努力去了解這個聲音從何而來,也並未深究它要對我揭示什麼。我會如此處理,正是因為我原本期望能從自身以外得到療癒,一種適時而幸運的療癒。我把希望都放在西方科學上。
如今,我承認我罹患的病狀已非現有治療方式可以治癒。從醫學觀點來看,我的病是不治之症;此外,我的醫療照護者也已經放棄了對我的希望。打從一開始,他們就不斷重覆地告訴我,我的腳踝已然壞死,我等得愈久,我的腿也會跟著壞死;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我的結果就只有死路一條。從外在與生理層面來分析我的病症正是如此,更別說X光片、組織分析、血液檢測也都支持並確認了這項結論。大勢已定,我宛如被頒布了死刑的執行令。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達賴喇嘛在詢問我這個問題時,也同時提醒了我,如果醫院無法治療我的壞疽,並不代表它就是不治之症。它不是致命的,而是可以被治療、甚至可以痊癒的――透過另一種治療方法,而不僅是肉體上的治療。昆敦敦促我去意識到,我的疾病真正的本質為何。
佩瑪多傑告訴我,一位來自尊勝寺(昆敦的私人僧院)的年輕僧人遭遇的悲劇。他的名字也叫佩瑪,他是達賴喇嘛最喜愛的藝術家,聰明絕倫且才華洋溢,可以說寫流利的英文。他在紐約市進修,受教於羅伯特.瑟曼並被授予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後來,他突然出了嚴重的健康問題,肺部長了一個腫瘤;除了諮詢西方的醫生,他也諮詢了西藏的醫生,而後者是建議他不要開刀。他們診斷出來的病因並非身體的問題,而是由水神那伽(naga)引起的;在達蘭薩拉達賴喇嘛的住所,佩瑪曾經參與過將寺廟獻給水神作為祭祀之用的法會,或許他在未察覺的情況下,冒犯到這些極為易怒的神靈;這些神靈如今因環境汙染及森林砍伐而遭受強烈痛苦,因為水道與林木正是其棲居之所。
佩瑪無疑對美國的醫療體系信心滿滿,就跟我剛到貝爾維尤醫院時一樣。醫生懷疑他罹患了肺癌,催促他接受手術治療;於是,腫瘤被切除了,之後的切片檢查顯示這個腫瘤是良性的,但是傷害已然造成。為了移除這些纖維組織,醫生不得不切掉一段氣管;因此,佩瑪總共進行了五次的侵入性手術,並取出一段腸子來重建氣管。最後,他死於這些手術的併發症。
佩瑪離世之前,羅伯特.瑟曼曾到加護病房看望他;就在他離開人世的前一晚,他帶著堪為典範的靈魂力量,一如往常地愉快說笑。他要鮑伯為他保留獎學金,說他下次轉世時會用得上,屆時他將回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寫他的博士論文!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就像佩瑪,我的病因也可能是來自內在;當時,西藏的醫生懇勸佩瑪不要動手術,而是進行閉關禪修並念誦特定咒語。當人們受到那伽影響時,對應到能量層面是水元素的不平衡,對應到身體層面則是痰黏液的不平衡。多虧了安撫勸解的法會,自然的和諧才得以重建並恢復。
在西藏時,我經常舉行獻給水神那伽的法會,因為河神以及整個自然界的神靈,都深受中國人對環境的剝削濫用之苦。後來,羅伯特.瑟曼也邀請我每年到訪門拉山,那是位於紐約卡茲奇山地區的一處佛法靜修所,以便為棲居於該地區的偉大水神舉行法會。達賴喇嘛在某一次的拜訪中,曾經為這裡的水神加持,我也將得窺這位神靈;有一天,水神將會把碩大無比的頭探進我的窗框之中,然後在瞬息之間消失無蹤。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我寫信給達賴喇嘛
二○○三年十一月,醫生給我的最後通牒已然迫在眉睫。時序已進入秋天,在紐約市的貝爾維尤醫院接受了六個月的治療之後,我的病況愈來愈糟。壞疽仍繼續化膿,不斷粉碎我的右腳踝骨。最新的X光報告顯示,踝骨已完全被摧毀,病症更開始侵蝕脛骨底部。抗生素治療無法限制其進程:既無法阻止胸膜炎、也無法抑制骨結核病。在這種情況下,遵循醫生的建議並接受截肢,是更合情合理的做法;然而,我內心的聲音仍繼續警告我,我必須拒絕截肢手術。
肢體的傷殘當然會使人失能,但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問題。切掉我部分的腿,也意味著摧毀了精微神經系統對應的肉體支撐部位,其後,這將會是我練習內在能量瑜伽時的障礙;因為在進階階段時,這項練習要求生命力得以在完整的身體中循環。即便是在死亡的過程中,盡可能保持經絡與脈輪的完整性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心識會經由九大脈輪門戶其中一門――包括位於囟門上通往梵天之門,以及上方與下方的孔竅,離開我們的肉體。但是,唯有位於頭頂的頂輪是一道「白」門,其餘的門都是「黑」門;因為,後者是通往低等生存境界的重生之門。為了成功地將人的心識從頭頂射出,命氣的能量必須保持在正確軌道上並且不能被堵塞住。由此可見,保持完整的能量精微體及與其相互關聯的身體,是多麼地重要。
由於我心中充滿了類似的問題,瑪麗娜出於好意地提供了我一個建議:她告訴我,羅伯特.瑟曼兩天後要前往達蘭薩拉;瑪麗娜告訴過他關於我的事,如果我有意願的話,他同意幫我傳達訊息給達賴喇嘛,我可以向他說明我的情況,並懇求他建議我該做什麼樣的決定。
達賴喇嘛是我今生與生生世世的庇護源頭。每天早晨當我醒來時,我會觀想他就在我的頭頂上方,散發出慈愛的光環照亮我的一天;到了傍晚,我會祈請他降臨到我心輪之中的蓮花杯上,然後我會闔上圍繞這道神聖之光的蓮花花瓣,讓它從我的內心照亮我。我日夜都為世間慈悲之佛的化身達賴喇嘛誦念祈願文,他在我內心的存在,已經幫助我度過在監獄中最痛苦的時刻,並支持如今在貝爾維尤醫院承受磨難的我。想到能夠把這個決定留給他,我感到平靜而寬慰。
儘管我急切地想寫信給昆敦,但這封信必須符合嚴格的禮節。為了這封非常特別的信,我求助於佩瑪多傑。透過廷禮的傳達,這名僧人已經在紐約市的藏族社區中聽說過我,而當他來看我時,我總是很高興;他會幫我做美味的素食饃饃,一種西藏的蒸餃,並帶給我糌粑跟犛牛奶酪。我不僅感謝他帶給我這些菜餚,它們為醫院尋常而平淡的伙食添加了變化,而且他令人快活又溫暖熱情的陪伴,對我來說更是一大安慰。此時此刻,他是我在紐約市遇到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僧人,他的故事彷彿是所有流亡海外藏人的故事縮影:經由各種慘痛事件的失落、分離、對摯愛之人的哀悼,標記了兩個世代的西藏人。
佩瑪多傑比我年長十歲左右,出生在世界屋脊阿里地區的高草原上,西藏西部沿著拉達克邊界的一個遊牧家庭,他的父母擁有大群的犛牛、馬、羊;每年,他的父親納剛格都會帶一小隊有篷卡車前往尼泊爾,以產於鹹水湖岸的鹽、黃油、緊密編織的犛牛毛等物資來交換米、玉米、小米、辣椒以及紙張。佩瑪對他的出生地有著美好的回憶,那是一個岩石會祈禱的壯麗所在,由「冰雪的珍寶」康仁波切(Khang Rinpoche)――西藏對吉羅娑山的暱稱――守護著。他回想起瑪那薩羅瓦湖(Lake Manasarovar),宛如迷人的鏡子,映照著轉瞬即逝的雲彩行經鈷藍色的天空;這座湖被暱稱為瑪旁雍錯(Mapham Tso),意思是「無敵者」,據說它在這片神聖水域中蒐集了全知心智的無限力量,並以其戰勝了幻相。
佩瑪一家人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威脅,不得不在一九六○年離開這處廣袤無垠的仙境,並將他們的牲畜託付給一位年長的阿姨跟她的兒子來照顧;然而在逃亡途中,他們還是遭到中國巡邏兵的攔截。佩瑪的父親與兩個叔叔都被送進監牢,而只有他的父親從這場慘絕人寰的牢獄之災中倖存下來。被釋放出來一年之後,他與家人團聚,但他的家人們則跟其他的游牧民族一起被集中在可憎的監獄中,生活條件極糟,食物與衛生狀況也慘不忍睹,他的父母在一週內相繼死亡;佩瑪的母親臨終時,要他答應將以平等的善意與慈悲來對待眾生。她臨終的願望就是希望佩瑪可以不惜任何代價地去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在達賴喇嘛的教導下接受佛法教育並成為一名僧人。一九七五年,佩瑪二十二歲,他申請進入乃瓊寺,也就是西藏流亡於達蘭薩拉的國家神諭處總部;之後,一九九四年,他來到紐約市尋求庇護。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乃瓊基金會的祕書以及專為紐約與紐澤西藏族社區設立的週日學校校長。
佩瑪多傑跟我一見如故,不僅因為我們都是僧侶,更是因為我們藉由艱困經歷淬鍊出來的韌性而深有共鳴;不像其他糾結於仇恨與憤怒情感的西藏人,我們對中國的兄弟姐妹們深感同情。但我們之間的情誼尚不止於此,因為我們的關係還可以回溯至我們的前世。
在我所有轉世化身的經歷中,帕雅仁波切與乃瓊護法(Nechung Oracle)的命運曾經在不尋常的情況下交會。乃瓊住持也是達賴喇嘛的私人護法,亦擔任著西藏流亡政府的副部長職務;身為密宗法教傳播的護法,他被視為一名吹忠(ku-ten),也就是神靈的人形化身,在出神狀態下可以接收訊息與預言。「就像我會徵詢幕僚的建議或是捫心自問我的良心,我也會尋求神諭的忠告。」達賴喇嘛曾經如此承認。
我的前世,也就是第七世的帕雅仁波切,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剛好來到拉薩;當時三十三歲的他,正好前來這座神聖的城市朝聖,遇上第十三世的達賴喇嘛在哲蚌寺傳授灌頂。於是,他也在七千多名僧侶中毫不張揚地默然坐下,身著雲遊四海的瑜伽士法衣,看起來跟其他僧侶沒有兩樣,但乃瓊護法一眼就認出了他,來到他面前向他禮敬並獻供,稱呼他為日巴帕津巴(Rigpa Zinpa),亦即「心的明光持有者」。乃瓊護法邀請仁波切跟隨他,並陪同仁波切來到台前,請他坐在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腳下。
八○年之後,二○○三年的初冬,遠離西藏的我在紐約市的醫院裡,而一位來自乃瓊寺的僧人來到了我的病床邊。只是這一次,是為了撰寫要傳達給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訊息;業力巧妙安排著時空,用看不見的絲線織成了我們所謂的命運。
我很高興看到佩瑪多傑出現在我的病房門口。他不高但肩膀寬闊,有著高聳顴骨的三角形臉龐總是因他對眾生的慈愛而顯得容光煥發、平靜沉著。他在美國還是維持著僧人的身分,但只有在宗教法會與社區慶典時會穿上他的袈裟;白天,他在建築工地辛勤地工作,所以他寧可穿著平民的便服。而我的選擇則跟他不同,我仍然穿著我的袈裟,儘管廷禮從我抵達之後便一直要求我將袈裟留在櫥櫃裡;拄著枴杖走路的確不容易,我的袈裟只會更礙事,我得非常小心才不會絆倒。同時,穿著這樣的衣服會讓人們更注意我;而當我們經過人群,人們全都轉頭看我時,廷禮感到極為尷尬。
但是,袈裟對我的意義遠非平常的簡單服飾;我在剃度受戒時接受了我的袈裟,它象徵了為眾生奉獻我的生命。穿上這套服裝,我宛如披上了佛陀的祝福,讓佛陀的愛散發、照耀在他人身上。在醫院,儘管護士大力讚揚醫院的病服穿起來舒適多了,我每天早上還是把我的深紅色袈裟穿在藏紅色襯衫外頭。
但就算佩瑪多傑看起來不像僧人,他也體現了僧人平靜、十足謙卑、喜悅的特質。我昨晚打電話給他,他今天下午就來看我,因為今天星期一是他的休假日。我們一起準備我寫信給達賴喇嘛的措辭用語,並用足以表達虔敬之情的既定公式寫給他:「慈悲聖尊」(Holy Compassionate Lord)、「妙樂」(Gentle Glory)、「如意寶珠」(Wish-Fulfilling Jewel)以及「寶勝者」(Precious Conqueror)。首先,佩瑪多傑抄下一份虔誠的祈禱文,以佛經華麗的詞藻風格來致敬並讚揚昆敦的不凡了悟:
嗡梭地!諸佛菩薩之化現,一切智愛功德力,具足圓滿相顯現。
慈悲化身蓮華手,手持白蓮觀自在,幻化藏紅袈裟相。人間之至尊導師,世間之和平使者,雪域眾生救護主,大能之最勝尊者。丹增嘉措,吾等謹以滿懷虔敬之情獻供予您的身語意!
正等覺佛淨土現,苦難世間自示現,施出離與了悟智,學究能者如浩海,傳承佛經與密續,頂禮供養白蓮尊。
三界眾生齊熱望,祈願親炙尊者容,祈願聆聽尊者言,光照大地遍四方,世間最勝無倫比。
接著,我們簡單而直接地敘述了我的問題。首先,我們回溯了一九九四年時,昆敦正式認證我為第八世的帕雅仁波切,阿什寺的法座持有者。去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帶著他的祝福啟程前往美國;抵達之後,我的右腳就被診斷出罹患了無法治癒的壞疽;我該接受右腿膝蓋以下的截肢,還是我該尋求其他的治療方法?
待我們打好草稿又反覆閱讀了好幾次,寫得一手好書法的佩瑪多傑便將信件內容以金色墨水寫在淺綠色的美麗有機紙上,那是他為了這類場合而特別購買的紙張,最後我再附上我的簽名。當瑪麗娜下午來取信時,信封也已經準備好了。瑪麗娜會親自拿給羅伯特.瑟曼,而他第二天早上即將啟程飛往達蘭薩拉。
達賴喇嘛很迅速地回覆了。五天之後,十一月十六日,瑪麗娜接到羅伯特.瑟曼打來的電話,然後她打給我;當她傳達給我達賴喇嘛回覆的訊息時,我的心怦怦地跳,因為剛好這時,曼哈頓正下著一場雷聲轟隆的大雷雨,我得請她重覆說好幾次才聽得清楚,每個字都宛如銘刻在我的記憶中,令我永誌不忘。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昆敦問我,「療癒的智慧就在你的內心,一旦痊癒了,你會教導這個世界如何療癒。」
這項訊息以二十五個藏文寫成,這二十五個字決定了我的命運。
訊息還有些其他的指示,包括了有幫助的練習建議、適當的觀想以及誦念的咒語。
病由心生
昆敦並未叫我拒絕截肢,他只是試煉我、質疑我。事實上這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反覆思考這個問題。我來到美國,深信美國先進的醫療體系必能輕易地治好像我這樣的人――正當壯年、被高原簡樸而健康的生活方式鍛鍊得身強力壯的人。掌握了這麼多驚人技術的西方文化,怎麼可能不知道如何治療我腳踝的病症?我花了好幾個月才了解,事實並非如此。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當我內心的聲音第一次告訴我別接受截肢,我的確聽從了它的話,因為我拒絕了醫生們不斷催促我接受的手術療程;但是,我並未深入思考這件事的原因;我並未努力去了解這個聲音從何而來,也並未深究它要對我揭示什麼。我會如此處理,正是因為我原本期望能從自身以外得到療癒,一種適時而幸運的療癒。我把希望都放在西方科學上。
如今,我承認我罹患的病狀已非現有治療方式可以治癒。從醫學觀點來看,我的病是不治之症;此外,我的醫療照護者也已經放棄了對我的希望。打從一開始,他們就不斷重覆地告訴我,我的腳踝已然壞死,我等得愈久,我的腿也會跟著壞死;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我的結果就只有死路一條。從外在與生理層面來分析我的病症正是如此,更別說X光片、組織分析、血液檢測也都支持並確認了這項結論。大勢已定,我宛如被頒布了死刑的執行令。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達賴喇嘛在詢問我這個問題時,也同時提醒了我,如果醫院無法治療我的壞疽,並不代表它就是不治之症。它不是致命的,而是可以被治療、甚至可以痊癒的――透過另一種治療方法,而不僅是肉體上的治療。昆敦敦促我去意識到,我的疾病真正的本質為何。
佩瑪多傑告訴我,一位來自尊勝寺(昆敦的私人僧院)的年輕僧人遭遇的悲劇。他的名字也叫佩瑪,他是達賴喇嘛最喜愛的藝術家,聰明絕倫且才華洋溢,可以說寫流利的英文。他在紐約市進修,受教於羅伯特.瑟曼並被授予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後來,他突然出了嚴重的健康問題,肺部長了一個腫瘤;除了諮詢西方的醫生,他也諮詢了西藏的醫生,而後者是建議他不要開刀。他們診斷出來的病因並非身體的問題,而是由水神那伽(naga)引起的;在達蘭薩拉達賴喇嘛的住所,佩瑪曾經參與過將寺廟獻給水神作為祭祀之用的法會,或許他在未察覺的情況下,冒犯到這些極為易怒的神靈;這些神靈如今因環境汙染及森林砍伐而遭受強烈痛苦,因為水道與林木正是其棲居之所。
佩瑪無疑對美國的醫療體系信心滿滿,就跟我剛到貝爾維尤醫院時一樣。醫生懷疑他罹患了肺癌,催促他接受手術治療;於是,腫瘤被切除了,之後的切片檢查顯示這個腫瘤是良性的,但是傷害已然造成。為了移除這些纖維組織,醫生不得不切掉一段氣管;因此,佩瑪總共進行了五次的侵入性手術,並取出一段腸子來重建氣管。最後,他死於這些手術的併發症。
佩瑪離世之前,羅伯特.瑟曼曾到加護病房看望他;就在他離開人世的前一晚,他帶著堪為典範的靈魂力量,一如往常地愉快說笑。他要鮑伯為他保留獎學金,說他下次轉世時會用得上,屆時他將回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寫他的博士論文!
「你為何向自身以外尋求療癒?」
就像佩瑪,我的病因也可能是來自內在;當時,西藏的醫生懇勸佩瑪不要動手術,而是進行閉關禪修並念誦特定咒語。當人們受到那伽影響時,對應到能量層面是水元素的不平衡,對應到身體層面則是痰黏液的不平衡。多虧了安撫勸解的法會,自然的和諧才得以重建並恢復。
在西藏時,我經常舉行獻給水神那伽的法會,因為河神以及整個自然界的神靈,都深受中國人對環境的剝削濫用之苦。後來,羅伯特.瑟曼也邀請我每年到訪門拉山,那是位於紐約卡茲奇山地區的一處佛法靜修所,以便為棲居於該地區的偉大水神舉行法會。達賴喇嘛在某一次的拜訪中,曾經為這裡的水神加持,我也將得窺這位神靈;有一天,水神將會把碩大無比的頭探進我的窗框之中,然後在瞬息之間消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