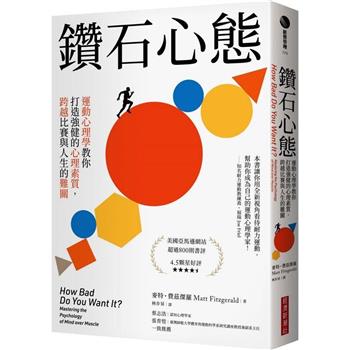前言
我的人生首次耐力賽是在新罕布夏州鄧恩(Durham)牡蠣河小學(Oyster River Elementary School)田徑場上跑了兩圈。那場比賽是運動會(Field Day)活動的眾多比賽項目之一,堪稱小學生的畢業典禮。我像大多數十一歲孩子那樣,曾參加過當地社區許多比賽,但先前都是短跑。除非有成年人的督導,否則孩子不會參加長跑比賽。在那場運動會後,我才明白真正的原因。
當時我們這群孩子都搞不清楚狀況,離開起跑線就全速奔跑起來。跑了六七十公尺左右,我雙腿出現類似得了流感般的無力感。每跨出一步,我的體重就好像增加了半公斤,食道像浸泡在鹽水中的開放式傷口般灼痛,頭皮出現一陣陣刺痛,意識成了一團微弱的火焰,在不祥的風中飄搖。我腦海中剩下的少數念頭既零碎又驚慌:「我的身體到底怎麼了?」「這樣正常嗎?」「其他小朋友也這麼難受嗎?」
我跑完了第一圈,不顧內心想要放棄的強大誘惑,開始跑第二圈。有名男生還跑在我前面,他是傑夫.伯頓(Jeff Burton),班上唯一和我一樣瘦的同學。我明白自己當時的處境:更拼命地追上傑夫,但代價是身體承受更大的痛苦;或是把痛苦設下停損點,讓傑夫贏得勝利。但第三個選項出現了:傑夫後繼無力。我看到他愈跑愈慢,接近最後一個彎道時便超越了他,接著衝過終點線贏得勝利,不過當下累癱了,只能在心裡默默慶祝。
從那次經驗中,我領悟了耐力運動的一大真相。雖然我的雙腿和肺讓我勝券在握,但其實真正把我推向頂峰的是我的心智—特別是我對於全新感受所帶來衝擊的吸收能力,以及我願意為了贏得勝利吃點苦頭。我明白,長跑比賽最關鍵的關卡存乎一心。
運動會上獲勝的三年後,我因為踢足球弄傷了左膝。幫我縫合傷口的外科醫師建議我從事其他運動。受傷前,我本來就兼差擔任牡蠣河中學田徑隊的一英里(約一點六公里)跑者,表現得算是可圈可點。因此,我決定把全副心力投注於跑步。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膝關節重建手術後康復與復建的過程仍不大先進。手術後,我整條腿打了六個星期的石膏,然後又穿了六個月的護具。於是,我高中時期室內田徑第一個賽季中,都無法擺脫與克維拉合成纖維(Kevlar)和魔鬼氈的累贅。隔年春天拆掉護具時,我覺得重獲新生。在室外賽季,我七度參加一英里賽跑,其中六次締造了個人最佳成績。
秋天,我帶領越野校隊奪下新罕布夏州三大校際體育賽事之一的州冠軍。一星期後,我在「冠軍爭霸賽」(Meet of Champions)上獲得了個人獎項第十名,該決賽由三項賽事中名列前茅的隊伍和個人一較高下。我在高二賽跑組別中排名第二、高一組別中排名第一。畢業前,我很有希望成為新罕布夏州最厲害的高中跑步選手。
但這個目標終究沒有實現。第一個失敗跡象,是在我在分區越野州錦標賽中取得重大突破的那一刻。那場比賽在曼徹斯特的德里菲爾公園(Derryfield Park)舉行,堪稱全美最困難的高中越野跑道,起點是一條滑雪坡道底部,得一路往上跑到坡頂再下來。我登頂時位居第二,僅落後尚恩.利文斯頓(Sean Livingston)這名完全屬於另一個次元的天才型高三生。我當時沒有多想,直到我們跑出樹林,女友一看到我就朝著站她旁邊的人大喊:「噢天哪!他第二耶!」我這才發覺自己超猛。
但僅僅數秒後,我就被來自史蒂文斯學院同樣就讀高二的勁敵塔德.蓋爾(Todd Geil)超越了。在山腳下,他還在我前方十到十五公尺;但最後得克服一段高難度上彎,跑道才會再度平坦直通終點。我比塔德更擅長跑上坡(當初也是這樣才領先他),便開始急起直追。
我們同時跑過最後一個彎道。塔德踮起腳尖加速,我也一樣,此刻耳畔傳來雙方父母、教練和隊友高分貝的加油聲,我們倆幾乎是齊步衝向終點線。
然後我就放棄了,直接投降,不想跑了。萌生此念頭的當下,塔德又把速度拉高一個檔次,進行最後一搏。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能否跟上他的速度、能否把速度再提升一點,因為我甚至連試都沒試。原因很簡單:太痛了。我內心有一部分好像在問:「你有多想贏?」另一部分則回答:「再想贏也比不過那傢伙。」我覺得塔德並非比我更有天賦或更有體力—實際上,接下來在我們高中生涯的五次冠軍越野賽跑中,我兩度都跑贏他。但那天我們倆的差別在於,他願意跑得更賣力。
十一歲時,我首次體驗到耐力賽伴隨的痛苦,內心遭受的衝擊自此揮之不去。我熱愛跑步,也愛培養更強健的體魂、更敏捷的身手,但我討厭比賽時必須承擔的痛苦。剛開始接觸跑步時,我對於這項運動潛藏的黑暗面雖然排斥,但還算應付得來,內心抱持的期待也不高。但我達到選手的水準後,才發現居然比以往更痛苦,而為了奪冠還得忍受更多痛苦。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過去雖然也很痛苦,但仍待在相對的舒適圈中,自以為拿出超越「百分之百」的表現就所向披靡。
但那並不是我的選擇;我反而成了被心魔所困的典型例子。每到比賽當天,我就會遭到無盡的恐懼感折磨。我的胃部不斷翻騰、心臟劇烈跳動,滿腦子都是即將面臨的痛苦。假如比賽是在星期二,我整天上課就會呈現恍神狀況,聽不到老師說什麼;假如是在星期六,我只能勉強吃下蜂蜜堅果口味的喜瑞爾麥片,然後出門與隊友會合,一起搭巴士前往賽場任人宰割。
大三時,我開始對比賽敷衍了事,假裝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其實內心明白只有百分之九十五。我跑步展現的認真程度不多不少,沒有人知道我在打混。即使如此,我仍然偶爾有成績亮眼的時刻,像是在一九八七年冠軍爭霸賽中獲得第六名,但我更常跑完步後感到自我厭惡,深知自己並沒有全力以赴。
這樣的狀況愈來愈糟。有次在波士頓的戶外田徑賽中,我參加兩英里(約三點二公里)的項目,結果才跑到一半便假裝腳踝扭傷,倒在地上故作痛苦地扭著身體。數星期後,我又假裝沒聽到另一場兩英里賽事起跑線就位的廣播,所有參賽者起跑後獨缺我一人。我的高三越野賽季結束後(我最後在冠軍爭霸賽中表現極差,僅排名第十七,勁敵塔德.蓋爾則奪下第二名),我放棄跑步了,輸給內心的懦弱。
一九九五年,我已從大學畢業兩年,仍然認為自己與跑步無緣,於是搬到舊金山。我的目標是接下一份像樣的文字工作。結果,最後的工作機會來自比爾.卡托夫斯基(Bill Katovsky),他在一九八三年創辦了《鐵人三項運動員》(Triathlete)雜誌,當時正準備推出全新的耐力運動雜誌《多項運動》(Multisport)。我當然大可接受《嗨翻時代》(High Times;按:提倡大麻合法化而惡名昭彰的雜誌)的工作邀約,但命運使然,我日後所處的工作環境充滿了熱愛健身、追求體魄與速度的選手。
該來的躲不掉。我再度受到訓練和比賽的召喚,起初只是當跑者,後來更成為鐵人三項選手,簡直愈陷愈深。我愈來愈投入這類嗜好,也愈來愈有雄心壯志。兩大內在動機相輔相成,促使我後半輩子又回鍋當耐力運動員。最重要的理由是,我想成為當初本來有機會可能成為的運動員。但我明白假如想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得克服第一次導致我放棄的內心弱點;我想要徹底剷除心魔。
我從未真正成為自己理想中的運動員。事實證明,我真正的弱點是不聽話的脆弱身體,只要我說出「足底筋膜炎」這個詞,跑起步來就會跛腳(這個弱點在我小時候就有跡可尋,包括十四歲時左膝關節斷裂)。但就算我當不了理想中的運動員,至少能拖著有缺陷的身體盡力做到最好。我終於克服了心魔。
假如我在分區越野錦標賽衝刺階段讓塔德.蓋爾超前那一刻,代表了我喪失身為運動員的誠信,那二○○八年矽谷馬拉松其中一刻則象徵了我的救贖。我在距離終點線大約三英里(約四點八公里)時,我萬分痛苦地經過一對站在路邊的年輕情侶,他們可能在等朋友經過。我超過他們十來步時,聽到那名女子脫口而出:「哇!」
這聲驚呼的背後也許能用不同方式來解讀:也許那位小姐很佩服我跑得很快,但那場馬拉松比賽的第一名(我最後獲得第三名)比我早四分鐘通過,所以想必不是如此;說不定她是在欣賞我漂亮的跑姿,但我並沒有漂亮的跑姿,當時步伐看起來很可能糟到不能再糟。
其實,我認為那名說出「哇!」的女子,是被我「悽慘」的模樣,以及無比吃力的動作所嚇到。在她眼中,我想必像是困在及腰的水中艱難地跋涉。我也確實覺得如此辛苦,一定還張著嘴流口水。那位陌生人的語助詞是在敬佩我的努力,肯定我寧願承受折磨、也要達成在特定時間內完賽這項毫無意義的目標。
但在那場馬拉松上,我並沒有實現個人時間目標,因為先前再度負傷,訓練時間只得縮短,導致我無法達標。可是我獲得更了不起的成就感:我知道自己這次在比賽時真的拼盡全力了。
二○○八年矽谷馬拉松的第二十三英里(第三十七公里),至今仍是我身為運動員最珍貴的時刻。不僅如此,我還認為這是這輩子數一數二美妙的時刻。當然,這只是一場比賽,但運動與生活並非互不相干,運動員的身分與個人也是一體兩面。我克服了對於比賽中遭逢痛苦的恐懼,因而更加敬佩自己,內在的力量協助我迎接其他難關,而且是運動場內或場外皆然。
我的人生首次耐力賽是在新罕布夏州鄧恩(Durham)牡蠣河小學(Oyster River Elementary School)田徑場上跑了兩圈。那場比賽是運動會(Field Day)活動的眾多比賽項目之一,堪稱小學生的畢業典禮。我像大多數十一歲孩子那樣,曾參加過當地社區許多比賽,但先前都是短跑。除非有成年人的督導,否則孩子不會參加長跑比賽。在那場運動會後,我才明白真正的原因。
當時我們這群孩子都搞不清楚狀況,離開起跑線就全速奔跑起來。跑了六七十公尺左右,我雙腿出現類似得了流感般的無力感。每跨出一步,我的體重就好像增加了半公斤,食道像浸泡在鹽水中的開放式傷口般灼痛,頭皮出現一陣陣刺痛,意識成了一團微弱的火焰,在不祥的風中飄搖。我腦海中剩下的少數念頭既零碎又驚慌:「我的身體到底怎麼了?」「這樣正常嗎?」「其他小朋友也這麼難受嗎?」
我跑完了第一圈,不顧內心想要放棄的強大誘惑,開始跑第二圈。有名男生還跑在我前面,他是傑夫.伯頓(Jeff Burton),班上唯一和我一樣瘦的同學。我明白自己當時的處境:更拼命地追上傑夫,但代價是身體承受更大的痛苦;或是把痛苦設下停損點,讓傑夫贏得勝利。但第三個選項出現了:傑夫後繼無力。我看到他愈跑愈慢,接近最後一個彎道時便超越了他,接著衝過終點線贏得勝利,不過當下累癱了,只能在心裡默默慶祝。
從那次經驗中,我領悟了耐力運動的一大真相。雖然我的雙腿和肺讓我勝券在握,但其實真正把我推向頂峰的是我的心智—特別是我對於全新感受所帶來衝擊的吸收能力,以及我願意為了贏得勝利吃點苦頭。我明白,長跑比賽最關鍵的關卡存乎一心。
運動會上獲勝的三年後,我因為踢足球弄傷了左膝。幫我縫合傷口的外科醫師建議我從事其他運動。受傷前,我本來就兼差擔任牡蠣河中學田徑隊的一英里(約一點六公里)跑者,表現得算是可圈可點。因此,我決定把全副心力投注於跑步。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膝關節重建手術後康復與復建的過程仍不大先進。手術後,我整條腿打了六個星期的石膏,然後又穿了六個月的護具。於是,我高中時期室內田徑第一個賽季中,都無法擺脫與克維拉合成纖維(Kevlar)和魔鬼氈的累贅。隔年春天拆掉護具時,我覺得重獲新生。在室外賽季,我七度參加一英里賽跑,其中六次締造了個人最佳成績。
秋天,我帶領越野校隊奪下新罕布夏州三大校際體育賽事之一的州冠軍。一星期後,我在「冠軍爭霸賽」(Meet of Champions)上獲得了個人獎項第十名,該決賽由三項賽事中名列前茅的隊伍和個人一較高下。我在高二賽跑組別中排名第二、高一組別中排名第一。畢業前,我很有希望成為新罕布夏州最厲害的高中跑步選手。
但這個目標終究沒有實現。第一個失敗跡象,是在我在分區越野州錦標賽中取得重大突破的那一刻。那場比賽在曼徹斯特的德里菲爾公園(Derryfield Park)舉行,堪稱全美最困難的高中越野跑道,起點是一條滑雪坡道底部,得一路往上跑到坡頂再下來。我登頂時位居第二,僅落後尚恩.利文斯頓(Sean Livingston)這名完全屬於另一個次元的天才型高三生。我當時沒有多想,直到我們跑出樹林,女友一看到我就朝著站她旁邊的人大喊:「噢天哪!他第二耶!」我這才發覺自己超猛。
但僅僅數秒後,我就被來自史蒂文斯學院同樣就讀高二的勁敵塔德.蓋爾(Todd Geil)超越了。在山腳下,他還在我前方十到十五公尺;但最後得克服一段高難度上彎,跑道才會再度平坦直通終點。我比塔德更擅長跑上坡(當初也是這樣才領先他),便開始急起直追。
我們同時跑過最後一個彎道。塔德踮起腳尖加速,我也一樣,此刻耳畔傳來雙方父母、教練和隊友高分貝的加油聲,我們倆幾乎是齊步衝向終點線。
然後我就放棄了,直接投降,不想跑了。萌生此念頭的當下,塔德又把速度拉高一個檔次,進行最後一搏。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能否跟上他的速度、能否把速度再提升一點,因為我甚至連試都沒試。原因很簡單:太痛了。我內心有一部分好像在問:「你有多想贏?」另一部分則回答:「再想贏也比不過那傢伙。」我覺得塔德並非比我更有天賦或更有體力—實際上,接下來在我們高中生涯的五次冠軍越野賽跑中,我兩度都跑贏他。但那天我們倆的差別在於,他願意跑得更賣力。
十一歲時,我首次體驗到耐力賽伴隨的痛苦,內心遭受的衝擊自此揮之不去。我熱愛跑步,也愛培養更強健的體魂、更敏捷的身手,但我討厭比賽時必須承擔的痛苦。剛開始接觸跑步時,我對於這項運動潛藏的黑暗面雖然排斥,但還算應付得來,內心抱持的期待也不高。但我達到選手的水準後,才發現居然比以往更痛苦,而為了奪冠還得忍受更多痛苦。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過去雖然也很痛苦,但仍待在相對的舒適圈中,自以為拿出超越「百分之百」的表現就所向披靡。
但那並不是我的選擇;我反而成了被心魔所困的典型例子。每到比賽當天,我就會遭到無盡的恐懼感折磨。我的胃部不斷翻騰、心臟劇烈跳動,滿腦子都是即將面臨的痛苦。假如比賽是在星期二,我整天上課就會呈現恍神狀況,聽不到老師說什麼;假如是在星期六,我只能勉強吃下蜂蜜堅果口味的喜瑞爾麥片,然後出門與隊友會合,一起搭巴士前往賽場任人宰割。
大三時,我開始對比賽敷衍了事,假裝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其實內心明白只有百分之九十五。我跑步展現的認真程度不多不少,沒有人知道我在打混。即使如此,我仍然偶爾有成績亮眼的時刻,像是在一九八七年冠軍爭霸賽中獲得第六名,但我更常跑完步後感到自我厭惡,深知自己並沒有全力以赴。
這樣的狀況愈來愈糟。有次在波士頓的戶外田徑賽中,我參加兩英里(約三點二公里)的項目,結果才跑到一半便假裝腳踝扭傷,倒在地上故作痛苦地扭著身體。數星期後,我又假裝沒聽到另一場兩英里賽事起跑線就位的廣播,所有參賽者起跑後獨缺我一人。我的高三越野賽季結束後(我最後在冠軍爭霸賽中表現極差,僅排名第十七,勁敵塔德.蓋爾則奪下第二名),我放棄跑步了,輸給內心的懦弱。
一九九五年,我已從大學畢業兩年,仍然認為自己與跑步無緣,於是搬到舊金山。我的目標是接下一份像樣的文字工作。結果,最後的工作機會來自比爾.卡托夫斯基(Bill Katovsky),他在一九八三年創辦了《鐵人三項運動員》(Triathlete)雜誌,當時正準備推出全新的耐力運動雜誌《多項運動》(Multisport)。我當然大可接受《嗨翻時代》(High Times;按:提倡大麻合法化而惡名昭彰的雜誌)的工作邀約,但命運使然,我日後所處的工作環境充滿了熱愛健身、追求體魄與速度的選手。
該來的躲不掉。我再度受到訓練和比賽的召喚,起初只是當跑者,後來更成為鐵人三項選手,簡直愈陷愈深。我愈來愈投入這類嗜好,也愈來愈有雄心壯志。兩大內在動機相輔相成,促使我後半輩子又回鍋當耐力運動員。最重要的理由是,我想成為當初本來有機會可能成為的運動員。但我明白假如想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得克服第一次導致我放棄的內心弱點;我想要徹底剷除心魔。
我從未真正成為自己理想中的運動員。事實證明,我真正的弱點是不聽話的脆弱身體,只要我說出「足底筋膜炎」這個詞,跑起步來就會跛腳(這個弱點在我小時候就有跡可尋,包括十四歲時左膝關節斷裂)。但就算我當不了理想中的運動員,至少能拖著有缺陷的身體盡力做到最好。我終於克服了心魔。
假如我在分區越野錦標賽衝刺階段讓塔德.蓋爾超前那一刻,代表了我喪失身為運動員的誠信,那二○○八年矽谷馬拉松其中一刻則象徵了我的救贖。我在距離終點線大約三英里(約四點八公里)時,我萬分痛苦地經過一對站在路邊的年輕情侶,他們可能在等朋友經過。我超過他們十來步時,聽到那名女子脫口而出:「哇!」
這聲驚呼的背後也許能用不同方式來解讀:也許那位小姐很佩服我跑得很快,但那場馬拉松比賽的第一名(我最後獲得第三名)比我早四分鐘通過,所以想必不是如此;說不定她是在欣賞我漂亮的跑姿,但我並沒有漂亮的跑姿,當時步伐看起來很可能糟到不能再糟。
其實,我認為那名說出「哇!」的女子,是被我「悽慘」的模樣,以及無比吃力的動作所嚇到。在她眼中,我想必像是困在及腰的水中艱難地跋涉。我也確實覺得如此辛苦,一定還張著嘴流口水。那位陌生人的語助詞是在敬佩我的努力,肯定我寧願承受折磨、也要達成在特定時間內完賽這項毫無意義的目標。
但在那場馬拉松上,我並沒有實現個人時間目標,因為先前再度負傷,訓練時間只得縮短,導致我無法達標。可是我獲得更了不起的成就感:我知道自己這次在比賽時真的拼盡全力了。
二○○八年矽谷馬拉松的第二十三英里(第三十七公里),至今仍是我身為運動員最珍貴的時刻。不僅如此,我還認為這是這輩子數一數二美妙的時刻。當然,這只是一場比賽,但運動與生活並非互不相干,運動員的身分與個人也是一體兩面。我克服了對於比賽中遭逢痛苦的恐懼,因而更加敬佩自己,內在的力量協助我迎接其他難關,而且是運動場內或場外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