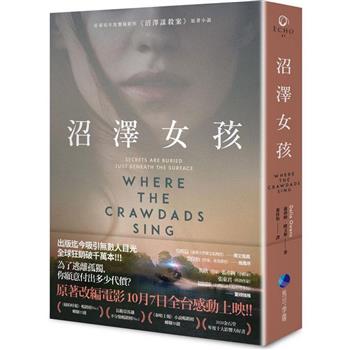第一部
溼地
序曲
一九六九年
溼地不是沼澤。溼地是光的所在,這裡的草長在水中,水波彷彿直接流入天際。溪水緩慢而閒散地流動,將圓圓的太陽送入海中,長腳鳥以出乎意料的優雅飛升而起――彷彿並不是生來就要飛翔――背後則是數千隻雪雁的躁鳴。
而在溼地中,時不時能看到真正的沼澤棲居於低窪的泥塘地,隱身在空氣潮黏的樹林內。沼澤內的水停滯、陰暗,所有光線都被沼澤的泥濘喉嚨吞嚥進去。就連夜間爬行的大蚯蚓在這帶都是白天出沒。這裡當然有聲響,但跟溼地相比顯得安靜,因為所有分解工作都在細胞層次上進行。生命在此腐朽、發臭,最後還原為一堆腐爛物質;這是一個死亡逐漸重拾生命力的刺鼻泥坑。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早上,柴斯.安德魯的屍體躺在沼澤地裡,沼澤本來打算安靜、公事公辦地將屍體分解吸收,永遠將其深藏於此地。沼澤對死亡瞭若指掌,不一定將其定義為悲劇,也絕不認為是罪惡。不過這天早上,兩個村裡的男孩騎腳踏車到這座老舊的防火觀察塔,然後在第三個大急轉路口時,瞄見了他穿的牛仔外套。
第一章
媽
一九五二年
這個早晨灼燒如同八月烈日,溼地的吐納潮溼,為橡樹及松樹掛上霧氣。棕櫚樹林地異常安靜,只能聽見蒼鷺從潟湖起飛時,以低沉、緩慢的節奏拍打著翅膀。當時只有六歲的奇雅聽見紗門砰一聲闔上。她站在小凳子上,停止把鍋上玉米碎粒刷掉的動作,把鍋子放進水槽內已無法再用來洗滌的肥皂沫中。周遭一片安靜,只有她的呼吸聲。是誰離開棚屋了?不會是媽。她從不會任由門這般隨便甩上。
不過奇雅跑向門廊時,看見的正是穿著棕色長裙的母親,她腳踏著高跟鞋走在沙土小路上,裙襬開衩的褶邊在腳踝處甩動。那雙鈍頭鞋是假鱷魚皮做的,也是她唯一一雙外出鞋。奇雅想大喊,但知道不該驚動爸,所以打開門,站在寬闊的磚造樓梯上。她可以從這裡看見媽帶著藍色化妝箱。奇雅總是有種幼獸般的直覺,知道母親會帶包在棕油紙內的雞肉回來,雞頭還會掛在那兒晃呀晃的。不過之前她出門從不會穿這雙鱷魚高跟鞋,也不會帶行李箱。
媽總會在小路連接大馬路那裡回望,單手舉高,一邊揮舞著白白的手掌,一邊轉向走上大馬路,那條路會穿過好幾片泥塘上的林地、長了香蒲的潟湖,又或者如果潮汐剛好幫忙,人還能一路走到鎮上。但今天她只是一股勁往前走,腳步因為車子留下的胎溝而顛簸。她高高的身影時不時從樹林間的孔隙透出,最後只剩白色圍巾自葉間閃現。奇雅立刻往另一頭衝刺,她知道從那裡可以清楚看到大馬路;媽一定會在那裡跟她揮手,但她趕到時,只來得及瞥見那只藍色行李箱一晃而逝──那顏色跟樹林完全不搭。她感覺到一種黑棉土泥般的沉重感壓上胸口,只能回到階梯口等待。
奇雅是五個孩子中最小的,其他人都比她大上很多,不過後來她老是想不起他們幾歲。他們跟媽、爸一起住,像被圈養的小兔子般擠在那種做工很粗的棚屋內;裝了紗窗的前廊彷彿兩隻眼睛,從橡樹下張大往外猛瞪。
喬帝是跟奇雅年紀最相近的哥哥,但仍大她七歲,他從屋內走出來,站在她身後。他的眼睛顏色跟她一樣深,頭髮也一樣黝黑;他之前教過她不同鳥鳴的曲調、星星的名字,以及在芒草間駕船的方法。
「媽會回來的,」他說。
「我不知道。她穿著鱷魚鞋。」
「當媽的不會丟下孩子。她們就是不會。」
「你之前說狐狸會丟下她的寶寶。」
「是沒錯,但那隻母狐狸的腿都被扯爛了。如果她想餵飽自己又餵飽小孩,最後一定會餓死。她只好先離開,把自己治好,等有辦法養小孩時再生上一窩。媽又沒挨餓,她會回來的。」喬帝的口氣聽起來根本沒那麼篤定,但還是對奇雅這麼說。
奇雅感覺喉嚨緊縮,悄聲說:「但媽提著那只藍色行李箱,好像要去某個很特別的地方。」
*
棚屋就位於棕櫚樹後方,那叢棕櫚樹長在一片沙地上,樹叢蔓延到項鍊般的一連串綠色潟湖邊,再蔓延向遠處溼地。這些綿延數哩的草葉非常堅韌,長在鹹水裡也沒問題,時不時打斷這片棕櫚樹叢的是一些被風吹彎的樹木。橡木林群聚在棚屋另一側,共同為最近的潟湖遮蔭;湖面因為生命旺盛而翻湧滾動。鹹鹹的空氣和海鷗的歌聲從海邊穿林而來。
這裡取得土地的方式打從十六世紀以來就沒什麼改變。散落各處的溼地歸屬不是透過法律詞彙來描述,而是由一群社會叛逃者隨意的插旗掠地──以這條小溪為界,在那棵死橡樹旁。正常人不會在泥塘內挨著棕櫚樹搭建小屋,除非他正在逃亡,或者人生旅程即將走向終結。
溼地被一條崎嶇破碎的海岸線守衛著,這條海岸線浪極大、風很猛,船常擱在淺灘後如同紙糊的一樣被扯碎,因此曾被早期探險家貼上「大西洋墓園」的標籤。這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知道的北卡羅來納海岸。曾有名海員的日記這麼寫道:「在海岸漫遊……但看不出任何入口……有場激烈的暴風籠罩我們……我們被迫跳下海,想保住我們的性命和船,卻被快速的強力海流推送……
「這片地都是溼地和沼澤,我們回到自己船上……那些之後決定定居在此的人們,一定會深受這類令人沮喪的事物侵擾。」
想找片像樣土地的人離開了,這片惡名昭彰的溼地成為一張網,撈捕到一大堆有的沒的傢伙,包括叛變的水手、社會邊緣人、負債者,以及那些躲避討厭的戰爭、稅金或法律制裁的逃犯。靠著生養孩子,這些沒被瘧疾殺死或沒被沼澤吞沒的人發展出一個林中部落,其中包含了許多種族的人及各種文化,不過每個人都能靠一把手斧砍倒一小座森林,或者背一頭雄鹿走上好幾哩。他們就像河鼠,每隻都有自己的領域,但必須想辦法適應林地的極端環境,不然總有一天會在沼澤中消失。兩百年後,這些人當中又出現了逃亡黑奴,這些逃進溼地的人被統稱為「逃奴」,另外還有被解放的奴隸。這些人身無分文,坐困愁城,因為沒什麼選擇可言,只好在這片水流漫溢的土地上四散求生。
這或許是一片環境惡劣的鄉間,但絕沒有一吋地是貧瘠的。這片土地上層層疊疊堆滿生命,包括彎曲的沙蟹、在泥中歪倒前行的淡水螯蝦、水禽、魚、蝦、蠔、油脂豐厚的鹿,以及肥嘟嘟的鵝。如果是個不在意晚餐湊合著吃的人,在這裡絕不會挨餓。
現在是一九五二年,四個世紀以來,陸續有人將部分取得土地的過程斷續記錄下來,但其中許多人沒留下紀錄。這一切大多發生在南北戰爭之前。其他人則是最近才開始占據土地,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案例尤其多,因為許多男人在從戰場回來後破產或沒了另一半。溼地不是他們的牢籠,反而定義了他們的存在,而且就像任何聖地一樣嚴守著他們的祕密。沒人在意他們占了這些地,因為也沒其他人想要。畢竟,這裡就是一片荒涼的泥塘。
就像私釀酒一樣,這些住在溼地的人也私自制定他們的法律──不是用火燒在石板上或抄寫在文件上的法律,而是銘刻於基因內的更深層的法則。這些法則既古老又自然,就像直接由老鷹和鴿子推論出來的通則:當你被逼到無路可退、絕望或孤軍奮戰時,人就會回歸本能,完全只以存活為目標。這樣的改變迅速、有效又正當。這些規則永遠是這類人的最後王牌,因為比起相對溫和的基因,這類基因遺傳給下一代的頻率更高。這不是一種道德判斷,而是單純的數學問題。畢竟在這些人之中,鴿派必須奮戰的頻率都跟鷹派一樣高。
*
媽那天沒回來。沒人提起這件事。爸更是不置一詞。身上散發魚腥味及劣質烈酒臭氣的他只是敲敲鍋蓋,「晚餐吃什麼?」
兄弟姊妹們垂下雙眼,聳聳肩。爸大罵了一串髒話,跛著腳走出屋外,返回樹林。他們之前也吵過架,媽也離家出走過一、兩次,但總是會回來,然後把需要擁抱的孩子一把抱進懷中。
兩個年紀比較大的姊姊煮了腰豆和玉米麵包,但沒人跟媽在時一樣坐在桌前吃。大家各自從鍋中舀了一些豆子,把玉米麵包堆上去,隨意晃回鋪在地板上的床墊,或者就在褪色的沙發上吃。
奇雅吃不下。她坐在門廊的階梯上望著小路。她的身材以年紀來說算很高,骨瘦如柴,膚色曬得很深,一頭直髮又黑又粗,就像烏鴉的翅膀。
黑暗讓她無法繼續偵查外頭的動靜。就算有腳步聲也會被青蛙的嘓嘓叫聲淹沒;即便如此,她還是躺在門廊的床上仔細聆聽。那天早上,她起床時聽到豬背肉在鑄鐵煎鍋內劈啪作響,還有比司吉在木柴爐中逐漸烤熟的香氣。她穿起連身工裝褲,跑去廚房擺好盤子跟叉子,挑出玉米堆裡的象鼻蟲。大多數清晨,媽會滿臉微笑地抱住她――「早安呀,我獨一無二的小女孩」――然後兩人彷彿跳舞般忙著各種家務事。有時媽會唱民謠歌曲,或者來個兩句童謠:「這隻小豬去了市場。」又或者她會拉著奇雅大跳吉特巴舞,她們的腳敲擊著合板地面,直到收音機逐漸沒電,聲音聽起來就像從酒桶底部發出的悶響。又有些早上,媽會跟她說一些大人的事,奇雅聽不懂,但她想媽需要有人聽她說,所以在把更多柴火插入烤爐時透過皮膚吸收了一切,還彷彿理解的不停點頭。
接著就是要忙亂地把大家叫醒後餵飽。爸不在場。他只有兩種模式:徹底安靜或大聲咆哮。所以最好他就是直接睡過頭,或者乾脆別回家正好。
不過今天早上,媽一直很沉默。她的臉上沒有微笑,雙眼通紅,還像海盜一樣在頭上綁了白色圍巾,幾乎蓋住了整片額頭,但頭巾邊緣還是透出了一些紫黃色的瘀青。才剛吃完早餐,連碗盤都還沒洗,媽就把一些私人物品放進化妝箱,沿著大馬路離去。
*
隔天早上,奇雅又坐在門前的階梯上等,深色雙眼緊緊盯著那條小路,彷彿那是等待火車通過的隧道。遠處的溼地受到霧氣籠罩,低垂的柔軟霧氣底部直接跟泥地貼合。光腳的奇雅扭動腳趾,捲起草莖挑弄著蟻獅,但六歲的孩子畢竟坐不久,很快地,她就溜達到灘地,腳趾從溼沙子中拔出時發出波波的抽吸聲。她蹲在清澈的水邊,望著小小的鰷魚在陽光的光點及陰暗處之間一次又一次短距離地衝刺著。
喬帝從棕櫚樹那邊大吼大叫地跑過來。她瞪著他。說不定他有什麼新消息了。但就在他從尖刺的細長葉片間揮舞手臂跑來時,她從他漫不經心的動作就知道,媽沒有回家。
「要玩探險家嗎?」他問。
「你說你已經長大,不玩探險家了。」
「沒啦,我只是說說而已。才沒有長大就不能玩這回事。來賽跑!」
他們拔腿跑過一片片沼地,穿過樹林後朝海灘跑去。她在他超前自己時大聲尖叫,一路大笑,直到抵達彷彿從沙中探出巨大手臂的那棵大橡樹邊。喬帝和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哥哥小莫在樹上釘了幾片木板當作瞭望塔和樹堡。現在那些木板幾乎全都鬆脫了,只靠著生鏽的釘子垂掛著。
之前就算獲准加入探險家的船員行列,她通常也只能當小女奴,負責從媽媽的平底鍋裡為哥哥們偷偷帶來熱呼呼的比司吉。
但喬帝今天說:「你可以當船長。」
奇雅立刻舉起右手發號施令。「趕走西班牙人!」他們揮斷好幾把樹枝做成的劍、衝破黑莓灌木,對著敵人又吼又砍。
接著――幻想總是來得快,去得也快――她走向一根長滿苔蘚的圓木,坐下。他沉默地跟著坐在一旁。他想說些什麼,好讓她別再想媽的事了,但什麼都想不出來,所以只是望著水黽映照在水面的影子。
之後奇雅又回到屋前階梯,等了好長一段時間,但望向小路盡頭的她始終沒有哭。她的臉上沒有任何波瀾,四處張望的雙眼底下,兩片嘴唇抿成一條細線。但媽那天也沒有回來。
第二章
喬帝
一九五二年
媽離開後,奇雅的大哥和兩個姊姊彷彿因為有了媽的示範,也在接下來幾個星期擺脫這個家。他們早已受夠爸總是臉紅脖子粗的怒氣,他一開始會大吼,接著升級成一輪猛拳,又或者用手背揍他們,於是他們最後一個個都消失了。反正他們也差不多成年了。之後,奇雅不只忘記了他們的年紀,也忘記了他們的真名,只記得大家都叫他們蜜西、小莫,和曼蒂。在她放在門廊的床墊上,奇雅找到一小堆姊姊留下來的襪子。
就在家裡只剩喬帝這個哥哥的早上,奇雅起床時聽到噹啷噹啷的聲響,還有早餐的油香味。她立刻衝進廚房,心想是媽在家炸玉米油條或玉米餅,但卻是喬帝站在柴爐前攪拌玉米粥。她用微笑掩飾自己的失望,他拍拍她的頭,溫和地提醒她保持安靜:若沒有吵醒爸,他們就能自己吃早餐。喬帝不知怎麼烤比司吉,家裡也沒有培根了,所以他煮了玉米粥,還用豬油炒了蛋,接著他們一起坐下,沉默交換著眼神及微笑。
他們吃完後迅速洗了盤子,出門跑向溼地,喬帝在前面帶頭。但爸就在此時大吼起來,腳步蹣跚地追上他們。他瘦到不可思議的身形似乎就要因為缺乏重量而撲通倒下,口中的臼齒就跟老狗的牙齒一樣黃。
奇雅抬眼望向喬帝。「我們可以逃掉。躲在苔蘚很多的那個地方。」
「沒事的。一切都會沒事的,」他說。
*
那天接近日落時,喬帝發現奇雅在沙灘上盯著大海。他站到她身邊,她沒看他,只是繼續盯著翻湧的海浪。根據他說話的方式,她知道爸揍了喬帝的臉。
「我得離開了,奇雅。沒辦法待下去了。」
她幾乎要轉身面對他了,但沒這麼做。她想求他別留自己跟爸相處,但想說的話全堵在喉頭。
「等你夠大之後就會懂了,」他說。奇雅想要大吼:她或許年紀小,但可不笨。她知道爸是所有人離開的原因,她不懂的是為何沒人把她帶走。她也想離開,但無處可去,身上又沒有巴士錢。
「奇雅,你自己小心,聽著,如果有人來,別進屋去。他們會在屋子裡抓住你。跑到溼地深處,躲在灌木叢裡。永遠記得掩蓋自己的足跡,我教過你。你可以躲起來不給爸找到。」她還是沒說話,他說了再見後越過沙灘走向樹林。就在他踏進樹林之前,她才終於轉身,望著他離開。
「這隻小豬留在家裡,」她對著海浪說。
她終於動了起來,跑向棚屋,對著走廊大喊他的名字,但喬帝的東西都不見了,他鋪在地上的床也清空了。
她沉重地坐在他的床墊上,看著最後一絲天光從牆面滑下。太陽落下之後,天光還沒有完全消失,其中有些還匯聚在屋內,所以有那麼短暫的一刻,跟外面的樹木相比,那些凹凸不平的床鋪和一堆堆舊衣的形狀及顏色能被看得更清楚。
她因為磨人的飢餓感嚇了一跳,多麼乏味的感受呀。她走進廚房,站在門邊。這個房間在她有生之年總是因為烤麵包、煮奶油豆子,或燉著滾燙的魚湯而熱烘烘的,但此刻卻顯得汙濁、安靜又陰暗。「誰來煮飯?」她大聲地問。乾脆直接問「誰來跳舞?」算了。
她點亮一根蠟燭,戳了戳爐子裡的熱燙灰燼,又加了些引火柴,擠壓風箱讓火點燃,接著加了更多柴進去。電冰箱被拿來當櫥櫃使用,因為棚屋附近接不到電。為了確保黴菌不會失控擴散,門總是靠一支蒼蠅拍卡著維持敞開,但綠黃色的霉斑還是在每個裂隙中蔓延。
她拿出剩菜,說,「我要把玉米粥倒進豬油裡,再熱一熱,」她確實這麼做了,也吃了鍋裡的粥,然後往窗外看爸有沒有回來,但爸始終沒出現。
就在弦月的光線終於撒在棚屋上時,她爬上放在門廊的床墊――那是一張凹凸不平的床墊,上頭鋪的床單灑滿了小小的藍色玫瑰,是媽在別人家二手出清時買來的真正床單――但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獨自躺在上頭。
剛開始的時候,她每隔幾分鐘就會坐起身,透過紗門往外瞧,也仔細聽著是否有來自樹林的腳步聲。她認得每棵樹的形狀,但仍有些樹似乎一下出現在這裡,一下又出現在那裡,彷彿隨著月光到處移動。她一度身體僵硬到連口水都吞不下去,但熟悉的樹蛙鳴唱和大螽斯的叫聲準時充滿夜色,比「拿著雕刻刀的三隻瞎老鼠」的童話故事還有撫慰效果。夜色中有一種甜香,又熬過一個溼熱白日的青蛙和蠑螈呼出的土味。溼地隨著低矮的霧氣籠罩過來。她睡著了。
*
爸連續三天沒有回來,奇雅從媽的菜園裡採了蕪菁葉後煮來當早餐、午餐和晚餐。她有走去雞舍找蛋,卻發現什麼都沒有。到處都沒有雞或蛋的蹤影。
「雞屎!這裡就只剩一堆雞屎!」她本來打算在媽離開後好好照顧這些雞,但卻幾乎什麼都沒做。而現在這群五顏六色的禽鳥已遠遠逃入樹林。她得到處撒些玉米,看有沒有辦法讓牠們待在棚屋附近。
第四天晚上,爸手上拿著一個酒瓶現身,大字型躺在床上。
隔天早上他走進廚房,大吼:「其他人哪去了?」
「我不知道,」她說話時沒看他。
「你就跟雜種狗一樣什麼都不知道。就跟公豬的奶子一樣沒用。」
奇雅默默地從通往前廊的門溜了出去,沿著沙灘走時眼睛搜尋著貽貝。她聞到煙味,抬頭看到一簇煙霧在棚屋那個方向升起。她用盡全力快跑,衝刺穿越樹林後看到一個火堆在後院熊熊燃燒,爸正往火裡丟媽的畫作、洋裝和書。
「不!」奇雅尖叫。他沒看她,只是把老舊的電池收音機也丟進火裡。她的臉和手臂在她想伸手拿畫時燙傷了,但熱氣逼得她不得不後退。
她衝進棚屋擋住想回屋子裡拿更多物品的爸,雙眼死瞪著他。爸作勢要用手背揍她,但她堅持不退縮。他突然之間決定轉身,跛腳走向自己的船。
奇雅跌坐在磚板階梯上,望著媽的溼地水彩畫悶燒為灰燼。她一直在那裡坐到太陽落下,直到所有衣物的釦子都成為黑得發亮的焦煤,而和媽一起跳吉特巴舞的回憶也消融在火焰中。
接下來幾天,奇雅學會了如何與他一起生活,她從其他人的錯誤中學到教訓,甚至從鰷魚身上學到了更有用的一課:避開他,別讓他見到你,從陽光中竄逃入陰影。在他醒來前先起床、離家。她在樹林及水邊生活,只有晚上才躲回屋內,睡到自己位於門廊的床上,而且盡可能靠近溼地。
溼地
序曲
一九六九年
溼地不是沼澤。溼地是光的所在,這裡的草長在水中,水波彷彿直接流入天際。溪水緩慢而閒散地流動,將圓圓的太陽送入海中,長腳鳥以出乎意料的優雅飛升而起――彷彿並不是生來就要飛翔――背後則是數千隻雪雁的躁鳴。
而在溼地中,時不時能看到真正的沼澤棲居於低窪的泥塘地,隱身在空氣潮黏的樹林內。沼澤內的水停滯、陰暗,所有光線都被沼澤的泥濘喉嚨吞嚥進去。就連夜間爬行的大蚯蚓在這帶都是白天出沒。這裡當然有聲響,但跟溼地相比顯得安靜,因為所有分解工作都在細胞層次上進行。生命在此腐朽、發臭,最後還原為一堆腐爛物質;這是一個死亡逐漸重拾生命力的刺鼻泥坑。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早上,柴斯.安德魯的屍體躺在沼澤地裡,沼澤本來打算安靜、公事公辦地將屍體分解吸收,永遠將其深藏於此地。沼澤對死亡瞭若指掌,不一定將其定義為悲劇,也絕不認為是罪惡。不過這天早上,兩個村裡的男孩騎腳踏車到這座老舊的防火觀察塔,然後在第三個大急轉路口時,瞄見了他穿的牛仔外套。
第一章
媽
一九五二年
這個早晨灼燒如同八月烈日,溼地的吐納潮溼,為橡樹及松樹掛上霧氣。棕櫚樹林地異常安靜,只能聽見蒼鷺從潟湖起飛時,以低沉、緩慢的節奏拍打著翅膀。當時只有六歲的奇雅聽見紗門砰一聲闔上。她站在小凳子上,停止把鍋上玉米碎粒刷掉的動作,把鍋子放進水槽內已無法再用來洗滌的肥皂沫中。周遭一片安靜,只有她的呼吸聲。是誰離開棚屋了?不會是媽。她從不會任由門這般隨便甩上。
不過奇雅跑向門廊時,看見的正是穿著棕色長裙的母親,她腳踏著高跟鞋走在沙土小路上,裙襬開衩的褶邊在腳踝處甩動。那雙鈍頭鞋是假鱷魚皮做的,也是她唯一一雙外出鞋。奇雅想大喊,但知道不該驚動爸,所以打開門,站在寬闊的磚造樓梯上。她可以從這裡看見媽帶著藍色化妝箱。奇雅總是有種幼獸般的直覺,知道母親會帶包在棕油紙內的雞肉回來,雞頭還會掛在那兒晃呀晃的。不過之前她出門從不會穿這雙鱷魚高跟鞋,也不會帶行李箱。
媽總會在小路連接大馬路那裡回望,單手舉高,一邊揮舞著白白的手掌,一邊轉向走上大馬路,那條路會穿過好幾片泥塘上的林地、長了香蒲的潟湖,又或者如果潮汐剛好幫忙,人還能一路走到鎮上。但今天她只是一股勁往前走,腳步因為車子留下的胎溝而顛簸。她高高的身影時不時從樹林間的孔隙透出,最後只剩白色圍巾自葉間閃現。奇雅立刻往另一頭衝刺,她知道從那裡可以清楚看到大馬路;媽一定會在那裡跟她揮手,但她趕到時,只來得及瞥見那只藍色行李箱一晃而逝──那顏色跟樹林完全不搭。她感覺到一種黑棉土泥般的沉重感壓上胸口,只能回到階梯口等待。
奇雅是五個孩子中最小的,其他人都比她大上很多,不過後來她老是想不起他們幾歲。他們跟媽、爸一起住,像被圈養的小兔子般擠在那種做工很粗的棚屋內;裝了紗窗的前廊彷彿兩隻眼睛,從橡樹下張大往外猛瞪。
喬帝是跟奇雅年紀最相近的哥哥,但仍大她七歲,他從屋內走出來,站在她身後。他的眼睛顏色跟她一樣深,頭髮也一樣黝黑;他之前教過她不同鳥鳴的曲調、星星的名字,以及在芒草間駕船的方法。
「媽會回來的,」他說。
「我不知道。她穿著鱷魚鞋。」
「當媽的不會丟下孩子。她們就是不會。」
「你之前說狐狸會丟下她的寶寶。」
「是沒錯,但那隻母狐狸的腿都被扯爛了。如果她想餵飽自己又餵飽小孩,最後一定會餓死。她只好先離開,把自己治好,等有辦法養小孩時再生上一窩。媽又沒挨餓,她會回來的。」喬帝的口氣聽起來根本沒那麼篤定,但還是對奇雅這麼說。
奇雅感覺喉嚨緊縮,悄聲說:「但媽提著那只藍色行李箱,好像要去某個很特別的地方。」
*
棚屋就位於棕櫚樹後方,那叢棕櫚樹長在一片沙地上,樹叢蔓延到項鍊般的一連串綠色潟湖邊,再蔓延向遠處溼地。這些綿延數哩的草葉非常堅韌,長在鹹水裡也沒問題,時不時打斷這片棕櫚樹叢的是一些被風吹彎的樹木。橡木林群聚在棚屋另一側,共同為最近的潟湖遮蔭;湖面因為生命旺盛而翻湧滾動。鹹鹹的空氣和海鷗的歌聲從海邊穿林而來。
這裡取得土地的方式打從十六世紀以來就沒什麼改變。散落各處的溼地歸屬不是透過法律詞彙來描述,而是由一群社會叛逃者隨意的插旗掠地──以這條小溪為界,在那棵死橡樹旁。正常人不會在泥塘內挨著棕櫚樹搭建小屋,除非他正在逃亡,或者人生旅程即將走向終結。
溼地被一條崎嶇破碎的海岸線守衛著,這條海岸線浪極大、風很猛,船常擱在淺灘後如同紙糊的一樣被扯碎,因此曾被早期探險家貼上「大西洋墓園」的標籤。這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知道的北卡羅來納海岸。曾有名海員的日記這麼寫道:「在海岸漫遊……但看不出任何入口……有場激烈的暴風籠罩我們……我們被迫跳下海,想保住我們的性命和船,卻被快速的強力海流推送……
「這片地都是溼地和沼澤,我們回到自己船上……那些之後決定定居在此的人們,一定會深受這類令人沮喪的事物侵擾。」
想找片像樣土地的人離開了,這片惡名昭彰的溼地成為一張網,撈捕到一大堆有的沒的傢伙,包括叛變的水手、社會邊緣人、負債者,以及那些躲避討厭的戰爭、稅金或法律制裁的逃犯。靠著生養孩子,這些沒被瘧疾殺死或沒被沼澤吞沒的人發展出一個林中部落,其中包含了許多種族的人及各種文化,不過每個人都能靠一把手斧砍倒一小座森林,或者背一頭雄鹿走上好幾哩。他們就像河鼠,每隻都有自己的領域,但必須想辦法適應林地的極端環境,不然總有一天會在沼澤中消失。兩百年後,這些人當中又出現了逃亡黑奴,這些逃進溼地的人被統稱為「逃奴」,另外還有被解放的奴隸。這些人身無分文,坐困愁城,因為沒什麼選擇可言,只好在這片水流漫溢的土地上四散求生。
這或許是一片環境惡劣的鄉間,但絕沒有一吋地是貧瘠的。這片土地上層層疊疊堆滿生命,包括彎曲的沙蟹、在泥中歪倒前行的淡水螯蝦、水禽、魚、蝦、蠔、油脂豐厚的鹿,以及肥嘟嘟的鵝。如果是個不在意晚餐湊合著吃的人,在這裡絕不會挨餓。
現在是一九五二年,四個世紀以來,陸續有人將部分取得土地的過程斷續記錄下來,但其中許多人沒留下紀錄。這一切大多發生在南北戰爭之前。其他人則是最近才開始占據土地,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案例尤其多,因為許多男人在從戰場回來後破產或沒了另一半。溼地不是他們的牢籠,反而定義了他們的存在,而且就像任何聖地一樣嚴守著他們的祕密。沒人在意他們占了這些地,因為也沒其他人想要。畢竟,這裡就是一片荒涼的泥塘。
就像私釀酒一樣,這些住在溼地的人也私自制定他們的法律──不是用火燒在石板上或抄寫在文件上的法律,而是銘刻於基因內的更深層的法則。這些法則既古老又自然,就像直接由老鷹和鴿子推論出來的通則:當你被逼到無路可退、絕望或孤軍奮戰時,人就會回歸本能,完全只以存活為目標。這樣的改變迅速、有效又正當。這些規則永遠是這類人的最後王牌,因為比起相對溫和的基因,這類基因遺傳給下一代的頻率更高。這不是一種道德判斷,而是單純的數學問題。畢竟在這些人之中,鴿派必須奮戰的頻率都跟鷹派一樣高。
*
媽那天沒回來。沒人提起這件事。爸更是不置一詞。身上散發魚腥味及劣質烈酒臭氣的他只是敲敲鍋蓋,「晚餐吃什麼?」
兄弟姊妹們垂下雙眼,聳聳肩。爸大罵了一串髒話,跛著腳走出屋外,返回樹林。他們之前也吵過架,媽也離家出走過一、兩次,但總是會回來,然後把需要擁抱的孩子一把抱進懷中。
兩個年紀比較大的姊姊煮了腰豆和玉米麵包,但沒人跟媽在時一樣坐在桌前吃。大家各自從鍋中舀了一些豆子,把玉米麵包堆上去,隨意晃回鋪在地板上的床墊,或者就在褪色的沙發上吃。
奇雅吃不下。她坐在門廊的階梯上望著小路。她的身材以年紀來說算很高,骨瘦如柴,膚色曬得很深,一頭直髮又黑又粗,就像烏鴉的翅膀。
黑暗讓她無法繼續偵查外頭的動靜。就算有腳步聲也會被青蛙的嘓嘓叫聲淹沒;即便如此,她還是躺在門廊的床上仔細聆聽。那天早上,她起床時聽到豬背肉在鑄鐵煎鍋內劈啪作響,還有比司吉在木柴爐中逐漸烤熟的香氣。她穿起連身工裝褲,跑去廚房擺好盤子跟叉子,挑出玉米堆裡的象鼻蟲。大多數清晨,媽會滿臉微笑地抱住她――「早安呀,我獨一無二的小女孩」――然後兩人彷彿跳舞般忙著各種家務事。有時媽會唱民謠歌曲,或者來個兩句童謠:「這隻小豬去了市場。」又或者她會拉著奇雅大跳吉特巴舞,她們的腳敲擊著合板地面,直到收音機逐漸沒電,聲音聽起來就像從酒桶底部發出的悶響。又有些早上,媽會跟她說一些大人的事,奇雅聽不懂,但她想媽需要有人聽她說,所以在把更多柴火插入烤爐時透過皮膚吸收了一切,還彷彿理解的不停點頭。
接著就是要忙亂地把大家叫醒後餵飽。爸不在場。他只有兩種模式:徹底安靜或大聲咆哮。所以最好他就是直接睡過頭,或者乾脆別回家正好。
不過今天早上,媽一直很沉默。她的臉上沒有微笑,雙眼通紅,還像海盜一樣在頭上綁了白色圍巾,幾乎蓋住了整片額頭,但頭巾邊緣還是透出了一些紫黃色的瘀青。才剛吃完早餐,連碗盤都還沒洗,媽就把一些私人物品放進化妝箱,沿著大馬路離去。
*
隔天早上,奇雅又坐在門前的階梯上等,深色雙眼緊緊盯著那條小路,彷彿那是等待火車通過的隧道。遠處的溼地受到霧氣籠罩,低垂的柔軟霧氣底部直接跟泥地貼合。光腳的奇雅扭動腳趾,捲起草莖挑弄著蟻獅,但六歲的孩子畢竟坐不久,很快地,她就溜達到灘地,腳趾從溼沙子中拔出時發出波波的抽吸聲。她蹲在清澈的水邊,望著小小的鰷魚在陽光的光點及陰暗處之間一次又一次短距離地衝刺著。
喬帝從棕櫚樹那邊大吼大叫地跑過來。她瞪著他。說不定他有什麼新消息了。但就在他從尖刺的細長葉片間揮舞手臂跑來時,她從他漫不經心的動作就知道,媽沒有回家。
「要玩探險家嗎?」他問。
「你說你已經長大,不玩探險家了。」
「沒啦,我只是說說而已。才沒有長大就不能玩這回事。來賽跑!」
他們拔腿跑過一片片沼地,穿過樹林後朝海灘跑去。她在他超前自己時大聲尖叫,一路大笑,直到抵達彷彿從沙中探出巨大手臂的那棵大橡樹邊。喬帝和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哥哥小莫在樹上釘了幾片木板當作瞭望塔和樹堡。現在那些木板幾乎全都鬆脫了,只靠著生鏽的釘子垂掛著。
之前就算獲准加入探險家的船員行列,她通常也只能當小女奴,負責從媽媽的平底鍋裡為哥哥們偷偷帶來熱呼呼的比司吉。
但喬帝今天說:「你可以當船長。」
奇雅立刻舉起右手發號施令。「趕走西班牙人!」他們揮斷好幾把樹枝做成的劍、衝破黑莓灌木,對著敵人又吼又砍。
接著――幻想總是來得快,去得也快――她走向一根長滿苔蘚的圓木,坐下。他沉默地跟著坐在一旁。他想說些什麼,好讓她別再想媽的事了,但什麼都想不出來,所以只是望著水黽映照在水面的影子。
之後奇雅又回到屋前階梯,等了好長一段時間,但望向小路盡頭的她始終沒有哭。她的臉上沒有任何波瀾,四處張望的雙眼底下,兩片嘴唇抿成一條細線。但媽那天也沒有回來。
第二章
喬帝
一九五二年
媽離開後,奇雅的大哥和兩個姊姊彷彿因為有了媽的示範,也在接下來幾個星期擺脫這個家。他們早已受夠爸總是臉紅脖子粗的怒氣,他一開始會大吼,接著升級成一輪猛拳,又或者用手背揍他們,於是他們最後一個個都消失了。反正他們也差不多成年了。之後,奇雅不只忘記了他們的年紀,也忘記了他們的真名,只記得大家都叫他們蜜西、小莫,和曼蒂。在她放在門廊的床墊上,奇雅找到一小堆姊姊留下來的襪子。
就在家裡只剩喬帝這個哥哥的早上,奇雅起床時聽到噹啷噹啷的聲響,還有早餐的油香味。她立刻衝進廚房,心想是媽在家炸玉米油條或玉米餅,但卻是喬帝站在柴爐前攪拌玉米粥。她用微笑掩飾自己的失望,他拍拍她的頭,溫和地提醒她保持安靜:若沒有吵醒爸,他們就能自己吃早餐。喬帝不知怎麼烤比司吉,家裡也沒有培根了,所以他煮了玉米粥,還用豬油炒了蛋,接著他們一起坐下,沉默交換著眼神及微笑。
他們吃完後迅速洗了盤子,出門跑向溼地,喬帝在前面帶頭。但爸就在此時大吼起來,腳步蹣跚地追上他們。他瘦到不可思議的身形似乎就要因為缺乏重量而撲通倒下,口中的臼齒就跟老狗的牙齒一樣黃。
奇雅抬眼望向喬帝。「我們可以逃掉。躲在苔蘚很多的那個地方。」
「沒事的。一切都會沒事的,」他說。
*
那天接近日落時,喬帝發現奇雅在沙灘上盯著大海。他站到她身邊,她沒看他,只是繼續盯著翻湧的海浪。根據他說話的方式,她知道爸揍了喬帝的臉。
「我得離開了,奇雅。沒辦法待下去了。」
她幾乎要轉身面對他了,但沒這麼做。她想求他別留自己跟爸相處,但想說的話全堵在喉頭。
「等你夠大之後就會懂了,」他說。奇雅想要大吼:她或許年紀小,但可不笨。她知道爸是所有人離開的原因,她不懂的是為何沒人把她帶走。她也想離開,但無處可去,身上又沒有巴士錢。
「奇雅,你自己小心,聽著,如果有人來,別進屋去。他們會在屋子裡抓住你。跑到溼地深處,躲在灌木叢裡。永遠記得掩蓋自己的足跡,我教過你。你可以躲起來不給爸找到。」她還是沒說話,他說了再見後越過沙灘走向樹林。就在他踏進樹林之前,她才終於轉身,望著他離開。
「這隻小豬留在家裡,」她對著海浪說。
她終於動了起來,跑向棚屋,對著走廊大喊他的名字,但喬帝的東西都不見了,他鋪在地上的床也清空了。
她沉重地坐在他的床墊上,看著最後一絲天光從牆面滑下。太陽落下之後,天光還沒有完全消失,其中有些還匯聚在屋內,所以有那麼短暫的一刻,跟外面的樹木相比,那些凹凸不平的床鋪和一堆堆舊衣的形狀及顏色能被看得更清楚。
她因為磨人的飢餓感嚇了一跳,多麼乏味的感受呀。她走進廚房,站在門邊。這個房間在她有生之年總是因為烤麵包、煮奶油豆子,或燉著滾燙的魚湯而熱烘烘的,但此刻卻顯得汙濁、安靜又陰暗。「誰來煮飯?」她大聲地問。乾脆直接問「誰來跳舞?」算了。
她點亮一根蠟燭,戳了戳爐子裡的熱燙灰燼,又加了些引火柴,擠壓風箱讓火點燃,接著加了更多柴進去。電冰箱被拿來當櫥櫃使用,因為棚屋附近接不到電。為了確保黴菌不會失控擴散,門總是靠一支蒼蠅拍卡著維持敞開,但綠黃色的霉斑還是在每個裂隙中蔓延。
她拿出剩菜,說,「我要把玉米粥倒進豬油裡,再熱一熱,」她確實這麼做了,也吃了鍋裡的粥,然後往窗外看爸有沒有回來,但爸始終沒出現。
就在弦月的光線終於撒在棚屋上時,她爬上放在門廊的床墊――那是一張凹凸不平的床墊,上頭鋪的床單灑滿了小小的藍色玫瑰,是媽在別人家二手出清時買來的真正床單――但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獨自躺在上頭。
剛開始的時候,她每隔幾分鐘就會坐起身,透過紗門往外瞧,也仔細聽著是否有來自樹林的腳步聲。她認得每棵樹的形狀,但仍有些樹似乎一下出現在這裡,一下又出現在那裡,彷彿隨著月光到處移動。她一度身體僵硬到連口水都吞不下去,但熟悉的樹蛙鳴唱和大螽斯的叫聲準時充滿夜色,比「拿著雕刻刀的三隻瞎老鼠」的童話故事還有撫慰效果。夜色中有一種甜香,又熬過一個溼熱白日的青蛙和蠑螈呼出的土味。溼地隨著低矮的霧氣籠罩過來。她睡著了。
*
爸連續三天沒有回來,奇雅從媽的菜園裡採了蕪菁葉後煮來當早餐、午餐和晚餐。她有走去雞舍找蛋,卻發現什麼都沒有。到處都沒有雞或蛋的蹤影。
「雞屎!這裡就只剩一堆雞屎!」她本來打算在媽離開後好好照顧這些雞,但卻幾乎什麼都沒做。而現在這群五顏六色的禽鳥已遠遠逃入樹林。她得到處撒些玉米,看有沒有辦法讓牠們待在棚屋附近。
第四天晚上,爸手上拿著一個酒瓶現身,大字型躺在床上。
隔天早上他走進廚房,大吼:「其他人哪去了?」
「我不知道,」她說話時沒看他。
「你就跟雜種狗一樣什麼都不知道。就跟公豬的奶子一樣沒用。」
奇雅默默地從通往前廊的門溜了出去,沿著沙灘走時眼睛搜尋著貽貝。她聞到煙味,抬頭看到一簇煙霧在棚屋那個方向升起。她用盡全力快跑,衝刺穿越樹林後看到一個火堆在後院熊熊燃燒,爸正往火裡丟媽的畫作、洋裝和書。
「不!」奇雅尖叫。他沒看她,只是把老舊的電池收音機也丟進火裡。她的臉和手臂在她想伸手拿畫時燙傷了,但熱氣逼得她不得不後退。
她衝進棚屋擋住想回屋子裡拿更多物品的爸,雙眼死瞪著他。爸作勢要用手背揍她,但她堅持不退縮。他突然之間決定轉身,跛腳走向自己的船。
奇雅跌坐在磚板階梯上,望著媽的溼地水彩畫悶燒為灰燼。她一直在那裡坐到太陽落下,直到所有衣物的釦子都成為黑得發亮的焦煤,而和媽一起跳吉特巴舞的回憶也消融在火焰中。
接下來幾天,奇雅學會了如何與他一起生活,她從其他人的錯誤中學到教訓,甚至從鰷魚身上學到了更有用的一課:避開他,別讓他見到你,從陽光中竄逃入陰影。在他醒來前先起床、離家。她在樹林及水邊生活,只有晚上才躲回屋內,睡到自己位於門廊的床上,而且盡可能靠近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