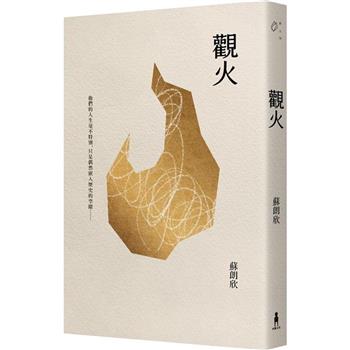打火
後來曉晴再見到智洋已經是十月。期中考最後一天,人潮湧出學院,曉晴在停車場裡尋到自己的單車,轉身一瞥,居然見到智洋在吸煙區抽煙。
智洋不高,戴眼鏡,頭髮削短,上掛一個殘破帆布袋,全身上下質樸無華。他倚坐在吸煙區的鐵椅上,左手搭上褪色的扶手,右手輕輕夾著剩下一半的香煙,擱在生鏽的鐵桌邊緣。桌子正中央是煙灰缸,已盛滿灰燼。香煙燒到盡頭,智洋目視星火散落,曲起指頭把煙頭彈入缸中,手勢俐落。
第一次見證那場面,曉晴愣住一下。
真想不到他會抽煙,她想,那麽乾瘦、無趣的一個男生。
然後她垂下眼眉,把背包塞進菜籃,轉身面向台灣同學,一邊跨上單車,一邊用流利的普通話談笑—從小看大陸綜藝學來的。
來台兩個月,作為港生的曉晴絲毫不認為跟台灣人之間會有任何溝通困難。對她來說,國語和普通話分別只在前者語氣溫柔,後者多捲舌音,僅此而已。她輕鬆融入環境,足跡遍布縱谷許許多多的什麽步道什麽湖什麽潭,她有自信自己去過的景點比得過本地人。所以,這次她們想去更遠的地方,慶祝順利熬過考試,要去瑞穗?玉里?要不往更南闖,台東三日兩夜?好啊,不然去墾丁,享受陽光海灘?
她夜裡躺在宿舍狹窄的單人床墊上,開始策畫一趟墾丁之旅,滑動手機查看海岸邊緣的民宿指南。
但智洋輕輕吐出的煙霧彷彿留在眼角,似有若無。
曉晴跟智洋兩個人,一個讀大學部,一個是研究生,幾近沒有相接之處。之所以認識,是因為疫情肆虐,初來乍到,每個人在機場都得先買一張電話預付卡,方便政府追蹤防疫,唯獨未滿十八歲的曉晴不能買,推拉折騰好一陣,最終找到二十四歲的智洋代辦,兩人才在五十幾位新生裡相認。
十四日隔離結束,新生們從宿舍魚貫離開,那陣時單車已經一輛伴著一輛停在樓下,港澳會的學長姊在停車場邊守候,手裡提著塞滿紙鈔和硬幣的文件袋。
當初港澳會迎新LINE群裡,學長千叮萬囑一定要買單車,不會踩的馬上去學,不騙人—畢竟這間東部大學校園廣闊是出了名—並隨訊息附上一張捷安特產品目錄。新生們慌了,趕緊下單,由學長代為訂購,聽說有特別折扣,結果還是一輛四、五千台幣,群組裡還有人猜疑是不是有詐?但得不到任何回答。
現在終於摸到車子,曉晴拍拍座墊,跨坐上去,在隔離宿舍門前的迴旋處繞兩個圈,感覺不錯,才付錢付得心甘情願。
「同學,你的車呢?」學長朝著曉晴背後發問。
她轉身,發現是智洋—她不記得他的長相,卻認得一對黑框眼鏡,還有身上洗到發白的格紋襯衫—他搖頭,說:「沒買。」
兩人對上眼。已經不可能裝作不曾遇見,唯有尷尬地搭話。
曉晴勸他不如乾脆添置一輛車,一邊給他看看手上的淑女車。智洋雙手抱胸,望著她,嘴角歪歪斜斜向下垂。道路兩邊栽滿了兩人都不認識的樹,夏日陽光穿透枝葉,在智洋的窄臉上打出交錯的光影,其中一片落在他的右眼。他眨眨眼,一直搖頭,堅持走路。
曉晴不服輸,糾纏好久。到最後,智洋才說:「我不會踩。」
她沒想到,忍不住笑:「我教你,當作報答之前辦的電話卡。」
智洋唯唯諾諾,隨便把話題帶過,那張嘴裡沒有流露出一絲鬆懈。
「好吧。」曉晴知道再講便是自討沒趣,於是隨意把話題了結,伸手一指:「那我差不多走了。去那邊。」
事實上「那邊」是哪一邊並不重要,純粹是擺脫對話的藉口°她跨上單車,疾馳而去。
智洋目送她離開,拿著學校派發的校園地圖,轉身走向宿舍。他得走很遠很遠的路才會抵達宿舍。
開學後,兩人就沒再見面。然而那十月的一瞥裡面,當煙霧飄過,在曉晴心中種下了歹念,慢慢地她竟想抽煙。一個人留學,難得擺脫了大人,就想自己當大人,可惜朋友裡沒一個像會抽的,她便不敢問。夜晚在四人宿舍,燈光滅了,曉晴躺在上層床,直到手機用盡電源,仍睡不著,她放空腦袋,想像什麽是吞雲吐霧。
受不了。
於是深夜一個人跑去旁邊的全家,硬著頭皮問:「我想買煙。七星,藍莓。」為了不出醜,還特地上網調查品牌。
大學裡的超商原來不賣煙。
曉晴隨手買了一支瓶裝茶,沿路走回宿舍。她不甘心。難得下了決心—決心像酒後的一瞬昏頭—儘管自己從未真正酒醉—就是這個晚上,她非抽上一根煙不可。她跳上淑女車,一路加快速度,從手把鬆開雙手,感受著輕盈的失重。快要踩到校門了,她在路口停下,左右回望有否機車轉出,這時候發現了一道身影。是智洋。
全是因為那種想像的酒醉,曉晴想,反正她踩過去攔在智洋身前。智洋一頓,猛地後退,狠瞪曉晴,神色警戒近乎凶狠。換曉晴嚇到了,連忙道歉。
「我只是想,嗯,跟你買一支煙。」曉晴說。
「買煙?」
「對,我想抽煙。」
智洋垂下手,尷尬地撥弄衣襬,沒有說話。
兩人陷入沉默,最終曉晴打圓場:「沒關係,我去外面買。」
「不用。」
智洋從格紋襯衫口袋掏出一包煙,抽了一根給曉晴,接著越過她,向校園走。格紋消失於幽深的樹影底下,他似乎還是低著頭,走自己的路。
曉晴拿著煙踩回宿舍,才想起自己沒有火。
那根煙不長也不幼,有一顆紫色的小球在吸嘴底端,煙紙寫著MЕVIUS。
她把煙含在嘴裡,嚐到薄荷的涼。這就是七星藍莓?她一直把玩,直到臨睡前才把煙收進襯衫口袋。卡其色半透明薄紗襯衣,防曬用,明天穿著出門。朋友說好下課帶她去七星潭看海。
隔天上課,要是有空檔,她就到吸煙區徘徊,想問煙友借火,卻又遲疑,昨天的膽色一下子全沒了。來回直到下午兩點才等到智洋,她一見那格紋就認出來,立即迎上去。智洋替她點火,手勢熟練。
曉晴終於抽到平生第一口煙,吸得輕輕淡淡,她聽說要是太用力的話,會頭暈。自問做好了所有防範措施,沒料到還是會暈眩—因為逆風,煙霧撲上她的眼睛,她用力瞇眼迴避,卻因而發昏。她閉上眼,聽見鴿子在上空迴旋,聽見枝葉搖動,聽見智洋輕笑時的鼻音。
這樣的一支煙她吸了很久,直至朋友來電,才出發去太平洋的海邊。
此後借火成為日常,她想像生活是電影《志明與春嬌》,一對男女在小巷交換一口煙,呼出了愛情°智洋不是她喜歡的類型,所以她心裡幻想的是一個高大台仔,會打扮,長著一張明星臉,在同樣的枝椏下突然出現。她其實沒看過那齣戲,和智洋相遇時也不曾談論過什麽愛情。
他們會一起嫌棄學餐又貴又難吃,嘲笑花蓮市區某些自稱正宗的港式茶餐廳,討論最近上榜的香港流行音樂,間或由她哼出一句歌詞,等他和聲—他通常都會和聲,即使每次開始時都害羞而困惑,而且聲音永遠細得幾乎不被聽見。
港澳會的同學若然不在同一個系所裡,幾乎全都在開學不久即各散東西,曉晴的校園生活沒有多少講廣東話的機會—唯獨在這一呼一吸的時刻,她終於使用母語。當舌頭發出倔強的入聲,她感到非常懷念。
到了樹葉枯黃的季節,兩個人已是心照不宣地,總在同樣時間出現在吸煙區。所有事情都成為習慣,因此在這天陰的日子,他們在吸煙區聚頭,當智洋抽出一根煙給曉晴,她仔細看著他連番開合煙盒的食指,突然感受到他情緒的變化。
她把煙遞到唇邊,還沒點火,馬上就察覺到不同。太甜。她仔細看。這不是七星藍莓。應該說,是七星,但不是藍莓,末端的晶球不是紫色而是黃色。
「這是另一個口味?」她問。
「哈密瓜。」智洋呼一口煙。他的嘴裡也有甜味。
「咦,我沒抽過。味道如何?可以先借我試試嗎?」曉晴問。卻又感覺不好意思。轉念想,不過一口煙,為什麽要尷尬。
智洋安靜了一陣,搖搖頭:「我不想。」
「哦。是哦。也是。容易交叉感染。會沾到口水。疫情嘛。」
然而智洋又搖頭,喃喃說不對。
曉晴問:「為什麽你會買這個?你平時每次都是藍莓。」
「以前抽過一次,那時跟我分享的人說是哈密瓜。我一直惦記在心裡。」
「所以就是有跟人分過嘛,女朋友?」曉晴扯開嘴角在笑。
「分享同一支煙對我來說等於分享了生死。」
智洋回答時,眉目低垂。
曉晴笑著說她聽不懂,正想叫他少裝模作樣,但眼見智洋的手凝在半空,煙沉默地燒,幾乎纏纒上指節,她便不再說話了。停頓中,有枯葉飄落地上,在曉晴眼角邊緣。有人走過,踩中落葉,葉片碎開,聲音清脆。
智洋像是突然被挖開了話匣子似地—她以為他身上沒有這東西—滔滔不絕:
「十一月那時候,我在理工大學,每一條路都被封死了。我一個人坐在七仔附近,有個陌生的手足問我有沒有煙。那時學校的七仔所有物資已被搶光,連一包煙都沒有剩下來。我身上本來還有最後一根七星藍莓,但在一次突圍時弄丟了。其實抗爭之前我都沒有抽煙,全都是因為後來壓力太大了。我跟那個人站在七仔爆開的玻璃櫥窗前,都沒說話。這時候另一個手足經過,和我們站在一起,從口袋裡抽出了一根哈密瓜的七星,我們盯著他,他也回望過來。那是他最後的香煙,但他遞過來,我們三個人輪流交換著抽,抽得很慢很慢,直到最後只剩下濾嘴,它自己熄滅了。凌晨五點半,警察打進來,我們的人往學校正門拋出雜物和白電油。當時天空是紅色的。」
智洋無意識地抖了抖煙灰,問:「你有去嗎?抗爭。」「有去遊行。」
她確實有去過一兩場六月的和平遊行,由銅鑼灣出發步行去金鐘,和朋友一起,出門前精挑細選當日的衣著配搭,也不戴口罩。後來事情逐步演變成另一個模樣,此後她對抗爭的認知都來自新聞報導、社交媒體、朋輩分享,但沒有一個朋友會跟她說起在抗爭現場抽煙。
智洋不再說下去,所有的話語彷似頓時煞停,他把煙湊近唇瓣。他總是吞吐輕盈,像在品嚐什麽人間美味;曉晴卻相反,別人一根煙的時間足夠她完成兩根,因為喜歡用力吸,用力呼,吐出來的煙霧特別多,也特別美—她不怕暈眩。已經不怕了。
「那另外兩個人,現在在哪裡?」曉晴問。
智洋還是搖頭,安靜眺望遠山。
搖頭算什麽?曉晴生起悶氣,兩個人之間落得如此尷尬,還不是因為他,是他硬要挑起這種無法輕鬆接下去的話題,挑起了又無以為繼,說一半又不說一半,像把她當成是局外人。
然而,難道她不是嗎?
曉晴沒有辦法輕率回答這個問題。
她坐到鐵椅上,問:「為什麽要來這裡唸書?我在港澳會的學長口中聽過,每年都有香港新生耐不住寂寞,決定退學,不然往北部轉學。台灣這麽大,選擇這麽多。」
兩人一同望山。除了山之外,沒有別的。
曉晴自問在奇莱山下活得很好。她不是那種會因為生活不便就放棄的人。
她已經適應濕潤的空氣,當把書本從架上拿下、發現手指摸著霉菌時,不會再感到驚訝;她清楚鄉郊地方交通不便,下定決心半年後考機車,請台灣人朋友教學,並且習慣了高速中猛風刮面的疼痛。她終於愛上這個地方——
「因為容易考上。」智洋戳穿真相。
見曉晴不答話,他苦笑:「好吧,你就當作是因為我不想再待在石屎森林,那種大城市,那種高牆。我想在花蓮看大山大海。我也喜歡散步。」
「你用走的未免太沒效率了吧,例如,如果你要買煙,由宿舍走到校外的超商要四十分鐘。」
「第一個跟我要煙的手足,說要走下水道逃亡,他彎著身向下爬,誰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成功。」
曉晴用力吸手上的七星哈密瓜。澄澈天色下,中央山脈清晰可見,彷彿永恆屹立。是它眺望我們──曉晴有種錯覺。智洋的側臉在霧裡頭隱隱約約,配合著落葉,有種少年憂鬱。曉晴突然覺得世上的一切溫和而善良,儘管這種想法如此不合時宜。她幻想著自己的大學,這一間花蓮風光明媚的大學,在夜裡著了火,焚燃出焦紅色的天空。
但是,在台灣,會有這種事嗎?她無法想像。這裡大概沒有什麼殘破的七仔,只有好山好水。
她沒頭沒尾拋出一句:「你去過七星潭嗎?」
「沒有。」
「去過哪個名勝景點嗎?」
智洋沉默,最後搖頭。
曉晴笑他:「來這麼久什麼地方都沒去過,還說什麼想看大山大海,根本騙人。」
然而話一出口,她就見到智洋的臉色頽靡下來,有如受傷。
曉晴心裡慌了,脫口而出:「不然我們一起去看好了。」為了加強說服力,還拉著智洋動身往校內的公車站出發。沒想到他真的任由了她。
兩人走到圖書館外,查看公車時刻表,好不容易等到一班,對司機一問才發現根本到不了七星潭,終點在花蓮火車站,必須抵步後再轉乘另一號公車,一路上風塵僕僕。智洋小聲嘀咕,不如別去了,卻被曉晴瞪回去,四十分鐘又四十分鐘的車程和等待,彼此默然無語,一個看風景轉眼流逝,一個合眼小憩。
抵達七星潭已經是五點,兩人下了車,望出去,偌大的風景園區裡大部分攤販都蓋上了帆布,也就是說,打烊了,沒有服務。車站只有他們倆。曉晴暗自反省,果真是太衝動了吧?還有回程的班次嗎?反而是智洋望向海,邁步前行,走到一半回身揚手召曉晴過去,似乎沒有了最初的慌亂。不安的人換成曉晴,但她又能怎樣呢,不就只能去看那日落時分的海了嗎。
十二月初,天氣說不上冷,只是天色反覆,剛才在學校還是好好的,到了海邊卻是烏雲一片,雲層低壓似欺身─花蓮一貫景觀─實在說不上什麼好天氣。然而智洋似乎非常滿意眼前陰翳的七星潭,他坐下來,伸長雙腿,兩隻手壓在鵝卵石上,支撐身體,呼出一口嘆息。曉晴猶豫兩、三,最終也跟著並肩而坐。石灘凹凸不平,久坐,屁股開始痛,她將包包墊在地上。眼前水花翻來覆去。岸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全都捲起褲管,穿著人字拖鞋,水來時驚呼,水退了又回到原來的位置,踩踏在被海水吞吐過的砂石上。在智洋和曉晴右方,有一對情侶帶了單眼相機和腳架,三根支架插在石頭的隙縫中,他們校正倒數計時,連續自拍十張。每個人都裝備充足,毛巾、遮陽傘、風衣、手套樣樣不缺;唯獨智洋和曉晴手上空空如也,沒水沒雨傘,什麼也沒有。
最多有一包,或者兩包,七星。和打火機。
七星潭的海分成三種顏色:花白的浪,近接的碧藍,到遠方的深藍。也許更遠的地方還會有其他顏色吧,曉晴記得上一次來—便是抽那第一口煙的日子,她乘坐在台灣同學的機車後座,天空沒有半片雲,一切明媚如許,他們大笑,拔足狂奔,撿拾起散發熱氣的石頭往水面擲出—她問過同學,為什麽海會有不同顏色?她從沒見過被分割的海水。同學也許回答了,也許沒有,她沒記住。海水翻起的時候,連綿成一道壯麗的牆,後面的浪會吃掉前面的浪,最終融為一體,直撲到岸上。她維持安全的距離看潮進潮退,並且為之著迷:所有的浪都如此相似,所有的浪都不會相同。
好幾次,浪越來越急進,曉晴甚至相信大水會馬上席捲而至,自己將會和前方倒插在沙地上的一個啤酒瓶有相同下場:當海水湧近,它會顫抖,卻不被帶走—她會被全身上下沖成濕透,但仍在這裡停留。
然而每一次,泡沫頂多只會湧到她的腳趾前沿,便立即爆開,退去。水從未撲上她的肌膚,哪怕一吋半吋。
智洋撿起一塊圓石,起身往海裡拋。石頭沒入浪中,無聲無息。他再來一次。曉晴過一陣子才猜出來,那是彆扭的打水漂。
「你那樣不行的啦。」她說:「擲出去的時候要彎身,腰要扭轉。石頭要旋轉。」 她挑了一片扁平的礫石,在遠離水邊的地方示範動作。
智洋回頭看她。逆光使她無法辨識他的表情。智洋再次抛出石頭,仍然連一次彈跳都沒有發生。他彎腰,挑剔地揀選,撿拾。
天空逐漸邁入澄黃,不過也許是因為天陰,他們沒有遇上期望中的渾圓夕陽。但海仍然美,泛著火一般的光澤,燦爛到刺眼。若是平常時候,曉晴會抓緊短暫的日落時光,拿手機拍照,換好幾個角度,發給朋友家人,但此刻她只是凝望智洋不屈不撓地拋擲的身影。每一顆石子都噗通跌入海中,一切都毫無起息,卻無礙他的興致,假如那稱得上是一種興致的話。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