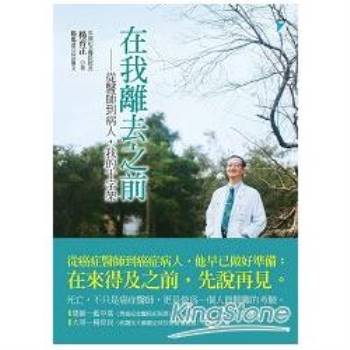摘文1
一封安寧病房體驗的邀約
「If I do not wake up tomorrow...」我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給我的孩子們。我希望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的小孩能讓神和他的父母都感到榮耀;我希望他們好好照顧他們的母親,但是不必要住在一起,保持一種生活上的距離,以減少摩擦,而能永遠保持心靈上的親近;我希望兩個孩子可以互相照顧,紀念他們的父親。
我是一名癌症醫師,二、三十年來,我的工作就是協助生死邊緣的病人與家屬,在身、心、靈求取最大的利益與平靜。求生有勝算時,用盡一切手段延長他們的生命;死亡已不可避免時,給予慰藉和支持,讓他們在道別之前,盡可能不帶著痛苦與遺憾上路,因為協助病人平靜地離開也是醫師的天職。
帶著遺書上班
我時時面對著他人的死亡,那激發我對工作的熱忱與慎重,對生命的想像與好奇。「時機成熟時,我們就會拋棄肉身,擺脫病痛、恐懼和人生的煩惱,逍遙自在,宛如一隻飛回上帝身邊的彩蝶。」我也常思考,我們是否可以如生死學大師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bler-Ross)的這般堅定信仰。
很長的時間,我身上都帶著遺書上班。我認為,男人年過四十後,就應該有這樣的「風險管控」意識。特別因為我一直有高血壓的毛病,也有慢性B型肝炎,長年以來都必須用藥控制。
B型肝炎,在台灣早年主要是母子垂直感染,但可能也是很多外科醫師的「職業災害」。早年,醫師開刀防護沒有那麼周密,在手術過程中不小心劃傷自己是家常便飯。在我還是住院醫師時,某一次跟老師的刀,不小心遭手術刀割傷,反射性大叫一聲,結果老師笑著喝斥:「病人肚子那麼大的傷口都沒有叫,你叫什麼?」
醫師手術受傷不只沒有喊痛的權利,在那個還沒有疫苗、沒有抗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而台灣B型肝炎帶原率極高的年代,有不少醫師就可能像這樣因為傷口的血液與病人的血液互染,被病人感染了而不自知。我猜測,自己也極可能是因此染病。
我很早就有生命風險的準備。在婦產科後半段的生涯,又以照護癌症病患為主,一直希望能為臨終前的病人做更多努力,為推廣安寧療護的觀念和精神盡心。
馬偕醫學院將開辦前,我即與當時安寧療護教育中心主任賴充亮醫師相約,共同推動高中生的生命科學教育。由賴醫師舉辦生命營,邀高中生們來安寧病房體驗;時任醫學研究部主任的我則負責設計科學營,讓學生從生物研究中接觸生命的奧祕。在高中生心底撒下生命和科學啟蒙的種子,不僅是替醫界的未來育苗,也能讓年輕學子及早體會生命的脆弱,學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時光。
從癌症醫師到癌症病人
當我接下院長職務之後,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舉辦全院主管「one day in hospice」安寧病房一日體驗活動,由各科室主管到安寧病房住一天,甚至身上插一管,譬如尿管、鼻管,體驗末期病人身體上的苦楚,日後無論在治療、服務或諮詢時,都能真正做到「感同身受」。
儘管三十年來都在醫院與「無常」交手,但沒料到,這回命運的俄羅斯轉盤指針,竟然指向了我!啊~我們穿著白袍的人,角色是病人的代理人,往往忘了,其實和一般人一樣,也是命運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就在我寄出「安寧病房一日體驗」邀請信函後,收到第一封主管報名回覆的當天,我同時也接到了另一封「通知函」──困擾我兩個月之久的三叉神經疼痛的病理切片報告出爐,瞬間宣告我由一名癌症醫師,轉為一名B細胞淋巴瘤的癌症患者!
我不需要去安寧病房「體驗」病人的身心感受,我已經立即成為「被體驗組」的一員。
為什麼會是我?!
我曾宣稱,自己用心治療我的癌症病人,一直用同理心對待病患,不僅治病,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心理,並且鼓舞他們的情緒,教導他們要「面對疾病,繼續生活」。
此刻,我深知以往自己是如此的不足。我何曾真正接近病人的真實感受?我何曾真正了解,當被診斷為癌症時,是如何期待有其他更好的可能?面對癌症、接受事實,豈是教科書上簡單的五個階段心理歷程可以全然描述。我對我全心信靠的上帝發出質疑:為什麼是我?我一直是那麼忠心的僕人,我是一個好人吶!
投身醫療四十年,我以為已成人師、已是沙場老兵了,我也自以為從未凋零,時時刻刻不放鬆地追求醫療新知的更新與研究。我更以為,自己由接生醫師到癌症醫師,完整通透地體會了生、老、病、死的生命曲線與意義。
歷經六次全身化療、八次標靶治療、四次髓鞘內化療與兩次嚴重併發症,熬過掉髮、嘔吐和肌肉萎縮。過去在無數病人身上看到因為疾病摧殘、藥物副作用,帶給血肉之軀的傷害與痛苦,我都親身經歷過了一回。一次又一次生命的鞭痕,都在刺激我一遍又一遍檢視自己信仰的核心價值,從最初的懷疑,到最後更堅定,心志更明確,態度更為謙卑。
原來,死亡的背後有許多我們不可知的部分,學習和面對它是人生成長的最後階段。這是一條試煉之路、恩典之路,更是學習之路。
罹癌,更激發我的熱情
疾病讓我變成一名「新生」,讓我了解,原來我還有許多未竟之處、未解之事,原來我還有很大的可塑性。透過癌症,訓練我通過最後的進階訓練,它讓我更清楚理解了人生的價值,更清楚看見了自己的使命。
我慢慢領悟,上帝要我經歷癌病的旨意,是在鞭策我更積極用生命去成就該做的事,更主動向我愛的人展露心意。對於人生、對於家庭及對於我的醫療工作,我湧起更大的熱情,我要用我這向上帝借來的生命,榮耀我所熱愛的一切。
現在,當我再對我的孩子們吟誦起多年前我為他們寫的那首小詩,心裡不再只是對他們疼惜的慰藉,而更有著堅強的篤定。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孩子,我卻從不曾離去。
早晨,陽光照進你的門窗,
你是否感到溫暖?
孩子,我就在你的身旁。
日落時,微風拂過樹梢,
在沙沙作響的枝葉聲中,
孩子,你可聽到風中夾雜著我的言語?
夜深時刻,當清涼的月光從門縫滲入,
那時我正躡手躡腳,
深情的凝視著你,
我的孩子,
縱然你從此不再看見我,
我卻從來不曾離去。
摘文2
癌末病人教醫師的事
「醫師,請您們不要放棄我太太,請務必要盡一切努力治療她,一分鐘也不要放棄!」
個子小小、經營小餐館的黃先生,一向沉穩謙和,那天他突然在病房裡失控,憤怒地大聲對著一名外科醫師說話,我嚇了一跳,停下腳步。原來,那名外科醫師嘗試向黃先生說明他妻子的病情,並提到應該是到了考慮在最後危急階段,是不是要進行侵入性急救措施的時候。
黃太太雖已年近六十,仍然一副白皙秀氣,一看就知道很受丈夫照顧與疼愛。她是以夫為天的傳統婦人,遇到任何問題,會立即回頭看著丈夫,所有決定與發言,都交由黃先生回答,彷彿隨著終身許配給丈夫,所有的一切也全然託付給了他。
「不准你們放棄我太太!」
黃太太先前在另一家宗教醫院診斷出子宮內膜癌,並已轉移到陰道下段,所有檢查都已在該院完成,之後才轉到我們醫院。據護理人員了解,轉院之前,黃先生為了確保妻子能夠康復,在該院捐了一大筆錢,希望妻子能得人天福報的庇佑。
由於黃太太的病況未獲控制,在轉到我們醫院之後,我們先為她動了手術,再給予化學治療。棘手的是,手術過程中,又發現黃太太除了子宮內膜癌外,還同時有不同細胞形態的卵巢澄清細胞癌,這是一種較為少見、且抗藥性較高的癌症。
因此,黃太太手術後就在疾病起落之間,經歷了許多次不同的化療,還包括一次腸阻塞嚴重而做了迴腸造口術。
黃太太本身是一位非常配合的病人,對各種治療從不喊苦,一切安排都仰賴丈夫決定。但歷經了多次復發,有一次再住院時,原先的迴腸造口術已無法解除她的腸阻塞,她又腹脹厲害,無法進食,所有的標準化學治療都已嘗試而無效。此時,我們的外科同仁善意地提出了可能須面對的最後抉擇:是否要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若急救已無法延長有品質的生命,是否不再勉強加諸包括氣管插管、人工呼吸器及心臟電擊等急救方式的「DNR」(Do Not Resuscitate)同意書。
就是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溫和的黃先生發怒,他誤解醫生不願再盡力救治黃太太,要求醫療團隊不能放棄。
為了我們所愛,提早做好準備
一身樸素、看來節儉的黃先生,卻替妻子選擇住差額負擔最高的單人病房,要求使用最好的藥物,價以萬計的標靶治療也要求盡量使用。但眼看疾病已到了失控的階段,做為醫療人員就當據實以告,請其預先準備。
然而,我們要怎麼告知真實情況,卻不奪去黃先生的最後一點希望?黃先生心裡一定早已知道疾病的程度,只是期待著奇蹟眷顧,我們何忍逼他提早面對他所不願面對的事實?
我們總對年輕醫師說,讓癌末病人簽署DNR,是為了免於「延長死亡的過程」,因為那些可能十分痛苦的急救過程,並未真正「延長生命」。
但捫心自問,若面對生命最後關卡的重病患者,是我們自己摯愛的親人,我們又能否如此以理性決斷?
誰來決定死亡過程的長短?誰來決定死亡的過程不是生命的一部分?這不只是癌症醫師,更是做為一個人最艱難的考驗,卻也是最深刻的自我學習與靈性成長。
因此,我們都該及早決定,並交代如何面對自己的最後時刻,避免讓我們所愛及愛我們的人,痛苦地處理如此艱難的課題。
一個感謝,讓我流下男兒淚
有一位我照顧六、七年的卵巢癌老太太,去世前她情緒極度不穩,她說,已經知道自己人生到了盡頭,不斷哀求我們:「讓我安樂死,早死早超生。」我們當然做不到。我只有對她說:「我可以給妳安樂。」就是協助她止痛,可以不痛苦。但老太太不能如願,常在病房裡鬧脾氣,最後,仍在「不安樂」中去世。
在老太太疾病的前半段,我們用心照料。她腹水嚴重,一抽水就得抽上一、兩個鐘頭;一般是插管子讓它自己引流,對於不是單一水囊的積水,這樣抽得不乾淨。我則和住院醫師輪流親手抽,十西西、十西西地抽,需要時,常一抽就抽幾千西西的腹水出來。當時老太太對我們的貼心照顧非常感謝,隨著病情惡化,卻開始對醫療人員發脾氣。
在老太太過世後的某天,一位病友特別來找我,告訴我,其實老太太臨終前囑咐,自己去世之後,請她一定要來找我,對我之前給予老太太的長久照顧表達感謝之意。
我對這名病友說,我當然知道老太太鬧脾氣不是她的真心。但這個遲來的感謝,仍讓我不禁在門診室裡流下男兒淚。這就是一名癌症醫師的「收穫」吧。
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
照顧癌末病人,讓我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思考:人到底是什麼?生命到底是什麼?這些病人都是我的人生導師,激發我的思想。
早年,我很滿足於做為一名接生的產科醫師,體驗生命初始的喜悅;現在,我則很珍惜能夠照顧癌症病人,對生命本質與醫者價值,有更深的體悟。
這樣近距離地觀察生命的起落、圓缺,確實給自己很大的成長,使我認知生命的有限、生命的不可控制,以及人對生命的無奈與無力。這些點點滴滴都讓我價值更清明、智慧更豐厚,無論日常生活或人生歷程,更能夠判斷什麼該執著,什麼不該執著;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
轉眼間,在無數人的生命裡歷練、體驗,我也成了一名年過六旬的資深醫師,若還有什麼可以傳遞給年輕後輩的,除了學術醫療上的職能、技巧,便是誠心建議他們,每一天都要注意自己的「靈性成長」。照顧病人時要以同理心、要投入自己的「感情」,如此而能豐富自己的靈性,而能感受到,醫師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
一封安寧病房體驗的邀約
「If I do not wake up tomorrow...」我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給我的孩子們。我希望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的小孩能讓神和他的父母都感到榮耀;我希望他們好好照顧他們的母親,但是不必要住在一起,保持一種生活上的距離,以減少摩擦,而能永遠保持心靈上的親近;我希望兩個孩子可以互相照顧,紀念他們的父親。
我是一名癌症醫師,二、三十年來,我的工作就是協助生死邊緣的病人與家屬,在身、心、靈求取最大的利益與平靜。求生有勝算時,用盡一切手段延長他們的生命;死亡已不可避免時,給予慰藉和支持,讓他們在道別之前,盡可能不帶著痛苦與遺憾上路,因為協助病人平靜地離開也是醫師的天職。
帶著遺書上班
我時時面對著他人的死亡,那激發我對工作的熱忱與慎重,對生命的想像與好奇。「時機成熟時,我們就會拋棄肉身,擺脫病痛、恐懼和人生的煩惱,逍遙自在,宛如一隻飛回上帝身邊的彩蝶。」我也常思考,我們是否可以如生死學大師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bler-Ross)的這般堅定信仰。
很長的時間,我身上都帶著遺書上班。我認為,男人年過四十後,就應該有這樣的「風險管控」意識。特別因為我一直有高血壓的毛病,也有慢性B型肝炎,長年以來都必須用藥控制。
B型肝炎,在台灣早年主要是母子垂直感染,但可能也是很多外科醫師的「職業災害」。早年,醫師開刀防護沒有那麼周密,在手術過程中不小心劃傷自己是家常便飯。在我還是住院醫師時,某一次跟老師的刀,不小心遭手術刀割傷,反射性大叫一聲,結果老師笑著喝斥:「病人肚子那麼大的傷口都沒有叫,你叫什麼?」
醫師手術受傷不只沒有喊痛的權利,在那個還沒有疫苗、沒有抗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而台灣B型肝炎帶原率極高的年代,有不少醫師就可能像這樣因為傷口的血液與病人的血液互染,被病人感染了而不自知。我猜測,自己也極可能是因此染病。
我很早就有生命風險的準備。在婦產科後半段的生涯,又以照護癌症病患為主,一直希望能為臨終前的病人做更多努力,為推廣安寧療護的觀念和精神盡心。
馬偕醫學院將開辦前,我即與當時安寧療護教育中心主任賴充亮醫師相約,共同推動高中生的生命科學教育。由賴醫師舉辦生命營,邀高中生們來安寧病房體驗;時任醫學研究部主任的我則負責設計科學營,讓學生從生物研究中接觸生命的奧祕。在高中生心底撒下生命和科學啟蒙的種子,不僅是替醫界的未來育苗,也能讓年輕學子及早體會生命的脆弱,學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時光。
從癌症醫師到癌症病人
當我接下院長職務之後,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舉辦全院主管「one day in hospice」安寧病房一日體驗活動,由各科室主管到安寧病房住一天,甚至身上插一管,譬如尿管、鼻管,體驗末期病人身體上的苦楚,日後無論在治療、服務或諮詢時,都能真正做到「感同身受」。
儘管三十年來都在醫院與「無常」交手,但沒料到,這回命運的俄羅斯轉盤指針,竟然指向了我!啊~我們穿著白袍的人,角色是病人的代理人,往往忘了,其實和一般人一樣,也是命運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就在我寄出「安寧病房一日體驗」邀請信函後,收到第一封主管報名回覆的當天,我同時也接到了另一封「通知函」──困擾我兩個月之久的三叉神經疼痛的病理切片報告出爐,瞬間宣告我由一名癌症醫師,轉為一名B細胞淋巴瘤的癌症患者!
我不需要去安寧病房「體驗」病人的身心感受,我已經立即成為「被體驗組」的一員。
為什麼會是我?!
我曾宣稱,自己用心治療我的癌症病人,一直用同理心對待病患,不僅治病,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心理,並且鼓舞他們的情緒,教導他們要「面對疾病,繼續生活」。
此刻,我深知以往自己是如此的不足。我何曾真正接近病人的真實感受?我何曾真正了解,當被診斷為癌症時,是如何期待有其他更好的可能?面對癌症、接受事實,豈是教科書上簡單的五個階段心理歷程可以全然描述。我對我全心信靠的上帝發出質疑:為什麼是我?我一直是那麼忠心的僕人,我是一個好人吶!
投身醫療四十年,我以為已成人師、已是沙場老兵了,我也自以為從未凋零,時時刻刻不放鬆地追求醫療新知的更新與研究。我更以為,自己由接生醫師到癌症醫師,完整通透地體會了生、老、病、死的生命曲線與意義。
歷經六次全身化療、八次標靶治療、四次髓鞘內化療與兩次嚴重併發症,熬過掉髮、嘔吐和肌肉萎縮。過去在無數病人身上看到因為疾病摧殘、藥物副作用,帶給血肉之軀的傷害與痛苦,我都親身經歷過了一回。一次又一次生命的鞭痕,都在刺激我一遍又一遍檢視自己信仰的核心價值,從最初的懷疑,到最後更堅定,心志更明確,態度更為謙卑。
原來,死亡的背後有許多我們不可知的部分,學習和面對它是人生成長的最後階段。這是一條試煉之路、恩典之路,更是學習之路。
罹癌,更激發我的熱情
疾病讓我變成一名「新生」,讓我了解,原來我還有許多未竟之處、未解之事,原來我還有很大的可塑性。透過癌症,訓練我通過最後的進階訓練,它讓我更清楚理解了人生的價值,更清楚看見了自己的使命。
我慢慢領悟,上帝要我經歷癌病的旨意,是在鞭策我更積極用生命去成就該做的事,更主動向我愛的人展露心意。對於人生、對於家庭及對於我的醫療工作,我湧起更大的熱情,我要用我這向上帝借來的生命,榮耀我所熱愛的一切。
現在,當我再對我的孩子們吟誦起多年前我為他們寫的那首小詩,心裡不再只是對他們疼惜的慰藉,而更有著堅強的篤定。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孩子,我卻從不曾離去。
早晨,陽光照進你的門窗,
你是否感到溫暖?
孩子,我就在你的身旁。
日落時,微風拂過樹梢,
在沙沙作響的枝葉聲中,
孩子,你可聽到風中夾雜著我的言語?
夜深時刻,當清涼的月光從門縫滲入,
那時我正躡手躡腳,
深情的凝視著你,
我的孩子,
縱然你從此不再看見我,
我卻從來不曾離去。
摘文2
癌末病人教醫師的事
「醫師,請您們不要放棄我太太,請務必要盡一切努力治療她,一分鐘也不要放棄!」
個子小小、經營小餐館的黃先生,一向沉穩謙和,那天他突然在病房裡失控,憤怒地大聲對著一名外科醫師說話,我嚇了一跳,停下腳步。原來,那名外科醫師嘗試向黃先生說明他妻子的病情,並提到應該是到了考慮在最後危急階段,是不是要進行侵入性急救措施的時候。
黃太太雖已年近六十,仍然一副白皙秀氣,一看就知道很受丈夫照顧與疼愛。她是以夫為天的傳統婦人,遇到任何問題,會立即回頭看著丈夫,所有決定與發言,都交由黃先生回答,彷彿隨著終身許配給丈夫,所有的一切也全然託付給了他。
「不准你們放棄我太太!」
黃太太先前在另一家宗教醫院診斷出子宮內膜癌,並已轉移到陰道下段,所有檢查都已在該院完成,之後才轉到我們醫院。據護理人員了解,轉院之前,黃先生為了確保妻子能夠康復,在該院捐了一大筆錢,希望妻子能得人天福報的庇佑。
由於黃太太的病況未獲控制,在轉到我們醫院之後,我們先為她動了手術,再給予化學治療。棘手的是,手術過程中,又發現黃太太除了子宮內膜癌外,還同時有不同細胞形態的卵巢澄清細胞癌,這是一種較為少見、且抗藥性較高的癌症。
因此,黃太太手術後就在疾病起落之間,經歷了許多次不同的化療,還包括一次腸阻塞嚴重而做了迴腸造口術。
黃太太本身是一位非常配合的病人,對各種治療從不喊苦,一切安排都仰賴丈夫決定。但歷經了多次復發,有一次再住院時,原先的迴腸造口術已無法解除她的腸阻塞,她又腹脹厲害,無法進食,所有的標準化學治療都已嘗試而無效。此時,我們的外科同仁善意地提出了可能須面對的最後抉擇:是否要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若急救已無法延長有品質的生命,是否不再勉強加諸包括氣管插管、人工呼吸器及心臟電擊等急救方式的「DNR」(Do Not Resuscitate)同意書。
就是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溫和的黃先生發怒,他誤解醫生不願再盡力救治黃太太,要求醫療團隊不能放棄。
為了我們所愛,提早做好準備
一身樸素、看來節儉的黃先生,卻替妻子選擇住差額負擔最高的單人病房,要求使用最好的藥物,價以萬計的標靶治療也要求盡量使用。但眼看疾病已到了失控的階段,做為醫療人員就當據實以告,請其預先準備。
然而,我們要怎麼告知真實情況,卻不奪去黃先生的最後一點希望?黃先生心裡一定早已知道疾病的程度,只是期待著奇蹟眷顧,我們何忍逼他提早面對他所不願面對的事實?
我們總對年輕醫師說,讓癌末病人簽署DNR,是為了免於「延長死亡的過程」,因為那些可能十分痛苦的急救過程,並未真正「延長生命」。
但捫心自問,若面對生命最後關卡的重病患者,是我們自己摯愛的親人,我們又能否如此以理性決斷?
誰來決定死亡過程的長短?誰來決定死亡的過程不是生命的一部分?這不只是癌症醫師,更是做為一個人最艱難的考驗,卻也是最深刻的自我學習與靈性成長。
因此,我們都該及早決定,並交代如何面對自己的最後時刻,避免讓我們所愛及愛我們的人,痛苦地處理如此艱難的課題。
一個感謝,讓我流下男兒淚
有一位我照顧六、七年的卵巢癌老太太,去世前她情緒極度不穩,她說,已經知道自己人生到了盡頭,不斷哀求我們:「讓我安樂死,早死早超生。」我們當然做不到。我只有對她說:「我可以給妳安樂。」就是協助她止痛,可以不痛苦。但老太太不能如願,常在病房裡鬧脾氣,最後,仍在「不安樂」中去世。
在老太太疾病的前半段,我們用心照料。她腹水嚴重,一抽水就得抽上一、兩個鐘頭;一般是插管子讓它自己引流,對於不是單一水囊的積水,這樣抽得不乾淨。我則和住院醫師輪流親手抽,十西西、十西西地抽,需要時,常一抽就抽幾千西西的腹水出來。當時老太太對我們的貼心照顧非常感謝,隨著病情惡化,卻開始對醫療人員發脾氣。
在老太太過世後的某天,一位病友特別來找我,告訴我,其實老太太臨終前囑咐,自己去世之後,請她一定要來找我,對我之前給予老太太的長久照顧表達感謝之意。
我對這名病友說,我當然知道老太太鬧脾氣不是她的真心。但這個遲來的感謝,仍讓我不禁在門診室裡流下男兒淚。這就是一名癌症醫師的「收穫」吧。
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
照顧癌末病人,讓我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思考:人到底是什麼?生命到底是什麼?這些病人都是我的人生導師,激發我的思想。
早年,我很滿足於做為一名接生的產科醫師,體驗生命初始的喜悅;現在,我則很珍惜能夠照顧癌症病人,對生命本質與醫者價值,有更深的體悟。
這樣近距離地觀察生命的起落、圓缺,確實給自己很大的成長,使我認知生命的有限、生命的不可控制,以及人對生命的無奈與無力。這些點點滴滴都讓我價值更清明、智慧更豐厚,無論日常生活或人生歷程,更能夠判斷什麼該執著,什麼不該執著;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
轉眼間,在無數人的生命裡歷練、體驗,我也成了一名年過六旬的資深醫師,若還有什麼可以傳遞給年輕後輩的,除了學術醫療上的職能、技巧,便是誠心建議他們,每一天都要注意自己的「靈性成長」。照顧病人時要以同理心、要投入自己的「感情」,如此而能豐富自己的靈性,而能感受到,醫師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