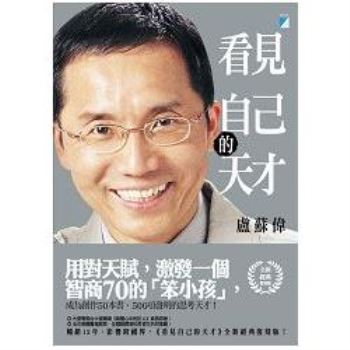(歡喜團聚的過年,八歲的盧蘇偉卻突然開始發高燒,一開始醫生說是感冒,但是爸媽見阿偉連續數日高燒不退,始終昏睡,這才發現情況不對勁……)
〈活著,真好〉
多活一天,就多賺一天!
◎不是植物人,就是重度智障?
除了四處看醫生,草藥、偏方、拜神、收驚、安公媽神位、改大門、移床位,所有能做的、能試的,爸媽都做了、試了。但我的病,卻並沒因爸媽的努力而有任何好轉的跡象,爸媽都慌了!
這段期間,我幾乎都是披著外祖母最珍貴的呢大衣,大衣口袋塞滿了各式護符,但我的發燒狀況仍然時好時壞,有時還會像中邪般地驚恐吼叫。當時的印象裡,我只要一睜開眼睛,就會看見一個紅著臉,長得很高壯的人,穿著一身綠蟒袍,手持大刀,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口,每次看到,我就會大聲地哭叫著:「紅面仔!紅面仔又來了!」
能拜的神都拜了,能求的符都求了,各種草藥、偏方也都吃了,面對我毫無起色的病情,爸媽真的慌了手腳,最後決定帶我去大醫院試試。我們從小村到鎮,最後換了幾趟車,到中壢、桃園。當時桃園地區最大的一間醫院是「聖保祿醫院」,掛了急診,還等了許久才輪到,急診室裡都是焦急的父母帶著發燒的孩子在求診,醫生也都忙翻了;好不容易輪到我看診,醫生見我四肢抽搐、眼睛翻白,便告訴爸媽,我很可能得了當時正在流行的「日本腦膜炎」,要爸媽立刻轉診台大醫院!
根據爸爸事後的描述,到了台大醫院以後,醫生先替我退燒及做了一些初步的診斷與處理,足足等了三天,才被送進病房,而且就如聖保祿醫生的診斷,是腦膜炎沒錯。台大的醫生說,因為我的病情被延誤了太久,即使有幸救活了,很可能會成為植物人或是重度智障,要爸媽心裡有所準備。
當時對國語不熟的媽媽,根本弄不清楚什麼是「植物人」,就用台語大聲地對醫生說:「是人,不管什麼人都不要緊,不要是鬼就好了!」◎這孩子最多只能活三年……
由於家裡還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顧,爸爸便要媽媽先回家,自己則找來礦場的至交好友水源叔一起輪流看護我。每天,除了吃藥就是打針,折騰了一星期以後,我終於醒來,不過,醒來的我不但不會講話,連爸爸都不認識,而且醒來不久,眼睛就翻白又沉沉地昏睡過去。爸爸看到這種狀況,更是焦急,不過醫生一再地告訴爸爸,我的情況已比預期樂觀,神經知覺都尚完好,只是意識不清而已,爸爸才放下心來。
當時沒有電話,當然也不可能寄信,因此我清醒的消息是水源叔坐了三、四個小時的車,回家告訴外祖母和媽媽的。
水源叔後來告訴我,媽媽一聽說我醒了,淚眼盈眶地跪地拜神。後來我常想,我的命或許是我媽求神求來的吧!
在台大住了三個星期,不知做了多少檢查,抽過多少次脊髓液化驗,才得以出院。在我出院時,醫生告訴爸爸:「這個孩子能活就好,不要期待他學什麼,而且最多也只能活三年!」
因為醫師認為延誤了救治的關鍵時間,腦部分因發炎化膿壞死,也許一輩子不會講話,或不會自理生活,甚至於大小便都要人照顧,讀書、上學就不用急,看情況再說。
但我看起來很好,眼睛看得見,嘴巴會吃,手腳會靈活地動;大小便原會失禁,後來也會控制。回到家,家人也慢慢都認出來了;又過了沒多久,也會說一些簡單的話了。爸媽根本不認為我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一開始,他們都能包容我喊錯人或講不出物品名稱。像二姊,她根本不管我認不得她,只要我發出聲音,不管是「煮」或「節」,她都認為我在喊她。外祖母也一樣,不分我喊的「媽」是在叫她或是在叫媽媽,我只要說:「媽!」她就感動得抱著我哭,她哭,我也跟著嚎啕大哭,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而哭。◎從這天起,我活的都是賺的!
關於我生病前後的記憶,都是爸媽、二姊轉述的;那段時間的我沒有記憶,也無法思考,更別說有什麼情緒了,整個人就像是中空了一樣,每天只會哭。我一哭,爸媽、外祖母,甚至全家人就會緊張起來,不是哄我吃就是哄我睡,再不然就是帶我去散步。
那時,我只要在睡覺,媽媽除了會幫我拉拉被子,還會用手指,放在我的鼻孔前,看看我是不是還在呼吸;這個習慣一直到現在都還改不過來。我的孩子因為不了解阿媽在幹嘛,有時也會有樣學樣,一看到我在睡覺,就會用手指來摸摸我的鼻子,有幾次不小心把我吵醒了,我問他做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學阿媽的動作而已。」
其實,在我生病以前,我就已經備受寵愛了;我生病之後,大人們更是對我呵護備至。那段時間,只要我和兄弟姊妹吵架,媽媽都會把他們拉到一旁,唸上好一陣子。記得有一次,媽媽又把大妹拉到一旁,不知媽說了什麼,只聽到大妹大聲說:「媽,免驚啦!哥會死老早就死了,不會活到現在。」
後來才知道媽媽是對妹妹說:「不要和妳哥吵架,妳哥隨時都會死!」
原來爸媽把醫生說我最多只能活三年的囑咐一直放在心上,因此,當我出院滿三年的那一天,我媽對我說:「從這天起算,你活的都是賺的!」
多活一天,就多賺一天!原來幸福也可以如此簡單。這樣算來,我轉眼間也賺了幾十年的生命經驗,不管這經歷是什麼,反正是多的、是上天免費送的,就不必太過計較了。
對於神明,我從不敢說我不信,因為神明的存在,爸媽在我生病無助時,找到了依靠,我怎能病好了,就忘了祂曾安過我父母的心,讓他們能懷著希望陪我走過那漫漫長夜呢?
活著真好!還好,沒在那時死掉,否則,我就沒機會經歷生命的許多苦痛、挫敗,嚐到甘美的果實。活著真好!不管未來的生命是何等遭遇,我會展開雙臂,迎接它們,與它們欣然相遇!
活著,真好!
我賺了幾十年,夠了!但如果再多給我幾十年,我會更豐盛,讚頌生命──活著,真好!【看見自己:珍視每個片刻】
在我們眼裡或別人眼裡,不論我們是好或壞,只要我們活著,沒有比擁有生命更珍貴的了,已經有了世界最珍貴的寶,其他的擁有,都只能算是點綴而已。
你或許也知道差點死掉的經驗,其實活著的每一片刻,都可能和死亡擦身而過,只是大部分我們不知道而已。當我們有機會慶祝歷劫歸來,或死而復生,我們才了解生命的珍貴;了解了生命的珍貴,其他值得我們計較的事物就不多了。
每一片刻,都值得慶祝,不要因為它來得容易而輕忽,慶祝它吧!活著,真好!
〈不會看時鐘的小孩〉
是誰沒事發明了時鐘,讓這世界如此緊張呢?
◎慢慢來,不要急
回到家之後的我彷彿是個風吹就會破的玻璃娃娃般,尤其是外祖母和媽媽對我,可說是小心極了,她們幾乎不准我出門,大部分的時間只能待在家裡;好不容易偶爾被允許去礦場的福利社買點糖果,也得有人陪著。甚至以前的鄰居、玩伴來看我,媽媽、二姊都要求我說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以及和我玩過什麼,就像我還是個小嬰兒般開始重新學話。
這樣當了一、兩個月的病人,我體力漸漸恢復,慢慢會講一些簡單的對話、處理自己的生活。我白天都一個人和妹妹玩,直到我看到別人去上學,好像很快樂,我開始想去上學;二姊發現我似乎很想上學,便拿以前我讀過的書給我看,但是不論二姊怎麼教,我怎麼看,就是什麼都記不起來,連簡單的數字也都沒有印象。二姊似乎發現了我的問題,便跑去和爸爸說,然而爸爸倒是樂觀得很,不但一點都不擔心,還要二姊慢慢來,不要急。◎重返學校的擔憂
又休息了一個星期,爸媽決定週一讓我回學校。我知道了以後,高興得不得了,但爸爸可沒有感染到我的高興。他看著替我準備好的制服及書包,臉色沉了下來,要上學,什麼都不會怎麼辦?怎麼跟得上?而外祖母及媽媽的煩惱也不比爸爸少,「阿偉現在這樣,不知同學會不會欺負他?學校離家又那麼遠,若暈倒誰來救他?」
爸爸把所有問題,逐一地思考及做了安排。
星期一,爸爸親自帶我去學校。進校門前,先至校門口前的衛生所拜訪「蕃仔醫生」,謝謝他之前的醫治及照顧,並將台大醫生的囑咐詳細地告訴他,希望他在我有緊急狀況時,能先給我治療,醫生親切地答應,並要爸爸安心。之後,爸爸又帶我去找他在附近開麵店的朋友──阿坤伯,拜託他每天中午為我準備午餐,並做學校的緊急聯絡人,一切交代好了,才帶我進學校。
◎我連名字都忘了怎麼寫
因為我生病的關係,在學校裡我享有許多特別的待遇,作業比別人少,照顧卻比別人多。印象比較深的是在二年級下學期的算術課,每次上課,老師都要搬出教學用的木板大時鐘,她把時鐘上的指針撥來撥去,同學就齊聲回答幾點幾分,然後老師開始教時間加減。一連幾個禮拜下來,課堂上都在教大家看時鐘,老師也沒發現我有什麼異樣,直到有一天,老師要大家收起課本,做筆記測驗,老師特別走到我身邊,我假裝很認真在寫,她看了我的測驗紙嚇一跳:「盧蘇偉,你不會寫你的名字?」
因為我只寫了個開頭,中間歪歪斜斜的湊不齊,下面就沒了!
老師又問:「時鐘你會不會看?」
我有點害怕地點點頭。
「真的會嗎?」
我又嚇得搖搖頭。
老師走到時鐘教具旁,隨便一撥問我:「這是幾點幾分?」
「1、2、3、4……」
「盧蘇偉,這些數字你會嗎?」
老師有點急了,聲音也提高了。
「會!我會!」我怕老師生氣,很快地回答老師。
老師用手裡的藤條指著3,我心裡就默默數著:1、2、3……
「3!」
老師又指了個9,我遲疑了很久,不確定地說:「8?9!」
老師似乎明白了怎麼回事。「盧蘇偉,你坐下。」
這天起,我的國語作業,不再和同學一樣,老師要我寫自己的名字十遍。下午下了課,她要住在我家附近的同學去通知我爸爸來接我。她把我留了下來,拿了數字的字卡,從0至9逐一地教;還好,在回學校前,二姊已經預先教我了,除了6和9偶會弄錯,十個數字,差不多都會了,1、2就比較容易,就1和2嘛!頁數 6/7
高老師接下來教分針,她用5、10、15、20、25、30、35……逐一地教,這真的有點複雜。
「1是五分,2是十分,3是十五分……」
老師還是很有耐心地教,我也很認真想學會,但不知為什麼就不能專心。
「盧蘇偉,你要認真,什麼都不會不打緊,但至少要會自己的姓名,要會看時鐘。認真地學,知道嗎?」
老師收斂起笑容,我頭皮一直麻起來,頭腦不知為什麼就一陣、一陣的空白,我很想哭,但我不敢。
老師接下來教我看時間。一開始,她撥的都是整點,我沒多久就學會了;半點(三十分鐘),也還算容易。但接下來老師撥的時間,不是整點,也不是半點(三十分鐘),我開始緊張了,只能勉強看短針。
「七點……七點……」
「盧蘇偉,如果一時記不起來就從頭開始算,5、10、15、20……這是多少?」
「二十……五!」
「很好,就這樣!」
老師手又撥時鐘,我眼睛偷偷望著外面,真希望爸爸趕快來!
「幾點?幾分?」
「八點……」
「來,跟老師唸,5、10、15、20……45。所以是?」
「四十五分!」
「這樣會了嗎?老師現在不講,你試試看。」
老師手又撥時鐘的指針,問:「幾點?幾分?」
「六點……」
老師用手比五。
「五分!」
「五你個頭啦!5、10、15、20、25……六點二十五分啦!」
老師開始沒什麼耐心了。天漸漸暗了,晚霞的紅光映照進了教室,老師的臉,大大的眼睛,輪廓分明的五官,我瞄她一下,再也不敢看她。
◎老師跟我一起哭
天暗了下來,老師打開了裝燈泡的電燈,米黃色的燈光應該會是溫暖的,但不知為什麼,我從腳底板一直冷顫起來,愈來愈沒辦法專心。老師似乎忘記我是生病的小孩,她像平常對其他小朋友的嚴格,用藤條狠狠地抽打課桌。
「專心!我現在開始考你,不會我就打你!」
老師撥了時鐘的指針:「幾點?幾分?」
「八……」
「還在八,這是九點!手伸出來!」
「咻!」打在我手心,痛得我兩手交互搓揉著,痛都還來不及消退,老師又撥動鐘面的指針,「說!幾點?幾分?」
我腦子一片空白,只好從頭默數,遲疑了許久,才心虛地回答:「七點。」
「七點?看清楚!」
「八點。」
「八點?時針是短的那支!」
「一、二、三,三點!」
「幾分?」
「七──七──」
「手伸出來!」又是咻一下!我痛得也管不得老師在講什麼,眼淚再也忍不住地湧了出來!
老師似乎沒要歇手,只是大聲斥責:「學不會,還敢哭!」
我淚眼模糊地看著老師重撥的鐘面。
「幾點?幾分?」
我眼淚不爭氣地湧了出來,搓一搓手,伸了出來,哽咽地說:「我不會──我不會──」
老師氣得把藤條重重地摔在地上,因為力氣太大,藤條彈起來打到講台,我嚇得不敢大力呼吸,低著頭偷偷看老師。
老師氣得跺著腳。「不會!不會!我教了你四個小時,你知不知道?你連時鐘都不會看,以後你怎麼辦?」
老師邊說邊向後退,一不小心撞到椅子,就跌坐在椅子上,竟然哭了起來!
我剛開始被嚇到了,不敢出聲,看到老師趴在課桌上哭,我也忍不住發痛的手,還有一肚子的委屈,開始嚎啕大哭,把緊繃了幾個小時的壓力用力地哭了出來,邊哭邊說:「我又不是故意的!」
也不知哭了多久,沉靜的教室,突然聽見了另一個哭泣,阻塞鼻管的抽泣聲,我和老師同時停住了哭泣,往聲音傳來的門口看去──
只見我爸爸站在門口,不好意思地拿著手帕拭淚、擤鼻涕。老師有些不好意思,馬上展現和藹可親的笑容,走到教室門口迎接爸爸,邊走還一邊擦拭自己的眼淚。
爸爸向老師一再鞠九十度的躬,「老師,謝謝妳為蘇偉的付出。」說著說著,眼淚又湧了出來。
我的心突然輕鬆起來,我知道我得救了!
爸爸和老師在說話,我也沒什麼興趣,眼睛盯著時鐘的板面,看著長、短的兩個指針。
「幾點幾分?說!」
「幾點幾分?」
「幾點?」
我自問自答,但頭腦卻完全沒有回應!
在生命的旅程裡,我常看著時鐘發呆。我真不懂,是誰沒事發明了時鐘,讓這世界如此緊張呢?
【看見自己:知道自己會什麼】
在生命的長遠旅程,我一直在乎自己不會拼音、不會四則運算、不會英文、不會樂譜、不會唱歌、不會……
直到好大了,才放心自己不會什麼根本是不要緊的事,要緊的是,知道自己會什麼!只要會一樣全世界沒有人會的,或少有人知道的技能就夠了!
你會什麼?你真的知道嗎?
〈活著,真好〉
多活一天,就多賺一天!
◎不是植物人,就是重度智障?
除了四處看醫生,草藥、偏方、拜神、收驚、安公媽神位、改大門、移床位,所有能做的、能試的,爸媽都做了、試了。但我的病,卻並沒因爸媽的努力而有任何好轉的跡象,爸媽都慌了!
這段期間,我幾乎都是披著外祖母最珍貴的呢大衣,大衣口袋塞滿了各式護符,但我的發燒狀況仍然時好時壞,有時還會像中邪般地驚恐吼叫。當時的印象裡,我只要一睜開眼睛,就會看見一個紅著臉,長得很高壯的人,穿著一身綠蟒袍,手持大刀,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口,每次看到,我就會大聲地哭叫著:「紅面仔!紅面仔又來了!」
能拜的神都拜了,能求的符都求了,各種草藥、偏方也都吃了,面對我毫無起色的病情,爸媽真的慌了手腳,最後決定帶我去大醫院試試。我們從小村到鎮,最後換了幾趟車,到中壢、桃園。當時桃園地區最大的一間醫院是「聖保祿醫院」,掛了急診,還等了許久才輪到,急診室裡都是焦急的父母帶著發燒的孩子在求診,醫生也都忙翻了;好不容易輪到我看診,醫生見我四肢抽搐、眼睛翻白,便告訴爸媽,我很可能得了當時正在流行的「日本腦膜炎」,要爸媽立刻轉診台大醫院!
根據爸爸事後的描述,到了台大醫院以後,醫生先替我退燒及做了一些初步的診斷與處理,足足等了三天,才被送進病房,而且就如聖保祿醫生的診斷,是腦膜炎沒錯。台大的醫生說,因為我的病情被延誤了太久,即使有幸救活了,很可能會成為植物人或是重度智障,要爸媽心裡有所準備。
當時對國語不熟的媽媽,根本弄不清楚什麼是「植物人」,就用台語大聲地對醫生說:「是人,不管什麼人都不要緊,不要是鬼就好了!」◎這孩子最多只能活三年……
由於家裡還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顧,爸爸便要媽媽先回家,自己則找來礦場的至交好友水源叔一起輪流看護我。每天,除了吃藥就是打針,折騰了一星期以後,我終於醒來,不過,醒來的我不但不會講話,連爸爸都不認識,而且醒來不久,眼睛就翻白又沉沉地昏睡過去。爸爸看到這種狀況,更是焦急,不過醫生一再地告訴爸爸,我的情況已比預期樂觀,神經知覺都尚完好,只是意識不清而已,爸爸才放下心來。
當時沒有電話,當然也不可能寄信,因此我清醒的消息是水源叔坐了三、四個小時的車,回家告訴外祖母和媽媽的。
水源叔後來告訴我,媽媽一聽說我醒了,淚眼盈眶地跪地拜神。後來我常想,我的命或許是我媽求神求來的吧!
在台大住了三個星期,不知做了多少檢查,抽過多少次脊髓液化驗,才得以出院。在我出院時,醫生告訴爸爸:「這個孩子能活就好,不要期待他學什麼,而且最多也只能活三年!」
因為醫師認為延誤了救治的關鍵時間,腦部分因發炎化膿壞死,也許一輩子不會講話,或不會自理生活,甚至於大小便都要人照顧,讀書、上學就不用急,看情況再說。
但我看起來很好,眼睛看得見,嘴巴會吃,手腳會靈活地動;大小便原會失禁,後來也會控制。回到家,家人也慢慢都認出來了;又過了沒多久,也會說一些簡單的話了。爸媽根本不認為我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一開始,他們都能包容我喊錯人或講不出物品名稱。像二姊,她根本不管我認不得她,只要我發出聲音,不管是「煮」或「節」,她都認為我在喊她。外祖母也一樣,不分我喊的「媽」是在叫她或是在叫媽媽,我只要說:「媽!」她就感動得抱著我哭,她哭,我也跟著嚎啕大哭,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而哭。◎從這天起,我活的都是賺的!
關於我生病前後的記憶,都是爸媽、二姊轉述的;那段時間的我沒有記憶,也無法思考,更別說有什麼情緒了,整個人就像是中空了一樣,每天只會哭。我一哭,爸媽、外祖母,甚至全家人就會緊張起來,不是哄我吃就是哄我睡,再不然就是帶我去散步。
那時,我只要在睡覺,媽媽除了會幫我拉拉被子,還會用手指,放在我的鼻孔前,看看我是不是還在呼吸;這個習慣一直到現在都還改不過來。我的孩子因為不了解阿媽在幹嘛,有時也會有樣學樣,一看到我在睡覺,就會用手指來摸摸我的鼻子,有幾次不小心把我吵醒了,我問他做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學阿媽的動作而已。」
其實,在我生病以前,我就已經備受寵愛了;我生病之後,大人們更是對我呵護備至。那段時間,只要我和兄弟姊妹吵架,媽媽都會把他們拉到一旁,唸上好一陣子。記得有一次,媽媽又把大妹拉到一旁,不知媽說了什麼,只聽到大妹大聲說:「媽,免驚啦!哥會死老早就死了,不會活到現在。」
後來才知道媽媽是對妹妹說:「不要和妳哥吵架,妳哥隨時都會死!」
原來爸媽把醫生說我最多只能活三年的囑咐一直放在心上,因此,當我出院滿三年的那一天,我媽對我說:「從這天起算,你活的都是賺的!」
多活一天,就多賺一天!原來幸福也可以如此簡單。這樣算來,我轉眼間也賺了幾十年的生命經驗,不管這經歷是什麼,反正是多的、是上天免費送的,就不必太過計較了。
對於神明,我從不敢說我不信,因為神明的存在,爸媽在我生病無助時,找到了依靠,我怎能病好了,就忘了祂曾安過我父母的心,讓他們能懷著希望陪我走過那漫漫長夜呢?
活著真好!還好,沒在那時死掉,否則,我就沒機會經歷生命的許多苦痛、挫敗,嚐到甘美的果實。活著真好!不管未來的生命是何等遭遇,我會展開雙臂,迎接它們,與它們欣然相遇!
活著,真好!
我賺了幾十年,夠了!但如果再多給我幾十年,我會更豐盛,讚頌生命──活著,真好!【看見自己:珍視每個片刻】
在我們眼裡或別人眼裡,不論我們是好或壞,只要我們活著,沒有比擁有生命更珍貴的了,已經有了世界最珍貴的寶,其他的擁有,都只能算是點綴而已。
你或許也知道差點死掉的經驗,其實活著的每一片刻,都可能和死亡擦身而過,只是大部分我們不知道而已。當我們有機會慶祝歷劫歸來,或死而復生,我們才了解生命的珍貴;了解了生命的珍貴,其他值得我們計較的事物就不多了。
每一片刻,都值得慶祝,不要因為它來得容易而輕忽,慶祝它吧!活著,真好!
〈不會看時鐘的小孩〉
是誰沒事發明了時鐘,讓這世界如此緊張呢?
◎慢慢來,不要急
回到家之後的我彷彿是個風吹就會破的玻璃娃娃般,尤其是外祖母和媽媽對我,可說是小心極了,她們幾乎不准我出門,大部分的時間只能待在家裡;好不容易偶爾被允許去礦場的福利社買點糖果,也得有人陪著。甚至以前的鄰居、玩伴來看我,媽媽、二姊都要求我說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以及和我玩過什麼,就像我還是個小嬰兒般開始重新學話。
這樣當了一、兩個月的病人,我體力漸漸恢復,慢慢會講一些簡單的對話、處理自己的生活。我白天都一個人和妹妹玩,直到我看到別人去上學,好像很快樂,我開始想去上學;二姊發現我似乎很想上學,便拿以前我讀過的書給我看,但是不論二姊怎麼教,我怎麼看,就是什麼都記不起來,連簡單的數字也都沒有印象。二姊似乎發現了我的問題,便跑去和爸爸說,然而爸爸倒是樂觀得很,不但一點都不擔心,還要二姊慢慢來,不要急。◎重返學校的擔憂
又休息了一個星期,爸媽決定週一讓我回學校。我知道了以後,高興得不得了,但爸爸可沒有感染到我的高興。他看著替我準備好的制服及書包,臉色沉了下來,要上學,什麼都不會怎麼辦?怎麼跟得上?而外祖母及媽媽的煩惱也不比爸爸少,「阿偉現在這樣,不知同學會不會欺負他?學校離家又那麼遠,若暈倒誰來救他?」
爸爸把所有問題,逐一地思考及做了安排。
星期一,爸爸親自帶我去學校。進校門前,先至校門口前的衛生所拜訪「蕃仔醫生」,謝謝他之前的醫治及照顧,並將台大醫生的囑咐詳細地告訴他,希望他在我有緊急狀況時,能先給我治療,醫生親切地答應,並要爸爸安心。之後,爸爸又帶我去找他在附近開麵店的朋友──阿坤伯,拜託他每天中午為我準備午餐,並做學校的緊急聯絡人,一切交代好了,才帶我進學校。
◎我連名字都忘了怎麼寫
因為我生病的關係,在學校裡我享有許多特別的待遇,作業比別人少,照顧卻比別人多。印象比較深的是在二年級下學期的算術課,每次上課,老師都要搬出教學用的木板大時鐘,她把時鐘上的指針撥來撥去,同學就齊聲回答幾點幾分,然後老師開始教時間加減。一連幾個禮拜下來,課堂上都在教大家看時鐘,老師也沒發現我有什麼異樣,直到有一天,老師要大家收起課本,做筆記測驗,老師特別走到我身邊,我假裝很認真在寫,她看了我的測驗紙嚇一跳:「盧蘇偉,你不會寫你的名字?」
因為我只寫了個開頭,中間歪歪斜斜的湊不齊,下面就沒了!
老師又問:「時鐘你會不會看?」
我有點害怕地點點頭。
「真的會嗎?」
我又嚇得搖搖頭。
老師走到時鐘教具旁,隨便一撥問我:「這是幾點幾分?」
「1、2、3、4……」
「盧蘇偉,這些數字你會嗎?」
老師有點急了,聲音也提高了。
「會!我會!」我怕老師生氣,很快地回答老師。
老師用手裡的藤條指著3,我心裡就默默數著:1、2、3……
「3!」
老師又指了個9,我遲疑了很久,不確定地說:「8?9!」
老師似乎明白了怎麼回事。「盧蘇偉,你坐下。」
這天起,我的國語作業,不再和同學一樣,老師要我寫自己的名字十遍。下午下了課,她要住在我家附近的同學去通知我爸爸來接我。她把我留了下來,拿了數字的字卡,從0至9逐一地教;還好,在回學校前,二姊已經預先教我了,除了6和9偶會弄錯,十個數字,差不多都會了,1、2就比較容易,就1和2嘛!頁數 6/7
高老師接下來教分針,她用5、10、15、20、25、30、35……逐一地教,這真的有點複雜。
「1是五分,2是十分,3是十五分……」
老師還是很有耐心地教,我也很認真想學會,但不知為什麼就不能專心。
「盧蘇偉,你要認真,什麼都不會不打緊,但至少要會自己的姓名,要會看時鐘。認真地學,知道嗎?」
老師收斂起笑容,我頭皮一直麻起來,頭腦不知為什麼就一陣、一陣的空白,我很想哭,但我不敢。
老師接下來教我看時間。一開始,她撥的都是整點,我沒多久就學會了;半點(三十分鐘),也還算容易。但接下來老師撥的時間,不是整點,也不是半點(三十分鐘),我開始緊張了,只能勉強看短針。
「七點……七點……」
「盧蘇偉,如果一時記不起來就從頭開始算,5、10、15、20……這是多少?」
「二十……五!」
「很好,就這樣!」
老師手又撥時鐘,我眼睛偷偷望著外面,真希望爸爸趕快來!
「幾點?幾分?」
「八點……」
「來,跟老師唸,5、10、15、20……45。所以是?」
「四十五分!」
「這樣會了嗎?老師現在不講,你試試看。」
老師手又撥時鐘的指針,問:「幾點?幾分?」
「六點……」
老師用手比五。
「五分!」
「五你個頭啦!5、10、15、20、25……六點二十五分啦!」
老師開始沒什麼耐心了。天漸漸暗了,晚霞的紅光映照進了教室,老師的臉,大大的眼睛,輪廓分明的五官,我瞄她一下,再也不敢看她。
◎老師跟我一起哭
天暗了下來,老師打開了裝燈泡的電燈,米黃色的燈光應該會是溫暖的,但不知為什麼,我從腳底板一直冷顫起來,愈來愈沒辦法專心。老師似乎忘記我是生病的小孩,她像平常對其他小朋友的嚴格,用藤條狠狠地抽打課桌。
「專心!我現在開始考你,不會我就打你!」
老師撥了時鐘的指針:「幾點?幾分?」
「八……」
「還在八,這是九點!手伸出來!」
「咻!」打在我手心,痛得我兩手交互搓揉著,痛都還來不及消退,老師又撥動鐘面的指針,「說!幾點?幾分?」
我腦子一片空白,只好從頭默數,遲疑了許久,才心虛地回答:「七點。」
「七點?看清楚!」
「八點。」
「八點?時針是短的那支!」
「一、二、三,三點!」
「幾分?」
「七──七──」
「手伸出來!」又是咻一下!我痛得也管不得老師在講什麼,眼淚再也忍不住地湧了出來!
老師似乎沒要歇手,只是大聲斥責:「學不會,還敢哭!」
我淚眼模糊地看著老師重撥的鐘面。
「幾點?幾分?」
我眼淚不爭氣地湧了出來,搓一搓手,伸了出來,哽咽地說:「我不會──我不會──」
老師氣得把藤條重重地摔在地上,因為力氣太大,藤條彈起來打到講台,我嚇得不敢大力呼吸,低著頭偷偷看老師。
老師氣得跺著腳。「不會!不會!我教了你四個小時,你知不知道?你連時鐘都不會看,以後你怎麼辦?」
老師邊說邊向後退,一不小心撞到椅子,就跌坐在椅子上,竟然哭了起來!
我剛開始被嚇到了,不敢出聲,看到老師趴在課桌上哭,我也忍不住發痛的手,還有一肚子的委屈,開始嚎啕大哭,把緊繃了幾個小時的壓力用力地哭了出來,邊哭邊說:「我又不是故意的!」
也不知哭了多久,沉靜的教室,突然聽見了另一個哭泣,阻塞鼻管的抽泣聲,我和老師同時停住了哭泣,往聲音傳來的門口看去──
只見我爸爸站在門口,不好意思地拿著手帕拭淚、擤鼻涕。老師有些不好意思,馬上展現和藹可親的笑容,走到教室門口迎接爸爸,邊走還一邊擦拭自己的眼淚。
爸爸向老師一再鞠九十度的躬,「老師,謝謝妳為蘇偉的付出。」說著說著,眼淚又湧了出來。
我的心突然輕鬆起來,我知道我得救了!
爸爸和老師在說話,我也沒什麼興趣,眼睛盯著時鐘的板面,看著長、短的兩個指針。
「幾點幾分?說!」
「幾點幾分?」
「幾點?」
我自問自答,但頭腦卻完全沒有回應!
在生命的旅程裡,我常看著時鐘發呆。我真不懂,是誰沒事發明了時鐘,讓這世界如此緊張呢?
【看見自己:知道自己會什麼】
在生命的長遠旅程,我一直在乎自己不會拼音、不會四則運算、不會英文、不會樂譜、不會唱歌、不會……
直到好大了,才放心自己不會什麼根本是不要緊的事,要緊的是,知道自己會什麼!只要會一樣全世界沒有人會的,或少有人知道的技能就夠了!
你會什麼?你真的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