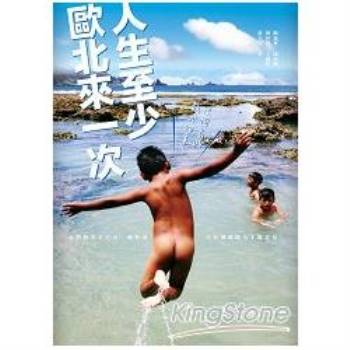真正的野蠻,
是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傲慢
布農青年的歌聲
花蓮萬榮鄉馬遠部落
「看著你的腳步你踩過的泥土,這崎嶇的山路走得好辛苦,你說過的話我何時才能領悟,再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溫度……dan na ngaus as zakuan mudadan, dis uni zaku pisihal nalahaiban……」
在政大金弦獎上,第一次聽到這首勇奪三項大獎的歌曲《腳印》,結合布農族語的創作,令人深深迷戀上這種從「土地長出來」的族群文化。
創作人馬詠恩是一名原住民獨立音樂人,他透過音樂、帶人走入部落,同時分享自己的族群與家鄉的故事,讓更多人藉由不同的方式認識布農族。他用他最擅長的方式,讓別人看見了他的族群和故鄉。
而我真的看見了。
就因為這樣,我跟著詠恩走入花蓮萬榮鄉的馬遠部落。
抵達馬遠部落的那個晚上,布農族獵人帶領我們,搭乘小貨車,行駛在崎嶇到讓人無法想像的山路,引擎聲低沉地嘶吼著,爬得有些吃力的小貨車不時因坡度太陡熄火,還數度朝車後方的懸崖倒退,驚險萬分,但獵人們面不改色,重新發動後的小貨車依舊賣力地爬著坡。
空氣中充斥著每道呼吸都不能懈怠的緊張感。
約莫一個鐘頭後,在海拔六百公尺處飄起了雨,我們的視線逐漸被大霧所遮蔽,伸手不見五指。「下車吧,從這裡開始我們得用走的,在這之前,我們要先告訴祖靈,我們來了。」獵人們開始準備獵前需要的用具。
米酒、獵槍、彈藥,一群布農族青年肩靠著肩,全部圍在置於木頭上的獵槍前,開始唱起了「獵前祭槍歌」。
布農青年的歌聲與自然的聲音手拉著手融入了彼此,如協奏曲般悠揚共鳴,一股敬畏之心油然升起,所有人似不自覺放輕了呼吸,可以感受到氣氛愈發肅穆、神聖,我們的神情也凝重了起來,深怕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布農族人獵前的禁忌。
「我們是要祈求山神與祖靈們保護我們得以平安、豐盛,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們賜予的,要抱著感恩的心,絕對不能開玩笑。」詠恩告訴我他們所進行的一切儀式最重要的核心意義。
儀式結束後,我們繼續朝山林深處走,耳邊傳來許多動物的聲音,「你聽到牠們的叫聲就不用去找了,因為那是牠們聞到氣味,相互警戒的方式,」獵人們沿途依據各類植物、地形、動物糞便、水源位置,繼續追蹤動物可能出現的地方。
在海拔一千多公尺處,已經沒有所謂「正常的路」可以行走,只能跟著獵人曾經踏過的泥土,確保你的下一步安然無恙,「很多人都以為我們人類佔了優勢,其實動物也在引誘你掉入陷阱,一失足將跌落山谷,沒有誰才高人一等,只有誰更瞭解這塊土地。所有保護自己的技能都是老獵人們代代相傳下來的智慧,一切的東西都在他們腦海中,你不去挖,以後就全都消失了。」
遠處忽然閃現兩顆圓球狀的淡黃色反光,正當我想看清楚那是什麼東西時,「砰!」只見獵人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開槍射擊。
獵人們趨步向前,手起刀落,迅捷地割掉了動物的左耳,留在旁邊的草叢裡,同時用母語對祖靈說:「這是獻給祢們的,一切都是祢們的賜予。」
年紀較輕的我,幫忙背起獵物返回獵寮聽獵人說著這片山林的故事,「上山最重要的是安全,獵不獵得到是運氣,絕不能強求。肉,本來就不是一個應該容易取得的東西。」獵人跟我們分享他們數百年來與自然共生的謙卑。
此時太陽已悄悄地升起,我們與晨光伸出的手一同肢解獵物,內心並不感到害怕,反而異常平靜,全身上下、發自內心充滿感恩之情。獵人拿起碗,將動物體內殘留的血液舀起,倒進米酒瓶中混合,「喝吧,一點一滴都沒有浪費的理由」,我接過酒瓶大口喝下,那是對牠賜予我們飽足得以延續生命致上的最高敬意。
多數人一邊吃著美味的雞、豬、牛、魚等各式生命,同時批判著狩獵的「野蠻」與「殘忍」。似乎是認為,我們食用的一切,「本來」就是飼養來成為肉品的生命,「理所當然」要成為我們的食物,而狩獵那些不在我們食用設定分類下的生命,才是人們眼中的野蠻。
相較之下,真正的野蠻,似乎是那些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傲慢。被需要的愛,
才是愛孩子的願望
台11線海岸公路
那天在台東碰上了調皮的孩子,它的名字叫太陽,在無拘無束的藍天裡玩著捉迷藏;沿著台11線前進,溫柔的海洋濺起浪花,金黃色的暖陽與白浪在擋風玻璃上盡情玩耍。
天空與梯田連成一線,從梯田裡的水看著天上的鳥,如顛倒世界一般,我們被海天包覆著。
世界緊緊地用土地環繞著我們,擁抱,很真實。
在這被稱作台灣最美的海岸,我們碰上了推動有機農業的孫大姐,吃著她自製的白吐司,聊起了關於海岸線上的故事。
「很多人為了展現他們關懷偏鄉地區孩童的處境,提供了非常多的物資。為什麼?因為「給物資」是最簡單又快速的方式。然後,孩子們養成了伸手就可以獲得的習慣,這些愛心物資,改變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創造力與想像……。」孫大姐無奈地說著。
「其實我不是很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孫大姐又遞上了一片白吐司,「這樣好了,我跟你說一個例子。某大企業,為了彰顯他們的豪氣與關懷,來到我們這裡,讓孩子們拿出紙跟筆,寫下他們想要的物品;孩子們開心地寫下許多願望,例如和人一樣大的絨毛玩偶、知名品牌摺疊腳踏車、以及各式各類的玩具……,當然,企業主說到做到,讓所有的孩子心想事成。禮物送來那天,孩子們興高采烈地拿著禮物說:『沒想到真的會送給我們耶,早知道我就寫貴一點的,如果是寫電腦、車子……更高級的東西就好了,下次一定要聰明一點。』聽了我當下心都涼了一半,漸漸地,孩子不再到田地裡玩耍,不再徜徉在美麗的大自然……。以前的孩子,就算只是簡單的竹片,甚至在小樹林都能夠玩上一整天,這是一種透過想像和創造,玩出屬於自己童年的遊戲,不像現在,孩子們天天和那些『愛心物資』膩在一塊。」
我瞪大眼睛反覆思考孫大姐這段話,繼續咬著我的白土司。
再跟你說一個例子。「企業因為所謂的愛心,贊助某幾間小學每天的三餐,孩子們都在學校用餐,不過說真的,也許有些家庭很需要,但其實就我瞭解部落的現況,其實食物是很充裕的,儘管粗茶淡飯了些,但營養還是足夠的;更重要的是,這邊隔代教養居多,上上一代與孫子間的互動時間已經不多,吃飯是最棒的相處時光,連這麼一個小小的幸福,都被企業以『不一定真正需要的』供餐所剝奪了。同時,孩子的胃口被愈養愈大,早餐不是某知名速食連鎖的早餐不吃(因為某企業說從部落到知名連鎖速食店開車要兩小時,能吃到很難得)。這樣,真的是幫助嗎?」
「孫大姐,究竟這裡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我們這個鄉鎮,一座游泳池都沒有,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這裡幾乎都是阿美族的孩子,阿美族的海是冰箱,他們得靠海生存。但如同剛剛提到的,隔代教養!青壯年都到外地討生活,阿公阿嬤沒有體力帶孩子到海邊玩耍,更別說是教孩子游泳了,可以想像嗎?沿海的國小學童竟然超過九成是旱鴨子,這已經不是不會游泳這麼簡單,而是文化、某種生活方式無法被傳承的重要警訊!」
「教育始終是我們最缺乏的,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活動,需要的是長期的人力資源。如果資源能夠提供給有心回到部落的青年,長期耕耘,才是真正對當地有所幫助,原住民的問題需要原住民自己才能解決。」
強勢的愛心,是愛嗎?
我不禁開始思考,究竟我們給予的,是他們真正需要的,還是我們「以為」他們真正需要的呢?從我們對朋友、對長輩、另一半、對家人……,以至我們和環境,以至人類和萬物之間。
如果沒有花時間瞭解當地或者某族群的需求,只是自我感覺良好地伸出「援手」,不僅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甚至只是一次次的資源浪費。
被需要的愛,才是愛。不要輕易說愛我,
請在你真心愛我以後
聽古老的住民之歌
烏來福山泰雅部落
因緣際會,走進了烏來福山部落,這是泰雅族的村落。
沿著山路蜿蜒而上,空氣愈來愈清新,景色由灰轉綠,自然的聲音如交響樂般美妙動聽:蟲聲、鳥鳴、溪水與瀑布聲,還有人的聲音。
「從這頭到那頭的山,都是我們的獵場。」我看到遠方非常非常古老的吊橋上,走著一對父子。
「 你看他背著竹籃,還有他身上的配備,那就是要去打獵的,後頭跟著的是他的兒子,小學四年級!他不是來跟著爸爸在山裡『拿東西』的,而是要學習拿東西的方法——追蹤動物留下的線索,辨識樹皮被山豬磨出痕跡的高度,判斷是幾百斤的山豬或是小豬;認識野菜和野生水果的種類,好讓這段路途中能夠有東西充飢;學會在山中的夜裡如何不會被凍死……,更重要的是,該用什麼樣的方法與態度來面對自然」,泰雅獵人緩緩地說著。
「長輩們從小就訓誡我們,必須對得到的一切心懷感恩,拿需要的就好了,絕對不要貪心,如果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沒有留下東西給後代,那孩子們不就會挨餓了嗎?我們原住民什麼都不怕,最怕的是漢族,只要讓他們知道某種東西有價值,隔天,那些東西就會全部不見了,根本就是『屠殺』……。希望我這樣說你不要生氣,但我真的感到害怕。
「牧師啊,滿多人認為原住民是弱勢族群,需要協助改善生活的環境,你認為呢?」
「其實,我們要的不多,只要給我們一個能以自己方式生活的空間,就足夠了。早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前,我們也沒有餓死,為什麼我們現在就需要人幫助呢?用漢人的生存方式來教育我們,就像是把魚養在山上,那是截然不同的啊。」
我們似乎總是將自己的觀點加諸在不同的文化與族群之上。
「你們都說想要解決我們的問題,可以請你們先來聽我們說故事嗎?」泰雅獵人悠然地唱起了泰雅古調。
活著,不只有一種方式;
每一個族群,都有他們的故事。
不要輕易說愛我,請在你真心愛我以後。大自然縱然可怕,
人類的驕傲也不遑多讓
達悟男人對海的敬畏
在蘭嶼堵羊的路上
上島不到半小時,我就上了第一堂課;
第一天,這塊土地為我重新上了一堂自然課。
小女孩緊緊牽著我的手,「哥哥,羊是我們這裡的紅綠燈喔!在路中間的時候是紅燈,走了之後就是綠燈了。」
蘭嶼的路上時常會「堵羊」,不堵都難。從羊群的自在,即可窺知達悟人對世界萬物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這裡的山羊不太怕人耶,人走到旁邊了還在吃草,我去澎湖七美的時候,那裡的羊遠在五十公尺之外就會開始警戒,再接近一點就會逃走。」
「山羊?我們這裡沒有山羊啊,那是我們養的啦,不是山羊喔。」老人家看著我疑惑地說。
一般我們所認知的山羊,是學者們依據牠的居住地或其他條件,方便品種的分類為物種命名,但對於達悟人來說,整塊土地都是羊隻與動物們共享的,因為他們不只住在山裡,所以羊就是羊,不是山羊。
除此之外,你還可以在島上隨處遇見慵懶地曬著太陽的豬、雞、貓、狗……。
「將動物圈養是一種剝奪,我們可以跟羊一樣攀爬將近九十度的峭壁嗎?我們總是認為自己比動物高等,他們做不到我們可以做到的事,相對而言,他們能做到的我們也未必做得到,那我們憑什麼限制牠們的活動範圍呢?」
「欸!你知道我們是不背水肺、氧氣瓶下海射魚的嗎?」
這是達悟男人對海的尊敬,「我們跟牠們站在同樣的位置上,沒有誰占誰便宜,靠你最純粹的力量和智慧去對決。」老人緩緩地說,「閉氣時間不夠長、無法停留在海中隨著海的呼吸等待、太急動作太大、姿勢不對、高估自己的身體狀況,你都可能被帶走,很公平。」
「所以也有很多人因為這樣就離開這個世界了嗎?」
「我有朋友被鯊魚『打哈欠』的時候不小心咬到,就死掉了……」,老人笑了笑。其實鯊魚平常並不會亂攻擊人,但如果碰上了……「嗯,運氣不好,被帶走也沒關係,就是時候到了,沒有人征服得了大自然。」
「沒有人,能夠征服的了大自然。」平靜卻鏗鏘有力的一句話,重重地打進我的心裡。
許多動植物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遠遠超過人類歷史的幾千幾萬倍,自認是高等生物的我們,只花上不過短短二十萬年,就幾乎要毀掉逾四十五億年的地球……。
不符合人類利益的都沒有意義,所有的存在,都以「人」是否得利而被評估其價值。
想起了兩條新聞:
■ 蘋果公司限制iPhone綁約價格違反市場機制裁罰兩千萬
■ 日月光排放廢水污染河川農田裁罰六十萬
也許有人會說,法條不同,所以根本不能拿來比;
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不是法條本身就出了問題?
也許,這就是我們對於「重要性」的價值判定。
我想起那天早上,一隻名為「阿貢」的小黑豬飛奔來到我的前面,好奇地聞聞我,要我摸摸牠。阿貢不時會望向海洋,我猜,牠或許在思念著因天氣終於放晴而出海奮鬥的主人吧。動物對人類無條件的信任,就這樣美好地存在這座島嶼上。
我們時常闖入他人的世界裡,肆無忌憚地掠奪那些我們認為「屬於」我們的東西,做超出能力所及的,獲得超出實際所需的,用那些「自以為聰明」的方式……。
國際研究報告指出,2040年前後,全球將無魚可吃。「我們都以為海裡的魚是吃不完的,其實海只是大了一點的冰箱,總有一天會被掠奪殆盡。」老人又點起了一支菸。
大自然縱然可怕,人類的驕傲,也不遑多讓。一個人的知識和見解,
絕不會超過他的經歷與體悟
讓他們用飛魚的方式翱翔
蘭嶼北部朗島村
如果海當鬼,我們一起玩躲貓貓,這是一個你始終都會被鬼找到的地方。
無論,你在哪裡。
躲在遮蔽物後方,偷偷瞄上一眼,你還是看得見她,完完全全的海洋民族,被太平洋緊緊擁抱著的淨土,朗島青年總威對我說:「就像有喝咖啡習慣的人一樣,一天沒有喝,整天會心神不寧,說不上來哪裡不對勁。」海洋之於蘭嶼人,就像咖啡之於某些人,或者,可以替換成任何一種你無法從生活中抽離的東西,一天沒有見到她、摸到她、聞到她,就是感覺身體哪裡出了問題。
我傻傻地問了老人家:「這邊的孩子幾歲可以開始去海邊跟大人學習如何和海洋相處、學打魚?」他愣了一下,反問我說:「為什麼要教呢?他們會跟在旁邊看啊,或著跟哥哥們一起去玩啊,要教什麼?」
然後,我恍然大悟。
在這個環境之下,海水跟血水早就融為一體,所有的一切都成為理所當然,讀再多的海洋知識,也不如給他一個只有海的環境。
對這裡來說,「海」,是勞動的場域、是教材、是教室、是糧倉、是冰箱、是競技場、是運動場、是遊戲室。生活在「大島」上的我們,努力用鋼筋水泥區隔出一個個小小的獨立空間,去營造這些場域,好似,沒有這些地方,我們就什麼都不會了。
學習單一化,是最可怕的教育。
還記得天枰颱風肆虐後,新聞瘋狂報導天枰颱風重創「蘭嶼」,尤其以島上唯一的農會與加油站最為嚴重,兩個加油箱更不知去向,是最嚴重的一場災害,媒體大篇幅刊登這兩處的照片,非常慘烈,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後來」興建的各項建設損失慘重。
「那是『海浪休息的地方』啊……」,當地人這麼說著。
「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你有看到那塊地上,除了農會與加油站還有其他的人住在那邊嗎?那是『海浪休息的地方啊……』。為什麼沒有當地人會去那邊蓋房子呢?大家有想過嗎?因為我們知道這座島嶼的呼吸,老人家也會告訴我們哪裡可以做什麼、哪裡不可以做什麼,也許他們無法明確地說出為什麼,但那都是祖先跟自然學習後,流傳下來的智慧啊。」
所謂重創,是那些不明白島嶼脈動的外地人,窺覷利益把自己放在了地雷區之上,政府為了「化外之島」的發展前景,認為「地下屋」居住環境不好,補助金錢讓當地人興建國宅,然而對於補助金額之外當地居民需自付的費用,政府卻錯估以為居民負擔得起,加上並不符合當地民情的居住習慣,以及輕視天候等各式因素,導致許多國宅只蓋了一半或者遺留空屋,現今許多都已成為羊群等動物居住的地方。
看著地下屋外面海的那一棟棟建築,應該說,是一道道阻隔了「一望無際」的水泥牆。
天空與海面的一體感,被一條一條的電線切割成大小不等的視窗,即便如此,你還是能夠感受那樣躍動的生命力。
雞、豬、狗、羊、人,在這裡都「只是」生物,名字只是個稱謂,但他們對於這樣的「標籤」並沒有賦予生命之外的意義,很純粹。
海浪會找地方休息;魚會引誘人類掉進陷阱;羊群是紅綠燈;草會找適合的泥土長大。每個存在都與眾不同,卻一點也沒有違和感。
目前有許多政策打算「照顧」這塊美麗的土地,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但該堅守不變的是:「讓蘭嶼起飛,請讓他們用飛魚的方式翱翔。」
站在岸邊,海真的有十種以上的藍,海浪不是打上灘頭,而是撞進心裡。
想起來到這裡之前,有人跟我說:「蘭嶼喔,你去一天就可以了啊,為什麼要去三、五天?」
如果是用「大島」人的角度,這裡不好玩。
這是一個必須用身體、用肌膚、用盡身體一切感官去學習的地方。
我無法告訴你現今存在島上的所有,什麼是對還是錯。必須用力地傾聽,然後由你來告訴在地人以及身邊的朋友,來到這裡,或者去到任何地方,你最喜歡的她是什麼模樣?
春天要到了,「這座一小時就能繞完的小島上,春夏旺季可以塞進十二萬人,很可怕」,朗島青年說著。
讓我們,
很溫柔、很溫柔地一起上島;
很謙卑、很謙卑地學習;
情緒很滿、很滿地離開。
然後,再回來。
一個人的知識和見解,絕不會超過他的經歷與體悟。
只有在走進深處後,才知道,什麼是多餘。
是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傲慢
布農青年的歌聲
花蓮萬榮鄉馬遠部落
「看著你的腳步你踩過的泥土,這崎嶇的山路走得好辛苦,你說過的話我何時才能領悟,再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溫度……dan na ngaus as zakuan mudadan, dis uni zaku pisihal nalahaiban……」
在政大金弦獎上,第一次聽到這首勇奪三項大獎的歌曲《腳印》,結合布農族語的創作,令人深深迷戀上這種從「土地長出來」的族群文化。
創作人馬詠恩是一名原住民獨立音樂人,他透過音樂、帶人走入部落,同時分享自己的族群與家鄉的故事,讓更多人藉由不同的方式認識布農族。他用他最擅長的方式,讓別人看見了他的族群和故鄉。
而我真的看見了。
就因為這樣,我跟著詠恩走入花蓮萬榮鄉的馬遠部落。
抵達馬遠部落的那個晚上,布農族獵人帶領我們,搭乘小貨車,行駛在崎嶇到讓人無法想像的山路,引擎聲低沉地嘶吼著,爬得有些吃力的小貨車不時因坡度太陡熄火,還數度朝車後方的懸崖倒退,驚險萬分,但獵人們面不改色,重新發動後的小貨車依舊賣力地爬著坡。
空氣中充斥著每道呼吸都不能懈怠的緊張感。
約莫一個鐘頭後,在海拔六百公尺處飄起了雨,我們的視線逐漸被大霧所遮蔽,伸手不見五指。「下車吧,從這裡開始我們得用走的,在這之前,我們要先告訴祖靈,我們來了。」獵人們開始準備獵前需要的用具。
米酒、獵槍、彈藥,一群布農族青年肩靠著肩,全部圍在置於木頭上的獵槍前,開始唱起了「獵前祭槍歌」。
布農青年的歌聲與自然的聲音手拉著手融入了彼此,如協奏曲般悠揚共鳴,一股敬畏之心油然升起,所有人似不自覺放輕了呼吸,可以感受到氣氛愈發肅穆、神聖,我們的神情也凝重了起來,深怕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布農族人獵前的禁忌。
「我們是要祈求山神與祖靈們保護我們得以平安、豐盛,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們賜予的,要抱著感恩的心,絕對不能開玩笑。」詠恩告訴我他們所進行的一切儀式最重要的核心意義。
儀式結束後,我們繼續朝山林深處走,耳邊傳來許多動物的聲音,「你聽到牠們的叫聲就不用去找了,因為那是牠們聞到氣味,相互警戒的方式,」獵人們沿途依據各類植物、地形、動物糞便、水源位置,繼續追蹤動物可能出現的地方。
在海拔一千多公尺處,已經沒有所謂「正常的路」可以行走,只能跟著獵人曾經踏過的泥土,確保你的下一步安然無恙,「很多人都以為我們人類佔了優勢,其實動物也在引誘你掉入陷阱,一失足將跌落山谷,沒有誰才高人一等,只有誰更瞭解這塊土地。所有保護自己的技能都是老獵人們代代相傳下來的智慧,一切的東西都在他們腦海中,你不去挖,以後就全都消失了。」
遠處忽然閃現兩顆圓球狀的淡黃色反光,正當我想看清楚那是什麼東西時,「砰!」只見獵人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開槍射擊。
獵人們趨步向前,手起刀落,迅捷地割掉了動物的左耳,留在旁邊的草叢裡,同時用母語對祖靈說:「這是獻給祢們的,一切都是祢們的賜予。」
年紀較輕的我,幫忙背起獵物返回獵寮聽獵人說著這片山林的故事,「上山最重要的是安全,獵不獵得到是運氣,絕不能強求。肉,本來就不是一個應該容易取得的東西。」獵人跟我們分享他們數百年來與自然共生的謙卑。
此時太陽已悄悄地升起,我們與晨光伸出的手一同肢解獵物,內心並不感到害怕,反而異常平靜,全身上下、發自內心充滿感恩之情。獵人拿起碗,將動物體內殘留的血液舀起,倒進米酒瓶中混合,「喝吧,一點一滴都沒有浪費的理由」,我接過酒瓶大口喝下,那是對牠賜予我們飽足得以延續生命致上的最高敬意。
多數人一邊吃著美味的雞、豬、牛、魚等各式生命,同時批判著狩獵的「野蠻」與「殘忍」。似乎是認為,我們食用的一切,「本來」就是飼養來成為肉品的生命,「理所當然」要成為我們的食物,而狩獵那些不在我們食用設定分類下的生命,才是人們眼中的野蠻。
相較之下,真正的野蠻,似乎是那些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傲慢。被需要的愛,
才是愛孩子的願望
台11線海岸公路
那天在台東碰上了調皮的孩子,它的名字叫太陽,在無拘無束的藍天裡玩著捉迷藏;沿著台11線前進,溫柔的海洋濺起浪花,金黃色的暖陽與白浪在擋風玻璃上盡情玩耍。
天空與梯田連成一線,從梯田裡的水看著天上的鳥,如顛倒世界一般,我們被海天包覆著。
世界緊緊地用土地環繞著我們,擁抱,很真實。
在這被稱作台灣最美的海岸,我們碰上了推動有機農業的孫大姐,吃著她自製的白吐司,聊起了關於海岸線上的故事。
「很多人為了展現他們關懷偏鄉地區孩童的處境,提供了非常多的物資。為什麼?因為「給物資」是最簡單又快速的方式。然後,孩子們養成了伸手就可以獲得的習慣,這些愛心物資,改變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創造力與想像……。」孫大姐無奈地說著。
「其實我不是很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孫大姐又遞上了一片白吐司,「這樣好了,我跟你說一個例子。某大企業,為了彰顯他們的豪氣與關懷,來到我們這裡,讓孩子們拿出紙跟筆,寫下他們想要的物品;孩子們開心地寫下許多願望,例如和人一樣大的絨毛玩偶、知名品牌摺疊腳踏車、以及各式各類的玩具……,當然,企業主說到做到,讓所有的孩子心想事成。禮物送來那天,孩子們興高采烈地拿著禮物說:『沒想到真的會送給我們耶,早知道我就寫貴一點的,如果是寫電腦、車子……更高級的東西就好了,下次一定要聰明一點。』聽了我當下心都涼了一半,漸漸地,孩子不再到田地裡玩耍,不再徜徉在美麗的大自然……。以前的孩子,就算只是簡單的竹片,甚至在小樹林都能夠玩上一整天,這是一種透過想像和創造,玩出屬於自己童年的遊戲,不像現在,孩子們天天和那些『愛心物資』膩在一塊。」
我瞪大眼睛反覆思考孫大姐這段話,繼續咬著我的白土司。
再跟你說一個例子。「企業因為所謂的愛心,贊助某幾間小學每天的三餐,孩子們都在學校用餐,不過說真的,也許有些家庭很需要,但其實就我瞭解部落的現況,其實食物是很充裕的,儘管粗茶淡飯了些,但營養還是足夠的;更重要的是,這邊隔代教養居多,上上一代與孫子間的互動時間已經不多,吃飯是最棒的相處時光,連這麼一個小小的幸福,都被企業以『不一定真正需要的』供餐所剝奪了。同時,孩子的胃口被愈養愈大,早餐不是某知名速食連鎖的早餐不吃(因為某企業說從部落到知名連鎖速食店開車要兩小時,能吃到很難得)。這樣,真的是幫助嗎?」
「孫大姐,究竟這裡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我們這個鄉鎮,一座游泳池都沒有,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這裡幾乎都是阿美族的孩子,阿美族的海是冰箱,他們得靠海生存。但如同剛剛提到的,隔代教養!青壯年都到外地討生活,阿公阿嬤沒有體力帶孩子到海邊玩耍,更別說是教孩子游泳了,可以想像嗎?沿海的國小學童竟然超過九成是旱鴨子,這已經不是不會游泳這麼簡單,而是文化、某種生活方式無法被傳承的重要警訊!」
「教育始終是我們最缺乏的,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活動,需要的是長期的人力資源。如果資源能夠提供給有心回到部落的青年,長期耕耘,才是真正對當地有所幫助,原住民的問題需要原住民自己才能解決。」
強勢的愛心,是愛嗎?
我不禁開始思考,究竟我們給予的,是他們真正需要的,還是我們「以為」他們真正需要的呢?從我們對朋友、對長輩、另一半、對家人……,以至我們和環境,以至人類和萬物之間。
如果沒有花時間瞭解當地或者某族群的需求,只是自我感覺良好地伸出「援手」,不僅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甚至只是一次次的資源浪費。
被需要的愛,才是愛。不要輕易說愛我,
請在你真心愛我以後
聽古老的住民之歌
烏來福山泰雅部落
因緣際會,走進了烏來福山部落,這是泰雅族的村落。
沿著山路蜿蜒而上,空氣愈來愈清新,景色由灰轉綠,自然的聲音如交響樂般美妙動聽:蟲聲、鳥鳴、溪水與瀑布聲,還有人的聲音。
「從這頭到那頭的山,都是我們的獵場。」我看到遠方非常非常古老的吊橋上,走著一對父子。
「 你看他背著竹籃,還有他身上的配備,那就是要去打獵的,後頭跟著的是他的兒子,小學四年級!他不是來跟著爸爸在山裡『拿東西』的,而是要學習拿東西的方法——追蹤動物留下的線索,辨識樹皮被山豬磨出痕跡的高度,判斷是幾百斤的山豬或是小豬;認識野菜和野生水果的種類,好讓這段路途中能夠有東西充飢;學會在山中的夜裡如何不會被凍死……,更重要的是,該用什麼樣的方法與態度來面對自然」,泰雅獵人緩緩地說著。
「長輩們從小就訓誡我們,必須對得到的一切心懷感恩,拿需要的就好了,絕對不要貪心,如果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沒有留下東西給後代,那孩子們不就會挨餓了嗎?我們原住民什麼都不怕,最怕的是漢族,只要讓他們知道某種東西有價值,隔天,那些東西就會全部不見了,根本就是『屠殺』……。希望我這樣說你不要生氣,但我真的感到害怕。
「牧師啊,滿多人認為原住民是弱勢族群,需要協助改善生活的環境,你認為呢?」
「其實,我們要的不多,只要給我們一個能以自己方式生活的空間,就足夠了。早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前,我們也沒有餓死,為什麼我們現在就需要人幫助呢?用漢人的生存方式來教育我們,就像是把魚養在山上,那是截然不同的啊。」
我們似乎總是將自己的觀點加諸在不同的文化與族群之上。
「你們都說想要解決我們的問題,可以請你們先來聽我們說故事嗎?」泰雅獵人悠然地唱起了泰雅古調。
活著,不只有一種方式;
每一個族群,都有他們的故事。
不要輕易說愛我,請在你真心愛我以後。大自然縱然可怕,
人類的驕傲也不遑多讓
達悟男人對海的敬畏
在蘭嶼堵羊的路上
上島不到半小時,我就上了第一堂課;
第一天,這塊土地為我重新上了一堂自然課。
小女孩緊緊牽著我的手,「哥哥,羊是我們這裡的紅綠燈喔!在路中間的時候是紅燈,走了之後就是綠燈了。」
蘭嶼的路上時常會「堵羊」,不堵都難。從羊群的自在,即可窺知達悟人對世界萬物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這裡的山羊不太怕人耶,人走到旁邊了還在吃草,我去澎湖七美的時候,那裡的羊遠在五十公尺之外就會開始警戒,再接近一點就會逃走。」
「山羊?我們這裡沒有山羊啊,那是我們養的啦,不是山羊喔。」老人家看著我疑惑地說。
一般我們所認知的山羊,是學者們依據牠的居住地或其他條件,方便品種的分類為物種命名,但對於達悟人來說,整塊土地都是羊隻與動物們共享的,因為他們不只住在山裡,所以羊就是羊,不是山羊。
除此之外,你還可以在島上隨處遇見慵懶地曬著太陽的豬、雞、貓、狗……。
「將動物圈養是一種剝奪,我們可以跟羊一樣攀爬將近九十度的峭壁嗎?我們總是認為自己比動物高等,他們做不到我們可以做到的事,相對而言,他們能做到的我們也未必做得到,那我們憑什麼限制牠們的活動範圍呢?」
「欸!你知道我們是不背水肺、氧氣瓶下海射魚的嗎?」
這是達悟男人對海的尊敬,「我們跟牠們站在同樣的位置上,沒有誰占誰便宜,靠你最純粹的力量和智慧去對決。」老人緩緩地說,「閉氣時間不夠長、無法停留在海中隨著海的呼吸等待、太急動作太大、姿勢不對、高估自己的身體狀況,你都可能被帶走,很公平。」
「所以也有很多人因為這樣就離開這個世界了嗎?」
「我有朋友被鯊魚『打哈欠』的時候不小心咬到,就死掉了……」,老人笑了笑。其實鯊魚平常並不會亂攻擊人,但如果碰上了……「嗯,運氣不好,被帶走也沒關係,就是時候到了,沒有人征服得了大自然。」
「沒有人,能夠征服的了大自然。」平靜卻鏗鏘有力的一句話,重重地打進我的心裡。
許多動植物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遠遠超過人類歷史的幾千幾萬倍,自認是高等生物的我們,只花上不過短短二十萬年,就幾乎要毀掉逾四十五億年的地球……。
不符合人類利益的都沒有意義,所有的存在,都以「人」是否得利而被評估其價值。
想起了兩條新聞:
■ 蘋果公司限制iPhone綁約價格違反市場機制裁罰兩千萬
■ 日月光排放廢水污染河川農田裁罰六十萬
也許有人會說,法條不同,所以根本不能拿來比;
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不是法條本身就出了問題?
也許,這就是我們對於「重要性」的價值判定。
我想起那天早上,一隻名為「阿貢」的小黑豬飛奔來到我的前面,好奇地聞聞我,要我摸摸牠。阿貢不時會望向海洋,我猜,牠或許在思念著因天氣終於放晴而出海奮鬥的主人吧。動物對人類無條件的信任,就這樣美好地存在這座島嶼上。
我們時常闖入他人的世界裡,肆無忌憚地掠奪那些我們認為「屬於」我們的東西,做超出能力所及的,獲得超出實際所需的,用那些「自以為聰明」的方式……。
國際研究報告指出,2040年前後,全球將無魚可吃。「我們都以為海裡的魚是吃不完的,其實海只是大了一點的冰箱,總有一天會被掠奪殆盡。」老人又點起了一支菸。
大自然縱然可怕,人類的驕傲,也不遑多讓。一個人的知識和見解,
絕不會超過他的經歷與體悟
讓他們用飛魚的方式翱翔
蘭嶼北部朗島村
如果海當鬼,我們一起玩躲貓貓,這是一個你始終都會被鬼找到的地方。
無論,你在哪裡。
躲在遮蔽物後方,偷偷瞄上一眼,你還是看得見她,完完全全的海洋民族,被太平洋緊緊擁抱著的淨土,朗島青年總威對我說:「就像有喝咖啡習慣的人一樣,一天沒有喝,整天會心神不寧,說不上來哪裡不對勁。」海洋之於蘭嶼人,就像咖啡之於某些人,或者,可以替換成任何一種你無法從生活中抽離的東西,一天沒有見到她、摸到她、聞到她,就是感覺身體哪裡出了問題。
我傻傻地問了老人家:「這邊的孩子幾歲可以開始去海邊跟大人學習如何和海洋相處、學打魚?」他愣了一下,反問我說:「為什麼要教呢?他們會跟在旁邊看啊,或著跟哥哥們一起去玩啊,要教什麼?」
然後,我恍然大悟。
在這個環境之下,海水跟血水早就融為一體,所有的一切都成為理所當然,讀再多的海洋知識,也不如給他一個只有海的環境。
對這裡來說,「海」,是勞動的場域、是教材、是教室、是糧倉、是冰箱、是競技場、是運動場、是遊戲室。生活在「大島」上的我們,努力用鋼筋水泥區隔出一個個小小的獨立空間,去營造這些場域,好似,沒有這些地方,我們就什麼都不會了。
學習單一化,是最可怕的教育。
還記得天枰颱風肆虐後,新聞瘋狂報導天枰颱風重創「蘭嶼」,尤其以島上唯一的農會與加油站最為嚴重,兩個加油箱更不知去向,是最嚴重的一場災害,媒體大篇幅刊登這兩處的照片,非常慘烈,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後來」興建的各項建設損失慘重。
「那是『海浪休息的地方』啊……」,當地人這麼說著。
「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你有看到那塊地上,除了農會與加油站還有其他的人住在那邊嗎?那是『海浪休息的地方啊……』。為什麼沒有當地人會去那邊蓋房子呢?大家有想過嗎?因為我們知道這座島嶼的呼吸,老人家也會告訴我們哪裡可以做什麼、哪裡不可以做什麼,也許他們無法明確地說出為什麼,但那都是祖先跟自然學習後,流傳下來的智慧啊。」
所謂重創,是那些不明白島嶼脈動的外地人,窺覷利益把自己放在了地雷區之上,政府為了「化外之島」的發展前景,認為「地下屋」居住環境不好,補助金錢讓當地人興建國宅,然而對於補助金額之外當地居民需自付的費用,政府卻錯估以為居民負擔得起,加上並不符合當地民情的居住習慣,以及輕視天候等各式因素,導致許多國宅只蓋了一半或者遺留空屋,現今許多都已成為羊群等動物居住的地方。
看著地下屋外面海的那一棟棟建築,應該說,是一道道阻隔了「一望無際」的水泥牆。
天空與海面的一體感,被一條一條的電線切割成大小不等的視窗,即便如此,你還是能夠感受那樣躍動的生命力。
雞、豬、狗、羊、人,在這裡都「只是」生物,名字只是個稱謂,但他們對於這樣的「標籤」並沒有賦予生命之外的意義,很純粹。
海浪會找地方休息;魚會引誘人類掉進陷阱;羊群是紅綠燈;草會找適合的泥土長大。每個存在都與眾不同,卻一點也沒有違和感。
目前有許多政策打算「照顧」這塊美麗的土地,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但該堅守不變的是:「讓蘭嶼起飛,請讓他們用飛魚的方式翱翔。」
站在岸邊,海真的有十種以上的藍,海浪不是打上灘頭,而是撞進心裡。
想起來到這裡之前,有人跟我說:「蘭嶼喔,你去一天就可以了啊,為什麼要去三、五天?」
如果是用「大島」人的角度,這裡不好玩。
這是一個必須用身體、用肌膚、用盡身體一切感官去學習的地方。
我無法告訴你現今存在島上的所有,什麼是對還是錯。必須用力地傾聽,然後由你來告訴在地人以及身邊的朋友,來到這裡,或者去到任何地方,你最喜歡的她是什麼模樣?
春天要到了,「這座一小時就能繞完的小島上,春夏旺季可以塞進十二萬人,很可怕」,朗島青年說著。
讓我們,
很溫柔、很溫柔地一起上島;
很謙卑、很謙卑地學習;
情緒很滿、很滿地離開。
然後,再回來。
一個人的知識和見解,絕不會超過他的經歷與體悟。
只有在走進深處後,才知道,什麼是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