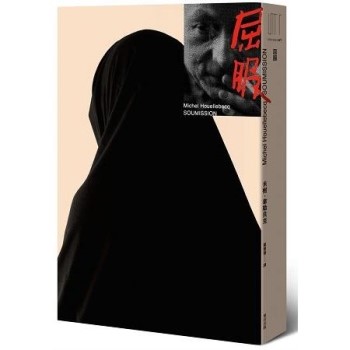眾所皆知,在大學研讀文學幾乎沒什麼出路,只有最優秀者能繼續留在大學教文學──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滑稽可笑的情境,一個以自我複製為唯一目的的系統,淘汰剩餘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被淘汰的倒也不會造成什麼干擾,甚至有時候還能起一些邊際效益。一個去Céline或愛馬仕應徵售貨員的年輕女子,首要的當然是注重儀容外表,但若有份現代文學學士或碩士文憑,在雇主眼裡也多少能起加分的作用。如果缺乏真正能派上用場的能力,會念書也或許能增加一點事業發展上的可能性──更何況,在奢侈品工業中,文學一向具有高輔助性的良好聲譽。
我自知屬於稀少的「最優秀學生」。我寫了一本很不錯的博士論文,預期會得到「優良」的成績;最後,我得到最高的「全體評審一致嘉獎」,當我後來看到論文審查報告非常完美,幾乎是過度讚美,很驚訝也很高興:如果我要的話,很可能得到晉升講師的資格。我的人生可以預期會和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於斯曼一樣,平淡無趣地過完。成年之後的頭幾年,我在一所大學裡度過,或許最後的幾年,也會在同一所大學裡度過(事實上並不全然如此:我拿到的是巴黎索邦第四大學的文憑,後來任職於巴黎索邦第三大學,名氣稍遜但同樣位於巴黎第五區,兩所大學相隔不過百公尺遠)。
我對教書從來沒有一丁點熱忱──十五年的教書生涯更證實了我原先的欠缺熱忱。以前為了改善生活,教過一些私人補習課程,讓我很快領悟到,在絕大部分的時間,傳授知識是不可能的;智力的範疇如此不一,差異又如此之大,基礎的高低差異不但無法消除,連減低都難以辦到。更糟糕的可能是我不喜歡年輕人──我從來沒喜歡過年輕人,就算我自己也被視為年輕人的時候也是。我覺得,年輕的意思是對生命抱著某種熱情,或某種反叛,而且至少對將被自己取代的一代帶著依稀的優越感;至於我自己,從未有過以上的感受。然而我年輕時期還是交過一些朋友──或者正確地說,有一些同學讓我可以不帶厭惡地在課間一起去喝杯咖啡或啤酒。尤其,我還有過幾個情婦──或者以當時代的說法(或許現在也還這麼說),我有過幾個女友──大約一年一個。這些羅曼史都以幾乎一成不變的模式進行。學年一開始一起做報告、互借筆記,反正就是大學生涯中經常會出現的社交機會,因此,一旦進入職業生涯,這些機會一一消失,讓大部分的人驚愕地陷入完全的孤獨之中。羅曼史進行一整年,她來我家或我去她家過夜(大都去她家,我慘淡、甚至破爛的房間終究不太適合浪漫約會),進行性行為(我私自猜想兩人都滿享受)。暑假結束,大學新學年開始,戀情就結束,而且幾乎都是女方開口結束。據她們的解釋──大部分時間沒有添加更多細節──暑假期間她們經歷了某些事情;某些女孩比較不考慮我的感受,直接告訴我她遇到了某個人。是喔,那又怎樣?我也是某個人啊。回頭想想,我覺得這些純敘述事實的解釋根本不明確:她們確實遇到了某個人,這我不否認,但遇到某個人這件事的重要性足以切斷我們的關係,以便進行一段新的關係,這就是一個強烈而無以名狀的戀愛造成的典型行為,也因無以名狀,所以更為強烈。
以我自己年輕歲月的戀愛形式來說(而且我不認為情況會有多大改變),年輕人經過一段青少年前期的短暫性追尋之後,都會開始進行「排他」的獨占戀愛關係,嚴格堅守一夫一妻型態,不僅牽涉性關係,也牽涉人際的社會關係(約會、度週末、假期)。然而這些關係毫無確定性,只能算是戀愛關係的練習,有點像實習階段(在職場上,實習也很廣泛,是得到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先聲試啼)。戀愛關係維持的時間長短不一(我本人的戀愛經驗每次維持一年,這算是可以接受的時間長度)、次數多寡不一(可信的平均數據是十至二十次),一次次經驗後昇華成最終關係,也就是一錘定音的婚姻關係,隨著孩子出現,演變為一個家庭。
我許久之後才發現這個模式極端空洞,其實是最近幾個星期之間偶遇奧菲莉以及桑塔拉之後,才發現的(但是,我相信遇到的若是珂蘿艾或米歐蓮娜,結果也不會有太大不同)。當我一抵達和珂蘿艾相約吃晚餐的巴斯克風味餐廳,就預感會度過糟糕的一晚。儘管我幾乎獨自灌下兩瓶伊盧雷基白酒,依然覺得要維持勉強熱情的交談難度愈來愈高、甚至很快就到達難以克服的程度。不知道為什麼,我立刻覺得談及我們的過往回憶是不得體、甚至難以想像的。學年一開始一起做報告、互借筆記,反正就是大學生涯中經常會出現的社交機會,因此,一旦進入職業生涯,這些機會一一消失,讓大部分的人驚愕地陷入完全的孤獨之中。羅曼史進行一整年,她來我家或我去她家過夜(大都去她家,我慘淡、甚至破爛的房間終究不太適合浪漫約會),進行性行為(我私自猜想兩人都滿享受)。暑假結束,大學新學年開始,戀情就結束,而且幾乎都是女方開口結束。據她們的解釋──大部分時間沒有添加更多細節──暑假期間她們經歷了某些事情;某些女孩比較不考慮我的感受,直接告訴我她遇到了某個人。是喔,那又怎樣?我也是某個人啊。回頭想想,我覺得這些純敘述事實的解釋根本不明確:她們確實遇到了某個人,這我不否認,但遇到某個人這件事的重要性足以切斷我們的關係,以便進行一段新的關係,這就是一個強烈而無以名狀的戀愛造成的典型行為,也因無以名狀,所以更為強烈。
以我自己年輕歲月的戀愛形式來說(而且我不認為情況會有多大改變),年輕人經過一段青少年前期的短暫性追尋之後,都會開始進行「排他」的獨占戀愛關係,嚴格堅守一夫一妻型態,不僅牽涉性關係,也牽涉人際的社會關係(約會、度週末、假期)。然而這些關係毫無確定性,只能算是戀愛關係的練習,有點像實習階段(在職場上,實習也很廣泛,是得到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先聲試啼)。戀愛關係維持的時間長短不一(我本人的戀愛經驗每次維持一年,這算是可以接受的時間長度)、次數多寡不一(可信的平均數據是十至二十次),一次次經驗後昇華成最終關係,也就是一錘定音的婚姻關係,隨著孩子出現,演變為一個家庭。
我許久之後才發現這個模式極端空洞,其實是最近幾個星期之間偶遇奧菲莉以及桑塔拉之後,才發現的(但是,我相信遇到的若是珂蘿艾或米歐蓮娜,結果也不會有太大不同)。當我一抵達和珂蘿艾相約吃晚餐的巴斯克風味餐廳,就預感會度過糟糕的一晚。儘管我幾乎獨自灌下兩瓶伊盧雷基白酒,依然覺得要維持勉強熱情的交談難度愈來愈高、甚至很快就到達難以克服的程度。不知道為什麼,我立刻覺得談及我們的過往回憶是不得體、甚至難以想像的。至於目前呢,珂蘿艾很顯然並沒有成功地邁入婚姻階段,露水姻緣的關係讓她愈來愈厭惡,總而言之,她的感情生活無可救藥地全盤覆滅。言談之中,我側面猜到她曾一度試著穩定下來,卻沒成功,創傷一直無法復原。她談及男同事時充滿尖酸苦澀(實在找不到話題,只好聊工作──她在波爾多酒商公會擔任公關,經常出差,尤其得去亞洲進行法國名酒促銷),顯示她吃了不少苦頭。下計程車時,我很驚訝她邀我「再續最後一杯」,我心想,這女的真是走投無路了。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已知道今晚什麼都不會發生,我甚至不想看到她的裸體,寧可避開這一幕,但這一幕還是出現了,也證實了我的預感:她不只在感情層面吃了苦頭,身體也遭受了無法彌補的毀損,胸部和屁股只剩下貧瘠的表面,縮小了、鬆垮了、下垂了,她已經不是且再也不會被視為慾望對象了。
和桑塔拉的共餐也是差不多的模式,只有些微差距(這次是海鮮餐廳、她的工作是跨國藥廠管理階層祕書),結果也和上次大同小異。只不過桑塔拉比珂蘿艾豐滿,也比較能聊,無依無靠的感覺沒那麼強烈。她非常悲傷,沒救了,我知道她最後還是會全盤說出,就和珂蘿艾一樣,她也是一隻「羽毛沾上瀝青的鳥」,但──按照我的形容──她鼓動翅膀的能力比較大。一、兩年之後,她會把所有結婚的企圖擺到一邊,氣數未盡的性期待會讓她極力尋找年輕男伴,這在我年輕時期稱為「如狼似虎」,最多持續十來年,之後就是肉體日漸成為瑕疵貨品,導致最後無法挽回的結果。
二十歲的時候,我可以在任何刺激下勃起,或是沒來由就勃起,有點無謂,那時候的我很可能樂於這種關係,總之比上家教課來得滿足且好玩。我想那時候的我應該可以勝任愉快,當然,現在是不可能了,勃起次數愈來愈少、愈來愈難,對象必須是一具緊實、柔軟、零瑕疵的軀體。
至於我自己的性生活呢,第一年當上巴黎索邦三大講師時,還沒有多大差別。持續一年接一年和系上女學生上床──其實對她們來說,我的老師身分並沒有改變什麼情況。一開始,我和女學生之間年紀的差異並不構成問題,而是漸漸產生了一種禁忌,原因來自我大學講師的身分,而非是我的年齡或是外表大她們很多。總之,我占盡男人在性感層面變老非常緩慢的好處,相對的,女人老化經常令人訝異地快速,幾年、甚至幾個月之間就全都垮了。和學生時代相比,真正的差異在於,現在每年開學斷了舊情的,是我。這完全不是出於嘗鮮的唐璜心態,也不是想花心縱慾。我和同事史蒂夫相反──他和我一起負責大一、大二的十九世紀法國文學課程,我並不會一開學就貪婪猴急地檢驗大一的「最新到貨」。他的運動衫、Converse球鞋、有點加州氣息的調調,每次都讓我想到電影《瘋狂假期》(Les Bronzés)裡,男主角蒂埃里.萊爾米特面對每週度假俱樂部的成員抵達時,走出小屋接待的那個樣子。我斷掉和這些年輕女孩的關係,毋寧是出於沮喪、厭倦:我不覺得自己的狀態能夠真正維持一段戀情,而且我想避免所有的失望、所有的幻滅。我都是在學年中改換女友,起因都是外在、無足輕重的原因──通常是一條短裙。
之後,連這個也中斷了。我和梅莉安九月分手,現在已是四月中,學年都快結束了,我都還沒換新女友。我被任命為教授,學術生涯可說達到了某種圓滿終點,但我認為這兩者之間並沒有真正的關聯。和梅莉安分手後不久,我就遇見奧菲莉,然後是桑塔拉,這之中產生了一種令人困惑、不安、不舒服的連結。經過一段時日的思考之後,我必須承認:我和那些前女友之間的關係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親近,沒有長相廝守遠景的那些短期性關係,最後卻讓我們產生了近似於幻滅的感受。和她們不同的,是我不能和任何人坦白談心,因為男性社交的談話並不容許談論私人感情生活:他們談的是政治、文學、財經、體育,符合他們的天性;至於感情生活,他們至死都不會透露。
我是老了,進入了所謂男性更年期了嗎?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我決定弄清楚,每晚掛在You-porn上,這個時有經年的網站已經成為色情網站的龍頭。一開始進入遊戲,結果立刻讓我心安。You-porn提供全球各地正常普通男性的性幻想,從進入網站第一分鐘起,我就確定自己是個絕對正常普通的男性。這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確定,我花了生命中一大部分時間研讀一個經常被視為「頹廢派」的作家,性在他的著作裡並不是一個清晰的議題。出了網站,我因獲得證實而心中平靜。這些影片有的品質極佳(洛杉磯劇務組拍攝的,有工作小組、燈光師、攝影棚布景工、攝影師),有的粗糙復古(德國業餘三流片),大抵不出幾個如出一轍但令人愉悅的情節。最常見的一個情節就是,一個男人(年輕男子?老頭子?兩種版本都有)笨兮兮地讓陽具在內褲或短褲裡沉睡。兩個種族隨著版本而變的年輕女人察覺了這不恰當的情況,立刻不停地把該器官從臨時庇護處裡端請出來。她們百般媚態挑逗讓他興奮起來,這一切都在女性的同謀友好的氣氛下進行。陽具輪流在兩張嘴裡進出,舌頭像燕子有點狂亂的交叉飛舞,那些在塞納河─馬恩河地區南邊劃過陰沉的天際,準備離開歐洲過冬的燕子。那個男的欲仙欲死,只能吐出幾個薄弱的單字;在表達這種情境上,法語尤其薄弱得可憐(「喔!媽的!」「喔媽的我射了!」差不多就是這個僵硬民族能說的了);美國人詞彙就比較華麗比較強烈(「喔我的上帝啊!」「喔耶穌基督!」),這些詞彙似乎表達了不該忘記上帝的眷寵(不管是口交或是烤雞),不論如何,在iMac二十七吋螢幕前的我勃起了,因此一切都會好轉。
我自知屬於稀少的「最優秀學生」。我寫了一本很不錯的博士論文,預期會得到「優良」的成績;最後,我得到最高的「全體評審一致嘉獎」,當我後來看到論文審查報告非常完美,幾乎是過度讚美,很驚訝也很高興:如果我要的話,很可能得到晉升講師的資格。我的人生可以預期會和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於斯曼一樣,平淡無趣地過完。成年之後的頭幾年,我在一所大學裡度過,或許最後的幾年,也會在同一所大學裡度過(事實上並不全然如此:我拿到的是巴黎索邦第四大學的文憑,後來任職於巴黎索邦第三大學,名氣稍遜但同樣位於巴黎第五區,兩所大學相隔不過百公尺遠)。
我對教書從來沒有一丁點熱忱──十五年的教書生涯更證實了我原先的欠缺熱忱。以前為了改善生活,教過一些私人補習課程,讓我很快領悟到,在絕大部分的時間,傳授知識是不可能的;智力的範疇如此不一,差異又如此之大,基礎的高低差異不但無法消除,連減低都難以辦到。更糟糕的可能是我不喜歡年輕人──我從來沒喜歡過年輕人,就算我自己也被視為年輕人的時候也是。我覺得,年輕的意思是對生命抱著某種熱情,或某種反叛,而且至少對將被自己取代的一代帶著依稀的優越感;至於我自己,從未有過以上的感受。然而我年輕時期還是交過一些朋友──或者正確地說,有一些同學讓我可以不帶厭惡地在課間一起去喝杯咖啡或啤酒。尤其,我還有過幾個情婦──或者以當時代的說法(或許現在也還這麼說),我有過幾個女友──大約一年一個。這些羅曼史都以幾乎一成不變的模式進行。學年一開始一起做報告、互借筆記,反正就是大學生涯中經常會出現的社交機會,因此,一旦進入職業生涯,這些機會一一消失,讓大部分的人驚愕地陷入完全的孤獨之中。羅曼史進行一整年,她來我家或我去她家過夜(大都去她家,我慘淡、甚至破爛的房間終究不太適合浪漫約會),進行性行為(我私自猜想兩人都滿享受)。暑假結束,大學新學年開始,戀情就結束,而且幾乎都是女方開口結束。據她們的解釋──大部分時間沒有添加更多細節──暑假期間她們經歷了某些事情;某些女孩比較不考慮我的感受,直接告訴我她遇到了某個人。是喔,那又怎樣?我也是某個人啊。回頭想想,我覺得這些純敘述事實的解釋根本不明確:她們確實遇到了某個人,這我不否認,但遇到某個人這件事的重要性足以切斷我們的關係,以便進行一段新的關係,這就是一個強烈而無以名狀的戀愛造成的典型行為,也因無以名狀,所以更為強烈。
以我自己年輕歲月的戀愛形式來說(而且我不認為情況會有多大改變),年輕人經過一段青少年前期的短暫性追尋之後,都會開始進行「排他」的獨占戀愛關係,嚴格堅守一夫一妻型態,不僅牽涉性關係,也牽涉人際的社會關係(約會、度週末、假期)。然而這些關係毫無確定性,只能算是戀愛關係的練習,有點像實習階段(在職場上,實習也很廣泛,是得到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先聲試啼)。戀愛關係維持的時間長短不一(我本人的戀愛經驗每次維持一年,這算是可以接受的時間長度)、次數多寡不一(可信的平均數據是十至二十次),一次次經驗後昇華成最終關係,也就是一錘定音的婚姻關係,隨著孩子出現,演變為一個家庭。
我許久之後才發現這個模式極端空洞,其實是最近幾個星期之間偶遇奧菲莉以及桑塔拉之後,才發現的(但是,我相信遇到的若是珂蘿艾或米歐蓮娜,結果也不會有太大不同)。當我一抵達和珂蘿艾相約吃晚餐的巴斯克風味餐廳,就預感會度過糟糕的一晚。儘管我幾乎獨自灌下兩瓶伊盧雷基白酒,依然覺得要維持勉強熱情的交談難度愈來愈高、甚至很快就到達難以克服的程度。不知道為什麼,我立刻覺得談及我們的過往回憶是不得體、甚至難以想像的。學年一開始一起做報告、互借筆記,反正就是大學生涯中經常會出現的社交機會,因此,一旦進入職業生涯,這些機會一一消失,讓大部分的人驚愕地陷入完全的孤獨之中。羅曼史進行一整年,她來我家或我去她家過夜(大都去她家,我慘淡、甚至破爛的房間終究不太適合浪漫約會),進行性行為(我私自猜想兩人都滿享受)。暑假結束,大學新學年開始,戀情就結束,而且幾乎都是女方開口結束。據她們的解釋──大部分時間沒有添加更多細節──暑假期間她們經歷了某些事情;某些女孩比較不考慮我的感受,直接告訴我她遇到了某個人。是喔,那又怎樣?我也是某個人啊。回頭想想,我覺得這些純敘述事實的解釋根本不明確:她們確實遇到了某個人,這我不否認,但遇到某個人這件事的重要性足以切斷我們的關係,以便進行一段新的關係,這就是一個強烈而無以名狀的戀愛造成的典型行為,也因無以名狀,所以更為強烈。
以我自己年輕歲月的戀愛形式來說(而且我不認為情況會有多大改變),年輕人經過一段青少年前期的短暫性追尋之後,都會開始進行「排他」的獨占戀愛關係,嚴格堅守一夫一妻型態,不僅牽涉性關係,也牽涉人際的社會關係(約會、度週末、假期)。然而這些關係毫無確定性,只能算是戀愛關係的練習,有點像實習階段(在職場上,實習也很廣泛,是得到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先聲試啼)。戀愛關係維持的時間長短不一(我本人的戀愛經驗每次維持一年,這算是可以接受的時間長度)、次數多寡不一(可信的平均數據是十至二十次),一次次經驗後昇華成最終關係,也就是一錘定音的婚姻關係,隨著孩子出現,演變為一個家庭。
我許久之後才發現這個模式極端空洞,其實是最近幾個星期之間偶遇奧菲莉以及桑塔拉之後,才發現的(但是,我相信遇到的若是珂蘿艾或米歐蓮娜,結果也不會有太大不同)。當我一抵達和珂蘿艾相約吃晚餐的巴斯克風味餐廳,就預感會度過糟糕的一晚。儘管我幾乎獨自灌下兩瓶伊盧雷基白酒,依然覺得要維持勉強熱情的交談難度愈來愈高、甚至很快就到達難以克服的程度。不知道為什麼,我立刻覺得談及我們的過往回憶是不得體、甚至難以想像的。至於目前呢,珂蘿艾很顯然並沒有成功地邁入婚姻階段,露水姻緣的關係讓她愈來愈厭惡,總而言之,她的感情生活無可救藥地全盤覆滅。言談之中,我側面猜到她曾一度試著穩定下來,卻沒成功,創傷一直無法復原。她談及男同事時充滿尖酸苦澀(實在找不到話題,只好聊工作──她在波爾多酒商公會擔任公關,經常出差,尤其得去亞洲進行法國名酒促銷),顯示她吃了不少苦頭。下計程車時,我很驚訝她邀我「再續最後一杯」,我心想,這女的真是走投無路了。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已知道今晚什麼都不會發生,我甚至不想看到她的裸體,寧可避開這一幕,但這一幕還是出現了,也證實了我的預感:她不只在感情層面吃了苦頭,身體也遭受了無法彌補的毀損,胸部和屁股只剩下貧瘠的表面,縮小了、鬆垮了、下垂了,她已經不是且再也不會被視為慾望對象了。
和桑塔拉的共餐也是差不多的模式,只有些微差距(這次是海鮮餐廳、她的工作是跨國藥廠管理階層祕書),結果也和上次大同小異。只不過桑塔拉比珂蘿艾豐滿,也比較能聊,無依無靠的感覺沒那麼強烈。她非常悲傷,沒救了,我知道她最後還是會全盤說出,就和珂蘿艾一樣,她也是一隻「羽毛沾上瀝青的鳥」,但──按照我的形容──她鼓動翅膀的能力比較大。一、兩年之後,她會把所有結婚的企圖擺到一邊,氣數未盡的性期待會讓她極力尋找年輕男伴,這在我年輕時期稱為「如狼似虎」,最多持續十來年,之後就是肉體日漸成為瑕疵貨品,導致最後無法挽回的結果。
二十歲的時候,我可以在任何刺激下勃起,或是沒來由就勃起,有點無謂,那時候的我很可能樂於這種關係,總之比上家教課來得滿足且好玩。我想那時候的我應該可以勝任愉快,當然,現在是不可能了,勃起次數愈來愈少、愈來愈難,對象必須是一具緊實、柔軟、零瑕疵的軀體。
至於我自己的性生活呢,第一年當上巴黎索邦三大講師時,還沒有多大差別。持續一年接一年和系上女學生上床──其實對她們來說,我的老師身分並沒有改變什麼情況。一開始,我和女學生之間年紀的差異並不構成問題,而是漸漸產生了一種禁忌,原因來自我大學講師的身分,而非是我的年齡或是外表大她們很多。總之,我占盡男人在性感層面變老非常緩慢的好處,相對的,女人老化經常令人訝異地快速,幾年、甚至幾個月之間就全都垮了。和學生時代相比,真正的差異在於,現在每年開學斷了舊情的,是我。這完全不是出於嘗鮮的唐璜心態,也不是想花心縱慾。我和同事史蒂夫相反──他和我一起負責大一、大二的十九世紀法國文學課程,我並不會一開學就貪婪猴急地檢驗大一的「最新到貨」。他的運動衫、Converse球鞋、有點加州氣息的調調,每次都讓我想到電影《瘋狂假期》(Les Bronzés)裡,男主角蒂埃里.萊爾米特面對每週度假俱樂部的成員抵達時,走出小屋接待的那個樣子。我斷掉和這些年輕女孩的關係,毋寧是出於沮喪、厭倦:我不覺得自己的狀態能夠真正維持一段戀情,而且我想避免所有的失望、所有的幻滅。我都是在學年中改換女友,起因都是外在、無足輕重的原因──通常是一條短裙。
之後,連這個也中斷了。我和梅莉安九月分手,現在已是四月中,學年都快結束了,我都還沒換新女友。我被任命為教授,學術生涯可說達到了某種圓滿終點,但我認為這兩者之間並沒有真正的關聯。和梅莉安分手後不久,我就遇見奧菲莉,然後是桑塔拉,這之中產生了一種令人困惑、不安、不舒服的連結。經過一段時日的思考之後,我必須承認:我和那些前女友之間的關係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親近,沒有長相廝守遠景的那些短期性關係,最後卻讓我們產生了近似於幻滅的感受。和她們不同的,是我不能和任何人坦白談心,因為男性社交的談話並不容許談論私人感情生活:他們談的是政治、文學、財經、體育,符合他們的天性;至於感情生活,他們至死都不會透露。
我是老了,進入了所謂男性更年期了嗎?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我決定弄清楚,每晚掛在You-porn上,這個時有經年的網站已經成為色情網站的龍頭。一開始進入遊戲,結果立刻讓我心安。You-porn提供全球各地正常普通男性的性幻想,從進入網站第一分鐘起,我就確定自己是個絕對正常普通的男性。這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確定,我花了生命中一大部分時間研讀一個經常被視為「頹廢派」的作家,性在他的著作裡並不是一個清晰的議題。出了網站,我因獲得證實而心中平靜。這些影片有的品質極佳(洛杉磯劇務組拍攝的,有工作小組、燈光師、攝影棚布景工、攝影師),有的粗糙復古(德國業餘三流片),大抵不出幾個如出一轍但令人愉悅的情節。最常見的一個情節就是,一個男人(年輕男子?老頭子?兩種版本都有)笨兮兮地讓陽具在內褲或短褲裡沉睡。兩個種族隨著版本而變的年輕女人察覺了這不恰當的情況,立刻不停地把該器官從臨時庇護處裡端請出來。她們百般媚態挑逗讓他興奮起來,這一切都在女性的同謀友好的氣氛下進行。陽具輪流在兩張嘴裡進出,舌頭像燕子有點狂亂的交叉飛舞,那些在塞納河─馬恩河地區南邊劃過陰沉的天際,準備離開歐洲過冬的燕子。那個男的欲仙欲死,只能吐出幾個薄弱的單字;在表達這種情境上,法語尤其薄弱得可憐(「喔!媽的!」「喔媽的我射了!」差不多就是這個僵硬民族能說的了);美國人詞彙就比較華麗比較強烈(「喔我的上帝啊!」「喔耶穌基督!」),這些詞彙似乎表達了不該忘記上帝的眷寵(不管是口交或是烤雞),不論如何,在iMac二十七吋螢幕前的我勃起了,因此一切都會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