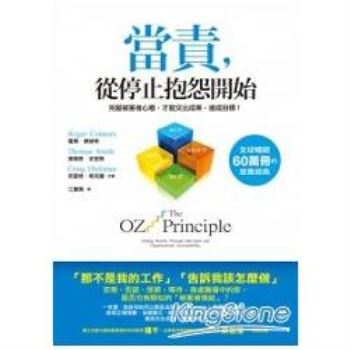*卸責的六個階段、當責的四個步驟*
以下從卸責邁向當責的過程,能幫助你看見水平線下的受害者情結,以及水平線上的當責態度之間有何不同。
【水平線下的被害者循環】陷入怪罪遊戲(blame game)的被害者循環(victim cycle)六階段
▲階段一:忽視或否認▲
落入被害循環的典型起點,通常是忽視或否認,也就是人們假裝不知道發生了問題,對影響到他們的問題渾然不知,或選擇完全否認問題的存在。
被害者循環的這個「忽視或否認」的階段算是一種挑戰,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說:「問題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事實並非如此。」假裝不知道或忽視問題,只會讓你落入水平線下,並且減低交出成果的能力。
▲階段二:那不是我的工作▲
捫心自問,我們自己曾說過多少次「那不是我的工作」?這個經常被提起的藉口是個老掉牙的慣用語,做為不採取行動的煙霧彈,或轉移別人的譴責,並且逃避責任。
在這個階段,人們其實明白該做些什麼事,才能取得成果,但同時也明顯欠缺足夠的責任感或參與的欲望。採取這種被害者態度的人們,認為自己將會徒勞無功,個人的犧牲毫無益處,這種思維就是自己的避難所。
「那不是我的工作」是一種永無止境的循環,成為普遍的藉口,意指「別怪我,那不是我的錯。」
▲階段三:怪罪他人▲
這是人們的拿手好戲,十根手指頭全都指向別人,沒有一根指向自己。
不好的結果發生時,自己不願負起責任,卻將歸罪到別人身上;「別怪我」成為避責的口頭禪。把問題丟來丟去、責怪他人,卻無法解決問題。
▲階段四:茫然困惑╱告訴我該怎麼辦▲
被害者循環的這個階段比較微妙,人們用茫然無知來做為推卸責任的藉口。假如他們不了解問題或狀況,當然不能期待他們有何作為。
在經過怪罪與困惑的階段之後,自然會產生這樣的反應:「告訴我你究竟要我做什麼,我照做就是了。」
然而,當員工的責任感加深,組織內的人走到水平線上,公司文化才能從「告訴我該怎麼辦?」轉移到「我打算這麼辦,你看如何?」。
▲階段五:藏住你的狐狸尾巴▲
在這個階段,人們繼續在想像中保護自己。例如:編造故事、虛構情節,萬一出問題時可以除罪卸責。
人們會用幾個方式想辦法藏住「狐狸尾巴」——從書面記錄每一件事,到儲存電子郵件,方便稍後證實自己一清二白。有時候,這種行為無疑有其正當性,例如,你會有些必須保護自己免於受到小人誣陷的時刻,這甚至似乎是必要的行為。但是,無論正當與否,藏住狐狸尾巴的行為對所有相關人等而言,都是浪費時間與資源的舉動。
▲階段六:等等看▲
剛開始,人們暫時留在被害者循環的泥淖之中,等等看情況能不能自行改善。但是在這種氣氛之下,問題只會變得更糟。
即使經過討論的方案,然而大家心存猶豫、決定要等等看,等到大家的情緒都冷靜下來之後,再看看會不會有正確的方案「自動」誕生。
「等等看」,只會成為解決方案的墳墓——因為,一切可能的解決方案,都會遭到怠惰無為的黑洞吞噬。
如果想要脫離被害者循環,你就必須走上當責步驟(steps to accountability),採取正視現實、承擔責任、解決問題、著手完成的態度,才能自我提升到水平線上。這四個步驟其實只是常識,然而,這些相當有道理的常識,終將成為使人們踏入水平線上的主要力量。
【水平線上的當責步驟】?茲法則(Oz Principle)的四個當責步驟(steps to accountability )
▲步驟一:正視現實(See It)▲
認識及承認現實的情況。你會看到,這一步十分困難,因為大多數人很難誠實地自我評價,並承認自己可以為績效付出更多。
▲步驟二:承擔責任(Own It)▲
為你和他人所創造出來的經驗和事實負責。這一步,讓你踏上行動之路。
▲步驟三:解決問題(Solve It)▲
以發現或實現未曾想過的解決方法來改變現狀,當障礙出現時,避免落入水平線下的陷阱。
▲步驟四:著手完成(Do It)▲
做出承諾,鼓起勇氣,去完成你所認定的解決方式,即使這些解決方式非常危險。
*當責的轉化力量*
一九六七年,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杜拉克談高效能的五個習慣》(The Effective Executive)(編按:繁體中文版由遠流出版)一書中,提出一個問題,只要人們不斷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協助引導任何地方的領導者和員工為他們的組織帶來成功:
我要做出什麼貢獻,才能夠大幅影響到我所服務的組織的績效與成果?
四十多年之後,終於,大多數執行長和企業領導者都已經認清創造組織文化的需求,而這個文化就是要創造出強烈的個人責任感,讓他們不斷自問並實踐杜拉克的問題。
吉姆.柯林斯在暢銷書《從A到A+》(Good to Great)中,如此形容卓越的工作環境:
「當你將有紀律的文化和企業倫理結合,就可以得到獲取成果的神奇煉金術。」
我們同意,全心全意地同意,但我們會說,有紀律的文化和企業倫理本身就是一種成果,來自於員工與團隊都能夠隨時自問這個奧茲法則提出的問題:
我還能做些什麼,才能夠在水平線上運作,以取得成果?
人們這麼做的時候,他們就學會了一個祕密,讓他們能夠用更快而且用成本更低的方法取得較佳成果。比起十年前,這點在今日的企業環境裡更是重要。因為績效與期待的門檻逐步升高,要清除這個門檻所需花費的功夫自然也是如此。
這句話值得再說一次—這種負責任的態度,是改善品質、滿足客戶、授權、建立團隊、增強效率、達成目標等努力項目的核心。
看起來簡單嗎?答案既肯定又否定。它是個簡單的訊息,卻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勇氣,才能使得責任感成為組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你所處的是自己初創的小型企業,還是《財星》五百大(Fortune 500)的管理階層,假如你採取的是逃避的態度,就無法開創更美好的未來。除非你開始花時間,找到讓自己爬到水平線上的勇氣。
陷入被害者循環
第二天早晨,是個陰天,但他們依然啟程,猶如確知自己前進的方向。「如果我們走得夠遠,」桃樂絲說,「相信總能到個什麼地方。」
但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除了深紅色的農田,什麼也沒看見。
稻草人開始嘀咕起來:「一定是迷路了。我們非得趕快找到往翡翠城(Emerald City)的路,否則我就找不到我的腦袋了。」
「我也會找不到我的心,」錫樵夫(Tin Woodsman)說:「我真是等不及要到奧茲國,你得承認這真是一趟漫長的旅程。」
「你知道嗎?」膽小獅(Cowardly Lion)啜泣著說:「我沒有勇氣漫無目的一路走下去。」
然後,桃樂絲也亂了分寸。她坐在草地上,望著同伴,而同伴也坐下來瞧著她。桃樂絲的愛犬托托(Toto)發現,有生以來,他第一次累到懶得去追逐飛過頭頂的蝴蝶,他吐著舌頭、大口喘著氣,望著桃樂絲,好像在問:「我們該怎麼辦?」 —《綠野仙蹤》法蘭克.包姆
*被害感與責任感之間的分界線*
想像責任感和被害感之間的一條線,這條線分隔了二種行為方式的你,其中一種能夠不受環境限制達到成果,另一種則會陷入讓你進退不得的被害者循環裡。個人或組織都無法停駐在這條線上,因為各項事件本身就會殘酷地將他們推到水平線下。當人們和組織在許多情況中能夠展現出當責力,而卻在其他處境下做出被害者的行為,那麼就會有些議題和情境會影響到他們,讓他們決定採取水平線上或水平線下的觀點來思考或行動。
如何辨識自己何時落在水平線下?
你一旦陷入被害者循環,便無法脫身而出,除非你承認自己正處於水平線下,而且已經付出代價。你在承認之後,才會正視它,也才能給你站到水平線上所需的視野。通常,你不容易克服被害者循環中的慣性,你需要一個客觀的人給你意見,例如朋友、配偶、或是奇異的案例中,費城那個壓縮機壞了的顧客。無論如何,留意如下的警訊,便能夠大大提升你辨別自己是否陷入被害者循環的能力。
【當責祕技】落入水平線下被害者循環的十八個警訊
‧ 你感到自己為際遇所困。
‧ 你覺得無法控制現況。
‧ 當別人直接或間接告訴你,你可以更努力完成更出色的結果時,卻是一場忠言逆耳。
‧ 你發覺自己在怪罪他人。
‧ 你討論問題時,愈來愈集中在自己做不到的事,而非自己能做的事。
‧ 你無法面對最艱難的議題。
‧ 你發現自己成為某些人取暖的對象,這些人告訴你,別人這回又如何對他不仁不義。
‧ 你發現自己不願提出深入的問題,好了解自己是否有能力當責。
‧ 你認為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感到無能為力。
‧ 你不斷發現自己採取防禦的姿態。
‧ 你花許多時間談論自己無法改變的事(例如:老闆、股東、景氣或政府法規)。
‧ 你覺得自己茫然失措,也拿它來做為沒能採取行動的藉口。
‧ 凡是要求你交代自己職責的人、會議或處境,你都加以迴避。
‧ 你發現自己說:
「那不是我的工作。」
「我無能為力。」
「該有人告訴他。」
「我們只能等著瞧。」
「告訴我該怎麼做。」
「如果是我,我會做的不一樣」
‧ 你常浪費時間精力批評老闆或同事。
‧ 你發現自己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只為編織一個牽強的故事,好證明自己沒有錯。
‧ 你不斷重複訴說著老掉牙的故事,說整個世界對不起你,又說別人如何占你便宜。
‧ 你對世界感到悲觀。
【案例】攸關人命卻遲未裝設的紅綠燈
地方政府在決定何時該裝設紅綠燈與暫停標誌時,其決定方式總是讓我們覺得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我們還記得在南加州有個非常危險的十字路口,視線極端不良,行車速度又快。交通官員卻遲遲不願在這個路口裝設紅綠燈,因為他們追蹤的不是人們對該路口安全問題的抱怨,而是留意車禍發生的數字。在小型車禍發生達到某一個數目時,就裝個暫停標誌意思一下。假如發生幾件重大車禍,無疑地,就會裝設紅綠燈。至於那個十字路口,則因為發生過許多車禍和幾次重大事故,因此現在已經從四向的暫停標誌換成了紅綠燈。
這真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必須用到疼痛、痛苦、傷害、甚至生命,才能得到合宜的結果。因此我們非常不喜歡反應式,而非主動積極的當責觀點。在事情發生之後,才來調整行為,避免接下來的負面後果,都已經太遲了。
無論有心或是無意,通俗心理學(pop psychology)總是鼓勵現代社會的人們,將自己所有的苦難與問題歸咎生命中的一個或幾個經驗,促成人們對眼前與未來的行為態度及感受,抱持著不需要負責的態度。人們遭遇到惡夢連連、飲食不正常、潔癖、焦慮、自我改善的衝動,身體的疾病,財務問題,以及對他人的不耐煩等問題時,往往會從自己早年發生的某個問題或經驗去尋找原因,這樣的作風已經可以說是稀鬆平常。將一切怪罪到自己過去的身體、情緒或心理上的創傷,藉以解釋自己無法控制飲食,和子女的關係拙劣,感覺孤立或寂寞,彷彿其他現代成人都未曾有過類似問題。
然而,真相是無論你是個真正的被害者,或是偽裝的犧牲者,你都一樣不可能克服過去所受的創傷,除非你能夠為自己的現在與未來當責,讓自己能夠從生命中得到更多收穫。要改變自己對當責的看法,就得從一個比較完善而主動的定義開始。
*共同當責*
奧茲法則對當責的定義有個重要的層面,也就是大家一同分享環境與成果之時,當責的效果最好。當責的舊有定義會讓人們去各自分配「個人責任」,而不承認共有責任。然而,事實上,後者往往都是組織行為與現代生活的寫照。當單一個人必須為某些惡果負責,其他的人都會鬆一口氣,這件事情終於和自己「沒有瓜葛、完成切割」。
將責任歸屬推到一個人身上,這可以讓其他人覺得好過些,但是事實依然存在,組織的成果都是來自集體而非個人的活動。因此,當組織表現不佳,這是集體或共同分擔的失敗。對組織內的責任要有完整的認識,就必須先接受「共同當責」的概念。例如,想像有支棒球隊,每一位防守的球員都必須負責照顧一塊場地。沒有清清楚楚的界線來畫分每一個人的區域。有了這樣一些重合的責任地帶,取得佳績(即防守整個球場)就成為團隊努力的目標,其間個人的責任會根據環境改變而有所異動,球員所受的訓練就是要去接球,只要他們接得到,無論有幾個人在球的附近,自己依然義無反顧。
比方說,或許你會看到球被打到左外野偏中間的場地。頃刻之間,游擊手、左外野手與中間手同時跑來接球,沒有人完全知道誰該來接。有時漏接了,因為球員遇到對方時,彼此都以為那是對方的球,大家都等著別人接球—這時,就不確定該由誰來負責。組織內的遊戲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場「團隊球賽」—每一個人各司其職,每一個人對最後的分數都有貢獻,而共同當責就主導著整場比賽。
【案例】每個人都舉手說:「讓我來!」
有家公司的總裁,說明對他而言共同當責的意義:
「大家同心協力避免漏接;不過,一旦漏接,每一個人都衝向前去撿球。」
他接著說:「不幸地,當人們看到球在二位球員之間落地,有太多人的反應只是說:『那是你的球。』」
在大多數組織中,我們很容易看到一連串成效不良的計畫,有的是人們錯過重要期限,有的是造成意想不到的花費,還有中途放棄,或是未曾留意重要細節。在這些情況發生時,沒有人會跳出來把球撿起來。每一個人都是坐在場邊說:「唉,這回他(她)真的搞砸了。」
這家公司的總裁形容他的員工過去都是如何思考品質。
「我們問到誰該來為品質當責?」他說,得到的答案竟是:「有一個人會舉起手來,其他的每個人都會指著他。」
然後,他形容他們在了解了共同當責之後,大家的思考方式產生了什麼改變。
「今天,我們問到誰是品質的主人時,所有的手都會舉起來。」
以下從卸責邁向當責的過程,能幫助你看見水平線下的受害者情結,以及水平線上的當責態度之間有何不同。
【水平線下的被害者循環】陷入怪罪遊戲(blame game)的被害者循環(victim cycle)六階段
▲階段一:忽視或否認▲
落入被害循環的典型起點,通常是忽視或否認,也就是人們假裝不知道發生了問題,對影響到他們的問題渾然不知,或選擇完全否認問題的存在。
被害者循環的這個「忽視或否認」的階段算是一種挑戰,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說:「問題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事實並非如此。」假裝不知道或忽視問題,只會讓你落入水平線下,並且減低交出成果的能力。
▲階段二:那不是我的工作▲
捫心自問,我們自己曾說過多少次「那不是我的工作」?這個經常被提起的藉口是個老掉牙的慣用語,做為不採取行動的煙霧彈,或轉移別人的譴責,並且逃避責任。
在這個階段,人們其實明白該做些什麼事,才能取得成果,但同時也明顯欠缺足夠的責任感或參與的欲望。採取這種被害者態度的人們,認為自己將會徒勞無功,個人的犧牲毫無益處,這種思維就是自己的避難所。
「那不是我的工作」是一種永無止境的循環,成為普遍的藉口,意指「別怪我,那不是我的錯。」
▲階段三:怪罪他人▲
這是人們的拿手好戲,十根手指頭全都指向別人,沒有一根指向自己。
不好的結果發生時,自己不願負起責任,卻將歸罪到別人身上;「別怪我」成為避責的口頭禪。把問題丟來丟去、責怪他人,卻無法解決問題。
▲階段四:茫然困惑╱告訴我該怎麼辦▲
被害者循環的這個階段比較微妙,人們用茫然無知來做為推卸責任的藉口。假如他們不了解問題或狀況,當然不能期待他們有何作為。
在經過怪罪與困惑的階段之後,自然會產生這樣的反應:「告訴我你究竟要我做什麼,我照做就是了。」
然而,當員工的責任感加深,組織內的人走到水平線上,公司文化才能從「告訴我該怎麼辦?」轉移到「我打算這麼辦,你看如何?」。
▲階段五:藏住你的狐狸尾巴▲
在這個階段,人們繼續在想像中保護自己。例如:編造故事、虛構情節,萬一出問題時可以除罪卸責。
人們會用幾個方式想辦法藏住「狐狸尾巴」——從書面記錄每一件事,到儲存電子郵件,方便稍後證實自己一清二白。有時候,這種行為無疑有其正當性,例如,你會有些必須保護自己免於受到小人誣陷的時刻,這甚至似乎是必要的行為。但是,無論正當與否,藏住狐狸尾巴的行為對所有相關人等而言,都是浪費時間與資源的舉動。
▲階段六:等等看▲
剛開始,人們暫時留在被害者循環的泥淖之中,等等看情況能不能自行改善。但是在這種氣氛之下,問題只會變得更糟。
即使經過討論的方案,然而大家心存猶豫、決定要等等看,等到大家的情緒都冷靜下來之後,再看看會不會有正確的方案「自動」誕生。
「等等看」,只會成為解決方案的墳墓——因為,一切可能的解決方案,都會遭到怠惰無為的黑洞吞噬。
如果想要脫離被害者循環,你就必須走上當責步驟(steps to accountability),採取正視現實、承擔責任、解決問題、著手完成的態度,才能自我提升到水平線上。這四個步驟其實只是常識,然而,這些相當有道理的常識,終將成為使人們踏入水平線上的主要力量。
【水平線上的當責步驟】?茲法則(Oz Principle)的四個當責步驟(steps to accountability )
▲步驟一:正視現實(See It)▲
認識及承認現實的情況。你會看到,這一步十分困難,因為大多數人很難誠實地自我評價,並承認自己可以為績效付出更多。
▲步驟二:承擔責任(Own It)▲
為你和他人所創造出來的經驗和事實負責。這一步,讓你踏上行動之路。
▲步驟三:解決問題(Solve It)▲
以發現或實現未曾想過的解決方法來改變現狀,當障礙出現時,避免落入水平線下的陷阱。
▲步驟四:著手完成(Do It)▲
做出承諾,鼓起勇氣,去完成你所認定的解決方式,即使這些解決方式非常危險。
*當責的轉化力量*
一九六七年,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杜拉克談高效能的五個習慣》(The Effective Executive)(編按:繁體中文版由遠流出版)一書中,提出一個問題,只要人們不斷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協助引導任何地方的領導者和員工為他們的組織帶來成功:
我要做出什麼貢獻,才能夠大幅影響到我所服務的組織的績效與成果?
四十多年之後,終於,大多數執行長和企業領導者都已經認清創造組織文化的需求,而這個文化就是要創造出強烈的個人責任感,讓他們不斷自問並實踐杜拉克的問題。
吉姆.柯林斯在暢銷書《從A到A+》(Good to Great)中,如此形容卓越的工作環境:
「當你將有紀律的文化和企業倫理結合,就可以得到獲取成果的神奇煉金術。」
我們同意,全心全意地同意,但我們會說,有紀律的文化和企業倫理本身就是一種成果,來自於員工與團隊都能夠隨時自問這個奧茲法則提出的問題:
我還能做些什麼,才能夠在水平線上運作,以取得成果?
人們這麼做的時候,他們就學會了一個祕密,讓他們能夠用更快而且用成本更低的方法取得較佳成果。比起十年前,這點在今日的企業環境裡更是重要。因為績效與期待的門檻逐步升高,要清除這個門檻所需花費的功夫自然也是如此。
這句話值得再說一次—這種負責任的態度,是改善品質、滿足客戶、授權、建立團隊、增強效率、達成目標等努力項目的核心。
看起來簡單嗎?答案既肯定又否定。它是個簡單的訊息,卻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勇氣,才能使得責任感成為組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你所處的是自己初創的小型企業,還是《財星》五百大(Fortune 500)的管理階層,假如你採取的是逃避的態度,就無法開創更美好的未來。除非你開始花時間,找到讓自己爬到水平線上的勇氣。
陷入被害者循環
第二天早晨,是個陰天,但他們依然啟程,猶如確知自己前進的方向。「如果我們走得夠遠,」桃樂絲說,「相信總能到個什麼地方。」
但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除了深紅色的農田,什麼也沒看見。
稻草人開始嘀咕起來:「一定是迷路了。我們非得趕快找到往翡翠城(Emerald City)的路,否則我就找不到我的腦袋了。」
「我也會找不到我的心,」錫樵夫(Tin Woodsman)說:「我真是等不及要到奧茲國,你得承認這真是一趟漫長的旅程。」
「你知道嗎?」膽小獅(Cowardly Lion)啜泣著說:「我沒有勇氣漫無目的一路走下去。」
然後,桃樂絲也亂了分寸。她坐在草地上,望著同伴,而同伴也坐下來瞧著她。桃樂絲的愛犬托托(Toto)發現,有生以來,他第一次累到懶得去追逐飛過頭頂的蝴蝶,他吐著舌頭、大口喘著氣,望著桃樂絲,好像在問:「我們該怎麼辦?」 —《綠野仙蹤》法蘭克.包姆
*被害感與責任感之間的分界線*
想像責任感和被害感之間的一條線,這條線分隔了二種行為方式的你,其中一種能夠不受環境限制達到成果,另一種則會陷入讓你進退不得的被害者循環裡。個人或組織都無法停駐在這條線上,因為各項事件本身就會殘酷地將他們推到水平線下。當人們和組織在許多情況中能夠展現出當責力,而卻在其他處境下做出被害者的行為,那麼就會有些議題和情境會影響到他們,讓他們決定採取水平線上或水平線下的觀點來思考或行動。
如何辨識自己何時落在水平線下?
你一旦陷入被害者循環,便無法脫身而出,除非你承認自己正處於水平線下,而且已經付出代價。你在承認之後,才會正視它,也才能給你站到水平線上所需的視野。通常,你不容易克服被害者循環中的慣性,你需要一個客觀的人給你意見,例如朋友、配偶、或是奇異的案例中,費城那個壓縮機壞了的顧客。無論如何,留意如下的警訊,便能夠大大提升你辨別自己是否陷入被害者循環的能力。
【當責祕技】落入水平線下被害者循環的十八個警訊
‧ 你感到自己為際遇所困。
‧ 你覺得無法控制現況。
‧ 當別人直接或間接告訴你,你可以更努力完成更出色的結果時,卻是一場忠言逆耳。
‧ 你發覺自己在怪罪他人。
‧ 你討論問題時,愈來愈集中在自己做不到的事,而非自己能做的事。
‧ 你無法面對最艱難的議題。
‧ 你發現自己成為某些人取暖的對象,這些人告訴你,別人這回又如何對他不仁不義。
‧ 你發現自己不願提出深入的問題,好了解自己是否有能力當責。
‧ 你認為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感到無能為力。
‧ 你不斷發現自己採取防禦的姿態。
‧ 你花許多時間談論自己無法改變的事(例如:老闆、股東、景氣或政府法規)。
‧ 你覺得自己茫然失措,也拿它來做為沒能採取行動的藉口。
‧ 凡是要求你交代自己職責的人、會議或處境,你都加以迴避。
‧ 你發現自己說:
「那不是我的工作。」
「我無能為力。」
「該有人告訴他。」
「我們只能等著瞧。」
「告訴我該怎麼做。」
「如果是我,我會做的不一樣」
‧ 你常浪費時間精力批評老闆或同事。
‧ 你發現自己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只為編織一個牽強的故事,好證明自己沒有錯。
‧ 你不斷重複訴說著老掉牙的故事,說整個世界對不起你,又說別人如何占你便宜。
‧ 你對世界感到悲觀。
【案例】攸關人命卻遲未裝設的紅綠燈
地方政府在決定何時該裝設紅綠燈與暫停標誌時,其決定方式總是讓我們覺得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我們還記得在南加州有個非常危險的十字路口,視線極端不良,行車速度又快。交通官員卻遲遲不願在這個路口裝設紅綠燈,因為他們追蹤的不是人們對該路口安全問題的抱怨,而是留意車禍發生的數字。在小型車禍發生達到某一個數目時,就裝個暫停標誌意思一下。假如發生幾件重大車禍,無疑地,就會裝設紅綠燈。至於那個十字路口,則因為發生過許多車禍和幾次重大事故,因此現在已經從四向的暫停標誌換成了紅綠燈。
這真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必須用到疼痛、痛苦、傷害、甚至生命,才能得到合宜的結果。因此我們非常不喜歡反應式,而非主動積極的當責觀點。在事情發生之後,才來調整行為,避免接下來的負面後果,都已經太遲了。
無論有心或是無意,通俗心理學(pop psychology)總是鼓勵現代社會的人們,將自己所有的苦難與問題歸咎生命中的一個或幾個經驗,促成人們對眼前與未來的行為態度及感受,抱持著不需要負責的態度。人們遭遇到惡夢連連、飲食不正常、潔癖、焦慮、自我改善的衝動,身體的疾病,財務問題,以及對他人的不耐煩等問題時,往往會從自己早年發生的某個問題或經驗去尋找原因,這樣的作風已經可以說是稀鬆平常。將一切怪罪到自己過去的身體、情緒或心理上的創傷,藉以解釋自己無法控制飲食,和子女的關係拙劣,感覺孤立或寂寞,彷彿其他現代成人都未曾有過類似問題。
然而,真相是無論你是個真正的被害者,或是偽裝的犧牲者,你都一樣不可能克服過去所受的創傷,除非你能夠為自己的現在與未來當責,讓自己能夠從生命中得到更多收穫。要改變自己對當責的看法,就得從一個比較完善而主動的定義開始。
*共同當責*
奧茲法則對當責的定義有個重要的層面,也就是大家一同分享環境與成果之時,當責的效果最好。當責的舊有定義會讓人們去各自分配「個人責任」,而不承認共有責任。然而,事實上,後者往往都是組織行為與現代生活的寫照。當單一個人必須為某些惡果負責,其他的人都會鬆一口氣,這件事情終於和自己「沒有瓜葛、完成切割」。
將責任歸屬推到一個人身上,這可以讓其他人覺得好過些,但是事實依然存在,組織的成果都是來自集體而非個人的活動。因此,當組織表現不佳,這是集體或共同分擔的失敗。對組織內的責任要有完整的認識,就必須先接受「共同當責」的概念。例如,想像有支棒球隊,每一位防守的球員都必須負責照顧一塊場地。沒有清清楚楚的界線來畫分每一個人的區域。有了這樣一些重合的責任地帶,取得佳績(即防守整個球場)就成為團隊努力的目標,其間個人的責任會根據環境改變而有所異動,球員所受的訓練就是要去接球,只要他們接得到,無論有幾個人在球的附近,自己依然義無反顧。
比方說,或許你會看到球被打到左外野偏中間的場地。頃刻之間,游擊手、左外野手與中間手同時跑來接球,沒有人完全知道誰該來接。有時漏接了,因為球員遇到對方時,彼此都以為那是對方的球,大家都等著別人接球—這時,就不確定該由誰來負責。組織內的遊戲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場「團隊球賽」—每一個人各司其職,每一個人對最後的分數都有貢獻,而共同當責就主導著整場比賽。
【案例】每個人都舉手說:「讓我來!」
有家公司的總裁,說明對他而言共同當責的意義:
「大家同心協力避免漏接;不過,一旦漏接,每一個人都衝向前去撿球。」
他接著說:「不幸地,當人們看到球在二位球員之間落地,有太多人的反應只是說:『那是你的球。』」
在大多數組織中,我們很容易看到一連串成效不良的計畫,有的是人們錯過重要期限,有的是造成意想不到的花費,還有中途放棄,或是未曾留意重要細節。在這些情況發生時,沒有人會跳出來把球撿起來。每一個人都是坐在場邊說:「唉,這回他(她)真的搞砸了。」
這家公司的總裁形容他的員工過去都是如何思考品質。
「我們問到誰該來為品質當責?」他說,得到的答案竟是:「有一個人會舉起手來,其他的每個人都會指著他。」
然後,他形容他們在了解了共同當責之後,大家的思考方式產生了什麼改變。
「今天,我們問到誰是品質的主人時,所有的手都會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