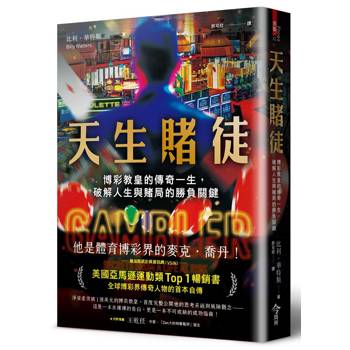第十二章 賭場大亨的旋轉輪盤
第一次遇到史提芬.永利是在一九八二年,我們剛搬到拉斯維加斯之後不久,當時我在金磚酒店玩撲克牌,這個有名的老闆走向我。
他問:「你為什麼不在這裡多玩一下?」
我已經準備好藉口了,他的牌室副理是我的好朋友鮑比。
「如果我在這裡贏了,鮑比可能會有點壓力。」我說。
說實在的,我不太想在金磚飯店賭博,除非玩撲克牌,因為二十一點的上限(每手一萬美元)比馬蹄鐵的上限(兩萬五千美元)低很多。馬蹄鐵還有一副牌的二十一點,金磚用六副牌。再者,馬蹄鐵的百家樂一般佣金比金磚低了百分之一。
因此,我客氣地回絕了永利。
這不是輕率之舉。每週我都有幾個晚上和永利玩牌,他是個活靶子,經常輸錢。只要鮑比還在那裡工作,我也希望和永利保持友好關係,更不用說永利就要成為拉斯維加斯先生,一個以記仇聞名的權貴人物。
永利在一九六七年,以二十五歲的年紀買下邊疆賭場飯店五%的股份,從而踏入大眾的視線。四年後,他借助他在酒類配銷業務的高知名度,以及和摩門教銀行(Mormon Bank)有不可思議的聯繫,成功獲得金磚飯店的控股權。兩年後,三十一歲的他成為最大股東。永利繼續打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度假酒店和賭場,包括夢幻度假村、金銀島酒店、貝拉吉奧飯店、拉斯維加斯永利酒店和澳門永利酒店等。
即使是賭場大亨最嚴厲的批評者(而且這種人絕對不少),也對他在地方和聯邦執法部門多次調查中,還能繼續經營業務表示出無奈的尊敬。多年來,永利被指控涉及諸多不法行為,包括性侵、猥褻、洗錢,以及縱容酒店內販賣毒品。他的運氣終於在二○一八年耗盡,當時他被控數十年來涉嫌多次不當性行為,因而被迫辭去了賭場公司職位。
但在他權利的巔峰時期,永利是個值得認識的好人,也是個不可觸犯的壞人,他是出了名的暴躁易怒,在商業上也是不留餘地。
我成功地透過一次的轉輪盤,讓他成為我的死敵。
賭城充斥著自稱可以百分之百打敗莊家的問題人物,輪盤、二十一點、花旗骰、老虎機、體育博彩──只要你說得出,總有一堆騙子準備好吹捧自己有可以戰勝賠率的革命性系統,有些是合法的,但大多數不是。
「就先借我錢吧,如果你贏了,我們平分利潤;如果輸了,嗯……」
有次,有對騙子向我推銷他們可以找出輪盤的某些偏差,從而精準預測那顆彈跳的球會落於何處。
「我們只需要你先出錢。」他們說。
「我不要。」我回答。
我跟奇普和道爾講這件事,他們差點笑翻。認真的賭徒會告訴你,輪盤是一個幾乎完全是坑的遊戲,在美國製造的輪盤上,除了十八個紅色和十八個黑字數字外,因為又加了綠色的零和雙零,讓中獎機會只有四七.三七%。(如果你對數學過敏,請跳過以下內容。)
讓我為你計算一下數字。美式輪盤的這種調整意味著你在一美元賭注的勝率為二.五六%,即三十八分之一,而賠率只有三十五比一,這使得莊家在每個賭注都擁有五.二六%的利潤率。在歐洲,輪盤只有一個零,勝率為二.七%。
我一邊叫騙子滾蛋,一邊好奇是不是有辦法找到一個讓玩家在輪盤中增加勝率的方法。作為一個凡事全力以赴的人,我花了四千美元自己買了一個美國製造的木質輪盤。
我在客廳將這個小寶貝一塊塊拆開,在它被分解、剝去浪漫魅力之後,我明白這個輪盤只是一堆零件組合在一起,就像洗衣機、攪拌機或割草機等其他機械設備,也會磨損。
例如,輪盤每次旋轉時,口袋之間「分隔板」的作用應該一致,如此才能產生完全隨機的數字結果。但如果木製輪盤已經有二十五年歷史,又沒有保養好呢?理論上,分隔板會鬆動,改變球移動的距離,輪盤軸和軸承如果隨時間磨損或鬆動,也可能產生潛在的偏差,導致軌道稍稍往某個方向傾斜,而使球較常落於輪盤的某個象限。
經過思考和操作後,我開始記錄金磚飯店幾個輪盤的結果,我的選擇不講科學,這幾個輪盤只是碰巧在我往金磚撲克桌的路線上,我晚上大多數時間都待在那裡。為了獲取我想要的數字,建立一個三千次轉盤結果的資料庫,我用時薪十二美元雇用一組人,在兩個金磚輪盤開放時,以一美元的最低下注額進行遊戲。後來,我們在其他地點也做了同樣的輪盤實驗。
收集資料後,我們將結果輸入一個特殊的軟體。我們發現金磚的輪盤和城裡其他地方的輪盤有些微偏差,但還不足以超越莊家的利潤率。
我繼續研究。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中,為大玩家將其中一個零指定為無投注號是很常見的,但這樣勝率仍有利於賭場。我心想,如果我找到一個輪盤的偏差足以帶來一○%的淨優勢,我就會抓住這個機會。
最後,我覺得我們已經在金磚的輪盤偏差累積到足夠的數據,我抓住了機會,而且是個重大的機會。我帶了四十五萬美元,開始依電腦分析的號碼下注:七、十、二十、二十七和三十六。
六個小時後,我只剩下五萬美元了,心裡想著:哎呀,你真是個白痴。在我還沒有勉強抽身或破產前,數字開始出現了。十二小時後,我賺了五萬美元,但我也懷疑這些壓力和汗水是否值得。
這一次,我拿著錢就離開了,但我知道自己還會再回到輪盤桌上。
快速提醒一句:在輪盤開始旋轉之前,我已經下注了。早在一九七○年代,拉斯維加斯就有玩家使用計時器或計算設備,根據輪盤開始旋轉時球落下的位置,計算出可能球落於哪個象限。玩家們戴著耳機,或將電子設備放在鞋子或靴子裡,好知道該怎麼下注。然而,如果玩家開始贏得大筆的金錢,賭場會直接要求他們在轉動輪盤之前下注,他們的優勢就消失了。這個策略只有在玩家能找到一個疏忽大意的賭場時才有效,無意冒犯。
碰巧,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在塔荷湖的凱撒皇宮酒店找到一個我能戰勝的輪盤。只有一個小問題:當時我正忙著在阿瑪里洛瘦子的超級盃撲克牌錦標賽中玩德州撲克,我手氣爆棚,打敗像道爾、奇普和羅德島布里斯托之光艾爾.傑伊.埃瑟爾(Al Jay Ethier)等人,贏得大賽,讓我的荷包裡多了一點小錢(十七萬五千美元)。在瘦子的錦標賽幾週後,我帶著幾個喜歡的數字飛回塔荷湖。
我就不該在那個輪盤上贏了凱撒兩百萬美元。我請凱撒酒店將錢匯到它在拉斯維加斯的姐妹酒店,後來我帶蘇珊和另一對夫妻去那裡吃飯,又不利用分析結果的玩了幾把輪盤遊戲,我又贏得了六十萬美元!
這不是什麼好事,原因有二。一、我本來想在那個輪盤上輸一點錢,好降低塔荷湖的熱度,我不想讓賭場知道我發現了輪盤偏差的事。第二個原因是電腦集團的調查正在進行中,國稅局的探員正在城裡四處尋查我的財務狀況,我沒有什麼要隱瞞的,但我之前見過他們的把戲──先沒收你的錢,之後再爭論。
我的國稅局朋友蜂湧而至,因為在肯塔基的非法博彩行動中,聯邦政府沒收了一九八二年一個NFL星期天早場比賽的半天賭博收入,經過一番數學計算,他們得出(錯誤的)結論,我欠下七百萬美元的未繳稅款、利息和罰款。胡說,但他們堅持要收錢,迫使我得努力爭取才能拿回點什麼。
有天早上,肯塔基案的主要探員跑來敲響拉斯維加斯鄉村俱樂部的前門,前面還停了一輛大型搬運卡車,這可不是什麼含蓄的暗示。我立刻認出了他,在應門前,我跑到後面,把我的三萬五千美元紙紗藏到泳池邊的水壺裡。
等我回來開門時,國稅局的人已經發火。
「如果你現在不付三萬美元,我們就要進去沒收屋內的每一件家具。」
我不想看到國稅局探員把我們的家具搬走,或是知道我有一大筆錢供他們質疑。所以我告訴他,我認識一個可以借錢給我的人。
「誰?」
「馬蹄鐵的傑克.比尼恩。」
「走吧。」
稅務探員和我一起開車去市區,找傑克進行一場臨時會議。
我向傑克介紹了探員。「他說如果我現在不給他三萬美元,他會把我們所有的家具都拿走。你有辦法借我這筆錢嗎?」
傑克享受著這種時刻,給了我一個那種眼神,然後吞吞吐吐地說:「比利,在你身邊,辦公室的日子永遠不會無聊。」
「好,比利,我想可以借你。」
我走到收納檯,簽了一張借據,然後給探員三萬美元現金。我們開車回到家,我沒有邀請他進來喝啤酒,所以他帶著一輛空蕩蕩的搬運車離開了。
問題解決了。我去了游泳池,把藏在罐子裡的三萬五千美元現金撈出來,蘇珊不得不把濕透的鈔票放入乾衣機中烘乾。順帶一提,這其實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親身洗錢的經驗。接下來的轉盤賭局,我轉戰大西洋城的金磚酒店,老闆是史提芬.永利,當時我們還是朋友。
那時候,永利和我是拉斯維加斯鄉村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好友。有次打球時,我們開始討論輪盤,然後談定一場比賽。基本規則如下:我可以在他的大西洋城賭場以每個號碼最高一千美元的賭注下注,作為交換,莊家會在輪盤上刪去一個零。為表誠意,我需要支付最低一百萬美元的保證金。
聽來值得一賭,所以我接受了,不過前提是我的人先找出有偏差的輪盤,我才覺得這對我有利。自信滿滿的我和蘇珊包了架里爾噴射機飛到太西洋城,金磚酒店派出豪華轎車到停機坪接我們,等我們抵達酒店時,又有兩位笑容可掬的酒店主管和一位賭場主人熱情迎接。將一百萬美元現金存入保險櫃後,我漫步到了我喜歡的輪盤旁。
我問荷官他打算封哪個零。
他回答:「做不到。」
我抱怨時,他叫來了值班主管,主管又叫來了賭場經理,賭場經理則叫來了賭場總裁丹尼爾.布恩.韋森(Daniel Boone Wayson)。
「抱歉,比利,西洋城禁止封零的行為。」布恩說。
「不可能,」我回答,「永利和我在拉斯維加斯談好了這場賭局,他擁有這個該死的地方,要是我得賭兩個零,再過一百年,我也不可能飛到大西洋城。」
布恩告訴我,永利可能不知道這條法律,但是他可以打電話給博奕委員會,看看能否例外。
他打了電話,沒得到特殊許可。
如果我在輪盤有兩個零贏了,這會引起懷疑,因為我擁有專業賭徒的背景和名聲。於是我走向酒吧,開始大量消耗他們的啤酒庫存,我成功喝醉,並在二十一點牌桌上輸掉整整一百萬美元。
隔天,蘇珊和我飛回賭城,我很氣自己,氣到說不出話。我們進門時,電話響了。猜猜是誰?
永利並不是為了輪盤的失誤而致電道歉,相反地,他邀請我去打高爾夫球。我接受了他的邀請,約定好兩天後開打。我們簡短地討論了大西洋城的事,我告訴永利我再也不去那裡玩了,因為我不會去玩有兩個零的輪盤。
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在金磚酒店玩牌時,永利邀請我們和他及他的妻子伊蓮一起,參加在長島舉行的美國高爾夫公開賽。
「我們會搭直升機去。」他說。
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史提芬,我不玩有兩個零的輪盤。」
「別擔心,」他說,「我想到辦法了,你每次都下相同的賭注,這樣很容易追蹤你每小時下注的金額,進而計算出莊家的百分比,我們只取一半,替代一個零,我會用拉斯維加斯金磚酒店的現金優惠券支付給你。」
有數學頭腦的賭徒們思維相似。
「那可以。」我說。
我們談定了一場新的賭局,這次我將投入兩百萬美元,每局在五個數字上下注兩千美元。
在大西洋城的金磚酒店裡,我找到我喜歡的那個輪盤,一遍又一遍下注在相同的五個紅色和黑色數字上──七、十、二十、二十七和三十六,直到凌晨四點賭場打烊為止。在輪盤最後一次轉動結束後,我贏了三百二十萬美元。
睡了幾個小時後,我回到賭場層,你知道嗎?那個輪盤還留在幾小時前我離開的地方,我繼續下注同一組號碼,並再次獲勝,這引起了不必要的注意。
我四處張望,每個賭區主管和樓層經理都在擔心我的玩法。四、五個小時過去了,我還在贏,此時一個生面孔坐到我身邊,開始找我說話。
你知道嗎?那是紐澤西博奕執法部門的成員,他對比爾.華特斯產生了濃厚興趣,正在尋找任何非法或不適當的行為。祝好運。
那傢伙就算用一把點四五手槍指著我的頭,我也無法告訴他輪盤到底哪裡有問題。無論問題是什麼──軸承、分隔板或其他部分,我只知道它存在偏差,而我找到自己想要下注的數字。我做的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
我在下午六點前又贏了六十萬美元,執法先生有了更多的同伴,一群身穿昂貴西裝、總是皺著眉頭的壯碩漢子。
是的,是時候滾出去了。
我去了收銀檯,取得了一張五百八十萬美元的支票,其中包含了我的兩百萬美元保證金。相信我,在不到四十小時內就輸了三百八十萬給他的高爾夫球好友,永利對此非常不爽。
有消息傳來,永利已經把輪盤交給製造商檢查是否有偏差,但他們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據說他後來又將輪盤送到能讓人登陸月球的太空總署科學家進行檢驗,他們將輪盤拆成碎片,仍然一無所獲。
與史提芬.永利的激烈仇怨自此開始,並且延續至今。這件事也代表真正的覺醒。在賭場都是會輸的,九八%的人在喝了一堆酒、對抗爛透的勝算時,下場都是輸,一切都有利於賭場的擁有者。但是投入數百個小時的時間和數千美元,挖掘出一個合法的數學優勢後,當權者就會非常憤怒。
舉例來說:永利毫不在意我上次去大西洋城玩二十一點輸了一百萬美元,也不在意我在金磚酒店玩百家樂和二十一點時輸了五十多萬。
但是當永利在輪盤輸錢給我時,就會覺得我好像走進他的豪宅,肘擊了他的畢卡索名畫。
在金磚酒店贏了三百八十萬美元後,我又在大西洋城和賭城的幾家賭場玩過幾次,但消息傳開後,賭場就不再讓我玩了。我轉為B計畫,邀請了一些合作夥伴一起玩我喜歡的輪盤。
第一次遇到史提芬.永利是在一九八二年,我們剛搬到拉斯維加斯之後不久,當時我在金磚酒店玩撲克牌,這個有名的老闆走向我。
他問:「你為什麼不在這裡多玩一下?」
我已經準備好藉口了,他的牌室副理是我的好朋友鮑比。
「如果我在這裡贏了,鮑比可能會有點壓力。」我說。
說實在的,我不太想在金磚飯店賭博,除非玩撲克牌,因為二十一點的上限(每手一萬美元)比馬蹄鐵的上限(兩萬五千美元)低很多。馬蹄鐵還有一副牌的二十一點,金磚用六副牌。再者,馬蹄鐵的百家樂一般佣金比金磚低了百分之一。
因此,我客氣地回絕了永利。
這不是輕率之舉。每週我都有幾個晚上和永利玩牌,他是個活靶子,經常輸錢。只要鮑比還在那裡工作,我也希望和永利保持友好關係,更不用說永利就要成為拉斯維加斯先生,一個以記仇聞名的權貴人物。
永利在一九六七年,以二十五歲的年紀買下邊疆賭場飯店五%的股份,從而踏入大眾的視線。四年後,他借助他在酒類配銷業務的高知名度,以及和摩門教銀行(Mormon Bank)有不可思議的聯繫,成功獲得金磚飯店的控股權。兩年後,三十一歲的他成為最大股東。永利繼續打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度假酒店和賭場,包括夢幻度假村、金銀島酒店、貝拉吉奧飯店、拉斯維加斯永利酒店和澳門永利酒店等。
即使是賭場大亨最嚴厲的批評者(而且這種人絕對不少),也對他在地方和聯邦執法部門多次調查中,還能繼續經營業務表示出無奈的尊敬。多年來,永利被指控涉及諸多不法行為,包括性侵、猥褻、洗錢,以及縱容酒店內販賣毒品。他的運氣終於在二○一八年耗盡,當時他被控數十年來涉嫌多次不當性行為,因而被迫辭去了賭場公司職位。
但在他權利的巔峰時期,永利是個值得認識的好人,也是個不可觸犯的壞人,他是出了名的暴躁易怒,在商業上也是不留餘地。
我成功地透過一次的轉輪盤,讓他成為我的死敵。
賭城充斥著自稱可以百分之百打敗莊家的問題人物,輪盤、二十一點、花旗骰、老虎機、體育博彩──只要你說得出,總有一堆騙子準備好吹捧自己有可以戰勝賠率的革命性系統,有些是合法的,但大多數不是。
「就先借我錢吧,如果你贏了,我們平分利潤;如果輸了,嗯……」
有次,有對騙子向我推銷他們可以找出輪盤的某些偏差,從而精準預測那顆彈跳的球會落於何處。
「我們只需要你先出錢。」他們說。
「我不要。」我回答。
我跟奇普和道爾講這件事,他們差點笑翻。認真的賭徒會告訴你,輪盤是一個幾乎完全是坑的遊戲,在美國製造的輪盤上,除了十八個紅色和十八個黑字數字外,因為又加了綠色的零和雙零,讓中獎機會只有四七.三七%。(如果你對數學過敏,請跳過以下內容。)
讓我為你計算一下數字。美式輪盤的這種調整意味著你在一美元賭注的勝率為二.五六%,即三十八分之一,而賠率只有三十五比一,這使得莊家在每個賭注都擁有五.二六%的利潤率。在歐洲,輪盤只有一個零,勝率為二.七%。
我一邊叫騙子滾蛋,一邊好奇是不是有辦法找到一個讓玩家在輪盤中增加勝率的方法。作為一個凡事全力以赴的人,我花了四千美元自己買了一個美國製造的木質輪盤。
我在客廳將這個小寶貝一塊塊拆開,在它被分解、剝去浪漫魅力之後,我明白這個輪盤只是一堆零件組合在一起,就像洗衣機、攪拌機或割草機等其他機械設備,也會磨損。
例如,輪盤每次旋轉時,口袋之間「分隔板」的作用應該一致,如此才能產生完全隨機的數字結果。但如果木製輪盤已經有二十五年歷史,又沒有保養好呢?理論上,分隔板會鬆動,改變球移動的距離,輪盤軸和軸承如果隨時間磨損或鬆動,也可能產生潛在的偏差,導致軌道稍稍往某個方向傾斜,而使球較常落於輪盤的某個象限。
經過思考和操作後,我開始記錄金磚飯店幾個輪盤的結果,我的選擇不講科學,這幾個輪盤只是碰巧在我往金磚撲克桌的路線上,我晚上大多數時間都待在那裡。為了獲取我想要的數字,建立一個三千次轉盤結果的資料庫,我用時薪十二美元雇用一組人,在兩個金磚輪盤開放時,以一美元的最低下注額進行遊戲。後來,我們在其他地點也做了同樣的輪盤實驗。
收集資料後,我們將結果輸入一個特殊的軟體。我們發現金磚的輪盤和城裡其他地方的輪盤有些微偏差,但還不足以超越莊家的利潤率。
我繼續研究。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中,為大玩家將其中一個零指定為無投注號是很常見的,但這樣勝率仍有利於賭場。我心想,如果我找到一個輪盤的偏差足以帶來一○%的淨優勢,我就會抓住這個機會。
最後,我覺得我們已經在金磚的輪盤偏差累積到足夠的數據,我抓住了機會,而且是個重大的機會。我帶了四十五萬美元,開始依電腦分析的號碼下注:七、十、二十、二十七和三十六。
六個小時後,我只剩下五萬美元了,心裡想著:哎呀,你真是個白痴。在我還沒有勉強抽身或破產前,數字開始出現了。十二小時後,我賺了五萬美元,但我也懷疑這些壓力和汗水是否值得。
這一次,我拿著錢就離開了,但我知道自己還會再回到輪盤桌上。
快速提醒一句:在輪盤開始旋轉之前,我已經下注了。早在一九七○年代,拉斯維加斯就有玩家使用計時器或計算設備,根據輪盤開始旋轉時球落下的位置,計算出可能球落於哪個象限。玩家們戴著耳機,或將電子設備放在鞋子或靴子裡,好知道該怎麼下注。然而,如果玩家開始贏得大筆的金錢,賭場會直接要求他們在轉動輪盤之前下注,他們的優勢就消失了。這個策略只有在玩家能找到一個疏忽大意的賭場時才有效,無意冒犯。
碰巧,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在塔荷湖的凱撒皇宮酒店找到一個我能戰勝的輪盤。只有一個小問題:當時我正忙著在阿瑪里洛瘦子的超級盃撲克牌錦標賽中玩德州撲克,我手氣爆棚,打敗像道爾、奇普和羅德島布里斯托之光艾爾.傑伊.埃瑟爾(Al Jay Ethier)等人,贏得大賽,讓我的荷包裡多了一點小錢(十七萬五千美元)。在瘦子的錦標賽幾週後,我帶著幾個喜歡的數字飛回塔荷湖。
我就不該在那個輪盤上贏了凱撒兩百萬美元。我請凱撒酒店將錢匯到它在拉斯維加斯的姐妹酒店,後來我帶蘇珊和另一對夫妻去那裡吃飯,又不利用分析結果的玩了幾把輪盤遊戲,我又贏得了六十萬美元!
這不是什麼好事,原因有二。一、我本來想在那個輪盤上輸一點錢,好降低塔荷湖的熱度,我不想讓賭場知道我發現了輪盤偏差的事。第二個原因是電腦集團的調查正在進行中,國稅局的探員正在城裡四處尋查我的財務狀況,我沒有什麼要隱瞞的,但我之前見過他們的把戲──先沒收你的錢,之後再爭論。
我的國稅局朋友蜂湧而至,因為在肯塔基的非法博彩行動中,聯邦政府沒收了一九八二年一個NFL星期天早場比賽的半天賭博收入,經過一番數學計算,他們得出(錯誤的)結論,我欠下七百萬美元的未繳稅款、利息和罰款。胡說,但他們堅持要收錢,迫使我得努力爭取才能拿回點什麼。
有天早上,肯塔基案的主要探員跑來敲響拉斯維加斯鄉村俱樂部的前門,前面還停了一輛大型搬運卡車,這可不是什麼含蓄的暗示。我立刻認出了他,在應門前,我跑到後面,把我的三萬五千美元紙紗藏到泳池邊的水壺裡。
等我回來開門時,國稅局的人已經發火。
「如果你現在不付三萬美元,我們就要進去沒收屋內的每一件家具。」
我不想看到國稅局探員把我們的家具搬走,或是知道我有一大筆錢供他們質疑。所以我告訴他,我認識一個可以借錢給我的人。
「誰?」
「馬蹄鐵的傑克.比尼恩。」
「走吧。」
稅務探員和我一起開車去市區,找傑克進行一場臨時會議。
我向傑克介紹了探員。「他說如果我現在不給他三萬美元,他會把我們所有的家具都拿走。你有辦法借我這筆錢嗎?」
傑克享受著這種時刻,給了我一個那種眼神,然後吞吞吐吐地說:「比利,在你身邊,辦公室的日子永遠不會無聊。」
「好,比利,我想可以借你。」
我走到收納檯,簽了一張借據,然後給探員三萬美元現金。我們開車回到家,我沒有邀請他進來喝啤酒,所以他帶著一輛空蕩蕩的搬運車離開了。
問題解決了。我去了游泳池,把藏在罐子裡的三萬五千美元現金撈出來,蘇珊不得不把濕透的鈔票放入乾衣機中烘乾。順帶一提,這其實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親身洗錢的經驗。接下來的轉盤賭局,我轉戰大西洋城的金磚酒店,老闆是史提芬.永利,當時我們還是朋友。
那時候,永利和我是拉斯維加斯鄉村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好友。有次打球時,我們開始討論輪盤,然後談定一場比賽。基本規則如下:我可以在他的大西洋城賭場以每個號碼最高一千美元的賭注下注,作為交換,莊家會在輪盤上刪去一個零。為表誠意,我需要支付最低一百萬美元的保證金。
聽來值得一賭,所以我接受了,不過前提是我的人先找出有偏差的輪盤,我才覺得這對我有利。自信滿滿的我和蘇珊包了架里爾噴射機飛到太西洋城,金磚酒店派出豪華轎車到停機坪接我們,等我們抵達酒店時,又有兩位笑容可掬的酒店主管和一位賭場主人熱情迎接。將一百萬美元現金存入保險櫃後,我漫步到了我喜歡的輪盤旁。
我問荷官他打算封哪個零。
他回答:「做不到。」
我抱怨時,他叫來了值班主管,主管又叫來了賭場經理,賭場經理則叫來了賭場總裁丹尼爾.布恩.韋森(Daniel Boone Wayson)。
「抱歉,比利,西洋城禁止封零的行為。」布恩說。
「不可能,」我回答,「永利和我在拉斯維加斯談好了這場賭局,他擁有這個該死的地方,要是我得賭兩個零,再過一百年,我也不可能飛到大西洋城。」
布恩告訴我,永利可能不知道這條法律,但是他可以打電話給博奕委員會,看看能否例外。
他打了電話,沒得到特殊許可。
如果我在輪盤有兩個零贏了,這會引起懷疑,因為我擁有專業賭徒的背景和名聲。於是我走向酒吧,開始大量消耗他們的啤酒庫存,我成功喝醉,並在二十一點牌桌上輸掉整整一百萬美元。
隔天,蘇珊和我飛回賭城,我很氣自己,氣到說不出話。我們進門時,電話響了。猜猜是誰?
永利並不是為了輪盤的失誤而致電道歉,相反地,他邀請我去打高爾夫球。我接受了他的邀請,約定好兩天後開打。我們簡短地討論了大西洋城的事,我告訴永利我再也不去那裡玩了,因為我不會去玩有兩個零的輪盤。
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在金磚酒店玩牌時,永利邀請我們和他及他的妻子伊蓮一起,參加在長島舉行的美國高爾夫公開賽。
「我們會搭直升機去。」他說。
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史提芬,我不玩有兩個零的輪盤。」
「別擔心,」他說,「我想到辦法了,你每次都下相同的賭注,這樣很容易追蹤你每小時下注的金額,進而計算出莊家的百分比,我們只取一半,替代一個零,我會用拉斯維加斯金磚酒店的現金優惠券支付給你。」
有數學頭腦的賭徒們思維相似。
「那可以。」我說。
我們談定了一場新的賭局,這次我將投入兩百萬美元,每局在五個數字上下注兩千美元。
在大西洋城的金磚酒店裡,我找到我喜歡的那個輪盤,一遍又一遍下注在相同的五個紅色和黑色數字上──七、十、二十、二十七和三十六,直到凌晨四點賭場打烊為止。在輪盤最後一次轉動結束後,我贏了三百二十萬美元。
睡了幾個小時後,我回到賭場層,你知道嗎?那個輪盤還留在幾小時前我離開的地方,我繼續下注同一組號碼,並再次獲勝,這引起了不必要的注意。
我四處張望,每個賭區主管和樓層經理都在擔心我的玩法。四、五個小時過去了,我還在贏,此時一個生面孔坐到我身邊,開始找我說話。
你知道嗎?那是紐澤西博奕執法部門的成員,他對比爾.華特斯產生了濃厚興趣,正在尋找任何非法或不適當的行為。祝好運。
那傢伙就算用一把點四五手槍指著我的頭,我也無法告訴他輪盤到底哪裡有問題。無論問題是什麼──軸承、分隔板或其他部分,我只知道它存在偏差,而我找到自己想要下注的數字。我做的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
我在下午六點前又贏了六十萬美元,執法先生有了更多的同伴,一群身穿昂貴西裝、總是皺著眉頭的壯碩漢子。
是的,是時候滾出去了。
我去了收銀檯,取得了一張五百八十萬美元的支票,其中包含了我的兩百萬美元保證金。相信我,在不到四十小時內就輸了三百八十萬給他的高爾夫球好友,永利對此非常不爽。
有消息傳來,永利已經把輪盤交給製造商檢查是否有偏差,但他們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據說他後來又將輪盤送到能讓人登陸月球的太空總署科學家進行檢驗,他們將輪盤拆成碎片,仍然一無所獲。
與史提芬.永利的激烈仇怨自此開始,並且延續至今。這件事也代表真正的覺醒。在賭場都是會輸的,九八%的人在喝了一堆酒、對抗爛透的勝算時,下場都是輸,一切都有利於賭場的擁有者。但是投入數百個小時的時間和數千美元,挖掘出一個合法的數學優勢後,當權者就會非常憤怒。
舉例來說:永利毫不在意我上次去大西洋城玩二十一點輸了一百萬美元,也不在意我在金磚酒店玩百家樂和二十一點時輸了五十多萬。
但是當永利在輪盤輸錢給我時,就會覺得我好像走進他的豪宅,肘擊了他的畢卡索名畫。
在金磚酒店贏了三百八十萬美元後,我又在大西洋城和賭城的幾家賭場玩過幾次,但消息傳開後,賭場就不再讓我玩了。我轉為B計畫,邀請了一些合作夥伴一起玩我喜歡的輪盤。